那些离开体制的年轻人
2018-09-03刘娉婷
刘娉婷
打印完需要应付第二天临时检查的材料,已是凌晨2点,整个办事大厅空荡荡地只剩王琪一个人,她要把将近1米高的材料从打印处一点点搬到办公室。回到住处后,王琪疲倦地躺在床上,双眼看着天花板,反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它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
这样的念头在为期两年的公务员生涯中时常出现在王琪的脑海里。2014年6月,本科毕业的她在父母的劝说下,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省党宣部,负责写一些宣传稿和政府文件。仅一年过去,“坚决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的声音几乎开始每天盘旋,甚至严重到她后期对待工作都产生了愤怒的负面情绪。“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真的要崩溃了。我不怕辛苦,但当时做的很多工作和加班都是为了应付检查,毫无意义。平时认真工作也不会被领导重视,后面愈发没有积极性,我不想变成发挥不出价值的人。”干满两年,她选择裸辞,离开了体制。
王琪是中国近5000万“体制人”中的一员,而体制在现实中就像一道高墙,将职场中的人区隔成体制内和体制外。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内”主要包括国家党政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体制内的组织架构是,从基层开始,每个人有明确的岗位分工,各司其职,员工的职位等级主要按照工作资历来评定,即论资排辈。
至今,王琪的父母还会因为惋惜她辞去工作而念叨几句。不难理解,在父母辈心中,体制几乎能够与一份理想职业画上等号。“大部分人选择体制内的原因都在于工作稳定、拥有可预见性的收入和福利保障,工作时长也相对固定,并且他们会拥有较好的社会地位,为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带来便利。”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李强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体制撑起了一道安全的屏障,意味着员工只需要完成本职工作,就能保障收入,且永远不会面临被辞退的风险。因此,进入体制就等同于拥有了一份“铁饭碗”,希望进入体制工作的人数还在逐年增加。根据国家公务员考试网公布的2018年国考人数显示,2018年报名过审人数达到165.97万人,较上一年增加了17.34万,创下近7年新高。
但近几年也有一部分和王琪一样的年轻人在尝试从体制内走出去。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更迭,他们的观念不断受到冲击。
这群年轻人拥有极为相似的背景和人物画像:他们中多数是为了顺从父母的意愿而踏入了体制这个舒适圈,却在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工作中,逐渐察觉到体制内的另一面,例如个人工作主观能动性的丧失、专业技能的退化、晋升通道的缓慢和沟通思维固化等问题,体制的光环在他们眼中黯淡下来,从而使他们下定决心离开体制。
脱离了刻板的层级制度和一成不变的工作环境后,跳槽进入市场化企业赋予了他们更多上升的空间和择业机会,但同时他们也需要面对和适应与体制内截然不同的一套职场规则,不断完善自身的职业竞争力。几位离开体制的年轻人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在他们的勇敢背后,有努力,也有迷茫。
A为什么我必须要离开?
2017年10月,在河北一家电视台工作了一年的张茜霖觉得有点儿不认识自己了。
她本科学习的是英语,毕业后,她没有像同专业其他同学一样去任教或从事翻译工作,而是听从父母的安排,考入了老家当地的电视台,担任新闻播音员。在父母眼里,“这份工作十分体面”。她也收到过来自北京一所语言培训机构的offer,但被父母阻拦了—在择业这件事上,过去的她几乎没有为自己争取过。
不过这并不代表她对体制毫无怨言,事实上从一开始她就有点排斥,甚至,在进入体制前,她“就知道自己在那里待不长”,因此她也表现得没什么“上进心”,只是觉得“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完,没有想过再往上走。”
而正式开始工作以后,实际的工作常态加速了她想要放弃的想法。每天上午9点,她听着新闻节目走进电视台,然后便开始坐在工位上发呆,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周围同事闲聊家长里短的声音使她烦躁不安。一直等到下午或者傍晚拿到记者发来的稿件,她才换上正装、化好妆容、戴上一顶栗色短发造型的假发,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播音间内,开始当天的工作,而通常她播完所有的新闻只需要半小时。

用張茜霖的话来形容,这是一份“动动嘴皮、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能完成的事,且可能要过20年才能转岗。”英语专业毕业的她,这一年中除了要面对自己在职业技能上没有任何提升的“痛苦现实”,最令她无法忍受的,还有漫无止境、虚度光阴的等待。“体制内的人都过得特别有恃无恐,即使工作做得不好也不会失业,但我不希望刚毕业就学会了推卸责任、放弃积极和努力的斗志,我很害怕被这个环境改变。”
职责明确使得体制内的很多工作都无法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也使得很多对自身有要求的年轻人,无法在岗位上体现自己的创造力,并因此丧失了成就感,自我驱动力也随之降低。
“体制内的工作就是要做专。”李强用在工商局办证的岗位来打比方,“这样的工作无法再往外延展到更多的边界,体制内也不会支持这样的情况发生。”
一次春节的高中同学聚会,触发王琪开始反思体制内工作的意义,并让她产生强烈的危机感。
因为受到体制内工作的父母影响,王琪一开始对体制内的工作并没有十分排斥,还在入职前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明确体制对于她而言的吸引力在于过得去的薪水和稳定闲适的工作环境。
但那次聚会上的“格格不入”却让她充满了“恐惧感”。来参加聚会的同学有些在一线城市工作,有些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即便大家围绕各自工作的困扰展开话题,王琪却感觉自己就像是那桌饭局里的“局外人”,“我的大学院校并不差,但经历了一年职场后,好像和同学成了两个世界的人。”王琪突然开始害怕了,“这是我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那个时候我意识到,在一些层面上,我和其他同学的差距已经拉开了,而且越来越大。”她突然清醒,自己不能再这样“与外界隔离一般”地继续闭塞地工作下去。
体制内也不乏最初对个人职业目标有清晰规划的年轻人。相比于薪酬,他们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但体制内无法逾越的“先来后到”的层级制度、缓慢的晋升通道和不完善的奖励机制,却在慢慢消磨他们的耐心和热情,使他们逐渐萌生离开的想法。
直到2015年研究生毕业,顾佳都没有想过进体制内工作。通过同学和老师,她对体制内工作的“刻板”和“循规蹈矩”早有耳闻,而另一方面,學习编程技术的她要找一份工作并不难。但当地农林局到校园招新时,她因不想违背父母的意愿,抱着随便试试的心态参加了面试,却意外地被顺利录取,并且还是与她所学对口的数据分析岗位。顾佳“虽然心里挣扎了一下”,但抱着“体验一下也好”的心态,开始了这份体制内的工作。
在顾佳对自己的职业规划里,不论去哪里工作,她都希望能运用所学的技术,解决工作上的具体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并且劳有所得。但一年时间内,经历了体制内的工作忙季和年底的绩效考核后,她对体制的固有认知一点一点得到了验证,顾佳的心理出现了波动和质疑。
“体制内就像一个封建社会,我过得很煎熬。”顾佳回忆道,“在体制内做事有些身不由己,很多时候我的工作内容、未来的工作去向全部都由领导决定,做事的条条框框很多,很多福利要讲究先来后到的顺序,并不会因为你的能力突出而给你。”
让顾佳决定辞职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体制内的一些行事方式,这在她看来已经触碰到了她专业素养的“红线”。技术出身的顾佳非常注重数据的严谨性,但在体制内,为了使领导业绩达标,她需要配合数据造假,甚至需要“精心设计”一套数据,录入到数据库内,最后使系统运行呈现合理的数值,这件事让她“至今无法理解”。
现在回看当时自己入职前立下的目标,不免显得有些“理想主义”,她发现个人的价值愈发得不到体现,努力也无法被重视,“我看透了,如果在这里干一辈子,我可能会废掉”,2018年春节期间,在和家人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之后,3月时顾佳裸辞了。
年轻人选择从体制内开始,大多出于长辈的压力,以及对稳定生活的渴望,但他们同时又有着强烈的自我实现的追求,当体制内的工作无法满足他们的自我成就感,他们越来越敢于选择离开。“现在不少年轻人在选择企业时,自我意识被点燃了。他们更看重自己是否在企业中获得尊重,是否能实现自我,而不仅仅把它看作是养活自己的一个工具。”李强观察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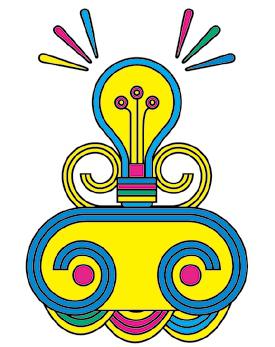
B离开体制前,我并不是毫无准备
因为工作性质的差异,体制内和体制外对个人的能力模型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此在离开体制前,需要对个人的职场竞争力重新做一轮复盘,提前做好适应新环境的准备。
王琪在意识到和外界环境的视野差距后,开始琢磨在工作范围内找一些能够挑战能力的事锻炼自己,为跳出体制加码。意外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挖掘出了自己能力上的优势,为接下来的求职明确了方向。
在宣传部内,有项工作需要员工通过查阅资料分析一些国际上发生的政经时事向省里汇报,因为工作量大且繁琐,过去王琪总是“能推则推。”但在跳槽念头的推动下,她开始为了写好一篇文章而去阅读大量书籍及外媒资讯,通常她会用一周时间写出一篇4000字左右的热点分析提交。
领导的好评让她对自己的文字功底有了信心,她发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只会按照套路半小时写一篇红头文件的普通职员。“这是一份我可以在体制内获得的宝贵经验,也是可以写到简历里的亮点,算是一种无形的技能吧。”有了这个经验,王琪认为自己之后可以从事跟文字相关的工作,作为跳出体制的新开始。
而起初就没有打算在体制内长待的顾佳近3年内都没有放弃过精进自己的编程技术。在休息日,她喜欢研究一些新出现的软件,并且尝试搭建新的模型算法。这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兴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主动提前缩小和企业技术之间的能力跨度。“我比较担心自己所学的知识到了企业内是否够用,他们是不是已经技术很先进了。但我本身比较爱学习,如果跟不上,花一两个月时间,提升起来也是很快的。”
在跳出体制前,首先要想好自己的职业目标,如果当下的工作不能为实现它贡献任何助推力,那还是越早跳越好。
对未来职业规划依旧迷茫的张茜霖选择离开体制的方式是去北京读研,因为在决定辞职寻找下一份工作时,她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核心竞争力,“我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这两年什么都没有学到。根本不及其他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是一张白纸,而且有一腔热情,但我做的事情,谁都能来做。”在没有想好下一步计划之前,张茜霖决定重回校园,继续深造或许能让自己进入一个相对更高的平台。
之所以从体制内跳槽,本质上和在体制外跳槽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无非是出于当下岗位与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路径不匹配。李强建议,“在跳出体制前,首先要想好自己的职业目标,如果当下的工作不能为实现它贡献任何助推力,那还是越早跳越好。”
很多从体制内出去的人无法顺利融入体制外的工作,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在离开之前并没有完全理解两种工作方式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李强分析道,体制内的工作对多数人来说,都属于“一个螺丝一个钉”,负责好个人位置上的任务就足够,而在体制外,个人需要比领导布置的任务想得更长远,甚至从企业未来发展的角度出发,也要兼顾个人能力的提升等多个方面的问题,更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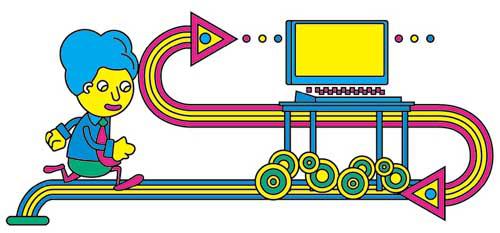
所谓主观能动性,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持续和快速学习的能力。APEX派思咨询创始人李晨面试过一些从体制内跳出来的年轻人,他发现,体制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对年轻人思维模式的固化。在体制内入职,上岗前可能会参加一个月的基本培训,之后就可以依靠这套模式完成后期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但在企业内可能每一天都需要学习新的内容,但很多体制内的年轻人在工作2到3年后,已经丧失了这种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价值的能力。
因此,在即将进入“非舒适圈”时,除了在心理上需要有面对未知新环境的预判意识,更重要的是在能力上要做好应对完全陌生的工作内容的相应准备。企业不再是温室,而是一个竞技场。
最理想的情況是,从体制内就开始弥补将来所需要的技能,重拾学习能力。“因为在企业内工作节奏开始加快,更讲究个人的综合能力。”李强以体制内的宣传岗为例,可能原本在体制内,公司人只要有比较好的文字功底就可以完成任务,但如果到企业去做公关工作,除了文笔好,还要有较强的项目统筹管理能力,了解公司的产品并能策划包装宣传等。所以一旦确定跳槽目标,在体制内就要开始寻找机会补课。尤其对于跨行业的跳槽来说,提前对行业有深入了解是非常必要的。
C新的开始,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即使已经在体制内有过几年的工作经验,但进入企业还是初学者的角色,从找工作开始,一切都要从零学起。这群离开体制的年轻人,在企业中重新开始一轮自我认知和成长,这其中有磕绊,也有惊喜。
王琪辞职后,先让自己放松了3个月,她去健身房锻炼、积极参加同城活动,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接触来自各行各业的不同人群,与他们交流。“我与社会脱节太久了,只知道未来会继续从事传媒行业,但如果让我现在谈职业规划,可能我连有哪些职业都不知道。”王琪感慨道。
但因为缺乏找工作的经验,以及判断一个公司好坏的能力,王琪的第一份工作没干满一个月就辞职了。今年6月,她陆续收到了3份offer,却选择了其中薪酬最低的一份—一家猎头公司的公关。“我更看重这个平台的价值。”在这家公司工作,王琪服务的客户都是全球500强企业,尽管目前这家公司在行业内并没有很明显的成绩,但王琪很快调整心态,把它当成是自己熟悉行业的机会。当上级要求她为公司写一份品牌策划时,她只用了3天时间就交出一个漂亮的方案,同时还分析了竞品公司的定位、需求、媒体投放形式等,得到了上级的肯定。新的开始让王琪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更加自信,尽管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仍然充满了迷茫,她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慢慢适应这个体制外的新环境。
今年4月入职企业后,顾佳相对顺利地开启了新的工作状态。她不再是过去在体制内单干的个体,而是整个项目团队中负责技术环节的一个成员,这让她第一次体验到了个人价值发挥的成就感,“大家都是合力将项目顺利完成,能真实感受到我的技术分享可以提高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且在完善的激励机制下,即使加班辛苦,顾佳还是觉得比起体制内的“心里苦”要更有干劲。
而相对于环境稳定的体制,她反而很享受企业内的变动,这种变动来自于项目排期的变更、身边同事的流动甚至工作地点的更换,这些都提醒着她要时刻保持应变的能力,也不再会有过去那种“职业生涯一眼看到头”的虚无感。
度过3个月适应期后,顾佳为自己做了职业规划。过去在体制内,个人的能力还被禁锢在某一个技术上,但之后,她希望自己能够培养大局观,往项目统筹或者管理的方向去发展,“我没有用新人的态度看待自己,希望自己能将上升的时间缩短一些,以最快的速度上升到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