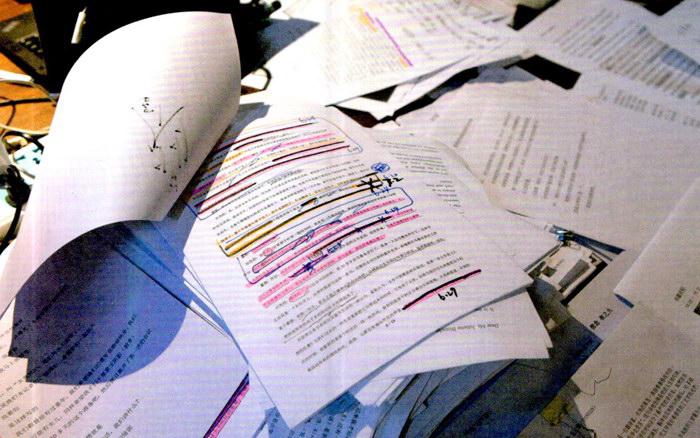董卿 重新定义理想
2018-08-22张宇欣
张宇欣
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董卿和刘谦表演近景魔术。
表扬只有一句,后面都是意见
董卿的人生态度继承自她的父亲董善祥。董善祥是农村孩子,父亲过世早,母子俩相依为命。他每天早上抓鱼抓虾去集市上卖,再去上学,一路刻苦,考进复旦。他笃信一切掌握在手中,命运要靠自己改变——也毫不质疑地将这份苦塞给独生女。
董卿开始洗碗的时候还没有水池高。十几岁时,她假期打过工,当过营业员,跑过广播站。她高一那年,董善祥给朋友打电话,“你们宾馆要不要清洁工?我女儿免费来给你们打工。”对方不好意思,说一天给一块钱吧。第一次打扫,领班分了董卿10间房,让一上午清洁完。
半天才打扫了两间,人是动弹不得了。领班鞭策,“怎么才干了这么点点事情啊?你还要不要吃饭了?你爸爸已经打过电话来了,让我们严格对待你。”父亲到场监督,她委屈地哭了,说累死了不干了。董善祥难得地摸摸她的头:“坚持一下。”
董善祥和董卿的经验加起来,等于要在逆境中寻找动能、自我鼓劲。董卿也真成了这样的人。看到“河流只有遇到石头才会激起浪花”,赶紧抄下来。母亲金路德总说,“你跟你爸怎么这么像呢?”她特别自豪,相信性格即命运,以此说服自己,也说服观众。
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董卿在安徽读小学,过年才回上海看外公和奶奶辈亲戚。坐12小时火车,她像行李一样被塞进椅子下,满鼻子怪味,老晕车,吐。但到上海睡一觉醒来,想起身在花花都市,马上高兴得蹦起来。她说那是小孩心性。成年后好像也没变,愿意盯住事物的光明面。
对董卿,父亲的要求琐碎而具体。每天到家门口的淮北一中跑一千米,“感觉特傻,整个学校的同学、老师好像都看着你,像阿甘一样。”有时她偷懒躲在楼道里,算准时间,再气喘吁吁回家。
金路德年轻时作风朴素,董善祥可能看惯了,也不让她给女儿做新衣服,“我要扯布,每次都跟我吵。顶好是我的旧衣服改一下给她穿。一照镜子(她爸)就说,臭美什么呀,长得又不好看!”金路德回忆。
还没上学,董善祥就要求女儿看书要把成语抄在小纸片上,贴墙上等待检查。“四个字的就是成语。”董善祥教。有一回,董卿把“回维也纳”也当成语抄了。父亲通常在吃饭时批评。他这这那那地指摘一通,董卿边吃边哭。
虎爸教育的果实是丰硕的。董卿大学毕业后到浙江台,在《人世风情》(1994)栏目学习主持、编导、撰稿,讲话轻轻柔柔,还有学生腔。两年后到东方卫视,主持情感节目《相约星期六》,一年创下10%的收视率,“优雅从容”“大气谦和”等词开始成为她的注脚。2000年在悉尼用英语主持音乐会,给她带来了国内主持人最高荣誉“金话筒奖”。
到央视后,董卿以技巧与状态稳定著称。2006年最后一天《欢乐中国行》元旦晚会直播,要等到零点敲钟。23点57分,所有节目演完了,一位导演给她传达救场指令。走到舞台,又有个年轻导演说:“董卿,不是两分半,是一分半,是一分半!”她带着标志性微笑抒情式地展望起2007。话至尾声,第一位导演又发话:“董卿,不是一分半,是两分半,现在再填补一分钟,听我的!”她毫不迟滞,继续感谢观众,有了主持史上的“金色三分钟”。
她成了中国最好的主持人之一。学者孙良撰文,“如果说《朗读者》把朗读行为领上了大众文化的神坛,那么董卿则在有意无意间充当了缪斯的角色,将民族文化审美意趣的呈现者、媒介文化仪式的主导者和社会核心价值的阐释者诸般角色集于一身,实现了新传播环境下主持人文化形象的完型塑造。”
可她觉得自己能力并不优于他人,只是父亲打下的烙印太深,“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
董卿的每一台节目父母都看。董善祥不会用手机,写信把批评传真过去。抬头三个字“致女儿”,表扬的话只有一句,后面都是意见:这个发型不精神。这么笑不淑女。最后一场是不是该感谢评审、观众、工作人员?
朋友们告诉她,松弛一点
八九年前,董卿回母校上海戏剧学院,台下师弟问,艺术是一条艰难的路,当年有没有准备?
她马上回:没有。“身体上的累是可以克服的,但‘再造巅峰谈何容易。每天都在脑海中回旋,什么是好,什么是最好?你真的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离开吗?”
董卿大一寒假回家,董善祥提议一家三口下馆子。吃着吃着,他突然敬了董卿一杯。“我跟你道個歉,我想了想,这么多年,我对你有很多方式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但惯性不允许停步,她往前跑了20年。
当年在上海,已经事业成功,被拦下签名、拍照是寻常事。2002年,她决定来到只认识长安街的北京。做《魅力12》,三四天完成了一个多月的工作量,剩下的大半个月她养成自言自语的习惯:“睡觉吧”,“起床了”,“该吃饭了。”
1997年,上海,24岁的董卿
调到文艺部,等来主持第十一届青歌赛的机会,连续30场3小时直播,每天下午4点彩排,晚上10点直播结束,她换下礼服又和评审核对次日考题,到家凌晨3点,还打着哈欠背台词。凌晨做梦,要上台了,稿子没背完,急得撞墙。
2004年底,郎昆作为春晚总导演通知董卿,她成为春晚主持人之一。接到电话是半夜,她刚搬新家,灰头土脸,冷静地说了声“谢谢郎导”。父母睡了,没人看见她的雀跃。她拎着扫帚在屋里转圈,觉得有力气再搬一次家。
在郎昆的印象中,董卿工作上“从不对付”。春晚直播前,她在自家书房把主持词滚了上百遍,“中国中央电视台”音量之大,说得全楼的邻居估计都听到了。2011年公安部春晚,现场将有公安系统的6位英雄模范给观众拜年。董卿想为每个人做个介绍,自己前夜熬到4点,把万字的资料精简成几句话。
主持了13年春晚,董卿已是央视挂历上高居前三甲的“一姐”,像她的前辈一样成为“家喻户晓”的专属名词。2013年,录到第七场《我要上春晚》,她和嘉宾都疲态毕现。夜里12点到家,她坐在地上(这样就夺去了蜷在沙发里的安全感),把节目像电影一样从头到尾过一遍,“怎么说你好,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这么问,那个地方加一句话会不会更好呢?”这么复盘了三小时。
那也是她被“职业性冷漠”折磨的时期。花了将近二十年才在舞台中央站稳,但交到手上的娱乐节目她无法再100%投入,只感到无谓的消耗。两年里,内心翻滚、煎熬,终于放下“回来没有我的位置”的恐惧,急刹车。“刹得人咣当一下,自己的脑门都磕个包出来,但也必须要停下来。”
到南加大进修,做回学生。刚要租房就被逼疯,周末房产中介都关机,留言周一才回复。朋友们告诉她,松弛一点——她确实紧绷了很多年。那年在兴化,她举着雨伞上台,刚说完“兴化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脚下一滑,屁股落地。被工作人员扶起来后,职业笑容立刻绽放:“我把跟头摔在了兴化,这一跤让我这辈子永远记住了兴化!”一年130来场节目靠的是生扛。
一年又四个月里,她每天听课,不用微信,iPad上只有英汉词典和菜谱APP,像“离开一个很爱的人”一样放掉工作。
开始把孤独向外袒露
10年前就有人建议董卿做制片人。她觉得自己性格不合适,“我特别苛刻,可以六七点坐在书房不离开,一直到早上三四点,要把一台节目弄得明明白白,但这种行事风格不一定所有人能接受。”
观众不会看到,这个央视的“定海神针”如何“一点一点寻找我能在哪里说话,我能说什么,能不能说我想说的东西。”她尝试在撰稿人文案的基础上糅进自己的情感与观点,自己的准备可能全被剪掉,那就“要做得更好,要做到你剪不掉我的话”。
做《朗读者》的两年,她在台下说的话超过了过去5年的量。其实过去20年,她都顶着“知性”“优雅”的标签,默默在这条道上跑,“用灿烂的笑容、得体的语言甚至是美好的服饰唤起了大家的一些记忆,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感受。可那已经结束了。”
音乐人姚谦注意到了董卿的细微变化。他是《朗读者》的音乐总监,发现董卿在交流中对文字很敏感,会流露真性情,颇异于春晚的国家代言人形象。
《朗读者》印着董卿的审美观。演播室由两个空间组成,一为开放式剧场,有层层书架、观众席,是嘉宾朗读、对外输出的地方;二为小客厅,仅有沙发和矮几,是嘉宾和主持人谈心、流泪的私密空间,观众透过荧屏窥探。每每采访完毕,小客厅的大门打开,嘉宾通过甬道走向观众。
《朗读者》之前,董卿很少聊自己的心路历程。台面上的,全国都能看到。公开报道中也大多在诉说她作为制片人的体验:立项、找人、剪片、采访,对反响的焦虑,读书的意义与文字之美。她不演戏、不出书、没有流量。央视以外,很少看见她的身影。
顺藤摸瓜,也能找到她的小客厅。她从小爱哭,回想起学生时代的夏日午后,教室里是昏昏欲睡的同学,窗外是知了鸣个不停,还有阳光照出的树影,那场景美得让她想痛哭一场。
2008年,董卿与巩汉林(右一)、黄宏(左二)、林永健(左一)彩排春节联欢晚会小品《开锁》
每位嘉宾的场记稿都由董卿亲自批注图体刊记者梁辰
她开始把孤独向外袒露。春晚结束后,是失重的感觉。回服装间,把行头归置好,提溜大包小包往外走。演播室到大门口有长长的走廊,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回荡在走廊里,安静得有点寂寞。一出去寒风扑面。她总是回家一个人吃速冻饺子,等着看电视重播。头两年也可怜自己,身边没个说话的人。“繁华过后的落寞需要你去调整,你需要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你不能说刚才那么好,现在那么冷,那么黑,我不过了。”慢慢就习惯了。
阅读是能打量董卿个人趣味的少数的窗口。尽管热爱俄罗斯文学中的批判性,但她几乎不公开问责什么。除了对自己的节目,她很少持嚴苛的态度审视外部世界。聚光灯外,她不愿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敬一丹说,倪萍身上有一种“中国式的道德感”。这位董卿的前辈以自嘲的“大眼睛加春风般的笑容,长得符合工农兵的审美标准”改变了1990年代中国电视的主持风格。而董卿又异军突起,树立了某种意义上“完美女性”的标杆。
小时候她最怕写《我的理想》这样的作文,觉得都是胡编乱造,把所有美好的职业想象成自己的理想。“其实理想是有一天,你做了这件事后,开始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读书的时候,父母开了文学名著的书单,她认认真真看了,三五天就看完一本。母亲疑虑她读得太快,会抽出某一章节让她讲人物关系,结果全无错漏,她成了爱书之人。大学毕业的好长时间里,当主持人都不是她的理想,那只不过是“漂漂亮亮地站那儿把话说完就行了”。后来,她的完美主义告诉她,“要做成有价值的事情,要传递有价值的信息、有意义的情感。”
也许对她而言,理想是可以修正、可以再定义的。那些被重新定义的人生,又被她用数年一日的勤勉赋予了厚度。就像她喜欢的巴尔蒙特的诗中所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大海,和百花盛开的峡谷。
(参考资料:孙良,《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形象的完型塑造——以<朗读者>与董卿为例》,《电视研究》:刘琦、战迪,《董卿主持艺术圈点》,《青年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