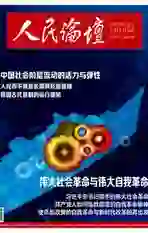我国古代县制的运行奥秘
2018-08-17高福顺
高福顺
【摘要】县制作为帝制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风向标,既是帝国征收赋税、劝课农桑、通官理民的主导者,又是保障黔黎生计、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护身符”。县制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县制 基层社会 官治与民治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传统中国社会最合适、最有效的治理模式,就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支配为特征的分地域、分层级而构筑的权力结构形态来约束帝国治域下的黔首黎氓。县制作为帝制时代官治与民治的“调节器”,具有承上启下、通官理民的特殊职能,清陈宏谋《寄刘含章书》曰:“县令一职,于民最亲,及民甚速,一切利弊风俗,惟县令知之最悉,行之甚便,遇上司有所兴除,其当者固可推广而力行之,即未当者亦可酌剂而变通之。”可见,县制既是“牧民”之司,统掌一县之行政、司法、教化等诸项政务,又是帝制时代中央集权所能触及的末端,向有“皇权不下县”之说,故而县制成为帝制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风向标,既是帝国征收赋税、劝课农桑、通官理民的主导者,又是保障黔黎生计、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护身符”。
传统中国县制渊源的追溯揭示出“县”之涵义的嬗变
所谓的“县”字,可追溯到西周时代,当时西周的铜器上就已出现以“县鄙”为标志的“县”,意指“王畿以内国都以外的地区或城邑四周地区”。“县”原作“寰”,《穀梁传·隐公元年》载:“冬,十有二月,祭伯来。来者,来朝也。其弗谓朝何也?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唐杨士勋疏:“寰内者,王都在中,诸侯四面绕之,故曰寰内也。”晋范宁集解:“天子畿内大夫有采地,谓之寰内诸侯。”“寰音县,古县字,一音环,又言患;寰内,圻内也。”可见,县者乃寰也。
“县”作为帝制时代的基层行政区确实存在一个变化过程,也就是说,“县”原属王畿以内国都以外的被分封的采邑,而逐渐演变为诸侯国君直接统辖的基层行政区,集权特征相当凸显,“县”虽还有分封制的残余气息,如晋国卿大夫赵简子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然诸侯国君直辖下的“县”却有了秦始皇于统治域内推行的郡县制之县制的属性。至战国时,各诸侯国君为增强抗衡诸侯之国力,渐趋废除周天子以来的世卿世禄制,代之而起的便是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官僚制,即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此已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秦始皇聚六合、一统天下后,在徘徊于世卿世禄制还是官僚制的关键时刻,廷尉李斯建议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于是,始皇帝排众议、挺李斯,帝国“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始皇帝的英明决策,导致传统中国社会为之一变,彻底废除世卿世禄制而行中央集权于天下,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以“郡县制”为准绳。自此之后,尽管有汉高祖刘邦“封王”之反复,但以郡县制为开端的基层行政区贯穿于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之始终。
县制稳定性成就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两千余年的不易不变
纵观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历史,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县制最为稳定,自秦始皇于其治域内全面推行郡县制以来,无论是秦汉的郡县制、魏晋南北朝的州郡县制、隋唐前期的州(郡)县,还是唐后期及辽宋金的道(路)州(府)县制、元明清的省(布政使司)府(路)州(直隶州)县制,作为权力结构金字塔的最底端的县制,其基石地位始终未曾改变,甚至连县的称谓都不作改易。县制于传统中国社会历行2000余年,若剔除疆域变化等因素影响,自秦至清,县之行政区的数量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尤其是与郡、州、道、路等行政区数量波动幅度相比,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县政作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官治与民治的关键基层组织,是沟通官民的桥梁,发挥着劝课农桑、征收赋税、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正常作用,不宜朝令夕改、频繁变动。正如公丕祥所云:“公元前221年,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秦始皇采纳廷尉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而秦县数目经推测约是一千之谱,每郡约辖20个县左右。‘汉承秦制,汉代地方政府制度及其县政制度因其郡县数额较为适中、地方行政区划较小、官级升转灵活等,而每每被后世所称道。无论后来的地方行政组织层级有何变化,县政始终是政区的基础性地域层级单元,因而县域治理便成为国家治理的‘枢纽。”
不过,县制稳定性仅是相对而言,县之行政区数量的不变并不等于县之行政区的地理分布及幅员之不变,如周氏所言,西汉与清之县行政区数量大体相当,然西汉与清的统辖区域范围却有相当大之不同。汉时,江南地区地旷人稀,政治、经济、文化开发尚欠发达,设置县行政区的数量便相当有限,而中原发达区设置县行政区的数量显然要比清朝的县行政区的幅员小且数量多,故秦汉时“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实际上,传统中国社会对县行政区的幅员并未有整齐划一的规范,多依据中央集权支配下的基层社会的实际状况或增或损之,如唐时江西的玉山县为“证圣二年,分常山、须江置”,四川蒙阳县为“仪凤二年析九陇、什邡、雒置”,被分割的县之幅员自然要缩减。因中央集权统治之需要,县行政区之幅员可因时利便,适时做出符合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需要的县行政区划,目的是提高县行政区的行政效率,正如周振鹤所云“行政区划是一项政治行为,其本意是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而设置”,正因如此,县制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高效性才使得县制历2000余年而不易不变。
县制稳定性成就了县政长官集权次第升级
统一的中央集权支配下的县制,在长达2000余年的演变过程中,县制始终是集权与分权的对立统一体,从秦汉分曹治事下的佐贰官之于长官的相对独立,至唐宋同职连坐制度下长官与佐贰官之间的相互制衡,再至明清幕僚间的共襄治理体制,均属集权与分权视域下的交错辉映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秦时的县政长官“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各署诸曹掾史”。对此,安作璋说:“主和典的意思表明,丞对于令长不完全是辅佐,更不是从属身份。”足见县政长官与佐贰官的分工并非明确,分工协作掌理县治域内的诸项事务,县政长官与佐贰官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征,当然亦存在权责不明的局限性,影响行政高效运行。
唐时,“京畿及天下諸县令之职,皆掌导扬风化,抚字黎氓,敦四人之业,崇五土之利,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若籍帐、传驿、仓库、盗贼、河堤、道路,虽有专当官,皆县令兼综焉。县丞为之贰。主簿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纠正非违,监印,给纸笔、杂用之事。录事掌受事发辰,句检稽失。县尉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宋时,县政长官“掌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平决狱讼,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境。凡户口、赋役、钱谷、振济、给纳之事皆掌之,以时造户版及催理二税。有水旱则有灾伤之诉,以分数蠲免;民以水旱流亡,则抚存安集之,无使失业。有孝悌行义闻于乡闾者,具事实上于州,激劝以励风俗。若京、朝、幕官则为知县事,有戍兵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宋神宗时,又重申县令、主簿、尉三者职权分工:“今后依旧簿专管勾稽簿书,尉专管捕捉外,其余县事并令通管。如此则吏不增员,事能协济。”与秦汉以来的县政长官相比,唐宋之际的县政长官与佐贰官之间的职权分工更加明确,县政长官直辖的诸项行政事务增多,多有话语权集中的倾向,导致佐贰官对县政长官的实际制衡作用明显有所降低。
明清时,县政又为之一变,县政长官的话语权进一步加强。明代“知县掌一县之政。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倩不时之役,皆视天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减之。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典史典文移出纳。”清代县政长官依然“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颂、兴教化、厉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与隋唐时代相比,明清县政的显著特征就是县政长官更加集权,几乎失去佐贰官的抗衡与制约,县政诸项事务无论大小,几乎概由县政长官一手包办。此种县政运行模式,虽然在提高行政效率上发挥主导作用,然滥权滥政风险亦日益增大,中央集权不利时,很可能导致基层社会的动荡与治理的失效。
县制稳定性成就了官治与民治的二元社会控制体系
传统中国社会县制在职能上更多的是利用自先秦以来的宗法社会的运行模式,充分发挥宗族、士绅和富豪等“地方精英”群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优势,形成官治与民治相结合的“指导渗透协同”的综合治理基层社会的二元社会控制体系。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有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层”,从历史上看,作为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有特定身份地位的宗族、士绅和富豪,其主要角色就在于“治其乡之事”,主导着基层社会的赈灾救济、纷争调解、立学导善、操办团练等诸项自治事务,对建构基层社会治理秩序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秦汉时,负责基层社会黔首黎氓的儒家思想教化之“三老”出自基层社会里选,民治色彩浓厚,规模亦相当庞大,而收赋税、听民讼的啬夫以及禁贼盗的游徼则为官府派遣至基层社会的乡官,东汉爰延“以为乡啬夫,仁化大行,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足见秦汉基层社会的官治与民治的密切协调,收到“通官理民”的理想成效。
唐宋时,虽有耆老、耆长掌率唐宋基层社会治理之重责,然乡官职役化所导致的重官治而轻民治的结果是基层社会秩序渐趋松驰。故苏颂《请别定县令考课及立乡官》说,“且古之治民,劝导教率无所不至。故孝弟力田有优异之科,三老廉吏有表率之义。由是农民众而土田辟,风俗厚而狱讼稀。今则不然,民勤于力苟致赡足,则惧外迁等第,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惰游者无罚也。父子聚居,丁产稍多,则惧差徭配率,遂有离析异居之弊。是孝弟无所劝,而奸恶未得止也。乡村但有耆壮、巡察、吏卒追捕,不闻以善道谕之者,是教化无由至,而狱讼不得息也”。正因非官方力量的削弱而导致基层社会儒家伦理道德秩序崩坏,才应运而生民间乡约。
明清基层社会权力结构中的里长、甲首等,“在官专掌催钱粮勾摄公事而已,其后乃以支应官府诸费。若祭祀、乡饮、迎春等事,皆责措办浸淫,至于杂供私馈,无名百出,一纸下征,刻不容缓”,几乎沦为职役化,任由官僚驱使,俨然成为征收赋税与维持基层社会治安的官治代理者,官治化趋势彰显无遗。尽管如此,县政长官仍然重视民治,从明代基层社会权力实际运行观之,在乡约宣讲圣谕或教化黔首黎氓儒家伦理道德秩序的场合,县政长官与士绅往往亲临现场,因为县政长官负有“兴教化,厉风俗”的职责,而士绅为“齐民之首,朝廷法纪不能尽喻于民,惟士与民亲,易于取信,如有读书敦品之士,正赖其转相劝戒,俾官之教化得行”。
总体说来,自秦汉以来,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官治与民治的博弈嬗变过程中,官治权力不断增强,而民治空间逐渐压缩,基层社会权力结构被完全有效地纳入中央集权体系视域内,基层社会无时无刻不在感受中央集权的存在,在集权与分权的协调共治之下,基层社会总体上呈现着秩序化的样态,可以说,官治与民治的结合,是中央集权支配体系视阈下最有效的基层社会控制模式之一,虽然中央集权在某种程度上让出了基层社会“自治空间”的代价,然收获的却是以较小的行政成本而取得最大化的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
(作者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影印清嘉靖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②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