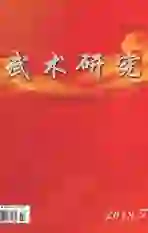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四川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研究
2018-08-11童国军
童国军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出发,对四川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研究认为:四川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处于哺乳期,对其体系建构的理论与实践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建议当前四川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应该在保持传统项目文化特色的基调上,突出文化内涵,保持文化本真;传承地域文化产业,构建文化生态系统,建立多元化立体宣传渠道,走民间传承与节庆整合之路,使其既能突出鲜明的文化特征,又能彰显一定的时代韵味,满足国家社会对体育文化发展的多元化需求。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川 少数民族体育 传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8)7—0078—04
“非物质文化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是一种具有时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策略性的文化表征,它不仅折射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原貌,也以极富活力的方式动态地保存和传演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四川省是我国具有历史悠久和文化积淀古老的民族聚居地之一,世居民族有鼻族、藏族、土家族、苗族、弟族、回族、满族、傣族、傈傈族、蒙古族、白族、纳西族、布依族等14个,拥有全国第二大藏区,最大的鼻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生活方式使四川少数民族体育表现出独特的人文特点,境内的少数民族体育资源不仅保留着民族起源发展的古老信息,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象征符号。因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域探析四川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问题,这不仅是解构少数民族体育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的一种文化策略,亦是其寻找现实定位和未来发展的科学依据。
1 四川少数民族体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
1.1 项目源起多样性
四川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浑厚的历史积淀和古老的文化气息,它与先古的生存息息相关,其不仅反映了早期人类与自然、社会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蕴藏着人类衍生的文化基因。四川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区域从生产劳动方式和地域要素来划分,可以分为三大文化区,即畜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区、半牧半农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区和农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区。如,土家族、苗族和部分彝族属于农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区,其生产劳动方式以耕地种植为主,主要是靠自然气候条件维持生计,为了粮食的丰收,所以常常祭祀以祈求风调雨顺,与此相联系的仪式庆典活动也就应运而生。再如,在草原环境中生存的藏族和蒙古族,牧民们以放羊牧马为生活基础来源,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避免狼群的伤害,射击就成为了蒙古族和藏族特色体育运动。凉山的布托县和四川的汶川阿坝州属于半牧半农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区,当地民众的生活还是以农耕和牧业为主,所以该地区在传统体育项目上,体现出农耕性与牧业性并重的特点。
1.2 传承凸显活态性
四川少数民族体育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里,它的传承方式并不囿于物质形态,同时也以动态的方式流动地显现一个民族的生活状态、个性及审美等。活态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基本特性,“这种‘活,本质上表现为它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创生并传承她的那个民族(社群)在自身长期奋斗和创造中凝聚成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为人,人是创造文化、繁衍文化的核心。应该说是处于“活态”文化的核心地位。“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场次或场景的表述、表演和技能操作,都会有所发挥,都是一种新的创造。”[2]四川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作为一种“身体文化”,如彝族的“格”,是即是为纪念祖先的,格能强壮人们的体格,培养坚忍不拔的意志品格,通过格来感谢族群的祖先。据考证,彝族的“格”(摔跤)起源于唐朝天宝年间,后代代相传至今。根据彝族史料记载“据传说摔跤是纪念民族英雄支格阿龙,因为他带领彝人战胜自然灾害,打败天王,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可见,彝族摔跤是和自身民族的文化黏合在一起,没有文化的熏陶,只靠自然条件的刺激,也难以传承不下去的,这也充分体现了彝族摔跤是一种活态文化。
1.3 形式表现复杂性
四川少数民族体育是具有浑厚历史积淀和浓烈人文气息的社会文化。“作为一种‘活态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数民族体育通过系列的身体活动则能够集中地体现具有同一性的规则、秩序、理念和信仰,某種意义上代表着一种文化典范和传统的指向性。”[3]按照体育学的分类标准、运动参与者的技艺类型和场地环境特征等因素,四川民族体育文化可以划分两大类、十一亚类(见表1)。
2 四川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
2.1 文化生态系统的破坏制约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求在对某一具体对象进行保护时,不能只顾及该事物本身,而必须连同与它的生命休戚与共的生态环境一起加以保护。民族与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大多产生于传统社会,流传于民间,尤其是较为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4]
自古以来,四川境内就有着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体育,它不仅为当地民众的娱乐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以简洁、实用的动作演练,彰显其体育风格。如:美丽优雅的彝族“多洛嗬”,雄壮浑厚的藏族诌舞、弦子舞(巴塘弦子舞)等,都是具有典型民族风格的传统体育。这些民族体育是贴合环境孕育而生的肢体文化,它们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自身寄予的社会环境。
“朵洛嗬”既是一种民族舞蹈又是一种曲牌,其寓意为:祈福纳祥、消灾送瘟、崇尚英雄、祭祀祖先,向往爱情和美丽人生。诌舞是一种传统或民间的表演艺术,是一种崇拜祭祀性舞蹈。弦子舞是一种藏族的歌舞艺术,表达人们对生活的体验和赞美。但是目前对于上述的民间文化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动作展示现代化、舞台化和竞技化,传承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这正如学者李伟在《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与发展研究》(2005)中描述的,“一个偏远的小山寨,男人们扮成原始荒蛮的样子,迎请火神为全寨去除污秽,只为这是一个传统的狂欢日。村里人想的很简单:按照传统举行,不过请来的客人与他们一道体验与神灵的交流。可衣冠楚楚的城里人似乎是冲那赤裸裸的、用兽皮、树叶装饰的身体而来的。办活动要花钱,过去的祭祀都是各家杀猪凑钱为神灵做祭品,让游客分担些费用也是应该的,由于种种原因,钱没有收到多少。几百号人座在村民们世代的村寨里饕餮一番,享用之后人去楼空,这却留给我们一个困惑:村民们在忐忑的心理下把他们与神灵间仅存的隐私公众于世,却没有留住自己民族的尊严,游客的介入,古老而神圣的祭祀发生的变化,毕摩成了表演者,村民成了旁观者,供游客拍照。这对他们淳朴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5]
2.2 法律法规不健全影响体育非物质文化遺产的发展
“目前,传统体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一些效果和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社会运行的灵活性差、发展的创新性不够、群众的积极性低迷等诸多弊端,直接制约着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6]基于这一点来讲,探究少数地区传统体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结合上,就应该紧密联系其得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并提倡建构一种“立体化”的保护机制,而这种保护机制就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做保障。目前四川境内的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还是处于哺乳期,成型的法律法规甚是缺乏。根据文献分析,主要有以下体现:第一,对传承人的保护一直是个盲点。虽然有部分政策文件提出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的保护,但落实程度却不大。第二,部分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影像到当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第三,有些开发经营者过大以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常常出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状况。如,四川某地区每年的赛马节,经营商为容纳更多的观众,将水土丰茂的草甸铲去,以扩大场地。其实这是不考虑对民族体育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不健全的今天,像这样类似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2.3 地方经济的落后,研究人才的匮乏制约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
了解现状,全面调查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当前就四川范围来看,展开对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普查是首要问题。现阶段四川境内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研究现状主要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第一,调研资金投入不足。四川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较广,加之四川地理环境复杂,这给调研和普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普查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实地考察田野调研的系统工作,在整个过程中不仅需要制定严密的计划,而且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组织工作极为复杂。而因为境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水平的滞后,使得经费投入方面略显捉襟见肘,这势必会给调研工作的顺利进行带来困难。第二,相关学科理论摄入不足、研究人才匮乏。民族传统体育学是一门建立不久的新型学科,其理论体系的构建还不成熟,有赖于借助于体育人文学、运动生理学、人类学等学科。尽管近年来社会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注较高,而与此同时,相关学科理论摄入不足、研究人才匮乏等问题也日益凸显,理论的摄人不足、人才的匮乏制约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对其进行保护应该厘清其内部组成要素并在方法上注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同时对研究人员来讲,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研究人员应该具有现代体育意识、宽厚的体育专业基本理论和传统文化知识。通过调查发现,就目前从事传统体育学术研究的梯队来讲,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研究的专家虽然人数甚多,当尚未形成固有的团队大都还是各自为战。这会造成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无序性和重复性,形成不了总体的研究工作的核心。与此同时,对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典文献研究的人员甚少,作为地方民族志的文化史料也少有人研究。
2.4 传统与现代对弈、融合冲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
“社会越发展,民族间的传统体育文化交流越加剧。”[7]而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在文化意识上传统与现代对弈、融合已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少数民族体育也在这的样文化大溶炉下接受着挑战。
四川民族众多,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多是民间自发的,不带功利性色彩,由群众组织参与活动,其存在形式大多是依附于传统民俗节日。近年来,西部大开发的挺进,四川民族地区的经济也出现快速的发展态势,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逐渐影响到曾经固有的劳动生产模式。近年来,许多少数民族人群也走向城市谋求生路开始打工、经商等现代生活,究其原因,这是传统价值观受到到现代社会观的冲击。当地民众希望将来自己儿女能有可观的经济收入、稳定工作,不必依靠传统的农牧生活,这造成了体育文化遗产在传承方式上的单一和缺失。于此同时,四川省体育文化遗产在其传承过程中也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许多参与者有抱着“凑热闹”的心理,没有深度参与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当然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不会长久。可见,在文化意识上少数地区传统与现代对弈、融合已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少数民族体育也在这样文化的大熔炉下接受着挑战。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四川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策略
3.1 突出文化内涵,保持文化本真
在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中,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始终以贴近民族生活生产需要为基础,以凸显浑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为主题。因此在挖掘民族体育活动时,一定要注重对其身上所负载的深刻民族风俗文化的传承,同时要积极挖掘和开发地方性民族传统文化活动。通过课题组的实地调查,在西昌市的火把节和普格县洛古波乡的火把节中,所展演的达体舞,从“牵手围绕而转,且跳且歌,初转徐徐行,再转小跃,行三转大跃,嬉笑追逐良久乃罢。”[8](据清咸丰七年(I857年)的《冕宁县志》)到如今踢、踏、勾、磐、跳,腰身扭动,双手摇摆的舞姿,这明显的注人了现代舞蹈的元素。这说明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舞蹈在商业化的今天,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基因正在消减或走向变异。在调查中,许多群众表达了这样的心声。“参加火把节不仅是为了来看热闹,主要还是来感受和体验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样在对“卡斯达温舞”的调查中获知,目前商业化趋势日趋浓重,旅游局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将“卡斯达温舞”的仪式过程简化,保留其表演的基本礼仪,使其向着舞台表演化的方向发展。而传统“卡斯达温舞”在仪式过程中本来应该体现出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却没有得到诠释。随着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山区的文化发展已经不再是块纯净的处女地,在发展地区经济的理由下,被扣上所谓“原生态民俗展现”的帽子,以吸引众多关注的目光,所以,突出民族文化内涵,保持民族文化本真,是四川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3.2 传承地域文化产业,构建文化生態系统
文化产业传承是一种动态的消费型传承。近年来,国内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慢慢的走上市场化的轨道,逐渐探寻自身发展与市场的切入点。如,第一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彝族阿细跳月,在我国开展广泛。彝族的支系阿细人历史久远,阿细跳月是具有彝家特色的传统体育,它的起源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在200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颁布后,当地政府将阿细跳月与村落文化建设联系起来,实现了文化重组,逐渐建立起一套以村落旅游经济、村落文化建设和村落政治发展,三位一体的村落体育发展模式,促进了阿细跳月发展。四川自古以来可谓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境内少数民族文化村更是富有浑厚的历史内涵,如九寨沟藏族村寨、理县桃坪羌寨、盐源泸沽湖摩梭村寨、汶川羌族的萝卜寨等,都是远近遐迩的著名民族村落,村落里除了拥有颇具民族特色的村落民居外,而且民俗节庆、传统体育活动也很具有特点。通过课题组的实地考察分析认为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体育活动可以与当地的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即将当地的传统体育纳入到村落文化的生态空间,实现当地传统体育与村落经济、村落政治建设、村落先进文化之间的合理耦合,建立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系统。
3.3 建立多元化立体宣传渠道,走民间传承与节庆整合之路
少数民族地区拥有活动内容丰富、民族风情浓郁、特色鲜明的民族体育活动,它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文化整合、拓展民族交往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民族地区对民族体育活动的推介不足,外界对其了解和认识程度还不够。根据作者对调查点的了解,在螺髻山镇少数民族体育的宣传中,还是以传统的宣传方式为主,主要形式有贴通告、发邀请函、口头交流为主,辅以电话、网络,这些宣传途径在血缘和地缘的区域内很有效果,但对外界社会所起的宣传效果不是很理想。四川众多的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大多与节庆活动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民间节庆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搭建了展演的平台。如:彝族磨尔秋(凉山州甘洛县)、彝族苏尼舞(布拖县文化馆)、朵洛嗬、甲搓(盐源县)傈僳族嘎且且撒勒舞(会东县)、藏族杜基嘎尔(木里县文化馆)等大多会节庆时刻浓重登场。上述民族体育都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每年的火把节也是它们展示魅力的时机。然而通过笔者的实际调查,官方网站显示火把节时间是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西昌市、普格县、布托县、喜德县等),但是在县下的每个乡镇火把节的时间却没有在网上得以公布,致使社会热点关注的“原生态民俗文化”少了很多受众。“现在县市的火把节活动太商业化了,没有什么好看的,我们都很想去地方乡寨看看富有地域风情的火把节,而哪个地方有,什么时间举办我们也不知道”。及时将地方节庆活动的动态在乡村政务公开栏更新公布,让更多外界人士了解节庆体育的开展状况,这样才能抓住展示的契机吸引更多人关注地方性民间节庆体育。据大会组委会的负责人介绍,以彝族火把节为契机,扩大彝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力,是目前国家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工作的体现,以后会有更多的彝族民间传统体育在火把节山展示的。四川境内有很多资源丰厚的少数民族体育,这些活动都是历代相传,具有浑厚历史积淀的民间文化,从历史维度,讲它是具有地方文化色彩的史记,从文化传承的视角说它是具有集体记忆的文化事项,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立足保护和发展的角度来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通过节日庆典、节庆整合之路等进行传播,在民间广泛的传播,这将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宋俊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刍议[J].江西社会科学,2006⑴:33-37.
[2]贺学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5(2):100-106.
[3]吴铎.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8.
[4]白晋湘.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J].体育科学,2008(28):5.
[5]李伟.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与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29.
[6]白晋湘.少数民族聚居区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建构研究——以湘西大兴寨苗族抢狮习俗为例[J].体育科学,201(32):16.
[7]崔乐泉.民族传统体育新文化的构建[J].体育文化导刊,2005⑶:43.
[8]http://baidu.com/link?url=cfCqsVoKBkIt01NYZu7GMBjwYZyOHTflS16JPClbnF5A-0HLDGKQRzO[D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