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东兴:66载离不了京味儿的根
2018-07-30张琳康旭晶封面摄影及部分摄影
□ 记者夯石(张琳) 康旭晶/封面摄影及部分摄影
作为北京唯一的地方戏——北京曲剧,说的是纯正的北京话儿,唱的是北京的音儿,演的是皇城根下北京人儿,讲的是发生在北京城里的事儿,而浓郁的京味儿更是北京曲剧离不了的根儿——
孙东兴,北京市曲剧团团长。诚恳谦虚,坦诚务实,这是笔者对他的最初印象。说自己,永远话不多;说北京曲剧,常常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自己的经历,似乎很简单:评剧科班出身,当年领导说行政工作缺人手,他就放下了演员的本行,从最基础的工作干起,年纪轻轻便成了中国评剧院的“管家”,杂七杂八管了一大堆事。后来调到北京市曲剧团,又是事无巨细,更加上改制后人心不稳,如何把大家伙拧成一股绳,孙东兴可没少吃苦受累费心思。
如今改制后的剧团像个“变形金刚”,随时会变身、变戏法儿。白天接洽演出任务,半夜和员工一起“装台”,这样的剧团团长,多吗?前些日子,就是最热那会儿,孙团长微信中告诉我刚从延庆回来,不是避暑,是为了团里的一部“定制剧”,已经忙活很长一段时间了。编剧、导演、演员,政府、市场、观众,孙东兴像一座桥梁,更像是黏合剂。这样的经历,又确乎不太简单。因为许多同样资历和条件的人早发了大财了。而据我所知,孙东兴收入并不高。好在,他深爱着北京曲剧,更深爱着团里的老少兄弟。所以他才能“眉飞色舞”地畅谈北京曲剧的美好愿景和前世今生,而轮到他自己,他还是笑笑。
老舍先生命名,北京唯一的地方戏,这是孙东兴关于北京曲剧说得最多的一句。那咱就先从“老舍先生命名”说起——

《杨乃武与小白菜》魏喜奎饰毕秀姑

《啼笑因缘》中魏喜奎饰沈凤喜

《骆驼祥子》李宝岩饰祥子,孙砚琴饰虎妞
老舍给了北京曲剧“立身之本”
北京曲剧、剧团与老舍先生有着深厚渊源。“北京曲剧”由先生命名,剧种开创剧目是老舍先生创作的《柳树井》。
要说北京曲剧的渊源,那还真不是老舍先生给“起个名儿”这么简单。所以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咱还是得从头说道说道。
北京曲剧,是唯一在北京这块土地上诞生的北京地方戏曲剧种。1949年4月,北京曲艺艺人曹宝禄、魏喜奎、顾荣甫等组织“群艺社”,在前门箭楼游艺厅演唱曲艺。为了使节目丰富多彩,他们在“拆唱八角鼓”(亦称“彩唱八角鼓”或“牌子曲”)的基础上,以单弦、琴书、大鼓、京剧、评剧等唱腔演唱了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探亲家》《新打灶王》《四劝》等“解放新戏”,这些小戏被称为“新曲艺剧”。此后,他们又排演了新戏《婚姻自由》,在听取了老舍和马少波等艺术家意见后,去掉了京、评等剧种的唱腔,改为以单弦牌子曲为主,并增加了北京曲艺中其他曲种的唱腔,使音乐风格更趋统一。孙东兴介绍说,北京曲剧是呈现老舍先生作品最多的剧种,北京市曲剧团是排演老舍先生作品最多的剧团,而这是有历史渊源的。1951年,老舍将宣传婚姻法的新作《柳树井》交“群艺社”排演,魏喜奎、关学增、孙砚琴等以声情并茂的演唱,生动贴切的表演,将这出用北京语言、北京音乐表现北京人新生活的新戏搬上舞台,受到北京观众的欢迎和认可,一个新的剧种伴随着新戏《柳树井》的演出诞生。“1952年,老舍先生建议把曲艺剧定名为曲剧,后又明确为北京曲剧,以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曲剧如河南曲剧等,并作为北京地方戏来进行曲剧剧种的艺术建设。”
四年前的2014年是老舍先生诞辰115周年,也是他创作生涯90周年,同时也是小说《四世同堂》创作70周年。为此,北京市曲剧团策划并一手打造了贯穿全年的“老舍戏剧年”。当年的1月13日开始,北京市曲剧团就在天桥剧场和海淀工人文化宫陆续上演《正红旗下》《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三部经典北京曲剧大戏……
孙团长介绍说,北京市曲剧团是单一剧种单一剧团。北京曲剧、剧团与老舍先生有着深厚渊源。“北京曲剧”由先生命名,剧种开创剧目是老舍先生创作的《柳树井》。“由此,先生的文学作品成为这一剧种和剧团重要的创作题材。北京曲剧有《柳树井》(1952年)、《骆驼祥子》(1958年)、《方珍珠》(1979年)、《龙须沟》(1996年)、《茶馆》(1998年)、《四世同堂》(2001年)、《正红旗下》(2004年)、《开市大吉》(2010年),以及话剧《老张的哲学》(2015年),目前为止已有9部之多,成为编创老舍先生作品数量最多的剧团。世界上改编同一作家作品最多的剧团只有两个,一个是英国的莎士比亚剧团,另一个就是北京市曲剧团。”北京曲剧的诞生弥补了北京地域在历史上没有自己地方戏曲的空白。老舍先生命名了北京曲剧,并给予北京曲剧源源不断的食粮和营养,“所以北京市曲剧团也始终围绕老舍先生的‘京味儿’来不断提升和拓展自己。”
老舍之子舒乙曾对孙东兴说:“改版后的北京曲剧版《骆驼祥子》是迄今所有改编老舍作品的各种演艺形式中,最贴合作品本意的剧目。”孙团长介绍说,旧版的《骆驼祥子》受时代影响,把重点放在祥子和虎妞的爱情上,“我们后来进行了全新的改版,以使其更贴近老舍先生说的祥子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没落鬼,从而揭示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青年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堕落的。”
苦出身的老舍和曲艺结下不解之缘
舒乙先生回忆说:由于父亲自小吃苦,知道生活的艰难,所以一直特别同情那些在旧社会地位和自己一样低下的艺人。
孙东兴还和笔者聊起剧团老一辈艺术家跟他讲过的那些老舍先生当年提携和关爱北京曲剧的故事。2009年8月,老舍之子舒乙先生在首图举办的《老舍和北京曲剧》讲座中也对此有过较为翔实的讲述。
众所周知,老舍非常喜爱曲艺,这和他的出身有很大关系。小时候若不是有好心人接济,老舍本来是上不了学的。在那个年代,大凡识文断字、能写写文章的人多是家里有几个闲钱的,因此穷人与作家好像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而老舍无疑是幸运的,他这个“穷人”不仅当了作家,而且成了一辈子写平民、为平民而写的“人民艺术家”。
老舍原名舒庆春,祖上在旗,但实际上到了老舍父亲这一辈,大清朝气数已尽。老舍的父亲作为底层的八旗兵丁,生活上已是举步维艰。老舍父亲一辈子的工作就是看守北京皇城,一块腰牌,一把铁片佩刀,每天巡守,中午还要回家吃饭,一个月才领三两银子俸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老舍父亲在抵抗时被日本兵烧伤,从镇守的正阳门一直退到西华门附近的一个粮店,重伤后下落不明,彼时老舍才一岁。
清政府因为赔款,各方面节省开支,老舍一家孤儿寡母的俸禄也被减半,再加上货币贬值等因素,老舍很小的时候就经常饿肚子。幸亏舒家祖上交了一位好友——刘大善人,他自己的女儿和老舍年龄差不多大,因此当自家女儿上学的时候,刘大善人便主动找到老舍母亲,包下了老舍上学的学费和吃住费用,就这样老舍才念了几年私塾……后来这位刘大善人出家,圆寂的时候老舍正在济南,他特意撰写《宗月大师》一文以纪念老人的知遇之恩。
舒乙先生回忆说:由于父亲自小吃苦,知道生活的艰难,所以一直特别同情那些在旧社会地位和自己一样低下的艺人,尤其是女艺人。老舍的多部作品就是反映这些底层艺人生活的,如为青艺创作的剧本《方珍珠》。那段时期,老舍经常和这些艺人来往,听相声、听鼓书、听太平歌词,了解了多种曲艺形式,也目睹了底层艺人的艰辛。
解放后,老舍应周总理之邀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但因为手术和路上周折耽误了行程,错过开国大典,作协和文联暂时没有相应的职务安排,周总理就暂时把老舍安置在北京饭店。在这段时间,也就是1950年至1952年期间,老舍等于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干,先是帮侯宝林等相声演员改编了《文章会》《维生素》《地理图》等新时代相声,接着又给剧团创作了第一部北京曲剧作品《柳树井》,讴歌当时新颁布的婚姻法,并给青艺写了话剧《方珍珠》,给人艺创作了话剧《龙须沟》。由此,老舍先生成为我国唯一享有“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艺术家。老舍对曲艺的贡献也赢得了艺人们的尊重,侯宝林视老舍先生为自己的老师和恩人,每年的大年初一,一大早就会去老舍先生家里拜年,一直坚持了许多年……
孙东兴说舒乙先生曾多次讲过,老舍先生关心曲艺和北京曲剧的发展,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社会上文盲较多,看不懂小说,因此用文学推动社会进步遇到了不小的阻碍,所以老舍先生就想,与其这样,还不如多创作老百姓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戏剧、曲艺和相声。

《柳树井》魏喜奎饰招弟

《黄叶红楼》左起:盛国生饰曹雪芹,卢雪文饰史湘云

1986年原群艺社成员前门箭楼合影(孙砚琴、关学曾、魏喜奎、尹福来、曹宝禄、顾荣甫、宋志诚、张润身)
从老舍文章看“北京曲剧”的诞生始末
“把曲艺由旧形式中解放出来”,说的是时代的要求;“用活人表现活人”,说的是艺术的创新;“收到更大的教育效果”,说的是艺术如何为人民服务。
老舍先生在1952年9月号《说说唱唱》上曾撰文记述了“曲剧”作为一个新剧种的诞生始末。从中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对于曲艺的历史和现状堪称了如指掌,同时对曲艺的发展以及“曲剧”如何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有着一套非常成熟明晰的想法和办法。不过,老舍先生并没有把为“曲剧”命名的功劳揽在自己头上,这倒也符合先生一贯的作风,他在文章开篇即写道:“‘曲剧’是个新名字。北京在解放后才有了‘曲剧’。‘曲剧’是用民间曲艺的各种曲牌子与腔调来表演歌剧的。有的歌剧剧本附有乐谱,有的歌剧剧本只有歌词没有乐谱。北京的曲艺艺人对上述的两种歌剧剧本都用自己唱惯了的牌子与腔调去表演。他们管这种剧叫做‘曲剧’”。
那么老舍到底为“北京曲剧”做了哪些贡献,使他被几代曲剧人如此念念不忘?
笔者认为,老舍先生在文章中揭示并论述了“北京曲剧”作为一个剧种诞生的历史必然及其产生的文化和生活土壤,同时从艺术和时代的高度为“北京曲剧”的发展和繁荣指明了方向。
老舍先生在文章中梳理了“曲剧”诞生前的历史脉络,“在三四十年前,曲艺在北京极盛行的时候,‘曲剧’已经有了萌芽。那时候,就已经有了拆唱快书、拆唱单弦牌子曲和彩唱莲花落。拆唱快书是由两个艺人拆唱一段快书,他们还是唱原词,不过是由两个人分开了唱。假若他们唱的是《草船借箭》,就由一位艺人演孔明,另一位艺人充鲁肃。这样的拆唱还没有戏剧的形式,因为除了二人彼此唱和,并不化装,也没有多少身段,只是角色分担显着更火炽,两条不同的嗓音也多少能使角色的语言更明确一些。拆唱牌子曲就比拆唱快书更进了一步,一个故事可以由三四个人拆唱。比如唱《翠屏山》,就可以由艺人们分扮杨雄、石秀、潘巧云与迎儿等。他们也化装,虽然他们的化装很简单,可是到底有了一点戏剧的气氛。他们的乐器在‘拆唱’的时候也增加了一些。这种演唱与方法还不能就算作戏剧,因为演员们都站在一张桌子后面,手中还敲打着乐器,所以不能自由地动作。这种办法,只能教观众一目了然地认识不同的角色,或者也更多了解一点人物的身份与性格。除此以外,并不比原来的形式增加多少戏剧性。彩唱莲花落就比拆唱单弦又多了一些戏剧气氛,演员增多了,都有简单的化装,而且在舞台上自由地活动。可惜,他们所表演的故事反倒比拆唱单弦更简单,所唱的腔调也很单调。这种‘曲剧’虽然像戏剧化了的曲艺,可是并没把曲艺的长处尽量地发挥出来。这种演法是采用曲艺中某一个调子重复地歌唱,不像是由复杂的民间曲艺发展出来的。后来另有一种类似文明戏的小歌剧,虽然由曲艺艺人表演,可是他们并不采取曲艺的唱法与腔调。他们投降给半话剧半京戏掺和起来的文明戏。这,不能算作‘曲剧’,就不多谈。解放后,北京曲艺界的艺人普遍地争取演唱配合政治任务的新曲子,同时也想突破旧形式,把曲艺由旧形式中解放出来。很显然的,由一位艺人演唱一段鼓词或琴书,就不如几个人合演一个故事那样具体、明确,能收到更大的教育效果。一个人唱总是由一位第三者述说几个人的事情,若是几个人合演一个故事,便能张三说张三的话,李四说李四的话,用活人表现活人。因此,艺人们就选用了流行的小歌剧或评戏,由几位艺人扮演出来。他们认真地化装,不像彩唱莲花落那么苟简,也不像文明戏那么半新半旧了。他们也有灯光和布景。从形式上看,他们所演的真像一种歌剧了。”
“把曲艺由旧形式中解放出来”,说的是时代的要求;“用活人表现活人”,说的是艺术的创新;“收到更大的教育效果”,说的是艺术如何为人民服务。然而,这时候的所谓“曲剧”还很难作为一个剧种独立存在,它有些“四不像”。老舍先生写道:“在他们头几次试验的时候,他们对自己原有的曲艺还没有十分的信心,所以演员们出场下场还用京戏的锣鼓点。他们所唱的腔调也一部分是曲艺,一部分是评剧的唱腔,或别的流行歌调。这样,曲艺虽然戏剧化了,但不完全以曲艺为基础。这种‘曲剧’是话剧、歌剧、京戏、评戏和曲艺掺和起来的东西,有点‘四不像子’。”
由此,老舍先生才创作出《柳树井》,以期通过这部作品进一步规范和定型“曲剧”作为新剧种的样式或程式,他总结道:“后来,他们试演小歌剧《柳树井》,他们才放弃了‘四不像子’的办法,而完全采取了曲艺的腔调。他们把剧中的故事分析了一下,然后按着每一情节的感情,配合适当的曲牌子,上场下场也不要京戏的锣鼓点。在《柳树井》里,他们选用了十四个不同的曲牌子,除了因牌子格式的限制非把原词增减字数不可,其余的他们都很忠诚地按照原词歌唱。这十四个牌子中有一部分是不很合适的,其余的都相当妥当,效果很好。”
至此,正如老舍先生所言:总起来说,“曲剧”的试验基本上是成功的。不过,在上文中老舍先生也指出了不足,并提出了改进的办法:“假若他们能再加工,把歌唱的牌子更用心地选择,牌子曲既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再加以适当的安排,一定会有更好的效果。在歌唱与歌唱之间他们没能用音乐配合演员的动作,这是一个缺点。他们若能用心地选择一些老牌子,来配合演员的动作,就能弥补这个缺点。在演员动作与舞台地位上他们也需要专家帮忙导演。”
文章中,借由“曲剧”老舍还清晰地表达出自己遵循党的文艺理论和路线的文艺观,他在总结“曲剧”的长处时写道:“第一,旧的曲牌子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人民对它们素有好感,用它们来演唱一个故事,很容易被群众接受。第二,各种曲牌子是说唱形式的,说也是唱,唱也是说,很容易教听众听得懂。在这一点上,它很接近评戏,但是比评戏的腔调更美好复杂一些,不像现阶段的评戏那么单调。第三,在评戏里女演员的‘弦儿高’,男演员的嗓音若无训练,就不易跟上,所以在评戏里往往女角突出,男角配搭不上。‘曲剧’中的男女演员都是能够独立地表演某种曲艺的,所以合演‘曲剧’的时候,大家都能发挥所长,不至于配搭不匀。即使嗓音的高低不同,若能巧妙地把曲牌子安排好,嗓高的唱高弦,低的唱低弦,也还不至于显着不谐调。有了上述的三个长处,若再加上音乐的加工和舞台经验,‘曲剧’的确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剧种,而且是由民间文艺发展出来的一个剧种。我想,在目前我们应当尽量地发掘老牌子,利用它们丰富现有的‘曲剧’,然后再逐渐地把具有民族风格的新音乐介绍进来,使它有更好的发展。”
孙东兴说,老舍先生关于北京曲剧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的论述及至今天依然是我们在剧种建设和创新方面的指南和圭臬。“当年《柳树井》的成功上演标志着北京曲剧终于有了定制,扎根于人民之中的老舍先生可以说一手打造了北京曲剧,使得这一从民间文艺发展出来的新剧种焕发出勃勃生机。老舍先生为北京曲剧设想的未来是:用北京的语言、北京的音乐素材创造中国式的民族歌剧。如今我们依然在朝着这一目标而努力!”
北京曲剧由《柳树井》创立剧种
上世纪50年代,北京曲剧可谓红遍大江南北。北京曲剧的一些老艺术家至今还记得1959年3月赴南方巡演的盛况。
《柳树井》这出小型歌剧创作于1951年,是老舍先生为配合“新婚姻法”的宣传而作。全剧的句法基本是对仗工整的鼓词结构,句与句之间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当时的歌剧、京剧、评剧、快板剧、话剧等都在演出《柳树井》,其中以曲艺形式演出的效果最好。根据老舍先生的建议,演员们选用了单弦里的一些曲牌,乐队也有了固定编制,除主奏乐器三弦外,还增加了四胡、二胡、南胡、洋琴、低音胡等,还在表演上增加了不少噱头,在塑造人物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随着《柳树井》的成功上演,一些曲艺艺人相继建起了“实验曲剧团”、“新中国曲剧团”、“新华曲剧团”等演出团体,移植演唱了一批如《罗汉钱》《清宫秘史》《喝面叶》等新的曲剧剧目。1953年,“群艺社”集中了北京戏剧界编剧、导演、音乐、舞美等各方面艺术力量,排演了根据话剧《妇女代表》改编的曲剧《张桂蓉》,参加了1954年举行的北京市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得剧本、导演、演员、音乐、舞美等多项奖励。北京曲剧作为北京地方戏的地位得到更广泛的肯定和确认。为了使曲剧这个新兴剧种健康发展,一批曲艺界、音乐界和话剧界人士刘吉典、关士杰、孙砚琴、李宝岩、韩德福、王素稔、刘书芳、于真等于50年代先后投身到曲剧队伍中来,同曹宝禄、魏喜奎、顾荣甫等曲剧创始人一起为曲剧的奠基、创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第一代北京曲剧艺术家的培养和带动下,又一批北京曲剧事业的后继者成长起来,创作改编并积累了一批代表性剧目,如《杨乃武与小白菜》《啼笑因缘》《珍妃泪》《少年天子》等。其中,《杨乃武与小白菜》《箭杆河边》《珍妃泪》等被摄成戏曲艺术片,《少年天子》入选文化部举办的第二届中国艺术节演出剧目。这些剧目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上世纪50年代,北京曲剧可谓红遍大江南北。北京曲剧的一些老艺术家至今还记得1959年3月赴南方巡演的盛况,本来带了八个戏,结果一个《杨乃武与小白菜》就火得不得了,每到一站观众都要求加演,可下一站观众又不干了,因为门票早已预售一空,不能改期。外地观众憋着劲想看有北京特色的戏曲,欣赏有北京韵味的表演。这一趟巡演,他们途经四个省、十一个城市,让北京曲剧名满天下……
“文革”期间,北京曲剧也处于停演状态。1973年为培养曲艺、北京曲剧的后继人才,举办了演员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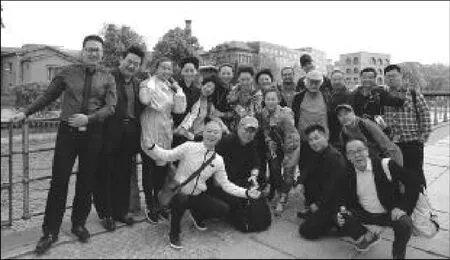
2017年9月北京曲剧赴德国柏林中国文化节演出《烟壶》
“团小心大”:小剧团的大目标
2017年,北京曲剧第一次走出国门:《烟壶》赴德国演出两场;《黄叶红楼》在莫斯科国立青年剧院、圣彼得堡国立喜剧院各演出两场,均产生轰动效应。
孙东兴介绍说,自剧种诞生以来,北京曲剧立足单弦牌子曲、曲艺说唱音乐的基础上,深深扎根老北京文化并一路发展、走向繁荣。上世纪80年代,北京曲剧创排了《珍妃泪》(讲述戊戌变法中光绪与珍妃的故事)、《少年天子》(讲述福临与乌云珠的故事),两剧目题材均是表现京味儿文化中的宫廷文化,与构成北京曲剧声腔音乐的单弦牌子曲的风格相契合,更相得益彰地呈现于舞台之上。北京曲剧表现京味儿中的‘宫廷文化’得到了业界、观众的认可。随后,90年代至今的二十余年里,北京曲剧创排、复排演出了一系列的京味儿题材剧目,如《烟壶》(根据邓友梅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以及由老舍同名文学作品改编的北京曲剧《骆驼祥子》《方珍珠》《龙须沟》《茶馆》《四世同堂》《正红旗下》。这些剧目,让北京曲剧在90年代重获动力,重归大众视野;这些剧目走遍我国大江南北,荣膺各类戏剧奖项;这些剧目将“京味儿”的剧种特色得以强调、彰显,在广大观众中成就北京曲剧“纯正京味儿”的口碑。
北京市曲剧团人人会讲这样一段“纯正京味儿”的顺口溜,从中足以见出“北京曲剧人”对北京曲剧的爱之深——“作为地方戏的北京曲剧,说的是纯正的北京话儿,唱的是北京的音儿,演的是皇城根下北京人儿,讲的是发生在北京城里的事儿,而浓郁的京味儿更是北京曲剧离不了的根儿!”
爱之深,更兼责之切。北京市曲剧团自改制以来,在团长孙东兴带领下真正让北京曲剧焕发出了新的时代光彩,可谓再度辉煌。仅以2017年为例,全年共演出450余场,观众人数20余万人次。其中公益性演出300余场,经营性演出近150场。与2016年相比,以北京曲剧为主的艺术生产和创作有了较大提升。同时,近年来剧团以“我爱北京曲剧”为艺术传播品牌与北京市各大中小学建立起战略合作关系。仅2017年就授课956节,内容不断丰富,授课教材也编制出不同版本,20余名剧团骨干参与教学授课,辐射中小学生1500名。
孙东兴说别看我们剧团规模不大,而且目前依然是“无团址、无排练厅、无剧场”,但我们“团小心大”,秉承老舍先生、魏喜奎先生等前辈大师的苦心孤诣和艺术风范,又乘着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东风,更兼单一剧种单一剧团的独特优势,未来必将成为一张独具异彩的北京文化名片。北京市曲剧团2017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北京曲剧第一次走出国门:《烟壶》赴德国演出两场;《黄叶红楼》在莫斯科国立青年剧院、圣彼得堡国立喜剧院各演出两场,均产生轰动效应,赢得国内外一致好评。《黄叶红楼》曾获得2015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及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优秀剧目奖。提及《黄叶红楼》在俄罗斯演出时的盛况,孙东兴说:“俄罗斯是戏剧大国,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最初关于场地、售票等事项的确定也有许多周折,后来演出时几乎满座,简直是一票难求,而且九成以上是俄罗斯观众。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演出后专门拍电报,向国内传回这一中俄文化交流的盛况。”

孙团长工作照

2017年5月22日《烟壶》第二场演于出海军上将剧场

剧团排练场景
传承之重:增强新生代演员的归属感
在名演员的培养和文化传承方面,北京市曲剧团近些年的成绩亦是有目共睹。魏喜奎、孙砚琴等老一代艺术家是北京曲剧的创始人。甄莹、许娣、张绍荣、孙宁等中年一代为北京曲剧新时期的代表。
在京味儿文化、京味儿戏剧领域,以及围绕老舍先生文学作品的舞台艺术创作方面,北京曲剧与北京市曲剧团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国内应该说是首屈一指的。
在名演员的培养和文化传承方面,北京市曲剧团近些年的成绩亦是有目共睹。魏喜奎、孙砚琴等老一代艺术家是北京曲剧的创始人。甄莹、许娣、张绍荣、孙宁等中年一代为北京曲剧新时期的代表。以郭曾蕊、李相岿、李永德为代表的2003年和以宋洁、彭岩亮、汪鹏、胡优为代表的2008年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北京曲剧大学本科生为北京曲剧的新生代。孙东兴对这批“新生代”演员放手使用,敢压重担、敢(让他们))挑大梁,从而使他们快速成长起来,个个独当一面、一专多能。
许娣、张绍荣曾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孙宁获文化部“文华表演奖”;甄莹获北京市首届“金菊花奖”……近年来,北京市曲剧团的创演剧目屡获殊荣,其中:《烟壶》获中宣部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第六届“文华新剧目奖”、第三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剧目金奖;《龙须沟》获文化部第八届“文华新剧目奖”、北京市委宣传部“十个一工程奖”;《正红旗下》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剧目提名奖”、第五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剧目金奖;《歌唱》获北京市第七届文学艺术奖;《黄叶红楼》获得2015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优秀剧目奖、入选北京市2015年度第二批文化精品工程重点项目。2017年《箭杆河边的新故事之十不闲传奇》荣获“第十五届中国人口文华奖组委会特别奖”。剧团于1997年、2000年、2013年三度携《杨乃武与小白菜》《烟壶》《龙须沟》《茶馆》《四世同堂》《正红旗下》《骆驼祥子》赴台湾演出。
北京曲剧以清代、近现代北京人生活为剧本创作题材,以北京的京味音韵为依托,确立了以代表京味特点的单弦牌子曲为唱腔的基调,吸收大鼓及民歌小曲,创造并形成了具有浓郁北京韵味的独特唱腔音乐。唱腔委婉动听、旋律优美、吐字清晰。北京曲剧的台词在普通话的基础上,以北京语言的声、韵、调为准,具有浓郁的京腔京味儿。北京曲剧的表演风格是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通俗易懂、京味儿浓郁;表演朴实、演唱清晰、说唱结合、韵律独特。
北京市曲剧团在1962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评为“北京市红旗单位”;1989年被国家财政部和文化部评为“全国以文补文先进单位”;1996年、1998、2008、2012-2014年四度被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评为“首都文明单位”;2006年、2009两度被北京市厂务公开协调小组评为“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2012年,按照中宣部、文化部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北京市曲剧团正式转制为集文艺创作、表演和文艺培训为一体的国有独资企业。2013年底,被文化部确定为“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2014年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
近些年,北京市曲剧团在不断创作改编名人名著作品的同时,还注重原创性、时代性,创作演出了一批舞台作品:《歌唱》《乡约青春》《锅儿挑》《五女拜寿》(2012年);《黄叶红楼》《正南正北一条街》《宝船》(2013年);《歌唱》(2014年新版);《箭杆河边的新故事之十不闲传奇》《老张的哲学》(话剧)(2015年);《徐悲鸿》《世界就在我眼前》(话剧)(2016年);《木石奇缘》(2017年)。与此同时,“化整为零”“八面出击”,采用灵活的经营和演出方式,深入基层、厂矿、学校、社区,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创造性地推出了“承制剧”“定制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17年,新排原创实验话剧《怀清台》,合作承制话剧《实现-突围》,完成原创北京曲剧《木石奇缘》创排演工作。2018年刚开始,就完成新排原创当代现实题材剧目《花落花又开》创排演工作,以及北京曲剧经典保留剧目《啼笑因缘》重排工作。目前,剧团上下全体演职员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大型原创剧目《翦氏夫人》的排练工作。
在谈到北京曲剧的传承和人才培养时,孙东兴表示:“我们现在主要是积极争取戏曲专项扶持项目,为北京曲剧经典剧目传承做好人才储备工作;再有就是鼓励并支持各专业领域人员进行不间断的进修学习,提升不同岗位的专业化水平,为剧团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奠定基础;同时我们还积极推进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北京曲剧中专班和中国戏曲学院合作招收北京曲剧表演本科班学生的工作。此外在当今环境下,为了传承好北京曲剧,如何留下人才与培养人才其实是同等重要的,有时候甚至更加重要,我们正在想办法增强新生代演员的归属感、成就感,让他们能够安心创作,减轻他们的后顾之忧。”
剧场瓶颈:何日建成老舍艺术剧院
在孙东兴的构想中,“老舍艺术剧院”不仅是艺术剧院的概念,它还应当成为一座以北京曲剧演出为主,集京味文化展示、会议展览、艺术衍生品展卖、讲座培训、旅游休闲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化服务设施。
笔者第二次赴北京市曲剧团采访那天,一进门,正听见孙团长在为剧团一位演员的伤病而四处托人……打了几通电话又安排了专人去协调、看望,总算是处理完了,他松了一口气,擦了擦额头上细密的汗珠,连声向我道歉“让您久等了”,之后坐在我对面一把老旧的椅子上,略显疲惫却又精神抖擞地聊起建设“老舍艺术剧院”的构想,他说这是几代北京曲剧人的梦想。
北京曲剧近年虽然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获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面对“无团址、无排练厅、无剧场”的“三无”状况,剧种的传承发展遭遇到日益严峻的“剧场瓶颈”问题。
孙东兴不无忧虑地说:“我们长期租借排练场地,这无疑也增加了艺术生产的成本。由于没有固定的演出剧场,观众想看北京曲剧没地儿去。目前,北京曲剧拥有上万人的注册会员。但我们苦于没有自有剧场,全年的演出大部分集中在社区、校园以及京郊乡村,因此造成了北京曲剧想在北京市区演出而无剧场,观众想在北京市区看北京曲剧而没地儿看的尴尬局面。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剧场,就可以提前一年或更早的时间来规划、安排演出。同时根据各大节庆,针对不同观众而细化剧目定位,策划不同特点的‘北京曲剧演出季’,可以月月演、半月演,既给年轻演员提供了丰富的舞台实践机会,又能培养观众观看北京曲剧的习惯……”
在孙东兴的构想中,“老舍艺术剧院”不仅是艺术剧院的概念,它还应当成为一座以北京曲剧演出为主,集京味文化展示、会议展览、艺术衍生品展卖、讲座培训、旅游休闲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化服务设施。具有浓郁京味儿的北京曲剧常年唱响在“老舍艺术剧院”,剧院亦因北京曲剧而散发出浓郁的京味儿,那将是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下新时代北京文化的又一张亮眼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