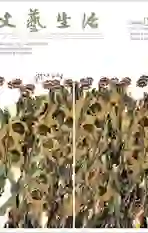简谈汪曾祺小说中的“现代性”
2018-07-23马贺丹
马贺丹
摘要:我们谈论汪曾祺时,视角往往着眼于“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可是我们在审视汪曾祺传统一面的时候,也要注意到他在传统背后的现代性面孔。本文就汪曾祺“最后一个”系列中的内容与文体两方面,剖析汪曾祺传统背后的现代性。
关键词:汪曾祺;审美现代性;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24-0010-01
一、內容中的“审美现代性”
对于“现代性”(modernity),我们不妨按照马泰·卡林内斯库曾对此作出的解释,“是资本主义带来的那场所向披靡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的产物——与作为一个美学观念上的现代性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分裂”。
美学观念上的现代性,对秉承进步学说、实用主义等价值观的资产阶级现代性是厌恶的,同时也是对之进行激烈反叛的。它是一种产生于一般的现代性进程中的现代性,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反观中国,“小说界”革命后,文学/小说就承担了的历史改革的重任。在整个现当代文学的脉络里,始终用实用主义鞭策着文学,我们在塑造着有益于时代的经典,张扬着“为人生而艺术”的基调。
回到汪曾祺身上,汪曾祺笔下出现了一系列“最后一个”的形象:最后一个羊倌老九、最后一个懂礼俗的吕虎臣,以及最后掌握孵化绝技的“名家”。他们是时代的缩影,同时也是正是在消逝的经典。我们从汪曾祺的笔下的“最后一个”系列中看到,时代的车轮高歌挺进,并不是张扬着文明进步与理性崇拜的,而是以牺牲了美好的市井生活为代价的。时代的滚滚洪流下,是“美”的流离失所,在不断地进步中,旧有的宁静和谐是被打破了的。
作者描写和谐被打破,将五行八作的人群在历史浪潮的席卷前的“朝不保夕”具象化,在美好的世界消失前,只留下众多悲剧的“最后一个”。汪曾祺的“最后一个”系列,所体现出的是“审美的现代性”,是与与文明进步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审美现代性。
同样的,当我们在讨论汪曾祺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作为中国传统民俗的代言人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注意到这种民俗的体现,是通过种种“最后一个”的悲剧系列完成的。他在代言传统的同时,却也在消解着那些日薄西山的传统。
换言之,汪曾祺的“最后一个”系列不仅解构了崇尚理性的“资产阶级现代性”,表现了对先前审美性让步于实用性的抗争,同时也在描写传统一代的覆灭中完成了自己的双重解构。
二、文体上的现代性
汪曾祺的现代性还体现在文体上面。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常是旁逸斜出,一笔泼开恣意纵深。这种独异的文体在1949年后那个树立典型的文学中显得尤为怪异。这种难以结构情节和塑造人物的散文化小说是对主流的反叛,其背后所体现的是现代意识的勃发,张扬的是“审美现代性”。
同时,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汪曾祺的小说。“小说”这一概念,中国古已有之,然而现代社会当我们再提及小说时,脑海中最先想到的却非中国的传奇或话本,而是西方的现代小说,尤其在八十年代前后,小说是如前文所述的有典型人物、有情节和阶级。
自“小说界”革命后,小说承担起“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后。为了适应历史的律动,小说地位上升,小说=现代这一概念深入人心,以至于中国文坛上小说几乎一统江山。正如柄谷行人所说的“文学”乃是一个十足的现代性装置,或者说文学同现代属于共生的关系,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小说便等于文学。
可是如果我们反观中国古代的文体——“诗”、“文”两大类型中,“文”的类型可谓源远流长。从曹丕《典论·论文》将“文”区分为“四科八体”后,“文”的类型就已经被建构起来了。
从《文赋》与《文心雕龙》对“文”的划分中,可见中国“文”的类型是有着历史渊源与逻辑推演的关于文学活动的秩序。可是现今“文”早已不复出焉,在小说/文学的冲击下,强大的“文”的传统已被吞噬殆尽,以至如今只有文学家而无文章家。
所以面对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我们是否可以说汪曾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重拾了“文”的一脉,他在散文化小说中仍留有清晰地自我观念,有着“讲故事”的清醒意识。旁逸斜出的散文化小说背后,一直有着作者这位“说书人”的形象。可以说汪曾祺是在用中国传统的“文”作为对小说的对抗,打破了小说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
所以在小说与现代性共生的文坛中,汪曾祺正试图用这种独异的文体终结二者的共谋关系,换句话说,即是在“现代性的规限内反现代”,是“反现代的现代性”。
贾平凹曾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当我们在不断地阐述着汪曾祺传统的一面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他背后多维的现代性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