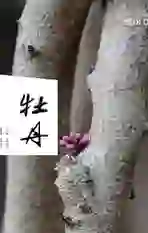从弗洛伊德理论角度看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中女性人物的悲剧命运
2018-07-22周倩
周倩
《寂寞的十七岁》是白先勇创作的11个短篇小说合集,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些鲜明生动的女性人物。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无一例外地拥有悲剧命运。本文采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解读《寂寞的十七岁》中女性人物的命运悲剧,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焦虑理论等角度入手分析造成小说中女性人物命运悲剧的原因并探究白先勇在人物塑造时所受弗洛伊德心理哲学的影响。
被誉为短篇小说创作奇才的白先勇在其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从备受传统压抑的金大奶奶,到为情所伤的玉卿嫂,再到性意识觉醒的福生嫂,都无一例外地拥有悲剧命运。白先勇在创作中通过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哲学理论对女性生命轨迹进行关注,实现对女性内心世界及悲惨命运的探索。
一、以弗洛伊德的三段式人格结构理论对金大奶奶的悲剧命运进行分析
在小说《金大奶奶》中,白先勇塑造了一个寡妇改嫁的悲剧故事。金大奶奶以前的夫家家境富足,丈夫因痨病早逝,留下三十出头无儿无女的她。守寡后,金大奶奶靠着丈夫留下的田产衣食无忧,但她耐不住寂寞,后来改嫁给油腔滑调的金先生,沉浸爱情的金大奶奶原以为找到幸福,便在婚后将田产全部交出。殊不知金先生爱的并不是她,在得到她的财产后非但没有善待,还利用她的财产接二连三猎取其他感情对象,并在婚后对她百般虐待。最后,懦弱却忍无可忍的金大奶奶选择在丈夫的婚宴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三层,分别是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人格发展阶段的最低一级,代表了人本能冲动的力量,并遵循“唯乐原则”;超我是人格中代表理想、文明的部分,是个体成长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及社会文化价值观而形成的;自我源于本我却又接受超我的刺激,在满足本我冲动的同时又遵守超我的规范,一旦三者关系失衡就会导致人格失常。故事中的金大奶奶仍旧“缠着小脚,走起路来,左一拐、右一拐”,对金大先生接二连三纳妾毫无话语权,在丧夫后勇敢追求幸福却被金家人称作“很不体面的女人”,被金大先生讽刺为“老娼妇”。因此,生活在父权社会的金大奶奶,她的“超我”人格是遵循封建礼教,深受男尊女卑思想影响的。然而,金大奶奶在丧夫后大胆追求爱情,甚至在婚后毫无保留将所有财产交出,对泼辣跋扈的二房言语和精神上的侮辱选择忍气吞声,即使受到金家上下精神和身体的虐待,“每天仍旧在脸上涂着一层厚厚的雪花膏,描上一对弯弯的假眉”,仍旧会在金大先生带女戏子来家里吃饭时吃醋。不难看出,金大奶奶的“本我”人格是善良的,是渴望爱情且深爱着金大先生的。
金大奶奶的命运悲剧正是来源于此,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她被迫对金大先生的感情欺骗保持沉默,内心善良的她选择压抑愤怒,对金家上下的精神虐待逆来顺受。如此,金大奶奶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她的“自我”在情感上备受压抑,却又迫于封建礼教束缚不能对金大先生的不专一明确表达她的真实感情;她在身体和精神上备受屈辱,却又因内心善良无法以牙还牙地反抗,所有壓抑的情绪无法找到发泄的出口。最后,白先勇对金大奶奶的命运安排是合理的,这个既受封建世俗伦理践踏又隐忍善良的“自我”终于选择在丈夫婚礼当天以生命为代价结束了一切,唯有这样才能解决金大奶奶“超我”和“自我”的冲突,从情感困境中挣脱。
二、以弗洛伊德的焦虑论对玉卿嫂的悲剧命运进行分析
白先勇在小说《玉卿嫂》中描写了一段孽缘。面容姣好的玉卿嫂是体面人家的少奶奶,因丈夫抽烟片死了家道中落,婆家容不下才迫于生计出来做佣人。在主人家她一直温柔少语,看似无可挑剔、恪守妇道的寡妇却在外租房养着“干弟弟”庆生,她近乎疯狂地爱着庆生,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倾注所有的感情,在庆生移情别恋后,无法接受背叛的玉卿嫂选择结束了她和情人的生命。
弗洛伊德根据焦虑产生的根源和性质的不同,将焦虑分为三种,即现实性焦虑、神经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现实性焦虑来自于外部世界的真实事件,被自我所感知;神经性焦虑产生于自我;道德性焦虑是意识的呼声,警告我们什么是不合适的。焦虑过度是病理性的。玉卿嫂在丧夫不久后便大胆冲出传统道德的束缚,与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庆生相恋。迫于父权社会的规范,她不敢公开自己的恋情。每次与情郎见面只能对外称回婆家一趟,在偶然被主人家小少爷撞破时,她也只敢以“干弟弟”相称。为了捍卫自己在父权社会自由爱人的权利,玉卿嫂变成了两个“我”,一个是在主人家做工的“平常只穿些素净的、不是白就是黑”的端庄文静的“寡婆子”;一个是穿“一件枣红束腰的棉滚身,一双松花绿的绣花鞋儿……搽了些香粉”内心激情狂热的“玉姐”。因此,封建伦理的压迫和与庆生相处时的偷偷摸摸造成了玉卿嫂的道德性焦虑。
年龄上的差距让玉卿嫂对与庆生的感情缺乏安全感,虽然她事事替庆生想得周全,将全部情感都投入其中,积极为两人未来规划,嘴里说着“我也不敢望你对我怎么好法子,只要你明白我这份心意”,但同时她又“一径想狠狠地管住庆生,好像恨不得拿条绳子把他拴在她裤腰带上”。年龄的悬殊让玉卿嫂知道自己付出的爱不能奢望回报,但她爱得痴情却又希望将对方完全占有,感情中的患得患失导致玉卿嫂的神经性焦虑。在这段感情中,爱得痴狂的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份爱或许对庆生来说是种负担。
庆生在与小少爷的一次聊天中提及他与玉姐的相识,“他早没了爹娘,靠一个远房舅舅过活,后来他得了痨病,人家把他逼了出来,幸亏遇着玉姐才接济了他”。对庆生来说,比起情人,玉姐更多是恩人。面对恩人的感情,庆生一直附和着,直到遇到真正心仪的对象,他再也不愿忍受情感羁绊,恳求玉姐:“我求求你,不要再来抓死我了,我受不了,你放了我吧……”庆生的背叛终于坐实玉卿嫂长久的担忧,残酷的事实造成了玉卿嫂现实的焦虑。这段虐恋中,玉卿嫂既想遵从父权社会规范,又想要忠实于内心情感,在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后她唯一精神情感寄托的庆生却移情别恋,这一切让她深陷焦虑情绪无法自拔,终于在一个寒冷的黑夜里,白先勇让她手刃情人后自杀,唯有这样她和他才能挣脱封建世俗,他才会永远只属于她,她的所有焦虑才会在生命结束的一瞬间戛然而止。
三、以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对福生嫂的悲剧命运进行分析
《闷雷》中的福生嫂是广西桂林军训部对面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她虽自幼丧母,但对日子毫不含糊。五官端正、眉目清秀的她虽在军训部异性缘颇好,却被父亲擅自做主嫁给一个既无志向又无品貌,还有生理缺陷的马福生。面对毫无生活情趣且有生理缺陷的马福生,长久的情感冷淡和性压抑使福生嫂几乎快忘了自己是个女人,直到遇到马福生的拜把兄弟刘英,她的女性本能终于被他的男子汉气概唤醒,跃跃欲试的她最终没能冲破束缚获得幸福。
弗洛伊德认为性是一种本能,称为力比多,是人不可缺少的内驱力。他强调,性作为一种原始驱动力,对人来说,其价值有二重性,一方面,性力是保证一个生命健康存活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这种原始性力必须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性的合理性既要从社会道德角度,更应从人性角度来审视。小说中,马福生“身子单薄、削肩佝背、细眉小眼,青白的下巴连胡渣都找不到”,有生理缺陷的他为了避免闲话还让福生嫂“装肚子装出来”原本抱养的儿子,为了这些,福生嫂暗地里流了不少泪。日渐麻木的她原本想着凑合罢了,岂料长期压抑的性本能却被马福生的兄弟刘英重新点燃。刘英身材魁梧,比马福生小十来岁,因工作原因搬來与福生家同住。刘英宏伟嘹亮的男人声音、挺拔的军人身姿,豪爽的作风、旷阔的肩膀和铁青的下巴都与马福生形成鲜明对比。充满阳刚之气的刘英让福生嫂对马福生愈发厌恶,然而每每想到刘英,福生嫂就“不禁脸发热,一股微醺醺的感觉从心底泛了起来”。沉睡已久的欲望满满在福生嫂心里发酵,“她害怕看见他的胸膛、他的手臂,可是愈害怕就愈想见他”,沉寂依旧的欲望终于在生日那天一触即发,“这么多年来这天她第一次感到这么需要一个真正的男人给她一点爱抚摸”。然而就在心中欲火正要燃烧之际,福生嫂却头晕目眩害怕得全身发抖,踉踉跄跄跑回房间锁上大门。这一锁,福生嫂锁上的不仅仅是自己一发不可收拾的性本能,她还锁上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内心欲望受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良心压抑,长期的性苦闷最终导致福生嫂丧失追求幸福的勇气。
白先勇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中的几位女性人物虽人生经历大相径庭,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面对残酷的现实都曾努力抗争,最终却都难逃悲剧命运。创作中,白先勇对女性人物心理刻画都流露着弗洛伊德心理哲学的影响。他在创作中利用弗洛伊德心理哲学对女性人物悲剧命运根源进行揭示,为女性自我意识觉、冲破封建传统束缚、摆脱命运悲剧指明了方向。
(铜仁学院国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