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路痴的“找路”人生
2018-07-19TeraKirk
Tera Ki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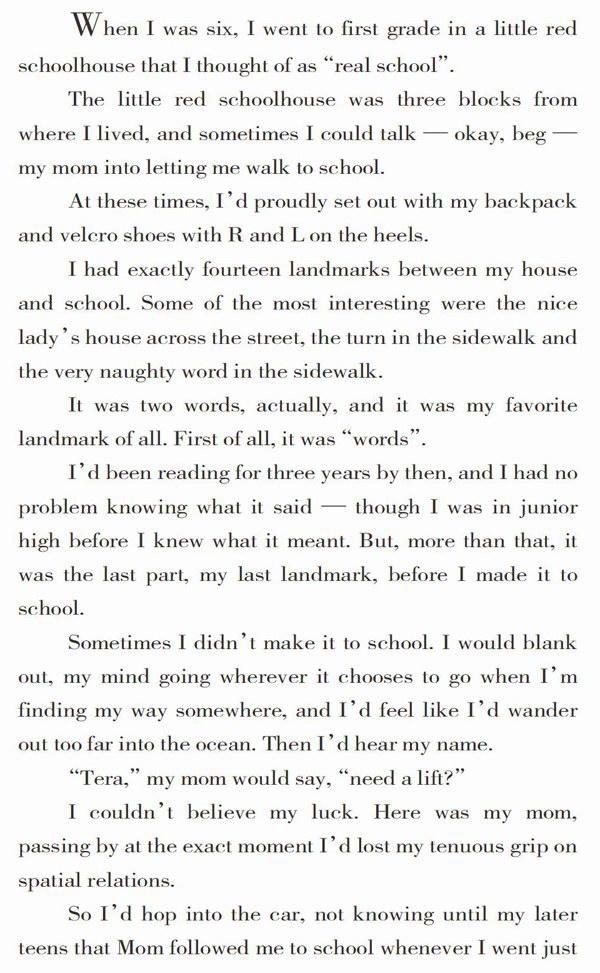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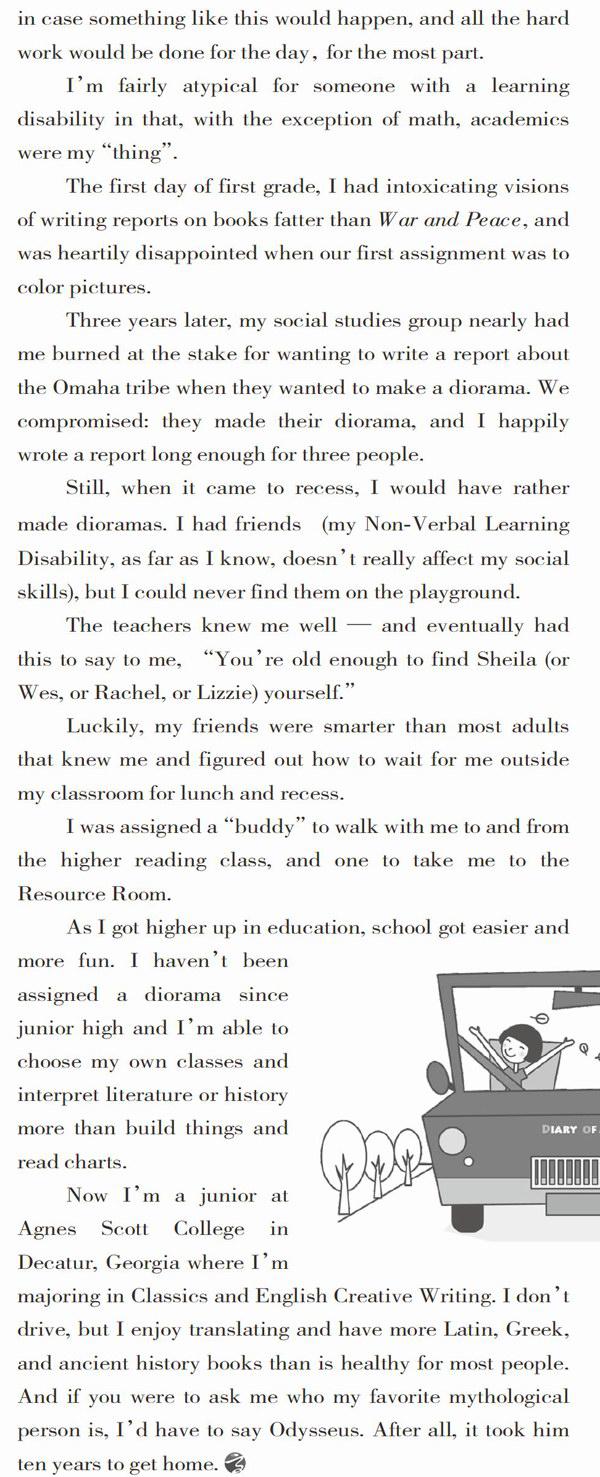
六岁的时候,我去一个很小的红色校舍里上一年级,我觉得那是所“真正的学校”。
那个红色的小校舍和我住的地方隔着三个街区。有时候,我会说服——好吧,是央求——妈妈让我走路去上学。
在那些日子里,我会骄傲地背着双肩包出发,脚上穿着一双魔术贴童鞋,鞋跟上还标记着“左”和“右”(编注:作者是一个非语言学习障碍患者,这类人群在语言上有优势.但可能在视觉空间和社交技巧上有障碍)。
在家和学校之间,我有不多不少14个地标。其中最有趣的几个是:街道对面的好心太太家,人行道的拐弯处以及路边人行道上出现的那个非常不文明的词语。
实际上,那是两个单词,是我最喜欢的地标。首先,那可是“词语”呀。
那时我已经学习阅读三年了,认出这两个词毫不费力——尽管我在上初中后才了解它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是这段路的最后一截,是我上学路上的最后一个地标。
有时候,我没能走到学校。我的大脑会一片空白,当我在某个地方找路的时候,我的思绪却随心所欲地飘荡,我会觉得自己游荡得太远了,到了汪洋大海里。接着,我就会听到有人叫我。
“特拉,”我的妈妈会说,“需要载你一程吗?”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竟然这么好。妈妈就在这里,就在我失去对空间关系的微弱把握时,她恰好从这里经过。
于是我会跳上妈妈的车,然后一天中所有的困难部分就完成了,多数时候是如此。直到十几岁时,我才知道,妈妈在我每次步行去学校的时候都会跟着我,以防类似的事情发生。
我差不多是一个非典型的学习障碍患者,因为除了数学,学术都是我的“菜”。
一年级的第一天,我还兴奋地幻想着能为比《战争与和平》还要厚的书写写读书报告,所以得知我们的第一个作业是给图片涂色时,我打心眼里感到失望。
三年以后,我的社会学习小组差点儿严厉地惩罚我,因为我想写一个有关奥马哈部落的报告,而他们想做一个立体模型。我们各让了一步:他们做他们的立体模型,我开心地写了一份报告,字数足够三个人的作业要求了。
不过,课间休息时,我宁愿去做立体模型也不想出去。我有朋友(据我所知,我的非语言学习障碍并不会真的影响我的社交能力),但我在操场上从来找不到他们。
老师们非常了解我,最后他们对我说:“你都这么大了,可以自己去找希拉(或韦斯,或蕾切尔,或莉齐)了。”
幸运的是,我的朋友们比多数认识我的成年人都要聪明,他们知道要怎么在教室外面等着我一起去吃午饭或度过课间休息时间。
我被分配给了一位“哥们儿”,他和我一起走路去上高级阅读课,下课后一起回来。还有一个哥们儿会带我去资源教室。
随着年级的增长,上学变得更容易也更有趣了。自初中起,老师就再没给我留过立体模型的作业,而我也可以自己选课,自己论述文学或历史,而不是建构东西或去看图表。
现在,我是位于乔治亚州迪凯特的阿格尼斯斯科特学院大三的学生了。我在这里主修古典文学和英语创意写作。我不开车,但是,我享受翻译,比多数人阅读更多有关拉丁語、希腊语和古代历史的书籍。如果你问我最喜欢的神话人物是谁,我一定会说是奥德修斯。毕竟,他用了十年时间才回到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