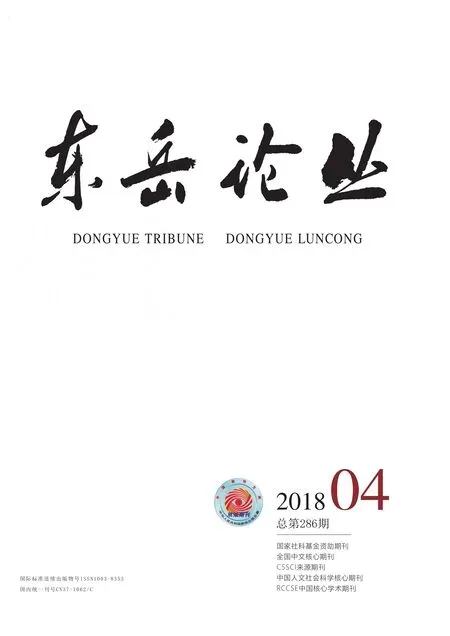论肯定性行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以美国实践为考察对象
2018-07-13齐延平
姚 天,齐延平
(1.中国政法大学 人权研究院,北京 100088;2.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是指从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出发,以矫正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对属于特定种族、宗教、性别人群的歧视和消除歧视给特定人群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为打破这种歧视造成的结构性社会分层为目的,在教育和就业上给予被歧视特定人群以优惠待遇的各种项目和计划的总称*关于肯定性行动的定义,国内外相关学者都有自己的总结,这里结合不同专家的意见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此定义借鉴和参考了: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24页。邱小平:《法律的平等保护——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Randall Kennedy,For Discrimination:Race 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e Law,New York:Vintage,2015,p.20.。在美国,一方面,自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发布第10925号行政令要求政府工程的承包商必须采取“肯定性行动”开始,该政策在保障和促进少数族裔平等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肯定性行动给予少数族裔以优惠待遇,与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法律平等保护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导致其自诞生伊始就一直面临着激烈的反对声浪。反向歧视正是肯定性行动所面对的重要反对意见之一,在去年宣判的费雪II案*Fisher v.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136 S.Ct.2198 (2016)该案中所涉及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的肯定性行动项目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合宪。中,白人原告阿比盖尔·费雪就认为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采用的考量申请人种族背景的肯定性行动项目就构成针对白人的反向歧视。在美国甚至也有人直接用反向歧视这个带有强烈政治和社会寓意的名称来称呼肯定性行动*[美]布莱斯特,烈文森等:《宪法的决策过程:案例与材料》,陆符嘉,周青风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76页。。美国学者邓肯认为反向歧视是指基于性别和族裔身份的肯定性行动对白人男性而言的一种歧视,并将其视为“最有感情色彩的反对”*Myrl L.Duncan,“The Fu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A Jurisprudential/Legal Critique”,Harvard Civil Rights-Civil Liberties Law Review,1982,17,no.2:p.533.。作为美国法官判断肯定性行动是否合宪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肯定性行动是否伤害了无辜白人”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和思索的问题。反向歧视尽管也面对着肯定性行动支持者们激烈的挑战和质疑,但是其也并非无本之木,它的背后同样也有理论上的支撑。本文将从三个层次分析肯定性行动反对者提出的反向歧视主张,首先从哲理层面分析反向歧视背后的“道德个人主义”,进而从实体权利角度分析肯定性行动“是否侵犯了公民的应有权利”,再从程序正义的视角分析肯定性行动“是否与美国宪法规定的法律平等保护相左”。尽管反向歧视的主张有合理的一面,但是不能无限夸大,只要相关具体项目满足宪法和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的要求,其就不能被视为是一种针对白人的歧视。换句话讲,不能仅仅因为给少数族裔带来的优惠影响(减少)了白人在高等教育或就业晋升、事业发展中的机会,就将肯定性行动视特别是本文主要涉及的族裔相关的肯定性行动视为不义之举予以彻底封杀。近年来我国自解放后一直实施的少数民族优待政策,在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地区间差距逐步缩小今天同样被部分人士认为存在“反向歧视”之嫌,通过对美国的肯定性行动和其面对的反向歧视的研究,也能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更好的认识我国的少数民族优待政策带来启示。
一、肯定性行动与道德个人主义
补偿正义是开展肯定性行动的重要依据,即由于黑人、印第安人等少数族裔在历史上曾经遭受过严重而系统的种族压迫和歧视,并且这种压迫和歧视的影响和伤害在当下仍未完全消除,以至于少数族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依旧处在较低的水平上,所以应当通过制度化的矫正措施对其给予补偿,以求通过社会利益的回转重建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的平等*See Michel Rosenfeld,Affirmative Action and Justice:A Philosophical and Constitutional Inqui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31.。然而,反向歧视论者认为这使属于白人的利益被夺走并被用于援助那些不值得援助的少数族裔竞争者,无疑就是针对白人的反向歧视,因为这些少数族裔竞争者并非过去制度性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真正受害人,换句话说当代的白人并不是历史上种族歧视和隔离的共犯,因而不应承担补偿责任。正如鲍威尔大法官在巴基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Bakke,438 U.S.265 (1978)联邦最高法院在总体上支持了肯定性行动,但是对肯定性行动提出了更高的合宪性要求,种族因素只可以作为考量的多个因素之一。加州大学在肯定性行动中所采取的配额制,并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中指出的,像原告巴基这样的白人个体不应由于并非他们所引起的错误而受到惩罚。谴责不正义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然而要为此道歉和补偿的责任主体却只能是那些在某种程度上牵涉了这一不义之举的人。
上述这种反对意见并非无稽之谈,其背后有一种强有力的道德观念——“道德个人主义”,这种理念主张“自由就意味着仅仅从属于那些我所自愿承担的责任,我所亏欠别人的任何东西,都是出于某种同意的行为而亏欠”,更直白的讲就是“我的责任仅局限于我自己所承担的”*[美]迈克尔·桑德尔:《公正》,朱慧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这种观念真正的意涵在于个人作为自由而独立的道德主体具有主体性,习俗、传统或继承状态都不是个人的道德责任来源,惟一约束我们的道德来源只能是每一个个体的自由选择。这种观念在近代和当代的公平正义理论之中都能找到理论支撑。近代著名自由主义先驱洛克的思想就是这种观念的早期代表,他认为政府之所以要建立于同意的基础上,是因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个人的政治权力”*[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9页。。康德的思想更加有力地呈现了这种道德个人主义。他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指出,个人想要自由先要在意志上独立于社会欲望和心理欲望之外,即超越各种偏好和欲望,而要成就自由意志就要受制于自己为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罗尔斯在康德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念,在无知之幕背后就社会运行机制作出选择,就是要求个人搁置自己的各种特殊的利益和优势,在选择正义原则之时从现实生活的各种独特的角色和身份中抽离出来,来思考何为公平正义。道德个人主义中那种自由选择的、独立的自我,在罗尔斯看来就是要求“我们不应当试图首先指望独立规定的善来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609页。。从道德个人主义出发,人们从各自特殊身份中脱离出来,去思考政府对黑人奴隶制的道歉和补偿的正义性,就会发现肯定性行动是不道德的和有损白人权益的。因为在这种自由观之下,个体如果有补偿义务的话就必须是建立在一种同意基础之上的义务,而不可能从那种跨越几代人的群体身份中产生义务。在这种自由观之下,罪恶是老一辈的事而非当下一代人的行为,如果没有先前的承诺,就没有为祖先的恶行赎罪的义务,因此当下的美国白人似乎不再肩负补偿和纠正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等罪恶的特殊责任。
道德个人主义除了要将个人从自己的各种特殊背景和身份中抽离之外,其背后还蕴含着另一层诉求——即政府应当在道德上保持中立。在道德个人主义观念中,个体是自由独立的自我,因此需要一个中立的立场,并拒绝在各种道德争议中偏袒任何一方,同时又允许公民自由选择各种价值观的权利。中立型政府和自由选择性的自我理想,是现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特征,更是美国当代政治的显著特征。自大萧条开始许多围绕政府和市场作用的争论,其实都是关于如何使公民更好地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自由地追求自己目的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不管是自由至上主义者还是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都能在道德个人主义找到依靠。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要使每个个体都能够平等地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政府就要保障他们作出真正自由选择所需的物质条件。而对于自由至上主义者而言,即便是为了使每个个体都能选择自己的目的,政府也不能为了部分人的利益去强迫另一部分人,而是“必须小心谨慎的在其公民中保持中立”*[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这种关于政府应当在道德上保持中立的诉求,同样也呈现在反向歧视论者的观点之中。他们认为肯定性行动对他们造成伤害,将政府和公共机构开展的肯定性行动视为在种族平等这个道德议题上对少数族裔的偏袒,是为了少部分人(少数族裔)的利益牺牲了一部分白人(主流群体)的利益。对白人能够作出真正自由选择所需物质条件的保障,因为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优待政策而受到影响。
虽然“反向歧视”论者所依凭的“道德个人主义”有合理之处,但是在肯定性行动的支持者眼中这种个体观念面临着共同体主义的强烈挑战和质疑——这种观念之下的自由选择,即便是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的自由选择,也未必就是一个真正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所需的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在麦金泰尔教授眼中“自我脱离于其社会和历史的角色和状态”是一种道德上的肤浅,因为“我们都是作为特定社会身份的承担者与我们自己的环境打交道的。……这样,我就从我的家庭、我的城邦、我的部落、我的民族的过去中继承了多种多样的债务、遗产、正当的期望和义务。这些构成了我生活中的既定部分、我的道德起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我的生活以道德特殊性。”*[美]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在共同体主义者看来,洛克和康德考虑的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罗尔斯无知之幕背后的原初状态也与洛克式的自然状态相差不大,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当我们需要界定我们的权利义务之时,我们不可能完全从重大的道德争议当中脱身而出而进入“自然状态”。道德个人主义所塑造的个体本身是有问题的,由于其独立于现实中种种独特的角色和身份,被切断了所有构成其生活的依附联系,因而更有可能失去行动权利,而非获得该理论所意欲实现的独立自主。因为道德个人主义中的个体被切断了与现实条件之间的联系,所以不再具有获得现实生活中的应得的所要求的那种“具有深厚的特殊品性的和彻底境况化的自我”*[美]迈克尔·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页。,实际上的权利可能遭到损害。

此外,在支持肯定性行动的人看来,那种认为“政府应当在道德上保持中立”的观念说穿了就是一种回避,一种对于道德争论的回避,一种对于什么才是良善生活的回避。道德个人主义者认为在日益多元的现代社会,人们在何为良善的问题上肯定存在不同意见,为了保障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在这种尊重之上的社会协作的顺畅,有必要将个人的道德观念放在一边存而不论。然而在处理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关问题时,完全超脱于各种有关良善生活的观念是不可能的。道德个人主义通过回避人们的道德和宗教理想来处理根本性的政治议题和宪法议题,无异于是对这些议题背后的重要道德问题的冷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是存在问题的。因为相互尊重和社会协作在当今社会是如此重要,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有人做到超越任何利益。林肯在1858年和其政敌道格拉斯的论战中指出,道格拉斯为了维护国家团结而回避奴隶制所引发道德争论的是不能解决实质问题的,因为道格拉斯所要维护的观念的可信性取决于对其声称国家应当保持中立的实质性道德问题(即奴隶制是否正义)的特定回答*See Paul M.Angle,Created Equal,The Complete Lincoln-Douglas Debates of 1858,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p.388-389.。这种对中立性的要求看似是在民主社会中对个体自由的保障,但是其“严重的限制了那些政治争论,尤其是对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政治论证的合法争论。因为民主政治无法长期把一种公共生活从道德目的中抽象出来。在政治商谈缺少道德共鸣的地方,对具有更大意义的公共生活的热望就会表现的让人失望。”*[美]迈克尔·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页、第246页。如果人类在决策重要的公共问题时,非要强装出一种无法实现的中立性,将他们心中各自的道德信念抛于脑后,表面上这似乎展现了宽容和尊重,但实际上只能提供一种缺少关键内容的政治对话,只能使我们的公共生活愈发贫瘠。这种看似的宽容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宽容,如果真的这样,公共生活将会沦为某些极端主义分子的乐土。当今美国和西方社会民粹主义再次抬头,在移民管控、福利分配、难民收容等问题上提出很多极端性意见。比如修建“边境隔离墙”、“把中东难民全部强制遣返”等等,其思想深处与这种中立性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尽管罗尔斯和德沃金*有关德沃金对这种中立性的论述,可参见 [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刘丽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的公平正义理论都呈现了对“中立于各种不同的良善生活观念”的追求,但是这些理论对中立性的追求,为向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提供补偿性救助留下了空间,以求更好地实现社会平等。这与反向歧视论者利用“道德个人主义”来抵制旨在帮助弱势群体(少数族裔)的肯定性行动形成鲜明对比。
二、肯定性行动与应有权利
反向歧视论者声称,在社会竞争中人们有权要求根据其个人的价值来被判断,即根据参与竞争的个体的能力和成就来评判他们的成败,而不依据其种族属性。在他们看来,对个人价值评估不能包含对于个人族裔背景的考量,因为如果少数族裔的特殊身份被视为一种有利的因素得以考量,这对白人而言是一种不利、更是一种伤害。这种主张在1974年得到了道格拉斯大法官的支持,他在德芳尼斯案的异议中指出:“不管他的种族和肤色,德芳尼斯作为一个白人的事实既不应当给他任何带来优势,也不应当给他造成任何不利。无论他属于哪个种族,他都拥有一种在种族中立的态度下使他的申请基于其个人价值被得以考虑的宪法性权利。”*DeFunis v.Odegaard,416 U.S.312 (1974) at 337.该案是肯定性行动进入联邦最高法院的第一案,但是由于该案成为虚拟案件法院并未作出实质性判决。尽管如此,道格拉斯大法官还是单独做出了一个异议意见支持了白人原告德芳尼斯的诉求。德芳尼斯认为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在录取中针对黑人和少数族裔的优惠措施给他造成了伤害,是一种反向歧视。这一论断成为日后反肯定性行动人士的有力武器,并为其他大法官所继承,在后续与肯定性行动相关判决意见中被引用。比如斯卡利亚大法官在其为克洛森案*City of Richmond v.J.A.Croson Co.,488 U.S.469 (1989)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中对肯定性行动的审查开始采用严格审查标准,并且里士满市市政当局在公共建筑合同中的肯定性行动项目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撰写的附随意见中就直接引用并重申了道格拉斯大法官的主张。道格拉斯大法官的主张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力,或许是因为其意见中所暗含的“机会是对那些应得者的奖励”的观念。这种观念在美国深入人心,在政客口中俨然是美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观念真正的源泉在于新教的工作伦理观,即所谓的“努力工作的个人理应获得(be entitled to)其劳动果实”,美国人把这种观念融入到了美国社会的正义观念之中*Myrl L.Duncan,“The Fu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A Jurisprudential/Legal Critique”,Harvard Civil Rights-Civil Liberties Law Review,1982,17,no.2:p.536.。基于这种道德应得的观念,白人认为肯定性行动为了帮助那些不应当获得这些机会的少数族裔申请人,从他们手中骗走了他们应得的赏罚,因此自己的权利遭到了侵犯。他们相信在传统的择优录取标准下,如果他们比其他竞争者做得更好,公平性的要求会使他们在分配录取机会时获得优势。反向歧视论者坚定不移地认为他们拥有一种权利,即在社会竞争之中被公共机构或政府基于能力和成就而非族裔背景等不相关因素来评判的权利。
尽管“反向歧视”论者为他们所受的伤害提供了事实上的证据和道德理论上的支撑,但是这也并不能充分证明肯定性行动就一定是侵犯个人权利的“反向歧视”。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就坚定地认为肯定性行动政策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他认为任何一个申请者,都不能享有类似道格拉斯大法官在德芳尼斯案异议中所主张的那种权利,即“高校应以一种首先对某些特殊才能(比如学术能力、运动才能或艺术成就等等)进行奖励的方式来设定其使命并制定该校的录取政策”,也就是说“没有人从一开始就拥有根据一系列标准被考量的权利”*Ronald Dworkin,“Why Bakke Has No Cas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24,available at: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977/11/10/why-bakke-has-no-case/ 最后访问:2017年5月20日。。在某个高校或公共机构确立了能够推进合法目标的公开标准之后,申请者们才拥有一种根据那种公开标准来判断其是否具备录取资格的标准,只要某人比其他申请人更加满足这些要求其就有资格被录取,若此时其被拒之门外才是不公平的。单方面为高校或用人单位预设使命和目标的权利,和单方面预先为高校或用人单位指定在选拔过程中应当考量哪些价值和因素的权利都不是任何申请人所享有的,因此那些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被考量和评估的“价值”必须是最适合高校或用人单位的发展目标的,而非预先被某一类或个别申请人所设定的*See Richard H.Jr.Fallon,“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from None According to His Race:The Concept of Merit in the Law of Antidiscrimination”,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1980,Vol.60,Issue 4:pp.815-816.。如果一个高校将促进种族融合和团结、推进校园文化多元化以及以前文提到的对于先前种族隔离制度影响的矫正作为其机构使命,那么在评估申请人对于学校实现其目标和使命的作用时,某个申请人的族裔背景是可以被视为一个相关的考察因素的。只要申请者能够对大学实现其社会使命和目标有所贡献,那么对其录取就是正当的。换句话讲,录取并不是为了奖励申请人的某些单独被界定出来的价值或优点。


道德应得之所以不能作为分配正义基础的另一原因在于偶然因素同样具有决定性,一个社会在某一时期所恰好重视的各种特质和才能,在道德上也具有任意性。诚然个人对其所具备的各种才能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利,而这些才能是否能获得利益,供求关系的偶然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偶然性又往往被人们忽视。美国首席大法官每年能赚到二十多万美元*苏永通:《美国大法官赚多少钱》,载《南方周末》网站,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602/,最后访问:2017年5月20日。,而在电影中扮演法官的好莱坞影星年收入一般都是以百万甚至千万来计算的,但是似乎不能说扮演法官的好莱坞影星就应当得到比首席大法官多出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年收入。这样的事实只能说明好莱坞影星们恰巧生在了一个人们乐意在娱乐产业进行投入的社会中,这是一种好的运气而并非他们就应当得到的东西。现代社会看重某些才能和天赋的事实并不是我们行为的结果,假如某人拥有极佳的数学天赋和软件设计才能,却没有生活在现在这样一个科技发达、追求创新的社会,而是生活在一个封建的、尚武的社会或是一个宗教性的、崇尚诸神之力的社会,这个人的才能会给其带来优渥的回报吗?只有在当下的社会竞争确立了其竞赛规则后,个人才有了基于其才能的发挥,对竞赛规则所承诺给予的利益的“合法期望”,要是继续坚持“人们事先就应得一个注重其所拥有的各种才能的社会的话”,无是异于一种错误和自负的表现。
最后,肯定性行动的支持者们认为公立高校和公共机构的使命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以高校为例,在当今日益多元的社会环境下,其存在的使命不仅仅是为了学术的发展和人类科学的进步,其(特别是公立高校)作为公共生活的一个部分,应当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在亚里士多的眼中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的政治,其目的不仅仅是建立一个中立于各种目的权利框架,而是要塑造好公民和培育好品质,以使人们能够发展各自独特的能力和德性,来关心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命运并推动共同善的发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90页。。亚里士多德的这番表述在共同体主义者眼中似乎是当下高校负有推进有益的公共使命的有力注脚。高校录取一名申请者,不仅仅是对其较高学术水准和良好德性的奖励,因为他能顺利完成学术训练并高效完成研究计划,同时也是对其能否有益于共同善的考量。比如其独特的文化背景能够丰富学校的文化,从而使每个师生都受益或者其未来发展能够为社会整体发展做出贡献。高校特别是公立高校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应当承担某些公共使命来推进公共善的发展,毕竟公共生活的目的就是良善生活,而公共善发展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高校把促进种族融合和团结、推进校园的文化多元化这一类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任务作为其使命和目标是符合良善生活的要求的,更何况高校在当下开展肯定性行动时只是把种族作为一个附加因素来评判,并没有把传统的对诸如学习成绩和学术成果等要素的考量彻底抛弃。中国高校招生录取中,面向少数族裔、贫困地区考生的优惠措施可以从上述考量中获得支持性解释。
三、肯定性行动与法律平等保护
反向歧视论者认为,他们受美国联邦宪法保护的平等权被肯定性行动侵犯了,毕竟“法律的平等保护”条款以及民权法案都要求给予包括白人在内的所有人免于歧视的权利。巴基案的原告巴基就认为白人只能申请医学院中的84个录取名额,而少数族裔申请人却可以竞争全部100个(包含肯定性行动项目预留给少数族裔的16个名额)名额,这对白人而言是一种不平等。也有白人原告请专家论证了在相同条件下,肯定性行动赋予了少数族裔相较于白人而言高出数十乃至上百倍的录取概率,并认为这侵犯了白人平等的参与社会竞争的权利*Carol Daugherty Rasnic,“The U.S.Supreme Court On Affirmative Action:Are Some of Us‘More Equal’Than Others? (With Some Comparisons To Post-Good Friday Agreement Police Hiring In Northern Ireland)”,Scholar,2004-2005,Vol.23 Issue.7:p.43.。基于美国传统公平观念中占有重要影响地位的公平待遇原则,他们认为肯定性行动项目考量了与学术能力无关的族裔背景,是对选拔(才)范围内的最合格个体的一种不公正歧视。公平待遇原则在美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要求把公平待遇和平等机会给予每个个体,并且这种观念也渗透在民权运动的最初愿景之中*See Morris B.Abram:“Affirmative Action:Fair Shakers and Social Engineers”,Harvard Law Review,1986,Vol.99,Issue 6:pp.1312-1314.。

然而,如果因某项社会政策而遭受不利的人都感到受到伤害,就说此项社会政策是不公正的和不明智的也是错误的。在传统的择优录取制下由于智力稍差而被淘汰的申请人感受到伤害并不能说明以智力和学术为标准的传统型考核选拔机制是不公平的。一切取决于被伤害的感觉是否产生于某些更为客观的政策特点,即使在感觉不到伤害的情况下,这种特点也可以表明这一政策是不合格的。假设巴基和费雪等白人申请者不认为他们被录取委员会拒绝是一种伤害,他们真的愿意成为某些少数族裔的成员比如非洲裔和拉丁裔吗,当然不会。因为即使在当下这样的民主社会,少数族裔的状况在整体上而言与白人依旧有着较大的差距。去年7月接连发生的两起警察枪击致死非洲裔男子事件,以及今年4月美联航公司殴打亚裔乘客的事件,表明在当下的美国社会少数族裔的权利还是很容易受到侵犯的。换言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伤害甚至侮辱,而在于对于少数族裔的种族歧视只能通过功利主义的考量来做辩解,但是对于将种族纳入录取考量的肯定性行动而言,可以用来辩护的观点不仅有功利主义的考量,还有理想主义的情怀。因为任何证明种族隔离合法性的功利主义观点都十分紧密的和种族偏见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其不能够证明在没有偏见的情况下对这一种族成员的不利影响也是合理的。更何况在民权运动开始之前的年代这种针对与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群体的偏见是广泛渗透在社会之中的,这种偏见使少数族裔申请人个人选择的成功依赖于“其他人对其的估价和批准,而非取决于与其他人的公平竞争”*[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力》,信春鹰,吴玉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页。,这实际上侵犯了黑人作为平等的个体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而肯定性行动不仅没有基于任何种族劣等的偏见,而且可以不依赖于功利主义的视角比如在社会的关键领域中适当增加黑人的比例,仅仅依赖于其所蕴含的理想主义观点得到辩护。那种理想主义观点就是更加平等的社会是一个更美好更值得欲求的社会。在这个理想主义的视角之下,没有任何人作为平等个体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受到侵犯。换句话说,只要一项(优待)政策是出于某种价值目的而有益于社会,而非评价社会当中的人的价值的高低,那么其就是合理的。基于“某个种族可能在本质上比另一种族更有内在价值”——这样一种恶意的偏见,美国高校几十年前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是找不到合理基础的;相反,由于没有涉及任何偏见,同时基于种族的优惠也不是为了侮辱任何人,只是为了促进关键职业和领域中的多元化,并基于黑人或拉丁裔“可能是特殊环境下对社会有益的特征”的理念,肯定性行动是具有合理基础的。此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硬性优待式的肯定性行动项目逐步减少,并且种族因素在肯定性行动中仅仅被作为众多要素中的一个被具体行动项目的开展者所考量,加之即便考虑了种族但是申请者的相关能力和业绩依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能说白人的利益被有意忽视了。巴基和费雪或许认为对他们的拒绝是不公平的,然而他们不能说把拒绝与种族隔离所包含仇恨和藐视等同起来。因为他们在高校招生过程中并不享有“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并且其利益并没有被有意的忽视,所以尽管他们遭遇的挫折值得同情和理解,但是让他们为更加普遍的社会利益让路是合情合理的。
结 语
首先,不能否认的是肯定性行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白人带来了不利影响,但这未必就一定是一种有害的歧视。为了给予少数族裔以优待,白人的机会确实被减少了,但是机会的减少和不利的影响不同于所谓的“反向歧视”,更不是历史上那种针对少数族裔恶意的、系统的种族歧视。美国学者布莱恩·费尔承认肯定性行动会给白人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但他强调“如果能用很小的损害换来更大的社会整体利益,这样的伤害可以被允许”,况且“白人所受到的伤害只不过是对他们有利的优先性和垄断的结束”*Bryan Fair,Notes of a Racial Caste Baby:Color Blindness and the End of Affirmative Actio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7,pp.60-61.。
其次,尽管白人的“反向歧视”主张有事实依据和理论基础,然而这并不能将肯定性行动彻底否定,肯定性行动究竟是否构成“反向歧视”还是需要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从上世纪70年代末联邦最高法院作出针对肯定性行动的首次判决开始,虽然推翻了个别的肯定性行动项目,但是其仍没有在整体上将肯定性行动彻底封杀,只是在不断对实施肯定性行动提出更加细致和严格条件。特别是在2014年的一个不直接涉及具体肯定性行动项目的案件中允许各州通过其本州的宪法修正案来禁止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录取过程中采用肯定性行动后*Schuette v.Coalition to Defend Affirmttive Action,134 S.Ct.1623(2014).,并没有在本文开头提到的费雪II案中彻底终结肯定性行动的合宪性。这似乎表明联邦最高法院承认,虽然肯定性行动的反对者认为肯定性行动和不公正的反向歧视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只要按照最高法院的要求经过精心设计,为了追求最高法院认可的“迫切的公共利益”的肯定性行动项目,在最高法院看来就是符合宪法要求的政策措施而非一种有害的反向歧视。
此外,美国近些年来族裔矛盾时有爆发,并且少数族裔特别是非洲裔和作为主流群体的白人之间依旧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作为一种临时性的优待措施肯定性行动在当下还没到终结的时候。综上笔者认为由于肯定性行动存在侵犯白人群体利益的嫌疑,就将其视为一种应当被宪法完全禁止的不正义的措施是有失公允的。肯定性行动在符合联邦宪法和联邦最高法院要求的情形下,其正义性和合理性是没有必要争论的,而如何更好地设计具体的行动项目,使其在不对白人的合法权益造成过大损害,并在不对传统的个体平等观和机会平等观产生过大冲击的条件下,更好地促进少数族裔乃至整个社会对实质平等的追求,才是真正应当细致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比如如何更好地确定具体项目的受益者范围,一方面这是开展肯定性行动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把不符合获益条件的少数族裔成员,比如来自特别富裕的家庭的黑人学生从项目中排除出去,不仅可以给真正有能力的白人竞争者创造更加平等的竞争环境,也可以避免黑人等少数族裔对肯定性行动产生依赖,促使他们真正地参与并融入到社会竞争当中。
最后,虽然我国对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的确存在“反向歧视”的嫌疑,但是少数民族整体而言相较于汉族仍旧存在差距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偏远的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方面建设依旧落后,落实和推进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仍有必要。以少数民族在高考中的加分为例,虽然加分不公的质疑长期存在,但是与美国高校类似,我国高校和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可以通过更为细致的设计来明确受益者范围,在帮助真正应当得到帮助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同时,杜绝伪造少数民族身份以及高考移民等不公平现象,真正使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只要在今后的执行当中精心布局、细化要求,对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就不会成为反向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