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生涯(1978—2018)
2018-07-12谢桃坊
中国新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是我人生在学术上开花结果和收获的最美好的时期。我出生于1935年,迄今跨越了两个世纪,深感个人的理想——即使它是合理的,而且为之作出艰苦的努力,但只有在国家昌明、经济文化正常发展的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个人的命运是不可能脱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我永远记住1978年,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我个人命运的转折点。
一、理想的人生归宿
我在小学毕业后,于1948年秋父亲送我到刘杲新先生私塾学习,因果新先生的引导而使我产生强烈的渴求知识的愿望。1950年秋,我回老家务农,迅即在农协会担任文教委员,继为成都市工农业余教育学校专任教员,后转入小学任语文与历史教员,1956年以同等学力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国语文系。我志于文学理论批评,准备从事纯学术的研究工作,虽然当时前途渺茫,却仍是我所坚持的理想。但1957年改变了我的政治命运。此后20年的苦难——包括在农村被监督劳动15年,并未泯灭我的初心。1978年8月初,我尚在成都郊区农村时,给金牛区教育局长寄去一封信,希望能为中国新历史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一点贡献。不久,我即到成都圣灯中学任语文教员。这时我已为今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进行准备,因而198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聘研究人员的考试,以助理研究员被录取,1981年3月分配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工作。我终于找到理想的人生归宿。新时期的到来,使我得以走上学术之路,而且很快适应了新的学术发展趋势和新的学术思潮。
初入学术界,我对一切甚感陌生,幸好在西南师范学院学习时已开始搜集宋词研究资料,并有初步研究的心得;然而要使专业研究成果为学术界认可却并非易事,必然找到突破之处。我的第一篇论文《宋代民间词论略》于1981年《贵州社会科学》杂志第3期发表,迅即为人大《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引起词学界的关注。1983年,我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略谈梦窗词与我国传统创作方法》,于《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宋代歌妓考略》,于《文学遗产》杂志发表《张炎词论略》以及其余3篇论文,遂一下在词学界知名。此后的数年间,我皆以研究宋词作家作品为主,同时写有80余篇宋词赏析小文。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体现新时期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社会思潮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反响。自20世纪初年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现代词学研究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经历了吸取世界近代人文学科成果以批判旧传统而创立新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学分析的两个阶段,于80年代进入反思、探索、开拓、创新的新历史时期。新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此背景下中国学术繁荣昌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弘扬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时期之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宋代文学研究开始出现热潮的趋势,它属于一个开发性的学术领域,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和浓厚的兴趣。宋词研究在宋代文学研究中是居于优势地位的,这大大促进了新时期词学研究的发展。当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时,由于社会价值体系的变化,必然引起社會审美理想与审美兴趣的变化。人们面对这样的现实,总是进行着深刻的历史反思,试图重新认识民族的文化传统,以探求新的价值观念。新时期的学者们对固有的艺术观点和方法进行检讨和批判,努力开拓新的学术道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面临怎样对待文学遗产,怎样研究古典文学,怎样建立新的文学史观等重大问题,于是采取以重新评价作家作品为学术的突破口。我在宋词研究方面,以柳永、吴文英和张炎为重点研究对象,重新评价了婉约词在宋词发展中的意义,阐述了词为音乐文学、词为艳科的观点,考察了宋词的社会化过程,申述了“律词”观念在重建词体规范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是我对宋词研究作的一点贡献。
1990年10月,我在桂林参加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的学术研讨会。当时《文学遗产》编辑都预见到90年代将会出现文学史的研究高潮。以什么文学史观、怎样去重写文学史正是学者们最关注的问题。我在会上表示:阐释文学史是表现每个时代的人们对于文学遗产的态度与选择;这是每一个时代文学研究者的权利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历史的阐释是没有终端的,正如历史的无限时间性一样。每一个时代的人只能以自己的尺度、自己的方式来观察历史和重新阐释历史,由此表现民族的文化精神。我顺应重写文学史的潮流,完成了《中国词学史》和《中国市民文学史》,它们至今均出了第三版,成为我的代表性的著作。
谢桃坊作品
我深感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获得了最佳的学术研究条件;因有充裕的时间、丰富的图书资料和宽松自由的环境,保证了专业研究工作的进行。我所从事的专业属于纯学术的基础研究。院领导、科组处和文学所未给我布置其他任务,由我自己选定课题,不进行任何干预,使我能独立地自由地进行研究。他们还支持我参加学术会议与活动。正是由于有了这样好的学术环境与条件,我才取得一些成就,所以社科院是我理想的人生归宿。
二学术新境界的开拓
新历史时期以来的40年,于我是两个发展时间:从1978年重新工作并到四川社科院讫于1998年正是20年;从1998年有幸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迄今又是20年。1952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决议全国各省及中央或大行政区的直属市设置文史研究馆,此时恰值我参加革命工作之时。50年代之初,每当我路过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深知此乃川中名流、社会贤达、文史专家聚集之所,总是怀着敬畏与仰慕的心情;故我能进入文史馆甚感荣幸,由此尚可发挥一点余热以报效国家和社会。在文史馆,我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专家和书画名家相结识,使我的学术视野开阔;而进行的各种地方文化学术的调研考察活动则使我开拓了新的学术境界。我于断断续续致力于词体规范的重建工作而外,将治学重点转到蜀学和国学研究。此两项工作均得到文史馆领导的大力支持。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地方经济文化迅猛发展,地方政府弘扬地方文化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取得显著的效益。在四川逐渐掀起研究巴蜀文化的热潮。“巴蜀文化”本是考古学意义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新时期地方文化研究的学者们遂将它扩展以涵盖四川从远古到现代的历史与文化的地域文化的内容。巴蜀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四川远古的历史文化,将神话传说与新发现的文化遗址联系起来,进行释古的论述;这的确对四川的经济,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及其依据都是经不住学理检验的。袁珂先生是将古巴蜀的传说视为神话的,而现在一些学者却将神话传说附会为信史甚至达到极其荒诞的程度——这是我不赞成的。西蜀的学术历史悠久,在宋代已显示出地域学术的特色,而在近代形成复兴之势,故蜀学很值得研究。已故的著名川籍文史研究专家王利器先生晚年回到四川访友,多次倡导蜀学。四川大学史学家胡昭曦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蜀学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开拓性的工作。我很支持两位先生弘扬蜀学的意见。2002年10月文史馆文史处处长筹划一次学术讨论会,征询我的意见,我建议讨论蜀学。此建议受到隗瀛涛馆长的重视,于12月21日由他主持召开“蜀学讨论会”,文史研究馆馆员及本地文史专家参加会议。我希望创办一个研究蜀学的大型学术专刊,以切实起到弘扬蜀学的作用。2003年7月3日下午,文史馆派我与文史处处长安山前去与西华大学商议共建蜀学研究中心,受到西华大学领导的重视和支持。2003年12月18日,蜀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于西华大学召开,接着又召开了两次学术研讨会。2006年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与西华大学主办的大型学术集刊《蜀学》创刊,由我负责组稿、定稿和编辑,每年出版一辑。到201 1年出版六辑后,西华大学研究蜀学的学者可以独立编辑此刊,我便不负主要责任。至今此刊已出版了十三辑,成为很有特色和影响的学术刊物了。我关于蜀中学者扬雄、苏轼、杨慎、李调元、刘咸忻、吴虞、郭沫若的论文属于蜀学研究,专题的论文则有《古蜀史料辨伪》《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论蜀学的特征》和《蜀都古史辨》。《蜀学》的创办,真正起到了弘扬地域学术的作用,其观念是经得住学理检验的,故得到广大蜀中学者的响应,从而使依托神话传说的古代巴蜀文化观念恢复其原有的性质。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于1993年创刊,标志国学热潮再度在中国兴起。国学的发展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学研究机构不断出现,而且出现世俗化和商业化的倾向。2006年我的词学论文集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后,词学研究可以告一大段落了,遂转向国学研究。在治学方面我有强烈的学科意识,以词学为研究方向;但存在好奇的心理,喜好泛观博览,对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皆有兴趣涉猎。尤其在西南师范学院学习时,奠立了关于传统文化研究的较坚实的基础,故可以投入新的学术领域。学术界对国学性质与对象的理解极为纷繁杂乱,以致令人困惑。我考察20世纪初年兴起的国学运动的历史,将国学研究分为国粹派与新倾向派,以为胡适、傅斯年和顾颉刚等新倾向派倡导的以科学考证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若干狭小学术问题的纯学术研究为国学主流;我极力反对国粹派的文化保守主义。2007年中央文史馆召开国学研讨会,四川省文史馆派我出席,所提交的《论国学》的论文表述了我对国学性质、对象和方法的意见,强调了新倾向派代表的国学运动主流的意义。我的见解可能偏颇而不为多数学者赞同,仅程毅中和赵仁珪先生支持。此文于當年《学术界》第6期发表,继而发表了系列论文,出版的著作有:《四川国学小史》(巴蜀书社,2009年);《国学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国学史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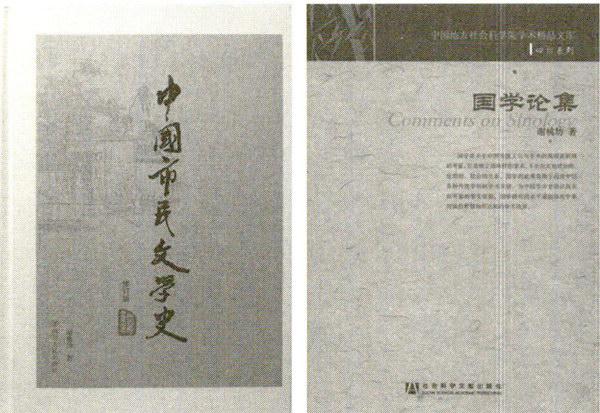
谢桃坊作品
四川社科院于2014年成立国学院,院长是向宝云先生。国学院和国学研究中心这类机构近年在国内蓬勃兴起,但绝大多数是徒有虚名的,甚至成立之后不知道做什么,或者以之作为产生经济效益的工具。向宝云先生曾长期担任院科组处领导,大力支持学者们的科研。我是国学院成员之一。他向我征询关于国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我建议与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合办《国学》集刊。建议得到我院李后强书记和侯水平院长的同意,并由院党委会通过和大力支持。不久,它便以大型纯学术高级国学研究刊物的面貌面世,每集60万字,繁体字横排,印刷装帧精美;以我院和文史馆学者为主要作者,面向全国和海外。我们的目标是将其办成第一流的国学杂志,以弘扬国学,为我省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切实贡献。《国学》集刊于2014年创刊,翌年5月隆重召开发行会,并在《光明日报》刊登目录广告;至今已出版五集,在国内外产生了学术影响。著名的国学家吴光先生认为这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国学研究刊物。现在看来,我们继承和发扬了国学运动新倾向派的传统,坚持了当初纯学术的办刊宗旨,提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但是还做得很不够,还得努力争取赶上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我负责组稿和定稿的工作,主编向宝云负责全面的领导,彭东焕负责具体的编校,赵海海负责编务。我们志同道合,有信心将《国学》办成国内最活跃、最纯正的学术集刊。(遗憾的是此种纯学术的高级的集刊并不为某些科研机构赏识,故最近可能停刊或由其他高校续办下去。)
三 学者的生命之树常绿
在我初到四川社科院时即定下从事纯学术的宗旨,稳步地向着设立的目标前进。为此,我避免卷入人事和世俗的纠纷,不参加集体课题,也不申报课题,不与任何人合写书和论文,最好不参加任何学会,不作任何社会的兼职,努力守愚藏拙,不求虚名,不显示自己,踏实地沉潜地工作。现在我仅是一名普通的学者。我很满足了,因为要成为真正的学者是很不容易的,那已是一种学术高境了。我自认为研究的对象是学术问题,是为学术杂志社和出版社写作的,作品须由它们发表和出版,而服务的对象是广大的读者,成果的评价是学术界的同仁。为此我得认真研究所发现的学术问题,取得编辑的信任并与他们交朋友,为读者提供最好的作品,交由学术界师友检验和批评。我已出的十余种著作,大多数是将书稿写成后,去与出版社联系,取得编辑和社长的同意,列入出版计划,付我合理的稿酬,面向全国及海外发行;还有的是出版社约我写书,列入出版计划。友人曾发现我的专著适应学术思潮,每得风气之先;著作的学术面较广,课题内容较丰富,多为专业基础之著,故颇为出版社的接受和读者的欢迎。这是我适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发展的现实需要所致的。
每项学术研究从发现问题到形成成果是一个科学的研究过程,此过程自始至终所采取的方法的正确或错误便可决定成果的学术价值。由错误的方法所产生的经不住学理检验的成果,必然是没有学术价值的;尽管它有时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我在西南师范学院学习时,读到德国经济学家伟·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他采用的是“理论的历史的”研究方法。西方近代学术存在“抽象的理论的”和“经验的历史的”两个学派,桑巴特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以为“只有对全部科学材料作根本深入的探讨,才能发现诸现象中最普遍的联系”。这实即通过对材料所提供的事实的具体的客观的历史的研究,发现现象或事实之间的普遍联系之后,再进行到理论层次的判析而作出结论。我接受了这种“理论的历史”的研究方法。我常对年轻学子说,我是学者,我没有理论,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学术问题。显然在解决某一学术问题时,总得有一定的理论为指导。我所理解的理论并非窃取的某种学说或自我设立的某种观念,而是一种由理论修养所产生的正常的具有较普遍意义的学理判断。所以我读任何哲学社会科学名著时舍弃其体系,仅吸收其个别的合理的观点,正如从日常食物中吸收各种营养。在研究过程中,当发现问题后,我特别注重材料的搜集与辨析,通过对事实现象的比较分析而立假说,再加以证实,并进而探讨其思想的、学理的、社会的或文化的意义。我坚信立论所依据的材料的事实是实在的。它若是不容否定的,而由此合理推衍出的结论也就是不容否定的了。学界友人发现我长于考辨,“考”即依据事实和材料,“辨”即学理的判断。我曾写过关于宋词和词学的系列考证论文,自研究国学以来很关注胡适、傅斯年和顾颉刚等学者提倡的科学考证方法。他们引入西方近代科學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其中美国的实用主义和德国的兰克学派的影响尤大;同时他们又继承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亦使二者结合起来为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我探讨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及其流派引入中国的过程,又追溯了北宋考据学的兴起,以及清代考据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察了它们在国学研究中具体运用的情况,于是在研究国学时自觉地力求方法的科学,而且更加注意采用科学研究的程序。学术论文实际也是文章,既是文章便得遵从它的规范,这关涉到行文的具体表述问题。每个学术问题具有独特的性质,我力求在将研究成果表述时寻找到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以使论述符合严密而合理的逻辑结构。我曾刻意学习中国学者译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的行文表述方式,以求语法规范,概念准确,结构谨严,风格典雅朴素,繁丰细密,文笔流畅;当然这只能是一种追求而已。我不用手机,也不用电脑写作,仍用旧的工具和程序,依然是读原著,抄卡片,起草稿,誊写抄正;曾经用圆珠笔,继用储水笔、中性笔,现在又用钢笔在白纸上书写。这种陈旧的写作方法看似落后、笨拙、迟钝、费事,但自有其优长。它可以使研究的心得充分地精细地表达,而且常有命笔快意之感。我所积累的专著和论文的第一手稿基本齐全,也许将来会是稀罕的文物了。
青年学者采访我时,问及治学经验,我概括为:树立学科意识,适当学术转移,努力探究学理。我们从事的学术工作,应明确它属于什么学科,属于学科的哪一级,必须对此一学科具有系统的知识,了解它的历史和现状,由此确定具体的研究方向。学者的使命便是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形成崇高的学术信念。然而长久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犹如开发矿产一样终有尽时,或专业研究告一段落时,必然由疲劳与过于熟悉而缺乏新鲜的感觉,导致失去灵感和想象,难以发现新的学术问题,甚至可能出现江郎才尽的现象。如此,为保持学术的新的感觉与活力,应当向邻近的学科或有兴趣的其他学术问题进行暂时转移。这有利于产生新的成果,扩大学术的视野,增强学术的活力。每当我们发现一个学术问题时,虽然对它有些了解,也有怎样去研究的初步考虑,但它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尚是一个彼岸的未知的东西。它的奇异、深奥、玄秘引起我们探索的兴趣。此种学理的研究探索是为求得一种真知,去接近真理。已故的老友洛地先生曾说,一个创造性的谬论胜过重复千百次的常理。在求真知的过程中是可能出现错误的,某些片面的极端的真知,或一个创造性的谬论,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避免学术的平庸,激起学术的涟漪,表现学者的锐气。然而这一切又必须经过学术界长期的验证才可为定论的。现在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一般不再参加馆里的活动,但由我负责的与《蜀学》《国学》的联系工作还将继续下去;同时我的学术探究亦将继续下去。我们对学术真知的探索是无止境的,只有一步一步地去逼近它。学者生命之树常绿的秘密即在于此。
谢桃坊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