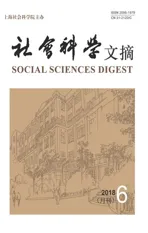软实力的神话?
2018-07-09卢凌宇
文/卢凌宇
软实力是小约瑟夫·奈在1990年创造的概念,指通过吸引力让别人采取他们本来不愿意采取的行为的能力。奈声称软实力对于美国在全球担当重要角色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他还专门强调了美国培养的外国学生尤其是外国领导人对改善美国国际环境的重要性。
奈的原创著作催生了大量的软实力研究。它们主要集中于探讨软实力的概念、度量以及探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建设和强化它们的软实力。相比之下,很少有研究致力于探讨软实力的作用机制和政策效果。
本文的贡献在于填补了软实力理论大样本统计检验这个空白。本文的基础数据囊括了20世纪毕业于美国高等院校的各国外交决策者。他们是奈所高度重视的美国培养的外国政治精英。由于基础数据是个人层次的,虽然分析单元聚合为国家/年,本文的经验分析至少可以部分地克服理论与数据不匹配的问题,是一个比传统的宏观关联度分析更恰当的分析途径。不过,为软实力理论提供一个跨国时间序列检验并不是本文唯一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本文以美国培养的外国外交政策精英为自变量,把软实力理论还原为一个三阶段的因果机制。这个机制的起点是美国高等教育,终点是目标国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输出。随后,本文剖析了这个连环因果机制的三个环节,论证了软实力的政策效果即使不是零,也是不显著的。
留美国际学生的类型划分
本文关注的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软实力载体,即美国高等院校培养的国际学生。软实力研究者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国际教育对于促进美国的经济和全球竞争力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国际学生确实履行了促进国家间和睦关系的职能。
这个困境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外国学生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他们具备很不相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据此,为了促进理论建构和经验检验,有必要对国际学生进行分类。第二,由于相关数据不存在或者难于获取,所以无法进行大样本经验检验。本节将讨论第一个问题,把第二个问题留到研究设计部分。
就国际学生的外交政策影响而言,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在于学生是异质的。本文尝试把国际学生分为四种类型(见表1)。
本文设置了两个指标来对留美的外国学生进行分类。第一个指标是身份(地点)。它报告毕业生的工作(生活)地点是在美国,还是在自己的母国。第二个指标是识别国际学生的政治功能。本文把国际学生划分为两类:外交决策者或非外交决策者。只有第一类学生能够直接地参与制定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以这两个指标为基准,我们可以把国际学生分为四种。
第二种学生在美国归化,但同时参与母国的对美决策。这种情况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它被排除在分析之外。第一种学生是美国的永久居民或者公民,但不是母国的外交决策者。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对美国对母国政策的影响远大于母国对美国政策的作用。所以,本文的理论建设也不考虑这种类型。
第三种学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他们返回了自己的国家,同时担任外交决策职务。在所有四种学生中,他们距离母国的政治权力最近。如果说美国的高等教育确实能够产生政治回报,那么他们是最可能让这种期待变成现实的人群。
第四种学生是美国培养的大学生中最大的群体。他们可能会变成本国的知识或经济精英,但却处在外交政策圈以外。他们影响本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途径是公共舆论和大众媒体。但普通公众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政治精英在决策时几乎不考虑公共舆论。
综合以上的分析,上述四种学生对美国产生积极政策效应的可能性和强度从大到小的排列是:第三种>第四种>第一种>第二种。显然,决策者和非决策者影响外交事务的途径和力度存在显著的区别,其中前者拥有难以比拟的优势。笔者假定第三种学生是对奈的软实力理论最恰当的检验对象,以此为基础的反驳会对软实力理论形成有力的挑战,至少可以严重质疑以国际学生为载体的软实力。因此本文将集中分析第三种学生。

表1 国际学生的类型
软实力、留美外交决策者和美国国际关系
奈编织了一个多阶因果链,把软实力和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产出联系起来。他本人曾经很简要地勾勒出两个模型:一是直接模型,二是间接模型。在第一个模型中,软实力资源作用于政府精英,对他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精英决策和政策结果。对于后一个模型而言,软实力资源作用于公众,吸引他们,影响精英决策的社会—政治环境,转而对精英决策施加影响。这两个模型的共同点可以总结为以下的因果链:资源(比如文化)→政策工具→转化技术→目标反应→政策结果。
本文的理论建构与奈的直接模型相似。对于国际学生而言,这条因果链以美国校园生活为起点,到热爱美国文化,再到对美国有利的政策偏好或利益,最后到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输出。上述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实际上都构成了软实力理论的隐性假定。这个因果结构意味着美国高校培养的外国决策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惠及美国国家利益取决于三个隐性假定在何等程度上是真实的,即美国校园生活转化成对美国文化的认同、美国文化认同转化为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偏好以及亲美的政策偏好转化为同质的政策结果。它是这三个隐性假定的概率的乘积。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这个积很小,不会构成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
(一)美国大学生活与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并非线性正相关
软实力暗示着特定国家在未来所选择的政策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交决策者在留学国度的经历。但只有积极的异国留学经历才可能产生正收益,一个学生痛苦的经历很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事实上,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对于许多学生来讲不是愉快的经历。来自世界某些地区的国际学生会在不同程度上遭受种族歧视。来自非白人国家的学生会遭遇更多的消极经历。文化和语言的异质性也会给外国求学者应对校园生活和开展有效交流制造巨大的障碍。这些学生发现很难和美国学生建立并维持友谊,因此,外国学生更可能产生强烈的隔离感。
许多国际毕业生对美国抱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对于那些毕业后回国的学生而言,这样的感情可能长期存在。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负面的情绪,尤其是挫折感、恼怒、失望和羞愧比感激、理想、胜利和自尊等积极情绪更持久。因此,美国的学生生活很可能留下负面的印象。
即使所有外国学生都享受美国的学院生活,学生们是否会因此而认同美国文化和社会,也是值得质疑的。新的身份本质上源自国际学生的信念改变。鉴于国际学生是美国社会的短期移民,对移民观念变化的研究值得本文借鉴。应该承认,学者们对此存在分歧,但都倾向于认为产生观念变化的概率是很低的。
(二)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并不等同于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偏好或利益
这个命题针对的是文化认同会转化为亲美的政策偏好或利益的假定。奈在阐述软实力的概念和作用机制时,很强调软实力对偏好的塑造作用,即在美国求学的未来的领导者更可能支持他们的国家与美国保持积极的关系。该假定的真实性很值得商榷。即使经过在美国几年的生活,国际学生确实美国化了,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主流的意识形态,但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尤其是那些在美国生活了3—7年的学生,这个过程的遗留影响可能不如设想得那么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价值也会逐渐褪色,从而削弱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美国价值和规范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未来外交政策制定者的政策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在本国再社会化的影响。在再社会化过程中,新的价值能否生存下来,并不取决于它们是否更正当、更符合人性,而是取决于它们是否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留美国际学生在一些国家处于政治上的边缘化状态。出于文化的差异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他们很难进入重要的政府部门或被提拔到政府部门重要的岗位。由于主权国家是世界政治的基本单元,国家利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至高无上的。为了个人在政府和公共部门的事业发展,适当拉开与美国的距离,甚至表现出反美倾向,有时候是必要的安全保障。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面临着世界范围内严重的信用危机和善意赤字。认同和追逐美国梦与对美国及其外交政策深厚的敌意并存。这个冲突可能意味着人们喜欢美国人而不是美国。反美情绪在不同的关键时刻起起落落。美国外交政策决定了反美主义的兴衰,对美国的文化认同很可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影响变量,并不会像软实力学者所预测的那样促进生成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偏好。
(三)决策者的政策偏好未必会转化为相应的政策产出
这个命题所要质疑的是个人政策偏好/利益会转化为相应的政策产出的假定。它与前两个假定的一个区别在于它只适用于留美外交决策者,而前两者则普遍适用于美国高校培养的外国学生。这个推论的真值毫无疑问是概率性的。它的真实性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外交决策结构和决策者的政治计算。
外交决策者是一个决定在国际事务中如何作为或不作为的小集团。决策单元的性质显著地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决策结构主要有三种类型:独裁决策、单一集团决策和自主行为者联盟决策。每种类型都有一定的生成条件。外交决策的不同类型决定了影响政策产出的因素,包括先在的知识、信念、开放决策还是封闭决策等。第一个亚型的代表是绝对王权或者独裁者。这种决策结构围绕着一个高高在上的个人,由该决策者对政策负全责。不过,无论决策结构如何,从程序上讲,外交决策总要经由决策者及其助理组成权威机构,就某个政策问题展开讨论,做出决定,并授权执行。在上述三种结构中,联盟决策模式在西方民主国家和非西方民主国家都很盛行,同时也受到很多政治变量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决策规则的性质,比如是全体同意、简单多数,或者“非决定规则(no decision rule)”。
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偏好在独裁者模式下最有可能转化为相应的政策。如果外交决策由一个小集体或者自主行为者联盟来决定,这个可能性被显著地降低。相较而言,在其他两个决策结构之下,作为个体的决策者所能发挥的作用会受到其他决策者偏好的掣肘。
假定决策是独裁型的,亲美偏好能否转化为亲美政策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政治计算。决策者将采取的政策姿态取决于特定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力。“亲美”的政策主张只有在与决策者现实的政治考量相符合的前提下才会出台。这里存在一个判断上的困难,那就是除非对具体决策做深度个案分析,否则我们无从判断一个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选择是被现实政治考量驱动的,还是美国文化、规范和价值濡化所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从逻辑上看,一个国家的对美政策产出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二是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冲突。后一种局面一旦出现,可以断定软实力在外交政策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并未胜出。如果出现前一种情况,那就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因为它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该政策选择与独裁决策者的现实政治考量相符合,二是它与独裁决策者的现实政治考量不吻合,或者相互矛盾。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表示软实力产生了期待的作用。这就进一步拉低了软实力对国际关系产生积极影响的概率。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美国培养的政治精英制定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外交决策的概率很低。必须强调的是,特定外交政策的实施结果不一定符合对该政策的期待。两者之间的反差大小是决策者、政策执行者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可控制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逻辑上看,外交政策产出期待的外交政策效果是软实力理论的第四个前提。由于软实力理论的重点是对美有利的政策产出,所以本文不对这个前提进行专门讨论,但假定政策结果符合政策期待。本文假设:美国培养的外交决策者不会显著地影响美国的双边关系。
实际上,奈本人承认软实力并不必然产生期待的政策效果,因为软实力资源的转化过程是动态的,受到许多干预变量的影响。在权力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场景、施动者和施动对象之间的关系、施动战略和手段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从而使软实力对结果变量的影响产生高度不确定性。从历史上看,美国培养的外国学生与美国反目成仇并不罕见。
数据和方法
为了检验留美学生对美国软实力的影响,本文使用了1980—2000年之间159个国家的相关数据。本文的分析单元是国家/年。
(一)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美国与外国的双边关系。本文使用埃里克·加茨基(Erik Gartzke)所编制的“国家亲密关系指数(Affinity of Nations Index)”作为结果变量。该指数覆盖1946年至2002年所有联合国会员国。较高的取值意味着两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时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较低的取值则表示相反的情况。这个数据是衡量国家间利益或政策偏好的一个值得鼓励的尝试。从理论上考虑,“国家亲密关系指数”这个结果变量能够较好地避免政策产出与政策结果不一致的问题,它所反映的是决策者的态度或者政策姿态,避免了决策本身在从政策产出到政策结果的过程中被不可控因素扭曲。
(二)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取自美国国务院下设的教育和文化事务局编写的题为《昨天的外国学生、今天的世界领袖》的报告。它收录了20世纪曾留学美国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字、官衔、任期以及他们母校的名称。截至2007年,美国大学已经培养了317位外国或国际组织领导人,包括46位总统、29位首相、30位驻美大使。本文关注的是那些参与外交决策的领导人。
根据上述报告,本文设置了两个变量:一是虚拟变量,度量是否存在能够影响或决定外交政策的留美学生。二是有序区间变量,测量特定国家某年共有多少位能够影响或决定外交政策的留美学生。后一个变量试图捕捉留美外交决策者对美国双边关系更细微的影响。按照奈的逻辑,这样的情况会改善美国的国际环境:如果他们执掌外交决策大权,会产生更有益的政策结果。不过,本文期待这两个变量的影响都是非显著的。
(三)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冲突研究的几个常规变量。首先,统计模型中纳入了双边贸易这个变量。很多的证据表明贸易显著地缓和国家间关系。本文期待双边贸易会增加联合国大会双方的投票吻合程度。
第二和第三个控制变量是地理因素,分别为邻国和国家间距离。这两个变量的数据取自“战争联系数据库”的“直接邻国”数据。许多学者认为如果两国接壤,关系恶化和冲突的概率会增大。而随着两国地理距离的增加,战争的机会成本会相应上升,反过来限制了冲突或战争的冲动。国家间距离被操作为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所以,有理由期待地理距离与结果变量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军事联盟成员国被认为较少发生冲突。“战争联系数据库”提供了“正式联盟数据”。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签订防守协议、进攻协议或者中立/互不侵犯协定,那么就可以认定为存在军事联盟关系。
本文还控制了对象国的政权类型。“民主和平论”的一系列文献发现民主与和平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也做同样的期待。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冷战这个变量。冷战的终结标志着国际关系结构的质变。在冷战期间,由于苏联的威胁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美国的国际环境相对恶劣。对这个变量的期待是冷战会削弱美国与对象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的概率。
(四)模型设定
现有数据样本覆盖了159个国家,时间是从1980年到2000年。本文选择1980年作为分析的起点是由于美国培养的外国领导人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比较集中地进入政坛。
本文的经验分析采用两种回归方法。第一种是普里斯-魏斯坦可行性普遍化二乘回归(Prais-Winstein 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简称FGLS),第二种方法是固定效果(fixed effects,简称FEs)模型。通常认为,如果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下出现相同或相似的经验发现,这样的模型会被认为是比较稳健的。笔者期待本文的假定会在两种不同的模型中出现相似的结果。
经验发现和分析
根据FGLS回归的结果,两个自变量都没有对结果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就支持了本文的猜想:留美外国外交决策者没有显著地改善美国的双边关系。除了这种非显著性,自变量与美国双边关系的方向出人意料地是负的,也就是说此类领导人掌权的结果很可能会对美国的双边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贸易依存显著地促进了美国对外关系。政权类型和直接邻国都符合本文的期待:一方面,民主国家更可能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美国的邻国在联合国与之合作并不很愉快。
本文发现地理距离与因变量的关系是负的。这个发现与理论期待不吻合,但并不是无法理解。美国是全球性霸权国家,它的利益在世界范围分布。军事干预、战争、冲突以及对外援助都在遥远的国度播下了仇恨的种子。而且,作为工业世界的领袖,美国也导致包括西欧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的不满。军事联盟的影响则符合期待:盟友更可能在联合国大会采取和美国一样的政策立场。这个效应并没有由于控制了时间而发生变化。美国对外关系看起来受到军事战略的显著影响。此外,冷战的冲突效应并不显著。
固定效应模型排除了相对静止的变量,即邻国和地理距离。军事联盟显著地支持了美国的联合国外交。美国的联盟倾向于在联合国事务中与美国采取相同或相似的立场。美国的国际环境受到冷战期间苏联及其盟友的消极影响。相反,贸易量和政权类型都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为了检测上述经验发现的稳健性,本文以战争关联数据库的“军事化国际争端”数据为结果变量,以留美外交决策者的两个指标为自变量,重新运行了一系列模型。发现表明,美国培养的外交决策者不仅不会显著地影响美国双边关系,甚至会恶化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些证据不仅支持了主模型的发现,而且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含义,那就是留美外交决策者的影响对美国国际环境的影响可能是消极的,这与奈及其追随者的期待背道而驰,很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索。
结论
美国的决策者和学者都假定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是培养软实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但是,笔者涉猎所及,学者们既没有分析软实力发挥作用的机制,也没有提供宏观的个案分析以外的经验检验。本文剖析了软实力理论的前提,揭示并批判了国际学生会改善美国国际关系这个命题。
本文的研究设计还存在一些突出不足,所以对于本文的经验发现要谨慎地解读。对于度量国家间关系而言,本文的因变量是一个恰当的选择,然而,该数据有自己的缺点。本文的自变量也需要更精致的处理。
所以,与其说本文证伪了软实力理论,还不如说它验证了奈的洞见,那就是“吸引力”本身并不产生直接的政策结果。所以奈才提出了更具现实意义但影响要小得多的“巧实力”概念。实际上,软实力并不柔软,而是以硬实力作为后盾的。也许,未来的研究者会发现“巧实力”才是塑造国际关系的神兵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