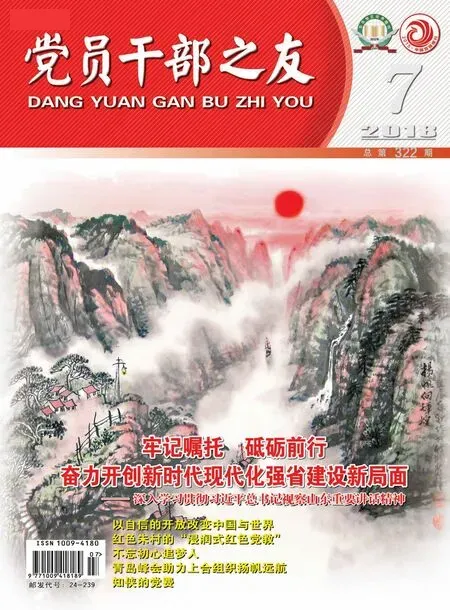诗人徐志摩的政治人生
2018-07-05

1918年8月14日,上海十六浦码头,“南京号”轮船缓缓起锚离岸。21岁的徐志摩站在甲板上,挥手向前来送行的亲友告别,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但离愁别绪并未在他心中停留太久,回到船舱,他提笔写下了《赴美致亲友书》:“诸先生于志摩之行也,岂不曰国难方兴,忧心如捣……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国运以苟延也今日,作波韩之续也今日,而今日之事,吾属青年,实负其责。”
这番话,极具其恩师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一文的气魄:以青年之躯,担兴衰之责。
徐志摩逝世时,年仅34岁。当后世习惯于把他的一生简略成两段婚姻和几首口耳相传的爱情诗时,那个怀揣着救国梦想渡海、以政论文章针砭时弊的青年,却渐渐地不为人知。事实上,徐志摩是一个思想精进、有社会担当的人。
徐志摩曾说:“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汉密尔顿)。”这位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首任财政部长。徐志摩以其为目标,是想从经济入手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为此,他还取了个英文名“汉密尔顿·徐”。
徐志摩到美国后,进入伍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就读,选学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商业管理》《劳工问题》《社会学》等课目,成绩很好。但他真正收获的并非是课堂上的知识,而是被点燃的爱国热情。
1918年11月,当一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美国人自发上街头欢呼庆祝,发自肺腑地为国家骄傲。徐志摩初到异邦就旁观了这一幕,感触颇深。他与同居室的董时、张道宏、李济商定,遵守共同制定的章程,其内容包括:“六时起身,七时朝会(激耻发心),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散步阅报。”
到美国后不久,徐志摩听说有一个留学波士顿的中国学生建立了爱国组织国防会。他认为,与其穷居,不如张扬,况且附近的纽约有不少英贤之士,不可失之交臂,于是约了好友前往波士顿,还去了哈佛大学。他在哈佛大学待了3天,不仅加入了国防会,还结识了吴宓、赵元任、梅光迪等中国留学生。
1919年底,徐志摩获得克拉克大学一等荣誉学位后,来到纽约,进入汉密尔顿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政治学。徐志摩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实业救国,转而关注社会问题。1920年,他以毕业论文《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结束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日子,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读博士。这一次,他追随的目标变成了哲学家、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伯特兰·罗素。
谁知等徐志摩到了英国,罗素却去了中国。既来之,则安之。徐志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英国社会主义主要思想家拉斯基教授,并有了一些政治实践。这一时期,他给国内的《改造》杂志写了几篇文章,谈的也大都是政治话题。
1921年春,在作家狄更生的介绍下,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即国王学院)就读。同年10月,他得知罗素回英的消息,立刻写信请求见面,很快如愿以偿。
徐志摩发乎本心的崇拜和尊重,给罗素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成了罗素家中的常客。罗素攻击卑鄙虚伪,提倡世界政府,热爱和平、文明、人类,捍卫思想自由及创作自由的观点,都对徐志摩影响很深。
然而1922年8月,徐志摩却突然放弃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决定回国。这个决定的背后,既有众所周知的原因——追寻林徽因的脚步,还有一个少有人道的理由——因为恩师梁启超“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需要其回国相助。
徐志摩的恩师梁启超,对其影响极深。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徐志摩就被梁启超的学识、文采和思想所折服,赴美留学前,又成了梁启超的弟子。梁启超是一个敢于担当的文人,他主导的大部分文学活动,都是有政治意味的。梁启超召唤徐志摩回国参与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要做一个振兴中国文化的计划。
徐志摩回国后不久,就搬到了北京的石虎胡同7号,负责处理图书馆和讲学社的英文信件。工作之余,他就带着皮包四处投稿,逐渐在新文化运动后群雄割据的格局中打出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等人提出要建立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的“好人政府”。于是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法学家王宠惠、北大教授罗文干等人入阁。但财政总长罗文干的被捕让“好人政府”如昙花一现。
这激起了知识界的强烈不满。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辞呈,声援罗文干。初回国的徐志摩,带着满腔理想主义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写下了《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在这篇文章中,他发出了“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呐喊。
徐志摩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毕竟是学政治经济的,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独立的思考,也常有发表的欲望。1923年冬,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一说要办《理想》杂志,徐志摩就迫不及待地写下《政治生活与邻家三阿嫂》《青年运动》等文章。回国后的两三年间,在建树诗人声望的同时,徐志摩更多的是以时政评论家的身份说话。
1926年3月,日舰轰击大沽口炮台,国民军还击,史称“大沽口事件”。是时,徐志摩就被困在大沽口外的通州轮上,听着传来的阵阵枪鸣炮响。回北京后,因八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通牒引发的“三一八”惨案,让徐志摩难抑愤怒,写下了《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闻一多、饶孟侃等人纷纷发表诗文谴责北洋政府的暴行。《晨报副刊》上的《诗刊》创刊号几乎成了“三一八”惨案纪念专号。后来“济南惨案”他也在日记中痛陈:“日本人当然可恶,有血性的谁能忍耐,没有一件我们受到人家侮辱的事是不可以追原到我们自己的昏庸。”
1931年10月29日,徐志摩决定和外交官顾维钧一道,乘张学良的专机南下。此前因顾维钧一再延期,徐志摩不得不在北平逗留了12天。这12天,他几乎与北平的好友都见了面。一次次的见面,竟成了彼此皆不知的诀别仪式。
临行前,他与剧作家熊佛西最后长谈。熊佛西回忆:“我们互谈心曲,他说往事如梦,最近颇想到前线去杀敌!他恨不能战死在沙场上!他什么样的生活经历都已经历,只没有过战场上的生活!他觉得死在战场上是今日诗人最好的归宿。” 在徐志摩去世后的友人悼念文章中,这些“诀别”常被提及。
徐志摩回到上海后,又于11月19日清晨,乘“济南号”飞机去北平,终因飞机误触山头而遇难。11月9日滞留北平时,徐志摩还给陆小曼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此行专为看你:生意能成固好,否则我也顾不得。且走颇不易,因北大同人都相约表示精神,故即(使)成行亦须于三五日赶回,恐你失望,故先说及。”所谓北大同人,就是北大的教授们,所谓表示精神,就是要在日寇步步进逼、东北局势危急、华北几将不保的国难时刻,表示他们同仇敌忾的信念。这为徐志摩匆匆返回北平提供了解释。徐志摩这一生,要说他坚持了什么政治思想,其实并不明确。但有一件事他坚持,那就是爱国。当初渡海是为了救国,回来后针砭社会是希望国家变得更好,至死也是想为民族救亡做些什么。他是一个始终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