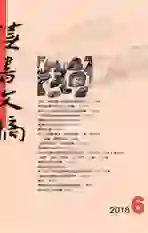“乡愁”之前:“西潮”与“后土”之间
2018-06-25艾江涛
艾江涛
“当时台湾大部分诗人都在盲目西化,写作超现实等别人难以看懂的诗歌。可余光中回归中国的抒情传统,当时台湾还在联合国有席次,有文化中国的底蕴在,所以余光中提出新古典主义的诗歌,只能说风靡一时。镜头全部照在他身上,大概就是在 《莲的联想》 之后。”
“后土”难离
1949年春,为了躲避内战的战火,金陵大学外文系大二学生余光中,不得不转学到厦门大学。几个月后,他跟随家庭辗转香港避难。这样的逃难经历甚至路线,对21岁的余光中来说,并不陌生。1937年底,南京陷落日寇之前,余光中便跟随母亲逃回常州外婆家,随后一路迂回到上海法租界,在那里渡过一段寄人篱下的日子后,在1939年夏天经香港、越南,历经艰辛,才到重庆与父亲团聚。
不同于还能在厦门大学插班就读,香港一年是在无学可上的苦闷中渡过的。1962年,刚刚在台湾获得年度“中国文艺协会”新诗奖的余光中,应 《自由青年》 杂志之邀撰文自述写诗经过,回忆起那段日子:“面临空前的大动乱,生活在港币悲哀的音乐里,我无诗。我常去红色书店里翻阅大陆出版的小册子,我觉得那些作品固然热闹,但离艺术的世界太远了。我失望,我幻灭。我知道自己必须在台湾海峡的两岸,作一抉择。而最苦恼的是,我缺乏一位真正热爱文学的朋友。有一位朋友劝我回大陆,不久她自己真这样做了。我没有去。最后我踏上来基隆的海船。那是1950年的夏天,舟山撤退的前夕。”
隔着十多年的时光,当初的赴台成了更多出于艺术考虑的某种抉择。只是,余光中没有想到1949年夏天于甲板上回望的那片大陆,从此犹在梦中,一别就是近半个世纪。而在梦的彼端,则是二十多年在华山夏水中度过的日子与点滴记忆。写诗,用余光中日后的话来说,如同叫魂与祷告。
但在20多岁离开大陆,而不是更年轻,对他来说则是一种幸运。2002年,74岁的诗翁余光中,在为即将在大陆出版的九卷本余光中集序言中写道:“因为那时我如果更年轻,甚至只有十三四岁,则我对后土的感受就不够深,对华夏文化的孺慕也不够厚,来日的欧风美雨,尤其是美雨,势必无力承受。”显然,这块被他称为“后土”的大陆,已为日后的诗人打下最初的积淀。
在国民政府侨委会任职的父亲余超英,本身具有相当古文水平,一有机会便为余光中阅读讲解 《东莱博议》 《古文观止》 中的道德文章。1939年,余光中在四川江北悦来场的南京青年会中学就读,曾做过小学校长的远房舅舅孙有孚也逃难到附近,并带来大量藏书,这些线装本古籍很自然地为他打开古典文学的大门。初三之后,国文老师换了一位前清拔贡戴伯琼,在他的指点下,余光中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从而打下扎实的古文基础。而早在上海法租界时,余光中便有幸接触到英文,在中学他又遇到出身金陵大学的英文老师孙良骥,高一便崭露头角,一举夺得英文作文第一名,中文作文第二名,英语演讲第三名。
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余光中随父母回到出生地南京。1947年,余光中先后考取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其时内战的硝烟已经蔓延北方,在母亲的劝阻下,他最终选择了金陵大学外文系。
刚读大学时,尽管班上已有几位同学在热烈地写着新诗,但余光中颇看不惯他们那种诗意淡漠的分行散文,他最初的兴趣还在五七言古诗之中。后来接触到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的诗集 《凤凰》,还有新月派诗人臧克家的诗集 《烙印》,又在一本批评文集 《诗的艺术》 中读到卞之琳和冯至的诗歌,再加上对英国浪漫诗人及惠特曼的原文阅读,余光中开始写作新诗了。多少有些幸运的是,在厦门大学的短短数月内,他竟在当地报纸副刊接连发表了六七首诗作。
这种幸运一度延续到渡海之后的台大时期。一次,同班同学蔡绍班擅自将余光中写作的一叠诗稿拿给梁实秋看,没想到余光中不久便收到梁的一封鼓励有加的回信,后者自此也成为他在文学上最重要的引路人。1952年,即将毕业的余光中出版首部诗集 《舟子的悲歌》,不出意外,梁实秋不但为他写了序言,还亲自撰写书评称“他有旧诗的根柢,然后得到英诗的启发,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路线。”
尽管处女诗集没有带来幻想中的轰动,但已足以使余光中成為声名鹊起的年轻诗人。据台湾诗歌史研究者刘正伟讲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空气紧张、文化寥落的台湾,能够出诗集的人很少,某种程度上,也正因此,比他年长十几岁、有台湾现代“诗坛三老”之称的覃子豪、钟鼎文 (另外一位为纪弦) 后来才会亲自找上门来,拉他共组蓝星诗社。
“诗是必然,诗社却是偶然”
台湾现代诗歌运动滥觞于 《自立晚报》 的 《新诗周刊》。1951年11月5日,《自立晚报》 总主笔钟鼎文创立 《新诗周刊》 版面,并与纪弦、葛贤宁、覃子豪、李莎等人轮流主编,为战后台湾新诗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表园地。之后,由于与同仁诗歌观念不同,纪弦脱离 《新诗周刊》,独自分别于1952年8月创刊 《诗志》、1953年2月创办 《现代诗》。不同于之后成立的蓝星诗社,现代诗社是“先有刊,后有社”,纪弦持续在刊物上主张“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提倡主知路线排斥抒情的诗歌,并很快拉了115人的盟友加入,一时之间声势极为浩大。
而这显然让覃子豪、钟鼎文这些主张抒情传统的人感到紧张。于是,1954年3月,覃子豪、钟鼎文两位诗坛前辈专门跑到余光中位于台北厦门街的家中看他,表示想另组诗社与纪弦抗衡。不久,在一个初春的晚上,在诗人夏菁家中的餐桌上,蓝星诗社成立,最初的成员包括覃子豪、钟鼎文、邓禹平、余光中、夏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在1986年出版的蓝星诗人诗选 《星空无限蓝》 的序言中,被余光中总结为“诗是必然,诗社却是偶然”。
余光中去世后,与他同岁的蓝星诗社后期重要成员向明不禁陷入不知所措的失落之中。目睹蓝星诗人渐次凋落,他依然清楚记得诗社成立时的情形: “因当时也是从大陆来台的诗人纪弦先生正成立现代派,要将在西方流行的现代派诗作横的移植到中国来,并且要打倒抒情,而以主知为创作的导向,这对诗的认识有所本的蓝星诗人言,一直是以秉承诗以抒情传统为己任,承袭固有的抒情风格写诗,非常不以为然,是以蓝星的这时结社有点像是对纪弦现代派的一个反动。然蓝星诸君子对英美诗及法国象征诗亦各早有涉猎,认识其优劣取舍所在,故并不排除吸收西方诗所具有的现代营养,故后来亦有将蓝星以‘温和的现代主义相称。”
用刘正伟的说来说,台湾现代诗歌的三个球根,分別是从大陆跑到台湾来的新月派、现代派,以及在1920—1930年代日据时期受日本影响而起的本土现代主义。蓝星诗社、现代社与创世纪社、笠诗社,便是这三个球根上生长出来的产物。不过,1954年10月在高雄左营成立的以军旅诗人张默、洛夫、痖弦为代表的创世纪诗社,起初以“新民族诗型”对抗现代社,后来因服膺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而走向更为激进的现代诗歌路向,引发现代诗内部论战,甚至令纪弦一度要宣布取消现代诗的概念,则是后话了。
与其他诗社不同,蓝星诗社的组织异常宽松自由。这种沙龙式的同人聚合,正如余光中在1973年所写的回忆文章 《第十七个诞辰》 中所说:“一开始,我们似乎就有一个默契,那就是,我们要组织的,本质上便是一个不讲组织的诗社。基于这个认识,我们也就从未推选什么社长,更未通过什么大纲,宣扬什么主义。”
蓝星最初的阵地,是由当时在粮食局任职的覃子豪在 《公论报》 副刊商借而来的一个约三批宽的版面,所创刊的 《蓝星诗周刊》。1950年代初,台湾教育非常不普及,当时为了满足求知若渴的军中青年,中华文艺、军中文艺、中国文坛等函授学校应运而生。
“那时候没有电话和电视,主要通过通信与杂志学习,老师把讲义寄给学生,学生再把作业寄给老师批改。距离近的一些熟悉的人一起到台北聚聚。这些学员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军中青年,当时主要有国文识字班、小说班、散文班、诗歌班这样四个班。”刘正伟说。
蓝星诗社前期的核心人物覃子豪便长期担任这些函授班的老师,向明、痖弦等人正是在覃子豪的班上被培养挖掘而出。由于办函授班,办杂志,为学员提供发表园地,帮助诗人出版诗集,蓝星诗社的影响很快得以扩张。
蓝色星空下的变奏
诗社成立后,大家经常在台北市万国戏院的咖啡室或中山堂的露天茶座聚会谈诗。那种相与激励的诗歌氛围,在余光中的记忆中,天真可爱,也许幼稚但并不空虚,一度他甚至觉得那就是一个小的盛唐。另一方面,梁实秋对台湾诗坛的肯定与奖掖,也让他志得意满:“梁实秋先生说目前台湾的新诗要比中国以往的新诗进步得多,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数十年内,中国将会涌现一群伟大的诗人,其盛况将可比美盛唐,其光辉将可照耀千古!让我们为他们开路!”
不过,对余光中个人来说,在诗社成立的最初两年里,他仍然深受新月派格律诗的影响,写下大量诸如“我向高空射枝箭,/飕飕落在云后边。/当时天阴风雨紧,/云深箭渺看不见”那样不古不今的“豆腐干体”。走出新月派的余绪,迈入更为现代的写作实践,始于1956年。这一年,余光中翻译完了 《梵高传》,同时着力美国诗人艾米丽·迪金森诗歌的翻译,还与表妹范我存结婚,在综合的灵感刺激下,余光中宣称自己诗的现代开始了。另一间接的因素还来自当时诗坛的论战,余光中回忆道:“先是联合报上有人写一连串批评的文章,我也是受攻击的目标之一。尽管其人骂得并不很对,却使我警惕了起来。然后是五六、五七年的现代化运动的全盛期,许多优秀的新人陆续出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如何一个接一个认识了夏菁、吴望尧、黄用,以及他们周末在我厦门街的寓所谈诗 (或者争吵) 的情形。我一面编‘蓝星周刊与‘文学‘文星的诗,一面投入这现代化的主流,其结果是 《钟乳石》 中那些过渡时期的作品……”
1958年,30岁的年轻教师余光中,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进修一年,在那里选修了现代艺术课程。在1956—1960年,这一后来被研究者所划分的“现代化时期”,除了 《钟乳石》,余光中还写作了诗集 《万圣节》。即使是这一时期的诗作,大概也只能称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现代诗”,即富有现代精神的作品,而非狭义上合乎现代主义理论的现代诗,与洛夫等人不同,余光中从未服膺于某种主义或流派,始终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主知与抒情之间。所谓改变,以他自己所举的例子便能看出端倪,由于在新大陆受到现代画趋于抽象的启示,他渐渐在写作中扬弃装饰性与模仿自然,追求一种高度简化后的朴素风格,比如“常想沿离心力的切线/跃除星球的死狱,向无穷蓝/作一个跳水之姿”,是抽象化的“无穷蓝”,而非“无边的蓝空”。
很快,苏雪林、言曦等人发起对现代诗的攻击,批评当时的台湾新诗,不过是象征派的余绪,以艰涩掩盖空虚。余光中在内的许多诗人纷纷起来撰文保护现代诗。这次论战的结果,虽然巩固了现代诗的国防,却也再次显露出现代诗内部的分化。1961年余光中在 《现代文学》 第8期发表长诗 《天狼星》,洛夫随后发表长文 《天狼星论》,批评其从主题到意象,不符合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原则,注定要失败。在反批评文章 《再见,虚无》 中,余光中认为台湾多数现代诗已冲入晦涩与虚无的死巷,宣布自己要告别虚无。
从此,余光中更多从对传统的认识与挖掘入手,进入所谓“新古典主义”写作时期,代表作正是从 《莲的联想》 到 《白玉苦瓜》 的一系列诗集。这种转折,与他后来1964—1966年、1969—1971年的两次赴美教学也不无关系,在异国他乡,萦绕心头的儿时记忆与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传统自然地浮现出来,汇聚成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当时台湾大部分诗人都在盲目西化,写作超现实等别人难以看懂的诗歌。可余光中回归中国的抒情传统,当时台湾还在联合国有席次,有文化中国的底蕴在,所以余光中提出新古典主义的诗歌,只能说风靡一时。镜头全部照在他身上,大概就是在 《莲的联想》 之后。”
尽管如刘正伟所说,新古典主义诗歌令余光中风靡一时,但这依然不足以概括诗风多变的他。1986年元旦,余光中在第8本诗集 《敲打乐》新版序言中写道:“不错,我曾经提倡过所谓新古典主义,以为回归传统的一个途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新古典主义是唯一的途径,更不能说我目前仍在追求这种诗风。”
事实上,1971年从美国回来后,震撼于当时在美国风起云涌的摇滚乐,余光中格外注重探索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随后在台湾兴起的民歌运动中,余光中的许多诗歌被改编成音乐,他还直接写了合曲而作的诗歌。1967年在台湾苗栗出生的刘正伟回忆,少年时代的自己,正是一边听着杨弦等人谱曲的 《乡愁四韵》、《在雨中》 等歌,一边在课堂上读着余光中的诗。
不愿被提及的论战
余光中曾把1959年到1963年称为自己的“论战时期”,那也是围绕现代诗论争的国防时期。年轻时喜欢论战的余光中,中年之后便无心恋战,原因正如他后来所说:“年轻的时候我多次卷入论战,后来发现真理未必愈辩愈明,元气确实愈辩愈伤,真正的胜利在写出好的作品,而不在哓哓不休。与其巩固国防,不如增加生产。”
然而,围绕现代诗的论战并未结束,余光中在1970年代现代诗论战和其后的乡土文学论战中的表现,似乎也并没有随着他晚年的自陈而被忘却。其时的台湾,历经保钓运动、国际孤立,蒋介石 “反攻大陆”的意识形态陷入困境,台湾内部陷入苦闷与彷徨之中。伴随着对台湾自我身份的追问,在一些人看来,1960年代以虚无主义、反工业文明、反立法体制、存在主义达到对戒严体制反抗的现代文学 (诗),也便有了再检讨的必要。1972、1973年,曾参加过北美保钓运动的文学评论家唐文标接连发表 《先检讨我们自己吧!》、《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诗的没落》 等文章,对现代主义诗歌提出批评。对这一震动文坛的事件,余光中显然没有沉默,在 《诗人何罪》 一文中,他将论争对方视为“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的同类。
不久,台湾发生日后影响深远的乡土文学论战。继 《“中央日报”》 总主笔彭歌发表 《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将批评矛头指向乡土文学代表作家和理论家王拓、陈映真、尉天骢等人,还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余光中,在1977年8月20日《联合报》 发表 《狼来了》 一文,影射台湾乡土文学是大陆的“工农兵文艺”。由于文章中提到的“狼”和“抓头”的动作,显得寒气逼人,以至于陈映真多年后都难以释怀,认为这对当时的乡土文学界是一个政治上取人性命的、狰狞的诬陷。事实上,新儒家代表徐复观在不久后发表的文章中便表示过类似的忧虑:“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所幸的是,在胡秋原、徐复观还有郑学稼等国民党营垒中开明人士陆续出面说话后,对乡土文学作家迫害的恐怖阴影逐渐散去。
如果说 《狼来了》 与余光中反共的政治立场有关,那么后来所披露的余光中向军方“私下告密”的行为,则更让他陷入了争议的漩涡。2000年,陈映真在与陈芳明的论战中,提及后者在 《死灭的以及从未诞生的》 一文中公布的余光中在70年代后期给他写的一封密信片段:“隔于苦闷与纳闷的深处之际,我收到余光中寄自香港的一封长信,并附寄了几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陈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马克思文字的英译。余光中特别以红笔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方法,指出陈映真引述马克思之处……”陈映真在文章中表示,自己多年以前已由郑学稼亲口告知,这份材料被直接寄给了其时权倾一时、人人闻之色变的王昇将军,而在那个阴森的年代,这是足以置他于死地的一封信。
2004年,九卷本 《余光中集》 在大陆刚刚出版,余光中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一时间备受瞩目。面对当时的“余光中热”,北京学者赵稀方发表长文 《视线之外的余光中》,详尽披露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表现,感叹大陆对台湾历史的无知,并对余光中的人品提出质疑。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相关论争文章也很快以专辑“余光中风波在大陆”刊载于同年秋天出版的台湾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爪痕与文学》中。在这些文章中,有对赵稀方表示佩服并提出“余光中热”难以接受的台湾学者吕正惠,也有陈漱渝、陈子善等以持中的观点认为追问并非求全,这样的批评也是对研究者不够了解台湾文学史的提醒。台湾佛光大学教授黄维樑则写了长文 《抑扬余光中》,为其辩护,核心观点在于 《狼来了》 中虽有意气的话,但余光中反对的是工农兵文艺,并非乡土文学;关于“告密”一事,余光中曾亲口对他说:绝无此事。王昇最近也亲自以书面声明:绝无“告密”一事。
在舆论的发酵下,余光中事实上已不得不正面回应,这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 《向历史自首?—— 溽夏答客四问》。在这篇文章中,余光中坦承 《狼来了》 是一篇坏文章,缘于自己初到香港大受左派攻击之后,情绪失控之下的意气之作,并非受任何政党所指使。而对于“告密”一事,余光中表示自己绝未“直接寄材料向王昇告密”,只是将这份来自友人的材料作为朋友通信,从香港寄给了彭歌,自己还在信中说明“问题要以争论而不以政治手段解决。”
事实上,余光中在写作此文前,曾通过自己的学生钟玲,与陈映真取得联络,并在私人通信中对陈映真一再表示道歉。只是这份公开答复并未让陈映真真正谅解,他认为将材料交给彭歌的性质与直接告密并无多大区分,而私人通信中那些道歉的好话的消失以及标题中的问号,都让他感到寂寞、怅然和惋惜。
其时,论战已然过去几十年,两岸文化政治语境截然不同,令陈映真与余光中两个“统派”共同感到怅惘的,自然是在台湾日益崛起的台独话语。学者古远清对两人都比较熟悉。古远清回忆道,2005年8月,他在长春开会期间遇到陈映真,谈及这段公案时还劝他“你和余光中的恩怨都是以前的事了,不要記得那么清楚,宜粗不宜细,你们两个都主张统一,当然一个左统,一个右统,应该团结起来。”陈映真当时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2009年,古远清在 《传记文学》 发表 《余光中的“历史问题”》,讲述当年这段公案,并在之后出版的余光中传记中将这篇文章列为专章。传记出版后,古远清第一时间将其寄给余光中,据说他看后很不高兴。古远清说,由于此事,之前与他多有交往的余光中,再没有见他。
无疑,对向来以美为追求的诗人余光中来说,对此多少有些讳莫如深。余光中曾说自己从不写日记,也不写自传,因为作品就是最深刻的日记,而“我的艺术思想、人文价值,都在我的评论之中。我的情操与感慨,都在我的诗文散文里,我在母语与外语、白话与文言之间的出入顾盼,左右逢源,不但可见于我所有的作品里,也可见于我所有翻译的字里行间。”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