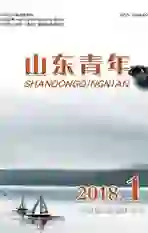诗意笔调下的孤独之美
2018-06-23陈银汇李秋
陈银汇 李秋
摘 要:自传性写作这一特点在《情人》这一小说的创作中显现得淋漓尽致,杜拉斯以独特的叙述角度和诗意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那位少女的孤独美学,外在环境、内在心理的共同作用造成了“我”的孤独,小说在“我”的孤独里触及人性中的方方面面——自私、嫉妒、善良、贪婪……
关键词:《情人》;杜拉斯;叙述;孤独
《情人》作为一部意识流小说,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叙述模式,通过“我”的回忆慢慢展开故事全局,小说的开端就好似现实与虚幻的边际连接处。诗意而富有哲理的语言、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小说中畸形的家庭、现实的爱情、疯狂的迷恋、死亡的恐惧等等改变着“我”的一生,“我”无所依靠,没有寄托,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沉浮,缔造自己的孤独。金钱、性满足、亲情、爱情、尊重这些东西,越追求就越是遥不可及,这种幻灭感使小说充满着孤寂意味,在“我”云淡风轻的叙述里,往事都是随风而去再没有什么值得大悲大喜。
一.外在环境造就“我”的孤独
首先,身份焦虑带给“我”孤独,在越南这片法属殖民地上作为白人少女的“我”是受到优待的,但种族的差异让“我”与当地的居民格格不入,“我”又是白人中的穷人,一块盐碱地,一个一无是处的大哥让生活持续困顿,这种贫穷让“我”处于白人世界的边缘化。其次,家庭里畸形的氛围是“我”感到不安、孤独的一个重要原因,父亲早逝,寡居的母亲只看重长子,“我”和小哥哥得不到母亲的关注与爱。在那个家里“从来不庆祝什么节日……而且也根本没有死去的人,没有坟墓,没有记忆”[1],除了冰冷,再感受不到什么其他的东西,“我”的母亲活着只为了大哥,那个“家中的流氓”、“不拿凶器杀人的杀人犯”[2],“我”在面对这位大哥时无数次涌起杀人的欲望,并且我还想把母亲关起来杀掉,在这样的孤独里,“我”对唯一给“我”温暖的小哥哥产生了疯狂的爱恋。最后,情人的家庭对“我”的排斥,学校下达的不许其他学生与“我”交谈的禁令,都使得“我”陷入了更深一层的孤独。
作为女儿、妹妹、爱人、学生的“我”在任何身份里都是孤独的,没有人真正了解“我”,“我”不断地追逐自由、爱情、亲情、金钱,那段追逐的道路始终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在《情人》这本小说里,“我”的孤独始终是优雅而富有诗意的,是不落于俗套的,这里的孤獨是平稳的,源于命运接受这种孤独的坦然。杜拉斯用自己独特的叙述语言缔造了这一番诗意的孤独。
阿兰·维尔贡德莱曾评价杜拉斯: “对一切都无动于衷,被自己的故事和传奇迷得神魂颠倒”[3],她就是这样一个专注于自己内心的孤傲女子,她的叙述语言里没有什么精巧绝伦的布局,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起伏,有的只是简单的平铺和自然的渲染,孤独就在这看似散漫随意实则精细独特的语言里慢慢发酵。《情人》中大多都是简单句,句子的结构都很简单,隐藏在话语中的深思和激情让她无需再用复杂的句子。在舒缓平稳的叙事节奏中,那些简单句经常被重复使用,“我么,我知道那不是什么美不美的问题,是另一回事,是的,比如说,是另一回事,比如说,是个性的问题”[4]。这样简单的重复带来一种迷人的节奏感,像一首可以被诵读吟唱的诗词。
作品中将大段对自然风光景物的描写与富含哲理意味的话语糅合在一起,在散文的诗意里透出理性之光,也只有杜拉斯这般的奇女子才能将这些处理得这般天衣无缝了。“黄昏在一年之中都是在同一时刻降临……时间十分短暂,几乎是不容情的。在雨季……天空浓雾弥漫,甚至月光也难以透过”[5]。空间和时间似乎在黄昏、在雨季里消失了,世界空荡荡的,“我”在那里独自回忆往事,没有人陪伴的自己是寂寞的,没有人关怀的自己是孤独的……
二.内在心理注定“我”的孤独
《情人》整本小说几乎全部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叙述的,即使偶尔出现第三人称也带着鲜明的第一人称色彩,那是一个生活在越南的法国白人少女在年老之际,带着自己满腔的情感,以回忆的口吻向我们絮叨了她的孤独,她的讲述并不连续,仿佛记忆的断层,也只有在这样一部完全用第一人称来做叙述的作品里,才能做到这样自然又不突兀的跳跃吧,倒叙、插叙手法的紧密切换也正是得益于此。《情人》就像是一首抒情散文诗一样,忧愁、愤怒、寂寞、悲伤等情绪热烈地流淌在其中,我们听凭情感的牵引而不用过度关注事件情节呆板的发展,我们时刻同主人公在一处,关注着她的孤独。
跟随着“我”的讲述,15岁半时在湄公河畔“我”结识了那位出身富贵、风度翩翩的中国情人。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使叙述者能够酣畅地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从而更真实地架构起回忆与现实的内容,让主人公自己完成孤独内心世界的剖析,展现出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个性化人物形象,使读者能感人物之痛,知人物之乐。正因为如此,小说在讲述完“我”与中国情人的初遇后,并没有开始大谈特谈两人的感情发展路线,而是转而阐述女人的欲念、阿杜给我改的旧连衫裙以及我对母亲的不满厌恶等等,“我”的想法和情绪时刻与读者保持交流,这样的跳跃并不会让人感到任何的奇怪或不适。
“我”在满足欲望、追求情感时所体会到的孤独,是小说中最为明显的孤独感。“我”有着明显的恋父情节,小说中对父亲的描写很少,但只要提到,就可以感受到“我”对父亲那种深沉的爱意,“我父亲死前在双海地方买了一处房产。这是我们唯一的房产。他赌输了”[6]。简简单单陈述房子没了的结果,其中愤恨却喷薄而出,父亲留给“我”唯一的念想没了,这让“我”痛苦,让“我”对大哥的恨又多了一层。那位中国情人满足了“我”的恋父情节,他给了“我”富足的物质生活,让“我”摆脱了生活的不堪,有了依靠,他的爱抚让“我”感到心安,“我变成了他的孩子。每天夜晚,他和他的孩子都在做爱”[7],长期的压抑和不安,使得“我”偏执而又自我,父亲在“我”的脑海中永远是最美好的存在,“我”极度渴望得到父亲的爱,“我”对母亲强烈的恨与不满,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对父亲疯狂的爱所造成的。另外,“我”对小哥哥的爱是不可理喻的,是不可同他人分享的,“我”怀揣着这些隐秘而疯狂的感情注定是孤独的,无从诉说,只能任由它们在心里生根发芽。感情只能留存于心底时,欲望就开始争夺主权,对金钱的欲望,对性的渴望,支配着“我”,在那一刻,“我”是冷漠而无情的,为了情人的财富而接近他,“我”觉得自己并不爱他,然而女人的感情总是这样没有道理,当他彻底离开,再也无法重新陪伴自己时,才有勇气审视内心理清自己的情感,最后的那滴泪告诉了读者真相。
死亡带来的孤独感是最为深刻而长久的,父亲、母亲、小哥哥、大哥、沙沥地方长官的儿子都死了,一个又一个人离开这世界,活在这世上的人随着自己一天天变老,变得更孤独、更无依。小说中对小哥哥死后“我”的心理状况描写得格外详细,“仿佛从四面八方,从世界深处,悲痛突然汹涌而来,把我淹没……”[8]。小哥哥的离开注定了“我”永远的孤独,心底最隐秘的情感在一瞬间被狠狠拔出来揉碎,“我”跟着小哥哥一块死去了。“不朽就是朽,不死就是死,不死也可以死去”[9],生命变得虚无而没有意义,没有什么是能够永存的,孤独也总有一天会消失,麻木会掩盖掉孤独的本质。
杜拉斯的世界经历了悲惨与疯狂后,变得丰富而冷凝、清醒而纯净。她向我们讲述了有关于自己的爱恨情仇,直白地袒露心底的欲望与秘密,大胆地向读者分享她在孤独中的反抗与挣扎、沉迷与欢愉。人生注定是辛苦而无奈的,会有压抑、困惑、折辱等等,容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发沧桑,心底的坦然与热度则更为坚定纯粹,彷徨褪去,孤独成为生命之底色,既然人生种种经历注定是旁人无法代替的,那就在孤独中沉思自己、善待旁人,杜拉斯用《情人》这部特别的小说,以动人的叙述语言、特别的叙述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她的孤独美学。
[参考文献]
[1][2][4][5][6][7][8][9]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3]阿兰·维尔贡德莱,《玛格丽特·杜拉斯:真相与传奇》,胡小跃译,作家出版社,2007年.
(作者单位: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