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画家:洁癖是一种生活方式
2018-06-23郑骁锋
◎ 郑骁锋

图/春 生
在1351年,距离忽必烈将国号定为“大元”已经过去了80年,这个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广阔的铁血帝国逐渐散发出了腐臭的死亡气息。这年五月,在治理黄河决口的工地上,17万治河民工和军队以红巾为号发动大规模起义,正式拉开了全面反元战争的大幕。
或许是预感到了这场注定要将所有人都卷入的剧烈动荡,这年的暮春,当河工起义还在酝酿时,与黄公望等人并称为“元四家”的画坛巨匠倪瓒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很多鬼怪,有的像飞禽,却长着角;有的像走兽,却会飞,它们像人一样直立着,发出野猪一样的尖叫,在他面前舞蹈腾跃,丑态百出。
在梦里,倪瓒并不惊慌,只是静静地看着它们上蹿下跳。他始终表现得很淡漠,直到被报晓的晨鸡拉回现实世界。
这一夜,倪瓒借宿在宜兴的重居寺。醒来后,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标志了倪瓒后半生的开端。
这一年,倪瓒50岁。两年后,他偕同夫人抛弃全部田产,乘着一叶扁舟隐入太湖浩渺的云水间,在二十多年的流浪中度过了余生。
倪瓒所抛弃的并不是寻常的家业,而是一笔数额惊人的资产。
自从倪瓒祖父那一代起,无锡倪家便是富甲东南的一等大户,明朝人往往将其与稍后的沈万三等人并称为富可敌国的“江南首富”。出生在这样一个钟鸣鼎食的豪门巨室,倪瓒生活之优裕可想而知。
最能说明倪瓒前半生生活状态的是一座由他亲自设计督造、用以收藏图书文玩的小楼—清閟(bì)阁。这座高三层、四面有窗的方形阁楼在中国美术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都赫赫有名,阁内收藏了包括王羲之、陶渊明、吴道子、王
清閟阁本身已极尽人间之奢华,倪瓒又在其周边配以云林(倪瓒的号)堂、雪鹤洞、洗马池等堂馆洞泉,再植以修竹乔木,富丽清雅难以名状,被时人视作神仙洞府。倪瓒极其珍爱此阁,若非至交好友,一概不得入内。曾有一位西域胡商苦苦哀求,希望能入阁观览片刻,但遭到了倪瓒无情的拒绝,胡商只能留下沉香百斤,怏怏而去。
倪瓒还留下了一本《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其中提到了五十余种菜点饮料的独特做法,后人可以从中窥测这位富家子弟近乎奢侈的日常起居。清代大学者袁枚是个极其苛刻的美食家,曾将李渔等前辈撰写的菜谱贬得体无完肤,但在自己的《随园食单》中收录了倪瓒的“烧鹅”,并命名为“云林鹅”,可见倪瓒对于饮食享受标准之高。
如此家庭背景使倪瓒养成了不同寻常的生活态度:清高孤傲,洁身自好,不问政治不出仕,自称天地之间一“懒瓒”。如果没有意外,这位与世无争的“懒瓒”将在安逸富足中度过一生。
然而,这一切都终结于1353年。在那个下着小雨的清晨,曾经令多少人仰慕、猜测的清閟阁与云林堂突然被它们的主人遗弃。从此,倪瓒浮家泛宅,足迹遍及江阴、宜兴、常州、吴江等,宁愿远远地围绕着太湖徘徊流离,也不再回头,重新推开故园尘封多年的大门。
失去主人的清閟阁很快化作了一片荒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明确的结局。很多人猜测它可能毁于元末战乱,不过,无锡民间世代相传:倪瓒离开的那天,点了一把火,亲手将这座凝聚了他半生心血的阁楼烧成了灰烬。
面对着熊熊燃烧的火焰,倪瓒想必是满脸平静,谁也猜不透那一刻他在想些什么。
正史及大部分野史笔记都将倪瓒的弃家赋予了浓厚的传奇色彩。《明史》记叙:当时“海内无事”,倪瓒忽然散财离家,人们都很纳闷;不久,“兵兴”,豪门都遭了灾祸,唯独倪瓒没有罹难。朋友为他作的《墓表》则描述得更加生动:一天,倪瓒抛弃了家宅,说“天下多事矣,吾将遨游以玩世”,于是“人望之若古仙异人”。
“异人”“世外人”是人们形容倪瓒时用得最多的词语。在弃家这件事上,由于之后不久战火就烧到了江南,尚未出逃的富户大都遭到荼毒,人们更是赞叹倪瓒独具慧眼,早早便能预见灾祸,毅然捐弃所有身外之物,好不逍遥自在,从此倪瓒又被称为“倪高士”。
倪瓒的弃家果真如此潇洒,他对故乡果真视如敝屣、毫无留恋吗?
倪瓒的好友画过一幅《清閟阁图》,画的款识中有这么一句话:“至正壬寅(1362年)秋八月十八日过访云林老友,因出素纸命予作此。”也就是说,在离家九年之后,倪瓒终于按捺不住思乡之情,借助朋友的笔表达了对清閟阁的思念和哀悼。
八月十八是一个海洋与月亮共同制造一年中最大潮水的神奇日子。在那一夜,平日温和如镜的太湖湖水同样在倪瓒胸中滂湃起了滚烫的大浪。
或许,只有倪瓒知道,无家可归的这些年,自己心中究竟有多么苦涩;而踏上船板的第一步又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元明之际,江南一带流传过这样的民谣:“昔日田为富之础,今日田为累之头。”在倪瓒的时代,做一个富户,尤其是江南的富户,其实并非一件幸事,从前的万顷良田如今却成了套在自己脖颈上的沉重枷锁。
随着元朝朝政日益崩坏,统治者穷奢极欲,加之天灾民变迭起,朝廷的财政亏空越来越大。在此形势下,以富庶著称的江南自然备受经济压力,缴纳税粮的数量是元初的三倍,江南的地主则被视作砧板上最肥美的鱼肉,遭受残酷的剥削。在高额田赋之外,朝廷还派专员携带空白官员任命书
原本,这些财富所带来的烦恼与倪瓒无关。虽然自幼丧父,可他有一个能干的好大哥,即便是天塌下来也有大哥顶着,倪瓒身为小弟,只管关起门来读书、作画、吟诗、弹琴。只可惜好景不长,在倪瓒27岁那年,大哥骤然得病,离开了人世。
倪家兄弟三人,大哥已逝,二哥生有残疾,一夜之间,毫无准备的倪瓒成了倪家唯一的当家人,从此赋税杂役迎来送往全部落在了倪瓒的肩头。可以想象,对于一个从小浸习于诗文书画、生活在纯净艺术世界中的年轻人,这样的生活有多么焦躁难耐,简直无异于从圣洁的天堂直接坠入烂泥坑。
让不谙世事的倪瓒理财原本就是赶鸭子上架,更令倪瓒头疼的是,到了他当家的时候,家业已经摇摇欲坠,面临着全面崩溃,即便是大哥复生恐怕也无法力挽狂澜。
屋漏偏逢连夜雨,倪瓒当家之后,江浙一带接连遭遇灾荒,有一年甚至整整八个月没下过一滴雨。至迟在1341年,倪瓒就开始出卖田产以填补税粮亏空,他的诗文中也屡屡出现了遭受官府逼税、疲于奔命的悲苦诗句。
“遗业忍即弃?吞声还力耕”“虽曰先业,念毋坠失;守而不迁,至此忧郁。”从倪瓒留下的诗作看,弃家于他,诚然是愧对祖宗的无奈之举,而从诞生弃家的念头到付诸实施,至少经过了八年的犹豫。不难想象,这八年中倪瓒内心的极度痛苦。
所谓的“高士”,所谓的“吾将遨游以玩世”,实际上不过是倪瓒一次强咽泪水的凄惨出逃。
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与鲁迅、曹雪芹等文化巨匠类似,倪瓒同样经历了家族由盛转衰的过程,甚至比他们更能深切体会其中滋味—毕竟他本人就是抛家弃业的责任人。通常,这样的经历会使当事人在作品中表现出激愤等相对强烈的情绪,然而,倪瓒尽管偶尔也在诗句中抨击时政的黑暗,但并没有在笔墨中流露太多怨恨,他的书画一如既往的宁静散淡—区别在于,此后,他的用笔愈发空灵,意境愈发悠远。
明清时,倪瓒的字画受到了狂热追捧,被奉为不可多得的“逸品”,江南一带甚至以有没有收藏“倪画”作为判断一户人家文化素质高低的标准。不过,虽然明清画家以仿倪画为荣,但几乎没任何人能够模仿出倪瓒特有的气韵。
倪瓒的画似乎不难学,尤其是山水画,笔墨疏阔简略,就像他的故乡无锡,地势平缓,平远荒山灌木竹石而已,并无峥嵘险峻的奇观。然而,这么一种看似平淡无奇的画风,为何后世竟无一人能承其衣钵,得其精髓一二呢?
答案在倪瓒的挚交为他创作的一幅肖像画中。当时倪瓒尚未弃家,挚交在清閟阁中为他画像。与一般肖像画不同的是,倪瓒左右的僮婢一个怀抱尘掸,另一个臂搭长巾、手提水罐,都是洗漱清洁用具。
一尘不染,这是倪瓒对生活最低的标准,同时也是他一生最高的精神追求。
倪画的无法超越大概应该归结于,这人世间再无一人的内心能达到倪瓒的洁净。某种程度上,倪瓒对于洁净的追求已近乎一种病态。
除了绘画大师,倪瓒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中国历史上洁癖的代表人物。
在朋友们看来,被倪瓒选中做僮仆绝对是人生一大悲哀,因为这就意味着从此再也没有片刻空闲。用“眼里容不下半粒沙子”来形容倪瓒对卫生的要求再合适不过,仅是一间书房,他便安排了两个书童日夜不停地洒扫拂拭,无论座椅砚台,只要是平面,他都要求能够照出人影来。
清閟阁是倪瓒最主要的起居场所,自然是清洁工程的重中之重。他在整个楼面都铺了厚厚一层青毛毡,几案则覆以碧云笺,并准备了几十双五色丝履,所有人进入必须先换鞋。
阁内倒也罢了,倪瓒对阁外也要求做到尽可能洁净,就连庭院里的梧桐树和假山石也命人每天早晚三次挑水揩洗。可怜梧桐受不起这般殷勤的待遇,竟有几株烂根而死。
因为怕外人弄脏自己的家,倪瓒轻易不留人住宿。
某日,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友从远方来拜访,倪瓒实在无法推脱,只能安排老友住下。这一夜,倪瓒辗转反侧,仔细聆听着客房的动静。忽然,老友咳嗽了一声,倪瓒顿时变了脸色,难受得彻夜未眠。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匆匆送走老友后,倪瓒立刻命令仆人寻找老友吐的痰。仆人们找遍了整个院落也没看见痰的痕迹,又怕挨骂,只好随便找了一片有斑点的树叶送到倪瓒面前,说痰就在这里。倪瓒远远斜睨了一眼,便厌恶地闭上眼睛,捂住鼻子,叫仆人送到三里以外的地方丢掉。
生活中,倪瓒更是竭尽全力远离一切污浊:喝水,他只喝挑夫担子前面那桶,原因是挑夫身后的水会有矢屁之气;他洗脸要不停换水;他每天戴的帽子、穿的衣服要换好几套,还得不停拂拭;人免不了如厕,他便设计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空中香厕,用香木搭好格子,下面填土,铺上白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不闻有秽气也”。
在当时,倪瓒就时常成为被取笑的对象,还得了个“迂”的评语。倪瓒却丝毫不以为意,在落款时傲然题下了“倪迂”二字。
倪瓒的洁癖大概是一种类似于强迫症的精神疾患,而他在作品中呈现的删繁就简、追求素净完全是他的洁癖体现在笔墨中的真实反映。从这个层面上看,他的散淡境界是任何普通人永远无法企及的。
如果说在27岁之前,倪瓒的洁癖多少还因不惜物力的纨绔习气而停留于表面的话,那么随着家业不可挽回地走向下坡,被逼出清閟阁的倪瓒对洁净的追求逐渐沁入了内心。
最终,倪瓒的创作形成了一种极具个性的风格:他的笔下从此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主角。在他传世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出一幅画中有人物。而倪瓒画中一个最具其个人烙印的美术意象便是空亭。
倪瓒的山水画最常见的构图是远处一抹横山、近景平坡上有三五杂树一二怪石,以及一座亭子。与一般画家通常于亭下点染高士不同,倪画中所有的亭内都空无一人。
当时的人们感到不解,有人曾当面向他提出了这个疑问。倪瓒一翻白眼,反问道:“这世上难道还有人吗?”
这并不是随意的应答。倪瓒还写过一首著名的散曲,结尾处苍凉地感叹:“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
清洁的过程就是祛除污浊的过程。洁癖之于倪瓒,就是对所有丑恶之物的芟除。倪瓒的一生就是在做极致的减法,减到无可再减之际,连人本身都成了他厌恶和清减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倪瓒的生日是正月初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传说女娲创世,造出了鸡狗猪牛马等六畜后,在第七天造出了人,所以这一天是属于全人类的节日,被称为“人日”。一个出生在“人日”的人却在自己营造出的笔墨世界中没有给任何一个人—包括自己—留下一个位置,只用寥寥几笔淡墨勾勒出一座空空荡荡的亭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洁癖对于倪瓒似乎是很自然的。当初,接触人间的主动权掌握在倪瓒手里,想见谁、不想见谁全凭他自己的喜好,他可以随时关上清閟阁的大门,为自己保留一个纯粹而洁净的世界。而在他并不频繁的出游交往中,朋友们也会谅解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迂兄弟,对他的种种荒唐行为尽可能给予包容。
有一天,倪瓒和几位朋友聚会喝酒,一位著名诗人也在场。喝得兴起,诗人突然做出了一个很符合诗人性格的放浪举动:脱下身旁陪酒侍女的鞋子,将酒杯放了进去,大家轮流捧着鞋子喝酒。倪瓒见状大怒,竟然一把推翻桌子,破口大骂龌龊,拂袖而去。朋友们虽然扫兴,但也只能相对苦笑。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倪瓒开始独自支撑庞大的倪氏家族而被画上句号。从此,再不由倪瓒挑三拣四,三教九流,他想见得见,他不想见也必须见。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从前他远远遇到都要闭上眼睛捏住鼻子避开的粗俗汉子—税吏、保甲、衙役,如今都可以欺凌、敲诈倪家。从小没学过低头的倪瓒不得不屈辱地弯下腰,生涩地陪起笑。
倪瓒的洁癖更是令他比普通人多吃了许多苦头。
在元朝廷杀鸡取卵式的盘剥下,江南富户纷纷破产。倪瓒不善理财,倪家更是首当其冲,倪瓒也因欠下巨额税粮无力偿还而被关入了监狱。蹲班房时,每逢开饭,他都要求送饭的狱卒将盛放食物的托盘举到齐眉高。狱卒纳闷,问他原因,倪瓒闭口不答。旁边的难友点破了其中的奥秘:这是怕你的唾沫落到饭里。狱卒大怒,干脆拿链子把倪瓒锁在了马桶边上。
陪伴马桶度过的一夜让倪瓒难受得死去活来,他彻夜呕吐,连胆汁都吐了个精光,从此落下了脾泄的病根。不过换个角度看,这位狱卒也似乎试图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拉倪瓒回到烟火人间。
类似的努力,很多年前就有人做过。
那是倪瓒刚开始当家的时候,有一次,倪母得了急病,想请江南名医葛仙翁诊治。那天天气不好,下着雨,葛仙翁提出要倪瓒牵着他那匹最心爱的白马来接自己。倪瓒无奈只好答应,葛仙翁骑上马后,故意从泥潭中过,人和马被溅了全身污泥。到倪家之后,葛仙翁先不看病,要求先上清閟阁瞧瞧。倪瓒不敢拒绝,葛仙翁也不换鞋,就那么脏兮兮地登上了楼,将所有古玩图书乱翻一气,还不停咳嗽吐痰,将整个清閟阁搞得一塌糊涂。倪瓒不能发作,心疼得几乎当场昏厥。
后来有人说,葛仙翁这样做是有意为之,因为他看出倪瓒生有仙骨,想点化倪瓒、令其看破洁与浊,只可惜倪瓒始终不能领悟。
换句话说,对于人间的领悟,倪瓒固执地采取了另一种只属于他个人的方式。
在1368年秋天,67岁的倪瓒为朋友画了一幅墨竹,并在画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著名的题款:“余之竹……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倪瓒这样表达自己对绘画的理解:“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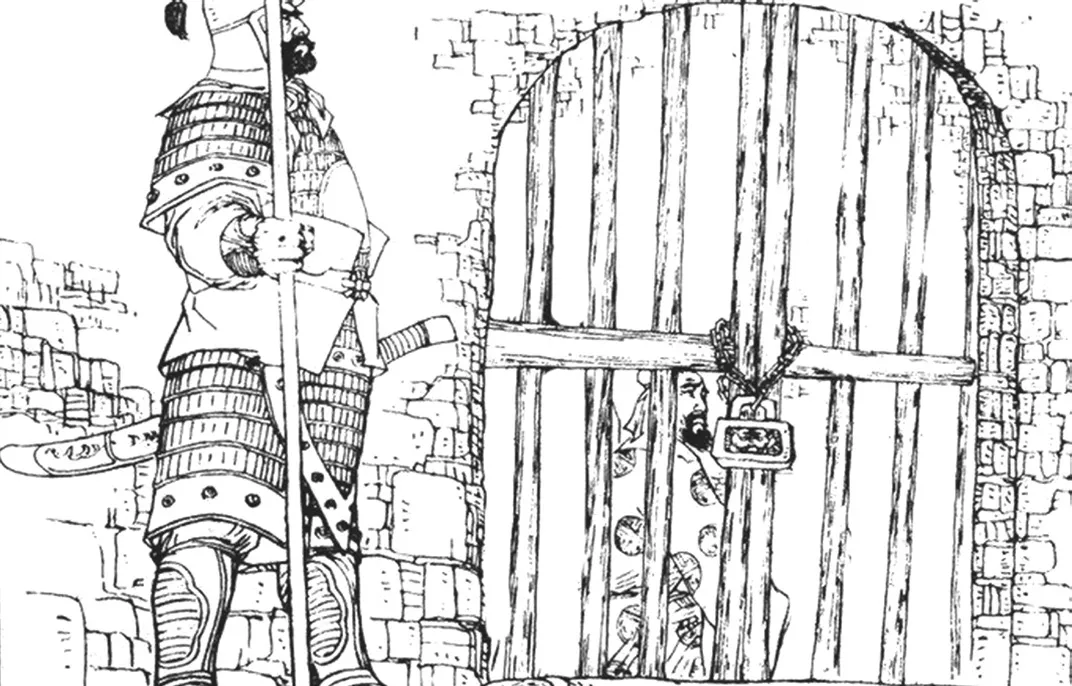
“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他画的是竹,旁人看来是麻芦。在倪瓒的眼中,一切都不再是原来的模样了。天地之间,所有庞杂的颜色都已然淘净,只剩下了黑白二色。
他胸中一股郁气蜿蜒吞吐,随物赋形,从此,竹不再是竹,石不再是石,山不再是山,水也不再是水。
在倪瓒的世界中,有如破茧化蝶,万物都挣脱了各自不够完美的躯壳,呈现出了最本真的神韵。
那么人呢?
一想到人,倪瓒脑海中又浮现了那年在宜兴做的梦。刹那间,群魔又在他面前出现,他们挤眉弄眼,做出各种丑陋的表情,带着野兽令人作呕的腥臭,无数张或是狰狞或是猥琐或是阴险或是谄谀的鬼脸将他围得水泄不通。倪瓒厌恶地闭上了眼睛。
他告诉自己,这就是人间的真相。所以,他只能出逃。
弃家那年,倪瓒写过一首诗描述逃出无锡的情形,最后一句是:“挈家如出鬼门关。”
初入太湖的那些年,倪瓒手头还有些积蓄,虽然居无定所,但日子过得还算舒适。被他当做家的船并不是普通的渔船,而是经过精心装修的大船,雅洁而舒适。他在船上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中也往往有赏古玩、集书画、馈赠鱼酒、听人弹琴等高雅内容。他还在吴江附近买了座小别墅,戏称为“蜗牛庐”。可以想象,倪瓒早期的流浪生活虽然比不上在清閟阁时,但也悠然自得,别有一番野趣。
有人描述过倪瓒不无高调的湖上生涯:出游时,他的小船垂翠幕、焚异香,倪瓒则一袭白衣,在氤氲的香烟中独立船头,须发飘扬,大袖翻滚;船行所过之处,闻讯赶来观看的人都会在两岸排成两道人墙,人人都怀疑这是神仙下凡了。
值得注意的是,倪瓒对焚香的癖好维持了终生。人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倪瓒对自己的最后一重保护—用氤氲的香烟笼罩全身,将自己与这个肮脏的世界隔绝开来。
然而,这只是美好的幻想。有一次,他还因为这个癖好差点儿丢了性命。
张士诚割据东南,他的弟弟听说倪瓒善于作画,便派人带上重金向倪瓒求画。倪瓒一口拒绝:“我不能当个王门画师!”还当着使者的面撕裂了张士诚之弟给他作画的白绢。张士诚之弟因此怀恨在心。一天,张士诚之弟乘船游太湖,闻到芦苇丛中传来异香,认为倪瓒一定就在附近,当即命人搜索,果然搜出了倪瓒躲藏的渔船。张士诚之弟大怒,想当场杀了倪瓒,幸亏旁人求情才住手了,不过还是命人将倪瓒痛打了一顿。事后,有人问倪瓒:“你当时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呢?”倪瓒回答道:“一说便俗。”
毕竟,这是一个人类的世界,谁也无从逃避。很快,倪瓒发现,太湖的云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浪漫,而一叶扁舟也避不开现实的残酷重压。
有出无进,坐吃山空,加之倪瓒禀性豪爽忠厚、视钱财如粪土,对朋友的需要有求必应,他的口袋渐渐见底,开始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
倪瓒晚年的诗文时常会哀叹生活的困顿。69岁那年的五月,他与三五好友聚会,午饭时间过了,主人家还是筹办不出食物,大家只好你出一瓶酒、我买一点儿面筋,加上一点儿酱蒜苦荬菜将就着果腹。可即使这样粗劣的食物,倪瓒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形容自己“如享天厨醍醐也”。联想到他少年时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令人不胜唏嘘。
随着年龄的增大,倪瓒在船上的时间越来越少,除了亲友家,他在寺庙道观留宿最多。寄人篱下,也就计较不了干净与否了。有时遇到雨季,借宿的房子上漏下湿,他也只好坐在泥泞中悲叹。
对于倪瓒来说,清贫还不是最难忍受的,更令他痛苦的是,朋友们一个个逝去。尤其是62岁那年,夫人的去世更是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夫人是在旅馆中病逝的,从中也可看出当时倪瓒的生活状态。对于这位陪伴自己一生、吃尽颠沛流离之苦却又毫无怨言的爱妻,倪瓒内心充满了愧疚,但他竟然已经没有能力将妻子的棺柩送回故乡安葬,只能就地草草掩埋。
倪瓒的晚年过得十分寂寞,非常渴望结交朋友。他寄宿在一位朋友家时,有一天,朋友的女婿来了。倪瓒听说这个年轻人是个读书人,竟然激动得鞋子也没穿好就跑出去迎接。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更符合倪瓒的性格。见面之后没说几句话,倪瓒竟然狠狠地打了对方一耳光,骂道:你小子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滚!
暮年,倪瓒也没有降低对人的标准。这份不可化解的寂寞最终渗入笔端,使他的作品愈发苍茫寂寥。
倪瓒老年喜欢画墨竹怪石,一贯的空灵萧疏之外,用笔更加枯瘦,气质更加冷傲孤寂。
这一时期的倪画还有一个特殊现象:题款时,倪瓒一概只书写干支,从不提及年号。而那时已经是朱元璋执政的大明洪武年间了。
倪瓒一生经历元明两朝,都没有出仕,这也是他被称为“高士”的原因之一。明朝后期,倪瓒被朝野视为不事元廷的气节之士。不过他们故意回避了这样的事实:与入明后只书干支恰恰相反,倪瓒在元朝时的作品常常题有元顺帝“至正”的年号。
很多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阐释,分析倪瓒究竟是“明处士”还是“元遗民”。倪瓒如若地下有知,对此大概只能苦笑,还一句“一说便俗”。
不书年号,只是因为倪瓒看了太多英雄豪杰闹哄哄的表演,逼得他的洁癖由空间发展到了时间,因此题款时将世俗强加给岁月的玷污尽行洗去,回归纯粹罢了。
看破了时空的倪瓒终于得到了真正的彻悟。
明朝的建立对于倪瓒也不是全无意义的。革故鼎新,天下重新安定,前朝的欠税一笔勾销,倪瓒便有了回家的希望。
对于一个在外漂泊了十几年、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没有什么比叶落归根分量更重的梦想了。事实上,在太湖上流浪的那些岁月中,回家的念头一直萦绕在倪瓒心中,尤其是丧妻那年,当他见到一幅已经去世的故人描绘的无锡风景时,还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不归吾土亦已十年”的感叹,竟“不能自已,捉笔凄然久之”。
这种思乡情绪与日俱增。71岁那年,在一场初夏的雨后,他不顾体衰臂痛,画了一幅《清閟阁图》,同年还为故乡的朋友作了一幅《容膝斋图》。在图中,倪瓒题下了一首诗赞美故乡风景,并声称“他日将归吾乡”,憧憬着到时登上画中的书斋,举起酒杯,再次赏玩此画,“当遂吾志也”。
“吾志”大概是这样的:“屋角,应该有几株杏花,门前,种一片竹林;房子也不必太大,能容得下两三个好友对坐就行。最好,能面对着太湖,能听到鱼儿跃出湖面的声音。我将在那里,度过我所剩无几的余生……”
但他已经回不去了。确切地说,无锡已经没有了他的家。
1374年秋天,倪瓒回到无锡,但无处居住,只能搬到邻县江阴,借寓在亲家家中。当时倪瓒的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之前因狱卒虐待引发的脾泄症日益严重。中秋,亲家开宴赏月,一生嗜酒的倪瓒竟然已经不能再喝酒。
这年年底,倪瓒溘然病逝于江阴,时年73岁。
饱含着倪瓒乡情的《清閟阁图》早已不知所终,《容膝斋图》至今犹存。画面上是典型的倪瓒式“一河两岸”构图,近景的土坡上照例有一座四角茅亭,亭下照例空无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