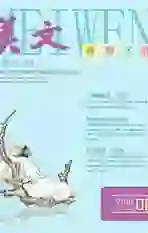昨日饮酒赴雅集,今日兰亭空一人
2018-06-15汪驰
汪驰
春日乍现,发觉时已是暮春,不知是否还有人留意春日瑰丽的曼妙时光。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最伟大与随性的文集,莫过于这场让所有人倾醉倾倒又为之迷恋与痴狂的曲水流觞。
而这杯温黄酒盛在檀木盒中,在历史与文学的过去中漂荡了许久。上游曼舞下的桃瓣,是江南盛放之后的满园春色。那样的情怀令人彷徨,但它却美得渐行渐远。
这种让所有文人向往的,在意料之中却又在情景之外的洒脱,又要到哪里去找呢?
现在的人们早就沉睡在大都市的灯红酒绿与霓虹晚霞之中,不知寒暑,有几人醒来?我问了问身旁之人,竟无一人知晓那暮春的雅集,甚至连“觞”这个字都无从知晓。
可问起《兰亭序》,那是家喻户晓。人们记得它,也许是周杰伦的一次纸扇清摇,只是因它有名,而不是有魂。因名而记,这种想想都可笑。可现实给予我们的就是如此,却也是无可奈何的。
我有几个朋友也学书法,但并不热爱书法。其中有人在行草行楷方面更胜于我,可他们对于古典之触感却是一丝一毫都没有,只是照猫画虎。
我曾经与四五个志同道合的人在云南游玩,寻到一处山峻水清、树荣草盛的秘境。那里有一条小溪向山脚淌去,蜿蜒曲折,如曲渠一般。我们便叫成年人买来土酒,放到从村子里借来的木盘中,置于中游(因为找不到尽头)。我不知古人是如何做到的,我们的木盘总是被溪中的棱石碰翻。尝试了十几次,只成功寥寥几次。我们实在作不出诗,象征性地润湿嘴唇,虽未痛快饮酒,却也留下了情怀。
村中外出打工的几个年轻人看到此景,他们于是在背后嘻笑指点。我们也不理睬,依然乐在其中。我们的文集与雅怀,与古人相比自是相形见拙,但我们依然期盼着有一份情怀让我们浸润自己的灵魂。
这比起今日那些有钱有权,占有着贵重雅物的土豪,却是多了他们所不能及的东西。
柴静曾经这样评价野夫:“这个年头处处都是精致的俗人——不是因为不雅,而是因为无力,无情怀,没有骨头。”还好“礼失,求诸野”,遗失的道统自有民间传承,江湖还深埋了奇人隐者,诗酒一代。
但也看见过大腹便便、油嘴肥肠的秃顶中年人,在茶馆中用紫铜香炉点着香,抿着上等的茶与大红袍,戴着串佛珠,笑谈今年又赚了几百万。
这却已然不是可笑,而是让我汗毛直立了。
大街上四处都是这样的俗人,他们的“雅”不在于自身言行与气质,只需别人看他有品味,有所谓的情调就心满意足了。
人们能将这种“雅志情怀”包装成所谓的有格调,实在让我痛心。而那雅集却像是昨日之事,我们就像喝醉酒的人,也确实因头痛而忘却了离愁。
但世上却也有许多人拥有雅怀。
野夫与苏家桥一行人喝到酣处,学魏晋中人裸体上街散心头热,恰路遇一些机关门前挂着的木牌,就去摘下,抬着一路狂奔,找了个角落扔下。有次扔完发现木牌上赫然大书“人民法院”,觉得这个还是不惹为好,便又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挂上。
而这也只是诸多事务中小小的一件,却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洒脱。
他面粗而雅细。在郑世平的家庭中,父亲并没有保护家庭,他的职责是抓捕地主及儿子。母亲也是在暮年投入长江,翻遍浮尸无果。
我曾读过一篇散文,作者与他人有机会共赴蘭亭,有的人身穿晋服却接着电话,手拿事先准备好的诗稿,无人在意与明了所谓雅集流觞到底意味着什么。
三月上巳日,人们水边饮宴、郊外游春,从西周便开始传承,是否断在我们手里?
而公元前352年的暮春,从上游漂下的盛满黄酒的觞,好似迷失在了那桃园芳华的江南情怀中。
在那纵诗美酒的年代,却只有十一人各成诗两篇,十五人各成诗一篇,而在这42个才华四溢的诗人之中,依然有16人未能成,各罚酒二觥。
有人作出千古绝唱,万年名句,被世人景仰。
这即兴赋诗饮酒的风雅是雅集的基础,若真为雅集,那飘逸情怀便为必然。
想必王羲之也没想到千万年无人超越的妙言,在雅醉时竟是挥笔而成。
昨日的兰亭,是否依然敞着那紫檀大门,又是否如《石渠宝续编》中所记述的“临流而弹,竹涧焚香,登峰远眺,坐看云起,松亭试亭,曲水流觞,相波钓叟 ,蓬窗富卧?”
而我的梦里,兰亭依旧,却唯有王羲之一人围着曲渠张狂豪放地饮酒。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有点寂寞地笑着,把手伸给我。而我疯狂地奔跑,企图去触碰那双手,但它却又飘忽而去,怎么也够不着。
我想,现在的兰亭仿得真像,而过去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王羲之最爱的墨竹与白天鹅失去了野性,一切都那么合理。.
到底是什么吞噬了这一切,是我们还是时间?
随着漩涡消去,只留下《兰亭集序》。我想几十年后,是否还有人认识酒与诗,是否还记着那春日乍现的暮春,是否还拥有自由洒脱,拥有那样的散文与雅集?
昨日饮酒赴雅集,今日兰亭空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