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找食儿去
2018-06-12谢淼焱
谢淼焱
餐厅边上有一个小柜子,是女儿专门用来存放各种零食的,就现在的经济条件来说,保持她柜子里的零食取之不尽,已经不算什么难事。每每女儿拿出自己心爱的小点心要与我分享时,我总是象征性地吃上一点,除非是当真饿了,否则,没觉得她那堆宝贝疙瘩对我有什么吸引力。
“爸爸,难道您不喜欢吃零食吗?”女儿鼻头皱出个小川字,不解地问我。
我笑,摸摸她的头,说:“不是我不喜欢吃,只是你的小柜子里,找不到我想吃的。”
尽管我说的是实话,但女儿不一定听得懂,因为我的童年与她的相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物质相对匮乏的80年代,我生活的小山村基本还是刀耕火种,食物全靠自给自足,小孩子的零食也不例外。过年的糕点、饼干,需要阿妈用小石磨一点点推出来,虾片、粉条也得把红薯一个个捣碎,用筛子一把把将淀粉筛出来。就算最简单的应季水果,也得自己爬到树上去摘,自然生长的果树杆高、枝长,摘几颗果子也非得费一番周折不可。像一年生的瓜果、小菜,更得从春到秋一点点守望,往往一垅地伺候大半年,到头来也就够呼朋唤友吃个三两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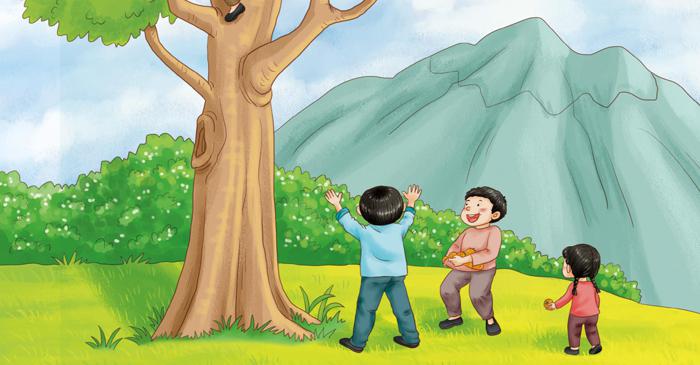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肯德基是什么鸡,也不常能见到冰淇淋和巧克力,这些东西,至少要到镇子以外的地方才能找到。有一回,过年时跟阿爸去县城,他给我买了一块巧克力,那玩意儿,泥乎乎,苦不拉叽的,不好吃。这种味觉印象,一直影响着我对食品的选择,除了来自村子里的东西,外面的一概不好吃。我们的美食必须经由自己找寻,在家门洞开、路不拾遗的村子里,随手到别人园子里摘几个瓜果,在人家门前的晒篮里挑几样点心,算不得偷。于我们而言,整个村子就是一个巨大的美食广场,我们总在村子里四处转悠,口头禅便是——走,找食儿去。
找食儿去,山里没有去河里,东家不行去西家,偌大个村子,总能找到想要的好东西。我们对季节的判别,甚至也与美食有关。春天到了,映山红开了,那花瓣儿酸溜溜甜滋滋,摘一朵丢进嘴里,芳香四溢,连同春天的味道一齐吃进了肚子里;夏天到了,知了在琵琶树上叫个不停,知了喜欢待的地方,琵琶一定熟得早,坐在树上挑最软的一颗扯下,就那样毛茸茸地囫囵吞下去,一个夏天都藏在了心间;秋天到,叶子黄,黄叶子下面,藏着各种各样的美食,挂满长刺的野板栗轻轻一摇就掉下来一大团,一脚狠踩下去,栗子蹦出老远。还有绯红的野柿子,刚摘下来时太苦太涩不好吃,必须到石灰坛子里闷个十天半月才能熟透,还有野草莓、桑葚、沙棘果、丝茅根、嫩刺芽,这些都是信手拈来味道不错的美食。就算是冰霜覆盖的冬天,各家屋里自制的食品也取之不尽,这些东西,都是从四时八节里储备而来的。果脯菜干家家都在做,但每一家的作料不一样,味道也大有出入,谁家的好吃,谁家的难吃,我们掰着手指头说得清清楚楚。你若问我怎么知道得这么详实,嘿嘿,就不告诉你。
要说地瓜干,当数凤婆婆家的最好吃。凤婆婆办事妥贴,地瓜干也做得精致,地瓜是和着大红枣一同煮的,还抹上糯米浆,晒干后又香又软,想起来就流口水。那一次,田娃嗅到了味道,确定凤婆婆又煮了一大锅地瓜,为了防止我们这群馋猫半路袭扰,特意晒在屋后的天井檐下,足足两大盘,黄澄澄的煞是惹人。
“怎么样?”田娃一想到风婆婆家的地瓜干,嘴里便像含了颗酸梅,口水就止不住,一阵阵往外涌。
我也咽了口唾沫,手痒得不行,握着拳头挥了挥。
我们俩一对眼,不用开口,一句话已经从眼神里流出来——走,找食儿去。
“那梅梅去不去呢?”田娃说,他指了指自家的跟屁虫小妹妹。
“当然要去,咱什么好处都少不了梅梅,不过,她在山坡下等着就行,如果一个人待着害怕,可以让我家猴子陪着她。”我说。
猴子是条狗,年龄和我差不多。猴子也是大家的朋友,它乖巧,驯服,听得懂人话。事情就这么安排完了,梅梅由猴子陪着在凤婆婆家后山的山坡下玩耍,我们两个前去找食儿。
梅梅和猴子到达山坡下时,我和田娃正在漫山遍野地找蚂蚱。我最先抓到一只褐头青身的大蚂蚱,得意得不得了:伙计,一会儿就靠你大显神通了。我用一根准备好的长棉线将螞蚱牢牢捆住,小心地塞进口袋中,动作轻巧,像捂着个宝贝。
“你们干什么呀?”梅梅没见过我们的手法,好奇地问。
“抓蚂蚱呀,没看见吗?”田娃一边说着话,一边扑向前方的草丛,也抓到了一只,尽管嘴里啃了一把沙土,但由于手里的蚂蚱够大够壮,他还是满欢喜的。
“蚂蚱能吃吗?”梅梅表示不解,因为她得到的消息是跟我们来找食儿的。
“蚂蚱不能吃,可蚂蚱能帮我们找食儿啊,你等着,一小会儿工夫,我们就有好吃的了。”我俩捂着各自的蚂蚱,一溜烟地朝凤婆婆家房后摸去。
猴子站在梅梅身边,伸着舌头,摇着尾巴,静静地等着我们。
这一带的树林子,我们天天在里面摸爬滚打,熟络得很,三绕两绕,就绕到了凤婆婆房后。我先出去探了探地形,确认凤婆婆没在天井里,便站在土坎上向田娃招招手,从怀里掏出用棉线捆好的蚂蚱使劲往下一扔,那蚂蚱刚好落在晾地瓜干的盘子里,蚂蚱着陆后,拼了命地抓住一个地瓜干,想以此逃出我们的控制,这时候,我们只需慢慢将棉线提起来,一点点小心地往上收,一个硕大的地瓜干就成了囊中之物了。
一次,两次,三次,我们乐此不疲,直到口袋都鼓起来了,我才轻喊一声:“撤。”
我们像打了胜仗一样回到梅梅身边,围坐成一圈,将口袋里的地瓜干掏出来,分给梅梅。我还将顶大个的一块塞进猴子嘴里,猴子试探着咬了几口,发现有点不对它的口味,忙不迭地吐了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失望地看着我们三个。
梅梅吃了两块地瓜干,捂着脸说:“不好吃。”
“你们两个,”我指了指猴子和梅梅,“这话要是让凤婆婆听到,估计得气半死。”
一场找食儿的历险因为梅梅和猴子的不喜欢而有始无终,我不服气地问:“那你想吃什么?”
梅梅倒也爽快,挥舞着小手抱成一个大圆圈,说:“我想吃西瓜,大大的西瓜,从中间劈开,拿勺子一勺勺挖着吃。西瓜才好吃呢,地瓜干不好吃,太硬了,咬得腮帮子酸痛。”
“西瓜?”我和田娃瞪大了眼睛,西瓜太大了,超出了我们的找食儿范围,平常随便到别人家里摘两个桃子李子,确定人家不会把我们当贼,但如果真要到地里去摘西瓜,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我们的屁股会不会因为这事挨上板子,谁都说不准。
可是,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被一个小丫头给难住呢?就算梅梅要的是地雷,我们也要想尽办法挖回来。在村子里,就没有我们办不到的事,无非是要冒一些险罢了。
“问题是,哪里有西瓜啊?”田娃犯愁地挠了挠脑袋,说。
“哪里有西瓜?村头罗爷爷地里就有西瓜,你没见他总是挑着西瓜在村子里叫卖吗?那西瓜就是他家种的。”我说,这事我已经观察很久了,只是兜里没有钱,一直没尝过罗爷爷的西瓜。
“这好像有点难,”田娃皱着眉头说,“罗爷爷可凶可凶了,看他一眼腿肚子就发酸,谁还敢上他家去找食儿,再说,罗爷爷瓜地里还有大狼狗呢,那狗比罗爷爷更凶,别说去偷瓜,就是打他家瓜地里过,也要冒一身冷汗。”
“有我们家猴子在,罗爷爷那条狗算个什么?我看,梅梅吃西瓜的事情,咱还得抓紧办,不如今天晚上就行动,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说不定没那么难呢。”我说。
梅梅听完我俩的决定,站起身来拍着手掌跳起了圈圈舞,嘴里欢快地喊着:“噢,西瓜,西瓜瓜……”
猴子看到梅梅高兴的样子,也卖力地摇头晃尾巴。
当天傍晚,田野里蛙鸣声此起彼伏,我和田娃悄悄出发了。罗爷爷家的瓜地就在村口池塘下的旱田里,借着明亮的月光,远远望去,罗爷爷把凉床架在了瓜地埂上,上头还用竹竿儿挑起一顶蚊帐。罗爷爷在凉床上睡大觉,只有他家的大狼狗在瓜地里跳来跳去地斗小虫。
我拍了拍猴子的脑袋,把它往前一推,说:“猴子,靠你了。”
猴子哼哈着打了个喷嚏,撒欢往瓜田跑去。人有人的交往,狗也有狗的交情,猴子跑到瓜田边摇着尾巴东拱拱西嗅嗅,还在罗爷爷的凉床边撒了一泡尿。那条大狼狗对猴子的到来熟视无睹,看来,它们也算是老朋友呢。猴子在瓜地里悠闲地转了一圈,然后转身就往池塘边的山林里跑。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这死猴子,叫它去探路,怎么自己跑山里去了呢?话还没有说完,那条大狼狗竟然也打着响鼻,跟着猴子往林子里钻去。
我一拍脑门,才算明白过劲来,看来这猴子比我们聪明多了,都知道用上调虎离山的计策了。
眼见着大狼狗消失在山林中,我朝田娃一挥手:行动!两人鱼贯而出,摸进了瓜田里。
田娃直接奔向月光下泛着青光的大个西瓜,我却并不着急下手,一个就地十八滚,滚到了罗爷爷的凉床下,将蚊帐的下摆一把抓过来,绕着凉床底下打了个死结,然后才放心地摸向瓜地。
我俩摸到了自己的目标,田娃一时得意,竟然举起手中的大西瓜,重重地拍了两下,装模作样地举到耳畔听了听,然后说:“哎哎,熟透了呢!”
田娃的这个冒失举动把我吓出一声冷汗,压低嗓子想制止,已经来不及,拍瓜声惊醒了罗爷爷,手电光立时就在瓜地里扫射。
“谁?谁在地里?”罗爷爷大喝一声。
我俩迅速趴在地上,大气不敢出,一动也不动。
罗爷爷起身就想往凉床下跳,找了一圈却找不到蚊帐的出口,急得他弓着身子在凉床上团团乱转。
我一见形势不妙,抱起西瓜,撒腿就跑。
罗爷爷越急越找不到出口,气得在蚊帐里嗷嗷大骂:“哪里来的小毛贼?让我抓着了,扒你们的皮!”说话间,我俩已经窜出瓜地,來到了山林里。
在林子里立定,我俩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好在手里的西瓜都在,今天的战斗基本顺利。
我抱起西瓜欲往村里走,田娃这时却蹲在地上,忧心忡忡地不肯离开。
“怎么啦,扭脚了?”我问。
“坏了坏了。”田娃自顾自地说。
“什么坏了?西瓜摔坏了吗?没事,摔坏了也能吃,梅梅不吃咱们也得吃。”我说。
“我书包丢瓜田里了。”田娃哭丧着脸说。
“你怎么背个书包出来呢?又不是上学。”我责怪道。
“双手只能抱一个,好不容易找一次大食儿,我想用书包再背一个。刚才罗爷爷一喊,我忘了书包的事,抱着瓜就跑了。我那书包里还有作业本,上面有我名字呢。”田娃说。
“死定了,这回死定了。”我说。
“那咱们把西瓜送回去,认个错,大不了挨顿揍呗。”田娃实在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说。想着罗爷爷那凶巴巴的样子,我就犯了蔫。
“要不再等等?等罗爷爷睡了,再去把书包捡回来。”田娃试探着问我。
可是,自从发现有人偷瓜以后,罗爷爷就把他那看瓜用的大矿灯挂在了床架上,把进瓜田的路照得通亮,等到后半夜,也不见罗爷爷有放松的样子,我俩只好悻悻地抱着西瓜各自回家了,到了家也不敢把西瓜拿出来,找个地方埋起来,等着明天罗爷爷找上门来,也好把西瓜原封不动还回去,这样挨板子的时候估计可以少几下。
想着明天一早,田娃的书包就会被罗爷爷发现,而田娃免不了要把我也供出来,我辗转反侧,静等着一早的开堂会审。田娃当然也好不到哪去,无论怎样,这件事情如果败露了,他的处境比我要坏更多。
鸡叫头遍的时候,我就早早起了床,坐在门槛上,惶恐不安。门前的路才刚刚看得清人,田娃已经急匆匆跑了过来,趴在我耳朵边说:“你说这事奇怪不?”
“什么事?”
“书包,书包自己跑回来了,挂在我家大门口,而且,里面还装着一个大西瓜。”田娃满脸惊诧。
这事有什么好奇怪的嘛,秃子头上的跳蚤,明摆着,书包就是罗爷爷赶早送过来的。不仅送过来,还白给了一个西瓜。
那天上午,我们三个围坐在一起,以梅梅最喜欢的方式,拿勺子分吃最大的那个西瓜,直吃得肚皮鼓鼓,直不起腰来。
吃完西瓜,我和田娃满脑子都是对罗爷爷的愧疚,但又不敢主动去道个歉。于是悄悄打探到罗爷爷的西瓜多少钱一个,决心在假期里去挖泥鳅、捡田螺换钱,把三个西瓜的钱挣回来,然后找个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给罗爷爷送过去。
那笔瓜钱到底送没送过去,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有一次给田娃打电话,说起这事,田娃在电话那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完说:“送是送回去了,但送回去以后,紧跟着的几天,我们几个就搬到罗爷爷的瓜田里,吃了个天翻地覆……”
我说:“那些个搬到罗爷爷瓜田里的人,绝对没有我,要不然,我怎么一点印象没有呢?”
田娃在那边又笑开了:“你记不起来,不证明你没去,也许你当时被西瓜给撑傻了也说不准。”
我拍一拍脑门,这事没记起来,到另一家找食儿的趣事,却在脑海里一点点清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