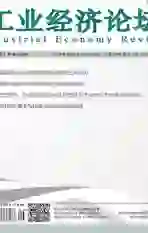真实型领导、真实型追随影响工作繁荣和主动性行为的多层次研究
2018-05-30张建平林澍倩
张建平 林澍倩
摘 要:探索员工主动性行为的驱动因素与促发机制是当前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作者从自我决定理论(SDT)的视角出发,构建了团队真实型领导、个体真实型追随共同影响主动性行为的理论模型,以48个团队中298名成员的调研数据为样本,采用Mplus7.0 统计程序包进行跨层结构方程路径分析来检验研究假设。结果显示:(1)真实型领导、真实型追随对工作繁荣有显著正向影响;(2)真实型领导调节了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的关系;(3)工作繁荣对主动性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4)工作繁荣在真实型领导、真实型追随与主动性行为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5)真实型领导调节了真实型追随通过工作繁荣间接影响主动性行为的关系,即在强真实型领导的团隊中,这一间接效应越强。
关键词:真实性;真实型领导;真实型追随;工作繁荣;主动性行为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866 (2017) 04-001-013
工业经济论坛 URL: http//www.iereview.com.cn DOI: 10.11970/j.issn.2095-7866.2017.04.001
Abstract: It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o explore the drivers and mechanism of employee proactive behavior. Using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s a guiding framework, the authors propose that authentic leadership, authentic followership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employee thriving at work, which, in turn,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employee proactive behavior. The authors conducted a survey study of 298 employee from 48 working teams. The results provide evidence of positive relationship for both authentic leadership and authentic followership with employee thriving at work in a cross-level model where authentic leadership was aggregated to the group level of analysis. Cross-level interacti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uthentic leadership strengthe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entic followership and employee thriving at work. Employee thriving at work was shown to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of authentic leadership and authentic followership with employee proactive behavior. Perhaps most important, cross-level moderated mediation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authentic leadership strengthe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entic followership and proactive behavior via thriving at work.
Key words: Authenticity; Authentic Leadership; Authentic Followership; Thriving at Work; Proactive Behavior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和全球化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企业经营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扁平化、团队、授权、自我管理、项目孵化等话题充斥着所有商业企业[1, 2]。在此环境下,企业越发依赖员工超越狭隘的工作界定与要求,自发学习新技能、主动识别潜在威胁与机会,并积极投身于问题解决中[3]。主动性行为(Proactive Behavior)成了组织有效应对外部挑战和不确定性的关键,它是员工自我发起的、着眼于未来并试图改变现状的积极行为,能给员工、团队和组织带来正面影响[4, 5]。然而,组织和管理者却难以对其预先指定或标准化,只能依靠员工的自发与自主。因此,探索主动性行为的驱动因素及促发机制成了当前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研究发现,领导者的风格、态度和期望是主动性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4]。但相关研究还不够完善,研究者多局限于探讨变革型领导行为、领导愿景激励及领导-成员交换质量对主动性行为的影响,而较少考虑其他领导类型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一些组织在经营中诚信缺失及部分领导者不道德行为频发,管理实践领域和学术界开始推崇真实型领导(Authentic Leadership)的重要性[6]。真实型领导者(Authentic Leader)诚实、正直、忠于自己,会与下属建立真实的关系(Authentic Relationship),被认为是其他积极领导类型的“根源构念”[7, 8],也被认为契合了中国人对领导者德才兼备中“德”的要求[7]。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真实型领导与主动性行为的关系,而是探讨其对组织公民行为、创新行为、谏言行为的影响,但上述行为与主动性行为是既有联系又显著区别的[9-11]。组织公民行为不一定是自发的,也未必是变革导向的;创新行为虽属变革导向,但未必出于自发;谏言行为虽是自发、变革导向,但主动性行为的范畴要比其广得多[11, 12]。因此,为深入了解真实型领导的效能,且扩展主动性行为驱动因素的研究,探索两者间的关系显然极其必要。另外,领导力(Leadership)的研究长期以来都延续着领导者中心(Leader-centric)视角,很少考虑追随力(Followership)的作用[13]。因此,我们将响应Gardner等[6]的呼吁,将真实型追随(Authentic Followeship)纳入研究框架。从主动性行为的研究趋势来看,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是主流研究取向,但较少探讨二者共同作用下给主动性行为带来的影响[11]。我们预期真实型追随,即员工与领导者共事时呈现真实的自我[14](To Be Their Ture Self)会对其主动性行为的实施带来影响。
此外,主动性行为由员工自我发起,它的实施受员工自身心理状态的直接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心理资本、角色广度、自我效能等在领导影响与主动性行为关系间起中介作用[4]。然而,主动性行为的实施是一个过程,涉及到发现问题、构思解决方案、实施方案,故必然会受员工自身能力感知和精力状态的影响,工作繁荣(Thriving at Work)正是反映员工能力感知与精力状态的构念。在Spreitzer等[15, 16]看来,工作繁荣是个体在工作中同时体验到“学习(Learning)”和“活力(Vitality)”的综合心理状态;其中,活力维度体现了个体在工作中活跃且充满热情;学习維度则代表个体获取和利用知识与技能树立信心的能力。研究表明,工作繁荣的员工有着更高的工作绩效、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及更低医疗支出[17, 18]。本研究拟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视角出发,探索工作繁荣在真实型领导、真实型追随与主动性行为间的中介效应。
总的来讲,本文将以自我决定理论(SDT)[19]为分析框架进行跨层次研究,从团队领导和个体追随的二元视角去剖析上、下级真实性(Authenticity)对主动性行为的影响。首先,可以同时从个体和团队层面去揭示主动性行为的驱动因素;其次,有利于推进现有领导力的研究,将追随力纳入到领导力研究中;再者,有助于揭示促发因素和主动性行为间新的中介机制;最后,本文还对工作繁荣的相关研究有所贡献,将实证检验Spreitzer等[16]提出来的工作繁荣的“工作中个体成长整合模型”(Integrative Model of Human Growth at Work)中的部分内容,即工作繁荣对个体主动性性(Proactivity)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丰富现有真实型领导、真实型追随、工作繁荣和主动性行为的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领导力研究的视角。
一、理论背景和研究假设
(一)真实性、真实型领导与真实型追随的相关概念
真实型领导与真实型追随的概念共享“真实性”这一内核,真实性一词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拥有自我对于你来说才是真实的”思想,现代意义的真实性概念则出自积极心理学[20]。Kernis[14]在最佳自尊(Optimal Self-Esteem)概念化研究中提出了真实性四成份模型,将其定义为“个体毫无障碍的控制真实的、核心的自我”,四成份包括:(1)与他人交往时表现真诚而不弄虚作假(真实的关系取向);(2)客观理性的加工和理解自我相关的信息(无偏见的信息加工);(3)能意识到并信任自我的动机、情感、需求及认知(自我意识);(4)以内心真实自我相一致的方式行事(真实的行为)。Kernis认为真实性是最佳自尊的外在表现,并将传统高自尊区分为最佳高自尊和脆弱高自尊,前者趋于稳定和非防卫性,后者则是不稳定的、防卫性的;脆弱高自尊的人渴望被外界认可,他们对可能威胁到自尊的信息特别敏感,倾向于实施防卫性行为以维护脆弱的高自尊,因而也阻碍了积极的自我开发与成长;相反,最佳高自尊的人能对负面信息保持开放性和非防卫性,他们更能维持内心自我和外在行为的一致性,表现为高水平的真实性。
本世纪初,国际知名企业安然(Enron)、泰科(Tyco)、世通(Worldcom)等相继爆出财务丑闻,此后人们便开始反思企业领导者的道德问题[21],希望他们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保持正直与诚实。Avolio和Luthans等[22]在领导学、伦理学、积极心理学等领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真实型领导这一积极领导理论,将其定义为“领导者将自身积极心理能力与高度发展的组织情境相结合而发挥作用的过程,该过程能激发领导和下属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积极的自我调控行为,从而促进双方共同的自我开发与成长”,真实型领导者自信、乐观、充满希望、富有韧性,拥有高尚的品德并且是未来导向的[20]。与真实性的四成份模型一致,多数学者认为,真实型领导也包括自我意识、无偏见程序、真实行为、真实关系导等内容。Walumbwa等[23]进一步将真实型领导定义为“通过提升和利用积极的心理能力和积极的道德氛围来促进强烈的自我意识、内化的道德观、平衡的信息处理和透明关系的产生,从而促进积极的自我开发的领导行为方式”。由于领导过程的参与者既有领导者也有追随着,因而真实型追随的概念也几乎同时间出现在研究文献中。Gardner等[24]认为,真实性的内容不仅能体现在领导者身上,也能体现在追随者身上。换句话说,下属的真实型追随同样具有自我意识、内化的道德观、平衡的信息处理、透明的关系等内容。随着近年来追随力理论(Followership Theory)的兴起,大量学者强调追随者并不只是领导者影响的消极接受者,他们同样在领导——追随二元关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13]。因此,真实型追随被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该过程,追随者形成了更加自主的工作动机,并以主人翁、开放性和非防卫性的意识去处理与他们的工作相关的任务和领导关系[24, 25]。
(二)真实型领导与工作繁荣的关系
工作繁荣被界定为:“个体在工作中同时体验到“学习”和“活力”的综合心理状态”[15, 16],“学习”和“活力”分别代表个体成长的认知成份和情感成份。“学习”是指个体感知到自己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在工作中得以持续提升;“活力”则反映了个体在工作中活跃且精力充沛、充满热情,二者对工作繁荣缺一不可。学习有余而活力不足,繁荣体验将大打折扣,易导致厌倦;活力有余而学习不足,繁荣也将难成气候,个体成长将停滞不前[18]。繁荣的员工会感知到自身的持续成长与工作动力,表现为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不断学习和日臻完善。尽管当前工作繁荣的研究还较为缺乏,但已初步证实它能提升个体的短期效能和长期工作适应能力[26, 27]。工作繁荣为个体提供了自我调节的内部线索,帮助员工评估自己的成长过程。对于工作繁荣的促发机制,Spreitzer等[15, 16]先后提出了“社会嵌入模型”(Socially Embedded Model of Thriving at Work)和“工作中个体成长整合模型”。前者认为繁荣的驱动因素包括部门情境特征和工作中产生的资源;后者则指出自主决策、广泛的信息共享、信任和尊重的氛围等情境因素,会通过自治感、胜任感、归属感等基本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来促进个体的工作繁荣体验,并最终影响个体的适应性、主动性性、工作绩效和身心健康。
结合“个体成长整合模型”与自我决定理论[16, 19],本研究认为真实型领导是员工工作繁荣的重要驱动力量。首先,当领导者具备较高水平的真实性时,他们的自尊类型属于稳定的、非防御性的,因而,他们较少将下属视作威胁的来源;在日常共事过程中,真实型领导总是以真实可信的形象出现在下属面前,容易在团队内部营造出上下级彼此信任的工作氛围,提高下属对组织的信任和心里安全感。因此,在团队真实型领导的带领下,员工能感受到被信任与尊重,这是促进工作繁荣的重要情境因素之一。其次,真实型领导会与下属建立真实的关系,为员工提供有积极意义的反馈信息,鼓励他们自主决策,帮助她们积极的自我开发与成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工作繁荣所需的信息共享和自主决策的情境资源。最后,真实型领导不仅追求自我的真实呈现,还致力于帮助员工成为真实的自己。当员工能在工作中按照内心真实的想法行事时,便会体验到更高的工作自主与胜任感,从而促进工作繁荣的产生。在实证研究方面,Hildenbrand和Sacramento等[27]发现变革型领导能促发员工的工作繁荣,Paterson等[29]和Russo等[30]也证实支持型领导与主管的支持行为能够预测员工的工作繁荣,而真实型领导又被认为是其他积极领导类型的“根源构念”。因此,本研究认为真实型领导能帮助员工体验到更高水平的工作繁荣。
假设1. 真实型领导对工作繁荣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的关系
尽管“社会嵌入模型”和“个体成长整合模型”并未涉及到个体因素对工作繁荣的影响。但自我决定理论的有机辨证视角指出,个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是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从组织情境方面去探讨工作繁荣显然存在一定局限性。Spreitzer等[15, 16]也指出诸如调节焦点(Regulatory Focus)、主动性性人格等可能对个体的工作繁荣有着积极影响。现有研究也初步证实了这一观点,发现调节焦点、核心自我评价和主动性性人格对工作繁荣有着显著影响[31, 32]。因此,我们进一步推测员工的真实型追随能对工作繁荣带来积极的影响。
真实型追随是指员工以一种自我主导、开放性和非防卫性的意识去处理工作相关的任务和领导关系的过程[13, 25]。真实型追随与真实型领导一样具备真实性的相关内容。Kahn[33]认为如果个体能在工作中呈现他们真实的自我,便更容易感知到工作相关的活动是出于自主动机。按照Kernis[14]对真实性概念的论述,真实性水平较高的人兼具较高的外显自尊和社会期望,他们有着真实、稳定和一致性的最佳高自尊,不轻易被外界的质疑和偏见所左右。然而,员工在呈现真实自我的同时,也可能体验到工作要求与自我能力、认知和价值观的强烈冲突。此时,真实型追随者可能会试图改变这样的处境甚至选择离开当前组织。但是,真实型追随者更可能将这些外在角色要求内化为已有的自我概念。作为成长导向的个体,真实型追随者保持着开放、非防卫性的态度去面对那些挑战他们的能力、认知和价值观的工作要求。换言之,真实型追随者较少强迫自己去保护自我形象,也很少在失败面前感受到强烈的挫折。他们在执行工作任务时都是源于内心真实的意愿,因而也更容易体验到自主感、归属感和胜任感,而这三种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正是促发工作繁荣的重要直接因素[16]。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真实型追随对工作繁荣有显著正向影响
(四)真实型领导对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关系的调节效应
自我决定理论强调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间交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认为两者会共同作用于个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19]。这与个人-环境交互作用框架相一致,个体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会积极强化对方的作用,在两者之间产生协同增强的效应[34]。因此,我们预期真实型领导能强化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间的正向关系。理由如下:领导者在与员工共事过程中呈现他们真实的自我,可以让员工意识到在当前团队中是非常重视真实行为的,不用担心呈现真实的自我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因而便塑造了一种高心理安全感的工作氛围;在此氛围中,员工可以相对轻松地承认错误、大胆尝试新事物、以及按照内心的真实想法去行事,这些事项可以给他们带来胜任感、归属感和自主感[25],此三种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又成了工作繁荣体验的“营养基础”[16];此外,在团队中承认错误让个体更容易接受新的知识和技能,而不用为维护自我的高自尊而对错误和新事物避之不及,因而更容易帮助员工体验到“学习”的心理状态。由于真实型领导倾向于对下属一视同仁,在所有团队成员面前呈现他们真实的自己,并帮助每位成员去成为真实的自己[35]。因此,在本研究的模型中,真实型领导对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关系的强化效应体现在跨层次上。基于以上论述,我们预期当团队领导者的真实性水平较高时,个体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之间的正向关系会较强。
假设3. 真实型领导跨层次正向调节了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的关系
(五)真实型领导、真实型追随通过工作繁荣对主动性行为的间接影响
“主动性”的英文表述是“Proactive”,也有学者将其译成“主动性”或“前瞻性”,本研究中采用了心理学界的普遍译法。牛津词典将“Proactive”解释为在事件或问题发生之前,通过对它们进行预见,自发实施干预行动来试图改变或控制现状,以使事件能顺利进行或问题得以解决[36]。当前学界对主动性行为的概念界定存在心理学、行为理论和过程论3种视角,但都强调自发性、提前行动和变革导向3大特征[4, 36]。Parker等[5, 37, 38]从行为视角出发的定义被众多学者所认可,即主动性行为是员工自我引导的、具有前瞻性的行为,其目的是改善环境或自身状况以适应外界的变化。在市场竞争如火如荼的今天,企业需要借助员工的主动投入、诱导他们实施主动性行为创造性地解决复杂环境下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现有研究发现,主动性行为对个体工作绩效、团队创新绩效、职业生涯成功、工作满意度等有着积极的影响[39]。主动性行为的表现形式有多种类型,包括问题与机会搜索、谏言行为、议题营销、创新引领行为、创新支持行为等[5]。尽管这些“碎片化”的行为类型都强调主动性行为的3大特征,但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既存在交叉又存在区别[36]。Crant等[40]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待整合,囿于类型学的分析思维不利于构建研究主动性行为的分析框架与研究路径,因而有学者开始从整合的视角对主动性行为进行归纳研究。Griffin和Parker等[37]通过因子分析技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类了针对自我、团队和组织的主动性行为。
尽管现有工作繁荣效果的研究集中在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和身心健康等方面,探讨工作繁荣影响主动性行为的研究相对匮乏,但Spreitzer等[16]在“个体成长整合模型”中提出工作繁荣对个体的主动性性有积极影响。Carmeli等[41]和Wallace等[31]的研究为探讨工作繁荣和主动性行为的关系提供了启发。首先,当员工在工作中体验到学习和成长(“学习”维度)时,他们便处于更加理想的状态去识别问题并构思新颖的解决方案。Amabile[42]认为在工作中持续学习能帮助个体建立专家技能(包括技术、工作流程、专业知识等),这些技能为他们从事主动性行为奠定了基礎;另外,个体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帮助他们在团队中形成专家权力,这能给他们带来更多同事的认可,从而赋予他们更多的“合法性”去实施主动性行为。其次,当员工在工作中体验到活力(“活力”维度)时,他们便拥有充足的精力和动机去实施主动性行为。Carmeli 等[41]发现“活力”体验能显著预测员工创新行为,而创新行为属于主动性行为范畴的一个子集。由于主动性行为具有变革性,通常会受到那些安于现状的同事甚至领导的反对与质疑,此时,员工对自我能力的知觉与信心、以及对工作的热情便成了他们从事主动性行为的坚强后盾[43]。最后,当员工在工作中体验到“学习”和“活力”时,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问题解决技能就会得到相应的激活与提升,从而有利于他们从事主动性行为。Fredrickso[44]的“积极情绪扩展与建构理论”认为,当人们体验到诸如“活力”等积极情绪时,不仅能扩展他们体验积极情绪时的思维认知能力和行为实施系统,还能建构和增强个体的智力资源、心理资源和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扩展与建构能改变个体原有的注意-认知-行为模式并使之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资源的增强和思维-行动模式的提升让个体有能力和信心去实施主动性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 工作繁荣对主动性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社会嵌入模型”和“个体成长整合模型”都指出,当员工身处合适的环境支持下时会体验到较高水平的工作繁荣,这种繁荣体验会进一步影响到他们后续的态度与行为[15, 16]。这些积极的效果包括个人发展、身心健康、工作绩效、主动性性、适应性等[26, 29, 41]。因此,当团队真实型领导为员工提供了合适的工作情境与领导支持时,会促发员工体验到更高水平的工作繁荣,在体验到“学习”和“活力”的基础上员工便会从事更多的主动性行为。理由如下:首先,工作繁荣的个体有着较强的延续当前繁荣状态的愿望,因此,他们会基于自身的专业知识去从事主动性行为以给当前组织或自我带来新的改变。其次,员工在和领导共事过程中,上下级之间彼此的自我真实呈现容易建立起真实的关系。现有研究发现,这种建立在双方真实性基础上的关系会带来更高水平的承诺和回报义务[30, 45]。因此,真实型追随者可能基于感知到的互惠义务而从事主动性行为,以给团队领导带来利益。本研究中我们预期员工的工作繁荣会在团队真实型领导与个体主动性行为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5. 工作繁荣在真实型领导与主动性行为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真实型追随是指员工以一种自我主导、开放性和非防卫性的方式去处理工作相关的任务和领导关系的过程。真实性水平较高的员工有着较强的对自我行为负责的直觉意识,他们能在潜在外部压力面前保持内心想法和外在行为之间的一致性[24]。由于员工比团队领导更接近或处在工作活动的一线,他们对工作流程、工作内容和潜在的问题有着更直观的了解。当员工发现或意识到可能给当前团队或自身带来有效变革的机会时、以及可能给团队带来危害的潜在问题时,真实性水平较高的员工便会忽略可能给自身带来负面影响的顾虑去实施主动性行为。因此,在假设2和假设4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 工作繁荣在真实型追随与主动性行为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六)工作繁荣的被调节中介效应
上文中已经论述了真实型领导的调节效应,假设3认为,真实型领导能够强化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间的正向关系;此外,上文还论述了工作繁荣的中介效应,假设5和假设6认为,工作繁荣在真实型领导、真实追随与主动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基于同样的逻辑推导,综合假设3、假设5和假设6的论点,本研究认为,真实型领导跨层次调节了真实型追随通过工作繁荣间接影响主动性行为的关系。这一假设推导与自我决定理论的理论逻辑是一致的,依据该理论的有机辨证视角,我们认为个体因素(真实型追随)和情境因素(真实型领导)会对工作繁荣产生协同效应,而此协同效应的影响效果(工作繁荣体验)又会进一步影响个体的行为表现。理由是工作繁荣是员工的主观心理体验,繁荣的个体会同时体验到“学习”与“活力”,这种内隐的主观心理体验必然会外显在行为表现上。因此,当真实型追随遇上团队真实型领导这样的情境因素时,员工基于真实性水平所促发的工作繁荣再影响到主动性行为的链式关系会更强。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认为在强真实型领导者团队中,真实型追随通过工作繁荣间接影响主动性行为的关系也会越强。因此,本文的最后一个假设如下:
假设7. 真实型领导跨层次正向调节了真实型追随通过工作繁荣间接影响主动性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调研程序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研法收集数据。调研对象为广州、东莞和佛山三个地区的5家大型企业,包括2家IT企业和3家制造企业,各企业人员规模均在1000人以上。在这些企业中,我们将抽样对象锁定在5名以上成员和1位领导组成的工作团队。调研开始之前,我们与各企业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进行了多次协商,最终确定48个团队共405名成员为本次调研的被试,各负责人还提供了以团队为单位的所有成员的电子邮箱。在调研过程中,有2家企业由我们去现场发放问卷并回收,另外3家则通过给被试发送邮件的形式来完成,两种形式的问卷在内容和布局上完全一致。所有被试需在问卷抬头填写自己的邮箱,以便我们对数据进行分组。在邮件调研时,我们向被试发送完邮件之后便立即要求各企业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在公司内部通知被试去填答问卷,以及在发送邮件一周、两周之后,分别再次提醒未完成问卷调研的成员去填写问卷。
本次调研共发放405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98份,有效回收率为73.58%。具体信息如下:现场调研的2家企业中,包括21个团队181名成员,收回问卷155份,其中不合格问卷18份,有效问卷137份,有效回收率为75.69%;邮件调研的3家企业中,包括27个团队224名成员,收回问卷186份,其中不合格问卷25份,有效问卷161份,有效回收率为71.88%;总的有效问卷中,各团队均有4~9名成员的数据,故参与调研的48个团队都有效。这298份样本中,男性175人,占58.72%;年龄在30岁及以下153人,占51.34%,31~40岁112人,占37.58%,41歲及以上33人,占11.07%;学历为专科及以下116人,占38.93%,本科153人,占51.34%,硕士及以上29人,占9.73%;工龄在3年及以下64人,占21.48%,10年及以上87人,占29.19%。上述信息表明本研究的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测量工具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信效度,本研究中各变量的量表均选自西方学者发表在一流期刊上的文献。为保证问卷题项在语义内涵上的准确性和表述上的得体性,我们采用了“翻译-回译”的策略,由一位人力资管理教授和两名人力资源专业博士生来完成。在形成初始问卷后,我们邀请了被调研企业的5位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对各题项的表述提修改意见,最终形成本次调研的问卷。此外,为有效规避国人的中庸倾向,问卷中除人口统计学变量外,其余均采用Likert 6点量表计分,从“1”到“6”,代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本次调研的问卷以团队为单位发放给各成员,所有变量的测量均由同一被试完成。
(1)真实型领导。采用Walumbwa等[23]开发的量表,共4个维度16个题项。Walumbwa等在开发此量表的研究中就用到了中国样本,韩翼等[7]也对其进行过中文翻译并用于本土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度。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总体α系数为0.92。另外,由于真实型领导在本研究中被定义在团队层面,而数据则来源于团队成员,因此需将个体数据聚合到团队层面。在聚合之前,我们采用了Bartko提出的组内相关系数ICC(1)、ICC(2)和James等提出的组内评分者信度Rwg来判断数据聚合后的可靠性[46]。经计算得出,真实型领导的ICC(1)、ICC(2)分别为0.21、0.83,均超过了0.10和0.70的经验标准值;各团队的真实型领导Rwg都大于0.7(均值为0.76, 中位数为0.82),超出了经验标准值。以上结果表明本次调研中真实型领导数据满足聚合要求。
(2)真实型追随。采用H Leroy和F Anseel[25]的研究所用的量表,该量表是两位学者在结合Kernis和Goldman[47]开发的真实性目录(Authenticity Inventory)和Walumbwa等[23]开发的真实型领导的基础上修订得来的,共4个维度16个题项。在H Leroy等的研究中,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5),在本研究中α系数为0.82。
(3)工作繁荣。采用Spreitzer和Porath等[26]编制的量表,共2个维度10个题项。已有学者对该量表进行过中文翻译,并被时勘等[48]应用于本土情境的研究。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总体α系数为0.89。
(4)主动性行为。采用Griffin和Parker等[37]编制的量表,在该量表中,员工的主动性行为被划分为针对自我、团队和组织三个维度,各维度均有3个题项。考虑到组织结构和制度方面的事项与普通员工相距甚远,他们很难对此类事项造成影响,因而本研究遵循了林叶和李燕萍[1]的做法,只考虑针对自我和团队的主动性行为,共6个题项,作为一个整体来衡量。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总体α系数为0.83。
(三)验证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的测量工具均来自西方学者发表在一流期刊上的文献,且为国内外众多研究者所借用,说明这些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为确保各变量间的区分效度,我们还对真实型领导、真实型追随、工作繁荣和主动性行为4个构念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结果如表1所示,假设的4因子模型比各备选模型有着更好的拟合指标,这说明本研究中4个构念间的区分效度良好。此外,由于本次调研的全部题项由同一被试回答,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CMV)问题。尽管前面的CFA分析结果显示4个构念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为了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程度,我们采用了研究者广泛使用的Harman单因素检验法[49]。结果显示:未经旋转的第一主成分解释了30.46%的变异(小于40%的临界值)。由此可见,各变量间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可接受范围内。
(四)假设检验方法
由于本研究的主要变量涉及个体和团队两个层面,团队成员嵌套在工作团队中,变量间的关系包含跨层次的作用。所以,我们借助Mplus7.0统计程序包进行数据分析,采用被调节中介作用的跨层结构方程模型(MSEM)路径分析法来检验各项假设,同时,运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Robust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法来进行参数估计。在检验跨层被调节中介作用时,跨层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法将多层线性模型(HLM)和结构方程模型(SEM)整合在一起,可同时解决数据的多层(嵌套)结构和潜变量的估计问题[50]、以及处理多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非常适合本研究的假设检验。路径分析法的最大优势在于既能有效避免将变量间关系的组内和组间效应混为一谈而产生的偏差,又能直接(而非间接)估算出变量间作用的间接效应及相应的路径系数,从而获得质量更好的统计结果[51]。另外,由于跨层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法估计得到的间接效应,往往不满足标准正态分布的要求,因此我们参考Preacher 和Selig[52]的建议,采用参数自助法(Parametric Bootstrap)进行重复抽样(Monte Carlo 20,000次)生成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以此判断模型中各间接效应的显著性及调节变量处于不同条件值时相关间接效应的显著性。
三、假设检验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括号内数值为各量表的α系数)。由表2可知,真实型领导与工作繁荣(r=0.47, p<0.001)和主动性行为(r=0.34, p<0.01)显著正相关;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r=0.42, p<0.01)和主动性行为(r=0.31, p<0.01)显著正相关;工作繁荣与主动性行为(r=0.46, p<0.001)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为后续的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二)路径分析结果
本研究中两层次被调节中介模型的跨层结构方程路径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具体结论如下:第一,假设1认为真实型领导对工作繁荣有正向影响;假设2认为真实型追随对工作繁荣有正向影响;假设4认为工作繁荣对主动性行为有正向影响;图2显示,真实型领导与工作繁荣显著正相关(γ=0.39, p<0.001),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显著正相关(γ=0.27, p<0.01),工作繁荣与主动性行为显著正相关(γ=0.36, p<0.001),故假设1、2和4得到了支持。
第二,假设3认为真实型领导调节了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的关系;图2显示,真实型领导对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关系的随机斜率(Random Slopes)有显著影响(γ=0.15, p<0.01),根据Cohen等[53]建议,我们画出了这一调节效应的示意图(图3所示)。图3表明,当团队真实型领导处于不同条件值(高于或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斜率。具体而言,在强真实型领导的团队中,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的关系斜率显著(γ1=0.47, p<0.01);而在弱真实型领导的团队中,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的关系斜率不显著(γ2=0.16, n.s.),且二者存在显著差异(Δ=0.31, p<0.01),故假设3得到了支持。
第三,假设5认为工作繁荣在真实型领导与主动性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假设6认为工作繁荣在真实型追随与主动性行为间起中介作用;由于图2中的数据支持了假设1、2和4的内容,因而为此部分中介效应检验提供了前提基础,满足了Baron和Kenny[5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的前两大条件,但本研究中我们不采用两位学者提出的分步检验法,而是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法来估计这两项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结果显示:真实型领导通过工作繁荣影响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显著(γ=0.14, p<0.001),99.9%置信区间为[0.059, 0.218],0不在该区间内,假设5得到了支持;另外,真实型追随通过工作繁荣影响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也显著(γ=0.097, p<0.01),99%置信区间为[0.004, 0.188],0不在此区间内,假设6得到了支持。
第四,假设7认为真实型領导对真实型追随通过工作繁荣间接影响主动性行为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在假设3和6得到支持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法来估计在真实型领导的跨层次作用下工作繁荣的中介效应[52]。表3显示,真实型追随→工作繁荣→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在高真实型领导的团队中显著(γ=0.136, SE=003, p<0.01, 99%置信区间为[0.005, 0.265], 不包括0),在低真实型领导的团队中这一关系较弱(γ=0.067, SE=0.02, p<0.05, 95%置信区间为[0.001, 0.136], 不包括0),两者的组间差异显著(Δ=0.069, SE=0.02, p<0.01, 99%置信区间为[0.002, 0.115], 不包括0)。因此,假设7得到了支持。
四、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真实型领导、真实型追随均能促发员工的工作繁荣;真实型领导跨层调节了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的关系;工作繁荣对主动性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工作繁荣在真实型领导、真实型追随与主动性行为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真实型领导跨层调节了真实型追随通过工作繁荣间接影响主动性行为的关系,即在强真实型领导的团队中,真实型追随通过工作繁荣对主动性行为的间接影响越强。总体而言,本研究的各项假设均得到了调研数据的支持。以上研究发现,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了现有真实型领导、真实型追随、工作繁荣和主动性行为的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现有领导力研究的视角。
(二)理论意义
首先,本研究发现团队真实型领导是下属主动性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延伸了现有真实型领导和主动性行为的研究。纵观已有文献,研究者较少探讨真实型领导与主动性行为的关系,跨层次的研究更是稀少。现有研究也多局限在“碎片化”的主动性行为,即谏言行为、创新行为、组织公民行为等,这些细分的行为类型与主动性行为处于既有交叉又有区别的态势,而且诸多类型的行为与其驱动因素间的关系更是玲琅满目,这让管理实践者无所适从,因此有学者呼吁对这些行为进行整合研究[40];另外,真实型领导的核心是领导者致力于呈现真实的自我,他们倾向于对下属一视同仁,因而更可能在团队层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正是基于以上问题而开展的研究,从团队层面去探讨真实型领导对下属的整合性主动性行为的影响。
其次,本研究发现真实型追随亦对主动性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丰富了日益被研究者所重视的追随力理论相关研究。真实型追随与真实型领导有着相似的维度,包括自我意识、内化的道德观、无偏见的信息加工、真实的行为和关系导向,都是在共事时彼此呈现真实的自我。真实型追随的概念几乎与真实型领导理论的提出同时间出现[24],但相关实证研究却一直在延续领导者中心视角[13],而未给予真实型追随足够的重视,因此,有学者呼吁在研究真实型领导的同时考虑真实型追随的作用[6],本文正是响应这一呼吁而开展的研究。实证结果发现,真实型追随能够预测个体的主动性行为,同时团队真实型领导调节了真实型追随与工作繁荣的关系,进而驱动着员工的主动性行为。追随力理论强调下属并不只是被动接受来自领导者的影响,他们也积极的决定着自己的行为甚至影响着领导过程[13]。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追随力理论的相关研究。
最后,本研究发现工作繁荣在真实型领导、真实型追随和主动性行为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作为一个新颖的研究构念,工作繁荣是指个体在工作中同时体验到“学习”和“活力”的综合心理状态[15, 16]。在知识经济和无边界职业生涯主导的今天,基层员工渴望持续学习与进步,他们要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因而“学习”和“活力”的综合体验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工作繁荣犹如温度计一般帮助员工即时地读取心理状态,判断它是过热(易造成倦怠)还是过冷(易阻滞发展)[18],员工通过关注自身“学习”和“活力”的感受来进行自我调节,从而获得更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表明,工作繁荣的个体有着更好的工作绩效、创新绩效、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及更少的医疗支出。这意味着工作繁荣的个体职场表现更好、身心更健康。本研究中工作繁荣与主动性行为显著正向相关支持了Spreitzer[16]等“个体成长整合模型”中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工作繁荣模型的理论发展。此外,本研究也对工作繁荣的内容有所扩展;首先,发现了真实型领导能够促进工作繁荣,以往研究主要从下放决策权、信息共享、积极反馈、尊重和信任的角度去解读工作繁荣,本研究将其延伸到具体的领导类型;其次,有学者认为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容易实现工作繁荣,比如调节焦点不同的员工会有不同的繁荣体验[16, 31],本文进一步扩展了现有研究,发现员工的真实性程度能够影响工作繁荣。
(三)管理启示
当今企业面临着快速变化和持续创新的压力,为有效应对环境的挑战,企业需依赖基层员工更多的施展主动性行为,因为他们更接近产品和顾客。正如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前不久所说:“今天的企业要想成功须做到员工听消费者的,企业听员工的”。故激发员工的主动性行为成了领导者面临的首要挑战与目标。本研究发现团队真实型领导对员工的工作繁荣及后续的主动性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跨层次调节了真实型追随影响工作繁荣再延伸到主动性行为的关系。这说明团队领导若是真实型的,就会通过自我意识、无偏见信息加工、真实的行为和关系导向等方式来促进员工的主动性行为。由此可见,领导者需要在团队中呈现真实的自我,努力与下属建立真诚、开放、透明的关系,以高道德标准的方式来提升员工的心理安全感,进而激发他们更多的从事主动性行为。
此外,由于真实型追随亦通过工作繁荣间接影响主动性行为。故企业应同等重视领导和下属的真实性。Kernis等[14]认为个体真实性主要是成长过程中与父母、老师等相处而形成的,但也会在进入职场后与领导相处而有所改变。因此,企业应重视领导者的真实性,在选拔人才进入领导岗位时考虑他们的真实性程度,通过将真实性水平较高的候选者安排在领导岗位上,借助他们的示范效应来影响下属的真实性;同时,在新员工招聘过程中应适当考量应聘者的真实性,以有效保障企業员工整体的真实性水平。鉴于个体的真实性程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兼具稳定性和可塑性,因此企业还可以通过适当的干预措施来提升领导与下属的真实性水平,如在企业中鼓励个体的真实性呈现、营造开放包容的环境以鼓励员工成为真实的自己。
最后,企业应重视基层员工的工作繁荣,跟踪调查和分析他们的工作繁荣状态,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促进员工的工作繁荣,提升员工的“学习”与“活力”体验,最终激发他们的主动性行为。借鉴Spreitzer等[16]提出的工作繁荣个体成长整合模型,企业可以对各级管理人员进行相关培训,让管理者充分认识到工作繁荣的内涵与功能,指导他们通过个别座谈、群体讨论和问卷调研的形式定期了解员工的工作繁荣状态,引导他们通过更多的授权、参与决策或自主决策,与员工共享相关信息,对员工充分信任并予以尊重,与员工建立积极的情感和关系资源等途径来促进员工的工作繁荣,并激励他们为推动员工的工作繁荣向实施主动性行为转化营造开放包容的环境,以促进员工积极的发现问题并投入到问题的解决中。
(四)局限性及未来展望
尽管本研究的调研数据支持了模型中的各项假设,但受到主客观条件的约束,依旧存在以下局限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采用了横截面研究设计,使得各变量均来自被试在同一时点的自我报告数据,容易导致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虽然本文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证实该问题不严重,但仍难以有效削弱该问题带来的影响;另外,横截面数据无法严格满足变量间因果关系推导的各项条件,故本研究中因果关系验证存在说服力不足的缺陷。未来,研究需采取纵向研究设计,以进一步降低上述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本研究的测量工具均来自西方学者的研究,尽管这些量表在以往研究和本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都是通过“翻译-回译”程序获得,由于文化差异和翻译差异的存在,可能导致问卷在表述上的细微差别而影响被试对具体题项的理解。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借用国内学者开发的真实型领导问卷,以及开发本土情境下更适合被试阅读与理解的真实型追随、工作繁荣和主动性行为等问卷,以降低文化和表述习惯上的差异给研究结论带来的影响。最后,本研究仅在广州、东莞和佛山三个地区选取被试,所涉及到的地域和行业略显单一,被调研企业的规模都比较大,故相对而言管理制度也更加规范,这可能降低研究结论在其他行业领域或不同规模企业中推广时的适用性。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大抽样范围,以进一步提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772067)
参考文献
[1] 林叶, 李燕萍. 高承诺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前瞻性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6, 19(2): 114-123.
[2] 胡青, 王胜男, 张兴伟. 工作中的主动性行为的回顾与展望[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10): 1534-1543.
[3] 朱瑜, 黄丽君, 曾程程. 分布式领导是员工主动行为的驱动因素吗?——一个基于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4, 36(09): 38-51.
[4] 吴佳煇, K.Parker S. 深谋远虑:前瞻行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英文)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04): 679-700.
[5] Parker S K, Collins C G. Taking Stock: Integrating and Differentiating Multiple Proactive Behavior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0, 36(3): 633-662.
[6] Gardner W L, Cogliser C C, Davis K M. Authentic Leadership: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Agenda [J].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1, 22(6): 1120-1145.
[7] 韩翼, 杨百寅. 真实型领导、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领导成员交换的调节作用 [J]. 管理世界, 2011, (12): 78-86+188.
[8] 王震, 宋萌, 孙健敏. 真实型领导: 概念、测量、形成与作用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03): 458-473.
[9] 罗瑾琏, 赵佳. 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 [J]. 软科学, 2013, 27(12): 41-44.
[10] Hsiung H H. Authentic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A Multi-Level Psychological Proces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2, 107(3): 349-361.
[11] 赵欣, 赵西萍, 周密. 组织行为研究的新领域: 积极行为研究述评及展望 [J]. 管理学报, 2011, 8(11): 1719-1727.
[12] Methot R J, Lepak D, Shipp A J. Good Citizen Interrupted: Calibrating a Temporal Theory Of Citizenship Behavior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7, 42(1): 10-31.
[13] Uhl-Bien M, Riggio R E, Lowe K B. Followership Theory: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3, 25(1): 83-104.
[14] Kernis M H. Toward a Conceptualization of Optimal Self-Esteem [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3, 14(1):1-26.
[15] Spreitzer G, Sutcliffe K, Dutton J. A Socially Embedded Model of Thriving at Work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5, 16(5): 537-549.
[16] Spreitzer G, Porath C. Self-Determination as Nutriment for Thriving: Building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Human Growth at Work [M]. In M. Gagné (Ed.), Oxford Handbook of Work Engagement,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7] Spreitzer G, Porath C, Gibson C. Toward Human Sustainability : How To Enable More Thriving at Work [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2012, 41(2): 155-162.
[18] 鄭晓明, 卢舒野. 工作旺盛感: 关注员工的健康与成长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07): 1283-1293.
[19] Vallerand R J. Deci And Ryan's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 View from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0, 11(4): 312-328.
[20] 韩翼, 杨百寅. 真实型领导:理论、测量与最新研究进展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9, 30(02): 170-175.
[21] Luthans F, Avolio B. Authentic leadership development [M]. In Cameron K, Dutton J, Quinn R.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 Foundations of a new discipline. San Francisco: Barrett-Koehler. 2003: 241-261.
[22] Avolio B, Luthans F, Walumbwa F. Authentic Leadership: Theory-Building for Veritable Sustained Performance [J]. Working paper. Gallup Leadership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2004b).
[23] Walumbwa F O, Avolio B J, Gardner W L. Authentic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Theory-Based Measur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 34(1): 89-126.
[24] Gardner W L, Avolio B J, Luthans F. "Can You See The Real Me?" A Self-Based Model of Authentic Leader and Follower Development [J]. Leadership Quarterly, 2005, 16(3): 343-372.
[25] Leroy H, Anseel F, Gardner W L. Authentic Leadership, Authentic Followership, Basic Need Satisfaction, and Work Role Performance: A Cross-Level Study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41(6): 1677-1697.
[26] Porath C, Spreitzer G, Gibson C, Flannery G. Thriving At Work: Toward its Measurement, Construct Validation, and Theoretical Refinement [J].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in Organizations, 2012, 33(3): 250–75.
[27] Hildenbrand K, Sacramento C A, Binnewies C.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Burnout: The Role of Thriving and Followers' Openness to Experience [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in press).
[28] Cooper-Thomas H D, Paterson N L, Stadler M J.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roactive Behaviors and Outcomes for Predicting Newcomer Learning, Well-Being, and Work Engagement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4, 84(3): 318-331.
[29] Paterson T A, Luthans F, Jeung W. Thriving at Work: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upervisor Support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4, 35(3): 434-46.
[30] Russo M, Buonocore F, Carmeli A, Guo L. When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s Meet Employees' Need For Caring: Implications for Work-Family Enrichment and Thriving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1-25.
[31] Wallace J C, Butts M M, Johnson P D. A Multilevel Model of Employee Innovation: :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Regulatory Focus, Thriving, and Employee Involvement Climat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6, 42(4): 982-1004.
[32] Zhou J.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Career Adaptability: The Role of Thriving at Work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7, 98: 85-97.
[33] Kahn W A.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of Personal Engagement and Disengagement at Work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0, 33(4): 692-724.
[34] Grizzle J W, Zablah A R, Brown T J. Employee Customer Orientation in Context: How the Environment Moderates the Influence of Customer Orientation on Performance Outcome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9, 94(5): 1227-1242.
[35] 郭玮, 李燕萍, 杜旌. 多层次导向的真实型领导对员工与团队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J]. 南开管理评论, 2012, 15(03): 51-60.
[36] 李新建, 苏磊. 创新情境下员工主动性行为研究脉络与综述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2, 33(12): 144-152.
[37] Griffin M A, Neal A, Parker S K. A New Model of Work Role Performance: Positive Behavior in Uncertain and Interdependent Context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2): 327-347.
[38] Parker S K, Williams H M, Turner N. Modeling The Antecedents of Proactive Behavior at Work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6, 91(3): 636-652.
[39] Den Hartog D N, Belschak F D. When Doe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Enhance Employee Proactive Behavior? The Role of Autonomy and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2, 97(1): 194-202.
[40] Crant J M. Proactive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0, 26(3): 435-462.
[41] Carmeli A, Spreitzer G M. Trust, Connectivity, and Thriving: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ve Behaviors at Work [J].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2009, 43(3): 169-191.
[42] Amabile T M. How To Kill Creativity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76(5): 77-87.
[43] Dutton J E, Ashford S J, O'neill R M. Moves That Matter: Issue Selling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4): 716-36.
[44] Fredrickson B. The Value Of Positive Emotions [J]. American Scientist, 2003, 91(4): 330-335.
[45] Candidate A V M, Vlerick P, Clays E. Authentic Leadership and Thriving Among Nurs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athy [J]. Journal Of Nursing Management, 2016, 24(3): 357-65.
[46] 罗胜强. 管理学问卷调查研究方法 [M].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47] Kernis M H, Goldman M B. A Multicomponent Conceptualization of Authenticity: Theory and Research.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6, 38(06): 283-357.
[48] 时勘, 万金, 崔有波. 基于人-情境交互作用的工作旺盛感生成机制 [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5, (17): 65-72+83.
[49]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Y.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5): 879-903.
[50] 王濟川, 王小倩. 结构方程模型: Mplus与应用(英文版)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51] 黄亮, 彭璧玉. 工作幸福感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一个多层次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J]. 南开管理评论, 2015, 18(2): 15-29.
[52] Preacher K J, Selig J P. Advantages of Monte Carlo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Indirect Effects [J]. Communication Methods & Measures, 2012, 6(2): 77-98.
[53] Cohen J, Cohen P, West S, Aiken L. Applied Multiple Regression/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rd Edi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2003: 267-272.
[54]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 1173-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