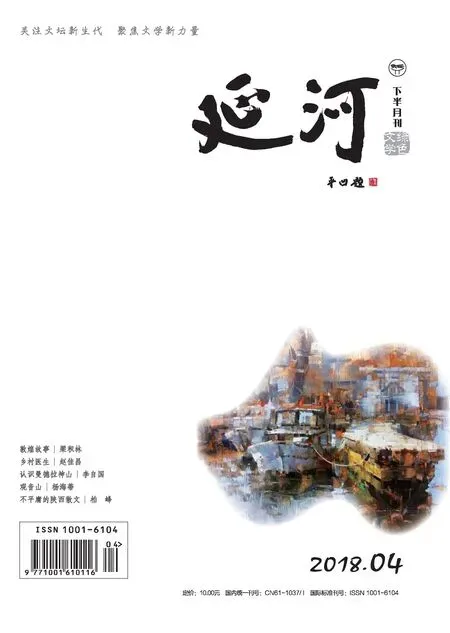沧桑水鸟
2018-05-28徐泰屏
徐泰屏
凫水鸡
每一次在故乡的鄂南西凉湖上操桨弄舟而行,总能看见一两只浮游的水鸟,若即若离地出没在船头艄尾和船左船右,忽而水上,忽而水下的潜着游着,让人心痒又心动。
它就是被村人们称为“凫水鸡”的水中之鸟。对一种水鸟以鸡相称,并且一叫就是千年万年,这也算得上是故乡的独有和专利。不管这样的一种叫法是否准确和科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你把“凫水鸡”这三个字读过念过之后,就一定会用心感受到人和鸟的距离是多么的贴近。
凫水鸡尖嘴短尾,长着一身灰褐色的如绒之羽,体重多在250克左右,食性以小鱼小虾为主。凫水鸡在一些地方也被称为“水钻儿”,它的最大特性,就是善于在水下隐蔽潜行,一个水猛子扎下去,就能一口气潜出100多米。在渔人们眼中,凫水鸡是一种不怕人的水鸟。它总是在不远不近的水面上看着你,望着你,待到渔船快要与其靠近时,就陡地把头一埋,尾巴一翘,一个猛子扎到水底里面去。再不就是拍打着两只短小的翅膀,拖着一双细脚,在水面上滑翔而行,然后停歇在不远处的水面上,再次回过头来看着你,望着你,显得特别的调皮和乖巧。
凫水鸡与下蛋之鸡的最大共性之处,就是它们都不能飞得很高、飞得很远。凫水鸡每次起飞时,尽管很用力地把一双翅膀在水面上拍得声声生响,却很难把自己的整个身躯飞离水面,并在空中停留二分钟以上。所以凫水鸡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湖面上浮游着,在水下面潜行着,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一般是不会振翅而飞的。但凫水鸡绝对不是那种容易捉弄的水鸟,每当有渔人打起它的主意时,凫水鸡就会亦潜亦飞地交替而行,直至把人弄得筋疲力尽和罢手罢脚为止。
善潜能飞的凫水鸡不好捉,但也不是不可捉,只要是保持强大的决心和下足十分的力气,还是能够偶有斩获的。听长辈们讲,捕捉凫水鸡的最佳时段,是在风平浪静的落日时分。因为这个时候的凫水鸡通过一天的进食,已是肚饱身圆,故而潜行能力和飞行能力都大打折扣,加之湖水波澜不惊和澄澈清明,凫水鸡的潜行路线一目了然,所以捕捉起来也就容易得多。以小鱼小虾为食的凫水鸡,肉质肥嫩、体骨纤细,自古就是渔人们津津乐道和难得一尝的美味珍馐。它的那个鲜、那个腻,让许多渔人在不禁的欲求下,一次又一次地向其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并最终把一只只不怕人的凫水鸡,变成了囊中之物和盘中佳肴。
凫水鸡喜欢独来独往,最多时也就二三只,或三五只地聚在一起嬉戏一下,接着又各奔东西地觅食而去。作为一种与人走得很近的水鸟,凫水鸡像所有的飞禽走兽一样,既有着生为禽兽的快乐和幸福,也有着生为禽兽的无奈和悲哀。只是当我一回回在故乡的岸边行走和操桨弄舟于湖面之上时,仍然能够看到一二只或潜或游的凫水鸡,在不远不近的地方看着我、望着我,仍是那样的调皮,那样的可爱……
荡鸡
荡鸡,是又一种被故乡渔人以鸡相称的水鸟。
简单地说,荡鸡就是一只只停歇在广阔水面上的野鸭。从我们西凉湖的季节湖特征和物体之间形似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故乡把那些习惯在湖水里栖身的水鸟称其为“荡鸡”, 要比别的地方呼作“野鸭” 更形象更地道。特别是那个“荡” 字和“鸡”字的创造性组合,让一个乡里称谓显得特别生动和有趣。
在黄叶飘零时急急而来,在春暖花开时匆匆而去,荡鸡是一些把湖水的冷暖谨记在心的候鸟。在我的印象中,荡鸡总是成群结队地翻飞而至,千千万万地把一片片空阔水域,拥着挤着地歇成蔚为壮观的泳动翅影。荡鸡有着如鸡一样的体形,如雉一样的红色浅冠,以及如鸠一样黄色的眼睛和一身黧黑的羽毛,它们浮游在水面上,恰似凌波仙子一样漂亮和悠然。荡鸡能潜,但更加善飞,像雁一样飞得很高很远,像鹰一样飞得从容和恣意。它每一次在湖面上击水而飞时,一如挟雷带电的战斗机一般矫健和敏捷,那种成千上万只荡鸡一齐起飞一齐降落的场景,让人在看着叹着的同时,总能听到一阵阵急风暴雨的声音。
西凉湖肥美的水草,为主食水草草籽和小鱼小虾的荡鸡,提供了无比丰沛的食粮,这也是它们一年又一年歇满湖岸港湾的主要原因。除了偶尔在冬天的湖岸上捡到一二只因雪盲而迷路的荡鸡外,故乡的渔人们,一直对那些能潜善飞的荡鸡,很少产生什么非分之想。荡鸡无论是浮游在湖面上觅食,还是飞翔在空中迁徙,历来都只是人们眼中的一道风景,表现得既真实,又虚无。
对荡鸡能够构成事实伤害的,大多是来自洪湖和汉沔等地一些专以打水鸟为生的火铳手。他们驾着一种特制的微型扁舟,在每年的冬天如约而至地出现在西凉湖上。之后,再把扁舟伪装成一堆漂浮在湖面上的干枯水草,将一丈多长、手臂一般粗细的铳管和装满了火药的铳身,统统隐蔽和固定在扁舟的舱板上面,接着就开始悄悄地向浮游的荡鸡群缓缓靠近。在扁舟完全接近荡鸡群的一刹那,他们迅即扣动火铳的扳机,对着那些惊飞的荡鸡进行扫射和轰击,然后把一只只亦死亦伤的荡鸡,堆码成一舱舱的战利品。但这还不是对荡鸡的最大伤害,真正给荡鸡带来灭顶之灾的,是一种名为“呋喃丹” 的剧毒农药。在利欲熏心的强烈作用下,一些故乡的渔人开始把那种极似水草草籽、且漂浮能力特强的呋喃丹细小颗粒,一斤又一斤地播洒在荡鸡群浮游觅食的水域,使其在误食了剧毒农药之后,成为了一具具漂浮在水面上的僵硬浮尸。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整个西凉湖都成了毒杀荡鸡的屠场,一些人还因为争霸毒杀荡鸡群的水面和抢夺毒死的荡鸡而大打出手,血染碧水。贪婪与残忍,不仅直接造成了荡鸡数量的急剧减少,也让贪婪和残忍者本身,变得更加的残忍和凶狂。

再后来,一根根拦网养殖的竹篙,在“开发利用” 的口号下,把偌大的西凉湖,紧紧密密地插成了荡鸡们无法歇脚的森严之壤。十几年来,每当我望着这湖荡鸡们再也很难回来的湖水,就禁不住遐想着那些大难不死的荡鸡,现在究竟去了何处,并想切切地问一声——你在他乡还好吗?
马鹞
马鹞似乎应该属于海鸥一类的水鸟,也许就是人们习惯喊作的红嘴鸥。可是故乡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们,老是叫它“马鹞”, 叫着叫着,就子子孙孙地再也改不了口了。
但马鹞与海鸥翼长而尖和褐颈黑爪的模样,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大如鸽子,红嘴红爪,一身白羽,歇在水里格外的醒眼,飞在空中十分的夺目,停在莲荷丛中恰似一团白色的火焰。马鹞那一袭素羽,要比白鹅白得明丽,比白雪白得温暖,比白垩粉白得自然和舒服。
一群群马鹞在湖岸港湾上空飞着旋着的时候,总要发出一声声“呃、呃、呃”的悠扬鸣叫,那声音像渔家妹子的船歌一样清脆干净,似喜庆锣鼓一般具有强烈的穿透力。马鹞张着洁白的羽翅,在湖面上翻腾扶摇地搜寻着鱼群游动的轨迹,其飞翔的翅影,让渔人们一次次准确地找到了鱼群聚散的方位。
与大多数以鱼为食的水鸟一样,马鹞也是一边在湖面上空飞着旋着,一边用双眼紧盯着水中的游鱼,一旦发现有可食的小鱼浮上了水面,就会“嗖” 地一声扎到水里,然后再“腾” 地一下冲到空中,将叼在嘴里的鱼儿慢慢吞到肚里。马鹞大多数时间都在湖面上飞翔着,实在飞得累了,也会歇在水面上浮游一会儿,但时间绝对不会超过十分钟,又会重新拍水振翅而起,继续飞着叫着追循着游动的鱼群而去。
马鹞是故乡生命力最强的水鸟。因为机敏和善飞,它很少被人活捉;因为主食活鱼,亦很少被人毒害;因为肉少羽丰,也历来不为人所看好、所在乎。在一种又一种水鸟先先后后飞离西凉湖的时候,马鹞是为数不多仍在湖面之上飞着叫着的鸟儿,使得故乡日渐空乏的天空,不致特别的冷清和寂寞——它们在水天之间与渔船渔人和岸柳莲荷所构成的美丽景象,让人看着特别的生动,特别的漂亮,也特别的慰藉……
长颈鹅
“长颈鹅,吃食多,不下蛋,只唱歌……”
每当想起这首童年的歌谣,每当想起童年时唱着这首歌谣在西凉湖里戏水逐浪时的情景,人就变得一往情深和心宁神静起来。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看到的长颈鹅,要么是独站在临水的岸沿边,要么是孤立于凸现水面的小土墩上,只要是没有人打扰,它就会一站几个小时不挪地方。它那一尺多长的高脚和尺半有余的长颈,加上二三公斤重的鸟身,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站在湖边,酷似一位钓者蹲在岸旁,既孤独,又孤傲。
说长颈鹅“吃食多” 和“不下蛋”, 是因为它体大胃大和从来无人寻见过它的窠巢。但长颈鹅的歌,的确唱得很响亮、很高亢,有着已故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一样的嗓门和音色。一声声“嘎、嘎、嘎”的长歌,撞到湖面上,仿佛可以激起一圈圈涟漪;越过岸柳的枝桠,就会发出“沙沙” 的声响。长颈鹅一旦亮开它那鲲鹏一样黑白相间的翅膀,就能遮住一片阳光,产生一爿荫凉。
把一根标志的长颈,时而伸到水里,时而回缩到羽翼里面,长颈鹅饿了就用半尺长的尖喙叼鱼而食,饱了就站着立着地打个盹儿,显得非常的自在和悠然。遇有顽童贸然偷袭,它就会从容不迫地扇动长长的翅膀,有节有奏地高歌曼舞而去,然后停歇在又一个看得见、够不着的地方,很优雅地看着水面,或是重新打个盹儿。
长颈鹅守株待兔一样的觅食方法,经典而传统,它让自己在有别于其它水鸟的同时,特别经得住守望和等待。长颈鹅是我有形有影看到的最大水鸟,也是我看到活得最独立最自我的飞禽。记得我最后一次看见脚高颈长的长颈鹅,大约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夏日,现在想来,长颈鹅应该是最早从故乡西凉湖悄然离去的鸟儿之一。多年的不见和记忆的模糊,让我在一次次默念着“长颈鹅,吃食多,不下蛋,只唱歌” 的童谣时,把长着一身灰褐色羽毛的长颈鹅,慢慢读成了故乡湖岸一帧渐渐发黄的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