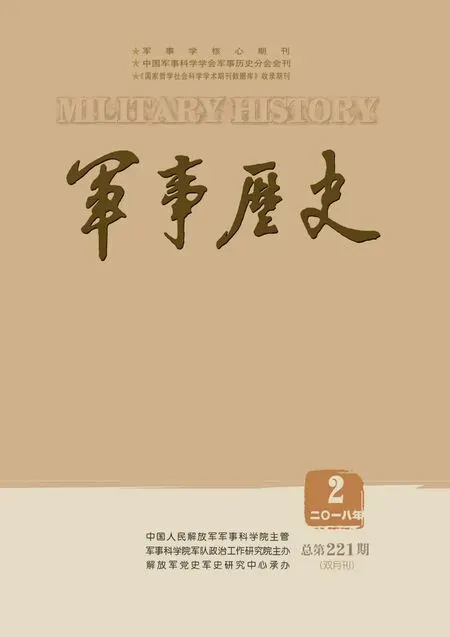兵道尚诡:试说宋代的军用蜡丸
2018-05-21★
★
② 目前学界尚无专文探讨宋代的军用蜡丸,但有研究者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有所涉及,代表作包括李琛:《宋朝间谍问题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张丽娜:《宋代间谍情报活动初探》,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陈武强:《北宋西北边防军事情报来源与间谍保障制度》,载《甘肃高师学报》2011(1);黄纯艳:《宋朝搜集境外信息的途径》,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李书永:《宋代保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此外一些军史专著中也会提及中国古代的蜡丸,例如黄富成:《中国古代间谍史》,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褚良才:《中国古代间谍史话》,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凡此种种,兹不赘述。拙文为行文方便起见,除引用史料原文外,皆用“蜡丸”一词代而称之,特此说明。
在古今中外的军事斗争中,有效掌握、利用敌我双方的情报动态,是影响战事走向乃至战局胜负的关键一环。《孙子兵法》有言:“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为了实现事无巨细而无所不知,甚至要做到“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的程度。*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用间篇》,362、37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而人事上的“用间”自然需要技术上的支持,于是各种形制隐秘、用途诡谲的情报工具层出不穷,始于唐而兴于宋的蜡丸便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种。
一、蜡丸的基本形制
军用蜡丸的记载大致出现于唐代,且史籍中对其形制已有描述:永泰二年(766),同华节度使周智光“聚亡命不逞之徒”“据州反”,唐代宗遂“密诏关内河东副元帅、中书令郭子仪率兵讨智光,许以便宜从事。时同、华路绝,上召子仪女婿工部侍郎赵纵受口诏付子仪,纵裂帛写诏置蜡丸中,遣家童间道达”*《旧唐书》卷114《周智光传》,33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此时的蜡丸,已经是由外层的蜡质膜壳与内层的帛布文书两部分构成,密封的腊壳体积小巧,在增加隐蔽性的同时能更好地保护帛书,避免损毁。此后,军用蜡丸的基本形制得以延续,至南宋布衣赵升编纂《朝野类要》一书中,对蜡丸的描述依旧是“以帛写机密事,外用蜡固,陷于股肱皮膜之间,所以防在路之浮沈漏泄”*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4《帅幕·蜡弹》,9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尽管蜡丸用于军事领域的记载始于唐代,但真正推广使用还是在宋代。笔者以为这并非单纯是由于存世史料的多寡不同所致,农业史和医学史的研究为分析这一现象提供了参考:据《博物志》记载,中国古代人工养殖蜜蜂的技术在晋代基本成型,“人往往以桶聚蜂,每年一取。远方诸山蜜蜡处,以木为器,中开小孔,以蜜蜡涂器,内外令遍。春月蜂将生育时,捕取三两头著器中,蜂飞去,寻将伴来,经日渐益,遂持器归”。*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10《杂说下》,1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随着经验的累积与水平的提高,至宋代时养蜂业已有重大进步*张显运:《宋代养蜂业探研》,载《蜜蜂杂志》,2007(5)。,出现了“蜡有二色,黄者造烛,白者医家用之”*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36《风土门·土产》,7559页,《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的区分,而医用蜡丸的制药工艺,恰也成熟于宋代*颜隆、朱建平:《蜡丸的历史演变》,载《天津中医药》,2014(4)。。由是观之,宋代养蜂业的发展为包括蜂蜡在内的蜂产品开发、推广提供了物质保障,而这正是蜡丸最终得以在军事领域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条件。

作为机要情报的载体,蜡丸需要通过信使的传递才能实现信息的交流。如何保证蜡丸在此过程中的安全,成为使用者的难题。史载唐建中二年(781),朱泚、朱滔等谋划军变,曾令密使“以帛书纳蜡丸中,置发髻间”*《旧唐书》卷200《朱泚传》,5386页。,但将蜡丸藏于发髻之中,恐怕还是容易被敌方拦截、搜获。前述北宋末年秦仔于金兵围城之际潜出开封,至赵构处方才“拆敝衣以出”蜡丸,究竟是将蜡丸藏于破衣夹层?还是因其紧贴身体需撕破衣服方可取出?此处语焉不详,只好两存之。建炎三年(1129)“苗刘之变”爆发,立足未稳的南宋朝廷陷入动荡,此时赵不凡竟“刲股纳蜡书”*《宋史》卷247《宗室四·士·传》,8754页。,将召唤张浚“勤王”的命令传递出去,可见非常之际以简单的外科手术将蜡丸植入人体也是可行的。至于《朝野类要》将蜡丸“陷于股肱皮膜之间”的记载,究竟是将蜡丸“粘附”皮肤之外还是“植入”肌体之内?二者似乎亦均有可能。不过大致而言,蜡丸藏匿的隐蔽性有越来越强的趋势。
二、秘密的情报载体
军用蜡丸的记载在中唐以后开始见诸史册,如唐肃宗于灵武称帝后,颜真卿曾“数遣使以蜡丸裹书陈事”*《新唐书》卷153《颜真卿传》,48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前引周智光、朱泚、朱滔“蜡丸传书”,皆如此类。五代战乱之际,“蜡丸传书”继续受到重视,其中尤以契丹与南唐的情报交流引人关注:契丹会同三年(940)十一月至会同六年(943)三月,南唐数次“遣使奉蜡丸书”*《辽史》卷4《太宗本纪下》,49~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这一时期内,契丹在北部中国的威权日盛、后晋政权则由石敬瑭转入石重贵之手;南唐李昇去世、李璟继立,且其与倾向北宋的吴越冲突激化,故而南唐与契丹靠拢可谓是现实的选择。至天禄元年(948)十一月,“南唐遣李朗、王祚来慰且贺,兼奉蜡丸书,议攻汉”*《辽史》卷5《世宗本纪》,64页。,双方已直接协商夹攻后汉。密谋如此重大的问题,采用隐蔽性强的蜡丸自是上选;不过受古来“华夷”观念的影响,加之各方关系瞬息万变,南唐以“蜡丸传书”与契丹沟通,可能也有在政治上预留空间、舆论上避免授人以柄的考虑。
随着北宋的建立,统一的局势更趋明朗,看似微不足道的蜡丸更屡屡发挥着出人意料的作用:乾德二年(964),宋太祖欲伐后蜀却苦于师出无名;而后蜀“素无勋业”的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妄图“建立大功”,“劝蜀主遣枢密院大程官孙遇、兴州军校赵彦韬及杨蠲等以蜡弹帛书间行遗北汉主”,密约北汉夹攻北宋;不料一行人路过开封时赵彦韬竟“潜取其书以献”,宋太祖闻讯而笑曰:“吾西讨有名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十一月,134页。,遂大举发兵,旋即获胜。开宝九年(976),江南兵败降宋的李煜君臣被送抵开封后,宋太祖责问张洎“教李煜不降”,继而“出帛书示之,乃王师围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蜡弹内书”;张洎“顿首请死”却“辞色不变”,宋太祖嘉其胆魄,谓曰“今事我,无替昔之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开宝九年正月辛未,361页。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围攻太原,北汉向契丹“遣健步间道赍蜡丸帛书求救”,却为宋将郭进捕获斩于城下;自此“外援不至,饷道又绝”,宋军攻城又“矢石如雨,昼夜不息”,北汉守军力不能支而降。*《宋史》卷482《世家五·北汉刘氏》,13939页。纵观上述事例,北宋方面正是通过在截获的敌方蜡丸上做足文章,方能实现相应的战术乃至战略目标。
当然,不可避免的是,宋在使用蜡丸的过程中,也曾因“不密”而饱尝苦果。据《金史》记载:靖康年间,金军压境,北宋君臣臆断曾经仕辽而后降金的萧仲恭、耶律余睹“皆有亡国之戚,而余睹为监军,有兵权,可诱而用之,乃以蜡丸书令仲恭致之余睹,使为内应。”遂试图拉拢彼时正出使宋廷的萧仲恭。然萧仲恭“素忠信,无反复志,但恐宋人留不遣,遂阳许。还见宗望,即以蜡丸书献之。”以此为借口之一,金“再举伐宋,执二帝以归。”*《金史》卷82《萧仲恭传》,18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宋廷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轻率盲动,致使原本用于秘密策反的蜡丸变成引火烧身的铁证。至绍兴八年(1138),王伦往祁州与完颜昌议和,当时韩世忠、岳飞、吴玠“各遣间招诱中原民”,完颜昌“得其蜡弹旗榜,出以语伦曰:‘议和之使既来,而暗遣奸谍如此。君相绐,且不测进兵耳。’”几位大将以“蜡弹旗榜”等秘密招诱中原故民,却为金人发觉并掌握证据,这自然不利于宋;幸而王伦处变不惊,将责任推给边将,并称“主上决不之知”,且“若上国孚其诚意,确许之平,则朝廷一言戒之,谁敢尔者?”在场金军将领闻言“相视无语”,紧张局面方得以缓和。*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9,绍兴八年四月,221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综上可知:一方面是在当时的秘密情报活动中,“蜡丸传书”的做法已十分普遍;另一方面,一旦蜡丸被敌方所截获,贻误战机、泄露军情,甚至令其洞悉己方困境,最终给敌方以政治或军事上的可乘之机,才是“蜡丸传书”失败而致泄密后,可能带来的最棘手问题。
由是可见,尽管通过蜡丸传递情报的隐蔽性相对较强,但仍然存在泄密风险,因此除“蜡丸传书”之外,烽火狼烟、飞鸽传书等手段也仍在使用,且宋人还有“字验”之法以助兵机。据《武经总要》载:“旧法军中咨事,若依文牒往来,须防泄漏;以腹心报覆,不惟劳烦,亦防人情有时离叛。”此处所谓的“文牒”“泄漏”“腹心”“离叛”两种情况,都曾出现于“蜡丸传书”的过程中,而“字验”正可加以避免:“今约军中之事,略有四十余条,以一字为暗号……凡偏裨将校受命攻围,临时发以旧诗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条,与大将各收一本。如有报覆,事据字于寻常书状或文牒中书之,加印记。所请得所,报知即书本字,或亦加印记;如不允,即空印之。使众人不能晓。”*曾公亮、丁度等撰:《武经总要·前集》卷15《制度·字验》,466页,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即便情报遭到拦截或信使叛入敌营,没有对应的解析密码,敌方也无从知晓文牒密语的真正含义。不过,看似更加保险的“字验”并未取代蜡丸,又是二者使用条件相异使然:“字验”之法需联络双方事先知晓相应的密码编排,但战场风云瞬息万变,恐难随时随地准备充分或临机调整,其使用自会受到局限,故而此时“蜡丸传书”及时、灵活的优点便会彰显。
在宋朝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用于秘密传递军政情报的蜡丸自然会让位于正式官文流转渠道中的政务公文,这是政权构建与行政规范的必然结果*相关研究,参见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前言),1~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但在某些紧急事态之下,蜡丸仍有用武之地:皇祐四年(1052)侬智高兵犯广州,知州仲简“使人间道以蜡丸告急”,正是周边“十县民皆反,相杀掠,死伤蔽野”而造成交通瘫痪、联络断绝的客观条件使然*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11,2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前述开州秦传序在面对李顺军时“蜡丸传书”,也是类似情况下的非常做法。此外宋与辽、夏、金、元之间,不论战时还是平时,长期开展着反间谍斗争,蜡丸作为秘密情报载体,其应用广泛自不待言。
三、诡谲的离间手段
秘密传递情报可以说是蜡丸的基本军事功能,但随着实战需要的发展,人们意识到完全可以逆向利用其“隐蔽”“保密”的属性,故意将写有虚假情报的蜡丸“泄漏”给敌方,借此离间其将帅官兵,干扰其战略判断,最终施展“疑兵之计”以达成心理战的目的。

此外,随着宋金战事愈演愈烈,游寇乱兵四起、社会动荡加剧,在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之下,“蜡丸传书”的用途继续扩展,不再仅仅是针对高层军政官员实施离间的工具,更成为一种被普遍使用的心理战手段。史载靖康二年(1127),“建康府牙校周德叛,执帅宇文粹中,杀官吏,婴城自守,势猖獗”。李弥逊“以江东运判领郡事,单骑扣贼闱,以蜡书射城中招降”,叛军“开关迎之,弥逊谕以祸福,勉使勤王”,恰好其后李纲“行次建康,共谋诛首恶五十人,抚其余党,一郡帖然”。*《宋史》卷382《李弥逊传》,11774页。李弥逊弹射蜡丸的目标并非“秘密联络”而是“公开招降”,结合此后叛军开城投降、李纲仅惩办“首恶五十人”的记载来看,说明李弥逊射向城中的蜡丸确实起到了分化、争取多数叛军的作用。绍兴元年(1131),宋高宗镇压“闽贼”范汝为,在下令“尽行翦戮”之时,提出“王师到日,其诸徒众能执汝为请命者,当受重赏”,又命“宣抚司多出榜示,及箭射蜡弹入贼中,使明知朕意”。*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0,绍兴元年十二月庚午,1035、1036页。为实现这一目标,南宋官军弹射的蜡丸数量必不会少,如此才能让更多“乱兵”了解朝廷意图,瓦解其士气、离间其官兵。而前述诸大将以“蜡弹旗榜”招诱中原故民,应当也有削弱金后方统治、瓦解其战争潜力的考虑。
四、余论
如前所述,蜡丸被应用于军事领域的记载大致始于唐代,入宋以后由于制作技术的成熟及实战需要的推动,军用蜡丸的使用愈发普及,其功能也从秘密联络的情报载体拓展至离间敌军的战术工具。
有趣的是,在承平年代的历史书写或价值观念中,蜡丸在军事领域的“秘密”色彩,似乎常会被转化为一种并不十分正面的文化意象。《邵氏闻见录》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
元丰二年,予居洛。有老父年八、九十,自云少日随丁晋公至朱崖,颇能道当时事。呼问之,老人曰:“公初自分司西京贬崖州,某从行……至崖州,久之,某辞归,公授以蜡丸,戒曰:‘俟西京知府某官与会府官,即投之。’某如所教,知府王钦若也,对府官得之不敢开,遽以奏,乃自陈乞归表也。其中云:‘虽滔天之罪大,奈立主之功高。’继有旨复秘书监,移光州。”嗟夫!任智数者,君子所不为也。世谓丁晋公、王冀公皆任智数,如老人之言,则晋公智数又出冀公之上。*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7,63、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这段文字中的褒贬之义自不待言,不论是丁谓使用蜡丸的“史实”、还是邵伯温记述此事的“书写”,蜡丸自身及其用法所附着的“秘密”特性,正是印证丁谓“任智数”之手腕机巧的生动例证;而王钦若“不敢开”“遽以奏”的反应,更表明丁谓使用蜡丸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除此之外,有关张洎使用蜡丸之事所引发的后续议论,更可突显蜡丸文化意象微妙。史载寇准与张洎同为给事中时,“尝为庭雀诗玩张洎曰:‘少年挟弹何狂逸,不用金丸用蜡丸。’讥洎在金陵围城中,尝为其主作诏纳蜡丸中追上江救兵也”。*王闢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卷10《谈谑》,1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在正史中宋太祖只是诘责张洎“教李煜不降”,提及蜡丸帛书也仅仅是作为证据加以展示,反而是张洎坦荡承认、顿首请死之举博得了赵匡胤的另眼相看;而此处记载寇准“讥”“玩”张洎的用词及诗句,却反映出此事对张洎声名的负面影响,而坐实这种影响的事由,恰是张洎使用了“蜡丸传书”的手段。无独有偶,宋神宗君臣某次讨论对夏战和,文彦博、冯京主张要“师出有名”,并且特别提到了宋太祖伐蜀时得蜡书而用兵的“故事”,但王安石对此不以为然:
太祖偶然有此语,若蜀可伐,恐虽无蜡书,太祖不患无辞,如太祖伐江南,岂有蜡书?但我欲行王政,尔乃擅命一方,便为可伐之罪。如夏国既称臣,未尝入觐,以此伐之,亦便有辞。臣以为不患无辞,患无力制之而已。*李焘:《长编》卷237,熙宁五年八月壬午,5760页。
不论文彦博、冯京还是王安石,都承认宋太祖使用了蜡丸,但王安石却刻意削弱了那封蜡丸帛书的重要性,这固然有其为“不患无辞,患无力制之”的制夏方略开说的意图,但蜡丸在军事实践中渐积而成的文化意象,恐怕并不符合北宋进步士大夫寻求“治道”的旨趣。故而王安石强调的“虽无蜡书”“但我欲行王政”,“尔乃擅命一方,便为可伐之罪”,实际上乃是以理想政治中“王道”所蕴含的“吊民伐罪”,解构了现实操作中“蜡丸”所带来的“师出有名”。这种对蜡丸“用”与“说”的微妙差异,颇有值得玩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