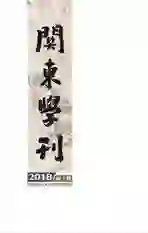茅盾作品的经典性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启示
2018-05-14张丽军妥东
张丽军 妥东
编者按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变迁、中国人生命情感与精神历程的最好见证者与思考者。对经典的认识与理解,我们在保持敬畏的同时,也要警惕把经典神圣化、固定化、不可变更化的神化、僵化思维方式。经典的神化与僵化,不仅造成一谈经典就是一种老、旧的陈腐历史气息,让年轻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畏惧情绪,阻隔了年青一代与经典的亲近感;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阻断了经典的持续性发展、变动性流变,把经典与现代、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文化创造阻隔起来,带来的是经典老化、经典已死的审美与教育恶果。
每一部经典都是活的、流动的经典,是对那个时代以及当今时代的精神生活发挥影响和作用的经典。在接受美学看来,文本只有被阅读,才是活的、有生命力的作品,而没有被人阅读的作品,只是一部“沉睡的”文本。经典不仅是活的,而且应该是生长的,是与当代人的生命、生活、情感,与当代人精神文化创造相衔接的。当代文学经典化,就是要“阅尽天下好文章”、“摆渡经典入瀚史”,即在不断的选择、淘洗中,把最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呈现出来,进入当代中国大众的阅读与审美视野之中,接续人类文明经典,从而实现同时代人的文学鉴赏与批判之使命。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百年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已经铸就了新文化、新文学经典。王富仁先生在“新国学”概念中,把传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等文化一起凝铸为新的包容性的、整体性的新国学文化。事实上,五四新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忽视、不可阻隔的新文化传统。而在这一新文化传统的大厦之中,现当代文学经典就是其中的一块块无比坚实、坚固、厚重的被历史猝火过的文化之砖。所以,我们今天去重读现当代文学经典,不仅有着进行当代经典化的历史使命,而且有着建构新国学、接续中华现代新文化的“旧邦新命”。
基于此,《关东学刊》从本期肇始开设“经典对谈”栏目,就是以与最年轻最富有活力最接地气的博士、硕士们的对谈方式,来对经典致以最自由奔放的敬意,是“经典”重新被阅读、被阐释、被激活的最佳方式,是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化的最鲜活实践路径。事实上,人类诸多文化经典就是在对话中诞生的;而经典及经典教育就是在“对谈”中实现的。“经典对谈”就是站在“文化巨匠”的肩膀上,用我们当代人的精神“心火”锤炼百年文学经典,给历史和未来一份来自当代中国学人的精神心灵图景。
一
今天我们来讨论经典作家茅盾。鲁郭茅巴老曹是现代文学对这些作家的定位,今天的现当代文学已经非常普及,很多作家小报小刊,都被发掘了出来。所以,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今天还有没有研究的余地?好像自己能想到的话题都被研究过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别人研究过并不等于没有研究的空间,我们可以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前进。时代会给我们提出无穷无尽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有心人,我们是不是一个有问题意识的人。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研究。前几年钱理群老师有一篇文章,他提出现代文学研究要重新回到大作家去。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立足点依然要对大作家进行研究。他说我们对小作家研究是可以的,具有一些史料的价值,具有许多补充材料的价值,挖掘出很多信息,让文学史进一步完整。大作家所面临的问题,他所触及的问题,遇到的困境,探索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小作家们无法达到的。所以他提出,要很好的很深入的进行现代文学研究,我们依然要从大作家着手。因为小作家所遇到的问题,他在作品中所处理的问题都不是最重要的,而大作家却时时刻刻在面临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中心经验。
大作家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是因为他所处理的问题扭结着这个时代的最核心的经验,很多问题都汇聚在他这里。这就是大作家和小作家的区别。我觉得这个讲得特别好。我们的文学研究依然要迎难而上,去触及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而这个问题却恰恰在大作家那里才能触碰到。就像鲁迅一样,他走得比常人更远,更能够触及那个时代的核心命题,他的伟大也在这里呈现了出来。他的痛苦、迷茫、困境都是超越别人的,所以具有代表性。我觉得钱老师的问题是非常具有探讨意义的。这也是我们要探讨文学巨匠的意义所指。
就具体而言,从这些年的茅盾研究来看,并不是很理想,甚至有点停滞不前。这几年的研究热点集中在沈从文、张爱玲、萧红等作家的身上,每年都有一批学术文章和学位论文出现,倒是茅盾等作家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一种两极化的评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清华大学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认为,恰恰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焦虑、局促、空间的逼仄,导致了文学创作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和不足。就像一个生命一样,由于气候、阳光、水分等问题,引发了很多不良的状态。就像我们看鲁迅一样,鲁迅也有遗憾。鲁迅一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他没有写出来。他的创作后期,基本上都是以杂文为主。现在看来可能存在很多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有很多多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蓝棣之要进行一种症候式的分析。其实这种研究恰恰是我们今天所匮乏的。我们总是沿着一个向度在进行研究,总是从正面予以肯定。他则反其道而行之。别人肯定的我要去找到它的不足,看到它的弊端。我就分析它们的不足、局限,看看我们的困境到底在哪里。而这种困境和局限恰恰是中国现代文学所呈现的问题核心所在。在蓝棣之的这部著作中,他对茅盾的作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茅盾的作品,是高级政治文件,不具有艺术性或艺术性含量很少。显然,这个评价是很低的。这个评价准不准确呢?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个人认为,倒是这种评价的方式给我带来了启发,让我思考为什么茅盾的作品会有这么一种被贬低化的评价,原因何在?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茅盾作品所呈现出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或者它今天对中国当代文学启发在哪?那么,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我认为茅盾对当代文学具有启示性的价值和意义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茅盾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书写。茅盾笔下塑造了很多光彩夺目的新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在每一个小说故事中都是中心人物,都是光彩熠熠、灿烂无比的。她们一出场就是中心,而且这些女性形象与以往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有一次我跟作家刘玉栋交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写女性形象,茅盾写得依然是很精彩的,依然无比耀眼。茅盾的《蚀》三部曲,包括三个中篇,分别是《幻灭》《动摇》《追求》。在《动摇》里,他没有写这个女性具体如何,只是写在街上两个人看到一个美男子挎着一个像银子般耀眼的女性从他们面前走过。这就是他对女主人公孙舞阳的侧面描写。
其二,是茅盾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独特眼力。事实上,茅盾不仅是一个作家、编辑,更是一个出色的评论家。他的文学评论眼光是非常尖锐的,他对很多作品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比如他对鲁迅的评价。在创造社与鲁迅论争的时候,李初梨等创造社小将对鲁迅指责,说鲁迅是双重的反革命。他们提出,鲁迅的阿Q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时代已经没有阿Q了。这个社会是一个新的社会,是农民开始觉醒的社会,大家都是觉醒的人。而茅盾认为,鲁迅依然有他的价值,鲁迅写的是老中国儿女,木偶般的,没有希望的老中国儿女。同时他也承认社会在变化,是有新的人物在出现,但是,老中国儿女依然存在。茅盾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的。
其三,是茅盾对长篇小说的贡献。以他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对社会发展以及长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他也因此被诟病。评论家说他的作品与社会太近,是“主题先行”。还没有写小说,就已经决定了人物的命运、观念、思想,称之为主题先行。但是不是真正的小说就没有了主题的观念了呢?这个我觉得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个人认为,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写作观念。汪曾祺的小说写作可能就是一团意绪,一种感觉。对于茅盾来说,他所要呈现的是一个问题,一条道路。我认为,主题如何前行才是问题。如何避免观念的写作,成为艺术的写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有观念是很正常的事情,关键是如何不让观念成为空洞的说教。这是目前茅盾的研究现状和评价,我们先做一点梳理。
我们回到茅盾的新女性形象书写中来。文学与我们的肉身密切相关,我们首先是一个肉身的存在、具体的存在、感性的存在。文学从来都是以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为中心。儒家文化强调对人的身体的重视,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是另一个方面,又追求杀身成仁的道义。这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悖论。佛教文化则认为身体是一种需要舍弃的存在,而道家文化则强调养生。中国古代的身体叙述,止于头部。比如《红楼梦》中描写林黛玉,只描写她的面部表情,接着就是写她穿什么衣服。古代的言情小说,我们看到的是人物的面部,身躯则是用棉布包裹的躯体。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以及海派文学笔下的身体是与北方的描写有很大区别的。《海上花列传》也是如《红楼梦》一样,以服饰描写为主。而到了新文学时期,像郁达夫的《沉沦》里面的女性身体描写就已经不一样了,已经出现了裸体的书写。《沉沦》里面有一个场景,“我”作为一个忧郁症患者,“我”在房东家里看到房东女儿洗浴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的身体和以往的身体描写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到了后来20世纪20年代的新感觉派文学,像穆时英的小说《白金的女体塑像》,写一个医生,他对以往的身体感觉只是生理上的医学上的理解,但是有一天,一个女性坐在他面前,他突然感觉到这个女性是一个异性的存在。他提议这个身患肺病的女性需要裸体的灯光治疗。在治疗过程中,他的性意识突然萌生了。这种身体的性意识的萌生,是海派文学的一个路数。
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显然是这个路数来的,虽然茅盾非常喜欢传统文学,他特别喜欢《红楼梦》,甚至可以背诵,但是他的写作并不是沿着传统的路子在走。有人分析茅盾的女性形象来源于北欧女神。事实上,茅盾的写作要比新感觉派早。新感觉派文学在1928年才开始,而且像刘呐鸥等人也并不是写作那些都市题材,而是进行乡土小说的写作。他们最早写的是进城农民的生存境遇,而在这之前,茅盾已经开始塑造这些女性形象了。在茅盾笔下,《幻灭》里的静女士,如名字一样,是安静的、静美的传统的女性。在学校里读书时静女士受到了一个男人的欺骗,跟他发生了关系之后,她发现他是一个特务并选择了离开。小说中的慧女士,展现的是动态的美。她从海外归来,身边有很多男人,走在哪里,都是中心。小说写这两个女性同时离开了上海来到武汉,静女士她不希望热闹,希望安静的热情的生活,希望为革命工作。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一个是指向了身体的叙述,另一个是指向了革命,而革命与肉身在某一个时刻达到了和谐共振,那就是青春。她们是一个个热血的身体,热血一方面来自于体内,另一方面则是时代的革命的热潮。她们希望融入,但是却找不到路子。静女士来到武汉,革命如火如茶。一场一场的运动,但是她找不到方向。她来到工作单位,人人都要为她介绍对象,她很烦。最后她找到了一个在伤病医院给病人洗衣服的工作,她突然变得安静下来了。她说,我在做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革命随时都在流血牺牲,为他们洗浸泡着鲜血的衣服。在这个过程中她遇到了一个军官——强连长。强连长这个人从来都没有性意识,从来都是没有什么男女性别观念,只有战斗。但是这样一个男性,第一次在静女士柔弱的个体面前软化了。他们恋爱了。本来,静女士受到欺骗之后已经没有了其他的情感需求,但是在强连长面前,她重新找回了情感。小说描写强连长跟静女士度过了一段蜜月生活,他们去庐山、去很多美丽的景点去玩。里面有很多描写很有意思,描写了一些性隐喻的东西。光洁美丽肉身的呈现用一种比喻的手法描写了出来。
慧女士也同样苦恼,她的状态是周围的男人尽管很多,但是都不是真心的,都是负心汉。小说写静女士的甜蜜美好的时光突然一下子就停止了,因为前方發来了电报,战争爆发了,强连长要归队。那是回还是不回呢?最后还是去了。静女士重新进入了新的幻灭。在《动摇》里,孙舞阳女士是上级派来的革命指导者,是一个美女。她一站在那里,总有目光关注她。方罗兰也是一个革命者,但是她处于革命的摇摆状态之中。孙舞阳却是一个动态的热情的人,方罗兰每天都在动摇。
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叙述有一个很重要的现代性词汇,就是对“乳房”的多次书写。香港学者陈建华在文章中谈到了茅盾小说关于乳房的关注。他认为在以往的小说描写中,这样的词汇是很少的,关于乳房的描写也是很少见的。而茅盾的小说中这样的描写是很多的。小说描写孙女士当着方罗兰的面换内衣,多次直接或间接涉及了这方面的描写。小说还写到女性革命者的联盟。联盟倡导所有女性都要解放,连地方尼姑庵的尼姑都要找到一个男人生活。这引起了地方的一些地主的恐慌。这些地主组成了反革命势力,由于方罗兰等在革命中的摇摆不定,使得反革命势力迅速反扑。小说描写反革命势力在掌握主动权的时候,对那些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将她们的乳房穿起来,在大街上游行,场面极其残忍。这些女性身体的描写很多,也都和革命有关。
如果说《幻灭》《动摇》还很隐晦的话,《追求》里就更为明显了。《追求》里的章秋柳女士,爱上了一个革命者。当他们在一起拥抱,寻找恋爱的感觉的时候,第二天那个革命者就消失了。章女士很受伤,过了几年,这个人又回来了,她接受不了。章女士表达自己对革命的热爱时说,我要用我的身体去拯救一个人,最后她遇到一个叫史循的人,这个人是一个颓废症患者。怎么办呢?章女士说,我要去用我青春的身体去拯救这个人。小说写,章女士和史循在一所房间里裸体相看的时候,史循看到一个无比优美的光洁的身体呈现在他的面前,他的心灵被撬动了,他感受到了力量。但是当他的身体出现在镜子面前的时候,突然他就橡皮球被戳破了一样,软了下来。他的身体是那么苍老,那么赢弱。他突然就颓唐了下去,甚至走上了自杀的道路。章女士尽管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拯救这个人,但是她最终失败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革命加恋爱小说。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里面有一个叫王曼英的女性革命者形象,她和许多同志一样,在革命中遇到了失败,她遇到了自己以前的恋人,他成了反动派的头目。后来她发现自己得了性病,她非常绝望,后来又遇到一位仰慕的革命者,虽然她仰慕他,但是却和他保持着距离。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希望她用身体去报复那个反革命头目——她昔日的恋人。用身体作为一个炸弹,来毁灭他们。这是她的选择。后来她遇到了让自己走出困境的革命者,并发现自己的病只是一个小病,并不是性病,最后她和这个革命者相爱了。这就是《冲出云围的月亮》。这里我们看出一种“肉身成道”的方式——用自己的肉身成就一种革命之道。事实上,茅盾笔下的肉身是一个光洁的美丽的肉体,它追求的是崇高的目的。但是,她们都遭遇到了挫折。
在茅盾的另一部小说《虹》中,梅女士也是一个饱受苦难的女性形象,她的婚姻是被包办的。重庆到上海的旅途中,看到三峡美妙的景色,让她终于摆脱了旧时的那种沧桑。三峡壮丽的景色展现在梅女士面前时,她的革命热情一下子被激起来了。在这里,对梅女士身体的描写已经减少了,转而增加了对梅女士欲望的描写。梅女士来到上海,她决定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但是每当雨夜的时候,她女性意识或母性意识依然会萌生出来,她说,我依然是一个女性。在她看来这是一个耻辱,她依然没有成为一个钢铁一般的革命者。后来她遇到了她情感的转移者——梁钢夫,她将自己的情感转移到了这个人身上——尽管她认为这是不对的。小说结尾是另一种呈现,梅女士认识到,我爱的不应该是一个具体的男性,我爱的是主义,是刚性的、雄性的、至高无上的革命主义。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梅女士已经完成了从个体的、肉身的到一个共性的、刚性的、神性的革命者的转变。梅女士爱的是主义:在这里,她与革命合二为一,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神性的存在。所以,我们看茅盾的女性形象书写有一个动态转变的过程。在早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肉身、性、身体,而在《虹》所呈现的革命中我们看不到身体,只看到欲望和近乎神性的革命的表达。
在茅盾后来的作品中,肉身的书写已经微乎其微。比如在《子夜》中,虽然也有很多女性形象,但是早期的那种身体的描写已经不复存在了。这部小说开头依然写得很有意思,这里面有很浓的新感觉派的味道。吴老太爷带的那些金童玉女的视角描写上海的霓虹灯,尤其是吴老太爷的视角,呈现出了旧式视角下的上海。在这里,他把女性形象的书写和革命的道义连接在了一起,这恰恰是和时代的精神共振,虽然这些女性形象非常光彩照人,但是到后面这种描写就变得很淡了。所以,梅行素说她在上海是和马克思主义的语汇联系在一起,已经脱胎换骨了。新的革命者梁钢夫革命化的气势依然在是她陷入情欲的苦痛,既然梁钢夫把自己纳人有意义的生活,那么梅行素的自我救赎道路就是循着梁钢夫的道路,把自己的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所以,小说描写革命者共同走上街头的一个壮美的场景,这让我们联想到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女神带领人们走向胜利的场景。实际上,女性形象的身体意义在其他的作家的眼里同样呈现了出来,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提出,萧红、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是和民族国家的隐喻联系在一起的。
身体叙事在延安文学中又发生了很大的转折。袁静、孔厥合写的《新儿女英雄传》里面的牛大水和杨小梅。杨小梅在革命的叙述中已然是一个异性形象,但是这个异性形象所呈现的美是和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是截然不同的,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是一种肉身的美,但是在孔厥笔下,杨小梅身体很强壮,皮肤透着红润的颜色,很强壮、很能干。她的身上透着坚强能干的劳动美,她的身体指向了劳动。这是这个时期的劳动的革命之美。牛大水看重的杨小梅的美是符合劳动人民审美的。这一时期的女性叙述是一种革命的女性叙事。到了新时期,女性叙事重新回归身体和肉身的写作。像林白、陈染的作品。当然,这里的肉身写作就显得无比沉重了。贾平凹的《废都》里,那些女性的身体是被围观的,是被消费的。在这里已经回到了精神隐喻的层面,贾平凹讲的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沦落,人们在这里逃离自我,在这里颓废,做一种无望的抗争。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田小娥作为一个抗争者,她和礼教抗争的奋斗,就把一个个虚伪的人全部拉下来,回到最原始的肉身和欲望上去。这在白嘉轩看来无疑是一个妖魔鬼怪,是这一时期所有怪事的来源,他想要一座雷峰塔,将田小娥压在雷峰塔下。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文化的冲突在里面。这就是陈忠实的独到之处。
新世纪张炜的《独药师》里性的描写很多,但是他写得让人感觉不出它的存在,它是以寻找爱情为名,是一个男性的爱情寻找史;如同金庸里的描写一样,每一段描写都是一种真情的存在。文学是以情感为核心的,而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爱总是和欲望联系在一起,和身体联系在一起,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肉身。但是肉身仅仅是抵达的此岸,绝不是彼岸。它的彼岸是对道的追寻,其以生命为轴的对道和爱的追寻。我们下面开始讨论。
二
隋雅倩:我覺得茅盾对于女性肉体的描写,在我看来是对当时的时代审美的反叛。因为按照当时的传统来说,那种静态、安静、闲适的美在大家心中是比较认同的,但是茅盾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他对孙舞阳的描写,突出她的肉体之美,并且追求一种身体上的刺激。孙舞阳大胆地展现自己的美,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觉得这是茅盾所传达的一种对女性形象的一种重新建构的理解。就像您刚才所说,这也能反映出茅盾对于时代女性解放的思考。
张丽军:当时的女性解放运动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支。女性倡导自由恋爱,突破自己的婚姻束缚,和自己心爱的人同居。在20年代,同居是一个革命性的词汇。就像涓生和子君,就像萧军和萧红,鲁迅在给萧红和萧军的书信上说,“我祝贺你们同居五年了”,肯定的就是他们这种追求个人独立和解放的行为。
李文慧:茅盾的作品我读的不是很多,我只读过他的《蚀》和《虹》。您前面通过梳理茅盾作品中对女性书写的变化,来展现茅盾对于革命态度的演变。但是,我想说的是,有的人可能会把茅盾的小说归结为成长小说,也就是说他会通过几部作品描写女性对于革命态度的改变来展现他本人的成长,所以我想问的是,是不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茅盾是通过对几个女性不同阶段的变化来展现她们的成长呢?
张丽军:这个角度不错,从个人的精神成长来看,其实我们会发现里边的静女士她和时代的关系也是一个探索式的。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她对时代的认识和探索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生活给她教训、快乐、幸福,也给她迷茫,她依然在往前行走。包括梅女士,她是一个追求自己婚姻幸福的反抗者,到后来,她真的成为了一个从具有女性意识到女神一般存在的人。她完全是一种升华的、蜕变的、化蛹成蝶的一种存在。
妥东:我觉得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如您所说是有一些贡献的,但是问题在于,在茅盾的这些专注于表现女性的小说中,他往往将女性写得很到位,她们的个人成长也好,内心纠葛也罢,也包括对于女性情感的分析以及身体的描写,都比较到位,但是相对于他笔下的男性来说,就显得比较单调了。这是茅盾在人物形象上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我觉得这一方面与他本人的性格相关,另一方面我觉得茅盾对女性的描写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他对于所描写的女性往往处于一个仰视的态度,以一种仰视的姿态在看待这些女性,所以,这样的写作姿态的问题在于,本来属于女性的一些平常的特点就有可能会被夸大,而真正属于女性气质的东西可能会被遗漏掉。另外,他在描写一些女性的时候,比如孙舞阳、静女士等人的时候,往往关注于她们的表面,对于她们的身体描写更多的是以一种欣赏的姿态去刻画她们。他与这些女性似乎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而在他的观察和欣赏中,女性内心中的丰富特质反而表现得不够,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
张丽军:我们知道,茅盾童年是没有父亲的,童年时代跟母亲一起度过。这点“五四”的很多作家都存在这样的情况,比如鲁迅、老舍等。那么这种仰视是不是就是一种高扬的姿态或者说作者没有深入到女性的生活中呢?我觉得可以进一步思考。茅盾笔下的女性的革命生活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态的生活,革命是要放弃一切利害向着一个目标前进的,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则是琐碎的、千丝万缕的。革命生活和日常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革命时代的要求和现在的要求是非常不同的,我们今天的时代是后革命时代。后革命就是日常生活,革命之后就是进入了日常的安定和秩序。
亓慧婷:刚刚听老师讲,我就想到了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面也有很多性描写,他的性描写总是与很多爱和欲望以及生殖有关。那么我就想茅盾的女性身体描写是不是也和这些有关,或者说是对生命重量的强调,即用身体来传情达意,引向女性走向自我的一个思考。女性对于身体的重视以及为了革命牺牲自我这样的表现,是不是就是如老师所说的与“肉身成道”的主题相关。通过对“道”的强调来突出茅盾对革命的一种传达,就像蓝棣之所批评他的一样,他的小说是一种政治文件。
张丽军:是不是牺牲呢?为“肉身成道”而牺牲?那么和米兰·昆德拉的描写有什么区别呢?
亓慧婷:米兰·昆德拉更多地写的是女性对于男性的爱的束缚。他的性描写尺度比较大。茅盾的性描写成分不是很重,他主要是利用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展现一种生命的重量。
张丽军:好,说得很好。其实茅盾笔下更多地写的是一种性意识,而不是性行为,是一种“性感”,对性的感觉;是一种观感,而不是动作。米兰·昆德拉更多的是一种行为。亓慧婷提出的问题很好,就是茅盾笔下的女性是不是有一种“肉身成道”的行为,“肉身成道”是不是为“道”而牺牲呢?其实我觉得这是茅盾书写的另一个困境所在。如果肉身是要为道而毁灭的话,那么这个道,是不是真正的值得追求呢?虽然我们说要为革命而抛头颅洒热血。另外,在他笔下实际上是一个“去肉身化”的写作。他是成道的,但是这个道已经是一种近乎无情的道,去情的道。
刘仁杰:我也想谈一谈革命与日常的关系。茅盾的女性身体叙事是处于革命的风暴之下的,这可以看作是茅盾进行革命的手段,在风云变动的时代大背景下,这种女性身体描写突破了中國传统,表现了社会的转变,我觉得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价值,而在当今非常平稳的社会状态之下,像茅盾这种描写对我们当代的作家还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我看到的一些就是表现女性在金钱利益下的女性身体描写,没有了当时的女性的那种崇高和美,更多是成为一种被消费的存在。
妥东:我倒觉得这种“肉身成道”或许还有一种普遍的含义。就是说,女性作为弱者,这种表现可能更多的是与她寻求一种强力的一种过程。因为她们生而为弱,所以就需要寻找一种强力来维持自己的一种存在,这个我觉得,如果有这层含义的话,那么茅盾所写的所谓的“肉身成道”也好,仁杰提到的女性寻求金钱利益等等,其实都可以看作作为弱者的女性寻求强力的过程。我觉得从这点看,当代文学的描写和当时茅盾的描写是有共同之处的。
李文慧:老师我曾看到过一个观点就是有人把他和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比作画家和模特,他觉得模特永远是他的焦点,但是画家却永远走不进模特的内心。我觉得,茅盾笔下的女性跟这个是一样的,她们永远是焦点,但是却又有一种唯我独尊的傲视的姿态,所以我觉得茅盾笔下的女性其实是很强硬的,不存在弱的特点。
张丽军:我个人觉得茅盾笔下的慧女士其实还是很精彩的,慧女士说,你看我都26岁了,我还没有成家,虽然这么多人围着我,但是没有一个对我是真心的。她感到很痛苦。这里我觉得茅盾对于女性心理还是有关注的,但是是不是真正进入到了女性心里,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
妥东:我觉得茅盾笔下的女性毕竟是有时代背景的,他是要表现一个女性走向解放的过程的。无论在何种层面来讨论女性的身份地位,其实都无法避免的会谈到女性自身的地位,而对于那个时代而言,无疑,女性是处于弱者的地位的。茅盾自己的性格是比较懦弱的,而他对于女性内心的一种契合也是从这个弱者立场出发的,我觉得是这样。
张丽军:你谈到的是从作者出发看待女性的心理,但是,仁杰刚才也提到了时代的审美变化。就是说,肉身如何美?这显然是审美标准和眼光的问题,以往我们古代的美的传达是一种身体衣着所带来的美的气质,但是茅盾笔下的女性则指向了女性身体自身的美,这一点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来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或者说,中国古代的身体描写也有,但是它是被遮掩着的。这可能也是一种新的变化,包括作品里的语言和词汇的变化。
张艳丽:我看的《蚀》三部曲还有《莎菲女士日记》里的女性都是一种反叛的女性形象。不论是思想和行为都是反叛的,包括《雷雨》《安娜·卡列尼娜》这种比较经典的女性形象好像都是反叛的,西方的很多神话故事里也有很多反叛的女性形象,好像反叛的女性形象大都可以成为经典,她们身上的阐释性可能更丰富一些。这种类型的女性形象可能所蕴含的阐释空间相对于日常的女性来说可能更典型一些。
张丽军:你的意思是那些淑女形象可能很难进入文学史?在茅盾笔下对女性身体的描写是和古代的女性形象有很大的差异的,是创造新的审美经验的。张艳丽同学提出的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女性形象的反叛性和阐释性意义。其实我个人觉得,反叛就是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的独立,我们看到很多人都不是顺从的,而人类的发展史、进步史就是人的探索和独立的成长史。
徐晓倩:我只看了茅盾的《蚀》三部曲,我的一点看法是,我觉得茅盾是把革命和女性的书写联系在一起的,女性的身体激发了革命者的活力,革命者對女性的向往追求则是以革命的名义,感觉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为革命而走到一起,而是单纯的为了爱情。
张丽军:革命只是一种借口?
徐晓倩:对,他这样写是对传统的革命书写的解构,他似乎要向我们展现的是女性必须投身于革命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但是他其中的描写很多时候是与这种革命的精神貌合神离的,所以我觉得他的女性书写还是把女性边缘化了。
张丽军:如果把女性作为主体,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来写呢?是《莎菲女士日记》?对革命来说,女性可能并不是主体,方罗兰也好静女士也好,都是如此。但是我们看到另一个女性——梅女士的形象却是跟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她要去掉一种肉身的东西,要嫁给主义,要成为一个为革命抛弃情感的这样一个形象。
苗立群:老师上节课讲到女性身体叙事,我记得《动摇》中一个很有特点的场景,就是孙舞阳穿着裙子,站在房间中一边跳舞一边唱着《国际歌》,房间里有两个男性,我觉得这个画面很有意味。孙舞阳这个形象是一个自在的和外在的结合在一起的异化的女性形象,我觉得她在这个画面中展示出三种内涵,第一,她哼着国际歌,是一种隐秘的革命话语的体现;第二是她在房间中独自唱歌转圈的行为,体现了她追求解放或已经走在了解放的路上的这样一种状态;第三是房间中还有两个男性形象,所以,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一种站在男性立场的欲望话语。因为他们两个人在津津有味地欣赏孙舞阳。在他们的注视下,孙舞阳的女性解放被这样传达了出来。茅盾笔下的女性身体在进入到文本中的时候,不仅仅有女性自身的立场,也有男性、革命的立场参与其中。
张丽军:说的很好。女性书写的审美效应是一种多元目光的交织。我觉得你提到的这个场景非常好,孙舞阳自我得意的、自我欣赏的状态是和男性目光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在孙舞阳看来,她的这种行为本身可能就是革命的,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是在改变着这个世界的。
黄加秀:我觉得茅盾早期的作品如《蚀》三部曲,对女性的心理描写都比较到位,形象都比较突出,但是到后来,比如《虹》中的梅女士,她的身体是为革命而牺牲。包括后来《毁灭》中那些繁复的社会分析,我觉得在这里,女性形象相对薄弱了。我的疑问在于,茅盾写作的变化是否对于他的女性写作朋有裨益?在我看来,像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作品可能更能反映女性的特质,而茅盾的女性写作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比如后期的作品女性形象可能更单薄了一些。
孙悦如:我挺同意黄加秀的观点的。茅盾在写女性的时候,总觉得有距离,隔着点东西。他写孙舞阳的时候,其实是别人眼中的孙舞阳,她是被有距离的观看的对象。我觉得作者这样的写法可能是一种机智的回避,因为他可能真正的无法了解女性的内在,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王博:我读茅盾真的不是很多。我读阎连科的作品比较多。他也涉及许多女性生存状态的东西,比如《受活》。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茅盾作品中的女性的“肉身成道”的主题,与当代作家的写作不同的是,当代作家的女性写作更私密一些,比如陈染、林白的作品。我觉得这两种写作都是捕捉到了自己时代的特点的。茅盾的书写更符合革命语境,而现在的这种书写可能更加符合现在的追求私人化的写作。他们彼此都有处在时代的意义。但这两者之间可不可以对比,我还没有答案。
张丽军:到底是落到国家还是个人,这因人而异。对于茅盾来说,他的归结点可能还是要落在主义上,因为茅盾本人也是一个革命主义者,他是非常早的共产党员,虽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脱离了党,但是他还是那种意识追求很强烈的作家。像我们今天,革命语境已经离我们远去,所以可能更多要落到个人的话语之中。实际上,当茅盾的归结点落到革命上的时候,他的女性书写已经失掉了色彩。而文学始终是与肉身相关的,如果失去了这些,成了主义的话,那就离文学远了。
袁盼盼:茅盾的写作可能更多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关。茅盾笔下的女性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男性视角下的女性。陈染、林白对女性的描写满足了男性对女性的窥视欲望,但是茅盾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他这样写到底有多少女性意识呢?茅盾可能更多是站在女性解放的立场上来写女性的。女性的解放可能更多的是由男性推动的。
吴加艳:女性解放是男性推动,是因为男性的权力大一些,女性的推动会小一些。
于露:茅盾笔下的新女性是走进革命的时代女性,新女性让我想到的是鲁迅笔下那种反抗的女性,比如子君、爱姑等。新女性比如说莎菲等在精神的反抗中走到了时代的前沿。茅盾笔下的女性更多的将自己与时代结合在了一起,积极参加到了国家政治中,比如梅女士。茅盾笔下的女性更多是一种时代的女性。
张丽军:于露同学认为茅盾笔下的女性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往下想:女性走向革命道路是一种自觉的方式。比如,莎菲对于凌吉士的追求,其实是她走向自我要付出的代价。梅女士对革命的热爱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是不是还有其他?是不是有一种对于话语权力的追求呢?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勒庞所提出的那种“群盲”是不是在梅女士身上也有所体现呢?她对于革命追求的那种迷狂状态。
吴加艳:茅盾对于女性身体的关注是与古代的关注点完全不同的。我觉得这主要是道德审美观念的变化,再一个就是社会隐私的开放。过去的身体遮蔽是一种隐私,而随着社会的开放,这种隐私也慢慢开放,变得透明。还有就是对人的关注也推动了这种对人的身体的关注。
张丽军:很好。过去对美女怎么形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眼睛很好看,能够流转出秋波来。这是古人的审美。而现在把过去的束缚和压抑解放开了。所以在身体写作方面才有了新的关注,审美也出现了新的方式。
王含:茅盾的作品是关注女性解放的,他关注的女性怎样在解放中获得自己的力量。老师提到的“肉身成道”肉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性意识,不仅是女性自身的性意识,更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好奇,茅盾的作品就是探索女性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独立的、自主的力量的。他探讨的是女性对自我的发掘。葛兰西认为认同是一种隐秘的权力关系,就是说女性通过获得自我和社会的认同,从而获得一种话语权力,所以我觉得在茅盾的作品中,他的女性意识还是很强的。
张丽军:王含同学认为,女性意识更多的是一种女性对自我的认识。实际上我觉得里面不仅是一种女性意识,可能更多还有一种母性意识,比如章女士说我要拯救,看起来好像是女性在保护男性一样。
成志雄:我觉得茅盾的作品或许没有真正的女性解放的意义。首先,关于性别,我认为茅盾在性描写上更多的赋予了一种性别意识,而这种性别意识就是革命。古典的女性是气质上的静美,而“五四”的女性则是一种意志美,再往后像《儿女英雄传》是劳动美,现在则是性感美,它更多指向身体,对于男性而言是一种性消费,对于女性而言是一种性资本。茅盾的写作与其说是有一种窥伺,不如说是一种规训。女性有可能是通过革命获得自身的一种满足感,可能是通过自身发现自己的。但她可能更是一种群盲文化的体现。个人的精神意志非常容易在集体的裹挟之下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茅盾可能更多充当了这样一个推手。不管是“肉身成道”,还是自己的所谓的觉悟,其实都是在推动女性意识到自己有一个新的获得自身的方式,那就是革命。另外,《蚀》里面的核心是去女性化,也就是同性。它跟许地山的《春桃》一样把女性升华到一种意志,实际上是对女性的一种扼杀。所以我认为茅盾的笔下没有涉及女性解放。
张丽军:好。你认为你说的意志美和他小说中大量的性描写有什么关系?可能在方罗兰看来,她依然是一种女性身体的光芒。女性的身体描写的不同变化在今天看来,可能更多是一种消费的意味,而实际上,当时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也存在消费的意味。
杨雪:我觉得茅盾笔下的女性之所以细腻逼真,除了他的生活经历之外,可能还在于男性的特质。其实很多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可能比女性笔下的女性更加真实。是不是因为有一种女性情节?而很多作家之所以表现女性的反抗,可能不是她们弱,而是将女性从边缘推向前台的一种策略。
涂文萍:在茅盾笔下更多凸显出一种身体化的特点,这反映了他在时代浪潮中对于革命与伦理的一种观点和看法。就他写作的意义来讲,他将许多被遮蔽的女性的身体和意识展现了出来。我觉得他眼中的女性还是以男性视角去塑造的,写女性,更多是为了实现茅盾对于革命的一种想象,他的想象是在女性的身体上得以实现的。刚才袁盼盼提到女性的女性意识和男性的女性意识,在这两者的视野中其认识女性的角度同等重要,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当然,我很无奈的承认,女性在不平等的关系之下现在依然要去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力,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一种窘迫的境遇,很多时候,女性是通过男性来确认自己的存在的。所以,无论是缺乏哪一方的“观看”这种方式都是无法完成的,都是未完成的。
张丽军:其实强大不只是外在,还有一种内心的强大。我记得有一次在桂林开会的时候,程光炜老师说,我们男人啊,从小受母亲管辖,长大了受妻子管辖,一生都在女性的管理之下。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对于两性关系的认识,还是需要时间深入的。每一种书写都有独特的存在价值,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宋欣:我觉得我们要更多的把视点放在身体写作上,而不是去计较它是男性还是女性之间的权力。茅盾的写作更多的是将女性被遮蔽的状态展现了出来。这与现在的林白等人的写作是一致的。他们都关注到了女性作为女性的独特之处,当然,现在的一些写作走向了极端。
张丽军:身体写作不是谁都能写得好的,身体写作对作家是一种挑战。就像陈忠实的《白鹿原》一样,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
王珊珊:我觉得从《幻灭》里,我读到的是一种对革命的怀疑。就像静女士,外表虽然美丽,但是她的内心是无法捉摸的。这可能是一种回避,而这种回避则影射了她对于革命的态度。比如静女士,从一开始对革命的冷淡,到投身革命,再到觉得革命也是一种无聊的行动,进而对革命产生一种抗拒。静女士其实对爱情的追求是凌驾于革命之上的,她并未实际融入到革命之中,她的这种怀疑的态度是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不平衡造成的,这也造成了他的很多作品完成度不高。
张丽军:这个可以进一步思考。王珊珊同学对文本的感受很好。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把握要从自己的感觉出发,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实际上,革命从来都不是与我们无关的,它是真实发生的,它在改变我们的命运。就像子君、林黛玉,是不是个性很强?但是她们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束缚,就像子君,她没有一条合適的路。但是茅盾笔下的女性,尽管很迷茫,但是她们潜在的路已经有了,革命已经改变了她们的境遇。就像小说《星》里面的梅春姐,善良美丽,革命到来了,她有了新的选择,有了新的追求,她的命运与革命息息相关。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受到过革命的影响,不管你认可不认可。
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肉身如何安放自我的心灵,这都是一个问题。“肉身成道”好,“道成肉身”也好,这都是一种选择。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从身体出发。当代中国70后作家鲁敏的长篇小说《此情无法投递》里面写到的那个男大学生用望远镜观看那些女性,他那柔弱的心灵足以让我们震撼。这里面已经没有革命,而是回到了常态,回到了身体本身。所以说,文学对于身体的表现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征,茅盾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塑造了很多新的女性形象,这是他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精神性启示价值。好,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