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叙事的焦点
2018-05-14赵飞
赵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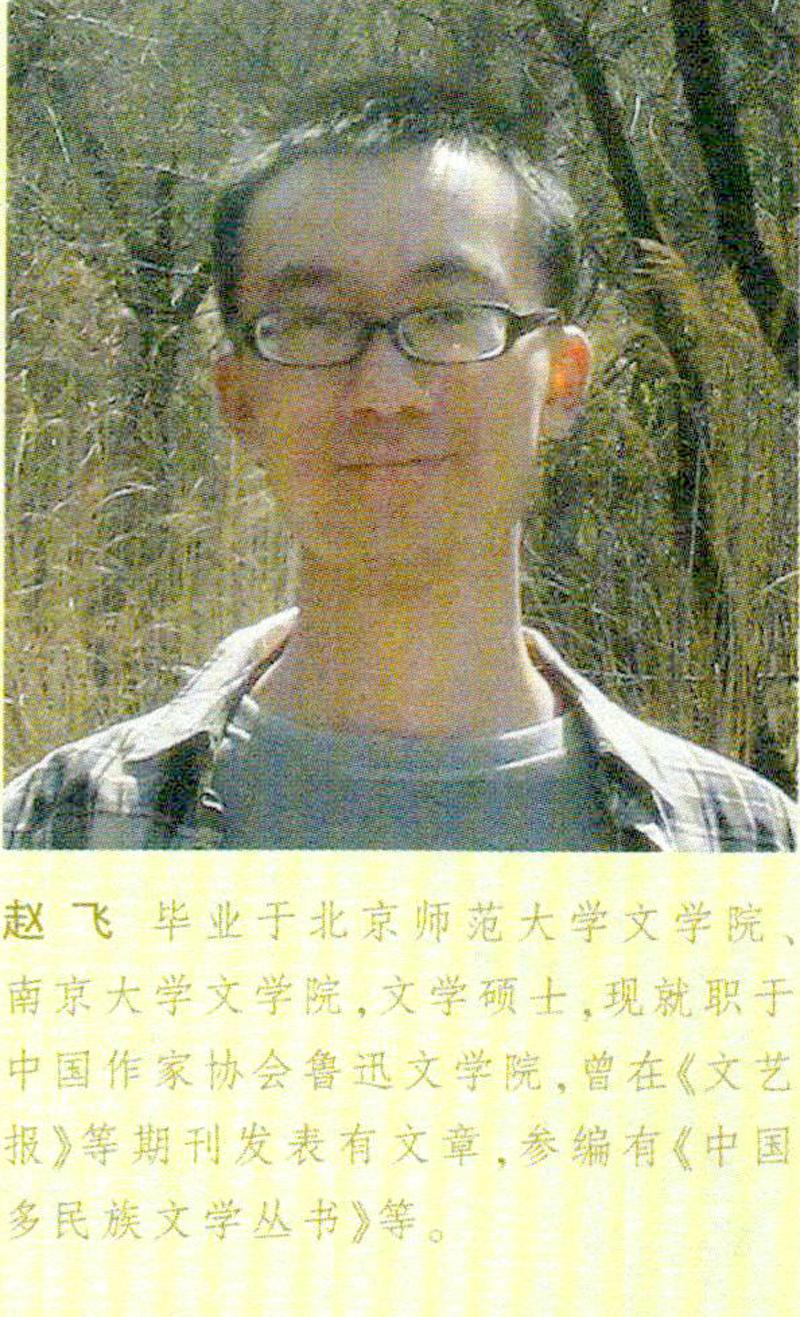
陈丹玲的《补白》是一篇令人惊喜的作品,文章充满地方特色,而又没有落入惯常的用地方特色博人眼球的窠臼;富有文化含量,而又不同于常见的掉书袋式、教科书式的散文。无论是在思想主题的把握上.还是语言文字的技术层面上,都是一篇让人眼前一亮的佳作。
“补白”的本意,是“填补空白”,原指用来填补报纸杂志上空白处的短小文章。鲁迅就曾写过三篇短小锋利的《补白》,发表在1925年的《莽原》上,后来结成一篇,收录在《华盖集》里。陈丹玲的这篇散文,挥挥洒洒一万三千余字.当然无论如何谈不上“短小”。全篇围绕西南一个名叫合水镇的小镇展开.镇上的人们世代以造纸为艺,以造纸为生,生产当地特有的一种白皮纸。取名“补白”.当是因为写的是一个被世人忽略的小镇,被世人忽视的小人物,都是不重要的.只是热闹喧嚣的现实生活和人们视野之外的一处“补白”——当然取的是反义,而“补白”也让人联想到白皮纸,可谓妙哉。
如前所说,《补白》是一篇富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含量的作品,从文章的思想主题入手,可谈的当然很多,但是在散文叙事的技术层面,《补白》这篇作品有诸多的可圈可点之处。所以本文试着从散文叙事的技术层面.谈一谈陈丹玲的这篇《补白》。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不同的文学形式对语言文字有着不同的要求。往往谈到叙事,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小说里的叙事,在小说的领域内。叙事学已经是一门独立、专门的学问,顺叙、倒叙、插叙,复调、多声部,叙事人称……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的理论,但是,在散文的领域内,也可以谈叙事。甚至叙事的技艺吗?
一、叙事的焦点
散文的叙事讲不讲求技法?作为不同的文体。散文和小说在叙事的技法上有哪些相同的要求,又有哪些不同的特点?这些问题,答案都是明显的,展开和深入下去,却也是非常值得探讨且是很有趣的。
今天,以“虚构”和“非虚构”作为小说、散文或者其他文体的划分依据,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争议,散文不能虚构的铁律也已经越来越受质疑。如果我们能摒弃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不把“是否虚构”作为一条黑白分明的划分界线.而是把“虚构”与“非虚构”看成一种定量而非定性的说法.即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而是“虚构的成分多一点”还是“写实的成分多一点”.是“虚构是主体”还是“写实是主体”,那么许多看似问题的伪问题.也许就能迎刃而解。本来,小说里的素材也许根本就是原原本本的生活,而散文里的故事也许也会有记忆的偏差.你要怎么清晰地界定什么是“虚构”.什么是“非虚构”呢?厘清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可以说.散文的非虚构成分要远远大于虚构的成分,应该是可以得到公认的。也就是说,散文在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写实的”“非虚构的”,基于这一点,散文的叙事就有了与小说叙事本质不同的艺术追求与特点,即散文叙事对于叙事“写实性”的要求。
也许可以打一个未必准确的比方:小说的叙事像是绘画.服务于作者内心的写意而非客观的写实,作者可以根据主观的需要,加工、处理、虚化;而散文的叙事则像素描、摄影或是摄像,作者可以裁剪、剪接、調度,但是无论如何。它的“焦点”对准的对象,必须是真实的。
需要指出的是,一篇散文叙事的焦点与一篇散文的题材或者主题并不完全相同.一篇散文写什么人、什么事,是题材和主题。而面对一个题材、一个人、一件事,作者注意到的部分,选择向读者叙述的部分,才是叙事的焦点。可以说,一篇散文的主题.是“写什么”,而一篇散文叙事的焦点。是“具体写了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作者在散文叙事的过程中,把叙事人的眼睛投向了何处,摄影机的焦点对准了哪里。
那么,《补白》叙事的焦点。具体对准了哪里呢?
二、叙事焦点的选取
如前所述,同样一个题材,同样一个人、一件事,不同的写作者看到什么、选取什么、选择向读者传递什么,就是不同写作者叙事焦点的差异。好比不同的摄影家面对同样一幅景象.拍出的照片仍然各不相同——这种散文叙事上不同焦点的选取.可以称之为“对焦”。
一个写作者在叙事过程中选取什么样的叙事焦点,首先取决于他能看到什么,作者自己看到了.才能让读者看到,所以跟写作者的眼界、高度、知识积累和素养息息相关;其次取决于作者叙事的功力,自己看清楚了,是否有能力让读者也看清.让读者清晰地看到自己所看到的。再进一步。写作者预备采取什么样的叙事距离,近一点还是远一点.虚一点还是实一点、长焦还是短焦、变焦还是定焦。有这样的想法,技术上能否做到随心所欲,游刃有余.这就是散文叙事对焦的能力。
《补白》的对焦,无疑是成功的。文章一共分为八节,表面上分别写了晒纸、舀纸和舂料的工序.白皮纸的来历,集市上的皮纸市场,造纸作坊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白皮纸的文化气质等八个部分.但我们说过,这不是叙事的焦点,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始终把叙事的焦点对准了这些表面背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第一节表面写晒纸.实际上是牵出了晒纸的人物——红光嫂;第二节表面写舀纸.实际上写的是红光叔开始造纸以前的童年;第三节表面写舂料,实际上写到了合水镇上的“女子们”:而第四节白皮纸的来历。实际上写的是红光叔开始造纸以后的青年阶段和镇上的小伙们……通过白皮纸这个核心的物件,作者成功地在叙事中勾连起了合水镇上的“人”,写出了他们的内心、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情,表面写事、写物。实际上写的是事与物背后的人。这是高级的散文创作正确的对焦方式.也是最能体现创作者功力的地方。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把叙事的焦点对准了事物背后的人,还采取了多点对焦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出了造纸人对白皮纸、对造纸作坊情感的矛盾性、复杂性,这就使得文中的人和事脱离了单一的、扁平的个体形象,变得立体、丰富而具有了普世的代表性,不仅在思想高度上得到了升华.整篇文章的质地也因此变得厚重起来。
譬如第二节写舀纸。作者把叙事的焦点对准了他红光叔,通过讲述红光叔童年偷学舀纸.为我们立体地塑造出了一个造纸人的形象。“一切仿佛从游戏开始”,作者的叙事从一群男孩子抽陀螺的场景开始,鞭子是构树皮做的.童年时只爱打陀螺不爱造纸的红光叔没有想到。家庭的变故父亲的去世,会让他童年时热爱的构树皮成为他一生辛苦劳作的原料,从此伴随他一生。构树皮本来是没有感情的事物,做成皮鞭时,它是红光叔童年时的挚爱。用来造纸时,它却变成了压在红光叔身上的全家人的生计,千斤重担,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构皮软鞭.红光叔曾那么熟练地用来抽打陀螺,而穷困、破败、丢人、饥寒绞缠成无形的长鞭,一鞭又一鞭抽在他的皮肉和心灵上,比任何时候都狠。”尽管如此.它又确确实实让红光叔养活了整整一家人.“在造纸人的眼中没有什么比构树这样的植物更动人的了也没有什么比构树更能赢得信任。”这样复杂的情感层次,通过叙事人的叙述向我们娓娓道来.让读者读来五味杂陈,尤其是那一句“构树皮生来不是专为造纸的,任红光生来也不是专为造纸的.可是命运的鞭子究竟抽在了哪一句咒语上.让他到底还是以造纸为生”,使得文段脱离了单薄的叙述,具有了一种厚重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又比如“舂料”一节.写女子们在河边“同一个动作循环重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方面.这样机械重复的劳作是枯燥单调的.人的目光都因此变得慵懒而幻化;另一方面。女子们对白皮纸的憧憬和想象又似乎战胜了舂料的单调:“女子想象数十张白皮纸做成一把红油纸伞。……在欢腾的唢呐中。在新娘跨过门槛的一瞬被新郎的双手接过去……一把红艳艳乐融融的油纸伞.一直吸引小镇女子们付出不尽的辛劳和期待。每天.这样的捶打都会持续很久,时光的意义被全部纳入其中。”单调乏味的现实与美好的想象交织。让我们既看到了造纸的劳作过程,又看到了劳作过程背后复杂的情绪和人心。然而作者的笔力还不止于此,接下来笔锋一转。又写到民间的传唱:“合水镇上有只木老虎.十个女人九个少颗手指拇”——木老虎就是舂料用的巨大水碓。在这个漫长而单调的劳作过程中.女子们常常会因为疲倦或分心,被碓锤砸伤手指.前一秒还沉浸在对红油纸伞美好的想象里.下一秒就被拉回到血淋淋的现实生活中。“因手上带了这一小点残疾,媒人说亲时,她们受尽了男方的挑剔”。这样复杂的多点对焦,构成了复杂的情感交织,使得“舂料”这一原本单调的劳作过程不再是一道简单的“工序”,而是把工序背后的人推到了前面,使“工序”与从事这道工序的人的情感紧紧连在了一起产生了多层次的审美。
这样精准、复杂的多点对焦.在第四节写合水镇人对“劳动”的矛盾情感和第五节写合水镇人对“集市”的矛盾心情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写造纸.但不只是写造纸。不只是写造纸的作坊和工具,而是写造纸的人.写造纸人的人生和人心。可以说,正是通过准确而复杂的多点对焦,《补白》得以从单纯的渲染地方特色、简单的叙述造纸工艺脱离出来,成为一篇具有高级审美的作品,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三、叙事焦点的转换
一篇万余字的散文.不可能通篇只有一个或几个叙事焦点,随着叙事的展开.可能要处理很多个叙事焦点,这就涉及到不同叙事焦点之间如何恰当转换的问题。焦点选取得再好,对焦再准确,如果焦点转换的逻辑和节奏处理不好,也会影响整篇文章的质量。
从整体上说,《补白》的叙事节奏在文章的前半段是控制得非常好的。各个小节之间的起承转合.叙事焦点的转换,连贯、流畅、自然,使得整个叙事节奏非常和谐,仿佛只感觉到叙事人的娓娓道来.几乎感觉不到叙事焦点的转换。
稍显不足的是文章的后半段,第五、第六和第八节,叙事焦点的转换在节奏上似乎有些乱.逻辑性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比如第五节写集市和皮纸市场,卢定毛这一焦点的出现就略显突兀和生硬.有强行插入之嫌,而卢定毛的故事好像还没讲完.焦点还没对准。作者的叙事焦点又很快转换到了“姓李的男人”身上。同样的问题在小节的最后再次出现,“地主徐吉祥”匆匆登场而又很快退场——其实文章当中像这样只出现一次的人物,还有不少。一方面,作者在叙事的过程中需要节制。尽可能地把高质量的叙事焦点合节奏、合逻辑地展现给读者,尽量不去浪费笔墨;另一方面,焦点转换得过快过频,过多可有可无的焦点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也容易让读者不明所以,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影响读者对文章主题的接受。因此,叙事焦点在转换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衔接、铺垫与过渡。
同样的,第六节写造纸作坊的历史。对方志和文献的直接引用越来越多,破坏了整个小节的叙事焦点;第八节写白皮纸的文化气质,先径直岔开一笔。满心陶醉地花费了大段文墨写“薛涛笺”和“黔江雪”,是否与之后作为叙事焦点的白皮纸关系过于疏离,也值得商榷。说到底,文章是思维的体现,而思维是有前后、因果和种种联系产生的逻辑的.这种逻辑,虽然可以跳躍、省略,但既然写成公开发表的文章.就绝不能只是作者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不能只是作者一个人自说自话、自言自语,而需要尊重和照顾到读者基本的接受与感受。
当然,对一篇总体已经相当出色的散文提这样吹毛求疵的要求,确实是太过苛刻了。前面已经反复说过.无论是在文章的思想主题还是语言文字上,《补白》都已经是一篇难得的、让人惊喜的佳作,陈丹玲曾两次来到鲁院学习.努力和成绩有目共睹。这几年散文创作更是日臻成熟。我衷心地祝福并期待她为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