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采风流润花笺
2018-04-25刘璁
刘璁
在书写载体终于从竹简缣帛过渡为纸张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纸因工艺水平的限制和产量的稀少,一直是官宦贵族阶层才能享用的物品,加入了审美趣味元素的色笺则更为难得。《南史·陈后主本纪》载,后主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后宫佳丽“襞采笺,制五言诗”,令江总、孔范等狎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可见当时色笺不过是用来供帝王之家娱情之物,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房用品。到了唐代,纸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女诗人薛涛曾将自己的诗作写在自制的染作深桃红色的小彩笺上,极受时人追捧,遂以“薛涛笺”之名传世。“薛涛笺”也被学界公认为笺纸的发端。
制笺工艺在经历了五代“砑光小本”、宋“谢公笺”以及明初雕版印刷诸阶段之后,在明代天启、崇祯时期进入全盛期,“饾版”“拱花”技术相继出现并施用成熟,摆脱了前代只能砑印简单花纹、线条的桎梏,开始能够复现传统绘画中水墨晕染和着色浓淡的艺术特征,于是由“朴拙”而入“鲜华”,变得繁复华丽起来,这个时期的笺纸虽形制窄小、尺幅不大,但其细腻精致的程度,却与传统国画不遑多让,所以也有了“画笺”的美誉,传统绘画所涉及的对象无不入笺,例如楼阁亭台、山川河海、花鸟草虫、飞禽走兽、仙灵搜奇等等。
笺纸的穷工极妍,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其实用属性,渐渐升格为文人欣赏和收藏的案头清玩。邓之诚著《骨董琐记》时,便将笺纸视为雅玩之属。民国以降,“生肖笺”“古钱笺”“古彝器笺”“指画笺”“古佛笺”“西域古迹笺”“唐画壁砖笺”等纷纷流行,后来还出现了“砚拓笺”“鼎拓笺”,甚至还有以明刻本《金瓶梅》绣像入画的马廉“不登大雅堂笺”等等。
正因为如此,笺纸作为中国文人诗文唱和与书札往来的重要载体,历来在文房用具中占有特殊地位,古人也并不吝惜对它的咏颂之辞。南朝徐陵在《玉台新咏》中便有“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的句子,北宋晏殊《蝶恋花》更有“欲寄彩笺兼尺素”的名句。明人颜继祖在《萝轩变古笺谱》小引中赞美笺纸说:“或藻绘以争功,偏支离而人俗。于焉刻意标新,颛精集雅。删诗而作绘事,点缀生情;触景而摹简端,雕镂极巧。尺幅尽月露风云之态,连篇备禽虫之名。大如楼阁关津,万千难穷其气象;细至盘盂佩剑,毫发倍见其精神。少许丹青,尽是匠心锦绣;若干曲折,却非依样葫芦。”可谓“固翰苑之奇观,实文房之至宝”。
笺纸堪称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作为一门渐行渐远的传统艺术,对笺纸的发掘、整理、推介就显得尤为重要。《花笺图说》即为这样一部有关笺纸渊源及艺术特色的一部著作。作者王双启自青年时代起就养成了搜集笺纸的习惯,琉璃厂的许多南纸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此外,他还亲身实践刻版印笺,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一日忽发奇想,何不自己写几个字,刻在木板上,印一印,制成信笺呢?于是用薄纸写了‘忆旧游斋制笺几个字,反着贴在一块木板上,为图简易刻成阴文,然后把水彩颜料调成淡色,毛笔一刷,把纸摆正,用手指按压几下,揭开来”。初试即告成功。在这部富含文化趣味和文人掌故的著作中,作者认为,花笺本身及其包含的使用价值体现出的正是一种文化现象。将花笺拿来写信、写诗,可以让人们在阅读信件品评诗文的同时,更多了一层欣赏、把玩书画小品的乐趣,从而增添文人交往的情致。
在《花笺图说》的综述部分,作者以最初出现的、仅具实用性的“八行笺”为缘起,阐释了信笺向笺纸演化过程中的变化和革新,直至论述到集装饰性和艺术性之大成的“花笺”,梳理了笺纸发展过程中文人雅士对美的不懈追求与笺纸本身的意象之美。作者将“花笺”分为两大类别,一为“色笺”,一为“画笺”。简单地说,制作过程中以染色为主的即为色笺,以印画为主的即为画笺。但两者又往往难分轩轾,互为补充,因此对这种区分方法也不宜过分拘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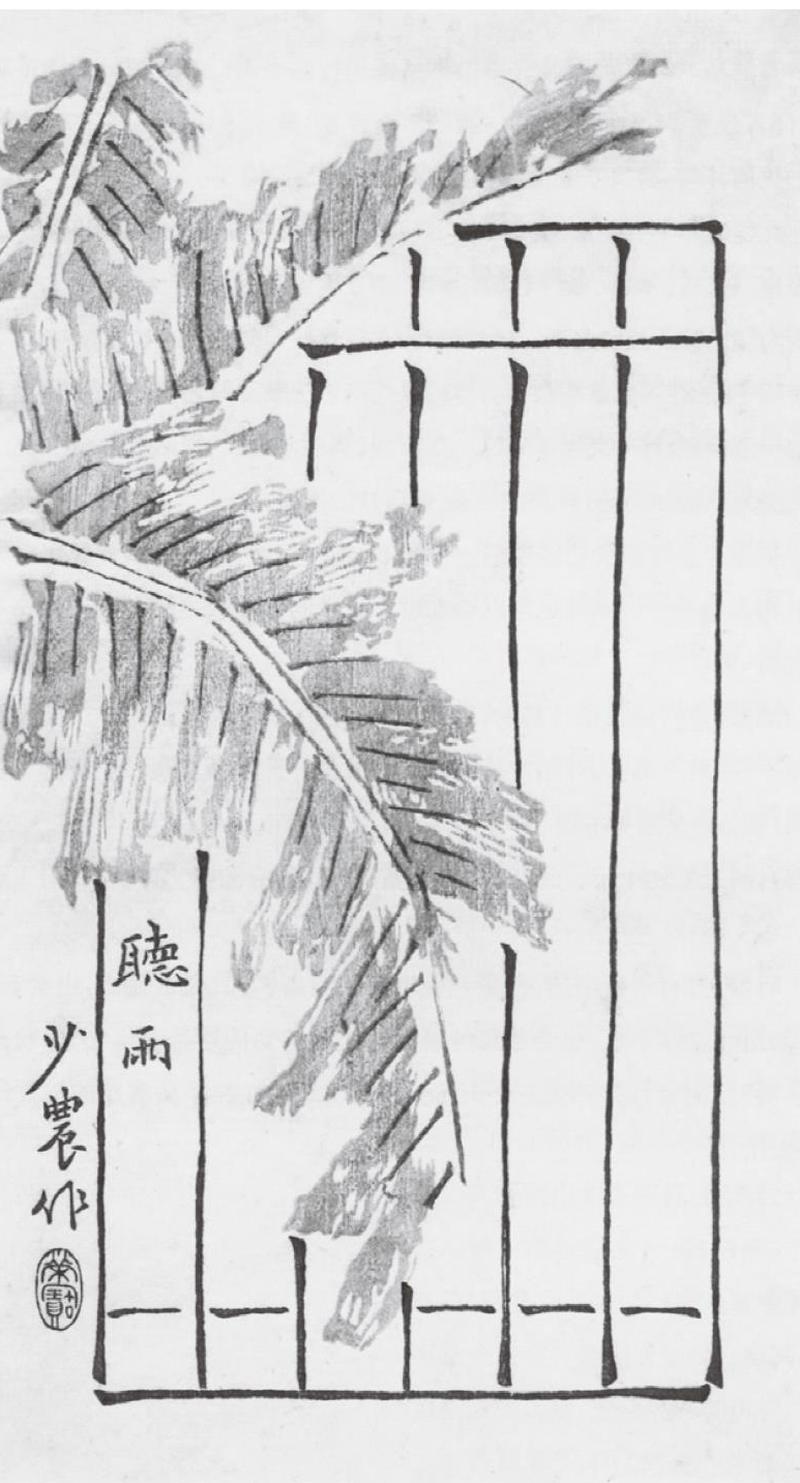
古人一向注重图像之学,南宋郑樵《通志·图谱略》云:“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所以“索像于图,索理于书”一直被视为治学的重要方法。因此,《花笺图说》的分说部分以对花笺个案的研究为重心,以图证说、以说系图,得收图文并茂之效。在书中,作者以数十年搜集、研究笺纸的经历,有选择性地列举了各类笺纸二十余种,除了制笺店铺批量印制的“一日相思十二时笺”“荣宝斋制林琴南宋人词意笺”“涵芬楼制吴昌硕花卉笺”“清秘阁制齐白石淡彩大笺”“荣宝斋制王振声蕉窗听雨笺”“清秘阁制丁佛言勾摹钟鼎文字笺”等之外,还有刘半农、黄宾虹等文人的自制自用笺,以及俞平伯据其曾祖俞樾(号曲园)所藏旧版重新印制的“曲园老人仿仓颉篇制笺”等等。此外,还有被作者命名为“色底画笺”的“淳菁阁制姚茫父陈半丁花卉笺”等。这些花笺,题材广泛,形式各异,给人以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之感。而且,这些花笺都和文人的介入有着直接的联系,从中可以领略往昔的社会风尚和人文情怀。
祥瑞图案一直是制笺铺肆所乐于印制的题材,因其寓意吉祥喜人,图案又具高古气息,用于书笺最是适合,深受人们的青睐。该书即介绍了作者早年搜集的一枚题为“甘露降盛露人”的花笺。画面上,一人手臂平伸,托盏承接树木所降之甘露,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企盼。《老子》云:“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史记·乐书》曰:“礼乐不失,则天降甘露,地出醴泉,是通于神明之德也。”甘露,古人谓之为太平征象,常常被封建君主视为祥瑞之兆。由此可见,花笺正是以简洁的画面,蕴含丰富的内涵。
作者在书中还描述了一套俞曲园的“会友笺”。这套花笺由俞曲园亲手绘制,共分四幅,分别题为“何时一尊酒”“如面谈”“跛予望之”“拜而送之”。作者根据四幅花笺的“连环”关系,将其命名为“思友”“邀友”“盼友”“送友”,對俞曲园在“会友笺”中的笔墨游戏以及文人风采进行了细致的解读:
四幅墨戏图,一套连环画,叙述了与友人会晤的一件完整的事情。奇怪的是,有思友、邀友、盼友、送友,唯独没有“会友”,这样的安排,很有意思。试想,如果把相会的场面画出来,二人对坐,难免与第二幅雷同,于是把第二幅题上“如面谈”三字,既显示了见面相谈的情景,也表达了以书信相邀的意思,如此含蓄而巧妙的手法也正是文人笺画的一种特点。(71页)
作者在书中还介绍了两幅文人自制的“砚拓笺”。纪晓岚对砚台情有独钟,书房为“九十九研斋”。一百多年后,一位胡姓文人偶然得到了纪晓岚的一方砚台,又从朋友那里借到了家藏的纪晓岚“九十九研斋”的印章,于是将砚拓和印拓组合在一起,同时请书法篆刻家寿石工书写跋语记其缘由,随后印制成为两幅古色古香的笺纸。从这两幅笺纸中,仿佛看到纪晓岚收藏砚台的喜悦,看到胡姓文人得砚的兴奋以及制笺的乐趣,不得不令人發思古之幽情。这也可以说是花笺的文化价值之所在。
在论述笺画的同时,作者还提出了判别笺纸雅俗的问题,且列举了许多实例进行分析。作者对于雅俗之别有着冷静的判断:“判别雅俗,至为重要,而其标准和尺度又是难以明确规定的。这里面既有制作的问题,也有鉴赏的问题。就制作而言,如前所述,有三道主要工序,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花笺的品位;就鉴赏而论,赏者各有所好,着眼亦不相同,做出判断必有差异。故而区分花笺的雅俗不能泛泛而言,必须针对具体品物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有说服力。”(19页)
《花笺图说》中所列笺纸全部是作者多年来于市廛中访求搜集到的笺样实物,其中不乏前人未曾述及过的笺纸种类和图像资料。这些零落于史海的文房小物重新出现在世人眼前,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和文化价值。当然,编辑出版这样一部书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对笺纸本身的绍介,更多的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这一艺术形式的记忆和兴趣。作者认为:“作为用软笔书写文字的载体的花笺,它的产生、发展与销沉,也正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的环节,对此,吾人应该理智地看待,毋须怅然叹息。花笺曾经有过辉煌,这就说明它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且给我们留下了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给我们留下了赞赏与追慕;这一切,就已经足够了。”(42页)
较为可惜的是,在出版过程中,由于一些编排上的疏漏,该书还是出现了部分舛误,如“穷款”错印为“寡款”、配图中笺画钤印“聋”字误释“龙”、“清秘阁”误排“荣宝斋”、笺画落款“远浦归舟”误作“远浦归帆”等。如有机会,当能在再版时加以更正。(《花笺图说》,王双启著,百花文艺出版社二0一五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