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台湾交往法案”有关条款的法理基础站不住脚
2018-04-23叶强
叶强
3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与台湾交往法案”(Taiwan Travel Act),使这部由联邦众议员提出、众参两院审议通过的法案在美“正式生效成法”。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国务院台办立即表态予以坚决反对,有关部门发言人同时指出:该案有关条款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
“与台湾交往法案”的通过路径
早在2016年9月15日,美国第114届国会的联邦众议员史蒂夫·沙博就联名其他11名位众议员提出“与台湾交往法案”(H.R.6047),指出“美国政策允许:第一,台湾高层级官员访美并获得相应礼遇,并可与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举行会晤;第二,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以及其他台湾在美设立的相关机构与美国进行官方交往”。9月27日,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等三人也几乎同时提出参院版本的“与台湾交往法案”(S.3397),内容与众院法案基本相同,认为“允许美台各层级官员互访是美国的政策”。不过,上述两项法案因联署人数过少而最终未能在第114届国会通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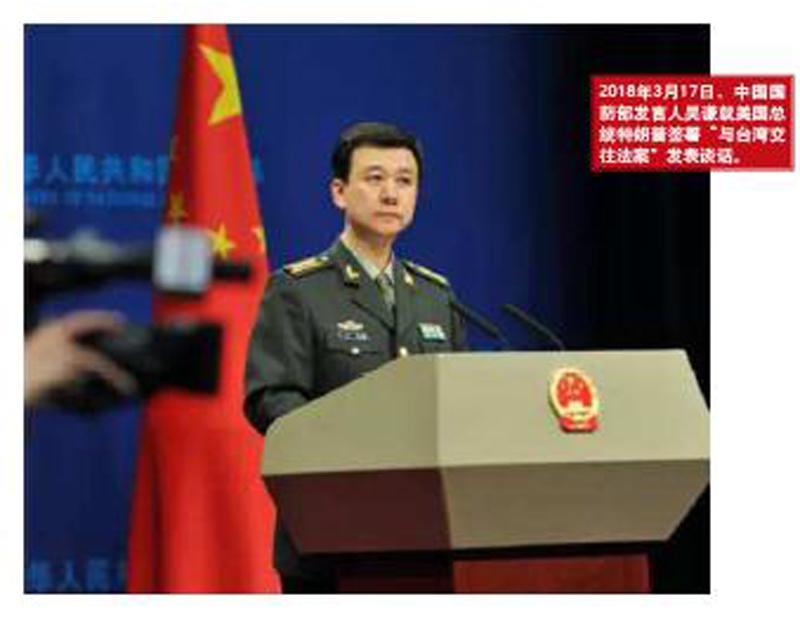
2017年1月13日,沙博在第115届国会上联名81位众议员再次提出“与台湾交往法案”(H.R.535)。该法案除了更加明确提出“允许所有层级美国政府官员访台”外,其余内容与2016年的版本基本相同。此后,该法案交由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及外交委员会审议,并于2018年1月9日在众院以口头表决(voice vote)的方式得到通过。2月7日、28日,该法案分别在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参议院获得通过。随后,国会于3月5日将法案送交白宫,待由总统签署生效。
对于该法案的内容,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睿哲认为,美国总统本来就有权指派高级别官员前往台湾访问,这项法案对行政部门并沒有约束力。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葛莱仪认为,法案的目的在于敦促美国政府“鼓励”美台官员互访,而并没有使用“應该”(shall)的字眼,因此对行政当局没有很强的拘束力,美国政府还是会依据个案进行考量,之后再决定该由何级别官员与台接触。一些台湾学者也持相同看法。
不过,这种从法案条款的措辞和潜在效果来推断“约束力”的办法,与法律本身的“效力”问题并无直接关联。在美国,国会议员可以采取四种不同形式提出新立法,即法案(Bills)、联合决议案(Joint Resolution)、共同决议案(Concurrent Resolution)和简单决议案(Simple Resolution)。在众参两院,大部分立法都是以“法案”的形式提出。而对美国宪法的修正案则必须以“联合决议案”形式提出;联合决议案成为法律的途径与法案相同。“共同决议案”和“简单决议案”的性质及审议程序,则与法案和联合决议案有所不同。这两种类型的决议案通常与制定法无关,而是用于表达两院对特定事件的看法及决定两院议事规则。因此,当这两种类型的决议案在两院通过后,并不会递交总统签署,也不具任何法律拘束力。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机构多年的统计,能够最终成为法律(Act)的法案不到提出法案总数的5%。而“与台湾交往法案”恰恰是以法案形式提出并最终通过成法的。
“与台湾交往法案”的法律效果
尽管“与台湾交往法案”在性质上应属于美国国内法,但它事实上的法律效果如何却存在很大疑问。
首先,“与台湾交往法案”的措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案用语。第3条(Section 3)是该法案的核心条款,标题为“国会的看法和政策声明”。这种措辞通常用于共同决议案而非法案,不具备可执行性。换句话说,“与台湾交往法案”是一个用正式法律程序包装的非正式政策陈述,并未规定行政部门的具体执行义务。
其次,“与台湾交往法案”中宣告的所谓“政策”严重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违反美国政府作出的国际承诺。长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刻意贬低三个联合公报的国际法效力。《八·一七公报》签署后第二天,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在国会参院作证时称,公报“不是条约,也不是协定,而是一个说明美国今后政策的声明。我们打算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执行有关政策”。
美国试图否定签署公报后所承担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根据国际法院(ICJ)对类似案件的判决(例如2013年“布基纳法索/尼日尔边界争端案”),中美联合公报毫无疑问构成国际协议。退一步讲,无论载明这种协议的文件是否具有法律拘束力,都不妨碍中美两国在台湾地位问题上达成的一致。《奥本海国际法》对此也有明确阐述:“宣言是正当地被视为国际协定的,因而宣言的法律效果是受条约法的支配的……由主要代表签署并包括一致同意的结论的官方声明,如果这些结论包含有明确的行为规则,则可以被认为对有关国家是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的。”因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国际法效力并没有因为“与台湾关系法”的制定而改变。美国所称“与台湾交往法案”中所宣示的“政策”是为了同“与台湾关系法”相一致,纯属无稽之谈。
第三,“与台湾交往法案”甚至已经突破和重构了“与台湾关系法”中规定的美国对台政策。美国强行把“与台湾交往法案”塞进其长期声称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凸显了其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性和两手策略。一方面,继续遮遮掩掩,把美台关系限定为“非官方关系”,称“保持和促进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广泛、密切和友好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另一方面,为美台官员交往大面积解禁,公然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破坏一个中国原则。而对上述政策的执行和美国国内法的适用,“与台湾关系法”明确规定:“根据美国法律有关保持外交关系或承认的任何明示的或默示的规定均不适用于台湾”。无论其能否被充分执行,“与台湾交往法案”都突破了上述制度框架。
美国行政部门如何执行有待观察
“与台湾交往法案”的措辞相对模糊,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法案并没有为行政部门设定具体义务和执行条款,也没有规定须受国会监督。因此,行政部门如何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白宫和国务院的决策。一个先例是,1976年“与台湾关系法”生效后,美国国务院每年都会据此发布“与台湾交往指导文件”,对美台官方交往做出规范。在美台关系问题上,美国政府不仅要考虑国会的意见,更要遵守其作出的国际承诺,包括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然而,自2016年以来,美国会众参两院提交了几十项涉台议案。2017年6月,总额超过14亿美元的、特朗普政府上任后首宗对台军售项目由美国国务院履行通知国会程序。12月,特朗普签署“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附加条款明确提出“强化美台防务关系”。而今,“与台湾交往法案”又企图解禁美台高层级官员“互访”,既对中国主权、国家统一及安全利益构成侵害,也在破坏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从立法背景看,“与台湾交往法案”是美国国会众参两院一手炮制的,白宫无法对其施加过多影响。按照立法程序,即使总统不签署,该法案也将于送交白宫10日(不含周日)后即3月16日自动生效。如果总统否决该法案,国会众参两院可以再次投票,三分之二多数票即可强行通过该法案,使之生效。然而,特朗普没有静候该法案自动生效,更没有否决该法案,而是选择在法案自动生效前主动签署了它,显然有着强烈的国内政治需要:一方面是为迎合美国国内不断上升的对华强硬舆论,另一方面是不愿因涉华议题与国会激烈对抗。不管怎样,特朗普的做法暴露出美国政府有意调整一个中国政策的动向,在中美关系史上写下了恶劣一笔。
(作者为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研究助理,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