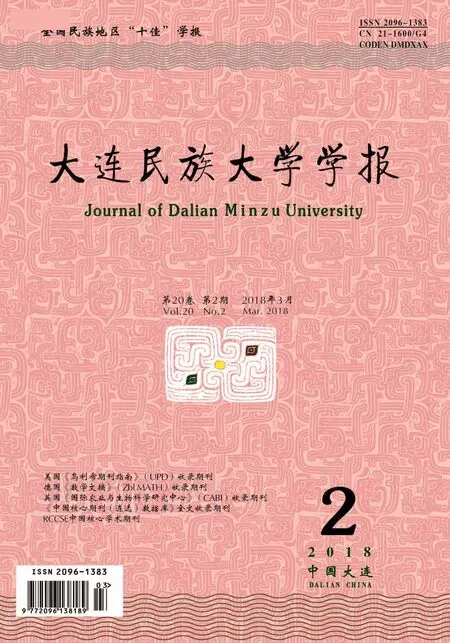史诗《玛纳斯》的习俗文化与民族认同
2018-04-16咸成海
咸成海
(新疆师范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民族认同是本民族的文化被民族全体成员体认、内化、弘扬、升华的过程。“在民族认同过程中,文化的影子无处不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明”[1]5。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史诗和史诗中颂扬的英雄人物,在民族叙事中,所有构成民族史的幻想情节会被认为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是能够让民族成员认同的文化,都可能被用于界定自身所属民族的特性。民族认同是文化范畴的问题,涉及风俗习惯、礼仪、家庭、生死、嫁娶等,而贯穿其中的是表明民族身份的共同历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认同感,因此,文化在民族认同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可以说,文化认同既是民族认同的基石也是其核心内容。
柯尔克孜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祖先曾生活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约从10世纪开始,逐渐向西向南迁徙到天山南北、帕米尔高原、费尔干纳等地区。现今主要聚居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也散居于南北疆的多个地区,另有小部分居住于黑龙江省富裕县,他们是在乾隆年间由新疆迁徙而去的。2015年新疆的柯尔克孜族有20.22万人。
与蒙古族英雄诗史《江格尔》、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并称为中国三大史诗的《玛纳斯》,是广泛流传于民间并世代传承的英雄史诗,“叙述了古代柯尔克孜族抗击侵略和争取自由的经历,也反映了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意识形态等”[2]。史诗里的英雄一出生即有非凡本领, 他英武豪壮,除暴安良,打击邪恶,拯救人民于水火,是柯尔克孜人顶礼膜拜的崇高形象,更是永远追求向往的精神境界。作为深受本民族世世代代喜爱的民间文学作品,史诗如大河奔腾不息,成为民族精神的支柱和文化的象征,在千百年的口耳相传过程中融入了具有古老文化的柯尔克孜族人对本民族的认同。
一、神树崇拜的文化习俗
在古代突厥萨满教信仰中, 苍天崇拜高于一切, 而与苍天有关的一切自然, 成为人们祭祀与崇拜的神圣对象。其中, 由于树木高耸入云天, 连接天界与人世,具有非凡的魔力,因此,人们认为它通晓着伟大天神的意志,是通天的阶梯, 崇拜树的习俗在突厥语民族生活中屡见不鲜就在情理之中了。“柯尔克孜等突厥语民族先民曾长期信仰萨满教”[3]157,树木有灵是萨满教习俗在史诗《玛纳斯》中的鲜明反映。
《英雄玛纳斯的诞生》故事中就有树木崇拜的例子:玛纳斯的父亲加克普巴依拥有数量可观的牲畜,却因妻子绮依尔迪未能生下一男半女而非常着急,“心事重重,愁眉不展”,无奈之下,“他向见多识广的柯尔克孜老人们询问,他向知识渊博的人们求援”。有几位知识渊博的老人告诉加克普巴依一个古老的求子习俗。于是,他依计将玛纳斯的母亲绮依尔迪送到了森林里生活,通过这个古老的在树林里求子的神奇方式,绮依尔迪成功怀孕,生下一个女儿。三年后,加克普“再一次遵从古训,把妻子送到森林之中,以此求得心中的儿男”来继承自己的家业和财产,绮依尔迪再次成功怀孕,艰难地生下英雄玛纳斯[4]。“这是树崇拜在史诗中典型的表现”[3]428。由此看来,树木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和巨大的生命力。因此,人们根据自己的想象,认为通过让不怀孕的妇女在树林里居住生活一段时间, 树木的繁殖能力就可以神奇地传给该妇女,她就能够获得生殖能力而怀孕生产。之所以有此种习俗是因为当时的柯尔克孜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知道性交与生育之间的关系,而把生育归结为一种神力的体现,以及这一神力对妇女作用的结果”[5]42。这种神木崇拜又和生殖崇拜联系起来,“生殖之事,造化生生不已的大德,原始的人很早就认识,是原始文明所崇拜的最大一个原则”[6]。
在古代突厥人心目中, 树木枝繁叶茂,果实丰盈,象征着旺盛的生育能力,故最能体现人们祈求生殖繁盛的愿望,因而视之为生命之树而加以崇拜。祖先卜古可汗被维吾尔人视为建国创业的英雄, 根据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的记载,卜古可汗即树木所生,卜古可汗品貌秀美,才智出众,通晓各族的语言文字。因此,他被推举为汗[7]。突厥族语神话《树大石二马三哥》亦是一个反映神树崇拜的故事:树最大,所以树生的孩子是老大,石头生的当老二,马生的,就当老三。“树大石二马三哥”兄弟就这样产生了[8]。可见,树在人们心目中处于至上至尊的地位,成为神树,逐渐成为一种对树木神力崇拜的原始信仰。其实,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亦存在树神崇拜,“在欧洲雅利安人的宗教史上,对树神的崇拜占有重要位置”[9]。
二、动物图腾崇拜及英雄崇拜的交织
图腾崇拜作为柯尔克孜人世界观中的最初信仰形式,从古代一直流传至今。《玛纳斯》产生于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崇拜时期,“在这个故事中,幻术多、巨人多,说不尽的习俗多”[4]6。那时, 对自然物的崇拜在游牧的柯尔克孜族人的原始信仰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玛纳斯的诞生也是在这一古老文化中展开的。原始文化中对自然物的崇拜观念是柯尔克孜族“原始初民用以弥补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历史局限性的重要手段”[5]23。
柯尔克孜族先民对动物十分依赖,曾长期以狩猎为主, 狩猎是游牧的柯尔克孜族民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自然界中的野兽,他们既畏惧又崇拜, 一方面害怕他们的袭击和伤害, 一方面又想拥有像它们那样的力量。在漫长的选择中, 其中一些最凶猛的野兽被人们作为自身力量的象征。于是出现了利用这些形象为氏族、为部落树碑立传的所谓图腾故事。恩格斯指出: “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他的宗教里”[10]。原始的动物图腾崇拜信仰蕴含于《玛纳斯》中,显然与柯尔克孜人在辽阔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密切相关。“萨满教是狩猎时代的宗教。食兽肉、着兽皮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狩猎民族对于动物的依赖关系。由于狩猎工具简陋,生产力低下,人类经常遭受野兽的袭击,猛兽成为先民致命的威胁。对于野兽这种既依赖又畏惧的心理,导致了先民动物崇拜观念的形成”[3]440。绮依尔迪怀玛纳斯后什么都不想吃, 于是对丈夫加克普巴依说她想吃“凤凰鸟的眼珠”“虎心”与“狮子的舌头”。人们认为只要英雄的母亲吃了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的精神品质也会传给玛纳斯。综上可见,动物图腾崇拜是柯尔克孜族狩猎生活方式的反映。族人亦常常将心目中崇敬的英雄玛纳斯比喻为凶猛的动物,这在史诗中随处可见。“曾长期在山林中以狩猎为生的柯尔克孜人的观念中,凶猛的野兽是力与勇的象征,是不可征服和战胜的象征。因此,他们往往把勇猛的动物形象集中到史诗英雄的身上,希冀他们崇拜的英雄如猛兽般令人生畏,不可战胜。”[3]440。
1.狼崇拜
狼是原始突厥部落所崇拜的主要图腾动物之一,在柯尔克孜族先民的心目中,狼具有神秘的神性和无限的神力,是护佑人们平安的神物,于是便逐渐产生了苍狼崇拜。《玛纳斯》中常将“青鬃狼”与玛纳斯相连,将他比喻为“青鬃狼”,既形容其威严与神力,也赋予玛纳斯非凡的英雄气概。如玛纳斯诞生前,史诗这样写道:
柯尔克孜人听到玛纳斯的消息,
都露出会心的笑容。
让我们暂且放下这一段,
说一说青鬃狼玛纳斯,
是如何在人间出生[4]40。
有时就直接用“青鬃狼”指代玛纳斯,如母亲怕儿子在家中虚度光阴,故支持儿子出去闯世界,但是又心存不舍,“绮依尔迪诉说完毕,她知道自己的儿子要离家而去,禁不住热泪涟涟痛哭流涕,这时的青鬃狼显然只是一个孩子,但他的心里装着说不完的事情”[4]103。玛纳斯的势力不断壮大,“青鬃狼英雄玛纳斯,随身带领四百八十名勇士”[4]218。他驰骋沙场时,光彩照人,“青鬃狼玛纳斯策马出击,太阳般的脸庞闪烁光芒”[4]241。他嫉恶如仇,不屈服于气焰嚣张的邪恶势力,具有非凡的气魄,“看到趾高气昂的巴努斯,青鬃狼玛纳斯挥鞭出战”[4]480。他反抗侵略,坚韧不拔,的确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正如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1]。
2.雄狮崇拜
《玛纳斯》将玛纳斯描绘成一位率军征战的无敌战神,凶猛、强壮、睿智,具有摄人心魄的英武。史诗常将其与“雄狮”放在一起,史诗开头就有这样的句子:“被人们永远怀念的英雄,像玛纳斯那样的雄狮,却始终没有出现”,“雄狮玛纳斯的故事,与人民休戚与共血肉相连”[4]5。当说到玛纳斯大展宏图时,史诗这样表达:
雄狮玛纳斯即将跨马出征,
为他制造神枪和宝剑,
已经是刻不容缓。
雄狮绝不会安然入眠,
他要将交劳依和其他卡勒玛克首领,
一个不留,统统驱赶[4]165。
史诗中描写当时的柯尔克孜人对玛纳斯的尊崇:
按照固有的传统,
遵照先祖玛玛依的礼仪,
铺开一条宽大的白毡,
请雄狮玛纳斯,
坐到洁白的毛毡中间。
七十名勇士抬起白毡,
把雄狮抬到上席位置,
让他稳稳地坐到宝座上面[4]274。
征战关系着部族的生死存亡,玛纳斯绝不逞匹夫之勇,而是在战争中讲究击败强敌的策略,因为他听从了阅历丰富的“巨人”巴卡依智慧老人的劝诫:
东奔西颠,四面征讨,
在战争中囤积财产,
只能算是无知的举动。
男人就应该沉稳凝重,
这样才会战无不胜[4]320-321。
睿智的他作战时从容不迫,沉着冷静,史诗在描写其威风凛凛的光辉形象时常用雄狮和其名相连,表现了民众对玛纳斯的尊崇与爱戴。史诗是如此描绘的:
雄狮玛纳斯昂首挺胸,
稳坐在阿克库拉马背上。
面对着千军万马的敌军,
来回走动器宇轩昂。
目睹雄狮的威猛,
卡勒玛克人惊恐万状。
无人胆敢出战交手,
谁敢再与他较量?[4]308
此外,史诗还说“他有白虎般的雄伟”“阿勒普喀拉神鸟的光辉”,说他是“柯尔克孜中诞生的雄鹰”[4]242。反映了人们的复杂情感,即对自然界凶猛动物的敬畏和对能征善战的本部落英雄的顶礼膜拜。可见,马背上的柯尔克孜人原始的动物图腾崇拜和对英雄的崇拜常常交织在一起,反映出柯尔克孜人古老的动物崇拜习俗,亦鲜明地体现出“柯尔克孜人民热爱玛纳斯,景仰玛纳斯,崇拜玛纳斯”[3]72的强烈思想感情。
三、崇尚数字“四十”
数字的神秘性和象征性产生于原始时代,很多民族都有数字崇拜与数字禁忌。柯尔克孜族历史文化中有崇尚数字“四十”的传统。
1.族源传说
关于柯尔克孜人的族源传说有两种,两种均显示柯尔克孜人有明显的崇尚数字“四十”的观念,说明该数字在人们的习俗中具有神秘性和崇高感意义。史诗《玛纳斯》记载,在很早以前,“有一个叫做叶尼塞的地方,那里土地肥沃,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人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他们的国王机智、勇敢、公正,名字叫卡勒玛玛依汗。居住在他们周围的是四十个部落,它们从四十个方向来归顺这位国王。国王的部众增多,于是国势强大起来。“四十个部落联盟就此出现”,国王称联盟为“柯尔克孜”,国王有五个妻子,都未生女育男,后来就娶了个多子多女的寡妇,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布多诺。国王死后,布多诺继位。布多诺死后,其子嗣布托依汗、波颜汗、恰颜汗、喀拉汗以及奥诺孜都汗相继嗣位,加克普“是奥诺孜都的第一个妻子所生”[4]11-25,玛纳斯就是加克普汗之子,他有“四十勇士”。此外,族源中还有“四十个姑娘”说。“据传,古代有个名叫舍赫·曼苏尔·哈拉智的人,他和妹妹阿纳勒一起犯了罪,被国王处死,尸首也被烧成灰,扔到河里。骨灰在水面上成了泡沫,流进王宫的花园。四十个宫中姑娘饮了这种水,都怀了孕。国王知道后大发雷霆,把这四十个姑娘赶到了无人居住的地方。这些姑娘在那里生儿育女,并且一代一代地繁衍起来,人们就称这些人为‘柯尔克克孜'。在柯尔克孜语里,‘柯尔克'意为四十,‘克孜'意为姑娘。”[12]11
2.婚丧嫁娶习俗
柯尔克孜族的婚姻生活中亦有关于数字“四十”的生动叙述:“姑娘的门前拴着四十匹马,有姑娘的人家身价大。”[13]549特别强调马是“四十匹”。可见,作为不可或缺的聘礼,马在柯尔克孜人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反映出当时人们深山放牧的生活环境中对数字“四十”的崇尚,向人们展现了西迁后柯尔克孜人过着草原放牧生活的画面。当加克普巴依为玛纳斯的结义兄弟英雄阿里曼拜特能够娶到阿茹凯而第二次到卡腊汗家求亲时,有相当生动的描写,更加证明了柯尔克孜人对数字“四十”的崇尚,史诗这样描写道:
四十个白天和夜晚!”[13]568-569
史诗《玛纳斯》展开的古代柯尔克孜社会生活的画卷中有关于祭典仪式的描绘:“死者死后三日、七日、四十日、一周年都要举行祭奠。”在第“四十天举行‘大乃孜尔',亲戚朋友都要来,富有人家还要清毛拉举行很大的追悼大会”[12]169。这种为悼念亡者选定的特殊数字并不是偶然的或随意取来使用的,而是因为这些数字的背后必然隐藏着古老的习俗文化和神秘的力量。
3.四十勇士
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玛纳斯策马挥戈,率领四十名小勇士和各部落柯尔克孜民众,与入侵的劲敌卡勒玛克人交锋。杀死卡勒玛克山冈般的猛汉肖茹克,立下赫赫战功。一个好汉三个帮,玛纳斯身边跟随有四十名亲如手足的勇士,这四十个能征善战的勇士是玛纳斯建功立业有力的支撑。
两头雄狮穿梭于敌阵之中[4]250-251。
史诗中关于“四十勇士”的内容主要描写的是柯尔克孜族人在玛纳斯率领下进行的波澜壮阔、气势雄伟的反抗卡勒玛克人的侵略战争。卡勒玛克人自恃强大,气焰嚣张,以武力强占柯尔克孜人的家园,掠夺畜群,奴役和蹂躏柯尔克孜族人民,在柯尔克孜族濒临灭亡之际,玛纳斯率领“四十勇士”及民众浴血奋战,英勇抗击卡勒玛克侵略者。“四十个勇士各有绝活”[4]291,个个身怀绝技,且英勇无比,战斗力可想而知。柯尔克孜人顽强抵抗,将入侵之敌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
由此可见,数字“四十”因在柯尔克孜族人的观念中具有神秘性和神圣性的特点而被视为崇尚,这个古老的习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已渗透到柯尔克孜族游牧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习俗来源于生活,在成为族人共同遵守的观念和行为的过程中积淀为民族的文化,进而成为民族认同的特殊符号。“在民族认同过程中,文化的影子无处不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明,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石。”[1]5柯尔克孜族自出现于文献记载至今已有二千余年,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的史诗《玛纳斯》,是柯尔克孜人智慧的结晶,也是寄予情感的精神家园,浓缩了柯尔克孜人文化的精华。“柯尔克孜族民间史诗《玛纳斯》展现了古代柯尔克孜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保留了不少专用名词,涉及牧业、狩猎、军工、习俗、礼仪、活动地域以及周边民族等等。”[14]对于柯尔克孜人而言,“史诗集中体现民族文化的传统,史诗是民族文化的旗帜。史诗在民族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它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3]9其影响力和重要地位无异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用特有的方式照亮和温暖了一代又一代柯尔克孜人的生活。
作为文化符号,史诗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柯尔克孜族包括生活习俗在内的历史文化。“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许多古老习俗,成为柯尔克孜民族精神生活与传统文化中较为稳固的部分。习俗就是传统,而传统的力量是相当巨大的。一个民族的习俗,能够潜入民族精神生活的深层,支配民族成员的观念与行为。”[3]63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生活习俗已深深地浸入到柯尔克孜族的血脉之中,逐渐成为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从本质上讲,与本族人民朝夕相伴密不可分的《玛纳斯》的升华和传承,就是柯尔克孜族文化意义和精神层面上的民族认同过程。综上所述,揭示民族认同过程中所蕴涵的精神文化因素,不但对于增进本民族认同,弘扬本民族精神而且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中华民族是高层,56个民族是基层。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基层的认同 ,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存不悖 ,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 , 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15]。
[1] 栗志刚.民族认同的精神文化内涵[J].世界民族,2010(2):5.
[2]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546.
[3] 郎樱.玛纳斯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4] 居素普·玛玛依.玛纳斯:第1部第1卷[M].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41-69.
[5] 戴佩丽.突厥语民族的原始信仰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6] 蔼理士.性心理学[M].潘光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6.
[7]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M].何高济,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63-64.
[8] 满都呼.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128.
[9] 詹·乔·弗雷泽.金枝:上册[M].徐育新,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166.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10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
[11] 孟子.孟子[M]. 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92.
[12] 《柯尔克孜族简史》编写组.柯尔克孜族简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13] 居素普·玛玛依.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下[M].刘发俊,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14] 贾衣肯.《玛纳斯》史诗中的“乌鲁姆”“克热木”考释[J].西域研究 2016(4):122 .
[15]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