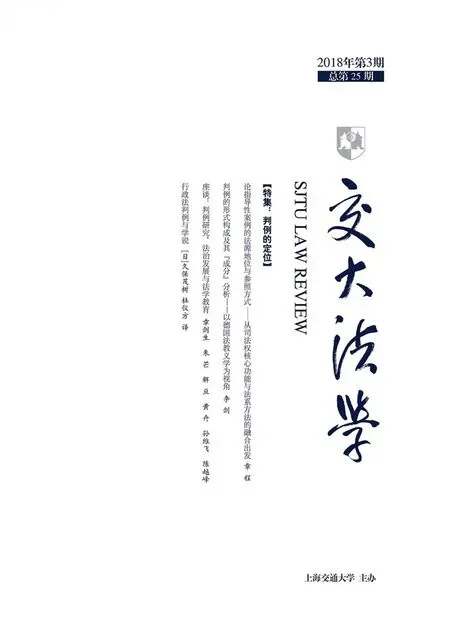民国“佛教入监”考
2018-04-15姜增
姜 增
引 言
监狱改良是近代司法改革之重要一环。因监狱实况常成一国文明程度之标尺,“觇其监狱之实况,可测其国度之文野”,*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晚清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2页。在当时世界各国将改良监狱“几视为国际上竞争之事业”的潮流中,*《第八次万国监狱会报告》,载《司法公报》(第1卷)1912年第1期。而“吾国法律裁判监狱三者均不能与世界各国平等”,监狱问题遂常为外人不愿放弃领事裁判权之口实。*许世英: 《改进司法革新狱制计划书》(1912),载湖北省司法行政史志编纂委员会: 《晚清民国司法行政史料辑要》,湖北省司法行政史志编委会1988年版,第85页。监狱改良重要内容之一,则是寻求良方感化囚犯,也即监狱教诲制度的制定与完善。这被视为彼时中国效法西方改良监狱所体现的“刑罚哲学的核心”所在。*冯客: 《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徐有威等译,潘兴明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监狱教诲,是促使监犯提升道德修养,劝导其悔悟迁善的制度。监狱当中的宗教教诲,是一种以宗教为内容对受刑者及其他在监犯进行德育的教育。*参见 我妻荣等编: 《新法律学辞典》,董璠舆等译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近代以来,规定对犯人可以进行宗教教诲的官方文件,最早见于《大清监狱律草案》:“在监人若请就其所信宗派之教职者,受教礼或行宗教仪式,斟酌情形得许之。”民国建立后,在制度设计上延续了此种做法。*《草案》后来成为民国暑期法政学堂专科教材和制定监狱法典的蓝本。北洋政府1913年12月颁布的《中华民国监狱规则》、国民政府1928年10月颁布的《监狱规则》和1946年颁布的《监狱条例》等,基本上都是《草案》的翻版。参见易花萍: 《〈监狱学〉点校者序》,载何勤华、李秀清、陈颐主编: 《“清末民国法律史料丛刊”辑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 77页。但具体以何种宗教作为教诲的主要内容,并未见具体的制度性规定。在各种入监教诲囚犯的宗教中,佛教是其中之一。*参见张东平: 《近代中国监狱的感化教育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142页。这与发端于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运动,提倡佛教主动介入人事息息相关,因入监宣讲佛法感化囚徒是符合其宗旨的关键内容之一。两相契合之下,“佛教入监”在制度渊源与实施基础上都有了极大的可能性与便利性。虽然目前关于民国监狱宗教教诲的文章不在少数,*相关的著作有: 见前注〔7〕,张东平书,第137~149页。(第三章第四节“监狱的宗教教诲”);见前注〔4〕,冯客书,第109~112页(“宗教和道德感化”)、第243~248页(“教育和改造”);明成满: 《民国佛教的监狱教诲研究》,载《宗教学研究》2016年第2期;韩霞: 《佛教与监狱服刑人员矫正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6年;见后注〔71〕,严景耀文;J. F. Kiely,“Making Good Citizens: The Reformation of Prisoners in China’s First Modern Prisons,1907-193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2001.等等。其中如明成满与韩霞的文章的研究范围与本文至为密切,都涉及了民国时期利用佛教教诲囚犯的内容,尤其是前者。两位作者的文章在提供史料线索与廓清制度发展脉络等方面对本文都有所助益。但二者基本限于对政策进行以内容(明成满)与时间(韩霞)为维度的静态梳理,而并未对利用佛教教诲囚犯政策的动态发展,以及背后的推动因素进行进一步追问。也即二者在论述“佛教入监”政策时,并未将该政策放置在一个能见到“人”的“时代背景”当中去。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中描摹一个能见到“人”的“佛教入监”政策,是笔者的立意之所在。但能够论述清楚民国时期佛教进入监狱教诲囚犯的阶段性特点与其背后的动力及所遇到的质疑与挑战,由此进一步揭示近代中西文明交流(或曰冲突)视域下,以近代中国监狱为竞夺场域的法律、宗教与政治文化的互动情状的学术作品,则尚付阙如。*日本学术界对近代日本汇聚了国家统治权、法律、宗教、国民道德等诸多重大问题的监狱宗教教诲制度,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并已有诸多研究作品问世。参见馬屋原成男「監獄における宗教的教誨制度」駒澤大学法学会『法学論集』,1978年12月;见后注〔87〕,片岡優子文;见后注〔88〕,長岡仰太朗文;禿川尊法: 「真宗における教誨の研究」『龍谷大学大学院実践真宗学研究科紀要』2013年第1期;前川亨「教誨師の光と影——その思想史的考察」『專修大學法學研究所所報』2016年第53期;见后注〔89〕,繁田真爾书,早大学位記番号: 新7566。因地缘紧密以及近代中国在诸多方面受到日本颇深影响的缘故,这些作品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本文将以新的视角,分别从进程、论争等方面对“佛教入监”做出解读。最终企望对“佛教入监”这一问题的考察,能为探求近代中国法律、宗教与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提供一个较佳的视域。
一、 从局部到全局
“佛教入监”在民国时期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全局的推演进程。此进程大致以居正执掌司法院院长,也即居正司法时期(1932—1948)为界点。在此之前, “佛教入监”政策基本局限于一隅一地。居正司法时期(1932—1948),“佛教入监”逐渐获得了国家层面上的支持,从而从局限于一隅一地转变为全国性的刑事政策被推广开来。
(一) 前居正司法时期
进入民国以后,利用佛教对监犯进行教诲活动一直为司法实践所认可。但民初(20世纪30年代之前),“佛教入监”只限于特定的地区,各省普及程度不一。1919年,在司法总长朱深主持之下所编写的监狱报告涉及了13家监狱,其中只有两家监狱明确表示在监狱教诲当中利用了佛教。*这13家监狱分别是: 京师第一监狱、京师第二监狱、京师第三监狱、直隶第一监狱、奉天第一监狱、吉林第一监狱、山东第一监狱、山西第一监狱、江苏第一监狱、安徽第一监狱、江西第一监狱、浙江第一监狱、湖北第一监狱。其中利用佛教教诲犯人者为京师第一监狱与浙江第一监狱。参见朱深编: 《京外改良各监狱报告要录》,司法部监狱司1919年版,目录、第14、194页。1924年之前,佛教教诲囚犯并无确定统一的参考资料,直到是年11月才由司法部确定以邵振玑《教诲浅说》“准各监采择作为教诲资料可也”。*《教诲浅说准各监采择作为资料令》(1924年11月15日),载《司法公报》1925年第201期。该书作者邵振玑系佛教徒,*其法名慧圆,参见释印光: 《〈教诲浅说〉序》,载《印光法师文钞全集》(第1册),团结出版社2013年版,第425页。书中亦有相当部分之佛教教义内容。但是从该令的措辞与语气来看,并不能看出其强制性所在。且在实际的推广效果上,司法部虽在1925年到1928年便在《司法公报》上连载其内容,但该书引起佛教界的广泛注意并为之宣传推广的时段,则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佛学半月刊》为例,最早见其引介《教诲浅说》为1935年第112期,此后其分别在1935年第113期,1936年第125期、第128期、第136期,1937年第148期、第166期、第167期、第168期、第169期,1940年第217期,1941年第234期,1942年第257期,1943年第276期、第278期、第279期、第285期,1944年第295期对该书进行了引介。《教诲浅说》被大力推广之时段,与居正司法时期(1932—1948)大致吻合,此时正是“佛教入监”政策向全国层面扩展的时段,具体论证见下文。更有四川绵阳地区的监狱,其在1936年始有“绵阳佛学社到监狱演说劝导”之举动,这在当时当地被认为是“有史以来之创果”。*《绵阳监狱讲演佛法》,载《四川佛教月刊》1936年第3期。
当然也有“佛教入监”普及度较高之省份,公认者为江浙二省。1923年12月,由金兆銮、黄庆澜所编的《感化录》一书,开宗明义地表达了浙江利用佛教教诲人犯的规模和效果,并表达了希冀其余各省能仿效此种做法的愿景:
监狱感化适用宗教已为万国所公认,释教明因果重忏悔感化,尤得实益,浙省试之已获大效……近岁浙省高检厅长陶叔惠先生,且已通饬所属厉行佛理教诲,囹圄为空,馨香以祝,故是编于浙省文牍选录较多,深愿各省司法当道德,仿而行之,造福圜扉,宁有限量。*金兆銮、黄庆澜编: 《感化录》,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凡例。
时人亦实地观察到佛教在浙江监狱教诲中的影响,1931年的浙江第二监狱虽然教诲事项较为简单,教诲书籍“别无他物”,但所仅有者即为“佛经数百册”。*梁绍文: 《浙江第二监狱概况》,载《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半月刊》1931年第7期。1933年的浙江第一监狱,为适应社会一般信仰起见,不仅将佛经讲述列为教诲资料,而且“教诲室中供有佛像”。*杜久: 《浙江第一监狱概况》,载《之江学报》1933年第2期。
江苏监狱教诲亦深受佛教影响。前述被司法部推荐为全国监狱教诲参考资料的《教诲浅说》,具有相当的佛教内容,其作者便是来自江苏第二监狱的教诲师邵振玑,一名佛教徒。该省高等检察长周诒柯积极提倡佛学,曾为了感化犯人以整顿监狱起见,上书司法部呈准在江苏省内施行佛法教诲,并组织感化会*该监狱感化会由佛教会所发起组织。参见《监狱佛化会今日正式成立》,载《申报》1925年4月30日,第4版。由各县监狱教诲师及各省监狱教诲师就所辖监狱内印发各项浅近佛经真言,派专员会同各教诲师对犯人演讲。*《苏法院查教诲成绩》,载《大云佛学社月刊》1926年第69期。
20世纪20年代,由浙江发端,曾一度想将利用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对监犯进行教诲的经验推广至全国。佛教居士林林长、浙江第一监狱教务所长王与楫鉴于监犯受佛化之后,监犯情形明显好于受佛化之前的效果,而上书浙江高等检察厅,恳请其转呈司法部“令行各省院转饬新旧各监署,就近延聘出家在家各高德入监演讲,令一切监狱实受无上妙法利益”。在浙江高等检察厅呈转司法部后,司法部旋即回复道:
教务所长王与楫,呈请转呈司法部通令各省高检厅,饬令新旧监狱延聘出家在家各高德入监讲演佛经一案,到厅比经据情呈司法部察核在案,兹奉第五八五号指令内开,呈悉查各省前送监狱教诲书籍现时正在审查之中,该教务所长所请饬各省监狱聘任讲演佛理一节,仰候并案办理。*《王与楫居士呈请监狱布教文》,载《海潮音》1922年第7期。
但之后司法部并未批准呈请通令全国通行佛教入监教诲之事。其后,王与楫退而求其次,他又以时任国务总理张绍曾友人的身份,函请司法部准予“携带法物亲至京师各监狱轮讲佛法”。*《司法部训令 第三○五号》,载《海潮音》1924年第5卷第5期。并最终获得了允准。1922年由杭州律师公会发起的所谓全国司法会议通过了诸多议案,其中有一项便为“监狱实行布教案”。*《司法会议昨日大会纪》,载《申报》1922年10月4日,第4版。但该会议虽名之以“全国”,但实际上只是地方性的、非官方的团体(律师公会与法校为主)所组成的会议,确切地说应该是一次局部范围的学术讨论会议,最后所做出的只是一种建议性的决议,并没有强制执行力。*典型表现就是会议通过的议案若想正式施行,还需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参见《张一鹏呈司法部文: 为司法会议各议案呈请施行事》,载《申报》1922年12月23日,第4版。从最后司法的实践效果来看,司法部并未采取相应的政策推动行为。*在这次会议之后,佛教团体或个人申请入监教诲囚犯之事上,并未看到有提及司法部认可此次 “监狱布教案”来论证入监的合法性的言辞。这与1934年司法行政部允准佛教团体入监宣讲的训令通过后,此后的佛教团体常常引申该训令来论证自己入监的合法性显有不同。因此,可以反推出当时的司法部对“监狱布教案”并未予以支持。而且此次会议通过的“监狱布教案”,其中的宗教并非指明是佛教,基督教往往利用该非正式议案作为引子来论述基督教入监教诲犯人“成绩也非常美满”,并将带来“结果的伟大”。*《全国司法会议通过监狱布教议案》,载《兴华》1922年第19卷40期。
20世纪30年代之前,“佛教入监”仍只限于局部,且往往受制于地方司法官的个人喜好。司法中枢并未明确反对“佛教入监”,但也没有积极制定法令政策使佛教通行全国各监狱。
(二) 居正司法时期
1934年1月9日,中国佛教会呈请司法院通令各级法院准予佛教团体至各监狱宣传佛教以资感化,*《本会呈司法院为请通令各级法院准予佛教团体至各监狱宣传佛教由》,载《中国佛教会月刊》1934年第55~57期。是月27日,司法行政部监狱司批准了此项呈请,向各级法院发函令其“转知所属各新旧监狱,准予佛教团体到监宣佛教,以资感化”。*上海市档案馆藏: 《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关于教育教诲(二)的文件》,档案号: Q181-1-876。1935年1月,监狱司又对湖北蒲圻县监狱人犯雷钧五等,“呈为深沐佛恩,愿切普度,祈通行各监狱,一律奉持佛法,并将念佛列为课程等”的诉求给予了允准,并致函各高等法院令其转知各监知照,意在施行。*参见上海市档案馆藏: 《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关于教育教诲的文件(1934—1935)》,档案号: Q181-1-883。对准予佛教团体到监狱宣讲佛教以资感化的政策,司法行政部亦有后续的跟踪与督促行为。1935年7月11日,在该政策宣布一年半之后,司法行政部专门发文至各高等法院询问“有无佛教团到监演讲其感化成绩若何”,并嘱转知各监狱查明详细回复。*上海市档案馆藏: 《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关于教育教诲的文件(1935)》,档案号: Q181-1-911。通过司法行政中枢机关的倡导与发布相应的函令,正式开启了佛教在全国层面入监教诲囚犯的进程。全国层面“佛教入监”的政策的推行在1935年9月份召开的全国司法会议上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强化,其重要表现便是安徽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王树荣的提案《关于充实新监教诲教育事项》得到首肯,*司法院编: 《全国司法会议汇编》,司法院1935年版,第32页。并于是年12月份,司法行政部向各家法院抄发该提案,令各监狱参照切实办理。该提案中明确建议“由监督官署函请中国佛教会高僧或居士担任新监集合教诲,并于原定预算内酌量津贴佛教会所派之人,以月支二十元为限”。*《司法部令地方法院实行监狱教诲教育》,载《申报》1935年12月13日,第3版。监狱教诲事项有两种路径,一为在监狱内设置固定的教诲师,此为主要;二为引入外来团体,此为补充。宗教团体向来对于入监教诲囚犯宣传教义具有较高的热情,且一般都是义务性质。但实际效果上,近代以来一些外来宗教如基督教若想入监狱教诲囚犯并非是简单的事,时常受到种种限制。*See “Work among Prisoners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1938),Jul 1, 1914;“Christian Endeavor Work in Chinese Prison”,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1938),Dec 1, 1916;J.S.Wasson, “Prison Work”,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1938),Oct 1, 1919;G.H.Seville, “Christian Endeavor Prison Work in WenChow”,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1938),Jan 1, 1919.具体论述的展开详见下文。能被“函请”进入监狱且有一定的津贴,可见此时佛教在监狱教诲方面中与官方的贴近程度。
担任监狱教诲一职的高僧或居士往往需由佛教团体呈名推荐,这样的推荐直到抗战后还一直可见,*参见上海市档案馆藏: 《上海监狱关于各教会来监传道情况(1946)》,档案号: Q177-1-95。足见这样的政策直到抗战后还在继续。1946年,更有以监狱教诲为主要任务的佛教团体成立,名为中国监狱弘法社,*1925年成立的上海监狱感化会是一个地区性组织,而监狱弘法社则是全国性的组织。其在简章中即表明“本社系参照民国二十四年司法会议第一四三号提案‘充实新旧监教诲教育案’办法设立”。*见前注〔33〕。此外,佛教团体或个人经常将“善书”(佛学书籍)赠予司法行政部监狱司,监狱司收下此类书籍并将其分配给地方监狱。*上海市档案馆藏: 《上海监狱教育事项(1947)》,档案号: Q177-1-26。
1934年由中国佛教会发起的“佛教入监”运动,以及此后的一系列举措,是“佛教入监”的重要时刻,标志着“佛教入监”获得了国家层面上的支持,从而从局限于一隅一地转变为全国性的刑事政策被推广开来。当然,由于民国时期政治格局的复杂,北洋政府时期不论,即使是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代表的中央在多大程度上能掌控“全国”,实有待定论。*如齐锡生认为1928年后军阀主义仍然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特征,虽然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军阀主义与民国初期的军阀主义有所区别。参见齐锡生: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页。但单从司法机关的认可度与各地监狱可以作为参照的规定方面,“佛教入监”政策的等级的确是有一个从局限于地域到辐射全国的进程。
从局部到全局,“佛教入监”之进程何以呈现如此特征?换言之,影响此种进程的可能动力会是什么?“人”的因素在制度背后起了怎样的作用?
二、 司法长官与“佛教入监”
“佛教入监”之刑事政策形成进程当中,呈现出的从局部到全局的特点,与不同时期司法长官个人的地位、信仰及其与佛教团体的私谊等有密切关系。中国近代法律人群体当中,有诸多带有宗教信仰者。*兹举几例: 谢铸陈(1883—1943),北洋政府时期,先后任司法官、律师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曾一度出任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被誉为“中华佛学会台柱”。李炳南(1890—1986),毕业于济南法政学堂,后任职山东莒县典狱长,亦是近代著名的佛教居士。参见于凌波: 《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551页。其他著名者如吴经熊(基督教),朱献文(佛教),居正(佛教)等。这些带有某种宗教信仰的法律人,为宗教因素影响法律提供了一种非正式的路径。也即他们自己的法律思想和实践往往受其所信奉的宗教的影响,且由于他们自身在法律界的影响力与地位,这种宗教影响亦会蔓延到国家法治建设进程中。利用佛教教诲囚犯即是其中一例。
(一) 陶思曾与浙江“佛教入监”
陶思曾,《湖南省志·人物志》《中华民国史辞典》《湖南名人志》都言他崇奉佛法。*参见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南省志·第三十卷·人物志》(上册),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728页;张宪文、方庆秋等主编: 《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0页;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南名人志》(第一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686页。陶思曾佛教信徒身份直接的证据则是在题为《时轮金刚法会之意义和解释》演说词按语当中,时人称之为“陶叔惠居士”。*参见陶思曾: 《时轮金刚法会之意义和解释》,载《佛学半月刊》1934年第78期。他于1916—1926年期间执掌浙江高等检察厅厅长一职,浙江能在民初走在“佛教入监”进程的前列,实与他有密切关系。陶思曾在位期间,大力推行利用佛教教诲囚犯之活动。他曾多次以训令的形式,对于“佛教入监”事宜作出安排。其中1923年7月12日编号为六五四的浙江高等检察厅训令,可谓是他关于利用佛教教诲囚犯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的内容表明了他对“佛教入监”的观感、具体的施行措施及他所期望达到的效果:
案照监狱感化以教诲为先,教诲方法以佛理为尚,诚以因果轮回之理,五戒六度之行,忏愆悔罪之规,离苦得乐之法,大觉慈悲。得未曾有在身羁囹圄备受众苦者,闻之尠不幡然信受,哀悔归诚。浙省新旧监狱自施行佛理以来,有假释出狱后,身不归家,径投寺为僧者;有强盗之犯,出其工作赏与金布施,或出狱后向其邻里说佛者;有在监日诵经若干卷,或念佛一万声者。具在牍文,可以覆按。无他,人穷则反本之思以生,身苦则向善之念易启,而佛法之有教无类,对机易人,尤足以度迷情而启凡愚也。惟官师既施教诲,监犯应有修持,非有记载,曷资征?考查本厅前核定第一监狱及上虞县监狱之在监人修持表登记格式尚属详明,合亟检发,令仰该知事转令管狱员遵照。自奉之日起即便查明该已决未决在监人等,凡已修持者督其精进,将修持者促其发心,未修持者起其信念。所有修持功课,如诵经或念佛等各各令其自认列册登记,逐日考查,毋任荒怠。其又勤修不懈或因故作辍或有其他善行或有顽梗不化者,均须据实逐事填注备考在内,每届月终汇造总表一份,迳呈本厅查核。该知事为有狱之官,亦宜认真督促,毋俾视同具文,总期善教丕革邪心,囚徒胥沭妙法,有厚望焉,仍将本文施行日期具报备查此令。
中华民国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检察长陶思曾*《浙江高等检察厅举行监狱佛法教诲之状况》, 载《佛化新青年》1923年第1卷第7号。
在具体的人事安排上,陶思曾则频繁委任僧人或者居士担任监狱教诲师一职,进行监狱教诲事宜。他特聘上海佛教居士林讲主王与楫为浙江第一监狱教诲师、教务所所长,还让王与楫承担杭州第一监狱及宁波第二监狱教诲事宜。*参见《浙江佛教徒监狱布教之进行》,载《海潮音》1926年第4期。委任明道法师(俗名戚思周)为教诲师承担嘉兴绍兴宜兴等处教诲事宜。*参见《上虞县监狱署来函》,载《心灯》1926年第11期。调上海佛教净业社协办武仲英至浙江第一监狱充任教诲师。*参见《杭州佛学会组织监狱感化会之呈文》,载《大云》1927年第79期。其所委任之教诲师郁延年、张圆成等都深研佛理。*见前注〔15〕,金兆銮、黄庆澜书,第33页。此外,谛闲法师任宁波第三监狱教诲师,*参见潮音: 《布教团监狱演说》,载《佛学旬刊》1922年第4期。范绅古农居士则担任嘉湖监狱教诲师,*参见《嘉湖监狱讲演佛学之情形》,载《海潮音》1922年第4期。则都直接由陶所委派。由司法长官主动发布训令,支持“佛教入监”,并对此作出实质性的规划,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实属少见。因陶的种种“善举”,时人特别是佛教界人士称他为“菩萨再世乎”。*见前注〔47〕。
因地方司法长官信奉佛教,而致使监狱教诲的内容偏重于佛教,也可见于当时的安徽。对此,有过四十年典狱生涯的尹屏东在其回忆录中说道:
我于民国十七年,应安徽省管狱员考试及格后,当时的皖省高等法院院长周心约氏,是一位佛教信徒,亲自率领我们在安徽第一监狱实习,实习的课程,着重在教化人犯。周氏亲至教诲堂,集合了数百名受刑人讲述佛经,谆嘱他们口念佛号,日诵千遍。那个时候,监狱行刑的重要法规为监狱规则,监狱规则规定,叫人犯为“在监人”,数百名在监人,都是穿着灰布、圆领,布带的囚衣,一律光头,也确像一群出家人在念经礼佛,秩序非常良好。安徽第一监狱的典狱长吴君(忘其名),也是一个佛教徒。吃长斋、灰色布袍、布鞋,布襪,道貌岸然,在监人都敬重他。*尹屏东: 《典狱生涯四十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3页。
时间来到了1932年,党国元老居正经历了短暂的牢狱之灾后,复归党国领导中枢,职掌司法院院长一职。正是在他任上,“佛教入监”的政策,完成了由局部拥护向全国推广的转变。
(二) 居正与全国“佛教入监”
居正,曾任职中华民国司法院院长十六年半(1932.1.11—1948.6.30),以及在任职司法院院长期间兼任最高法院院长(1932.1—1935.7)、司法行政部部长(1934.10—1935.1)、中华民国法学会理事长(1935.9—1948)、朝阳大学董事会董事长(1936—1948),他对民国后期的司法制度乃至法律建设的进程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居正及其思想,为我们思考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律的连续性与社会意义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视角。*参见江照信: 《中国法律“看不见中国”——居正司法时期(1932—1948)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法律人只是居正诸多身份当中的一种,除法律人的身份之外,居正还有一重要的角色: 佛教信徒。种种证据表明了居正与佛教的关联,如他自号梅川居士,他所编写的自传名为《梅川谱谒》……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除此,佛教界也对居正与佛教的关系认可有加,《近代中国佛教史》把居正列在与佛教有重要关系的人物当中进行介绍,*参见《居正先生与佛教》,载释东初: 《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中国佛教文化馆1974年版,第496~498页。佛教组织还专门举办关于居正的纪念会,探讨居正的佛学成就以及对佛教的贡献。*参见《中华佛教居士会举办居正与民国佛教讲座暨追思会》,载中华佛教准提网(http://www.zhfjzt.com/show-9-203080-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07-22)。居正佛教信徒这一身份在其任职司法院长期间,对“佛教入监”刑事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居正因自己曾身陷囹圄,对监狱里的种种陋习、对犯人的恶劣处境深有体会。*居正身陷囹圄期间念佛的举动对于其执掌司法时期的思想与政策的影响,学人已有所论及。如江照信认为:“这一点可以从居正从事司法后诸多论述中看出来,如居正(1947):‘法治前进观’一文: 居正认为修明法治,当务之急,是研究一种从根救起的办法,而其办法即是居正所主张的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事理无碍法界与事事无碍法界)之修明,最终达一个真法界,法治前进,处处都是坦途;又见居正:‘死刑存废论’,惓惓于废除死刑。按谢冠生《追怀居觉生先生》一文所记,1931年除夕两人初次相见,‘一见如故人,略事寒暄,即与余谈谈死刑存废问题……后月余,先生将之洛阳,复命余撰死刑存废论,置行箧中,谓将及时建议。卒以频年战乱,方且大刑用甲兵,无暇及此事。但有司谳,有大辟者,先生必每反复推敲,多方以求其生。遇有提议减刑大赦者,尤必倾全力以助成之。三十三年之减刑令,三十五年之大赦法案,皆发自先生之意为多’。”参见前注〔50〕,江照信书,第8页。陆多祥认为:“其在1930年前后近2年牢狱之灾中,抄经念佛,此后在司法院院长任上,一直坚持读经诵佛,并把法治建设的希望寄托于今世的修炼与来世的善报,甚至把法治社会的现实目标和实践画饼描绘成佛家四法界的玄境。”参见陆多祥: 《居正法律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2013年。他自己在监狱中主要的消遣或者说抚慰心灵之事,便是诵读与抄写佛经,并且常与监狱外的人通信讨论佛学之事。*居正在狱中的书简,次于居夫人的,就是给根尘居士(刘白)为多,两人常就佛法与世事展开讨论交流。他不仅自己在狱中诵念佛经以收其心,去除妄念,他还教居夫人及其家人“念佛以收其心”。参见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图书馆庋藏居正先生文献集录》(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5~337、429页。他自身的经历以及他对佛学的笃信,势必会影响其在监狱改造上的政策。改造旧监,兴设新监是其在任时的一项重要规划。他曾不仅三令五申监狱看守所必须符合卫生,还亲自到地方法院实地考察。*参见孙镜亚: 《居正行状》,载“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主编: 《革命先烈先进传》,“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版,第782页。居正关于监狱的具体看法和改革措施,可参见杨木高: 《居正监狱学思想初探》,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15年第4期。其中对人犯的教化工作又是监狱建制中的重要部分,而这部分工作在居正司法时期,因司法中枢领袖人物个人信仰等因,佛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位于上海的中国佛教会于1934年1月9日致函居正,呈请司法院通令各级法院准予佛教团体至各监狱宣传佛教。该会认为“人当顺境之时,教以佛法,大都淡漠。殆经挫,方始觉悟,若身系囹圄者,及时施以佛法之感化,俾资懺悔,收效更易,即他日出狱亦可为社会良好国民”,*见前注〔26〕。而在狱中诵读佛法,于逆境中对于佛学的信仰,居正曾深有体会。两相契合,自然是深合居意。但监狱事项本应由司法行政部监狱司管辖,居正旋即将此函转由秘书处交由司法行政部监狱司办理。*见前注〔26〕。监狱司于是年1月27日便向各级法院发函令其“转知所属各新旧监狱,准予佛教团体到监宣佛教,以资感化”。*见前注〔27〕。此时司法行政部虽仍隶属于行政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行政部的隶属在司法院与行政院之间有多次摇摆,具体为: 1928年10月到1931年12月隶属于司法院,1931年12月到1934年10月隶属于行政院,1934年10月到1942年12月隶属于司法院,1942年12月直到国民党退居台湾隶属于行政院。参见张仁善: 《司法行政权的无限扩大与司法权的相对缩小——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行政部》,载《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但作为司法院院长的居正,正值权势上升期,又在党内很具威望,其出面转呈此项呈请对于最后的批准,关系不可谓不大。9个月之后,司法行政部恢复到了司法院名下,作为直系领导,居正所认可的“佛教入监”政策的推广将会更加顺畅。
1935年1月,湖北蒲圻县监狱的善男信女投居正所好,致函居正,历数监狱长官的功绩,特别是认为以佛学感化犯人一节,收效甚好,因此建议司法院通令各监狱“一律奉持佛法,并将念佛,列为课程”。*见前注〔28〕。此函的落款为“全体在押男女一百二十人全叩”,似为在押人犯所做,但极有可能是监狱长官借人犯之口而作。*类似的如1947年7月15日,司法行政部收到一封来自赫章县司法处看守所男女囚犯发给司法行政部、歌颂审判官及所长政绩的快电。张仁善认为该快电由74名囚犯同时署名,为县司法处官员邀奖,是否属实,无从查证。但至少有两种可能,一是新任司法官员的确爱囚如子,所以联名为其请奖。另一种可能就是电文根本不是出自全体囚犯之手,而是官员自己所为,以讨好上司。因为电文落款没有具体哪一位囚犯的签名或盖章,在押犯人是否有发出电文自由也是疑问。即使出自囚犯之手,也很可能出自监所职员的指使。按照囚犯所陈,赫章监狱看守所几乎成了人间天堂,这种待遇,就是在都市某些“模范监狱”也不常见。参见张仁善: 《司法腐败与社会失控(1927—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他们之所以提此建议,表面上如函中所称冠冕堂皇之理由不可全部否定,但背后的缘由也不可忽视。笔者认为,其中之一是监狱长官借犯人之口以表功绩,求得晋升之机,此功绩可能有夸大之处,不完全属实;二是基层司法官迎合上峰之喜好,因为他们知道“我院长信仰佛法,曾获感应,佛法宏深真不可思议”,*见前注〔28〕。而在当时的佛教界看来,颁布准许佛教团体入教宣教的命令“皆由居院长一念造成之矣”。*《对于政府通令监狱宣传佛教之感想及希望》,载《佛教月刊》1940年第2期第103号。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古今同理。这一致函部分表明了基层司法人员对当时法律制度的观感与今后法律制度趋势走向的预估,即他们笃信一个信奉佛教的司法院院长的上任,必定会将其宗教信仰的印记带进司法。对于此函的处理,时由居正兼任部长的司法行政部的内设机构监狱司签呈奉谕如拟,并致函各高等法院令其转知各监知照,意在施行,还顺带强调了1934年通过的中国佛教会的呈请:
迳启者,案据湖北蒲圻监狱人犯雷钧五等,呈为深沐佛恩,愿切普度,口通行各监狱,一律奉持佛法,并将念佛,列为课程等情,到部,查前据中国佛教会呈请通令准予佛教团体,至各监狱宣传佛教,以资感化一案,即经由司通函各省高等止。业经由司签呈奉谕如拟等因,相应函请贵院转知各监知照。*见前注〔28〕。
“佛教入监”的政策在1935年9月由居正所主持的全国司法会议上得到了巩固与强化。这次会议与上文所提到的1922年全国司法会议有明显之不同,此次会议由官方司法机构——司法院——所发起组织,具体到个人,居正实则居功至伟,有学者评论道,“召集全国司法会议,是居正司法为司法进程改良做出的最大贡献”。*见前注〔50〕,江照信书,第117页。此次会议的参与者共有包括司法中枢各长官、各级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典狱长、律师公会代表、各法学院代表及聘请之专家等两百余人参加,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威性方面都与1922年全国司法会议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在此次由居正主导的会议上,通过了安徽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王树荣《关于充实新监教诲教育事项》的提案,以及此后一系列的落实措施,已在上文论及,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可知,“佛教入监”推行的范围与顺利与否,实深受信奉佛教的司法官的影响,受其助力良多。但整个过程并非毫无波折,其面临着来自多方的夹击。
三、 来自世俗与天堂的夹击
中国传统法律在“外儒内法”表征之下,呈现出了惩罚与教化的双重性格。但此种双重性格并没有完全体现在当时的监狱当中。当时的监狱当中,体现惩罚为多,而殊少教化内涵。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在论及中国古代监狱情状时,就曾认为古人设置监狱之宗旨,虽然“非以苦人、辱人,将以感化人也”,但实际情形却是“感化之地,变而为苦辱之场”,与古人之宗旨“不大相径庭哉”。*(清) 沈家本: 《监狱访问录序》,载沈家本: 《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37页。近代著名犯罪学家严景耀亦认为中国古代的监狱“皆以监狱事务委诸下吏贼卒之手,对于犯人,不是用威吓主义,就是用报复主义,专讲桎梏,决顾不到犯人生活,更想不到感化问题”。*严景耀: 《中国监狱问题》,载《社会学界》1929年第3卷。再加上中国法律的世俗化特征,刑罚既不以宗教为基础,也不是什么神意的表达。*参见 迈克尔·R.达顿: 《中国的规制与惩罚——从父权本位到人民本位》,郝方昉、崔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瞿同祖亦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制裁与宗教制裁或者仪式制裁是分开的。参见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85页。利用佛教对监犯进行教诲的宗教教诲制度,正是在缺乏传统根源以及借力西风之下,逐步施展其推演进程。在此进程中,其遭遇了颇多的阻力,一来自宗教外部世俗人士的质疑,一来自宗教内部基督文明的挑战。
(一) 世俗人士*这些世俗学者的异见往往不仅针对佛教,而且针对佛教在内的所有宗教。的质疑
1939年,蔡枢衡在总结自清末以来“推行三十年之监狱改革运动”之成效时,对监狱当中的宗教教诲,只以“少积极意义”寥寥几字一笔带过。*参见蔡枢衡: 《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155页。这简短且对宗教教诲颇不友好的评价,在当时并不只是其一人之观感,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类似的观点。兹在“佛教入监”方面,世俗人士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其颇有微词。
首先,佛教教诲效用的暂时性。持该观点的学者往往认为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教诲,对于犯人的教诲虽有效用,但却不能持久。严景耀在调查研究了北平监狱后认为对大众演说善恶因果之话,也即是运用宗教进行教诲,对少数人或许有“一时麻醉性作用”;*严景耀: 《北平监狱教诲与教育》,载《社会学界》1930年第4卷。而蔡兆祥以河北第一监狱为样本,调查后认为“佛教、耶教对犯人的诲训不过陈说祸福报应之理,仅足以警示犯人一时的意念,实非永久良策”。*蔡兆祥: 《河北第一监狱教育情形的调查及其建议》,载《社会问题》1930年第1期。
其次,佛教本身问题。与持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持此种观点者认为佛教因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其对教诲囚犯非但完全没有效果,反而可能会有恶果。针对1934年中国佛教会呈请司法当局要求派员赴各监宣传佛教以资感化狱囚一事,有人撰文认为,在当时,宗教团体已经被“商业化”,其内含的道德因素几乎消磨已尽,宗教“自救犹不暇,更遑论去感化他人”。*《宗教感化狱囚》,载《华年》1934年第29期。有文章则更进一步指出,从佛教本身的教义出发,认为佛教的教义太过消极,如“因果报应”“轮回”诸说,而“人的凡心太重所以不能超脱对于当下的劫难”,那么囚犯眼前的灾难便是“理有应得的”,在佛教思想感化下的囚犯,作者认为他们出狱后会“走到清净寂灭的大道上,如果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说,会创造出一批亡国的顺奴才”。*豸章: 《佛法感化囚徒》,载《礼拜六》1936年第366期。这样的措辞不可谓不激烈。近代著名监狱学家王元增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其认为若从佛教中挑选教诲师,首先要求得佛法上乘者已经很困难,即使求得,“恐犯人有趋于清净寂灭之弊,苟徒讲仁义道德,恐不足以动犯之听而感化主义不能全达”。*王元增编: 《北京监狱纪实》,北京监狱印刷出版1913年版,第8页。即使在1935年由居正主导的全国司法会议上,对佛教本身能否承担起教诲囚犯的任务,也并不是一片赞美的和谐之声,有人就表达了异议:“一般监狱当局多忽视教诲感化之意义,所设教务大半简索不堪,而任教诲师者又因经费不充而进行不力,且教诲宗旨多采取消极无为主义,讲授佛经倡言轮回,增加犯人迷信”,相应的,他提出了改良监狱教诲的建议,其中有一点便是“就犯人文化程度高低分组教诲教材,一面应力图避免增加迷信(如佛经或其他宗教迷信之说),一面应采用增加科学知识者(如公民史地算术等)”。*见前注〔30〕,司法院书,第296页。
再次,科学教育可容纳佛教教诲的作用。与上一观点相关联,既然论者往往认为佛教教诲囚犯毫无效果,且可能会有恶果,那么什么方式能使教诲囚犯达至良好效果且没有副作用呢?答案是科学教育。近代著名监狱学家李剑华便持此种观点。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认识的深入,人们的宗教信仰逐渐失去了根基,在此种情况之下,若硬要给监狱教诲“蒙上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造成的后果便是监犯出狱后“大之可以阻碍国家的生产建设,小之可以增加关于迷信的犯罪行为”。李剑华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不必于教育之外另设教诲”,而应“拿科学教育去教诲他们”。*李剑华: 《监狱学》,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6~89页。
最后,囚犯的性质。还是针对中国佛教会呈请司法当局要求派员赴各监宣传佛教以资感化狱囚一事的撰文,该文把狱犯分为三类: 先天有缺陷的天赋的犯人、惯犯、偶犯。其中偶犯又分两种,“一种是品性极为醇正的人,平日安分守法,只因一时受了刺激,在愤怒中作成犯罪的行为;还有一种是道德略弱的人,因为忽受外界的诱惑以致陷于法网”。偶犯在所有犯罪者当中占绝大多数,感化也一般只对偶犯才发生效力。但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把这些原本不是真正的犯人的“偶犯”改造成“社会良好国民”,只需有完善的监狱管理制度与适当的教育便可,而大可不必借助有种种流弊的宗教感化。*见前注〔73〕。
革命家涂国林1929年9月被关进上海漕河泾监狱,他耳闻目睹了佛教教诲的运行实态及效果:
监狱设有教诲师,是一个佛教徒,要犯人读佛经,宣传要行善不杀生。佛教徒每月有一碗素菜(黄花菜、木耳)……到时,看守就喊:“谁是教徒?来领菜!”这时犯人中就一片喊声:“我信佛,我信耶稣基督!”犯人把食物吃了,一抹嘴就骂:“去你妈的,老子不信你们!”*涂国林: 《狱中记实》,载麦华林主编: 《上海监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72页。在美国的监狱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有囚犯便利用监狱当中的宗教团体进行帮派活动(gang activity)、获取“惯常的”(ritualistic)酒、牛排以及对性的需求。See Jim Thomas,Barbara H. Zaitzow, “Conning or Conversion: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Prison Coping”, 86 Prison J. 242 (2006) .
可见,佛教教诲在实际运行中的确存在着问题,世俗学者对于佛教教诲人犯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
(二) 基督文明的挑战
如果说世俗人士对于“佛教入监”的质疑往往是出于功利评断,那么其受到基督教的挑战则事关信仰与文明之争。
1. 近世西方监狱中的宗教教诲
近代意义上的宗教教诲是源自西方,主要是欧洲监狱的产物。矫正机构的宗教服务,最早在1488年的英国开始,1716年在华尔多监狱(Waldeness Prision)的职员编制当中,即有一位传教士,1733年国会授权法院指派教士到各矫正机关。*See Ferderick C. Keuther, “Religion and the Chaplain”, in P. W. Tappen ed., Contemporary Correction (New York: McGraw Hill), p.255.转引自林茂荣、杨士隆: 《监狱学: 犯罪矫正原理与实务》,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90页。但实际运行过程中,英国在18世纪晚期以前,监狱当中很少有牧师的身影,牧师在监狱中的历史甚至比“牧师”语词的发展轨迹还要模糊不清。*See James A. Beckford and Sophie Gilliat, Religion in Prison: Equal Rites in a Multi-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p.26.此种情形的改变,当以被称为“世界改良监狱之泰斗”*见前注〔2〕.的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1726—1790)对监狱的改良为转折点。他对监狱体制进行了成功地改革,其中之一便是强调宗教在监狱中教诲人犯的作用。*See James A. Beckford and Sophie Gilliat,, supra note〔81〕, at 26.其开启了英国牧师入监的制度性源头。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宗教曾在美国监狱的改良中发挥过积极的影响,神职人员是将社会个案工作(social case work)技术引介到监狱的先锋,更是主张在教育囚犯、对违法者进行个别化对待(individualized treatment)时,需以感化主义为依归的先驱。*See James V. Bennett, “The Role of the Modern Prison Chaplain”, 1937 Proc. Ann. Cong. Am. Prison Ass’n 379 (1937).但是直到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在州监狱,宗教教诲的情况并不理想,以致时人评价道,“我们必须承认在对待犯人的肉体与思想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但是在提升犯人精神生活(spiritual life)方面,我们不能吹嘘已经做了很多”。*George O’Meara, “Coordination of Religion with All Departments of the Prison”, 1941 Proc. Ann. Cong. Am. Prison Ass’n 429 (1941). 宗教在美国监狱当中的发展状况,See also Jim Thomas,Barbara H. Zaitzow, supra note 〔79〕.近代以来向以欧美强国为学习榜样的日本,其监狱制度便是“再明显不过的学习成果”*John Lewis Gillin, “Japan’s Prison System”, 3(7) Soc. Forces 184 (1928) .之一,宗教教诲囚犯在近代日本监狱亦有体现,这其中基督徒原胤昭(1853—1942)*关于原胤昭的生平情况,可参见片岡優子「釧路集治監教誨師時代の原胤昭」『社会学部紀要』2006年第101号。与留岡幸助(1864—1934)*关于留岡幸助对于理想教诲师的论述,可参见長岡仰太朗「留岡幸助の理想的教誨師像とその背景」『青山學院大學教育會紀要「教育研究」』2010年第54号。被认为是近代日本监狱宗教教诲的先驱,但是随着基督教与佛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冲突,佛教占了上风,自明治25年(1892)后净土真宗几乎垄断了监狱教诲事业。*参见繁田真爾『「悪」と統治の日本近代——道徳·宗教·監獄教誨』,早稻田大學博士論文概要書,2017年,頁7。正如犯罪学家齐林(John Lewis Gillin,1871—1958)在20世纪20年代观察到的那样:“日本监狱近来只允许佛教徒固定地进入监狱教诲囚犯,而基督徒只有在监狱有需要且协商一致的时候方可进入监狱。”*See John Lewis Gillin, supra note〔86〕.
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利用宗教,主要是佛教对作奸犯科之人进行劝导的例子,*参见冯卓慧: 《唐〈御史台精舍碑〉碑铭(并序)评注》,载《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但从法律上进行规定,并形成一项具体的制度,则始自西风影响之下的清末。正如前述所说,具体以何种宗教作为近代中国监狱教诲的主要内容,并未见具体的制度性规定。因此,从理论与实践观之,除了佛教之外,基督教亦是近代中国监狱当中一支重要的教诲力量。
2. 基督教与佛教在中国监狱的交锋
在英美等国,基督教能入监教诲囚犯往往是信奉宪法信教自由条款的具体实践,*See “First Amendment — Free Exercise in Prisons — Fifth Circuit Holds That Prison’s Prohibition on All Objects over Twenty-Five Dollars Did Not Violate Prisoner’s First Amendment Rights or Substantially Burden His Religion under RLUIPA — McFaul v. Valenzuela”, 126 Harv. L. Rev. 1154 (2013).牧师在监狱中亦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与自主的行事方式,*See Henry C. Hill, “The Prison Chaplain”, 1936 Proc. Ann. Cong. Am. Prison Ass’n 198 (1936).其在近代英美等国的监狱改良中被视为是“中心人物”*见前注〔4〕,冯客书,第5页。;而在近代中国,移植自西方的新式监狱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发展出了结合自身语境而生的内涵,即近代中国监狱改良作为全球刑罚改良运动的一部分,既吸收了国际的思想和制度,又渗入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寻求一个更加传统的、由美德支配的有序和统一的社会群体的现代工具”,*见前注〔4〕,冯客书,第8页。以“造就良好公民”*J. F. Kiely,supra note 〔8〕.。佛教入监教诲囚犯亦以信教自由为标榜,从理论与字面上契合了当时的国际范例,*1934年国际刑法委员会向中国发送了《囚犯待遇最低标准规则》(Rules for the Minimum Standard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这份报告中“道德与智识上之改进”一节:“第二十七条 在情境许可下,须使各犯人得有机会,按期施行其所需要职宗教生活。犯人如欲延请其所信仰之宗教牧师入监接见,监狱官不得拒绝其请求。如监内有充足人数,信仰同一宗教者,监狱须延请一合格之教士,按期入监服务。”中国于次年(1935)提交给该会的报告的回应:“我国约法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故监犯信仰何种宗教,不加限制。各教士愿来监布教者,亦不拒绝。囚犯有愿与教士会面者均可允许。至为一部分信仰同一宗教之囚犯,专聘一教师,此种办法,河北第一监狱已经实行。”但实际上河北第一监狱的情形并不理想,其信教自由似乎只是适用于外国公民:“洎观教化设备,是俄犯教诲室一,为宗教式布置,每星期有天主牧师来此讲演教义,以事感化,室室颇有庄严洁净状态。本国人犯教诲室一,较为俄犯设备者小,而庄严亦不及。”参见《监狱待遇犯人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载《法令周刊》1935年第24期;监狱司: 《中国实施囚犯待遇最低标准规则报告》(本件系本部报告国际刑法及监狱委员会者),载《现代司法》1935年第1卷1期,刘陆民: 《参观河北第一监狱记》,载《法学丛刊》1934年第2卷第7—8期。但在实践中,佛教在监狱当中往往被当作道德教化的辅助,时人认为在监狱教诲中更重要者往往为“法律道德、三民主义及国家民族意识之灌输”。*见前注〔70〕,蔡枢衡书,第155页。基督教与佛教在中国监狱的交锋,不只是两种宗教文化,本质上是中西两种不同文明的交锋。
基督教作为一种异质文明,其能否顺利进入中国监狱教诲囚犯,与司法长官的允许与否、国内外政治格局等关系尤为密切。1914年,在中国某地的监狱,因为某位监狱雇员本身是个基督徒,基督教第一次被允许进入监狱向监犯传教。*See “Work among Prisoners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1938),Jul 1, 1914.1919年的湖北黄陂,在得到一位开明的非基督徒监狱长官的允许下,传教士得以顺利进入监狱。*See J.S.Wasson, “Prison Work”,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1938),Oct 1, 1919.当时湖南株洲的基督教也有类似的经历。*See “Christian Endeavor Work in Chinese Prison”,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1938),Dec 1, 1916.而在温州的基督教团体的经历则更为复杂,且在被允许入监后还要受到种种限制。该团体在经历数次被拒后,最终在一位新上任的开明长官的允许下,得以入监,但该长官规定入监的种种限制,诸如将教团的长官带到他面前、入监者需要有特定的证章(badge)等。*See G.H.Seville,“Christian Endeavor Prison Work in WenChow”,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1938),Jan 1, 1919.
除此之外,基督教在监狱教诲中还存在佛教这一强敌。基督教与佛教在谋求和扩大各自的生存空间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冲撞,*参见赖品超编: 《佛耶对话: 近代中国佛教与基督教的相遇》,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对监狱教诲权利的争夺便是二者冲撞的具体表现。虽然在整个民国时期,基督教入监教诲囚犯并没有像佛教那样,得到过司法中枢的明确认可,形成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政策。但其在一时一地,主动利用时事寻找契机,借助佛教之先例以及政治人物之言论,以获取入监机会,客观层面上挤压了佛教在监狱教诲当中的空间,对佛教教诲囚犯的地位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1914年,僧人觉先禀请在京师第一监狱进行布教,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以此为契机,于1917年秋同样禀请“向该监布教”,并经司法部核准。*见前注〔10〕,朱深书,第14页。更进一步,基督教徒认为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在京师第一监狱之教诲工作“成效昭著”,便呈请司法部将此种做法推广至全国:“拟各省已成立之新监均派支会教徒赴监布教,俾全国监犯受同一之教化。”由此可见,基督教热心监狱教诲事宜,并极力想确立起在监狱教诲中的一尊地位。司法部对这一请示并未完全允准,其以“各省情形不同习惯各别”为由,决定“先就通商大埠准该会派教徒布教”(苏州上海两监狱),这与基督教“全国监犯受同一之教化”之初衷相去甚远。*参见《基督教徒请教化全国监犯》,载《新民报》1918年第5卷第9期。但基督教企望挽救人心,获得如佛教般在监狱教诲的地位的愿旨并未因此消退。其行见机行事、见缝插针之能事,抓住一切可以利用之机会,积极倡导自己的主张。1934年在司法行政部通过中国佛教会拟准予佛教团体至各监狱宣传佛教的呈请后,基督教声请希望能够有相同待遇,他们称这为“辅翼之工作”:“我教会允宜援佛教会成例,呈请司法行政部通令各级法院,准予布道团体至各监狱宣传基督救恩。”*《宗教应注意感化狱囚》,载《兴化》1934年第31卷第42期。
此外,基督教还对某些政治领袖的话语进行发挥,引申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1937年,行政院蒋院长就当时新旧监狱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加强监狱教诲是其谈话内容之一,在该方面,他强调“尤应注重感化与劝导,更须以各种方法,灌输宗教,劝人为善之旨意,务使犯人之气质改善,精神有所慰藉”,*《蒋院长注意改良狱政》,载《申报》1937年4月2日,第1版。基督教抓住蒋介石的基督徒身份以及其此番发言,着力发挥。他们自信地认为“气质改善是各宗教所同,若求精神有所慰藉即非基督教莫属”,且他们认为作为基督徒的蒋介石曾亲身说过此类话:“在西安遇难尝向监视者索读圣经,益觉亲切有味,耶稣博爱精神之伟大更使我提高精神。”这表明蒋院长这种精神上所受基督教慰藉为人人所需要,尤其是苦难中的同胞。而为何蒋院长不明示提倡全国监狱同胞乃至全国人民信奉基督教呢?他们认为这与约法所规定的信教自由有关:“惟以国家行政领袖地位,未便形诸公牍,提倡任何宗教以与信教自由之宪章相抵触。”基于对国家政治领袖的推心置腹,对其话语的深度分析,基督教会提醒要“体会此意,扩大监狱布道组织以期全国监狱同胞人人得基督教福音的恩膏”。*琳: 《教会宜注重感化狱囚》,载《兴华》1937年第34卷第13期。
在来自世俗学者与基督教的夹击之下,“佛教入监”并未受到激烈的冲击。这从当时官方文件对佛教教诲囚犯有不错效果的表述可见端倪:
查本监自奉部令理施佛化教诲以来,除派由本监深通佛理之职员暨教诲师教师担任讲演,及提倡监房念佛外,并请当代高僧若太虚法师及锡兰纳啰达大师来监说法,人犯中发心皈依者,颇不乏人。本年一月复由大悲场惺两大法师,屈文六,唐住心,关綗之,王晓籁,胡厚甫,李经纬,赵云韶,赵朴初,诸大居士,组织十人讲演团,于每星期日来监轮流讲演,人犯更感兴奋矣。*上海市档案馆藏: 《江苏上海第二特区监狱三年来工作报告: 教诲(1937)》,档案号: Y5-1-20-122。
从上述报告可看出,佛教已经全方位地渗透入监狱教诲工作当中,且有不错的效果。不仅有固定的精通佛教的教诲师担任讲演,且有提倡监房念佛、延请高僧、组织佛化十人讲演团等各种佛教活动。而且1943年后,某些监狱当中,佛教甚至取代了基督教,成为监狱教诲的主要内容。*参见《华德路监狱内传道改用佛教》,载《申报》1943年6月8日,第1版。另1946年佛教入监教诲有了专门性的全国组织“监狱弘法社”,反倒是基督教入监教诲则是一度被叫停。*见前注〔33〕。
结语: 民族主义与“佛教入监”
民国时期,“佛教入监”呈现出的自局部推广到全局的推演特征,以及在世俗人士与基督文明的夹击之下,并未受到实质性打击的状况,其中当然与司法官个人的因素有关,但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日益向民族化与本土化发展,最终与儒、道一起,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一部分。清末民初,西风东渐下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受重大冲击,在当时读书人当中,无论少长,趋新被认为是一种潮流。而尊崇“西学”与趋新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参见罗志田: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119页。表现于清末民初的司法界,即在以废除领事裁判权为导向的近代司法改革进程伊始,便唯西方之制度为瞻,期望以西方文明为标准,完善国内之法律设施,尽速恢复司法主权之完整。作为司法当中的重要一环,监狱制度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亦着力效法西方,建造了诸如京师模范监狱等新式监狱。值此背景之下的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并没有入监教诲囚犯的良好契机,一般只能局限于一隅一地,且大都由于司法长官个人的信奉,方才能入监发挥其教诲之效。更有甚者,20世纪初叶设于北京的新式模范监狱,在希图仿效西方借宗教感化囚犯之制时,产生了一幕被许章润称之为“当时国人向西方学习慌不择食,甚至是鹿死不选音的紧迫而幼稚的漫画图景”: 即将儒、道、耶、回开山祖师的画像与19世纪英国狱制改良的领袖约翰·霍华德的画像悬于一堂,反而遗漏一般中国人所信、深入人心且已融为民间社会信仰的佛教。*时人在反对传统宗教时,常将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截然分开,进而肯定前者,否定后者。佛教往往与中国的落后连在一起。因此,当时反传统,主要针对的是非儒学的成分。具体观点参见徐跃: 《从排诋佛教到提倡佛教——以清末民初张謇为主的讨论》,载《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这反传统反得邪乎。”*参见许章润: 《说法 活法 立法: 关于法律之为一种人世生活方式及其意义》(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经历了清末民初司法改良唯西方制度马首是瞻的阶段,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刺激之下,政治、民族主义等因素逐渐渗入到司法领域,*关于近代以来,政治、民族主义等因素如何与司法进行协作,并渗透到司法领域,可参见江照信的相关文章: 江照信: 《由“司法革命”到“法官罢工”——民国司法进程问题(1912—1921)》,载《北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15卷第1辑;江照信: 《司法民族主义(1922—1931): 司法的政治参与、进程与意义》,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11卷第1期。等等。法律界涤荡起一股建立与中国本位文化相匹配的中国本位新法系的论潮。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部分,特别是经过人间佛教运动的洗礼,与世俗更相贴近,其在此种论潮中获得了优势地位。时势所趋,1934年之后居正司法时期全国范围内“佛教入监”的政策的形成,应该放置于此种大背景之下方可究其深层动力所在。
当然,佛教入监政策之所以能在居正司法时期成为全国性的政策,亦与相较于北洋政府时期,全国在形式上更加统一,政令有了一体遵行的可能性相关联。正是在这种客观因素的有力辅佐下,再加之个人有目的性的选择与推动,成为利用佛教教诲囚犯的全国性政策形成的重要契机。当然,在具有相同客观因素的前提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更加位高权重的蒋介石信奉基督教,*蒋介石的日记可以佐证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兹录二则如下,背景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遇到危难,想起了他的上帝,不由得向《圣经》求救: 12月19日: 鼎镬在前,刀锯之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承辱,谁复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无愧受洗礼矣。12月22日: 是日为冬至,清晨早祷告毕,翻阅圣经,恰至“耶□□(和华要)”一节。其文句为:“耶和华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也。”转引自: 山齐: 《蒋介石史实真相》,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更有甚者,在对待基督教与佛教的态度上,蒋私以为应以前者代替后者: 中国宗教应以耶教代佛教,方可与欧美各民族争平等,而民族精神之发扬与因有德性之恢复,亦能得事半功倍之效果。参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蒋介石日记(1917—1936)》(手稿本),1936年2月15日。但基督教并未因此如佛教那般,形成在全国范围内进入监狱教诲监犯的政策。这也表明了个人因素在时代潮流面前的无力感。
总之,时人多以佛教教诲人犯的实效来鼓吹其入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表象之下,实际蕴含着一种对佛教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合民族主义情绪的心理契合。信奉佛教的司法官,本就是民族主义的具体载体,其所为言行部分是主观能动性的表现,部分亦只是为时代风气所影响并且顺应和推动了当时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