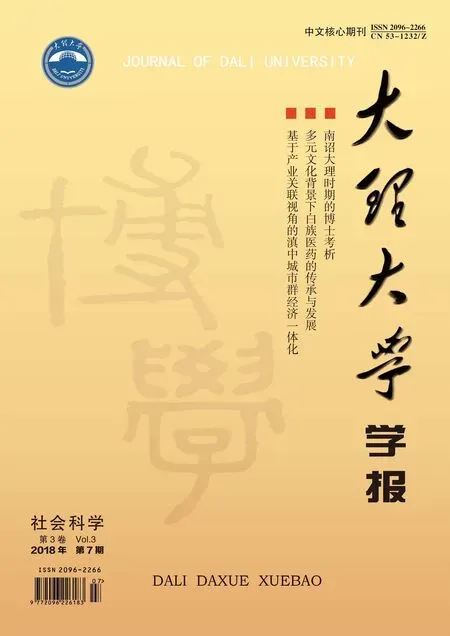仪式、表征、变迁与功能:一个汉族村落丧葬活动的人类学考察
2018-04-12徐俊六
徐俊六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昆明 650500)
人生命的终结就是丧葬的开始,丧葬是个人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人生礼仪,是生者为死者举行的最后的告别仪式。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丧葬,不仅仅是一场送别活动,更是村落民间习俗文化的重要呈现。为了更清晰全面地了解乡土社会中的丧葬文化,本文以一个传统的汉族村落的一场丧葬活动为考察对象,从丧葬仪式、丧葬表征、丧葬变迁、丧葬功能等方面进行探究,挖掘其仪式所蕴含的人类学内容与意义,为进一步研究乡土社会结构与村落文化提供新的视角与途径。
一、坡脚村的自然与历史图像
坡脚村坐落于中国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方路上丝路博南古道的北侧,历史悠久,具体年代现已无据可考。坡脚村位于今天云南省大理州永平县博南镇,距县城4千米,镇政府3千米,村东西两头分别流淌着银江大河与马街河,杭瑞高速与320国道从中间穿过,交通极为便利,因地处山脚而得名,是云南典型的坝区。坡脚村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落,以种植核桃、烤烟为主要的经济来源,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与个体经济的发展,村集体经济得到较大增长,村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各家均在翻修住宅或建盖新房,村落有了新的气象。坡脚村共215户,约900人,全部为汉族,汉族传统与民间习俗在这里保存相对完整,每年的节庆、婚丧嫁娶以及其他活动中的民间信仰遗风与宗祠祭祀礼俗依然活跃,一家有事全村帮忙是坡脚村的传统,村风村貌良好,村落整体和谐,呈现中国乡土社会的典型特征。
二、丧葬仪式
2016年9月26日,Y老人①笔者为Y老人的孙女婿。离世,其丧葬活动正式开始。Y老人享年74岁,3年前身体开始衰弱,医院已经下过几次病危通知。老人在其长子②Y老人的长子为笔者的岳父。的怀抱中离世,老人去世时,已有了曾孙,四世同堂,也算是人生的幸福与圆满,虽有病痛的折磨,走时也安详从容,没有太多的痛苦,这对老人也是一种解脱。从9月26日至9月29日,一共四天,是丧葬仪式的主体,3天后即10月2日,为上坟扫墓,脱孝仪式完毕后一次完整的丧葬活动才算真正结束。以下是Y老人丧葬仪式的全过程,每一个仪式并不严格遵循环环相扣的原则,有的是同时进行,有的是间隔进行,而有的是交叉进行。
(一)送终
家中亲人离世前,都有送终的礼俗。送终是丧葬仪式的开端,是家人、宗亲陪伴即将离世之人的场景,是亲人陪送其在人间的最后一程。“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之时,一个群体会出现某些变化,而伴随着这些变化的就是仪式。”〔1〕送终仪式是亲人去世前与家人的最后一次生前聚集,家人不愿意看到亲人的离世又不得不尽孝道,心理上处于煎熬的状态。送终一般没有什么既定程序,也没有约定俗成的具体内容,大致是即将离世之人与家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听取即将离世之人的遗言和家人对其的慰藉,这种场面虽有些严肃、心情有些凝重,但对于正常离世的老人来讲,可以从病痛中解脱其实也是一种欣慰,家人也会有另外一种祝福的心境。
Y老人离世前,其妻子、长子、次子、大女儿、小女儿(小儿子远在珠海未来得及赶回)、大儿媳、二儿媳、大女婿、小女婿、孙子女、外孙子女、孙女婿、外孙女婿、曾孙以及其他宗亲都聚集在Y老人的房间。因老人当时已不能言语,所以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大家都默默地注视着老人,再多看一眼,希望留住老人慈祥的面容以寄托哀思。
(二)迁移、报丧与筹办丧葬事宜
迁移与报丧是丧葬活动的第二个环节。迁移是指把即将离世之人从居住的房间移到在堂厅临时搭建的磅房①磅房是即将离世之人所处之地,以前用稻草搭建,现在主要用床单与竹条绑紧形似帐篷。,不能在旧房间去世,这是当地一种禁忌,主要考虑到此房间将会有其他用途,若在此房间去世会给家人带来霉运。Y老人本家已在堂厅中央搭建好磅房,在磅房中铺上草席,草席上放棉被,然后由老人的长子、次子把老人抬出房间放到棉被上。去世的人的身体不能接触到地面,这也是一种民间禁忌,不能让老人去世时的晦气留在家中。当老人咽气时,有专人负责向亲戚朋友通知老人离世的消息,这就是报丧。目前的农村,报丧也主要借助现代通信进行,除了通知亲友外,还有专人负责与念经祈福的法师联系,请法师等一干人到本家进行各种法事。当然,也有专人负责筹办丧葬事宜,如宴请宾客、购买各种丧葬物品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孝服,孝服的制式在坡脚村也特别讲究,离世老人儿子戴的是白色羊角状的帽子,儿媳与女儿戴的是白色方形状的帽子,孙子女、外孙子女戴的是白色旅游帽,曾孙子女戴的是红色旅游帽。
(三)入殓、献祭与念经
入殓是丧葬活动中圣洁、虔诚的仪式,具有非常重要的礼俗意义与人生意义。传统的入殓仪式分为小殓与大殓,小殓是指为死者洗浴与穿戴服饰,大殓是指死者入棺。在过去,两项内容都非常复杂,必须精心准备才能进行,现在随着社会的变迁,仪式程序与内容已经大大简化。Y老人去世后,由其长子、次子、女婿为他清洗身体、剃发等事宜,然后给老人穿上衣服,日常的内衣、衬衣、外套,最外层是一件特制的有花纹色样的黄袍,头戴旧时官样帽子,颜色与衣服相匹配,头后压一枚铜钱,口含一颗玉珠。
法师一干人共有6位,带头的是一位30多岁的青年男子,其他均是60岁以上的老者。到本家后,年轻法师与一伙人先到本家家堂上布置,另一伙在堂厅前摆上祭祀物品布置送葬场景。年轻法师到本家家堂前立刻换上道袍,装扮与道人一般模样。家堂上的布置内容是,先向灯盏倒油点灯、起香炉、燃香,然后摆上法师的法器道具,木子、木剑、道家的经书、各种符纸、柏树枝、洋姜花、菊花等等。念经的道具主要有锣鼓、片镲、云锣、大钹等,法师一干人从9月26日老人离世之日开始至9月29日每天从清晨6点到深夜1点都在做法事,敲打声响彻整个村落。
法师询问Y老人的生辰八字后,立刻在家堂上做起了法,说什么听不懂,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查看经书时而自言自语。过了一会,法师说可以入棺了,家族男性把老人抬入事先准备好的棺木,棺木的宽面朝向东方,也是本家大门,窄面朝向西方,老人入棺时头向东,脚朝西,符合自然生命的发展规律。法师面向老人念诵几句,用木剑挑起符纸左右来回几下放入火盆中烧掉,然后让人盖上棺盖,但不钉钉,只有等到出殡前才能钉钉。
(四)吊唁与还礼
当入殓仪式结束,老人的遗像、献祭物品摆上后,便可供人们凭吊。老人离世的消息传开后,不久家里来了很多人,有亲人、家族之人、宗族之人,也有很多老人的老友,还有其他远道而来的客人等等。在这些人中,很多已经多年未与本家联系,特别是老人的娘家人①Y老人为上门女婿。,过了四代,老人娘家一共有四位弟兄,只有老人与儿女这一辈还有联系,年轻的都不认识,但听到老人离世的消息后,其他四位弟兄的家人也来吊唁。坡脚村还保留吊唁还礼的习俗,若有人凭吊不论是什么人均须还礼,Y老人本家在老人灵柩左右两边专门设两座由家人用来还礼,当有人凭吊时,家人一起跪地还礼。
(五)告别先人
告别先人是在出殡前的头一天晚上与下葬后的当日进行,主要事项有在家堂前由法师引导至亲之人(一般是儿子、女儿、儿媳、孙子女)告别、下葬当日夜晚亲人必须夜宿老人所住的房间或是客厅。9月28日晚10点,告别老人的仪式开始,首先由法师一干人中的老者在房屋门口摆上一张桌子,桌子上用米粒画出一个相互对称的有9个顶点的图形,这个图形显得非常神秘,一是老者画图的方法,有点类似唐卡艺术的图形样式;二是图形的象征意义。米粒图形的每个顶点放上一根蜡烛,当本家亲人祭奠告别完老人后每人点燃一根蜡烛,一直到蜡烛燃尽为止,中间不能熄灭,燃烧情况象征生者与死者的关系,也预示着生者的命运如何等。亲人与老人之间的告别仪式也非常具有家族传统,同时也是村落民间信仰的体现。老人长子先到家堂前跪下,其他人根据长幼辈分依次轮流在家堂外的草垫上跪下。法师念经完毕后,把果盘放到长子头顶,盘中放入一个苹果,让长子端平盘子,法师再念一段经文,随后在法师助手的带领下长子到家堂外去解开在一棵小松树上用麻线拴着的铜钱,铜钱解开后随即掉入水盆中,泛起油印,然后去点燃桌上的蜡烛,同时法师的其他助手也在一旁不断地焚烧纸钱。当天晚上,一共有10位亲人参加告别先人的仪式。Y老人下葬当日,长子夜宿客厅长沙发、大女儿夜宿客厅左侧沙发,长媳夜宿客厅右侧沙发,这是和老人相息的最后一晚,因为当天非常劳累,大家深夜才休息,整幢房屋显得十分安静。
(六)挂礼与起坟
挂礼是指在老人出殡当天本家宴请亲朋好友时人们出的礼金,也叫随礼,以记账的方式登记在礼单上。随礼多少,是根据挂礼之人与本家的亲疏关系、家庭经济实力以及本家先前随礼情况而定。据事后统计,此次老人的丧葬活动共接收到礼金58 000元,其中单笔最高3 000元(老人长子好友所送),最低100元,本村村民大都出礼金100~200元。宴请中的帮厨以及记账、跑腿与打杂人员大都是本村村民,其他为本家的亲戚。
起坟是出殡当日清晨由本村村民与老人家属一起到事先找好的坟地上挖坑。因Y老人的墓地早年已建好,挖坑则在墓室中进行。起坟仪式由当地另一位法师主持,法师大约60岁左右,也是身穿道袍,一身漆黑,有点仙风道骨的风范。法师先用罗盘计算墓地的方位,然后用公鸡的血标注坑线的位置,经过法师念经、烧纸、祭祀各种神灵后村民们开始挖坑。
(七)出殡
经念经法师计算,Y老人出殡的时间是9月29日中午12时,这个时间是根据阴阳八卦学说中命理学的原理推算出来,计算方式也非常考究,首先需考虑老人的生辰、属相与当天黄历的时辰不犯冲,这是第一原则。出殡是丧葬活动中最为隆重的仪式,内容繁杂,程序众多。9月28日上午11时左右法师让送葬人群依次跪在老人的灵柩前,送葬队伍的跪拜顺序非常讲究,按照亲疏关系依次排列,第一排为长子、次子与小儿子(小儿子于出殡当日凌晨赶到),长子居中,第二排为儿媳、女儿,第三排为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第四排为其他非直系亲属,其余的送葬人群不再讲究顺序。出殡仪式包括,法师把老人生平简单介绍,特别介绍的是老人的丰功伟绩、好人好事等,然后把当天送葬人群中的家族姓氏念诵出来,让所有人知晓,念完后,法师做起法事,当天的法事与以往不同,不再是超度亡灵之意,更多的是送别,送丧之人一边聆听法师的讲道一边磕头,而大部分女性则是随着法器的音律不断发出哭声,这是哭丧仪式的内容。11时50分,由本村德高望重的老者与本家尚在人世的老人一起为Y老人钉钉,在钉钉之前,若没有来得及瞻仰老人仪容的亲属这时可以再看最后一眼,瞻仰完毕,12时整,老人灵柩被抬出堂屋,送殡队伍也跟着出发。送葬人群跟随老人长子出家门后在路旁跪送,跪送多次,直至老人灵柩抬上大路,送葬之人才可以原路返回,返回时,本家会给送葬之人每人一颗糖,并剥开吃掉,然后自己捡根木棍放在手中,到本家后放到火盆中。所有参加送葬的人员回到本家后,都要喝一碗姜汤,这种姜汤是出殡当日清晨用很多生姜与鱼香草一起混煮,喝汤主要是为了祛除人们身上的晦气霉运。
(八)下葬
送葬人群散去后,只有Y老人的直系亲属和抬棺村民到墓地举行下葬仪式。下葬是丧葬活动的最后一个仪式,也是丧葬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由当地的法师主持。在葬礼过程中,坚持“入土为安”的原则,既要保证离世老人在阴间的安宁,同时也要福佑后世子孙在阳间的昌荣。Y老人的坟墓已经起好,墓碑也已竖起,法师在祭祀完山神后,对灵柩进行祭祀,老人的亲属则跪在灵柩前祭拜,这时老人的妻子、女儿与儿媳开始哭丧,哭声响彻整个山坡。哭完后,法师引导大家左右绕行灵柩三圈,意为亲人间的最后离别。而其他人则把墓室的后侧与右侧打开,这个空隙刚好够灵柩进入墓室,这时法师又开始了念经仪式,用木剑在墓室深处点穴,一共七次,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进行。念经仪式完毕后,村民合力把棺木送入墓室,然后再用青砖砌墙,直至不留空隙,老人的直系亲属则在墓碑前跪拜,跪拜后所有下跪之人再次左右绕行墓地三圈,意为圆坟,同时有人在墓室旁不断烧纸钱,以示老人在阴间的用度。圆坟后,各位男性亲人砍断松枝放在墓碑前,再把各位宗亲送的花圈依次摆放在墓地两则,一阵鞭炮声后,下葬仪式结束,所有人原路返回。
(九)上坟与脱孝
10月2日,即Y老人离世的第7天,称为“头七”,民间认为第7天是去世之人“回家”探亲的日子,应该上山祭奠,意为上坟。这一天,老人的直系亲属,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一起到墓地祭拜。男性亲属把老人生前使用的所用物品搬上山,女性亲属则背着祭祀用的各种食物。当祭拜完毕,老人长子把老人生前物品搬到离墓碑10米的地方开始焚烧,其他人则把祭奠用的各种食物当场吃掉,不能剩余也不能带回家。老人的小女儿在墓地一侧烧纸钱,把老人生前使用的毛巾放在纸钱上,查看烧出的纹理形状,不同的形状代表不同的意义。当老人的物品焚尽、食物也一并分配完,大家在一阵鞭炮声中原路返回。回到家后,就可以不再戴孝,意为脱孝,至此,老人的丧葬事宜才算真正结束。
三、丧葬表征
丧葬是亲人对离世之人的送行活动,在广大的乡村,丧葬不论对于死者还是生者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乡村的丧葬活动尤为隆重,而丧葬活动中呈现的各种仪式蕴含丰富的民间村落文化,是“仪式在满足文化象征需要”〔2〕,体现村落儒释道及民间宗教多元交融的信仰体系,丧葬表征乡土社会的民间信仰。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其乡土性,乡土性是指“与土地的关系比较密切,人口流动率小,社会开放程度低”〔3〕1-9。这种特征导致中国乡土社会历史进程的整体发展缓慢,也基于这样的原因,各种文化基因一旦与当地乡村相结合,就不易断裂、分割与消失,所以在中国广大的乡村至今还保存相对完整的民间村落文化。在这些村落文化中,主要是以儒释道及传统信仰为主,形成一种多元融合的民间习俗文化。坡脚村是古代西南方路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位于博南古道一侧,从西汉时期就有商队经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文化、西南文化与南亚东南亚文化在这里汇集、交流与碰撞,经过千年历史的洗礼,这种多元交融的文化在坡脚村生根发芽,逐渐形成独特的乡土村落信仰体系。
丧葬活动是呈现乡土社会基本特征与展示村落民间风貌最集中的舞台,在丧葬活动的各种仪式中,集中体现民间社会的儒家文化、佛家文化、道家文化以及民间村落文化,各种文化在丧葬活动中相互交替呈现、互不冲突,共同演绎着丧葬活动的各个内容。
Y老人的丧葬仪式中,儒家文化的内容最多、程序最复杂,其中的家族伦理、孝悌、长幼尊卑、以男子为主等观念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老人的离世,是老人本家最大的事情,其他事宜只能排后。从老人去世那刻起,老人的直系亲人、家族以及宗族均以丧葬事宜为中心,并分别负责各自任务,为老人的丧葬仪式承担自己应有的义务,这是家族伦理的集中体现。老人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女、外孙子女等为看老人最后一眼,分别从四面八方匆匆赶回,这是晚辈对长辈的一种尊敬、一种缅怀、一种情感的联系,是孝悌观念在亲人心中生发后的行动,是约定俗成的家族传统。在丧葬活动中,处处体现长幼尊卑、以男子为主的儒家传统观念,在送终中,只有长子才能把老人搂抱在怀中,让老人安静祥和地离去;在各种祭典中,长子始终跪拜在第一排;在老人咽气后,也只有儿子才能迁移老人的尸身入棺,女性不能动,也不能碰尸身;孝服的制式更加体现了男子在家中的地位,儿子为白色羚羊状孝帽,女儿儿媳为白色方形状孝帽,羊是代表家族的权利和生命的繁衍;儿女辈是白色的孝帽,而孙子辈是白色的旅游帽,曾孙辈是红色的旅游帽,家族秩序清晰分明;灵柩钉钉时,只能是村中德高望重的老者或是本家在世的老人才有权利敲钉,其他人均不可;老人墓碑上的刻字均是按照长幼尊卑与前男后女的原则书写。丧葬仪式中处处体现儒家的传统观念,这是乡土社会民间习俗中最显著的特点。
Y老人的丧葬仪式中,因果、生死轮回、向善、阴间与阳间等佛家文化观念也有体现。“在汉民族的民间宇宙观中,死亡意味着一段新的神圣关系即死者作为‘神∕祖先’或‘鬼∕祖先’继续对子孙及社区加以影响的开始。”〔4〕老人生前曾找人算过命,说他前世是一位乐善好施之人,今生一世平安,不会有太多的磨难。老人生前能力较强,经常带领村民修路修坝,而且培养了五位优秀子女,在村中一直受人尊敬,至去世前,虽几次住院,但都没有给老人带来较多痛苦,离世前也是十分从容安详,家人认为这是老人前世积福所致。在老人去世后,家人也找人再次查看老人阴间归处、来世如何等等。坡脚村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村子中散落分布着一些墓地,有的年代久远,有的是最近新坟,Y老人去世后,他的墓地就选在坡脚村的后山,距本家只有500米左右。这说明像坡脚村这样的乡村还遗存佛家因果缘起、生死轮回的观念,这种观念对教人向善具有一定的村社意义,坡脚村是一个整体和谐的村落,与村民以邻为善的观念有紧密联系。
Y老人的丧葬仪式中,道家文化最具本土特色。丧葬仪式中的道家文化主要通过当地法师及其一干人的各种行为活动呈现。当法师与一干人到本家后,就开始着手准备祭祀本家先祖的仪式,在本家家堂上所进行的一切法事均属于道家文化范畴,包括请祖显灵、念诵道家经典文书、道士法术、洞经音乐、各种符咒等,主要是借用这些形式与道具超度亡灵,让其升天成道。除了家堂念经送葬仪式外,起坟与下葬仪式中道家的民间习俗也很多,如坟地的选择应当遵循风水宝地的原则,点穴时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进行等。在向先人告别的仪式中,在桌子上用米粒画出的九方方位,代表的是道家对自然宇宙的认识,九个顶点意示九个方位同时也象征着人的九种命运。丧葬活动中道家文化的显现是中国乡土社会中传统习俗的展示,是道家“顺任自然与长生久视”〔5〕观念的体现。
村落民间信仰具有地域性特征,不同地区的村落有不同的民间信仰习俗。涂尔干认为,“信仰是某个特定团体的共同信念,这个集体不仅宣称效忠于这些信仰,而且还奉行与这些信仰有关的各种仪式。这些仪式不仅为所有集体成员逐一接受,而且完全属于该集体本身,从而使这个集体成为一个统一体。每个集体成员都能感受到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他们可以借助这个信念团结起来”〔6〕。Y老人丧葬活动中呈现的村落民间信仰习俗是坡脚村及其周边村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土著文化与其他异文化不断融合发展的产物,具有复杂、多异、持久等特点。Y老人离世前,其身体必须迁移到堂屋,不能在居住的房间咽气。老人去世后,其尸身不能着地,不能被光线照射,也不能让任何家养动物靠近。在老人去世后的当天夜晚,家人不能熟睡,因为老人的魂魄会回到家中,需要聆听家中的动静,民间俗语称“收脚印”。下葬当晚,子女要在老人生前的房间或是家中堂屋过夜,这天夜晚老人的魂魄会再次回来,看望子女一眼,作最后的告别,民间俗语称“留守”或“值守”。在老人的丧葬仪式中,村落民间信仰习俗较多,主要表征生者与死者之间空间关系的转换,是一种精神领域的沟通交流,表达生者对死者的哀思与死者对生者的眷恋。
四、丧葬变迁
村落的乡土性特征决定其民间信仰的凝固性、传统习俗的持久性,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中村落文化的样态会在长时间内保持其不变性。在传统特色俱存的乡村,村落及其周边生态依然可以为乡土文化提供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因此,这些村落文化内容与习俗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在现代的乡土社会中依旧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文化与文化衍生出的各种习俗是与其周边环境相适应的,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文化与习俗也会相应变化,这就是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是文化的一种内在运动规律,每一种文化都处在运动变化中,不同程度地经历着由生长、发展、变化、衰朽和再生的过程。”〔7〕根据文化变迁的规律,村落的乡土文化也不会是亘古不变的形态,会随着乡村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在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激烈的改变,这种改变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广大村落的原生环境,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结构不断升级、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村民文化知识逐渐提高现代意识不断增强,乡村面貌有了根本性改变,这些变化影响并改变着村落的乡土文化及其习俗,村落的丧葬活动呈现出传统习俗与现代意识交织的格局。
在Y老人的丧葬活动中,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现象十分明显,丧葬变迁主要表现在由传统的重殓厚葬到简丧薄葬、死者为大与生者为先并存、为死者悲与为生者活并存等方面。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8“〕慎终追远”是儒家的传统孝悌伦理,指要谨慎地对待父母长辈的丧事,虔诚地祭祀先祖。在过去的坡脚村,为了凸显本家对已故亲人的孝顺,经常有大操大办、重殓厚葬、“送死多厚于养生”〔9〕的礼俗。过去重殓厚葬表现为:亡人穿的是金丝绸缎;口中一定要含有贵重的玉珠;棺木必是上好的杉木;宾客越多越好;依据亡人的年龄灵柩摆放在家的时间越久越好,短则一周长则一个月;出殡当日,还要请当地的戏班唱戏、演奏班吹奏等;陪葬的物品也很多,除了亡人生前贵重物品外,还有本家购买或请人专门制作的各种器物,以供亡者在阴间使用;本家不但要做头七,还有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与七七等等,天数较长,诸事繁多。现在的坡脚村,在丧葬活动中已经不再兴盛重殓厚葬礼俗,转为简丧薄葬。Y老人本家在当地属于富裕之家,若遵从以往旧礼,所有事项均可达到过去程度,但在实际操办过程中没有显现重殓厚葬的现象,与之对应的是:Y老人穿了三件日常衣服,均可在寿衣店买到;口中含有普通玉珠一颗;棺木是很多年前早已备下的普通木材;宴请的宾客基本是家族与宗教之人;老人的灵柩在本家只摆放了三天;出殡当日没有邀请当地戏班与吹奏班;也基本上没有什么陪葬品,只是把老人生前使用的物品和一只纸糊的马一并在坟前焚烧;本家只为老人做了头七,丧葬事宜就宣告结束。现在的丧葬与以往相比,隆重程度逐渐降低、规模范围逐渐缩小、用度开支逐渐减少。
村落丧葬习俗的变迁,是社会发展与乡土结构的改变所导致,其中国家体制力量的介入与村民现代思想意识的增强是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村落经济早已被纳入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内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目标,在这个宏伟目标的指引下,国家利用体制的力量介入村落管理,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引导村民保护与传承优秀文明的传统文化、摒弃与消除糟粕迷信的民间信仰,一同为新农村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在长期宣传、教育、帮扶与取缔的过程中,广大村民从现实出发,不断获取新知识与新理念,现代意识不断增强,村民思想发生了较大转变。“丧葬更多地表现出活着人的观念和处世原则。它一方面是子女回报养育的最后手段,另一方面帮助开启自己的新生活和新的人际网络。”〔10〕在丧葬事宜中,村民开始从重殓厚葬的传统观念转变为简丧薄葬,同时具有死者为大与生者为先并存、为死者悲与为生者活并存的传统与现代意识交织的观念体系。
五、丧葬功能
丧葬是生者为死者操办事宜,涉及死者家属,也关系死者家族与宗族,同时也是整个村落的事情,“传统丧葬仪式在沟通家庭、宗族、村落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一种本质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核心联结起来,并借力邻里互助关系进一步整合地缘联系的互馈机制”〔11〕。因此,丧葬是现今中国乡土社会中最具民间村落特征的活动,不但象征死者与亲人的关系,而且还表现死者与死者家人和家族与宗教的关系,当然还关联村落和谐关系的构建。
(一)家族认同与凝聚力的增强
村落的丧葬仪式及其内容表达的是生者与死者空间结构的转换,由现实界转换为精神界,内含生者对死者的颂扬、缅怀、追忆与眷恋,同时也有死者对生者的福佑。在参加死者丧葬活动的人员中,既有死者的直系亲属,更多的是家族与宗族亲属。家族成员组成丧葬活动中的主要人群,是丧葬得以顺利开展的核心力量。“婚丧嫁娶在内的乡土社会的各项活动仪式正是培养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的土壤。”〔12〕家族成员全程参与丧葬活动,是完整仪式的见证者,聚整个家族力量举办好死者之礼,是家族成员的心愿,表达了生者与死者关系的再次确认与升华,是家族认同感与凝聚力增强的体现。
Y老人是从本地外村到坡脚村的上门女婿,老人一辈共4个弟兄,其排行最小,老人去世前,已有两位兄长离世,还有一位大哥尚在,这位大哥今年84岁,在外工作至今定居异地,已行动不便。当听到老人离世的消息时,老人大哥非常悲伤,一度昏厥,已无力远赴家乡,随即吩咐自己的所有儿女尽快动身在出殡前替他看望祭奠自己现在唯一的兄弟,在出殡前,老人大哥一脉一行10人及老人其他两位兄长亲属一并参加了出殡及下葬仪式。Y老人上门的本家姓张,是坡脚村的大姓,人口众多,遍及整个村落。老人一共生育5个子女,其中3个儿子,2个女儿,每位儿女现已为祖父母,整个家族共有36人。在这36人中,大都在外地工作,亲人与亲人之间平时联系较少,特别是老人的孙子女辈,相互之间接触不多,平日关系不太紧密。但当听到老人离世的消息后,36人全部回到家中参加葬礼,不管过去的关系如何,在这场丧葬活动中大家一起出力,体面地办好老人的后事,表现出无比的团结,事后其他人对此次丧葬活动中家人的努力给予了较高评价。除了老人的直系亲属外,老人妻子家族的成员在此次丧葬中也付出了较多辛劳,与老人直系亲属一起以办好丧葬事宜为目标,每位家族成员也在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促成此次老人的后事十分顺利。
新时期新语境下的乡土社会正在发生激烈而深刻的变革,变革中传统的村落空间结构将逐渐被打破,以血缘和宗亲关系建构的村落空间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家族与宗族传统也将在不断的变革中受到强力的冲击。当下的乡土村落结构关系中,丧葬是最能集中家族与宗族成员齐心协力共同办事的契机,在丧葬举办过程中,不论家族成员之间、宗族成员之间过去关系如何,均会在家族之人特别是高寿老者离世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认同感,这时的家族凝聚力也最强,家族成员同根同源、同宗同族的意识属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与张扬,这是当下乡土社会村落家族传统与民间习俗表现最为充分的地方。
(二)家族邻里的空间结构与村落的和谐关系
中国的乡土村落虽然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各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但乡土村落的基本格局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3〕41。即家人与家庭的关系、家庭与家族的关系、家族与宗族的关系、宗族与村落的关系或是村民与村落的关系、邻里关系等还是十分紧密,这有别于城市社区。中国广大的乡村,其基本结构是由一个个家支、家族按照血缘与宗亲关系建立的大家庭,村民与村民之间大都是亲戚关系或邻里关系,这就赋予了村落成员之间无形的情感联系。家族与邻里是村落的组成部分,家族与邻里力量的团结与凝聚不仅是村落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家族与邻里在村落的集体活动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对村落和谐关系的构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Y老人所在的坡脚村主要由张、杨、李、王等大姓组成,张姓人口众多,为本村的第一大姓。当老人离世的消息传遍整个村落后,村民们自发到本家吊唁,并主动参与到宴请、买办、帮厨、登记、起坟、抬棺、下葬、圆坟以及其他组织安排等事项中,村民的参与是Y老人后事顺利进行的重要力量。在这些帮忙的村民中,与本家要么是家族关系、要么是邻里关系、要么是本家曾经也帮衬过的等等,这是坡脚村历代形成的村落格局及其衍生的村民关系,是一家有事全村帮忙、一家有难全村帮助的互帮与互助、互惠与互利的乡土关系,这种乡土关系对构建和谐的村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丧葬是一个村落的重大事项,在丧葬活动的举办过程中能够体现家族的认同、邻里的互助,而且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丧葬事宜不会停止,家家均会遇到亲人离世、每家均会举办丧葬事宜,并且这种认同与互助会延伸到村落中的其他事宜,在不断的家族认同与邻里互助中,村民关系始终维持在一个稳定合理的平衡状态,这对构建村落的空间结构与和谐关系至关重要。
坡脚村虽然只是滇西地区的一个普通村落,但坡脚村悠久的历史、保存相对完整的民间传统与宗祠祭祀习俗、和谐的村落格局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典型特征,坡脚村是广大汉族村落的一个缩影。对Y老人丧葬活动的人类学考察,采用深描的方式进行田野探究,有利于挖掘丧葬活动所蕴含的丰富的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学、宗教学等内容,为研究乡土社会村落民间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丧葬仪式全面与深度的记录,可以发现,丧葬不仅仅是一场生者对死者的纪念活动,更是乡土社会民间信仰的体现;当下的丧葬呈现传统习俗与现代意识交织的格局,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象征村落民间文化的变迁,其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整个乡土社会格局的变化与村落结构的改变;研究村落的丧葬活动,可以探究家族在村落中的空间结构与位置以及邻里关系在村落格局中的意义,进而为构建村落和谐关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1〕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2.
〔2〕黄秀蓉.贵州化屋歪梳苗“打牛”祭丧仪式探析〔J〕.民族研究,2011(6):21-29.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4〕肖坤冰,彭兆荣.汉民族丧葬仪式中对“运”平衡观念的处理:对川中地区丧葬仪式中“找中线”环节的分析〔J〕.民俗研究,2009(1):179-189.
〔5〕金元浦.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19.
〔6〕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9.
〔7〕张文勋,施维达,张胜水,等.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72.
〔8〕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论语〔M〕.程昌明,译注.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3.
〔9〕杨帆.“慎终追远”的背后:鲁西南“过三年”丧葬仪式的文化解读〔J〕.文化遗产,2011(4):121-129.
〔10〕方白寿.安徽放方庄的丧葬礼仪〔J〕.民俗研究,1996(2):65-68.
〔11〕李汝宾.丧葬仪式、信仰与村落关系构建〔J〕.民俗研究,2015(3):127-134.
〔12〕高小岩,全美英.超越回汉关系的“熟人社会”:以张家川的汉族葬礼为例〔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8(6):4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