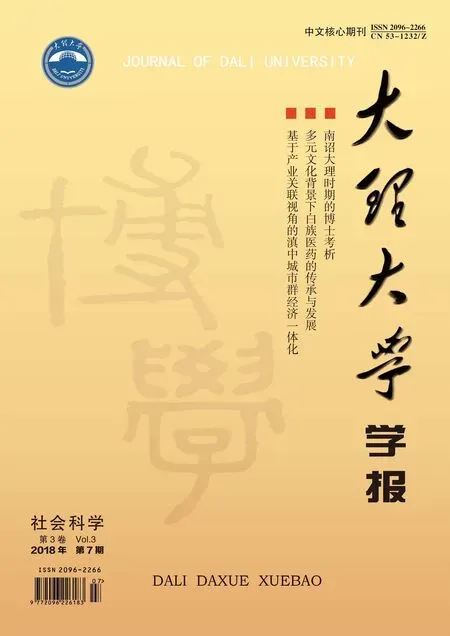多元文化背景下白族医药的传承与发展
2018-04-12吕跃军于昊燕
吕跃军,于昊燕
(大理大学,云南大理 671003)
白族医药可谓源远流长,璀璨夺目。对白族医药的研究,前人多从医学理论的视角进行解释,虽然这种探索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大理地区古代为“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的重要中转站,被称为“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历史上白族医药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因此,研究白族医药还应该看到其多元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各种宗教对白族医药的渗透。
一、早期的白族医药与巫医相伴
自有人类,即有疾病。远在4 000多年以前,白族先民就在生产生活以及与疾病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发现和创造了白族医药。
(一)白族医药的发端
洱海地区气候温和,寒暑适中。嘉靖《大理府志》卷2载:“四时之气,常如初春,寒止于凉,暑止于温。”在这一生态环境下,动植物种类繁多,采集果实和狩猎成为当时白族先民获取食物的主要方法。经过反复尝试,白族先民逐渐认识了许多植物以及可以用来治疗某些疾病的药物。这一漫长的实践过程,正是白族先民认识医药的发端。
据大理地区考古发掘报告,马龙遗址所处的时代大约属于石器时代〔1〕。当时人们沿苍山脚下的缓坡地带,居住在一种半穴式的房屋中。在这些房屋里有用于炊爨的炉灶和用于储存果实的窖穴,四周有引用苍山溪水的沟渠;银梭岛遗址的早期年代距今约为4 200年〔2〕。从遗址中出土的石器数量较多,有刀、镞、锛、网坠、石核及石片;白羊村遗址距今(3 770±85)年〔3〕。在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磨制生产工具以及储藏谷物的窖穴。以上考古材料说明,白族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脱离了穴居野处的状态,能够建造遮风避雨的房屋,谷物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可以将生食变为熟食,用镞、砺、刀、锥、凿等兼作治病的工具。这些就是白族先民早期的医药活动。
(二)白族医药与巫医
秦汉时期,分布在洱海地区的众多部落,经济文化水平各有高低,但信鬼尚巫的风俗却大致相同〔4〕。当时的人们还无法理解灾难、痛苦、疾病等事物,只能祈求于鬼神。在白族先民看来,疾病产生的原因是鬼神作祟,其中有痘鬼、咳嗽鬼、惨死鬼、暴死鬼、痨病鬼、产房鬼等20余种之多〔5〕。主持祭祀的巫师被视为人与神的交通者,白语称为朵兮薄。“朵”是大或伟大的意思,“兮”是神秘或主宰的意思,“薄”是尊者的意思。巫师是世代相传的,男的叫神汉或巫公,女的叫巫婆或女巫。巫师的家里都有香堂,香堂设有神案,案前摆放一个香盆,每天都在香盆里焚烧纸钱和甲马。“甲马”亦称纸马或脚力,为白族巫术仪式中的神圣法宝,是巫师借以交通鬼神的媒介,在白族民间广为流传〔6〕。
原始宗教信仰是巫医得以存在的思想基石。中国医学的演进,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立。以巫术治病,为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低级时代的普遍现象〔7〕。秦汉时期,白族医药活动总是伴随着白族巫术仪式,这种巫术和医术合一的巫医现象,正是这一历史时期白族医药状况的真实反映。大理地区流传至今的“打醋汤神”的巫术,就有防病治病的作用。在打鬼逐疫时,用柏枝烟熏,明火除虫,实则是除害灭病的措施。
二、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白族医药与宗教混杂
自公元738年至1253年,大理地区先后出现了南诏国和大理国两个地方政权。在长达500余年里,大理白族人民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白族文化。南诏大理国时期是白族医药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白族医药明显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一)南诏国的白族医药
唐朝初期,洱海地区分布有六诏。公元738年,南诏在唐朝的帮助下兼并其余五诏,建立了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南诏国。在这一背景下,白族医药得到了较快发展。南诏时期,开疆拓土,征战频繁,军中已有医生随行,且有医治伤员和病患的规定。《蛮书·蛮夷风俗》载:“用军之次,面前伤刀箭,许将息。傥背后伤刀箭,辄退者,即刃其后。”①赵吕甫按:以条文内容为叙军制,与《南蛮条教》性质相合,非关《蛮夷风俗》,殆为传抄者所误置。《新唐书》卷222载:“师行,人赍粮斗五升,以二千五百人为一营。其法,前伤者养治,后伤者斩。”其中“将息”和“养治”即是疗养治伤的意思。在南诏与唐朝发生战争期间,曾掳掠大批内地汉人至洱海地区,也包括医生在内。《会昌一品集》卷12载:“蛮共掠九千人”,其中有“医眼大秦僧一人。”此人即兼职医事的东罗马帝国的传教士。
南诏时期已有温泉疗疾的实录。康熙《蒙化府志》卷1载:“温泉,在封川山麓,蒙诏汤池也。相传细奴逻母病,浴此辄愈。今郡人冬春二季,咸往浴焉。”如今大理地区各族人民患有皮肤病、风湿病、关节痛者都习惯于温泉沐浴治疗,应该是南诏医药的孑遗。南诏时对药物已有较深的认识。《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载:“濩歌诺木,丽水山谷出。大者如臂,小者如三指,割之色如黄蘗,土人及赕蛮皆寸截之。丈夫妇女久患腰脚者,浸酒服之,立见效验。”说明南诏时期流传一种治疗风湿病的药物。大理地区属亚热带气候,光照和热量均特别充足,有毒的动植物很多,使得毒药的使用成为白族医药的一大特色〔8〕244。《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载:“郁刀次于铎鞘。造法用毒药虫鱼之类,又淬以白马血,经十数年乃用,中人肌即死。”
南诏时期,人们对瘴气十分畏惧。《蛮书·山川江源》载,高黎共(贡)山在永昌(今保山)西,下临怒江。左右平川,谓之穹赕(今道街)、汤浪(今坝湾),加萌所居也。草木不枯,有瘴气。自永昌之越赕(今腾冲),途经此山,一驿在山之半,一驿在山之巅。朝济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顶。冬中山上积雪苦寒,夏秋又苦穹赕、汤浪毒暑酷热。河赕贾客在寻传羁离未还者,为之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奈)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平(囊)中络赂(钱财)绝”。又说:“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充(冲)过宝山城(今昔马),又过金宝城(今密支那)以北大赕(今坎底,又称葡萄),周迴百余里,悉皆野蛮(裸形蛮),无君长也。地有瘴毒,河赕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阁罗凤尝使领军将于大赕中筑城,管制野蛮。不逾周岁,死者过半,遂罢弃,不复往来。”《岭外代答》载:“南方凡病,皆谓之瘴,其实似中州伤寒。盖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这些记载就是关于南诏时期流行地方性疾病的真实记录。
(二)大理国的白族医药
公元937年,大理国建立后,励精图治,发展生产,使大理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白族医药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成熟起来。大理国时期,已有世代名医出现,并有医学著作产生。这是白族医药形成的重要标志。《故溪氏谥曰襄行宜德履戒大师墓志并叙》②此碑出土于大理古城五华楼旧址,现存于大理市博物馆。记述了大理国名医溪智的事迹。溪智既是医生,又是高僧阿叱力,是一位“德年俱迈”的儒医和儒释,死后被“谥曰襄行宜德履戒大师”。其祖辈是一代名医,著有《脉决要书》。据考证,溪氏至今仍为白族世家,主要居住在大理市古城东郊才村等地。《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①此碑出土于大理古城五华楼旧址,现存于大理市博物馆。追述了墓主白长善的事迹。其先辈白和原,因医术高明而升为医长。白长善为白和原之八世孙,继承祖业,是祖传名医。他“宗教之学穷于精粹,脉能辨生死,药不问贵贱”,被封为僧长,赐号“医明道蕴由理大师”,对白族医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白氏行医八代之久,与阿叱力教关系密切。以上碑刻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大理国时期已具有了较高的医疗水平。
白族有将药物置入佛塔的习俗。1974年在建于大理国时期的洱源火焰山佛塔中发现大量药物,其中有金箔、珊瑚、玛瑙、绿松石、水精石、水中石子、雷楔子、珍珠、贝、琥珀、象牙、松香、檀香、干姜、槟榔、荜拨、荜澄茄、胡椒、桃仁、蚕豆、扁豆、草拨、草果、樟木子等〔9〕。大理崇圣寺具有“佛都”之称。1978年维修大理崇圣寺三塔时,在主塔千寻塔顶也发现不少药物,其中有朱砂、沉砂、檀香、麝香、珊瑚、金箔、云母、香蛤、松香、水君子等。据考证,这些药物是大理国时期置入的〔10〕。从以上佛塔中出土的这些药物可知,大理国时期已经具有了较为丰富的药物学知识。这是白族医药形成的另一标志。
大理国时期的写本佛经中载有一幅人体解剖图。图中人体的双手掌心和双脚背上分别标有地、火、水、风,双膝、双肘、双肩及大腿根部分别标有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和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东北方。李晓岑认为,“地、火、水、风”为印度佛教所说的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因此,这张人体解剖图应是受到了印度佛教的影响〔8〕239。据李东红考证,图中人体的额头应该标有中方。他认为“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中方”和“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东北方”为佛教密宗的“五方佛”和“四方之神”。这张解剖图所标示的文字,是为了说明八大明王之尊号及其所代表的诸佛菩萨。在白族民间,常以明王来斩除恶魔,并辅之以各种药物,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11〕165。
(三)白族医药与宗教
佛教最迟在公元9世纪中期传入大理地区,对白族产生了重要影响〔12〕。阿叱力教被称为大理白族佛教密宗,对白族医药的影响甚大。相传阿叱力教是观音的化身梵僧传入大理的,所以,大理的民众特别崇拜观音。阿叱力教引导人们“修身”,用以防病治病,强身健体。据考证,大理国时期的写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就有“祛病延寿”的功用〔11〕166。
大黑天神在白族民间受到广泛崇拜。传说玉帝看到人间胜过天宫,心生忌妒,派侍者把瘟药撒向人间,让人间人亡畜死,树枯水干。侍者不仅长得俊秀,而且心地善良,不忍心把这美好的人间给毁了,于是决计牺牲自己,拯救下方生灵,便把瘟药全部喝下。人间免除了一场大难,可是侍者面目发黑,浑身发肿,从天上掉了下来。白族人民感激侍者舍身相救,为其建盖寺庙,尊称为大黑天神,作为白族本主世代供奉〔13〕。大理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瘟疫流行,人们对瘟疫充满了恐惧,束手无策,因而祈求佛教神灵来控制瘟疫的肆虐。
剑川石宝山石窟最为罕见的是石钟寺第八窟,俗称阿姎白。主龛中部须弥座上雕刻一具女性生殖器,两侧有“大开方便门,广集化生路”的题联。据费孝通考证,“阿姎白”的雕刻是很简单的,可能是早期白族居民生殖器崇拜的遗物,反映了白族先民有过一个早期文化,与人石崇拜有关〔14〕。李东红认为,这里的女根造像,实际上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即送子观音,当地民众来此祈子的风俗,与佛教信仰有关〔15〕。
道教的炼丹术在唐代中期传入大理。据《蒙化志稿》卷15载:“玄珠观,一名玄龙寺,在城东南玄珠山。观有玄珠井。相传蒙诏时,蜀人有以黄白之术售于蒙者,蒙人因即其地设蒙化为修炼之所。”所谓“蒙化”即蒙舍②位于玄珠山上的蒙舍宗祠是南诏最早建盖的祖先崇拜和道教并存的一座殿宇,建盖之初内祀细奴逻的母亲茉莉羌,后改为道观,叫玄珠观。因火灾被毁,道教失势后无力修复。后佛教僧侣募集款项得以重修,遂易名玄龙寺,为佛道共存的场所一直延续至今。。“黄白之术”即炼丹术,“黄”是炼金,“白”是炼丹。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大理地区关于炼丹术的最早记载。大理地区所炼的丹药叫九还丹药〔8〕246。
白族民间有神药两解的观念。所谓“神药两解”,即将药物治疗与驱鬼神、念咒语相结合,来达到祛除疾病的目的。白族民间认为,疾病大都由鬼神引起,因此,南诏以来,白族民间即有医药神崇拜。在白族本主庙中,有专司医药之神。比如,痘儿哥哥专治小儿痘疹,送子娘娘是掌管生子之神。对白族民间来说,治病与求神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文化。
三、元明清时期的白族医药与中医交融
元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纳入国家的统一管辖之下,中原文化得到广泛传播,为白族医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明清时期成为白族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白族医药受到了中医的深刻影响。
(一)元代的白族医药
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大理路设医学提举司〔16〕。这是大理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个医学管理机构。据《元史》卷88记载:“医学提举司,秩从五品。掌考校诸路医生课义,试验太医教官,校勘名医撰述文字,辨验药材,训诲太医子弟,领各处医学。”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大理路总管府设官办医疗机构惠民药局〔16〕。惠民药局对中医在大理地区的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于南诏时期传入大理地区,经大理国,至元代,中医在大理地区开始有系统地进行推广〔17〕。在中医的影响下,白族医药吸纳中医的精髓,使自身得到了较快发展。
(二)明代的白族医药
明代在云南实施留兵屯戍、大量移民、推广儒学等措施,大批中医典籍涌入大理地区,白族医药受到中医的广泛影响,开始有了医学分科,出现了不少名医,如董赐、赵良弼、张羲、薛芬、李德麟、陈洞天、张辅高、居素、全桢、李星炜、李仲鼎、蓝成彩、赵廷猷等。他们既能熟练地运用中医理论,又能因地制宜地进行医疗实践,并有多部医学著作问世,如陈洞天的《洞天秘典注》,李星炜的《奇验方书》《痘疹保婴法》等。明代大理地区的药材已十分丰富。据《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载,徐霞客于明崇帧十二年(公元1639年)考察大理西门外传统的三月街,在日记中写到:“观场中诸物多药”。可见当时各种药材的交易十分可观。嘉靖《大理府志》卷2记载的大理地区的药物有180种之多。明代,白族医药在与中医的融合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清代的白族医药
清代在云南推行大规模的汛塘制度,实施改土归流、开科取士等一系列政策,开展广泛的儒学教育,汉文化在大理地区成为主流文化,中医在大理地区得到更深入推广。白族医药与中医进一步融合,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成果。一是名医大批涌现,不少医家以独特的专科名盛一时。如杨植、辛储贤、熊彬、杨世宾、宋淮、李允开、段锦章、王廷槐、赵子庄、李钟溥、周景濂、梁朝柄、王恩锡、马廷纶、周鸿雪、尹东夏、王泰交、杨宗儒、周霞、赵成榘、孙荣福、奚毓崧等。二是本土医著大量产生,且能在当地刻板印刷。如李允开的《征验秘法》,赵子庄的《本草别解》《救疫奇方》,李钟溥的《医学辑要》《眼科》,赵成榘的《述祖训言》《续千金方》,孙荣福的《病家十戒医家十全合刊》,奚毓崧的《训蒙医略》《伤寒逆症赋》《先哲医案汇编》《六部脉主病论补遗》《药方备用论》《治病必求本论》《五脏受病论》《舌苔歌》等。三是众多具有名号的店堂和药铺的出现,为百姓看病拿药提供了方便。店堂、药铺除配方售药外,尚有部分老字号药铺与内地及东南亚国家药商有贸易往来,自制膏、丹、丸、散等〔18〕。四是对道地药材有了深入研究,认识和掌握了一批治疗各种常见病、疑难病的药材和配方。据民国《蒙化县志稿》卷14载,清代已对大理地区常用的天冬、何首乌、黄芩、香附、荆芥、薄荷、石斛、柴胡、半夏、车前、干葛、紫苏、益母、川芎、黄精、丹参、白芨、苦参、夏枯草、当归、防风、金银花、王不留行、牛蒡子、茯苓等25种道地药材的性味、功能作了详细分析。五是白族医家具有较高的医德修养,体现出白族注重修身养性的文化传统。清代,大理地区已对从医人员的行为规范作出全面而具体的约定。
(四)白族医药与中医
每个民族传统医药的发生、传承和发展与各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中医有长期的医疗实践,有丰富的诊治经验,也有比较完整的历史记载,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几千年来,中医学理论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各科的临床实践。因此,中医在我国的传统医药中处于最高层次,各少数民族医药均受到中医不同程度的影响,与中医都有一定的血缘关系。白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自秦汉以来就与内地汉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随着汉文化在白族地区的广泛传播,作为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也在白族地区得到深入推广,进而与白族医药相融合。在与中医交流的过程中,白族医药尤其是白族地产药也很早就传播到了内地,并被中医加以吸收和运用。这种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现象,乃是各民族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而且这种相互融合的现象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包容性是白族文化的重要特征〔19〕。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大理处于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白族通过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交往,积极汲取各民族的先进文化,进而形成了开放、包容、多元的白族文化。在这样一种文化生态中生成的白族医药也就具有了兼容并蓄的特征。在与各个民族传统医药的交流中,白族医药与中医的交流最为密切,因而受中医的影响也最大。历史上,白族医药有着长期的医药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在此基础上,又学习和吸收了中医的理论知识和临床方法,从而将中医融入白族医药之中。但是,这种融合并不意味着中医可以取代白族医药,而是白族医药在自身发展的进程中,将中医的理论和方法本土化、民族化,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白族医药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有力地促进了白族医药的发展和提高,使白族医药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这种融合过程中,白族医药仍然保留着本民族传统医药的特点。
通过探讨白族医药与中医的关系,把握白族医药兼容并蓄的特点,阐明中医传入大理之后本土化和民族化的过程,运用民族医药的理论与方法,对白族医药进行研究与阐释,以建构和完善白族医药的理论体系,推动白族医药基础理论和临床医疗水平的提高与发展,是当代白族医药研究人员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四、近现代的白族医药与西医碰撞
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医大规模传入中国。白族医药和中医及其他少数民族医药一样,其生存和发展遇到了严重危机。但是,由于社会需要和实际疗效,白族医药在艰难中仍然有所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白族医药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一)西医在大理的传播
西医传入大理地区为时较晚。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天主教始到大理布道,传教士施舍西药,西医随之传入。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基督教亦到大理传教,在教堂内附设施药所,由外国人充当医生和护士。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加拿大传教士赖宏恩到大理传教,在大理古城朝阳巷福音堂设药室,备有阿司匹林、山道年、眼膏、黄降汞软膏等简易西药,当时称为洋药。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基督教内地会派遣加拿大传教士韩纯中夫妇到大理传教,在大理古城北门福音堂设另一药室,除用西药治病外,尚能开展外科小手术,为大理地区西医外科之始。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内地会英国医士海富盛到大理设西医诊所。
西医在大理经历了一个逐步被人们接受的过程。初期,由于医疗设备简陋,医疗队伍薄弱,当地居民颇感陌生,因而对西医多有不信任。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免费诊治和送药,治好一些病人,才逐渐为当地居民所接受。抗日战争时期,西医在大理地区得到较快发展。1941年,内地会福音医院由开封迁至大理,更名为大理福音医院。医院设有病床32张,配备有常用诊疗设备及检验器材,能开展阑尾、疝气等普通外科手术。先后有美、英、朝、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等外籍医务人员12人,中国职工36人,护士班练习生16人在该院工作。据有关资料统计,至1949年,大理地区有公立卫生院13所,西医诊所65家,挂牌助产士4家,镶牙馆14家,西药店39家〔20〕。
(二)民国时期的白族医药
西医传入大理,客观上带来了新的医学知识和技术,促进了大理地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西医相比,传统白族医药面临着许多挑战。民国时期,中医和民族医药受到排挤,白族医药也进入了最艰难的发展时期。一些白族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医,并在县城和一些重要乡镇开设西医卫生院或诊所。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西医的信任和依赖程度大为提高。但是,白族医药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并有确凿的疗效,因而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这一时期,大理地区尚有数百家店堂和药铺。据澳大利亚人类学家C.P.费茨杰拉德在大理的调查,1938年大理城有药店55家,仅次于餐馆和茶室,大部分药材来自西藏和缅甸〔21〕。民国时期大理的药材交易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与西藏、缅甸的药材交易数额巨大。大理已成为云南、我国西南乃至东南亚地区药材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白族医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白族的民族身份得到确认,白族聚居的大理州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大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扩大,外来文化与白族文化交流频繁,白族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白族医药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大理地区涌现出一大批白族名医,如彭子益、杨质夫、张叔葵、王子谦、李森、朱希仲、杨燕侯、舒子骧、李桐、李品荣、朱仲德、王保元、李子宽、张文伯、朱家鲁、王济承、冉瑞金、段洪光、李翠兰、李伯藩、朱兆康、洪显昌、段飞龙、王作端、张立平、段萍、郭文英等。他们不仅通晓中医理论,熟谙诸家方剂,还各有特长,对大理白族文化和地理环境有深入透彻的了解,为白族医药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在白族民间,还有一批具有一技之长的民间医生。他们大多在农村行医,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村里的百姓服务,是白族医药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20世纪80年代,以大理大学李树楠教授为首的科研团队,开始从事白族民间药物昆虫蟑螂的研究与开发。通过对蟑螂活性成分的提取分离,成功研制出治疗各种外伤的药物康复新滴剂。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该药用于对伤员的治疗,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疗效。随后,又相继研制出了抗心衰药物心脉隆注射液和抗乙型肝炎药物肝龙胶囊。“十三五”期间,云南省将打造服务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中心,蟑螂系列产品被列为重点打造的“云药”品牌之一。创办于清光绪年间的慎德堂诊所,位于南诏文化的发源地巍山县古城,至今传至第六代,济世百年。其悠久的历史、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技术,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患者幕名前来求医,被人民群众称赞为百姓健康的“守门人”。慎德堂将现代医学检测手段与传统家传诊疗方法相结合,对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进行诊治,取得了显著的医疗效果。其传统诊疗法于2017年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改革开放以来,对白族医药的研究方兴未艾。如杨延福《大理地区古代医药史料辑集》(大理师专学报,1989)一文,从古代文献中辑录了有关大理地区的医药史料;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写的《大理中药资源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收载了大理州各类药物1 647种;梁炳学在《中医药学在云南大理民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白族学研究,1991)一文中,对中医药学在大理地区的传播和发展进行了探讨;大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编写的《大理苍山药物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收载了苍山各类药物1 286种;刘毅、郑进的《云南白族医药》(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一书,收录了大理地区白族民间较为常用的植物药113种;大理白族自治州食品药品检验所编写的《大理白族药》(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对141种较为成熟的白族药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姜北、段宝忠主编的《白族惯用植物药》(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收录了白族常用植物药263种;大理白族自治州卫生局编写的《白族医药丛书》(云南科技出版社,2014),对大理白族医药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其中《白族古代医药文献辑录》收集整理了一批大理古代医药文献,《白族医药名家经验集萃》收集整理了一批白族医药名家的临床经验,《白族民间单方验方精粹》收集整理了白族民间单方验方1 835例;钱金栿、夏从龙主编的《大理苍山植物药物志》(云南科技出版社,2016),收载了苍山植物药1 511种。
白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和临床经验,并有许多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因此,白族医药在云南少数民族医药中处于较高层次。由于大理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白族医药受到周围各个文化圈的影响,其来源较为复杂。既有本土的医学成分,也有内地的中医成分,还有印度和波斯的医学成分,与藏医药也有交流。在其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又受到了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的渗透,以及现代西医的冲击,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龙江认为“白族医药文化既有自己的特色,又与中华深奥的医药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医药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过渡形态,具有很高的研究、传承价值”〔22〕。白族医药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医学体系,而中医对其影响最为深刻。在与中医长期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白族医药不仅显示出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而且形成了兼容并蓄的个性特征,是我国民族医药文化的瑰宝,也是人类多元文化交流的范本。
〔1〕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甲编)〔M〕∕∕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卷一).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300-335.
〔2〕闵锐,万娇.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9(8):23-41.
〔3〕阚勇.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J〕.考古学报,1981(3):349-368.
〔4〕范文澜.中国通史(第4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4.
〔5〕张旭.白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天鬼〔J〕.大理文化,1980(6):29-32.
〔6〕杨宪典.大理白族原始宗教:巫教调查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50-55.
〔7〕陈邦贤.中国医学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6.
〔8〕李晓岑.白族的科学与文明〔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9〕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洱源火焰山砖塔出土文物简记〔M〕∕∕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卷六).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2708-2712.
〔10〕邱宣充.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J〕.考古学报,1981(2):245-267.
〔11〕李东红.白族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
〔12〕张锡禄.大理白族佛教密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48.
〔13〕大理州《白族民间故事》编辑组.白族民间故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146-147.
〔14〕费孝通.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考察〔M〕∕∕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上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273-274.
〔15〕李东红.剑川石窟与白族的信仰民俗〔J〕.世界宗教研究,2006(3):137-144.
〔16〕大理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大理白族自治州志(卷8)〔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299.
〔17〕梁炳学.中医药学在云南大理民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J〕.白族学研究,1991(1):167-169.
〔18〕大理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大理市卫生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130.
〔19〕赵金元,饶清翠,凡丽.白族文化的包容性及其现实意义〔J〕.中国发展,2009,9(3):80-85.
〔20〕大理州卫生志编纂委员会.大理白族自治州卫生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3.
〔21〕C.P.费茨杰拉德.五华楼〔M〕.刘晓峰,汪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51.
〔22〕姜北,段宝忠.白族惯用植物药〔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