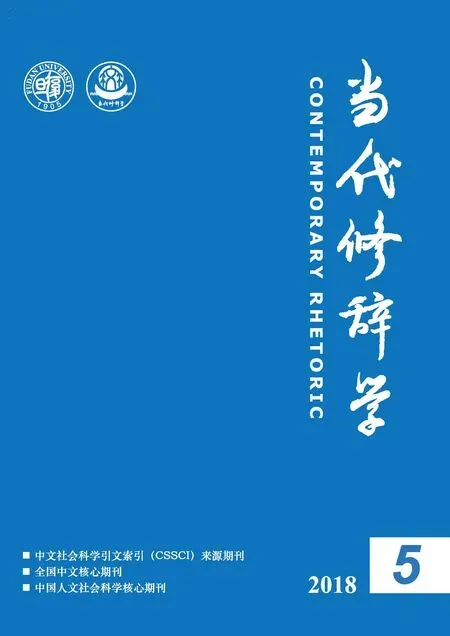语言工作与写作教学
2018-04-12布鲁斯霍纳
布鲁斯·霍纳
(路易斯维尔大学,美国肯塔基州)
廖巧云1 贾代春2 译
(1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上海 200083; 2 重庆工商大学国际商学院,重庆 400067)
提 要 本文认为写作课程应当被视为语言工作的场所和场合,而不是教授写作技能的场合。有关学习迁移的研究以及写作多变性及多样性的特征对写作技能的传输模式带来了挑战,笔者逐一综述这些挑战后提出了一种新的写作课程模式,该模式根据写作课程在维系和修正语言中的作用来定义写作课程的目的和价值,被称为语言工作。跨语言理论表明语言工作不但必要且应该坚持不懈;此外,写作课程为有意从事此项语言工作的人提供了物质手段。学生作文有助于阐释学生如何能够并且确实在完成语言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认为写作教学课程应当被视为服务语言工作的场所和场合。 但我意识到,人们对这类课程的理解以及开课目的与上述看法不一致。他们认为,写作课程就是把学生缺乏的写作技能传授给学生,语言也被归为传授的对象;其目的是向学生灌输正确和恰当的语言形式,更具体地说是书面语言(例如参见Smit 1)。在该模式中,成功的写作课程能够为学生提供完成写作任务必备的写作技巧,进而为将来所有的写作任务做好准备。据此,该模式就是一个预备模式:写作课程的目的在于为学生的后续写作做准备。因此,这类课程的价值不是根据课程期间的写作产出定义,而是根据课程期间的写作能为未来写作带来的预期效果来认定的,也就是指“迁移”的内容。
基于迁移问题和写作的多变性及多样性特征来理解写作和写作教学,并对该模式进行评析后,我提出了一种新模式,该模式根据写作课程在维系和修正语言中的作用来定义写作课程的目的和价值,我称之为语言工作。我将从跨语言视角来证明这种工作不但有必要,而且应该坚持不懈。 我认为,写作课程应该为从事此语言工作提供物质手段,而且学生能够也确实在完成这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写作课程的预备模式
写作课程的预备模式是为学生将来所承担的写作任务做准备的一种手段,该模式在全世界广为盛行。然而,尽管这种模式普遍存在,却从未有学者成功地论述过写作课程具有为学生未来写作任务做准备的功用。两大因素阻碍了学者们的论证。首先是迁移问题。关于跨语境知识迁移的研究,没有任何文献论及过一种简单、直接甚至容易识别的跨语境知识迁移——与此相悖的是,教育始终承诺将会传授学生技巧且该技巧将会从学校到其他语境亦或从某一学术语境向其他语境迁移——就写作课程而言,也就意味着存在从写作课程到其他学科课程或其他工作环境的迁移。事实上,一些学者曾经主张摈弃“迁移隐喻”这一说法(见Beach)。
尽管直接迁移的可能性得到了普遍认可,但是从迁移内容和迁移期间的变化两方面来看,主张放弃“迁移隐喻”的观点并非毫无道理。关于迁移内容的问题,表面上看,写作这一个词意味着写作传输的内容具有单一性。而事实却与此相反,写作这个综合性术语涵盖了大量且丰富的写作形式。因此,即便是“综合”写作课程中所谓的写作教学也不足以充分展现写作的内涵。正如Brian Street所主张的,我们拥有的不是读写能力(literacy)而是读写能力的表现形式,而且这些表现形式会因实践者的不同并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因为读写能力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个人拥有的稳定实体,而应是不断的社会实践(Street,Literacy)。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古往今来写作实践不胜枚举(见Lillis,SociolinguisticsofWriting)。一经审视便会发现,普遍、通用、恒久的读写能力的概念并不是读写能力本身,而应是读写能力的特定表现形式之一,是被认定为与学术写作相关的“论文作者”读写能力(见Trimbur, “Deproduction”),因而无法准确代表所有写作。
但是,即便是读写能力的这种表现形式也不是永恒不变、始终如一的,而是形式多样、变化多端的。因此,我们所展现的并非学术读写能力本身,而是其表现形式,且每一种形式都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Lea and Street, Lillis and Scott)。因此,即便那些旨在为低年级大学生提供“学术写作”技能的课程也注定不会成功,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学术写作的形式存在于写作练习中。虽然学术界有时似乎对学术写作的特点存在共识——应做到内容清楚、信息详实、论点明确等——但是对于具有这些特征的文章的理解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关于究竟什么才能算得上学术写作和优秀的学术写作由哪些要素构成等问题,在共识的虚饰之下仍暗藏着不可忽视又未被挑明的分歧(Lea and Street,Thaiss and Zawacki)。同时,关于识别书面错误的研究表明,尽管所有读者都谴责书面错误,但是就什么才能算是错误他们却各执一词(Lees, “Exceptable”; Williams, “Phenomenology”)。学术论文读者都一致认为学术写作应当内容清楚、论点明确等,但是对学术论文的具体接受程度却大相径庭。
写作的预备模式的第二大阻碍因素在于实现写作课程灌输给学生并被学生吸收的技能与知识的转化,而这种转化似乎不可避免,而且也有必要。因此,即便可以确定能够学习的某一种稳定的写作技能,在学习和掌握这种技能的过程中,学习者稳定地运用这一技能时似乎不可避免地对其进行转化(Donahue)。例如,DePalma和Ringer将迁移重构为“适应性”迁移,并将其定义为“在新的和可能陌生的写作情境中,有意识地或凭直觉地应用或重塑已学到的写作知识的过程”(141)。无独有偶,Rebecca Nowacek也提出了一种迁移模式,即把学习写作视为“语境重设”(recontextualization)和“重构”(reconstruction),“新旧语境——以及迁移内容——都因此有了不同的含义”(25)。在该模式中,包括学生在内的作者都是“新旧语境整合的主体”,而迁移被理解为一种修辞行为:作者努力“感知并有效地向他人传达此前两个不同语境之间的联系”(38,着重号系原文所有)。因此,这与其他的模式大不相同,即知识不再从一个稳定且自成一体的语境缓慢地向其他语境变动,学生/作者不再被动地充当一个呆板的知识传输通道的角色,且新旧语境、学生—传输通道或者知识本身都不再假定为恒定状态,新旧语境间、学生和知识本身之间存在相辅相成且不可分割的联系(见Horner,Rewriting[chapter 2])。
面对这些挑战,已有部分研究写作的学者反对教授一些公认的综合写作技巧。 由于迁移面临阻碍,综合的写作技巧无法彰明,而且这些技巧的迁移也面临阻碍,因此,他们另辟蹊径,主张教授与特定写作类别相关的特殊技巧,例如学科类写作,或特定工作环境写作 (见Smit,End; Petraglia,Reconceiving)。 该观点固然承认了综合写作或综合类写作技巧的匮乏,但却肯定了某些领域及其相关写作的稳定性。 因此,他们仍然保留了写作的预备模式,但与其他同行的区别仅在于缩减了写作课本应该教授学生的写作种类。
这种观点与Lea和Street所认定的学术读写能力的“学术社会化”模式相契合。 Lea和Street将这个模式描述为使学生适应不同的学科及专业行话、题材。学生可以习得象征着某一学科或专业领域的交谈、写作、思考以及操用读写能力的方法。学术社会化模式假定学科话语和体裁相对稳定,一旦学生学习和理解了某一学术话语的基本规则,他们就能顺利地重现这一语篇(“The‘AcademicLiteracies’Model” 369)。
我们可以看到,Smit的主张与该社会化模式契合,即“写作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写作新手学习以写作为工具来完成他们觉得有意义和有益处的特定任务,或者为了加入以写作为入会门槛的社会组织”(61,另见182)。然而,正如Lea和Street所言,学术社会化模式忽略了权力关系的作用,也忽略了在确定和洽商某一群体的话语特点上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正是因为这一缺陷,Lea和Street另辟蹊径提出了“学术读写能力”模式。该模式不仅承认学术读写能力的多元性,还认为学术读写能力的学习过程“(比社会化模型本身)更为复杂,是动态、微妙和情景化的,它涉及认识论的话题和社会进程如人、机构和社会身份之间的权力关系”(Lea and Street,“‘AcademicLiteracies’” 369)。
为语言服务的写作课程
很明显,在写作课程的预备模式下,学生课程写作练习的价值仅在于为日后写作,完成其他课程作业或办公室写作任务培养技能。换言之,写作课上的写作不被赋予任何内在价值,也称不上任何实绩,仅仅是为培养学生的写作技能。一旦掌握这些技能,其价值将会在后续写作中得以体现。也就是说,写作课上的写作只是实际写作的预演,因而并不能算是写作(Horner, “Revaluing”)。如前所述,该模式假设了写作技能顺利地跨语域迁移的可能性,比如写作课上学习的技巧可以轻易地应用到办公室写作中来,而且该模型同时还假定了迁移内容的一致性:假定写作不考虑语境,即在不同语境下保持不变——写作就是写作。
尽管这看似符合常理,但研究却证明写作随时间和空间而改变,即便写作的语境“相同”——如同一学科或同一工作类别——写作也会随时间而改变。跨语言理论有助于解释这一点。这里的跨语言理论指的是得益于全球范围内语言实践的异质性、融合性、多变性等愈发不可忽视的特征,写作与语言研究取得的新进展。①虽然全球通信技术的革新以及全球迁徙模式的转变促成了语言实践的这些特征,并进一步助长了语言的异质性和融合性,但全球化的进程并不会制约语言、语言关系、语言使用者和语境等方面的跨语言研究(例如,参见Khubchandani; Canagarajah,Translingual)。
更确切地说,面对当前被视为主流语言意识形态的单语制(monolingualism),跨语言理论提出了一种对立的语言意识形态。单语制意识形态把每一种语言都当作独立稳定而又自洽的实体,语言使用者说话写作时将自我置身于其中,每门语言都与一个特定民族和/或民族身份息息相关,例如:中文(代表语言和民族)、法语(代表语言和民族)和非洲裔美国语(代表语言和种族身份)。历史上,单语制的意识形态与所在民族—国家的崛起密不可分(参见Yildiz; Canagarajah,Translingual)。如今单语制意识形态依然存在,但不可否认它在语言、语言关系、语言使用者和语言使用的语境等方面的主张经不起推敲。例如,它不承认语言和语言行为变动和相互渗透的方式; 它忽略语言、用法和语境相互作用的方式;而且它不考虑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内部以及单一民族语言范畴内的语言行为的实际多样性及多变性,例如,“英语”这一单个词语所表现出的多样性和多变性。
虽然许多语言学者承认语言随时间而改变,语言之间也会相互借用,但往往未意识到,即使那些看似相同的语言行为—— 例如纯粹的复述 —— 也会产生变化。 只有通过改变语言行为的时间场域(复述通常如此),语言行为发生的变化才会变得明显。复述这一现象不同于复述的内容,因为两者的时间场域不同,而且时间场域不同也会带来意义的改变。最常见的情况是,原话语与复述话语的意义接近一致。 正如Pennycook所解释的那样,复述的话语与被复述的话语既相同又不相同 (Language)。 而且,考虑到所有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复述的话语(Bakhtin),两者的差异不是语言的异变,而是一种常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学家信奉的语言的构成规律不过是具体语言行为积淀的证明,例如在英语中某些名词之前使用“the”。 但是随着这样的积淀行为普及,积淀用语本身也会发生变化。虽然不排除(有意或者无意)摈弃积淀用语的可能性,但这样的做法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积淀行为,例如曾经的“外来”词如laissez-faire、 café、 canoe和 chow已经被本土化/英国化。
重要的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并非独立于人类实践的实体,人类不必习得语言行为并“置身于其中”说话写字。相反,语言是人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Louis-Jean Calvet解释道,“语言仅仅存在于并依靠言说者,每当言说者攀谈交流,语言都会经历改造、更新和改变”(7)。这意味着讲话人和作者通过(口头和书面)话语在维系和修正语言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常情况下,仅有精英层的讲话人和作者的作用才被认可,他们都被看作优异于普通讲话人和作者、当之无愧的(口头或笔头)文字艺术家。普通讲话人和作者在维系和修正语言方面的作用要么被全盘否定,要么被视为威胁:普通讲话人和作者一旦出现用语错误就会置语言于腐败和退化的风险中。
但是从跨语言角度来看,语言的不稳定性与生俱来,因为有实践就必定会有源源不断的语言出现,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稳定到可以作为标尺来衡量语言行为正确与否。此外,我们最多只能找到语言行为的一套“共同点”,且其特征受制于所有使用者的行为。由于语言行为的积淀,某些语言行为呈现出共同点,但语言行为方式的不同也会改变这些语言行为,且正如我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即使仅仅试图重复这些行为也会使其进一步积淀从而改变这类积淀用语的特征,正如一条老路,沿着路走的人越多,路会越来越破越来越烂,却也因此变得不同。
因此,所有讲话人和作者都会透过自己的话语改变语言的特征。事实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句话都具有“创新性”,因为在具体的语言行为中,创新需要根据现有的事物创造新的事物。因此,语言行为在社会创新和进步这一重要事业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从一方面看,人们可能认为,社会创新与进步作为维系和改善社会关系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与写作课程之间并无利害关系。写作课程确实无法“主宰”这一事业,但是相对于其他条件,写作课程为社会创新和进步提供了物质手段。在此我首先想到了一些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物质条件:在写作老师的指导下,一小群作者聚在一起写作和阅读彼此的作品,也可以(例如从图书馆)借阅其他文章,有共同时间阅读或者重读彼此的作品或其他作品,相互交流写作心得。如此条件下的收获远胜于我们的普通阅读。
我也考虑到写作课程在写作(尤其是书面语言)的表达创造及其传播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Calvet警告说,一方面,“语言并不存在;语言是一种抽象概念,建基于相当数量的事实、特征、讲话人的言语和语言行为规律上”,语言行为与语言表达共同存在,语言表达——人们的语言观和言语方式——作用于语言行为,并会诱发改变。它们会引发一种安全感/不安全感,促使言说者作出改变语言行为的某些行为(241)。
许多写作课程都会传播不少典型的语言表达,其中一种是把语言视为一种商品:语言不是使用者实践的产物,而是人们用来表达自身意图的一种工具。从这一表述看,写作知识就是对商品的了解——就如同懂行的消费者对冰箱用法的了解一样。因此,基于并推崇这种写作表达的写作课程强调并认定标准化的言语行为是正确利用写作的方式。在美国,“标准写作英语”(也称为标准美国英语)这一概念正好体现了这一写作表述。教材出版行业也认同这种(英文)写作表达,并由此发行了大量的写作“手册”,提出了许多关于如何正确运用英文写作的规则。
但是,尽管这是写作课程教授写作的主要方式(通常将这些手册发放给学生),但这并不是教授学生写作的唯一方式。比如,另一种方式是将写作课程作为维系和修正语言的手段来教授写作。具体而言,从跨语言视角看待语言的写作课程可以展现出作者和语言之间不同的关系。这类写作课程不把语言视为作者的写作工具,不要求学生必须按照这些固定规则写作;相反,作者透过写作不断塑造和重塑语言。所以,作者不一定是在“用”英语写作,而是一直透过写作书写(和修正)英语这种语言。
我曾在别处说过,基于递归原则、调解原则和翻译原则的写作课程可以上述形式展现写作、语言以及作者同语言之间的关系(Horner, “WritingLanguage”)。以上原则强调了学生以作者身份在维系和修正自己及其读者关于某一共同、“共通”话题的认识方面付出的具体努力。遵循这些原则的课程通常会有意地给学生设计一系列的任务,使其进行递归写作——这类写作让学生反复处理“相同”的文本或者现象。举个例子,递归写作可能会要求每个学生在学期初针对同一篇文章写出几个不同理解版本;在学期末时,学生正处于一个新的情境——比如在这个过渡期间学生已经有更多的后续阅读和讨论——此时再重读之前的文章并提供一个新的理解——翻译——版本。
这类课程的重点没有完全放在写作技能的培养上——如掌握单词拼写、标点符号、句子结构、文章结构、写作流程、论证的修辞策略等规则。虽然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定会运用到上述内容,但这并不是写作课的重点或者目的。换句话说,学生写作的价值不应在于培养学生把在写作课上学习的技巧运用到其他语境的能力。相反,学生写作的价值在于帮助学生向自己及同学更好地呈现知识。虽然知识的这种呈现形式可能会被引入到其他语境中,但根据这些课程的原则,把这些知识引入到其他语境——比如在其他课程中——会改变这种知识,进而需要根据新的语境或者为了构建新的语境而换一种知识的呈现方式。
通常来讲,人们更加关注知识在这类课程中的呈现形式。知识与知识的语言表达形式之间相互依存,两者间关系也颇受争议;鉴于语言在知识的表达形式中的作用,费尽心思去摸索两者间关系的学生往往尤为重视同时也爱“玩弄”语言。举个例子,在我曾经教过的大学一年级写作课上,学生们深入研究了知识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且为了明确这种关系,他们提出了新的表述方式。换句话说,他们以语言为工具,也以语言为对象,修改了惯用的表述方式,以此来体现知识与语言可能存在的关系。
例如,在下文中一名学生描写了西方历史学家因对夏威夷土著语言的知识匮乏而影响了对夏威夷文化的了解。
历史学家忽视了夏威夷语里的重要细节(使用词缀-a表示事物所有关系,区别于使用词缀-o表示人的内在所有关系),没有清楚地区分知道和以为知道(thinking to know)的差异。事实上,我认为历史学家并不熟悉正宗的夏威夷语,所以导致了信息错误。他们以为自己了解土著人的语言,所以并没有花时间进一步查清夏威夷语中的常见表达如o这个术语的含义。同样地,如果我认为我知道“分子”这个词语,就算我理解错误也不会花时间查明这个词的含义。结果是我会犯错。相反,如果我知道我并不熟知分子这个词语,那么我将会花时间查明并理解这个概念。这项额外的工作让我避免了错误。这正是历史学家忽略的事情。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知识,因而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纠正自己的错误观念。换言之,他们以为自己知道从而对自己的无知视而不见,这比知道自己不知道更加糟糕。②
这位作者就读于美国一所英文授课的大学,但母语并非英语。文中有证据表明这位作者至少对某些英语惯用语的特征不熟悉,比如在词组“blind of their ignorance”(向自己的无知视而不见)中用了介词of,而我偏向于使用“to”(对),我认为把词组“in consequence”(结果是)和“by consequence”(由而)改为“consequently”(因而)或者“as a result”(因此)更地道,以及“avoiding committing a mistake”[避免做错(判断错误)]变成“avoid committing an error”[避免犯错(违反规则)]更地道。随着时间推移,这位作者有可能会修改那些用法从而符合常见的——即地道的——美式英语表达习惯。
尽管如此,这名作者也贡献出了于知识有意义的新的措辞,即作者区分了“以为知道”和“知道不知道”(knowing to not know)。这种动名词形式的词语尽管可能显得有些别扭,但有效地警示了其他人不能措辞为“向自己高傲的无知视而不见”,同时也告诫科学从业者有必要承认当前自身的不足——意识到自己知道的并不(完全)如自己想象的多。然而,事实上,我无法找到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词汇表达来体现这种区别。其他同学也做不到,即便有同学把这两个词汇表达运用到自己的后续写作中阐述“近乎知道”(coming to know)的含义。事实上,含有这两个别扭的词汇表达的习惯用语数不胜数,但这种别扭有助于推动人们重新思考以为知道和知道之间的关系。
我没有想过学生在写作课上创造出来的词汇表达已经或者将要在学习这门课的学生之间或者在这门课程之外传播。而且从传播的广度来看,这样的表达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跨语言角度来看,作者创造了“认为知道”和“知道不知道”这样的词汇表达,这对于作者及作者的同行理解什么才是知道或者近乎知道(以及,具体来说,什么会阻碍人的认知)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作者创作的这些表达也意味着作者建立起了一套作者与语言间不同的联系——在上文中,作者并没有声称英语是他/她的母语——即语言是作者自己劳动的产物,而不是作者必须要遵从的一套规则或者实体。
考虑到作者的母语不是英语,这更加值得注意。但正如Claire Kramsch 所言,很少有学习者意识到他们作为非母语讲话人/行为者对一门语言的存亡、发展、用法和符号使用潜势等方面的影响……尽管学习一门语言会造成语言重心偏离、冲突,并由此带来新发现,但也不失为一种给予学习者自认为缺乏的话语介质的学术手段[“Contrepont”322 (我的翻译)]③。
换句话说,虽然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尤其是书面语言,被视为一种已存在的、学生必须置身其中写作的恒定实体。但是从跨语言视角来看,所有的作者包括那些语言初学者都通过写作在为维系和修正语言贡献力量。
赋予学生这种话语介质的角色以及让他们如同Kramsch那样肩负起一门语言存亡的责任通常会让人担忧学生会因为具备这样的能力而去破坏语言——他们会破坏习以为常的——也就是积淀的——行为。但是这样的担忧也表明我们甚至不够信赖我们可能想要维系的语言行为的效用性,也不够信任学生有兴致也有意愿去维系既存的社会结构,同时还对当前语言实践的无误性表现出令人不安的迷信——认为这门语言已经完美到不需要改变。然而,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的语言实践都表明这样的假定更合乎情理,即当前被视为常见的语言行为确实用法得当,这样的用法诠释了为什么这些语言行为会流传至今以及为什么大多学生和我们一样都希望能够创造新的意义而非破坏其原义。但是创造意义的手段的有效性还取决于语言使用者以及这些意义是否贴合当前的环境。如果这样的语言行为不贴切,正如这名学生作者在上文犯的错误一样,那就应该调整语言行为。
学习这门课的这位学生及他的同学所做的工作充其量被当做一种翻译工作:找词语来解释其他文章——如这些学生阅读过的文章中的词语,然后重新思考阅读的内容并找到两个语境间的关系最终再翻译自己的文字。语内抑或是语际翻译需要费力确定何物会益于达成理解。学生比较“相同”文章的不同理解(翻译)之后,再一次阅读和理解(翻译)该文章,此时的时间场域稍有不同,角度也略有差异,他们将会发现语言不仅仅只是思想的传输通道,他们应该并且必须不断地对语言进行重新加工从而尽全力表达自己的思想。
这样的工作对于学生在写作课上努力尝试的工作有实用价值。这无关乎技能培养,也不在于为其他类别写作铺路。反之,这是真正的作者所做的名副其实的工作,即改写语言。一般而言,语言改写为了达意会借用一些实用性强又用途广泛的积淀语言行为。这也是语言工作。并且,远超出我们想象的是改写意味着改变这些语言行为,无论这种改变多么微不足道(如上文列举的例子)都会带来不一样的含义。
多年来,从事这一工作的著名作者都得到了称颂,但我们可以试着去肯定所有作者在这一工作中的贡献。我们应当学会重视知道不知道的价值,而非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了解语言的本质、知晓学生写作的能力。如此,我们才能认识到学生每天通过写作为维系和修正语言所做的努力。
作者简介
布鲁斯·霍纳(Bruce Horner)路易斯维尔大学(University of Louisville)的修辞写作专业客座教授 (Endowed Chair in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教授写作和写作理论以及教学法。其最近的专著包括RewritingComposition:TermsofExchange(2016),EconomiesofWriting:RevaluationsinRhetoricandComposition(与 Brice Nordquist and Susan Ryan 合编,2017),CrossingDivides:ExploringTranslingualWritingPedagogiesandPrograms(与Laura Tetrault 合编 2017), 及RewritingEnglishinRhetoricandComposition:GlobalInterrogations,LocalInterventions(与 Karen Kopelson 合编,2014)。
注释
① 参阅Bawarshi et al.; Canagarajah,Translingual; Canagarajah,Literacy; Horner, Lu, Royster, and Trimbur; Horner, Donahue, and NeCamp; Horner and Lu, 《写作与修辞研究的跨语言方法》,《当代修辞学》2016年第5期; Horner and Tetrault,Crossing; Lu and Horner, “Translingual”; Pennycook.
② 除方括号内容外,文章中引用学生论文的部分与学生的提交稿保持一致。该学生同意以匿名方式使用该文章。
③ “Peud’ apprenantsont conscience du rlequ’ilsjouententant que locateurs/acteurs non-natifs sur la vie ou la mort d’une langue, son développement, son usage, son potentielsémiotique …. L’apprentissaged’une langue étrangere, avec tout cequ’elleapporte de décentration, de conflit et de découvertes, estune des matieresscolaires les plus propices a … redonner aux apprenants la puissance d’agir discursive dontilspensentmanqu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