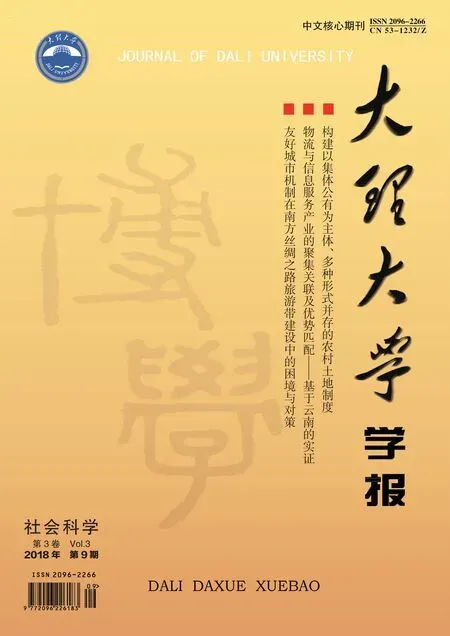先秦名家公孙龙“名实论”考辩
2018-04-11赵映香杨正华
赵映香,杨正华
(大理大学,云南大理 671003)
一、公孙龙学说的思想史背景和前景简介
“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1〕28。具体来说,公孙龙是战国时的赵国人,曾经做过平原君赵胜的门客多年,“公孙龙,赵平原君之客也”〔1〕34,活动于约公元前284至259年间,是当时名家重要人物之一。
公孙龙的学说主要集中在其遗存于今的六篇文章里,这六篇文章为:《迹府》《白马论》《坚白论》《通变论》《指物论》《名实论》,“窃疑此六篇中,《迹府》为后人序录,羼入正篇。”〔2〕521
名家学说曾在先秦时期非常流行,但到秦汉统一时就亡绝了。东晋鲁胜曾指出:“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馀岁,遂亡绝。”〔3〕210名家思想大都注重“‘循名责实’‘综核名实’”〔2〕1的方法。名家派别林立,惠施和公孙龙归属于“名辩”派,是其代表人物。这一派主要研究“‘正名’‘析辞’‘立说’‘明辩’的规律和有关问题”〔2〕2,在名家各派中影响最大,连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都兼修其派之学说。不过,惠施和公孙龙虽是这一派的代表,但其学说要晚于兼修其说的各家,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东晋鲁胜所著的《墨辩注》原叙中可窥一斑,“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3〕210。
名家学说成为绝学,其原因肯定是很复杂的。伍非百先生指出了两个原因:第一,“这些书所以散亡,理论太专门,太艰深难懂”〔2〕7,这第一因东晋鲁胜也有提到:“率颇难知……遂亡绝。”伍先生的弟子蒙默也道出了学习名家思想的艰难,“师自校勘、训诂、及于其意义,逐家逐句详于讲解,惜我诸生基础太差,不堪承担,不仅不克领会其深意,即欲粗知其旨,亦感吃力……此讲疑为伍师对诸生接受能力之试探,或即有鉴于此,此后未再续讲”〔2〕3-4。第二,伍先生认为其最大原因是受到政治因素干预,“因为名家综核名实,观察太精密,议论太锋锐,虚则虚,实则实,真真伪伪,丝毫不容假借。专制皇帝最怕他们明辨是非,揭露本质,动摇人心。一批所谓正统的学者,也怕他们甚于洪水猛兽。专制皇帝用牢狱、捕快、刀锯、鼎镬对待他们,而所谓正统学者在辩论真理方面,敌他们不过,就利用帝王的权威,以刑罚禁锢把这派思想扼杀。因此,名家书籍,亡绝得最早最速了”〔2〕7。
伍先生同时指出,名家书籍也并非全部亡绝,因为间接的、兼业的名家篇籍仍然流传至今,其得以保存至今日者,全靠它们与兼业名家的书众篇连在一起,假如单行,也就可能在秦汉时就亡绝了〔2〕7-8。鲁胜也曾指出:“《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3〕210鲁胜本希望“兴微继绝者”〔3〕210,可没想到他的注也失传了。
二、公孙龙学说研究概述
对公孙龙及其学说,从古至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相反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对公孙龙及其思想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公孙龙之学,先贤或以‘辟言’(荀况)、‘诡辞’(杨雄)相讥,近人亦以‘帮闲’(郭沫若)、‘诡辩’(侯外庐)置议。”〔1〕7黄克剑认为“‘白马非马’可谓诡谲之谈”〔1〕8。有些日本学者也认为,“与墨家并列的公孙龙等名家,玩弄了许多诡谲”,比如日本学者加地伸行指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等论点,至今仍被作为诡辩。在日本高等学校的习题汇编中,列有‘以下的语句是命题吗?’的问题,其中包括‘白马非马’的语句。而答案就特意说明这个语句是假的”〔4〕。无独有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卷中也有类似的考题:“白马非马”的错误在于割裂了什么?而答案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对公孙龙及其学说,也有一些与以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正面看法和评价。1932年,伍非百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名家者言》(今名为《中国古名家言》)一书中指出:“‘名家’之学,始于邓析,成于别墨,盛于庄周、惠施、公孙龙及荀卿,前后历二百年,蔚然成为大观,在先秦诸子学术中放一异彩,与印度的‘因明’、希腊的‘逻辑’,鼎立为三。”〔2〕31956年,谭戒甫先生在其《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中指出:“一九三五年,我的墨经易解出版,那里面有好些地方也曾提出名家和形名家所对争的论题。如果说不是二家对争,问题就不能解决;若作为对争,就觉得文从字顺,不烦牵扯了。这是事实,但学者们好像是一直没有谁引起多大的注意。不过,他们既没有表示承认,也很少有人提出过驳议,这是使我要怀疑的地方。”〔5〕4谭先生接着指出:“形名学说是战国百家里面的一派,它在当时确实掀起过相当大的波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批判。现在我希望并请求哲学家们,不吝赐教地来重新确定它的地位,并且重新估量它的价值,使我们的这份哲学遗产更加得到重视,也不使我白费这点力气。”〔5〕4冯友兰先生也指出:“过去这些观点都被看作‘反论’,但我们一旦知道了惠施和公孙龙的基本思想,就可以懂得,这些其实并非‘反论’。”〔6〕另外,祁润兴教授也指出:先秦名家们“比较自觉地探讨名称与事实的意义问题以及名称与名称的逻辑关系,在理论思维上有一定的超前性,因而长期被误解,甚至被贬斥为‘诡辩学派’,充满‘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7〕。
三、“名实论”考辩
本文虽然以考辩公孙龙的“名实论”为主,但也难免会涉及到其余各篇以及《墨经》中的名实思想。这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伍非百先生指出,公孙龙各篇“辞致一贯,枝叶根干,交相扶疏”,“大抵《白马》《坚白》为具体之论证,《指物》《通变》则抽象的说明”,《名实》则又是后两篇的“根本”,“明此一论,则一切正诡之论,皆可迎刃而解”〔2〕525。另一方面,公孙龙“祖述”前学,其名学特别与墨子的名学息息相关,二人之间既有高度一致的地方,又有相互对争或敌对的地方。关于后者,伍非百先生也曾指出:“公孙龙子之书,处处与墨子《辩经》为论敌,这是中国古代名家两大论宗。不懂《公孙龙子》,就不能读《墨经》,不懂《墨经》,也无法了解《公孙龙子》。所以研究这两家的书,应当相辅而行,才会相悦以解。”〔2〕12
(一)何谓“名”和“实”
1.何谓“名”
公孙龙所说的“名”是称谓“实”的名称或词语。他在《名实论》中说到:“夫名,实谓也。”〔1〕87《墨经》的《经说上》第八十一条也指出:“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3〕61大意为:名是用来称谓实的词语,实是被名称谓的物或对象。公孙龙在“名实论”中,用“彼”名和“此”名分别指称彼之实和此之实〔1〕86-87。而其《指物论》中的“物莫非指”的“指”就是通常所说的“能指”,即指认物的名。在其余各篇中,公孙龙提及的“名”是一些类名,比如“石”“坚”“白”“马”等等。
公孙龙对“名”没有进行分门别类的探讨,所以其“名”显得有些笼统和模糊。但较之公孙龙,墨子在《墨经》中对“名”的探讨就相对清晰和明确。比如《经上》第七十九条云:“名,达、类、私。”〔3〕58大意为:名,依外延大小可分为达名、类名和私名三种。《经说上》第七十九条接着作了解释和例示:“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3〕528大意为:物是达名即通名,凡实物必须用“物”这个达名来命它。“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声出口,俱有名,若姓字丽。”〔3〕58大意为:马是类名,这样的实物必须用“马”来命它。臧是私名,这个名只能命这个人。名与出口的声相丽,犹如姓与字相丽。
尽管墨子对“名”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对其探讨和分类仍不够明确和到位。因为一方面,墨子所说的“达”和“类”属于意指个别对象的类的普遍词,二者只是普遍性和抽象性程度不同而已,“私”则属于意指个别对象的个别词。另一方面,名家对“达、类、私”“指”“名”“实”等本身又该属于什么名或范畴,则没有自觉的、专门的探讨。关于后者,徐长福教授作了创造性的、自觉的、专门的探讨。徐教授把这些高阶的词归属于“范畴词”——表范畴意义的普遍词〔8〕254-257,“范畴意义指的是语言使用的各种类型,亦即范畴”〔9〕。
名家所说的“物”也称为“形体”,所以“形名家”是名家的别名,“‘名家’与‘形名家’乃异名而同实之称”〔2〕2。如果我们说“形体是物质的实体”,“实体是自立的事物”〔8〕19,那么名家就只是攀登到了“形体”这一台阶,即他们只是专门地探讨了“物类”——“‘形体’及其以下的属种”,而没有专门或专题地探讨“辞类”——“‘实体’及其以上的类”〔8〕199。
2.何谓“实”
前文论述“名”时对“实”已经有所涉及,在这里再作一点补充。公孙龙及其他名家所说的“实”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名或符号无涉的天地间实存着的“物”;一层是通过名或符号涉入而得以被指谓的“物”。“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1〕84这里的“物”就是第一层意义上的“实”。“物莫非指,而指非指。”〔1〕76这句话中的前两个“指”为“能指”,即“名”,后一“指”和“物”为“所指”,即第二层意义上的“实”。总之,“物为实之所依,实为名之所起”〔2〕527。
(二)正名实之缘由和方法
1.正名实之缘由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0〕墨家又为何要正名实呢。《小取》开篇就点明了名辩学的目的和作用,“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3〕196。公孙龙“祖述其学”,仍以厘正名实关系为己任,因“疾名实之散乱”,“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1〕28,30。有鉴于此,东晋鲁胜总结了名家正名实的缘由,“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3〕210。
公孙龙举例说明了当时“名实散乱”、充满“悖言乱辞”的情况。第一个例子是:孔穿(孔子的六世孙)想拜公孙龙为师,但惟独不赞同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所以请求公孙龙去此术,然后孔穿请为弟子。但公孙龙认为他之所以为名者是因为有其论,如果去之,则没有可教的东西,言外之意就是这样做将使他陷入有师名而无师实的境地。而且他认为孔穿之言既悖谬又会使孔穿也陷入有名无实的境地,因为公孙龙认为孔穿的先辈孔子是认可他的“白马论”的,当年楚王打猎时丢了弓,随从于是请求把弓找回来,楚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1〕31孔子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1〕31另外,孔穿“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1〕31,说明他有儒家之名而无儒学之实。
在这里可以帮其理顺此例。此例可以先简化为两个一阶主谓句:“公孙龙是老师”,“孔穿是儒家”。“公孙龙”和“孔穿”分属于“个别词”范畴,“老师”和“儒家”分属于“普遍实在词”范畴,“由于分属异质性范畴的词语之间缺乏比较和通约的共同标准,不能相互还原,因而其间结合的恰当性只能靠直观认定而不能靠逻辑推定”〔8〕224。据此,首先看主词“公孙龙”和“孔穿”所意指的对象是否存在,若存在就说明主词确有所指;其次看谓词“老师”和“儒家”所意指的种类在主词所意指的对象身上是否有先前例示而来的意义对应物,若有就说明述谓属实、指谓连接正确,反之就不属实、不正确。从公孙龙和孔穿对话的语境看,“公孙龙”和“孔穿”确有所指,但公孙龙指出,按照孔穿之言,“老师”对“公孙龙”,以及“儒家”对“孔穿”的述谓将导致不属实、不正确。因为在他看来,老师是有学识的人,儒家是修儒学的人,但如果依孔穿所言,公孙龙和孔穿身上将失去老师和儒家分别所内涵的“有学识”和“修儒学”的意义,最终将导致指谓连接不属实。
第二个例子是:齐湣王当年很喜好士,但不知所谓士。当时的名家尹文说:“今有人于此,事君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乡则顺。有此四行,可谓士乎?”〔1〕34齐王回答说这就是他所说的士。尹文接着追问,如果这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受辱而不敢斗或反抗,齐王是否将继续认为他是士并作为臣子。齐王认为受辱而不敢斗不是士。尹文认为虽然这个人受辱而不敢斗,但却没有丧失其之所以为士的四行,所以齐王一会儿说他是士,一会儿说不是士,显然其言是悖的,而且他之所以受辱而不敢斗,是为了保全齐国的法令:“杀人者死,伤人者刑”〔1〕34-35。齐王这是在对有功之士加以非士非臣的惩罚,这样一来,“赏、罚、是、非,相与四谬,虽十黄帝,不能理也”〔1〕35。公孙龙认为孔穿之言犹齐王“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类”〔1〕35。对此例的分析与上例相同,在此就不再赘述。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指谓关系的视角看,齐湣王和尹文没有意识到任何一个主词在理论上都有无数的偶性谓词,这也是他们后来争论和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他们一开始是相互认同“士”有四个偶性谓词的,但随着“士”的新的偶性谓词“勇敢的”“服从的”等的出现,他们开始争论某人是否还是“士”。当然,每一主词的偶性谓词数量虽然是无限的,但每一理论根据其特定原则所关注到的偶性谓词是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尹文对齐湣王的“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类”的指控还是成立的。
2.正名实之方法
公孙龙在“名实论”中指出:“夫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1〕85意思是说,正的目的在于正其实,如何正实,在于正其名。因为实不能正也不必正,关于这一点,伍非百先生作了详解:“盖实不可正,方圆大小属诸形,轻重长短属诸量,多寡丰啬属诸度,分合同异属诸剂。黄马黑马,坚石白石,望形可知,察色可睹,虽有巧辩,莫之易也。方圆既陈,岂因言辞而异状?黑白并列,不以辩说而殊色。服人之口,淆人之意,端在语言文字之间,其于实也无与。故实不可正,不能正,亦不必正。而正实者,惟在正其名而已矣”〔2〕530。
如何正名,“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其以当不当也。不当而当,乱也”〔1〕86。大意为:所谓名正,就在于彼名符合彼实,此名符合此实。如果称某事物为“彼”,而“彼”与以“彼”相称的事物之实不相应,那么“彼”这个名就是不符实的;同理,如果称某事物为“此”,而“此”与以“此”相称的事物之实不相应,那么“此”这个名就是不符实的。这是由于充当名的“彼”“此”不恰当。以不恰当的“彼”或“此”充当名,名与实的关系就乱了。“故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其以当而当也。以当而当,正也。”〔1〕86
在此举一阶主谓的一个例子简要地来说明其意。比如在一阶主谓“公孙龙是智慧的人”中,显然,从“公孙龙”这个词是推不出其必定是“人”的,因为,一方面,它可以被同名异义地使用,即它既可以是人类中的个体的名,也可以是其他类中的个别事物的名;另一方面,“人”是普遍实在词,它和作为个别词的“公孙龙”分属不同的范畴,所以二者之间是异质的,不可通约的,其间的连接不能靠逻辑推定,只能通过直观认定。首先看“公孙龙”所指的对象是否存在,若存在,再看“公孙龙”所指代的个别对象身上有没有先前例示而来的“人”所指的人这个属的“图像或图式”〔8〕234-236的意义对应物,若有就说明述谓属实、指谓连接正确,反之就不属实、不正确〔11〕。
从“公孙龙”这个词也是推不出其必定是“智慧的”,“智慧的”是偶性实在词,与个别词“公孙龙”是异质性的关系,所以二者之间的连接是否恰当也需要直观认定。首先看主词“公孙龙”所意指的对象是否存在或是否真有所指,若有或存在,再看谓词“智慧的”所指的实在偶性属在主词“公孙龙”所指的那个对象身上是否有意义对应物,如果有,那么谓词“智慧的”对主词“公孙龙”的述谓就是属实的,反之,就是不属实的。总之,凡分属异质性范畴的词语间的结合的恰当性只能靠直观认定而不能靠逻辑推定,而直观认定的具体做法就是“循名责实”。
公孙龙接着指出:“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1〕86大意为:因此,称彼为“彼”而仅限于彼,称此为“此”而仅限于此,是可行的。如果称彼为“此”,则“彼”既是彼又是此,称此为“彼”,则“此”既是“此”又是“彼”,是不可行的,因为那样就名实混乱了。其实这段话是对《墨辩》的《经说下》第六十八条的一个改写,《经上》云:“彼此,彼此,与彼此同。说在异”〔2〕188。大意是:彼名对应彼实,此名对应此实,理由在于彼实和此实是相异的或不同的。《经下》云:“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此且彼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此彼彼也,则彼亦且此此也。”〔1〕188
综上,公孙龙因“疾名实之散乱”,故把“名实论”等论辩推行开去,以“审其名实,慎其所谓”〔1〕88为理论旨归。
需要说明的是,公孙龙及其他名家的思想还处于萌芽阶段,正如笔者在文中指出的那样,公孙龙及其他名家都没有专门地、自觉地、有意识地探讨他们经常使用的那些名或词,如“孔穿”“尹文”“臧”,“坚”“白”,“石”“马”“物”,“彼”“此”“名”“实”“指”“谓”“达”“类”“私”等词又应分别属于什么范畴的问题,也就是说,名家只探讨了“物类”,而没有专门地探讨“辞类”,也就更谈不上探讨高阶主谓及判定其品质的方法〔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