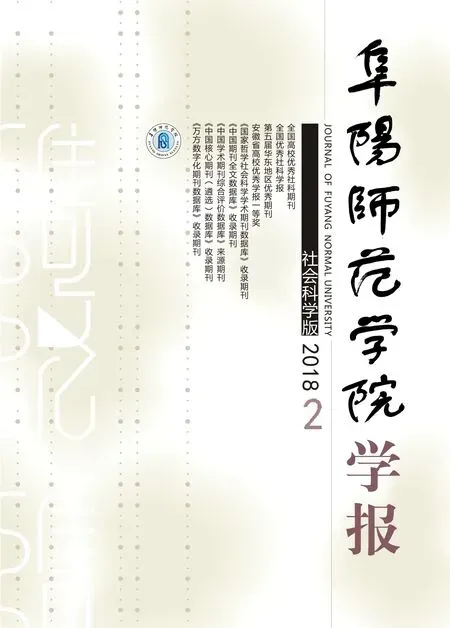徽商与明清徽州社会结构的变动
2018-04-03徐腾飞
徐腾飞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对于明清徽州传统社会变迁,特别是徽商对于明清徽州社会变迁的影响,学界多有研究成果,相关研究专著也颇多论及。如李琳琦从教育角度认为明清徽商的兴盛促进了徽州科举业的发达,直接或者间接地推动了徽州文化的繁荣[1];胡中生在人文精神方面肯定了徽商对于明清徽州社会稳定和人际关系和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2];卞利、何建木、谢超峰等也从乡村社会、区域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就徽商对于明清徽州社会的影响做了深入的研究[3-8]。可以说,明清徽商的繁荣使得徽州传统社会结构受到冲击,出现了一些变动。然而,这些新变化并未引起徽州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徽州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鉴于此,本文拟分析徽商的崛起对于明清徽州传统社会结构变动的影响,以期对明清徽州社会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新变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
一、徽商与明清徽州经济结构的变动
大体而言,在整个明清时期以商帮形式存在的徽商呈现繁荣局面,徽商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徽州本土传统经济结构的变动,主要表现为明清徽州从商人口比重的增加及徽州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明清徽州从商风气盛行,从商人数众多,甚至于超过农业人口比重。明清以前,徽州人社会生产活动以农耕为主,百姓日常生活遵循“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读曰耕”,躬耕农桑在自给自足的徽州传统自然经济结构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到了明清时期,徽州从商风气大盛,更多的徽州人选择外出经商,万历《歙志》对此描述道:“长老称说,成弘以前,民间稚朴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厚让,崇节俭。而今则……流域五方,轻本重末。”[9]1086徽商的快速崛起促进了徽州本土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徽州人口向商业流动,商人数量迅速增加,从事商业的人口比重甚至超过了农业人口。据记载,早在明代中叶,休宁、歙县以及祁门等地从事农商的人口比例就已是“十三本业,十七化居”[10]393了,汪道昆谈及当时徽州人“业贾者什七八”[10]12。王世贞在谈及徽州人热衷经商时,也涉及到了徽州经商人数的多少:“新安僻居山溪中,土地小狭,民人众,世不中兵革,故其齿日益繁,地瘠薄,不给于耕,故其俗纤俭习事。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11]631晚清时期,徽州从事商业的人数依然可观,同治《祁门县志》载:“(祁门)人性椎鲁,农者十之三……他则行贾四方,恃子钱为恒产。”[12]59从上述史料可以大致看出,明清时期徽人从商,差不多已经达到十居其七的地步,基本上可以称得上是全邑从商了,人数不可谓不多。即使上述史料可能有部分夸大的可能,但是明清徽州从商人数众多,商业人口比重超出农业人口也大体可以确定。可见,明清时期,徽州人“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13]680,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重较之于明清以前已经大幅下降,经商事贾已经是当时徽州人最重要的职业选择之一。
明清徽商的繁荣,还带动了以茶、木生产为代表的徽州本土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改变了徽州传统农业生产的面貌,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徽州的自然经济,带动了徽州本土商业的发展。关于茶业,徽州地处皖南山区,自然环境极其适合茶树生长,是著名的产茶区。明清以前,徽州已有茶叶贸易,《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载:“邑山多而田少……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踵而至。”[14]3733明清时期,随着徽商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徽州茶叶生产更为兴盛,种类繁多,明代徽茶以松萝、大方茶和屯绿著名,徽茶于清代进入鼎盛时代后,以红茶与绿茶并重,品类繁多,有安茶、祁门红茶、毛峰、白岳黄芽、石墨茶、屯溪绿茶、花茶以及太平猴魁等著名茶叶品类,徽州茶商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设茶号,徽茶产销更为旺盛,并开始远销国外。同时,徽茶的崛起也带动了徽州本土茶业的繁荣,茶树种植变得更为广泛,所出产的大量茶叶被徽商收购,为明清徽商茶业经营提供了大量优质且多样的货源。相应的,茶叶也成为徽州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作物,成为当时徽州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经济来源,“山郡贫瘠,恃此灌输,茶叶兴衰,实为全郡所系”[15]172-173。光绪《婺源乡土志·风俗》中也称:“我婺物产,茶为大宗……农民依茶而活。”[16]28可见,明清时期徽州茶叶商品化已达到较高水平。除茶业外,林业也成为明清徽州商品化较高的行业,在缺少田地的徽州,极利于林业的发展,林木生产是徽州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时,徽州就已有木材经营出现,罗愿所撰《新安志·风俗》中记载:休宁县“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淛河,往者多取富。女子始生,则为植檆,比嫁斩卖,以供百用”[17]17。到了明清时期,徽州木业更为兴盛,木业亦成为徽商四大支柱性产业之一,也使得徽州本土林木生产与商品经济联系开始紧密起来,林木经济的活跃使得徽州林业的商品化程度也大为提高。明清徽商在徽州林木生产中,一方面直接收购徽州本土的林木,直接将徽州林木贩卖出去;一方面则购置山地林场,直接经营林业,因为在经营过程中必然使用一定的雇佣劳动,又带动了徽州社会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可见,以茶、木为代表的农业商品性的提高,冲击、瓦解着徽州传统的自然经济,改变了徽州传统农业的面貌。此外,徽州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不仅为徽商提供了大量优质的商品,也为徽州本地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原材料,促进了徽州本土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和城镇的兴起与发展。
二、徽商与明清徽州政治结构的变动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政治结构“呈现出国家法定的正式组织即乡都、里(图)甲、保甲、乡约等和非正式组织宗族、会社等互相结合的态势”[18]66-74。徽商对于明清徽州政治结构变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徽商对徽州社会非正式组织为代表的基层权力的入侵上,即通过资助家乡公益事业以谋求更大社会影响或热衷捐纳以求得官爵等方式,大量跻身于徽州士绅阶层,增加自身在徽州地方上的政治话语权,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徽州地方社会。
明清徽商往往“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从而形成了‘贾而好儒’的重要特色”[19]381。这使得徽商不同于明清时期其他商人,诸多徽商热衷于通过捐纳、捐输等途径获得官爵,进入士绅阶层之中,致使徽州本地士绅阶级出现一些新变化,许承尧曾对此论述道:“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人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朊仕者,更未易仆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20]603明清徽商多“商而兼士”,说明部分徽商已经具有了“商人”和“士绅”两重身份,这是明景泰年间捐纳制度合法化后新出现的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士绅群体。这种新的具有商人色彩的士绅群体,不同于徽州传统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士人和商人,而是表现为商绅身份集于一身。对于明清徽商来说,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身份由商人转变为士绅,捐纳或捐输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也被当时的封建政府所承认。但是,徽商通过捐纳或者捐输,也仅仅只是获得了士绅的身份,他们必须通过积极参与徽州地方公共事务,方能树立自己在家乡的声誉与威信,从而渗透或掌握徽州地方政治权力,影响徽州社会。例如:祁门商人李秀,“作贾真州,多赀,每以济人为乐。尝建宗祠,置祭田,族人德之”[12]341。清代,婺源沱川人余增孝,“壮游岭南,不遇而归。授徒数十年,勤功课,族中列庠序、登贤书者多沐其蒙养。祖规禁赌博,孝总司其事,不辞劳怨,顽梗多折服焉”[21]1831。婺源汜川人余德基,“家稍裕,即为村栽树植竹以开财源,禁赌养生以培元气,豪强犯禁,诣县请示,不避怨劳”[21]1570。婺源诗春人施明礼,“少孤贫,后商于景镇,赀裕归里……闻村妇有溺女者,给赀养育”[13]1554等等。
由上述文献记载可见,这种由徽商捐纳或者捐输方式产生的新的士绅群体,他们往往利用自身经商积攒的财富和影响力,在徽州地方社会中积极从事兴学助教、兴办文会、济困救贫、严禁赌博、禁止溺女、培山育林、筑路修桥、平息诉讼、教授生徒、赡养节妇、修建祠堂、增置祀产等社会公益与慈善活动。徽州人对他们作出了诸如“允协乡评”“宗族称道弗衰”“族党称之”“族党至今道之”“族人称其义”“族党均以廉能称之”等高度评价,表明他们的行为获得了徽州地方社会的好评,此外这部分徽商还作为代表与徽州地方官府打交道,这些都体现出徽商对徽州本土社会的重要影响力。可见,这部分徽商或攫取宗族权力或与地方官府交往甚密,已经或多或少地掌握了明清徽州社会的话语权,也拥有了影响徽州地方权力的能力。这是徽商影响徽州基层社会政治结构变动的一种表征,表明徽商在客观上影响了徽州地方政治结构的变动。
三、徽商与明清徽州文化结构的变动
经济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徽州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极具典型性。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徽商在经济上的成功反过来又在各方面影响着徽州的文化发展,从而造就了明清时代徽州文化的昌盛。
在物质文化方面,徽州文化被烙上了浓厚的徽商色彩。明清时期,在徽商雄厚财力的支持下,在徽州教育、新安理学、新安画派、徽州刻书、徽派建筑、新安医学,以及徽剧、徽菜等,几乎各个文化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有的领域臻于极致,后世难以企及,其水平之高,人所共知。如:徽商重视教育,大力资助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函置塾学、广设义学、倡建书院、兴办文会等等。如:明徽商“佘文义,字邦直。……少贫,操奇赢,辛勤起家,性不好华靡,布袍游名卿大贾间,泊如也。置义田、义屋、义塾、义冢以赡族济贫,所费万缗”[15]457。同为祁门人的“胡天禄,字慕峰,祁门胡村人。幼贫而孝,后操奇赢家遂丰。先是族人失火焚居,天禄概为新之。又捐金定址建第宇于城中,与其同祖者居焉。又输田三百亩为义田,使蒸尝无缺,塾教有赖,学成有资”[15]305。徽州教育的发达离不开徽商物质上的支持,在以佘文义、胡天禄为代表的徽商群体的支持下,明清徽州教育呈现繁荣景象,科举登第者人数众多。徽派建筑的出现也直接得益于徽商雄厚的资本。徽州商人经商致富后,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或为安度晚年或为后世子孙计或为夸耀乡里等,不惜花费巨资在家乡大兴土木,各种建筑鳞次栉比。在徽商大量资金的支持下,明清徽派建筑更为艺术化,平面布局规整和谐,空间结构设计合理美观,装饰协调自然,村镇规划构思巧妙,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新安医学也得益于明清徽商的兴盛而广为流行。徽商在经济上的支持促进了新安医学的发展与繁荣。如明代歙人吴勉学,曾以白银十万两为资本,毕其一生从事出版事业,他所校刊的经史子集及医书达数百种之多,并于万历二十九年校刊了王肯堂《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215卷,对新安医学的传播与发展贡献颇大。可以说,明清徽商经营成功所获取的巨大利润为徽州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也为徽州文化烙上了浓厚的徽商色彩。
在精神文化方面,主要体现在徽商的人文精神对徽州人思想观念的影响上。一方面,体现为重视商业的思想冲击了徽州社会。上文提到,徽州号称“程朱故里”,明清以前,“民间稚朴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厚让,崇节俭”[9]1086。徽州人普遍崇尚“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读曰耕”,对经商不甚重视。到了明清时期,徽商经营取得的巨大成功深刻影响了徽州人的思想观念,重商思想在徽州社会得到普及。徽州人对从商的整体认知也出现了明显改观,经商业贾成为了当时徽州人较为普遍的职业出路。徽州人对商人的印象也从以前的商为四民之末转变为“士商异术而同志”[20]440,商人的社会形象得到了明显改观,认为“四民”只是谋生手段有所不同,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休宁宣仁王氏族谱》中就提及:“士农工商,所业虽别,是皆本职,惰则职隳,勤则职修。父母妻子仰给于内,姻里九族观望于外,系非轻也。”更有甚者,明弘治、正德年间歙县一商人教育其子时说:“余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若于耕也。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10]952可见,早在明代,重视商业的思想在徽州民间就已经深入人心,影响广泛。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徽商良好的商业道德对于明清徽州风气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徽州被称为“文献之邦”“礼让之国”,儒家道德思想在徽州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此社会氛围内成长起来的徽商普遍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戴震曾说:“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虽为贾者,咸近士风。”[22]257部分徽商所表现出的重视诚信、以义为利等良好道德风尚和顽强拼搏、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充实了徽州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极大地丰富了徽州文化的精神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对明清徽州文化的繁荣以及徽州社会的和谐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结语
徽商从明成化年间兴起,至嘉靖、万历时达到繁盛,在清代又有一个大的发展,执商界之牛耳达数百年之久。长期繁荣的徽商对于徽州本土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对当时徽州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都产生了冲击,引起了明清徽州社会结构的变动。但应注意的是尽管如此,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徽州传统的社会结构。其原因与明清徽商自身的封建性有极大的关系,明清徽商经过艰辛的经营,虽然获得了大量的商业利润,却依然摆脱不了封建的社会思维模式,除将一部分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以及转化为产业资本之外,大部分的商业资本“变成了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封建的政治经济特权,以及消耗于奢侈性的生活消费、强固宗法制度和封建的慈善事业诸方面。这反映了徽商商业利润封建化及其强化封建经济结构的消极倾向”[19]441。相比于经商徽商的兴趣更热衷于购买田地,捐纳官爵,想方设法挤入到封建官僚地主阶层中去,完成从商人到士绅社会身份的转变。徽商还利用其生产经营活动及所获得的大量财富,用于强固封建宗法关系,这就使得徽州封建保守的社会结构更为牢固。可见,不论徽商是对徽州封建宗法势力的支持,还是对于士绅身份的热烈追求,都使得徽商的封建性质显得十分明显,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徽商虽导致明清徽州社会结构发生些许变化,但却无力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的社会结构,甚至于反过来强化了徽州传统社会结构,使得徽州社会显得更为稳定和保守。
总上,在明清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社会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徽州的社会结构虽受到徽商繁荣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和冲击,但总体而言,并没有突破传统社会结构的固有状态。
参考文献:
[1]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科举业的发达[N].光明日报,2008-01-01(3).
[2]胡中生.徽商的人文精神与明清徽州社会[J].安徽大学学报,2009(7):113-118.
[3]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4]卞利.变迁、结构与转型:明清徽州的乡村社会[J].理论建设,2015(5):66-74.
[5]何建木.商人、商业与区域社会变迁——以清民国的婺源为中心[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6]谢超峰.明清徽商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向互动[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4):32-36.
[7]张海鹏.徽商与徽州文化[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4):24-32.
[8]章新芬.明清时期徽商与徽州农业互动影响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6.
[9]谢陛.歙志[Z].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
[10]汪道昆.太函集[M].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4.
[11]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Z].明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刊本.
[12]周溶,汪韵珊.祁门县志[M]∥中国地方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5册.影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3]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灵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4]全唐文[M].董诰,等,编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5]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16]董钟琪,汪廷璋.婺源乡土志:风俗[Z].清光绪三十四年复印本.
[17]罗愿.新安志[M].合肥:黄山书社,2008。
[18]卞利.变迁、结构与转型:明清徽州的乡村社会[J].理论建设,2015(5).
[19]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20]许承尧.歙事闲谭[M].合肥:黄山书社,2001.
[21]江峰青.婺源县志[Z].民国九年刊本.
[22]戴震.戴震集[M].汤志钧,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