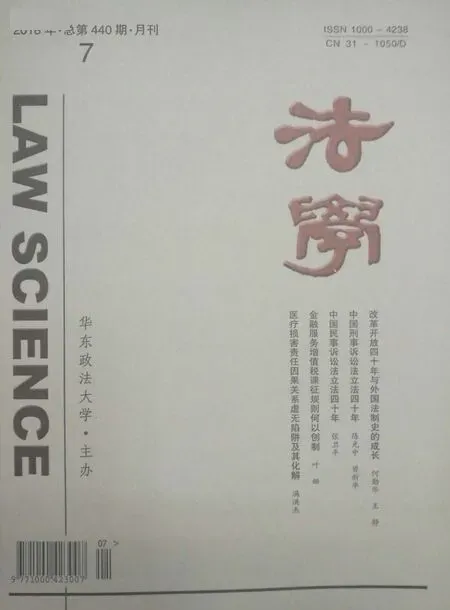医疗损害责任因果关系虚无陷阱及其化解
——兼评法释〔2017〕20号第12条
2018-04-03满洪杰
●满洪杰
一、问题的提出:基于相关实证数据的比较
2017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20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1条规定,“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属于可以申请医疗损害鉴定的事项。其第12条进一步明确了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中原因力大小的表述要求。该规定的意旨在于,“根据原因力的基本法理,从人民法院裁判案件的角度对医疗损害责任中诊疗行为与患者自身疾病等其他造成患者损害的原因之间的原因力大小区分了六种情形予以规定,从而规范鉴定意见对原因力问题的写法,以便法院更准确地确定当事人之间的责任”。〔1〕沈德咏、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224页。然而,笔者通过分析发现,当前司法实践中医疗损害责任案件裁判广泛存在因对“原因力”的错误适用而导致的因果关系虚无现象,而《解释》第12条将会进一步固化和扩大此种倾向,颠覆医疗损害责任构成法理,有碍立法目标的实现,应予纠正。
对于我国医疗侵权责任案件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学界认为“如果侵权行为造成损害的可能很小,则受害人的请求会被驳回;但如若侵权行为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很大,则受害人的请求会被完全支持”,〔2〕杨垠红:《丧失生存机会侵权中比例责任之适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即通过证明标准判断因果关系之“全有”或“全无”。但事实是否如此不无疑问。笔者委托“法合实验室”对“中国裁判文书网” 公布的 2014年至2016年医疗损害责任案件裁判文书进行检索,共获得判决书14 302件。其中,医疗机构的责任承担情况如下:承担全部责任的为435件,占比3.04%;承担部分责任的为11 154件,占比77.99%;不承担责任的为2 389件,占比16.70%;承担补偿责任的为324件,占比2.27%。从相关统计数据看,各年度裁判结果占比保持稳定,且均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医疗机构承担部分责任的占比近八成,远高于医疗机构承担全部责任和不承担责任的情形。二是原告胜诉比例极高。如将医疗机构承担全部责任、承担部分责任以及承担补偿责任均计为患者胜诉,则三者总计占比82.30%。
而根据美国全国州法院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State Court)于2011年发布的关于州法院医疗过失诉讼的统计报告,2005年美国各州法院共审理医疗过失案件2 449件,其中原告胜诉率仅为23%,而同期其他人身伤害案件中原告胜诉率则为59%。〔3〕See Cynthia G.Lee, Robert C.LaFountain, Medical Malpractice Litigation in State Courts,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Vol.18, No.1, April 2011,http://www.courtstatistics.org,2018年2月5日访问。该报告系基于2005年州法院民事诉讼普查所作出。
为进一步验证前述结论,笔者选取北京市中心城区某基层法院相关裁判文书进行了调查分析。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并获取该院2016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判决书共48件。其中,由医疗机构承担全部责任的为3件,占比6.25%;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的为6件,占比12.50%;医疗机构承担部分责任的为39件,占比81.25%,且其承担责任的比例从10%到90%不等。〔4〕有3起案件存在两个被告医疗机构,其中一个承担责任,另一个不承担责任,本次统计将其归入承担责任的案件。患者胜诉率总计为87.50%,与前述统计结果基本相当。
在该基层法院判决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的6起案件中,有4起案件系因患者不申请鉴定或者不预缴鉴定费,〔5〕参见“周学锋诉北京积水潭医院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6813号民事判决书;“廖旭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案”,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2415号民事判决书;“赵爱民诉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西城区平安医院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5982号民事判决书;“赵某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5515号民事判决书。仅有2起案件系鉴定无法确认因果关系。〔6〕包括按摩治疗与患者骨折之间无因果关系(参见“李佳晓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34003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患者出院后三个月感染丙肝与被告医疗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参见“单某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11166号民事判决书)。另外3起案件判决医疗机构承担全部责任的原因在于因果关系显而易见。〔7〕包括明知患者有过敏史而使用过敏药物(参见“肖某某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34117号民事判决书)、误用他人药物输液(参见“林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3051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整形手术未充分告知风险(参见“张金亮与北京军都医院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27511号民事判决书)。质言之,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主要是基于原告原因未能进行鉴定,或者显然不具有因果关系;医疗机构承担全部责任的则是因为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其余绝大多数案件均以“原因力”或者“过失参与度”为由判决医疗机构承担部分责任。
笔者登录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法学资料检索系统”,以“医疗过失”为关键词,对其中受案数量最多的台北地方法院的相关裁判文书进行检索,在该院2016年度共16起相关案件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为14起。在该14起案件中,医疗过失及因果关系未获证明的案件为9起,无过失案件为4起,原告所主张伪造病历事实不存在的案件为1起。而在其余两起判决医疗机构负有赔偿责任的案件中,一起案件认定医疗行为存在过失且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由医疗机构赔偿全部医药费损失及精神损失,而另一起案件认定医疗机构未尽风险告知义务,由医疗机构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但并无一例判决医疗机构承担部分责任。
笔者通过上述对比分析发现如下问题:一是相较而言我国大陆地区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原告胜诉率极高,除了医疗水平的差异及医患关系较为紧张的因素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原因;二是为何我国大陆地区的多数案件均判决医疗机构承担部分责任。案件胜诉与否取决于以构成要件为核心的责任确立,而部分责任则取决于损害范围的确定。《解释》的制定者认为,原因力在这两者中均能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原因力的定性问题,可以确认是否存在损害赔偿责任;通过原因力的定量问题,可以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8〕同前注〔1〕,沈德咏、杜万华主编书,第225页。因此,原因力规则及其适用就成为解开上述谜题的钥匙。
二、原因力规则的不当适用
(一)原因力规则的本质
所谓原因力,是指在导致受害人同一损害后果的数个原因中,各致害原因对于该损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所发挥的作用力。〔9〕参见张新宝、明俊:《侵权法上的原因力理论研究》,《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有学者认为:“原因力的基本规则是,在数个原因引起一个损害结果的侵权行为案件中,各个原因构成共同原因,每一个原因对损害结果具有不同的作用力;无论共同原因中的每一个原因是违法行为还是其他因素,行为人只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所引起的损害结果承担与其违法行为的原因力相适应的赔偿责任份额,对于非因自己的违法行为所引起的损害结果,行为人不承担赔偿责任。”〔10〕杨立新:《论医疗过失赔偿责任的原因力规则》,《法商研究》2008年第6期。
《解释》起草者指出,原因力概念来源于司法裁判和医疗损害鉴定中普遍采用的“医疗过错参与度”或“损害参与度”理论。〔11〕同前注〔1〕,沈德咏、杜万华主编书,第224页。一般认为,我国的医疗过错参与度或损害参与度理论源自我国法医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法上“寄予度减责”理论的引介。〔12〕参见何项跃:《损伤参与度的评定标准》,《法律与医学杂志》1998年第1期;刘鑫:《医疗损害鉴定之因果关系研究》,《证据科学》2013年第3期。“1968 年,日本的加藤一郎、野村好弘就提出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引起损害时,必然涉及如何采用分割的方法将损害结果归结各自不同原因的判断问题。1969年,野村好弘进一步提出在判断外因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应该采用定量比例制的方法去分析。”〔13〕同上注,何项跃文。
日本民法中的“寄予度减责”理论系指“由复数原因共同作用的,在确定各行为人的赔偿额时,要考虑各个原因的参与度”。〔14〕[日]潮见佳男:《不法行为法 Ⅱ》第2版,信山社2011年版,第143页。潮见佳男教授指出,“寄予度减责”并非存在于因果关系这一事实认定层面,而应将其作为规范的价值判断层面上的赔偿额限定标准予以理解。确切地说,将其区分为与前一层面对应的“事实性参与度”和与后一层面对应的“评价性参与度”,是在承认成立共同侵权责任的基础上,在不同于参与度的评价轴上尝试限定赔偿额。〔15〕同上注,第143~144页。也就是说,“寄予度减责”理论不决定责任的确立,而是通过考虑不同因素在损害发生中的作用限制加害人的赔偿范围。森岛昭夫教授也指出,在侵权行为的诸多竞合事实中,任何一个事实与损害后果之间必须具有条件关系,〔16〕参见夏芸:《医疗事故赔偿法:来自日本法的启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当可以确定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其他事实又对损害的发生具有显著影响时,由加害人承担全部责任从政策角度来看并不恰当,应该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17〕同前注〔16〕,夏芸书,第174~175页。这已不是事实因果关系(条件结果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而是针对赔偿损害(损害额)范围的界定问题。〔18〕参见[日]森岛昭夫:《不法行为讲义》,有斐阁1987年版,第284~285页。转引自前注〔16〕,夏芸书,第175页。
反观野村教授的“比例因果关系说”,其主张“不应当将事实因果关系仅看成是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原因结果关系,应当分析加害行为对损害的发生寄予了多大程度(即寄予度),从数量上对因果关系进行处理”。〔19〕同前注〔16〕,夏芸书,第211页。在加害行为与其他自然客观原因共同作用(即原因竞合)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如果加害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只起到一部分作用,那么在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只在加害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寄予度”范围内存在事实因果关系,加害人只须在自己相应比例的因果关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0〕同上注,第211页。其目的是解决“即使加害行为对结果的发生并没有起到全部作用,但也必须承担赔偿全部损害的责任”〔21〕同上注,第210页。之弊端。因此,野村教授的“比例因果关系说”实质上同样为责任范围限制理论,所针对的是侵权法上的全部赔偿原则。而加害人承担部分责任仍以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的事实因果关系为前提。〔22〕同上注,第213页。
国内学者如杨立新教授也指出在原因力规则的适用上,首先应当判断医疗过失行为与医疗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的则无必要进行原因力的比较分析。〔23〕同前注〔10〕,杨立新文。因此,适用“原因力(寄予度)减责”的前提是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必须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24〕同前注〔16〕,夏芸书,第173页。在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大陆法系采用“条件结果关系(condicio sine qua non)判断规则”,即加害行为是损害后果的必要条件,在加害行为A与损害后果B之间存在“如无A则无B”的关系,〔25〕同上注,第173页。英美法系则适用性质相同的“若无 /则不(but for)法则”。
(二)原因力规则在司法实践中成为因果关系的替代物
为进一步了解司法实践中法院如何适用原因力规则,笔者在分析前述北京市某区法院2016年的相关判决后发现,在多数判决由医疗机构承担部分责任的案件中,鉴定意见与法院判决在使用“原因力”时并未根据原因力规则首先确定医疗过失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张净净等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案”中,鉴定意见认为患儿身患肺炎合并先天性心脏病,疾病进展较快且重,患儿的自身疾病系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患儿输液结束后,医院未明确告知家属去找急诊医生,可能使患儿错失了诊治机会,建议由医院一方承担轻微责任,法院据此判令被告承担10%的损害赔偿责任。〔26〕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24994号民事判决书。在该案中,被告“未明确告知家属去找急诊医生”的“过失”与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如无A则无B”的关系,鉴定意见与法院对此未予查明。
在“韩啸与北京积水潭医院案”中,鉴定意见认为患者的自身损伤是导致患者遭受损害的主要原因,发生伤口感染及骨髓炎等为手术后并发症。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的医疗不足与患者所遭受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应承担次要责任。〔27〕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7077号民事判决书。在“王海燕等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案”中,鉴定意见认为急性肺动脉栓塞是治疗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并发症,该并发症系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被告医院的医疗不足为其在手术前后未考虑采取预防肺动脉栓塞发生的措施,该医疗不足在导致患者死亡后果的过程中具有一定作用,法院据此判定被告的赔偿责任比例为30%。〔28〕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00221号民事判决书。在该两案中,患者所遭受的损害均由术后并发症引发,但如无被告的“医疗不足”,是否不会出现并发症,鉴定意见和法院判决均未对此作出判断。
在“原告王秀英等与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案”中,鉴定意见认为医院在输液量的控制、记录以及抗凝治疗监测与控制方面存在医疗过错。“由于患者术后围术期突发心律失常以及心包积液的病因学,在医学上存在相当的复杂性,医院的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结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过错程度介于轻微至次要因果关系范畴”,法院判定被告对患者死亡承担30%的赔偿责任。〔29〕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18194号民事判决书。同样地,鉴定意见和法院判决也未确定被告的过失是否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
在上述案件中,鉴定意见所认定的“原因”实际上是损害发生的“条件”,〔30〕参见杨立新、梁清:《原因力的因果关系理论基础及其具体应用》,《法学家》2006年第6期。鉴定意见和法院判决均未通过条件结果关系判断规则对原因与条件作出区分,从而未将不具有事实因果关系的条件因素排除出去。被告之所以承担部分责任,并非是因为其过失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关联性已获事实因果关系检验,同时有可归于原告的其他原因减轻被告的责任,而是完全直接由被告的过失程度确定其责任承担,这在认定被告医疗行为的“原因力”小于或等于50%的案件中已成为普遍现象。
三、原因力本质与比例责任适用之辨
在上述案件中,原因力被直接运用于对医疗机构的责任确立,这从形式上看类似于比例责任。“原告只需证明‘一定比例’之因果关系可能性,即可成立因果关系,而令被害人负担一定比例之赔偿责任。”〔31〕陈聪富:《医疗责任的形成与展开》,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414页。故而,在此有必要探究司法实践中的原因力应用是否符合比例责任理论。
(一)比例责任的性质
比例责任是指被告因原告所遭受的部分损害或者可能遭受的损害,根据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就被告的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或部分损害,或者可能在将来造成的损害应承担的责任。〔32〕See Israel Gilead, Michael D.Green, Bernhard A.Koch, Proportional Liability: Analy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De Gruyter, 2013, p.2.法庭往往很难确定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只能依证据分析出被告行为与原告损害之间存在一定比例范围(1%~99%)内的概率。根据传统的“全有或全无”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只有在概率大于法定标准(50%、75%或90%)时才能确定其存在因果关系。这导致在因果关系不明的案件中,即使被告确有过错,且因果关系存在的概率达到一定程度(但尚未达到法定标准),被告仍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为此,比例责任被认为是弥合传统理论缺隙的补充性救济路径,〔33〕同前注〔2〕,杨垠红文。即根据被告行为造成原告损害的概率要求被告对原告的损害承担责任,即使该概率未达到法定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34〕同前注〔32〕,Israel Gilead、Michael D.Green、Bernhard A.Koch书,第5页。
根据吉利德(Israel Gilead)教授等的研究,比例责任被划分为三大类9种类型,与医疗侵害案件中的“原因力”相关的案件主要被归入“疑难案件”(the hard case)和“机会丧失”(loss of chance)类型。前者是指无法确定单一原告是否为某一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或被告的行为是否实际造成原告损害的情形。当被告的过失降低原告免受某种损害的可能性时,则构成机会丧失的因果关系。〔35〕同前注〔32〕,Israel Gilead、Michael D.Green、Bernhard A.Koch书,第14页。
欧洲侵权法小组于2005年起草的《欧洲侵权法原则》对比例因果关系持开放态度,其第3:103条(择一原因)、第3:105条(部分不确定原因)、第3:106条(受害人方的不确定原因)与第3:104条(假设原因)均全部或部分采用了比例责任,目的是确保加害人不应就由其他原因(包括他人或受害人的行为以及自然原因)或者可能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36〕See 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 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 Springer, 2005, p.46.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几种比例责任均要求过失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或者应当具有(实际并未发生的)条件结果关系,即假设没有其他原因介入,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必定有“如无A则无B”的关系,只是由于其他原因的介入,此种因果关系在客观上是否存在根据证明标准无法查明,并由此导致所谓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
(二)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中“原因力”的本质
医疗过错行为参与度的概念是由法医学鉴定中的损伤参与度概念引申而来的。“所谓损伤参与度,是指在外伤与疾病共同存在的案件中,诸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某种后果,即暂时性损害、永久性功能障碍和死亡,外伤在其中所起作用的定量分割(或因果比例关系)。”〔37〕同前注〔12〕,刘鑫文。野村教授就因果关系的比例划分了以下5种情形。(1)当原因A、B都是结果C的有力原因时, A的参与度比例相较B更大一些,则A的参与度比例在60%到90%之间。(2)A、B的参与度几乎相同的,A的参与度比例为50%。(3)A的参与度比例相较B更小一些,则A的参与度比例在10%到40%之间。(4)与A、B都被认为是结果C的有力原因不同,在原因尚未明确或是不太有力的情况下,如果A的参与度比例比B稍大一些,则A的参与度比例在20%到30%之间。(5)在与上述情况相反时,A的参与度比例在10%到20%之间。〔38〕参见[日]野村好弘:《寄予度为基础的比例责任》,载日本私法学会:《私法》第50号,有斐阁1988年版,第137~149页。由是观之,损伤参与度并非是指过失与损害之间在医学统计学上的概率关系和可能性判断,而只是代表了外伤(或医疗过失行为)与其他原因之间在损害程度上的比例关系。
对形成“我国特色的伤病关系评定标准”“具有深远意义”〔39〕同前注〔12〕,刘鑫文。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医室伤与病关系研究组编写的《外伤在与疾病共同存在的案件中参与度的评判标准(草案)》(以下简称《评判标准》),将外伤参与度划分为“活体损伤案件的外伤参与度”与“致人死亡案件的外伤参与度”两部分。以“致人死亡案件的外伤参与度”标准为例,其第17条规定:“既有外伤,又有疾病,若前者为诱发或加重因素,即外伤比较轻微,对人体重要器官没有直接危害,但能诱发或促使疾病恶化致死亡,参与度如下:(一)被鉴定人原患有疾病,并已表现出相应的症状和体征,参与度为10 %;(二)被鉴定人原有潜在性病变,而无相应的症状和体征,参与度为20%;(三)被鉴定人原有组织器官的特异性改变,或者其系特异体质,参与度为30%。”〔40〕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医室伤与病关系研究组编:《外伤在与疾病共同存在的案件中参与度的评判标准(草案)》,《法律与医学杂志》1994年第2期。
此后的法医学鉴定标准也延续了此种思路。2009年《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关于办理医疗过失司法鉴定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北京鉴定意见》)规定,根据医疗过失行为在导致损害后果发生中的原因力大小,医疗过失参与度可分为六级,具体如下。A级:损害后果完全由其他因素造成。B级:损害后果绝大部分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失行为起轻微作用。C级:损害后果主要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失行为起次要作用。D级:损害后果由医疗过失行为和其他因素共同造成。E级:损害后果主要由医疗过失行为造成,其他因素起次要作用。F级:损害后果完全由医疗过失行为造成。〔41〕参见《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关于办理医疗过失司法鉴定案件的若干意见》,http://www.bjsf.gov.cn/publish/portal0/tab93/info108544.htm,2018年2月5日访问。作为国家标准的《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GB/T 31147-2014)在其规范性附录中规定了“损伤参与度”,基于损伤参与度的划分标准规定了“本次损害及其并发症、后遗症”和“原有疾病或残疾”与所需护理之间的关系,并规定了相关比例标准,而不考虑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在医学上的因果关系。
(三)原因力与比例责任的不协调
由上可知,我国法医学中的原因力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法律上的原因与条件有着严格的区分,其判断标准即是事实因果关系,“对事实原因力的判断是为了区分原因与条件,将不具有实质原因力的条件剔除出去”。〔42〕同前注〔30〕,杨立新、梁清文。但是法医学在对原因力的判断中并未对原因与条件加以区分。如《评判标准》使用了“诱发与加重因素”,《北京鉴定意见》使用了“轻微作用”“次要作用”“共同作用”等概念,用以表达医疗过失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下的医疗过失只是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条件而非原因。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比例责任,均要求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或者应当具有(是否实际发生不明确)事实因果关系,但在实践中对此未能予以满足。例如,在“黄贵莲等与北京急救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案”中,法院认为医方因未能及时到达患者家中而存在医疗过错,不能排除其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患者自身病情与医疗过错因素在导致患者死亡的后果中各占50%的比例。〔43〕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12341号民事判决书。但是,法院并未在医方“未及时到达”与死亡之间建立事实因果关系。对此,应根据患者所患疾病获得及时救助时的生存概率,以条件结果关系进行判断。又如,在“苗庆芳等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案”中,鉴定意见认为:“根据出血部位分析主动脉穿孔原因,患者可能存在动脉血管弹性差、脆性高、升主动脉前移贴近胸骨相关因素,加上胸骨劈开后骨缘对该段主动脉产生磨蹭,造成主动脉破口出血。骨缘是否光滑与医方是否尽到注意义务有关,破口发生在用心包覆盖保护主动脉下方2cm处,与医方对主动脉保护范围有关,医方存在不足”;“与患者的损害结果有一定因果关系(医疗过失参与度为考虑B级,赔偿参考范围为1%~20%)。”〔44〕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27856号民事判决书。但是,其对此种“轻微作用”是否足以造成患者动脉破裂的损害未予查明。
第二,原因力只是表示医疗过失与其他原因之间关系的工具,而非表明医疗过失与损害结果之间在医学上的发生概率。“医疗过错参与度的理论系数值仅仅只代表特定过错医疗行为作为原因与患者损害结果之间的关联程度。”〔45〕同前注〔12〕,刘鑫文。此为责任范围意义上的比例关系,即外在的“伤”与原有的“病”在损害构成中的占比关系,而非判断过失引起损害的概率。上述几种标准只是在不同情形下根据外伤与疾病之间的表征进行判断,而非医疗过失或患者疾病在医学上所引发损害的可能性,其适用范围应仅限于原因力减责而非责任的确立。例如,在“孙维与北京伯华中医诊所有限公司案”中,鉴定意见认为患者损害主要是其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表现,但医方在诊疗过程中的过错包括未建立门诊病历、建议练习太极拳而未辅以规范和整体治疗以及风险告知不充分,由此导致患者练习太极拳对其原有的破坏性病变产生了促进和加重作用,故医方的医疗过错与患者遭受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参与度系数为20%~40%,法院据此确定被告承担50%的责任。〔46〕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23795号民事判决书。此处并未从医学上分析被告过失造成原告损害的“可能性”概率。
第三,参与度系数并非基于医学上的统计形成,而为抽象标准。比例责任规则要求“在由统计上之证据证明一定比例之因果关系存在时,即应认定被告应负赔偿责任,从而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47〕同前注〔31〕,陈聪富书,第404~405页。因此,医学统计上的证明是比例责任的基础。但从《评判标准》开始,对于侵权行为与原有伤病等其他原因之间的关系,不是考察具体的医疗过失在统计学上引发损害的概率,而是根据伤、病的外在表现规定一个抽象标准,参与度的数值则是按照该既定标准按图索骥的结果。该判断标准针对的是抽象的医疗过失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而非针对某种具体过失或者疾病与损害结果之间在医学上的可能性。例如,在“王浩谦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案”中,鉴定人认为该案件因果关系程度评定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1)依据影像片所示,患者存在双下肢力线异常,结合相关病历记载,患者具有手术指征,术前医方取得患方知情同意,而手术具有客观风险性;(2)医方的过错因素;(3)法庭对于本案相关客观事实的调查情况;(4)骨筋膜室综合征具有的治疗难度及预后不良特点。〔48〕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6032号民事判决书。该鉴定并未将手术期观察记录不周和处置迟缓的过失与患者损害之间在医学统计上的概率作为确定原因力的依据。
(四)以“原因力”之名行“生存机会丧失”赔偿之实
机会丧失是指被告的过失降低了原告避免因自然原因(如疾病)所受损害的可能性。〔49〕同前注〔32〕,Israel Gilead、Michael D.Green、Bernhard A.Koch书,第38页。机会丧失被视为一种具有可赔偿性的损害,且医方过失致患者病情恶化并死亡,其损害赔偿范围以被害人被剥夺的生存机会进行计算。〔50〕同前注〔31〕,陈聪富书,第387页。在法国和美国部分州,机会丧失理论可适用于医疗损害案件。
在相关案例中,部分案例以原因力的名义行“机会丧失”赔偿之实。如在“付红苓等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案”中,鉴定意见认为友谊医院未及时行腋窝淋巴结切除活检鉴别诊断存在过错,该过错可能与患者生存期减少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故法院确定被告的医疗过错责任比例为20%。〔51〕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7083号民事判决书。在此案中,患者的损害即为“生存机会丧失”。而在“汉兴茂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案”中,鉴定意见认为患者在阑尾切除术后尚不具备出院条件,如继续留院观察治疗,或可及早发现静脉多发血栓形成而获得及时治疗,医方过失影响了对患者疾病的及早发现和治疗,法院据此认定被告的医疗过错责任比例为60%。〔52〕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6031号民事判决书。此案更进一步将疾病被发现和治疗机会的丧失作为一种损害。
笔者认为,法院以原因力确定生存机会丧失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机会是否存在未获证明。机会之丧失作为一种损害,患者一方“要证明丧失的机会是真实存在的,是真正的严肃的机会,其病情的严重性没有剥夺任何治愈或生存的有效机会”。〔53〕叶名怡:《医疗侵权责任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外法学》2011年第1期。在上述两案中,此种机会的存在均未获得证明。其次,对机会与医疗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未作认定。机会丧失作为一种损害,与过失之间应当具有确定的因果关系,〔54〕同上注。但上述两个案件对此均予忽略。最后,损害赔偿范围模糊不清。机会丧失的损害赔偿范围如何确定具有争议性,存在“比例赔偿说”“精神损害赔偿说”“增加费用说”等观点。但上述案件对损害赔偿范围均作简单化处理,要求医方就患者的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质言之,法院将原因力规则适用于机会丧失理论缺乏合理性和逻辑性。正如学者所言,法院在相关案件中虽“已经认识到诊疗行为与丧失生存机会的患者最终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特殊性,但难以用现有的因果关系判断学说来阐释,故欲言却止,接着参考司法鉴定中的‘医疗过错行为参与度’,要求被告对最终损害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55〕同前注〔2〕,杨垠红文。
四、医疗损害责任因果关系虚化及其危害
(一)因果关系的闸门形同虚设
普遍依照原因力规则适用“比例责任”,导致我国医疗损害责任构成中的因果关系形同虚设,并引发“有医疗过失必有责任”的现象。这在医疗事故鉴定中表现为过错参与度或者原因力因素普遍获得认定。例如,对某鉴定机构就505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进行分析后发现,在鉴定认定医方具有过错的315起案件中,医方的“过错参与度”全部被认定,级别从B级到F级。〔56〕参见杨天潼等:《505 例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鉴定分析》,《中国法医学杂志》2014年第5期。对另一个鉴定机构在2008~2016年间就360起涉及死亡的医疗纠纷案件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进行分析后发现,不存在因果关系和因果关系无法认定的案件分别为30起和4起,占比分别为7.37%和0.98%。而在90%以上认定存在因果关系的案件中,认定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承担完全责任(参与度100%)的案件仅有1起;认定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承担主要责任(参与度60%~80%)的案件、存在临界因果关系承担同等责任(参与度45%~55%)的案件、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承担次要责任(参与度20%~40%)或轻微责任(参与度5%~15%)的案件占比总计达99%以上。〔57〕参见简俊祺、吴玉峰、张建华、陈忆九:《涉及死亡的医疗损害法医病理学鉴定360 例分析》,《鉴定科学》2017年第3期。也就是说,在鉴定意见确认具有医疗过失的案件中,绝大多数都认为医疗机构具有“过错参与度”或者对损害后果具有“原因力”。正是因为对原因力的普遍认定,加之法院在医学专业判断上高度依赖鉴定意见,以致法院对鉴定意见中关于原因力的结论基本照单全收,导致原告胜诉率和医疗机构承担部分责任的比例呈现“双高”的局面。此外,鉴定机构和法院对医疗机构的过失认定较为宽松,如将未告知患者看急诊、病历记录欠完整(不构成《侵权责任法》第58条的适用情形)、未能证明急救人员及时赶到以及未能告知患者家属有权要求进行尸检等情形均认定为存在医疗过失,其对医疗机构的诊疗效果提出了不合理的过高要求。
因果关系是近代以来各国侵权法普遍采用的损害过滤工具。基于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行为人所可能承担的侵权责任是由其过错导致的、直接受害人的、与其加害行为具有因果关系的、绝对权受侵害的有形财产损失。这种责任范围可由理性予以预见,行为人的风险被最小化,从而为行为自由提供了最大的空间”。〔58〕姜战军:《损害赔偿范围确定中的法律政策》,《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
随着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转变,“近代赔偿法通过因果关系理论过滤可赔偿损失的做法亦越来越不能被接受。无论有什么样美好的理由,那些过于遥远或不相当的损害毕竟亦为加害人造成,使加害人完全不承担责任而任由诸多受害人自行承担损失在很多情况下亦颇不公平”。〔59〕同上注。因果关系要件的松弛成为现代侵权法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医疗损害责任中则表现为证明义务的反转和证明标准的缓和。然而,因果关系要件的松弛并非要求完全放弃因果关系要件,盖因因果关系决定了损害转嫁的正义性基础。在现代侵权法的矫正正义论中,科尔曼的“混合概念论”认为侵权责任的根据在于被告行为产生的不当损害,〔60〕参见陈皓:《侵权法矫正正义论中的个人主义》,《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5期。爱波斯坦的“因果关系理论”将侵权责任的道德依据建立在矫正正义的因果关系之上。〔61〕同上注。没有因果关系这一归责的正义基础,侵权责任的泛滥势必会造成不公正。
相较于其他侵权责任,医疗损害责任中因果关系的作用更为关键。医疗行为与其他民事活动的重大区别在于,在某种意义上其“损害”具有不可避免性。即使是非致命性的伤病,其发展演进和最终后果也绝非如机械关系般一清二楚。因此,对医疗过失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必须更加谨慎。
(二)补偿和遏制的过度或不足
补偿和遏制是侵权责任的主要功能。侵权责任使侵权人就其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这不仅可以实现矫正正义,而且可以激励行为人按照社会规则行事。“让人承担责任是在要求他们就自己所带来的变化负责。为此我们需要原因的概念以确定人的行为带来了哪些改变。”“通过要求人们对其造成的变化负责,可以鼓励他们将世界变得更好,阻碍他们使之变得更糟。”〔62〕See Ian Freckelton, Danuta Mendelson (ed.), Causation in Law and Medicine, Routledge, 2016, pp.8-9.在这个激励和遏制的过程中,“通过使人对其行为的有利或不利后果负责,可为其构建行为、成就和失败的特定化历史,树立自身特质与身份,获得与他人不同的特性。而这些都有赖于因果关系的一般性”。〔63〕同上注,第10页。如果医生只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这不仅可以使其知悉自己行为的范围,预知其开展医疗活动的风险界限,而且可以激励其通过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不断提升自身的价值。
但是,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以原因力名义导致的因果关系全面虚无的现象无限度地扩大了医方责任的范围,其结果是要求医生不得有任何过失,否则即便该过失与患者所遭受的损害结果无关,最终也难逃被追责的后果。但是,人不是机器,不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机械结构;医学是经验的科学,充满了未知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现代医学中的过失,往往不再是主观上具有可非难性的“故意”或“过失”,而是复杂医疗系统中的某一环节出现了问题,“多数错误,是由工作努力、希望把事情处理好的好人们造成的”。〔64〕参见满洪杰:《医疗道歉法与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美国经验与中国进路》,《当代法学》2017年第6期。在原因力的名义下,要求“有过失必有责任”势必造成过度威慑,使医务人员慑于风险而畏首畏尾,不敢开展具有较高风险的诊疗活动,甚至不敢收治具有较高风险的患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本(Benjamin L.Liebeman)教授通过对我国某市医疗纠纷处理情况的实证研究发现,“医生承认会因担心不良后果引发‘医闹’而避开难度大的病例,代之以将患者推向省级医院”。〔65〕See Benjamin L.Liebeman, Malpractice Mobs: Medic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ina, Columbia Law Review, 2013, Vol.113,p.242.防御性治疗不仅会加大社会医疗成本,有碍医学的探索与发展,更会恶化医患关系,导致恶性循环。
此外,原因力理论的普遍适用也造成部分案件中对患者的赔偿存在不足。在因果关系明确的案件中,根据传统的因果关系“全有或全无”规则,患者有权获得全部赔偿。但受原因力理论的影响,法院往往将患者方面的某些因素作为原因力之一而只允许其获得部分赔偿。根据笔者的统计,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2014年至2016年的相关判决中,只有3.04%的案件判决由被告承担全部责任。日本学者森岛昭夫教授也指出,损害的发生往往是被告的行为、自然的因素、环境的物理条件、第三人的行为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采纳“比例因果关系说”,根据被告行为所起作用的程度令其仅赔偿一部分损害,则受害人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只能得到部分赔偿,这显然是不适当的。〔66〕同前注〔16〕,夏芸书,第213页。
(三)侵权法的证明体系被严重破坏
因果关系虚无还将极大地破坏现有的侵权法证明体系。奥利芬特(Ken Oliphant)教授在论及比例责任在英格兰法上只能是一种例外情形时认为,其原因在于普通法上根据可能性概率判断因果关系的路径造成比例责任与证明标准体系难以协调。〔67〕同前注〔32〕,Israel Gilead、Michael D.Green、Bernhard A.Koch书,第139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68〕其第108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在证明标准上明确了以下三项原则:(1)以高度盖然性为一般证明标准;(2)可以根据不同的待证事实确定不同的证明标准,〔69〕参见潘剑锋:《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纲要》,《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11期。但以法律的特别规定为限;(3)举证无法达到证明标准时则应由当事人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因果关系证明并无特殊规定,笔者认为其应遵循高度盖然性标准。以原因力的名义放弃因果关系判断上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必定会造成与其他侵权责任类型在证明标准上的不协调。当风险更高的高度危险作业或主观恶意更大的故意侵权仍需以高度盖然性标准证明其存在因果关系时,在医疗损害责任中仅以“多因一果”“证据偏在”“患者弱势”等理由放弃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要求或者大幅降低其证明标准,明显缺乏说服力。
此外,由于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之间存在互动制约关系,其中一种制度的设置会影响另一种制度的运用,〔70〕同上注。现有证明标准门槛的丧失实际上架空了《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分配,这也可为此类案件中原告的高胜诉率现象提供证据法上的解释。
(四)因果关系路径的随意性有损侵权法功能的实现
侵权法遏制功能的实现依赖于明确的和有可预期性的规则,否则行为人无法预见其后果,自然也难以主动避免此不利后果。日本学者贺集唱教授指出:“(因果关系要件松弛的)做法事实上使得因果关系变得很难被否定,并进而虚置了举证责任制度,其结果最终会对诉讼的期待性与安定性造成损害。”〔71〕杜仪方:《日本预防接种事件中的因果关系——以判决为中心的考察》,《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而我国的相关实践不仅证明存在因果关系要件松弛问题,而且直接将原因力作为比例责任的依据以确立相关方的责任。比例责任纵然能够克服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和证明标准在因果关系不确定案件中对原告不够公平的缺点,但并非可以普遍适用于各类案件并取代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即使是接受比例责任理论的国家也将其适用范围限定在特定类型的案件中。
更为重要的是,“影响比例责任实现其目的的因素是与之相连的确定性或者不确定性的程度。如果行为人或者可能的受害人不能预先知晓其是否将受比例责任调整,无论结果对他们是更为有利还是更为不利,或者法院对于其适用范围和界限举棋不定,这种不确定性将有损侵权法目的的实现”。〔72〕同前注〔32〕,Israel Gilead、Michael D.Green、Bernhard A.Koch书,第20页。我国当前相关立法和理论并未明确比例责任的适用范围,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则是在原因力的遮掩下进行的,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此外,“机会丧失”也会被用于架空因果关系理论,任何形式的实际损害都可被称为某种“机会”的丧失,从而使其成为因果关系的替代物。〔73〕同前注〔53〕,叶名怡文。
五、医疗损害责任因果关系虚化的原因
当前我国医疗损害责任因果关系的虚化是由实践和理论的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因果关系理论体系的不协调
第一,对事实因果关系和比例因果关系认识模糊。法医学界在论证参与度理论时认为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已经被抛弃并为比例因果关系所全面代替,且条件结果关系对于原因力而言不再有意义。“法学家对损伤相关伤、病在人身伤害事件结果中的相关程度判断早已认为不能单纯地以有或无的二者择一的思考方法去判断。”〔74〕同前注〔12〕,何项跃文。“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早已经抛弃了是和否的二分法因果关系,而是已经采用比例因果关系,这为因果关系的定量划分提供了基础。”〔75〕同前注〔12〕,刘鑫文。“无论是必要条件规则还是重要因素规则,这都是定性规则,在采按比例划分因果关系的司法制度下,需要对因果关系作定量判断,显然,这些规则都不再适用。”〔76〕同上注。而这种认知无论是从比较法还是从我国《侵权责任法》等实定法上均无法找到相关依据。
第二,原因力或参与度的概念模糊不清。当前,鉴定意见采用的原因力或参与度概念包含了责任范围的比例、过失与损害之间的可能性概率、所失机会大小等多重不同的含义,且在实际使用中任意混同。现有原因力或参与度理论源于交通事故等外伤参与度标准,外伤事故中过失与损害之间的条件结果关系往往不难证明,此时所需考虑的只是对责任范围的限定,以避免全部赔偿原则所造成的弊端。而在医疗损害责任方面,由于对医疗行为、患者疾病、术后并发症、患者特殊体质等条件及其与患者所受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直观认定,需要经由符合临床医学要求的技术判断,其争议焦点是责任确立上的因果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原因力或参与度却被作为确立相关方责任和限制损害赔偿范围的万能“良药”。
第三,医疗鉴定理论与相关民法学说存在概念落差。现有医疗鉴定理论所使用的概念体系与相关民法学说并不一致,如其将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立起来,并认为事实因果关系应当是由鉴定人予以判断的自然规律和自然事实,而法律因果关系是法官根据事实因果关系作出的法律事实判断。〔77〕同上注。由此可知,医疗鉴定理论中“事实原因”的实质是未经检验的条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直接将其等同于民法上的“原因”,从而忽略了条件结果关系的判断环节。受德国和日本相关民法学说的影响,我国侵权法理论也将因果关系区分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日本民法上的“寄予度减责”理论主要是从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角度限制责任,是对全部赔偿原则的反思,比例责任就其出发点而言同样如此。〔78〕参见郑晓剑:《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之检讨》,《法学》2017年第12期。但是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参与度和比例责任在我国被广泛适用于责任的确立难谓妥当。
第四,未考虑到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基于医学的经验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医疗损害责任的因果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如医疗损害除了包括患者总括的人身损害之外,尚有机会丧失、加重损害、加速损害〔79〕See Bernhard A.Koch, Medical Liability in Austria, in Bernhard A.Koch (ed.), Medical Liability in Europe: A Comparison of Selected Jurisdictions, De Gruyer, 2011, pp.14-15.及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等样态;医疗过失则包括错误诊断、治疗疏失、违反知情同意原则、产品责任、院内感染、过度医疗等情形;患者自身因素则包括特异体质、并发症、疾病自然发展等不同情形;因果关系的认定也存在达到证明标准、未达证明标准或真伪不明等不同状态。以原因力的单一尺度衡量如此复杂的因果关系无异于刻舟求剑。
(二)过度依赖鉴定结论
人类对自身和疾病认识的有限性以及现代医疗的高度专业性和发展性,均给司法者的事实认定带来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法官因而不得不高度依赖医疗鉴定机构的意见。根据学者的相关实证研究,纵使多数法官并非全然信赖鉴定机构或医学会的专业性或中立性,仍不妨碍“100%的法官对医疗损害案件的审理依赖医疗损害鉴定意见,高度依赖的比率为71.93% (123/171) ,中度依赖的比率为28.07%(48/171)”。〔80〕肖柳珍:《医疗损害鉴定一元化实证研究》,《现代法学》2014年第4期。法官往往也缺乏足够的能力和意愿对当事人就鉴定结论所提出的异议进行有效审查,其典型的处理方式是“原告(或被告)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均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此种路径依赖造成法官在对因果关系进行判断时很难探究原因力的实质内涵,从而将其径行作为确立责任和分配损害的唯一工具。
(三)法院寻求妥协的态度
面对来自患者的巨大压力,我国法院在医患纠纷处理中往往倾向于选择具有妥协性和较易使患者满意的路径,在患者与医方之间寻求平衡。国外也有学者发现,法院在受到患方较大压力时,往往通过调整裁判结果乃至要求无过错的医方承担一定责任安抚患者。〔81〕同前注〔65〕,Benjamin L.Liebeman文,第240~241页。据笔者的前述统计,自2014年至2016年,在医疗机构无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共计324起案件中,法院仍判决医方承担“补偿”责任。如在一起案件中,法院认定患者“感染丙肝病毒与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马鞍山市中心医院的医疗行为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82〕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5民终259号民事判决书。在另一起案件中,法院认为医学会的鉴定结论认定医疗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故患者的各项赔偿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但鉴定意见均明确指出了公利医院在诊疗行为中存在告知和沟通不足的过错,上述过错虽与李翔的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但会导致李翔产生合理的怀疑,引发医患纠纷,故因本次争议产生的鉴定费由公利医院承担,并由公利医院对李翔进行适当的补偿。”〔8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终3184号民事判决书。
基于上述理念,法院乐于在责任的承担上选择中庸路线,“倾向于通过判决寻找平衡而在很大程度上拒绝‘胜者全赢(winner-take-all)’的结果”,〔84〕同前注〔65〕,Benjamin L.Liebeman文,第288页。特别是避免出现有过失的医方完全不承担责任的情形。此时,司法鉴定得出的原因力即成为法院要求医方至少承担部分责任的依据。
六、医疗损害责任因果关系虚无主义的化解与因果关系的应然体系
(一)事实因果关系的坚守和发展
因果关系是侵权法中矫正正义的重要体现,是实现法的安定性价值及其补偿和遏制功能的基本保证。放弃因果关系的限制,意味着侵权责任法将发生从以损害为基础向以风险为基础的“巨变”,表面上似乎可以纠正现有理论的缺陷,但会带来更大的不公正结果和混乱局面。〔85〕See Arthur Ripstein and Benjamin C.Zipursyk, Corrective Justice in an Age of Mass Torts, in Gerald J.Postema, 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44-245.在因果关系的内容上,郭明瑞教授指出,“判断因果关系的存在仅以事实因果关系的存在为已足,无必要确定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存在”。盖因“相当因果关系说将过错性、违法性等因素纳入‘相当性’的判断中,实将侵权责任的各构成要件一同考察,将法律上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责任构成的必要的充分条件”。〔86〕郭明瑞:《侵权责任构成中因果关系理论的反思》,《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由于确定因果关系的目的仅是确定行为人可否对损害承担侵权责任,而非应否承担责任,〔87〕同上注。事实因果关系足当此任。日本学界通说也持此种意见。〔88〕同前注〔16〕,夏芸书,第168~169页。
基于医学的专业性,法官在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上需要借助鉴定意见,此时鉴定意见给出的应该是医疗过失与损害之间在统计学上的可能性概率,而非责任承担上的“参与度”。法官应当根据其概率和高度盖然性标准,确定事实因果关系之有无。《解释》第11条虽然将因果关系和参与度并列为鉴定事项,但第12条又将“全部原因、主要原因、同等原因、次要原因、轻微原因或者与患者损害无因果关系”均作为原因力的表述方式。由于全部原因和无因果关系并不存在原因力减责问题,此种表述显然扩大了原因力的概念范围,会加深实务中对原因力问题的错误认识,该规定难谓妥当。
在事实因果关系中,条件结果判断在多数情况下符合生活逻辑和社会公平观念,但在诸如“超定(overdetermined)原因”等特殊情形下则可能失灵。超定原因是指两个以上的条件都是造成损害的充分原因,以致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不符合“若无/则不”的必要判断。例如,当医疗过失足以造成患者死亡,患者因食物中毒死亡的,医疗过失和食物中毒都是导致死亡的充分条件,但都不符合必要性标准。即每一个条件都可单独构成损害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但由于同时或先后发生其他原因,以致每一个条件都成为充分非必要条件。此种情况又分为“先发的因果关系”(preemptive-causation)和“叠加的因果关系”(duplicative-causation),其主要区别在于各条件的发生顺序不同。〔89〕See Gemma Turton, Evidential Uncertainty in Causation in Negligence, Hart Publishing, 2016, p.47.为解决此种困境,1965年哈特(H.L.A.Hart)教授与奥讷勒(Tony Honoré)教授一起,从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规律性(regularity)认识出发,提出了“充分体系中的必要因素”(Necessary Element of a Sufficient Set,简称NESS)标准,〔90〕See Richard W.Wright, Causation in Tort Law,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73, Issue 6, 1985, p.1775.并由美国赖特(Richard Wright)教授加以发展,将其作为“若无/则不”标准的延伸和补充。根据NESS标准,“当且仅当某一特定条件是一组可引起后果产生的、先验的、实际的充分条件中的组成要素时,则其为特定结果的条件(或对结果产生贡献)”。〔91〕同前注〔90〕,Richard W.Wright文,第1790页。这一标准在必要条件的前提下考虑了充分条件的意义,具有借鉴价值。
(二)比例因果关系的有限适用
比例责任在责任确立层面突破了单个原因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限制,在责任承担层面使加害人仅基于其过错作用承担部分责任从而克服了全部赔偿原则的不公正。〔92〕同前注〔78〕,郑晓剑文。但是,比例责任的适用范围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比例责任不能完全替代事实因果关系。如前所述,事实因果关系在限制责任、实现正义和维护法律安定性的作用上无可替代,完全否定事实因果关系只会造成因果关系的虚化。根据吉利德(Israel Gilead)教授等的比较研究,比例责任迄今并未被多数法域接纳。与医疗损害责任密切相关的“疑难案例”类型之比例责任仅在奥地利、英格兰〔93〕其限于“Fairchild v.Glenhaven Funeral Services”一案中确定的例外情形,即损害发生原因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可以确定损害是因为原告所处的相同(至少相似)风险造成的。同前注〔32〕,Israel Gilead、Michael D.Green、Bernhard A.Koch书,第128页、第134页。、法国(以机会丧失的方式)、荷兰(个案判断)被允许,而在德国、美国等多数国家则被拒绝,且没有一个国家完全以比例责任取代事实因果关系。〔94〕同前注〔32〕,Israel Gilead、Michael D.Green、Bernhard A.Koch书,第39页。
第二,比例责任的适用范围。即使在接受比例责任的法域,其适用也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和领域内。例如,奥地利法院仅在医疗损害责任案件中针对因果关系无法确定的情形接受了比德林斯基(Franz Bydlinski)教授提出的比例责任,根据原因的可能性在双方之间分散风险,前提是证明被告违反其注意义务的行为极具危险性。〔95〕同前注〔79〕,Bernhard A.Koch书,第14页。此种比例责任是为了克服该特定情况下由于因果关系无法查明导致患者难以获得赔偿所引起的极大不公而采取的特例,其并非普遍准则。
第三,启动比例责任的政策考量。基于比例责任对传统因果关系的非替代性,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启用比例责任成为关键。吉利德(Israel Gilead)教授等指出,是否转为比例因果关系需考虑多重事实因素,包括相互冲突行为的性质、特性及其社会价值,原告和被告的相对过失程度,受害方所遭受损害的类型和性质,围绕证明责任的概率分配,所造成的诉讼数量及其成本的增加等,〔96〕同前注〔32〕,Israel Gilead、Michael D.Green、Bernhard A.Koch书,第38页。最终目标是根据公平和正义原则分配风险和损害,进而提高社会的整体利益(效率)。〔97〕同上注,第20页。
第四,比例责任的适用类型。《欧洲侵权法原则》所规定的“择一因果关系”(alternative cause)、“假设因果关系”(potential cause)和“部分不确定原因”(uncertain partial cause)均为复数行为的比例责任。与医疗损害责任最密切相关的是《欧洲侵权法原则》第3:106条规定的“受害人方的不确定原因”,亦即前述吉利德教授等所言的“疑难案例”类型。该条规定“受害人应当自行就其自身领域内的行为、事件或者其他情形引发损害的可能性承受损害”,即在一个属于加害人的原因和一个属于受害人的原因都可能造成损害但不知其中哪一个原因造成实际损害时,应以受害人自身原因的可能性减轻加害人的责任。但适用此规则的前提是任何一方的原因是或者应该是造成损害的事实原因。〔98〕同前注〔36〕,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 书,第56页。例如,一个登山者被一块山石击中,另一块山石也几乎同时击中他。两块山石中有一块是因侵权人的行为造成的,另一块是因自然原因坠落的,不能确定实际击中他的究竟是哪一块石头,此时应适用比例责任原理,根据每个原因引发损害的可能性承担责任。〔99〕同前注〔36〕,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 书,第57页。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医疗损害责任案件中适用比例责任应当符合以下要件。
1.医疗过失与患者自身原因均可能与损害之间具有事实因果关系,对此应有医学统计上的证明。以英国“Hotson案”为例,原告跌伤因被告误诊5日后才获得适当治疗,其髋部缺血性坏死。经专家证人证实,原告损害可能是由外伤导致血管破裂所致,也可能是误诊导致的充血所致,任一原因都足以造成患者损害,但无法证明到底何者为实际原因。根据原告摔伤的严重程度和病情,专家证人认为在医学统计上两种原因的可能性分别为25%和75%。〔100〕See Hotson v.East Berkshire Health Authority [1987]AC 750 (HL).
2.实际因果关系因不能归责于当事人的客观原因无法查明。当符合上述第一项要件,受限于认知能力,穷尽事实查明方法仍不能证明损害是由哪一个原因造成时,因“被告行为经证明确已增加损害之危险时,因果关系不确定之责任归由具有过失行为之被告负担,而非由无过错的原告承担。是以在有统计上之证据证明一定比例之因果关系存在时,即应认定被告应负赔偿责任,从而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101〕同前注〔31〕,陈聪富书,第404页。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客观因果关系无法查明的情况必须是由客观原因而非任何一方的原因造成的。如因果关系事实不明是因为医方隐匿、拒绝提供、伪造、篡改或销毁病历资料造成的,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第58条由医方承担责任。〔102〕《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的法律效果为“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笔者认为在该条第(二)项、第(三)项情形下,应同时认定存在过错和因果关系,否则仅认定存在过错而无法证明此种“过错”与损害有无因果关系实属枉然。张新宝教授关于将其改为“医疗机构一方应承担过错责任”的建议值得赞同。参见张新宝:《民法分则侵权责任编立法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3期。
3.应充分考量被告过失程度及原告损害范围等因素。适用比例责任是为了纠正因果关系不明时传统路径带来的不公正,其本质是一种证明责任的缓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阐述证明责任倒置或缓和的正当性理由时曾指出:法院必须考虑公平、诚实信用等价值以及参与者的社会角色、利益对立、冲突情势以及保护需求等。”〔103〕周翠:《〈侵权责任法〉体制下的证明责任倒置与减轻规范》,《中外法学》2010年第5期。在过错因素上,对于过错程度很高的被告和仅有轻微过错或者没有过错的原告来说,以比例责任原理使原告获得赔偿可能有助于风险的公平分配和合理遏制。〔104〕同前注〔32〕,Israel Gilead、Michael D.Green、Bernhard A.Koch 书,第37页。科茨欧(Helmut Koziol)教授强调:“侵权人承担部分责任必须局限于其行为具有最高等级危险性的具体场景下。比德林斯基教授认为因果链条薄弱时应当给予额外的补偿,因此只有在被告行为具有重大过失时才能确立此种责任。”〔105〕See Helmut Koziol, Problems of Alternative Causation in Tort Law, in Herbert Hausmaninger, Helmut Koziol, Alfredo M.Rbello, Israel Gilead (ed.), Developments in Austrian and Israeli Private Law, Springer, 1999, p.181.对原告所受损害的程度和范围等要素也应予考虑。
4.医疗过失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可能性概率应足够显著,由于比例责任系根据统计上的概率作为确定比例因果关系的依据,此种概率应该足够显著,过于细小的概率可能源于统计上的随机变量或正常误差,而非客观规律。〔106〕同前注〔36〕,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 书,第58页。如当自然原因引发损害的概率为98%时,法院一般不会考虑医疗过失引起损害的微小可能性;相反,当自然原因引发损害的概率为2%时,则医方应承担全部责任。〔107〕同上注,第59页。
(三)对机会丧失理论的谨慎认可
第一,机会丧失损害的性质与限定。医疗损害责任适用机会丧失理论一般将“所失机会”作为损害,但是在机会损失的性质与确定上,又有不同的观点和实践。一种路径为 “比例赔偿方法”,即以患者的最终损害乘以机会的比例作为可获赔偿的损失。〔108〕See Alice Férot, The Theory of Loss of Chance: Between Reticence and Acceptance, Florida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8,Issue 2, 2013, p.604.此种路径看似将机会作为一种损害,其实质仍是以机会丧失为介质,在医疗过失与患者最终损害之间迂回,以“概率因果关系”(probabilistic causation)替代“全有/全无”的因果关系,本质上是“伪装的比例责任”,〔109〕同前注〔32〕,Israel Gilead、Michael D.Green、Bernhard A.Koch 书,第40页。与其假机会丧失之名,不如直接适用比例责任。笔者认为,机会丧失主要侵害的是患者的自主人格利益,即由于医疗过失所丧失的获得及时、适当、有效治疗的机会,其损害范围主要为患者因此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痛苦,以及与机会相关的额外财产损失,如病情加速所造成的收入减少或增加的治疗费用等。
第二,对过失行为类型的限制。机会丧失理论应限定于错误诊断导致患者疾病未获及时治疗的“消极过失”情形,而不应当适用于治疗措施不当等“积极过失”情形,否则患者所受人身损害特别是死亡的后果均可能被解释为一种机会的丧失。这将导致原告在实际损害和机会丧失之间任意选择,当其所受损害与过失行为的因果关系已经达到证明标准时,其将选择主张实际损害以获得全部赔偿;当因果关系无法证明时,其将选择机会丧失理论以降低证明标准从而获得部分赔偿,〔110〕同上注,第42页。以致“将机会丧失规则作为因果关系存在的替代论证从而对其滥用”。〔111〕同前注〔53〕,叶名怡文。
第三,“机会丧失”应当获得医学统计的证明。机会丧失应当被证明是真实存在的,即在过失发生时患者本应有一定程度的生存或治愈机会,并与过失之后的残余机会存在差额。对此,必须以医学统计的方法加以证明。反观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法院往往不考虑生存或治愈概率在机会判断上的运用,而是以“原因力”作为判断机会有无的标准。如在“张某等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案”中,鉴定意见认为被告漏诊的医疗过失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存在次要因果关系,参与度理论系数值为25%,法院认定被告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112〕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少民终字第05756号民事判决书。这一思路在笔者所收集到的“机会丧失”案件中占绝大多数。〔113〕参见“朱秀兰等与枞阳县人民医院案”,安徽省枞阳县人民法院(2015)枞民一初字第01904号民事判决书;“武连彩等与胶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案”,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3)胶南民初字第459号民事判决书;“谢敬平等与黄山市人民医院案”,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0民终381号民事判决书;“徐允琚等与赣榆瑞慈医院案”,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原江苏省赣榆县人民法院)(2015)赣民初字第04949号民事判决书;“阮盛宗等与福安市妇幼保健院案”,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2014)安民初字第4859号民事判决书。此种进路并不能说明患者在医疗过失发生之前与发生之后各有多少比例的生存概率,不能证明机会的存在。鉴定机构和法院将判断过失行为和损害范围之间关系的原因力与判断机会是否存在的医学统计概率(生存率、治愈率等)混为一谈,应当予以纠正。
第四,医疗过失与机会损失之间需有事实因果关系。在机会丧失与医疗过失之间应当建立“如无A则无B”的条件结果关系,以达到责任确立的要件要求。
(四)对原因力减责的限制
只有当医疗过失是导致损害的事实原因时,才能根据“行为人有无过错、行为是否不法、有无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以及损害赔偿规则的具体运用”〔114〕同前注〔86〕,郭明瑞文。确定被告承担责任的范围和份额。故原因力只是减责情形的一种,不应被作为确定责任范围的唯一因素。同时,即使是通过鉴定确定的与损害有关的原因力,也并非一定可以减责。例如,对于受害人特异体质引起的原因能否减责,理论上不无争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性案例似乎建立了受害人特异体质不得减轻加害人责任的一般原则,但实践中“法院仍近乎100% 地斟酌疾病‘参与度’减轻加害人责任”。〔115〕孙鹏:《“蛋壳脑袋”规则之反思与解构》,《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笔者认为,在医疗损害责任中,完全适用或者完全排除受害人体质的减责作用均不可取,孙鹏教授提出的根据“因素程度”和“因素信息支配”类型化处理,〔116〕同上注。以及程啸教授提出的以特异体质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类型化处理〔117〕程啸:《受害人特殊体质与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案例评析》,《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的进路均有可取之处。当然,在具体运用中应当考虑医疗损害责任的特殊性。如在因素程度上,因医方须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正常的个人体质差异或者“缺乏最低限度的抵抗力”〔118〕同前注〔115〕,孙鹏文。均难以成为减责理由,但极为罕见的个人特质应斟酌考虑。在因素信息支配上,则应当充分考虑医方在信息上的优势以及疾病发展预见的不确定性。
综上,笔者认为对此应坚持构建多元而协调的因果关系体系。当前司法实践中医疗损害责任因果关系的虚化,除了对原因力规则的扩大理解和过度适用等原因,也反映出因果关系机制的单一化。为满足不同情形下因果关系判断的需要,应当建立包括事实因果关系(以及NESS因果关系)和特定情形下的比例责任、机会丧失理论在内的多元且相互协调的因果关系判定体系。
七、结语
当前我国的医疗损害责任司法实践将本应作为减责事由的原因力规则当作责任确立规则,造成了因果关系要件的极度虚化,减损因果关系的矫正正义功能。《解释》第12条将原因力因素规定在司法解释中,并将其与因果关系紧密联系,势必进一步固化和加剧因果关系的虚无现象,造成其法律适用的混乱,不仅有损医患双方的合法权利,导致赔偿责任补偿和遏制功能的不足或过度,亦可能导致防御性医疗和医学的裹足不前。因此,对该条解释可作如下修正:(1)原因力规则仅应作为减轻被告责任的因素加以适用,而不适用于责任确立场合;(2)有关责任确立的因果关系仍应适用事实因果关系,在特殊情况下适用比例责任和机会丧失理论;(3)在损害范围的判定上除原因力规则之外还应存在多元化的规则;(4)原因力规则在减责层面的适用上仍受特异体质等因素限制;(5)应明确司法鉴定意见中原因力概念的含义,避免将其等同于因果关系可能性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