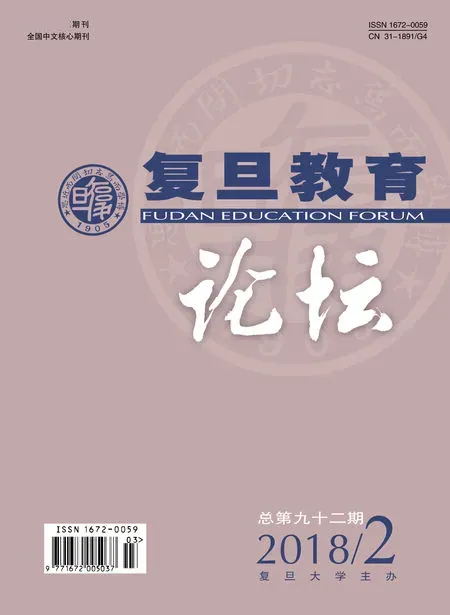形而上的大学
——罗纳德·巴内特论大学的未来可能性
2018-04-03山凌顾平
山凌,顾平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上海200062)
罗纳德·巴内特(Ronald Barnett)是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学荣誉退休教授,也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其主要著作包括《高等教育的理念》《能力的限度》《实现大学》《学习的意志》《使大学存在》等数十部,主编的论文集包括《重塑大学》《未来的大学》《大学中的智慧》等。作为世界级的高等教育专家,巴内特对于高等教育和大学事务的长期思考蕴含着一个极其鲜明的主题,即“大学的未来可能性”。巴内特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中,“某种类型的思考却远远不够,理应得到发展”,而此处所谓的“某种类型的思考”则是一种“富于想象力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思考”[1]。换言之,巴内特希望人们能够去更多地思考一种超越于经验层面的、更为基本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中,大学不断地“成为”大学。鉴于巴内特的高等教育思想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及其本身的理论价值,同时鉴于国内学界对巴内特相关著作的译介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将以他的重要著作《使大学存在》为主要的理论资源,简要勾勒出作者对于大学未来可能性的思考,以起到抛砖引玉的学术目的,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参与到对巴内特作品的研究当中。
一、“形而上的大学”的诞生与大学的“神秘性”
“形而上学”作为一个学科,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公元前1世纪的编者在整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时,发现其中一部分内容虽然与物理学有明确的联系,但是讨论的对象更加抽象和基础,于是将其置于有关物理学的内容之后,并命名为“形而上学”①。因此,“形而上学”一词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的是这部分内容在亚氏学说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指的是其所探讨的对象相对于物理学对象的关系——前者超越于后者。如果说物理学的对象是可被感知的大自然,那么形而上学的对象则是可感自然背后的本质,或者说超越于可感自然的本质。这恰好符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四卷中所指出的研究范围:形而上学的任务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as being)[2]。事物不单纯是个别的事物,它们同时还是存在。因此,“作为存在的存在”也就完全不同于个别事物的具体特征(如桌子的硬度或台灯的颜色),它是一切事物所共享的最高范畴。所以说,对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研究,就是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秩序的研究。
在这个意义上,将早期的大学形态命名为“形而上的大学”的确名副其实。巴内特认为,早期的大学是建立在下述观念之上的:人们可以通过知识而与上帝、宇宙、国家甚至存在本身建立联系,由于这些更具普遍性和一般性的事物超越于可被感知的自然,所以这种观念是一种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观念。那么,大学作为一个知识机构,作为这种观念“在制度和教学上的体现”[3],也就成了“形而上的大学”。在巴内特看来,“大学”(university)一词与“大全”(universe)一词在词源上的亲缘性已经暗示了上述观念:借由大学达到的认知状态和宇宙处于统一与和谐之中,“形而上的大学所具有的统一性对应于宇宙的统一性,因为在这片空间内,宇宙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得到探寻”。
我们自然需要询问:对于生活在已经去魅的世界中的我们而言,这种大学形态还具有任何意义吗?巴内特确实承认形而上的大学目前已经被新的、更具现代特征的大学形态所取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它的关注就只能出于对历史的兴趣;恰恰相反,形而上的大学以一种更加明确的方式向我们呈现出大学的“神秘性”。由于人们可以在形而上的大学中通过认识活动与超自然的世界建立联系,那么这种大学的理念或特征同时也要基于那个具有更高实在性的世界(一个试图在个人和上帝之间建立联系的大学必然要显示出上帝的至善或全知,而一个试图在个人和宇宙之间建立联系的大学必然要体现出宇宙的宏大与多面),否则我们不可能借由形而上的大学把握到世界的根本秩序。然而,由于这个世界的意义过于丰富、过于复杂,与这个世界紧密相关的大学也就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梳理清楚。“大学所伴随的情感及其喋喋不休的呢喃实在太庞杂又太模糊,我们没办法对它做出清晰的描述——上帝、精神、文化、存在和国家的心腹地带容不下精确性。”形而上的大学所承载的神秘性正源于此。
在巴内特看来,大学的神秘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近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孜孜以求并试图说明那个切中大学本性的独特理念,但最终却发现,大学的理念只能是复数的,并且处于不断累加的无尽过程之中。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先前探求大学本性的种种努力都是徒劳的,而是因为大学在其本性中自有其“存在”。巴内特沿袭了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存在”的解释,将这个古老的哲学概念理解为“可能存在”。既然大学的本性内在地蕴含着可能性,那么它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又不断从人们的视野中逃离,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二,如果说神秘性的第一个方面更多停留在抽象思辨的层面,那么它的第二个方面则随处体现在大学的日常事务当中。“大学的神秘性在于它所牵涉到的情感、理想甚至实践本身就是神秘的”,因为大学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总是要诉诸作为背景的价值框架,它可能包括真实、探索、服务、生成、友谊、好客、照顾和关怀等各种不同的价值元素,并且渗透到大学的行政与教学当中。但巴内特认为,我们几乎不可能把作为背景的价值框架表达为清晰的文字。虽然巴内特并没有解释这种不可能性的原因,但我们仍然可以向为巴内特所倚重的海德格尔求助,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既然任何解释都活动于在世的隐绰未彰的背景上,都对所需解释之事有了某种在先的领会,那么解释就不会是没有前提的”[4]。我们当然可以在反思中把握自身活动的背景,但是我们总是在背景中进行把握。所以,背景在呈现于我们的视域的同时,也在从我们的视域中逃离。大学的神秘性就体现在:大学在日常运转的经验过程中无法完全实现作为背景的价值框架,后者当中总有某一部分在经验中隐而不发。是以,巴内特将上述两者之间无法消除的距离称为“操作上的缺口”。
巴内特对于形而上的大学的关注旨在让人们意识到形而上的大学所直接体现出的神秘性,而这种神秘性为大学把自身投向未来、不断实现种种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基础。然而,巴内特敏锐地意识到:在数百年的现代性进程中,随着形而上的大学从人们的视线中逐渐隐退,这种神秘性也随之隐退——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被后继的大学形态遮蔽了。我们将在第二部分重点关注这种神秘性的隐退方式,而后再进一步考察其在当代的复兴。
二、神秘性的隐退与现代的大学形态
政治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曾将中世纪晚期以来的欧洲社会诊断成一个“内在世俗性”的基础不断得到构建的社会。他用了一段简洁的文字勾勒出这种社会的若干重要特征:“作为内容的世界压倒了作为存在的世界。科学方法作为研究世界内容的唯一形式,被宣告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必要基础。自19世纪以来直到今天的很长时期里,‘形而上学’一词被认为是一个被滥用的词语……‘世界之神秘’被清算出来并被解决掉。同时,关于存在的根本问题以及用来研究它们的表现形式的一般知识萎缩成一个个小领域。”[5]在沃格林看来,现代性进程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人们不再沿着超越性的维度进行思考,超越于可感事物的“作为存在的存在”从人们的视野中退出了。当这个既丰富又模糊的神秘世界不再受到人们的瞩目之后,剩下的就是没有任何神秘性可言的可感事物以及我们通过感官获得的有关这些事物的经验,而这两者均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等理性的科学方法进行分析。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仿佛事物的意义只需也只能由物理学给出,仿佛生存的意义只需也只能由心理学给出;世界更深层次的意蕴以及投向崭新未来的可能性在根本上受到了限定。
虽然巴内特在文本中并未指涉沃格林的诊断,但是两者对于现代性的看法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巴内特关于大学神秘性在现代性进程中的隐退的观点是沃格林的诊断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具体呈现。巴内特认为,自17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和世俗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下述假定开始流行起来:“世界彻底落入了人类的辖域,‘透明性’成了这种秩序的关键词。”这与上文提到的对形而上的大学构成支持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后者强调的是:世界拥有一个位于人类辖域之外的维度,人们可以通过认知行为与这个超出人类经验的部分产生关联。如果说这个不能被人类完全征服的部分是神秘性的源泉,那么一个可以被人类的经验活动彻底把握的世界就成了透明性的渊薮。既然形而上的神秘性已经被经验的透明性所取代,那么形而上的大学的衰微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这种透明性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层面:人们不再谈论大学的神秘本性,而是将大学仅仅视为由行政、教学、政策、效用等一系列经验事实汇集而成的场所,并且这些事实都是可以精确定义和量化的。人们甚至不再谈论作为背景的价值框架,仿佛一切事务都是价值中立的。虽然巴内特没有对此展开详尽的因果分析,但是这显然与科学研究中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相关:二十世纪初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潮一直要求“净化”我们的语言,在该学派所提出的“证实原则”——“理解一个陈述和知道它的证实方法是一回事……为了理解它的意义,我们必须看一下它是如何被证实的和如何被否证的”[6]——的指导下,逻辑实证主义者要求从语言中排除掉那些无法在经验中得到证实的命题,其中显然包括形而上学命题。由于价值表达式(无论是审美价值还是道德价值)同样无法在经验中得到证实,因此一个伪装成命题的价值表达式实际上与主观的情感表达无异。
在《单向度的人》中,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对这种把语言的意义完全建立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的语言哲学发起了猛烈批判。他并不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观只具有学术上的意义,相反,他将其视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如果人们所操持的语言本身丧失了批判性和否定性,那么人们就缺乏一套恰当的语汇去思考和展望一个不同的世界,在面对现状时也就只剩下了肯定的选择。[7]就高等教育而言,巴内特与马尔库塞的观点完全相同。在他看来,语言对于神秘性的关闭同样引发了一个深远的后果:大学的可能性被削减了,“它的特定存在被削减了”。正因为缺乏一套可供人们在一个更为基本的层面上去思考大学未来的语汇,所以“有关大学使命的陈述常常平淡无奇又千篇一律,在当前背景下出现这种状况并不奇怪”。因此,现代的大学形态面临着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悖论:无论是词源上的亲缘性还是历史上的确切关联,理想的大学(university)应当关切那些宏大(universal)的主题,然而这些主题在当下的大学中几乎完全消失了,仿佛只有金钱、排名、竞争力等世俗事物才具有意义。
为了更加清楚地表明大学的可能性是如何在现代性进程中受到影响的,巴内特分析了形而上的大学的若干后继者。它们自身诚然以具体的形态或理念呈现出大学的可能性,但它们又各以不同的方式限制了大学的可能性。巴内特将形而上的大学的后继者分为三类:科学型大学、创业型大学与科层制大学。
1.科学型大学(scientific university)
科学型大学并不仅仅是以追求科学进步为己任的大学,而且是以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研究唯一合法范式的大学。科学型大学的确立与更为广阔的社会变动紧密相关:随着自然科学以及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的技术向社会展示出巨大的威力与效用,社会反之也将自然科学视为具有唯一典范意义的知识。换言之,只有那些隶属于自然科学的知识或是那些参照自然科学建立起来的知识才是知识,其他类型的知识则被贬低为“非知识”。巴内特在此引用了美国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的观点:“科学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处在这种社会当中的大学在建制、经费、政策等方面绝对倾向于自然科学领域,这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在巴内特看来,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范式的绝对权威折损了大学的知识可能性,科学型大学“是一个封闭而非开启思想与理解的机构”。
2.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创业型大学已经成为当代高等教育领域的热词。这类大学的特征在于:它像一个创业者那样运用自身的某类资本(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资本,还包括文化、智力、声望、社会等方面的资本),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同时也试图获取更多的收益。不过在巴内特看来,与其说这种特定的大学形态限制了大学的可能性,不如说当下人们对于创业型大学的看法与讨论失之偏颇。“在‘创业型大学’的理念中,据说大学以及大学体系是不断趋同的,仿佛大学的一切变化都将带来创业精神。”然而,根据巴内特的分析,“创业型大学”的概念事实上是相当模糊的,它并没有止步于某种特定的存在类型,反而向人们提供了多样的选择与实践。
3.科层制大学(bureaucratic university)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原则即为由功利性目标、专业化分工、手续与流程、制度性权威等方面构成的科层体制。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并非现代社会中的一块飞地,它同样必须接受科层制的约束。为了更好地体现出科层制大学的特征,巴内特还把它称为“监督性大学”(surveillance university)。第一,建立在规章制度之上的科层制大学为其中的个体提供了应对情境的标准方式,人们无须多加思考就能做出符合组织要求的行动;第二,个体与个体的衔接依赖于组织的安排,个体之间原本自发的交往在科层体制中需要以流程化的步骤为中介。上述两个方面的监督过程对于学术活动也不例外。科层制大学诚然有其合理性:随着学术活动愈益成为一种集体性的活动,大学的科层制安排能够保证这些活动以符合标准的、讲求效率的、肩负责任的方式进行下去。然而,科层制的组织原则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于大学事务的反思。毕竟,处在科层制中的人只需按照既定的规章和流程将大学事务不断向前推进,即使不理解其他人的意图,也完全可以把事情做得符合组织标准。因此,科层制大学不仅对变革持保守态度,还压制了个体之间的交往理性,而交往理性是指人们试图通过一定的商谈形式来理解彼此并达成共识的理性。对此,巴内特质疑道:“难道大学不是最能够体现出交往理性的社会机构吗?”这句反问显然表明了科层制大学与理想中的大学形态之间的距离。
综上,巴内特对于三种主要的现代大学形态一一作了批判性的考察。作为形而上的大学的后继者,这三类大学各有其局限性:科学型大学限制了知识的复杂性,创业型大学限制了模式的多样性,科层制大学限制了交往的自发性。巴内特之所以检讨三者的得失,目的是为了让人们透过现代大学形态的细枝末节,辨识出曾在形而上的大学中直接表露出来的神秘性以及建立在这种神秘性之上的可能性,最终在富于想象力的思考中展望未来的大学形态。接下来,本文将考察巴内特所支持的一种大学理念,并表明这种理念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绽放出了大学的未来。
三、形而上学的复兴与生态型大学的构建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回答了文章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形而上的大学对于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我们来说具有何种意义?根据巴内特的观点,形而上的大学直接显露出大学的神秘性以及基于这种神秘性的无限可能;而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中,随着神秘性的陨落,大学的可能性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限定。因此,对形而上的大学的回顾让我们再度把握到大学的神秘性与可能性。那么,在上述答案的基础上,似乎有必要进一步询问:为了让受到遮蔽的可能性绽放出来,我们是否需要重返形而上的大学?事实上,巴内特无意恢复古老的形而上的大学及其陈旧的形而上学观念。在他看来,大学的形态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当下的时空既然已经与形而上的大学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大相径庭,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回归到先前时代的大学形态。但是,巴内特确实认可一种“弱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大学,其并不等同于在西方历史中绵延数世纪的、实际的形而上的大学。
巴内特这样描述道:“这种形而上的大学感知到一个不同于当前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并着力实现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大学……它明白世界可以超越自己在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中所呈现出的面貌,即便它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中应付这个世界。即便它不能清晰地表达诸如公平、自由、照顾、关怀、尊敬这样的大观念,但这些观念仍然可以启发它在世界中的存在。”
不难看出,巴内特试图复兴的那种形而上的大学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这种大学形态始终与既定的世界秩序保持一个潜在的或现实的批判关系与否定关系,不仅当下的世界没有耗尽大学的可能性,而且现实中的任何一种世界都不可能耗尽大学的可能性,大学始终可以在对世界的批判中不断实现自身无限的存在;另一方面,对可能性的展望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批判和否定现实中的大学,而是以宏大的价值观念作为实现的方向或目标,它在将大学推向未来的同时也在改善周遭的世界。所以,巴内特的见解绝非一种认为“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哲学和虚无主义哲学,而是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两个方面。事实上,在巴内特的心目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关于未来大学的具体蓝图,包括流动的大学、疗愈型大学、本真的大学和生态型大学,其中又以生态型大学最值得我们关注。
自美国社会学家帕克与伯吉斯于上世纪初采用生态学的视角研究城市社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人类社会问题[8],而系统的方法和动态的视角是贯穿生态学研究的两条轴线。正如巴内特所言:“生态的观念指向各种系统,指向它们的关联。它让人关注到环境、环境中的各种实体的动态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然而,生态学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的重要特征在于,前者务必在实证描述的基础上做出一定的价值判断,而这种判断的必要性演绎自“生态平衡”的概念。生态平衡指的是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在相互作用下处于高度适应、协调统一的状态,这显然是一种值得追求的良性状态。就此而言,巴内特认为:生态的观念同时包含着伦理的维度,它蕴含着面向整个生态系统的关怀与责任。
因此,基于巴内特所认同的弱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大学以及生态的观念所蕴含的伦理维度,生态型大学的内涵便非常清晰了。一方面,生态型大学作为一种未来的形而上的大学,总是保持着对无限可能性的敞开态度,并且以各种宏大的价值作为指引自己走向未来的路标;另一方面,这种价值的实现活动是面向环境整体的,而随着全球化的步步深入,未来的大学所面对的环境即是整个世界。根据巴内特的总结,生态型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值得青睐的未来大学形态,正是因为它统摄了上述两个方面。换言之,它与“无限”(infinite)和“大全”(universal)这两个形而上学观念之间的关联最为紧密。“生态型大学的理念沿着的空间伸展,并敏锐地察觉到针对世界的一切解读方式:它的包容精神在本质上是的。”
四、结语
综上,本文从巴内特对于大学面向未来的可能性的关注入手,首先考察他对于形而上的大学的回顾。作为历史中实际出现的大学形态,形而上的大学直接显露出大学的神秘性以及建立在这种神秘性之上的可能性。其次,本文追溯了大学的神秘性在现代性进程中逐渐隐没的原因和表现,分别分析了三种不同的现代大学形态及其各自对于大学可能性的限定。最终,本文表明,巴内特在当前时代对于形而上的大学的回顾并非意在恢复这一古老的大学形态,而是为了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大学的神秘性与可能性,他进一步提出生态型大学的概念,以便具体构想一个能够满足“无限”与“大全”的形而上学观念的未来大学形态。诚然,巴内特对于大学的畅想不乏乌托邦色彩,他本人对这一点也毫不避讳,但重要的是,巴内特的理论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衡量现行大学的重要尺度,并在他的启发下敢于畅想大学的未来形态。只要能够实现这一点,巴内特的工作就值得我们加以梳理并仔细研究。
注释
①“形而上学”一词的古希腊文是 τà μετà τà φυσικá,其直接的意思是“在物理学之后”。如果严格按照字面翻译,应当将其翻译为“元物理学”。
[1]BARNETT R.Thinking about Higher Education [G]//GIBBS P,BARNETT R.Thinking about Higher Education.Cham:Springer,2014:9-22.
[2]KIM J,et al.A Companion to Metaphysics[M].West Sussex:Blackwell,2009:413-414.
[3]BARNETT R.Being a Universit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1:11-56,141-154.
[4]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227.
[5](美)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M].张新樟,刘景联,译.谢华育,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12.
[6]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4.
[7]MARCUSE H.One-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M].New York:Routledge,2012:176.
[8]范国睿.教育生态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