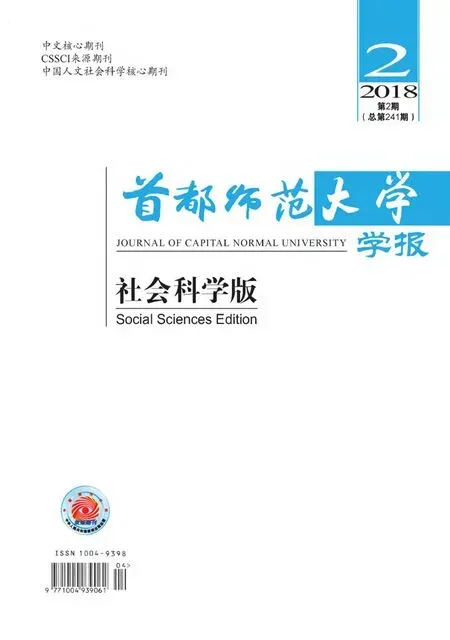哲学家的身体认知
——评舒斯特曼的“金衣人”系列
2018-04-03陆扬
陆 扬
一、无言的认知
2016年,理查·舒斯特曼出版了一本小书《金衣人历险记》。这是他同法国摄影艺术家扬·托马(Yann Toma)通力合作的一个硕果,记录了哲学家持续有年的一段身体美学行为艺术实践。有鉴于笔者承担了这本小书的中文翻译,舒斯特曼后来又发给笔者题为《无言的哲学家》的长文,交代了这一段身体力行身体美学故事的来龙去脉。由此我们可以回想到2008年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一书里开门见山的一段话语:当代文化焦虑日增,对于热点、过度刺激这类问题益发不知所云,特别是虚假的身体形象,让个人和社会都不满意。所以要提倡一种身体意识,来补充传统的哲学趣味。这不是说哲学总是忽略身体,就像大多数身体的热心人抱怨的那样,反之:
事实上,哲学前赴后继高扬心灵与精神的过程中,身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普遍是反面性的)。它天长地久的主导性负面形象,诸如囚牢、分心的累赘、错谬堕落的根源等,一方面充斥于唯心主义的偏见而推波助澜不断强化,一方面又为西方哲学家通常展示的身体修炼所视而不见。*Richard Shusterman, Body Consciousness: A Philosophy of Mindfulness and Somaesthe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ix.
舒斯特曼没有说错,身体在西方哲学中的确向来命乖运蹇。柏拉图便以《斐多篇》灵魂的自由对比身体的不自由,判定身体的七情六欲就像囚笼,禁锢了自由无羁的灵魂。所以死亡不可怕,它不过就是灵魂摆脱身体的束缚,重归自由天地。这个道理普通人不懂,但是哲学家深明其理。舒斯特曼并举例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指出根据他可敬的学生波菲利写的传记,普罗提诺羞于身体欲望,以至于不仅拼命节食,而且坚决不洗澡。这也没有说错,普罗提诺以肉身为耻是出了名的,差不多是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一心向慕精神,如他完全戒除肉食,而且从不言及家族身世,拒绝别人给他画像。要不是波菲利在老师去世后整理出他的《九章集》,这个哲学史上划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很可能就在本人自娱自乐、尽情享受过沉思冥想的快乐之后,就此隐没无闻。
普罗提诺醉心哲学一至于此,恐怕今天除了引来无比钦佩,很少人会乐于效法。但是舒斯特曼认为从柏拉图主义到新柏拉图主义,是彰示了古代哲学一个有别于文学和诗的传统,那就是哲学不但是一种语言形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哲学不但见诸于语言或文本表达,更应该付诸行动。是以古罗马哲学家如西塞罗、塞内加、爱比克泰德,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蒙田,都看不起只善于夸夸其谈,却忽略生活本身的哲学家,认为他们不过是“学究”,要不就是“数学家”,只会教人如何论辩,却不教人如何生活。而照蒙田的说法,吾人天责是为构造性格,而非构造书本。虽然,这一视哲学为生活方式的传统,随着现代社会学院派的兴起,日见凋落,舒斯特曼认为,我们依然可以来回味梭罗的哀叹:“今天我们有哲学教授,却没有哲学家。”*H. D. Thoreau, Walden, in Portable Thoreau, New York: Viking, 1969, p.20.不过另一方面,舒斯特曼也承认生活与哲学写作,也就是实践与理论之间,并没有矛盾。即以斯多亚学派乐天安命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来看,也是由它的哲学话语给予了充分佐证,将世界看做一个完美的活生生的有机体,万事万物莫不是整体的必然组成部分,所以必须接受下来。
但是说到底,哲学的真谛在于“认识你自己”,这是苏格拉底在德尔菲神庙里发现的神谕。舒斯特曼引述了柏拉图《斐德若篇》中的一段话,时当斐德若问苏格拉底是不是相信风神波瑞阿斯抢亲希腊公主俄瑞堤亚的神话。苏格拉底答道,他哪有功夫关心这些杂七杂八的一应知识呢,因为“我到现在还不能做到德尔菲神谕所指示的,知道我自己;一个人还不能知道他,就忙着去研究一些和他不相干的东西,这在我看是很可笑的。”(230a)*朱光潜:《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5页。
那么,舒斯特曼是不是知道他自己呢?舒斯特曼立足他广有影响的身体美学实践,或许感觉到已无必要像苏格拉底那样故作谦虚。他指出,柏拉图这篇对话是以认识自己为哲学目标,展开了对哲学文字的最猛烈批判。苏格拉底谴责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字,甚至肯定了文字给他本人也带来娱乐的文学价值,但是哲学不同于文学,哲学讲究严谨,即便将它同“高尚娱乐”并提,也还是不相宜,因为它关注心灵的健康。故而五花八门的知识,是有损记忆,荼毒心灵。文字则是给人提供空洞概念,无视记忆,一如过眼烟云。特别是哲学文字,认识论上先天不足,因为作者不在场,无法即时答疑解惑,所以就束手无策,任人误解。最后,书写的语词作为口头交流的苍白幻相,跟生气勃勃的鲜活话语,亦即“写在灵魂里的知识话语”,相隔两层,要低下一等。对于苏格拉底,更准确说柏拉图的上述思想,舒斯特曼表示完全认同。同时他强调指出,希腊语境中的“话语”或者说“言词”,是为“逻各斯”(logos)的衍生概念,而逻各斯不仅是指思想的语言表达,同样也指涉未经表达出来的内在的思想本身。
舒斯特曼本人著作丰厚,一如柏拉图谴责诗歌又以写诗手法来写哲学的言不由衷,不可能真心认同上述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传统派定给文字的种种不是。之所以枚举这类德里达解构主义更要耿耿于怀的所谓文字“罪责”,舒斯特曼主要是想说明无言的思考同样重要。换言之,逻各斯同样指涉这类无言的沉默认知。他引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话,“我语言的局限意味我思想的局限”,认为维特根斯坦同样认可无言的思考。但即便这类无言的思考,舒斯特曼强调说,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也需要某种概念和语词联系起来,因为这类思考倘若要连贯起来并见出意义,必是发生在思考者的生活形式之中,而这个构成他思想、目标和行为背景的生活形式,又必得借助语言交际予以创造和维持。所以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舒斯特曼表示,他也愿意认同无言的认知、无言的理解,以及无言的表达。既然无言,那么身体登场,便是顺理成章了。
二、金衣人的甘辛
《金衣人历险记》中,舒斯特曼开门见山,这样介绍了他从2010年开始,为时数年,远谈不上一帆风顺的一段哲学联手艺术、哲学家联手艺术家的行为艺术实践经历,对于身体美学可以提供何种启示:
这个故事的构思,故而是彰示了它的一个核心主题,那就是自我在走火入魔之后,是多么风雨飘摇、变幻无定。这个主题具有意味深长的美学和身体美学推论:通过金衣人对我身体的占领和转化,我体验到了审美经验的新能力和新手段,但同时我也希望,我的读者通过阅读这个故事,一样可以领悟到这些新能力和新手段。我开放自己、转化自己,也面临着伦理学上的困惑。它冒着丧失我们自治和自制意识的风险,即便这意识说到底不过是镜花水月也罢,就像金衣人教导我的那样。*Richard Shusterman and Yann Toma, The Adventure of The Man in Gold: Paths Between Art and Life, Paris: Hermann éditeurs, 2016, p. 8.
对于金衣人故事的诞生,舒斯特曼本人在《无言的哲学家》一文中也给予了一个说明,坦言他早在写作《身体意识》时,就有了通过身体力行的身体美学实践,来探讨上述无言之智慧的想法。盖因哲学作为一种生活的艺术,认识自我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生活哲学不光涉及认知,而且涉及行动,事关增强和美化我们的生活行为。鉴于近年来同艺术家联系频繁,舒斯特曼意识到他的身体美学主张不可能仅仅流于纸上谈兵,他必须回答其洋洋洒洒的身体美学理论,同艺术实践究竟能有多大关系。这个关系舒斯特曼事实在《金衣人历险记》中的序言部分已经作了回答。上文毋宁说更像是个提纲挈领的哲学说明。
关于“金衣人”的诞生,舒斯特曼《无言的哲学》一文中的回忆是,2010年他结识巴黎灯光艺术家扬·托马(Yann Toma),最初是在洛亚蒙中世纪修道院里拍摄艺术照。照相机固定在三脚架上以便长时间曝光,扬则手提摄影灯,不时在摄影对象身上打出特效光线,在转瞬之间追踪其身体能量。无奈他在一片漆黑的封闭空间里一动不动摆姿势,一天一夜下来实在难受得不行,终于忍无可忍,冲出黑暗,来到修道院阳光明媚的院子里。这时候他身上还穿着紧身演出服,那是扬的父母传下来的,他们当年是巴黎舞台上的芭蕾舞演员。舒斯特曼说,扬提议让他套上这件金光闪闪的紧身衣然后拍照,说是他穿进这件芭蕾服表现身体能量,是再合适不过,因为它紧绷住身体,而且闪闪发光。扬平时给他拍照,很少会出这类怪点子,不过这一次他以为舒斯特曼身材瘦削,而且胆大,不妨一试。一试下来,哲学家大吃一惊,居然正巧合身!迄至此时,金衣人故事的静态第一阶段,告一段落。
然后是扬提着器具紧追不舍,两人一先一后来到微风和煦、生机勃勃的院子里。扬手里换了摄像机,开始跟拍他的手舞足蹈,由此进入了这个故事的动态第二阶段。由于他的即兴表演耗去许多时间,修道院女主人安排好的周末午餐已经恭候多时,舒斯特曼来不及回到黝黑的裙房里替换正装,干脆就径直去赴午餐吧。顿时,桌边一众人瞠目结舌,望着眼前的幽灵不知所措,不过大家高高兴兴原谅了两人的迟到,女主人一声惊呼“L’hmme en Or”(金衣人)!舒斯特曼化身的幽灵,遂此有了自己的名字。
当天夜里,舒斯特曼与他的好搭档扬来到巴黎僻静一角,拍了一大段身体美学的操演视频。对于“金衣人”的正式诞生,舒斯特曼的感受是,他从以往静态的被拍摄对象解放出来,成为主动的合作伙伴,的确是如释重负、扬眉吐气的事情。巴黎午夜拍摄完毕之后,他们又先后去了哥伦比亚神秘的海滨古城卡塔赫纳、弗罗里达迷人的南部海岸、丹麦日德兰半岛的广袤农庄,以及波兰罗兹的废弃厂区。历时数年,而且有心向未来延伸。相关的照片和电影,舒斯特曼将之命名为《身体流量》(Somaflux),分别在巴黎、波哥大、赫尔辛基、斯托克霍尔姆等地办过展览。可以想见,假如中国有机会的话,舒斯特曼和他的摄影艺术家搭档,一定会非常乐于来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拓进展示他的“金衣人”行为艺术系列,进而示范他的身体美学,可以怎样从理论到实践,然后再度回归哲学的践行之道。
金衣人历险记远非一帆风顺。根据《金衣人历险记》书中的交代,酣畅淋漓的巴黎午夜,后来给扬的学生艾略特·斯托利(Elliot Storey)剪辑成了一个短片《舒斯特曼一夜情》(ANightwithRichardShusterman),并在2012年巴黎的一次艺术展上放映过。但是金衣人诞生还未及满月,舒斯特曼回忆说,当时他跟9岁的女儿在纽约机场,准备飞蒙特利尔,两人正兴致勃勃在电脑上筛选扬发给他的洛亚蒙原始文件,突然就有女保安矗立面前,凶神恶煞般勒令他不得给儿童看色情照片。全然不顾那是艺术、不是色情的无力辩解。然后是次年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金衣人又碰了一个钉子。当时舒斯特曼来到此间,出席法国—哥伦比亚身体美学双边会议,住在豪华酒店里。与他不期而遇的扬等一众,则住在城里的普通旅店。两人当晚相约来到海滩拍摄,但见波光粼粼,金衣人陶醉良辰美景,不能自已。结束拍片,已经是凌晨2点。金衣人回到酒店,意犹未尽,走进电梯,套上舒斯特曼的衣服,却突然发现杨临走忘了帮他拉开芭蕾服的后背拉链。金衣人背过手去,扭成麻花,也够不到拉链,无奈只得来到大堂前台求助。底下发生的事情始料不及似又在意料之中:
两个壮汉在那里值夜班,一面聊天,一面心不在焉瞟着电脑里一部日本色情电影。金衣人脱下我的外套,露出他的金色紧身衣,彬彬有礼问道,“请问能帮我拉下拉链吗?”这两个彪形大汉紧盯住我,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然后窃窃暗笑,满脸鄙夷地交换了几句表示嗤之以鼻的西班牙语。其中一位不屑地耸了耸肩膀,粗暴地一把扯下拉链,几乎扯到他的臀部,说道,“行你的,太太,还要来个晚安吻别吗?”*Richard Shusterman and Yann Toma, The Adventure of The Man in Gold: Paths Between Art and Life, Paris: Hermann éditeurs, 2016, pp. 49-50.
我们可以想象时年60岁的哲学家穿上芭蕾演员的演出服,突然亮相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情景,以及哲学家的尴尬,会是什么模样。艺术家的公共空间相对封闭小众,但是普罗阶层的趣味与生俱来,面对“金衣人”这个实用主义哲学麾下,身体美学的行为艺术时新实践,表现出的与精英空间判然不同的抵触态度,也许同样适用于布尔迪厄提倡的阶级区隔分析方法。上述2012年巴黎艺术展后,巴黎塞纳河边的一群醉汉,污言秽语恶声以向,同样曾吓得金衣人落荒而逃。这都可以显示,中产阶级见多不怪的形形式式行为艺术实践,在普罗阶层的普及似还尚需时日。
所以不奇怪,《金衣人历险记》题为《巴黎之夜与热带海岸》的第二章里,舒斯特曼自称金衣人背后有两股巨大的推力:爱和恐惧。爱自不待言,恐惧则一如他的爱具有世俗和神圣的两重性质,同样也是双重的:一是被拒绝的恐惧,一是被误解的恐惧。金衣人洛亚蒙修道院降生之初,固然是受到了热烈欢迎,可是后来的经历里他不断受挫,伤痕累累。有人疑神疑鬼,对他不屑一顾;有人怒目以向,拒之门外;有人挖苦嘲笑,恶言相斥。这一应尖酸刻薄的闭门羹,让他黯然神伤。舒斯特曼说,金衣人渴望爱,渴望被人接受。可是他天性胆怯,惧怕恶语相斥,只能远远避开社交圈子。只因为这一身金色肌肤,经常被人曲解为性欲和变态装备。有时候遇上近视眼或者小心眼观众,甚至误以为那是裸体,是以冲着金衣人尖叫,叫他披上衣服。或者指责说你这鬼模鬼样矗在那里,本身就是色情范本。这些痛苦的误解,舒斯特曼坦言,使他感到的确是有必要来深入谈一谈金衣人故事的艺术意义以及哲学启示了。
三、哲学家的身体与艺术
但是,我们发现在中产阶级社会空间中,金衣人便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金衣人历险记》的第三章《海盗王后的神舟》,便提供了这样一个近似世外桃源的艺术空间。时值2013年,舒斯特曼得到丹麦奥尔堡大学一年访学的邀请,却因丹麦移民法的限制,因为不是欧洲公民而未成行。但是奥尔堡大学最初发出邀请的两位女同事温柔化解了哲学家的在背芒刺,给了他非常热情的个人欢迎。于是金衣人的故事再度拉开帷幕,事件的起点是女主人艾尔丝·玛丽(Else Marie)质朴的海滩屋舍,屋舍矗立在延绵起伏、岩石裸露的沙丘上,那正是波罗的海和北海的交汇处,北日德兰半岛的尖端。舒斯特曼这样交代了这次金衣人北欧操演记的缘起前奏:
我们这次见面,目的是商议奥尔堡大学出版社同意刊行的《身体美学杂志》事项。但是艾尔丝·玛丽,这位丹麦皇家美术学院前院长,同时还想给我们看看两位雕塑家的工作室,他们是克劳斯·安托夫特(Claus Ørntoft)和玛丽特·班蒂·诺尔海姆(Marit Benthe Norheim),一对住邻近村庄附近旧农舍里的贤伉俪,周围是良田美景,树木葱茏。克劳斯刚刚完成一尊狮子雕像,打算作为礼物献给丹麦女王。班蒂正沉浸在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里,欲制作一系列大型维京海盗航海救生艇,材质是钢筋混凝土,以表达出一种坚强却又优雅的女性主义。是以船首不见龙头,但见一个可爱的女性脸庞,下面船体则勾勒出她起伏有致的乳房。我同艾尔丝、斯达尔在他们的寓所和工作室里,度过了一个长长的夏夜。这地方环境迷人、主人好客,特别是艺术能量想象力高张,我心想倘若金衣人重新出山,造访此间,岂不美哉。*Richard Shusterman and Yann Toma, The Adventure of The Man in Gold: Paths Between Art and Life, Paris: Hermann éditeurs, 2016, pp. 76-77.
就在这块令人心旷神怡的北欧土地上,次年5月一个周日,舒斯特曼跟扬携手,再度从巴黎飞往奥尔堡,来到艾尔丝·玛丽的海滩美居。待夏日长昼过去,太阳消失在地平线后面,已是将近午夜。习惯了黑暗的金衣人遂此现身,在克劳斯·安托夫特和玛丽特·班蒂这对贤伉俪艺术家的雕塑现场和工作坊里,尽情漫游。最后,金衣人与一尊被哲学家命名为“完美”的少女雕像之间,演绎了一段如火如荼的柏拉图式爱情。完美何许人也?按照舒斯特曼的交代,在班蒂雕刻出来的那些惊艳玉女中,有一位气质绝佳,尤其显得温婉可人,是为艺术家一切美丽创意的理想原型。她名叫Wanmei,这是中文,意思是完美。她那娇小玲珑的身躯是如此迷人,以至于一家日本色情公司找上门来,要买她过去,做性爱娃娃的生产原型。可是她不但美艳无双,而且意志如钢,即便遭遇色欲目光,也镇定自若。金衣人渴望同她相见,相信她能让他梦想成真:他天长日久期盼着母亲身上那种慈祥的爱,能化成肉身,让他拥抱一下!
金衣人到底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幽暗纵深处。《金衣人历险记》的封面上,刊出的便是金衣人与这尊少女雕像的奇妙合影,笔者曾这样描写过这个封面:“身着芭蕾紧身衣的舒斯特曼温情脉脉相拥低他半首的完美,鼻尖正对雕像额头,两人一为俯视,一为仰视,惊为天合。金衣人极是怜香惜肉的神情,完美仿佛通体燃烧,又满是仰慕的姿态,可谓哲学联姻艺术的绝妙写照。”*陆扬:《评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实践》,《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第164页。
回到前面的问题。金衣人故事的艺术意义和哲学启示又是什么?这一点,其实《金衣人历险记》一开篇就有记述。舒斯特曼坦率交代说:
我为什么要向这次吉凶莫测的魔幻行动开放自身呢?我也不知道答案。长久以来,我受惠于批判思维的哲学模式教诲,更良多感慨生活中的连连惊诧,故此对自知自觉的确定性和洞穿我们最深沉真实动机的能力,向来持怀疑态度。我们都是自欺欺人的大师。但是,我一旦来尝试理解金衣人给我带来了什么,三个因素马上凸显出来,横亘在我走火入魔的道路面前。首先,我经常去形形色色的法国艺术学校讲演身体美学,甚至用身体美学方法来开工作坊,在那里我反复面临着一个持久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直截了当,而且极其务实,那就是,“身体美学如何用于当代艺术?”我的回答通常是,身体,以及它的感觉、动量和情感资源,是我们创造和欣赏艺术作品的媒介,所以身体力行,有助于促生更好的审美经验。*Richard Shusterman and Yann Toma, The Adventure of The Man in Gold: Paths Between Art and Life, Paris: Hermann éditeurs, 2016, p. 8-9.
可见,哲学家的身体同样是有他的苦衷。不错,身体,包括身体的感觉、动量和情感资源,是我们创造和欣赏艺术作品的不息源泉,身体力行可以有最好的审美经验。但是舒斯特曼感叹说,这些高头讲章在艺术家那里其实行不通。艺术家读德里达、利奥塔,然后灵感滚滚而来的解构主义时代已是明日黄花,今天艺术家不以为然夸夸其谈,需要舒斯特曼能够示范,他的理论可以如何更具体地应用到当代艺术的创作实践上去,他的著作可以如何提供现成的艺术案例。对此舒斯特曼自称他也一头雾水。是啊,从哪里去发掘呢?是不是他非得来亲自付诸实践呢?舒斯特曼果不就是化身“金衣人”,用自己的身体实践了他的身体美学理念。
舒斯特曼阐述过他金衣人系列两个层面的艺术意义。《无言的哲学家》中他说,一方面,他认为自己这个金衣人系列超越了传统摄影的静态图像,而涉及到即兴舞蹈、即兴交流等一系列复杂的行为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极富有创造性的身体美学示范。而且创造是互动的,扬的灯光追踪金衣人能量,摄影和摄像构成这个系列的背景和场面调度,但是背景和现场调度,本身也包涵扬本人的能量和运动,反过来它又影响了金衣人的表演。故而无论是这个系列的摄影、剧照抑或录像,都是他所真心喜爱的。它们让摄影艺术从静态走向动态,一如其所激发的审美经验,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另一方面事关生活艺术与艺术世界的纠葛。舒斯特曼认为,他的金衣人系列不仅是给作为行为艺术的摄影提供了理论洞见,而且进一步就艺术、哲学与生活的复杂关系,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到他长久倡导以生活为艺术的实用主义哲学立场,但是先时著述尚未有充分论证。那就是,生活艺术和艺术世界的艺术,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倘若真正的艺术系由艺术世界来作界定,而且圈定在艺术世界之中;倘若艺术世界被定义为针锋相对于生活世界,是以艺术(从柏拉图到阿瑟·丹托的传统来看)同样被定义为针锋相对于现实事物,那么“生活的艺术”不过是一个比喻说法,它同艺术世界存在隔膜,没有实质性的亲密联系。舒斯特曼发现这一生活与艺术的二元对立,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便初露端倪,它表现在亚里士多德对praxis和poesis的著名区分,前者是我们的生活行为,后者是我们的艺术制作,而艺术在于亚里士多德,不过就是技艺,与我们的内在生活毫不相干。
由是观之,舒斯特曼以他的金衣人系列身体美学实践,无疑正如哲学家本人反复重申的那样,突破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壁垒和隔膜。据舒斯特曼观之,艺术不是别的,它就是生活中各种经验、能力和能量的表达,即便是死亡经验也不在例外。艺术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即便是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唯美主义信念也不在例外。艺术对于生活必有其实用价值,即便是纯粹消遣也不在例外。唯其如此,艺术可望超越文化的界限而无所不在、永世长存。今天方兴未艾的生活美学辩论中,实际上存在一个二元阐释分歧:生活美学究竟意味着艺术放低身段,向生活看齐;抑或生活升华品格,向艺术看齐?由是而观,舒斯特曼的上述实用主义身体美学立场,特别是金衣人系列的行为艺术实践,对于生活美学何去何从的两种进路,可以提供从艺术到哲学层面的多重借鉴意义,当是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