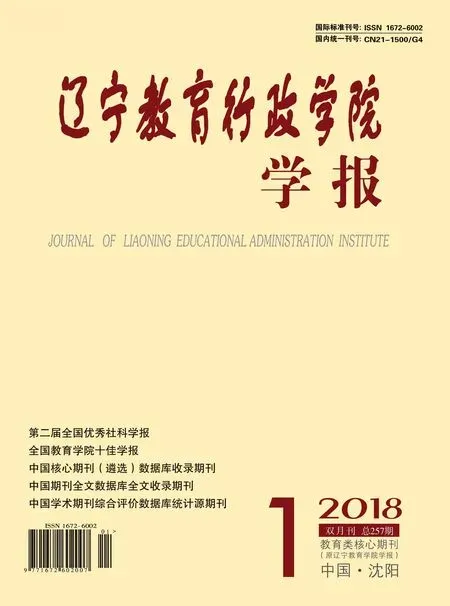庄子“天籁”论与毕达哥拉斯“诸天音乐”论比较研究
2018-04-03吴泽南
吴泽南
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136
庄子和毕达哥拉斯分别是中国和西方早期哲学美学的代表,而“天籁”论和“诸天音乐”论是他们论述美的问题和艺术问题的代表性观点。后人对庄子和毕达哥拉斯生平及其理论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争议和不明晰之处,我们今天所说的庄子哲学美学和毕达哥拉斯哲学美学基本是指他们及其弟子各自形成的庄子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美学理论,立足于《庄子》一书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残片断语。庄子的天籁论集中见于《庄子·齐物论》的开篇“南郭子綦隐机而坐……怒者其谁邪?”①[P16]一段。历来学者们对“天籁”的看法不一,历史上有关庄子“天籁”的解释可参看钱浩《再论庄子的“天籁”》和张和平《“天籁”新解——兼论“天籁”与庄子哲学》两篇文章,此处不再赘述。毕达哥拉斯的“诸天音乐”论见于亚里士多德等后学者对毕达哥拉斯学派言论的引用和阐释中,以残片断言的形式存在并传世。我国学者将毕达哥拉斯关于天体运动所产生的音乐的理论有“诸天音乐”论②[P24]、“天体音乐”③[P19]论、“天籁(天体的谐音)”④[P182)论等多种译法。一方面,毕竟“天体”与中国古代的“天”的概念内涵不同,为了区别于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天籁”论,而且也为了准确表达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作为整体的宇宙的理解,本文取阎国忠先生“诸天音乐”的提法。国内对庄子“天籁”论研究尚存争论,对毕达哥拉斯“诸天音乐”论的研究又尚不充分,对二人的美学思想的对比研究也仅有一篇硕士论文供我们参考,在这种研究状况下,本文试对这两种理论进行简要的对比分析,以抛砖引玉。
毕达哥拉斯和庄子音乐理论是其哲学理论在艺术领域内的自然延伸,要想弄清“诸天音乐”论与“天籁”论的异同,必须从其理论根基即各自的哲学理论开始辨析。庄子“天籁”并不是与“地籁”“人籁”属于同一层次的乐器或声音,而是指“道籁”,⑤即“道”之声,天籁正是道在声音方面完美的表现形态。与庄子“天籁”类似,毕达哥拉斯的“诸天音乐”也是作为万物本原的“数”的一种完美的表现形态。“任何一个物体的运动,都会产生一种声音,日、月、星辰也不例外,他们的声音决定于它们的速度,而它们的速度又决定于它们的距离”,②[P24]毕达哥拉斯“关于数是现实的本质的一般假定,在音乐中找到了最有效的证明”。③[P18]毕达哥拉斯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数量关系及其几何构成,世界的构成和运动都受制于某种数的关系,而这种数量关系使得整个宇宙的运动产生和谐的音乐,因此,我们也可说毕达哥拉斯的“诸天音乐”就是“数籁”。“道”与“数”是两位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规定,“道籁”与“数籁”是世界本原在宇宙层面和音乐层面上的完美形态。
一、“道”本体与“数”本体:“道籁”的无限无相性与“数籁”的形体结构性
毕达哥拉斯认为,作为世界本原的“数”,“是事物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几何形式结构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数,是一种图形数、几何数”,是“事物所由产生与存在的一种本质规定”。④[P173、176]与古希腊早期哲学的其他学派将世界本原理解为水火土气等具体的物体不同,毕达哥拉斯寻求事物内在的数的规定性,他不从事物的生成和复归的动态变化的时间过程中,而从事物的空间结构中,寻找世界的本原或原理;但毕达哥拉斯的“数”又与柏拉图的“理式”不同,他不从脱离于具体事物之外的精神实体中寻找事物的规定性,而认为“作为本原的数就存在于事物中,是表现在事物的形式结构中的一种数量关系”。④[P174]万物模仿数而构成自己,天体也是如此:由于数的规定性,天体运动的距离、速度等因素都具有了符合数的和谐的结构,这种和谐的结构中就产生了“诸天音乐”。由此可见,毕达哥拉斯的“诸天音乐”首先体现为一种形体性、有限性和确定性,而庄子的“天籁”正与此不同,体现出中国哲学中“道”的无相性、无限性和不确定性。
在庄子看来,“道”是“无为无形”“自本自根”“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刻雕众形而不为巧”。①[P102、207]从万物派生和复归的时间过程看,“道”类似于“水火土气”,“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①[P26]它是万物演化的起始和复归的终极目的;从万物存在状态的等级序列看,它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式”,它处在世界等级序列的顶端,它统摄万物的运动变化却脱离万物而自在;从世界的空间结构看,道浑然一体、无孔无窍、无形无相(当然,“道”与“水火土气”、“理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本文不作进一步的阐述)。从而,作为“道”的完美形态之一的“天籁”也就具有“道”的特性。首先,“诸天音乐”不同,“天籁”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形体和几何结构作为基础,“天籁”与“地籁”“人籁”的不同在于它不受孔窍和风吹的限制,即不受“物于物”的束缚,“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①[P16]而毕达哥拉斯“诸天音乐”则受制于天体运动和数的关系的几何构成。叶秀山先生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为“反无定形性学派”,④[P179]这就概括了毕达哥拉斯哲学美学和庄子哲学美学的区别,也就是“诸天音乐”和“天籁”的区别。其次,庄子“天籁”处于三籁的等级序列的顶端,这与“道”的序列位置一致,“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夫言非吹也”,①[P24]也就是说人籁处于最低等级而天籁处于最高等级;而在毕达哥拉斯那里,“诸天音乐”虽然是数的完美形态,但万物都模仿数而构成自己,各种音乐之间并没有明显等级序列的存在,只是模仿的完美程度上的差异。
二、否定的辩证法与和谐的辩证法:“道籁”的超越自反与“数籁”的和谐统一
毕达哥拉斯学派说“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⑥[P35]毕达哥拉斯的哲学美学建立在以数为基础的“和谐”与“对立”之上,音乐一方面,遵循着数的关系及其几何结构,另一方面,体现为对立面协调统一所形成的和谐之中,而“和谐是一种结构,数的结构。它使有限和无限相同一,使事物获得明确的规定性”。⑦[P4]“诸天音乐”是数的完美的表现形态,也是和谐的完美表现形态,“诸天音乐”如同一个有魔力的音乐盒,在固定不变的和谐的数量关系的控制下播放,周而复始永恒不变,它保持着一种永恒的和谐。这和希腊的时代精神和文学艺术创作风格有很大关系,“希腊思维具有静观性,因为它认可现有的存在,而不要求对存在作根本的改造”,⑦[P5]而希腊艺术则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诸天音乐”所蕴含的正是这种在固定不变永恒和谐的“数”的理性的宰制下的制度性结构性运动,就如同行星在固定轨道上或者按照固定的运行规律围绕恒星运动。
而庄子“天籁”则是对孔窍和“物于物”的超越,这种超越性是毕达哥拉斯“诸天音乐”所不具备的。在庄子看来,“地籁”与“人籁”是由于各种孔窍和是非之辨形成的,是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分辨而成的,而“天籁”则是道的“独”的结果,道的存在和运动无所凭借。“反者道之动”,对道的这种存在状态和运动过程的理解是为老庄所一以贯之的。道不断地进行自反性运动,又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完成自身,道本身就是道的运动和生成过程。道生成万物的过程是道自我否定的过程,正如混沌死而万物生。数是永恒的辩证和谐,“诸天音乐”围绕数的逻各斯而律动,就如同经济学中价格围绕价值的浮动。而道是永恒的自反性,“天籁”正是道的不断自我超越和复归过程中变化不羁的声响。由此可见,庄子“天籁”是一种无限、无为的,变动不羁的超越性的美,而毕达哥拉斯的“诸天音乐”更具数学性、形体性和程式、机械的和谐性。
三、经验的感知与理性的认识:“道籁”的大全不知与“数籁”的通灵神秘
庄子和毕达哥拉斯的宇宙学美学也影响到“天籁”论和“诸天音乐”论的内涵差异。毕达哥拉斯的宇宙观即是数的和谐的宇宙观,“星体以和谐的距离彼此相间隔,以预定的速度沿着自己的路线运行,而为它们运行所激起的灵气,则发出最强有力的旋律。可是,对人的耳朵来说,这无限美妙的乐曲却是绝对寂静无声的”。③[P19]前文讨论过的问题我们不再赘述,但有一点仍值得我们关注:庄子“天籁”与毕达哥拉斯“诸天音乐”都是寂静无声的,这是为什么?这之间有何异同?我们可以从他们各自的宇宙学美学理论中找到答案。
这里所谓的“宇宙学美学”,是指在人类思想早期,美学问题还没有作为独立的问题被讨论,美学问题总是与理论家的宇宙观相联系相混谈,人们谈美即是谈宇宙。庄子认为宇宙之美始终与宇宙之真相联系。一方面,他认为,“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①[P247],“道”的无为是美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认为,“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①[P262],没有真就没有美。此外,庄子追求宇宙的“大”而“全”,“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在“天籁”之后,庄子提到“昭氏鼓琴”①[P29]的故事,认为用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不论音阶如何美妙多样都不及“道”的大全,只要是“孔窍”奏出的音乐都是对音之大全的亏损,因此,真正的道之音“天籁”是“不鼓琴”的无声状态,是一种朴素的“全”“真”状态。也就是说,“天籁”无声。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人是小宇宙,模仿大宇宙”,一方面,人与宇宙具有同构性,都以数为本体;另一方面,人与宇宙具有相通性,人能够通过自己内在灵魂的数的结构来感受宇宙的数的结构,人能够由人自身而认识宇宙进而认识作为本体的数。这样看来,“诸天音乐”就具有了认识论和宇宙学美学意义。诸天音乐是数的完美形态,也就是体现最高的善的音乐。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音乐作为特殊的艺术形式能够与人的灵魂相联系,数就如同一条细线将灵魂、音乐与宇宙通联起来。这样,诸天音乐既是人的至善品格的表达,也能够对人的灵魂起到引领的作用。这种“同类相知”使得,诸天音乐是一部“由于不断发声我们才听不见的交响乐”,“人并不能任意创造它们,而只能适应它们”。⑧[P107、110]
从表面上看,庄子力图将人从“知”引向“不知”、从“有”引向“无”,似乎是想要把人从丰富生动的现实生存引向看不见摸不着的大道之境,但事实上,庄子是主张远离那些狭隘的知识和工具理性而回到混沌大全的感性的经验世界,回到对“道”的最原初的体验。而从表面上看,毕达哥拉斯似乎试图揭开宇宙世界至高的理性——数的秘密,将包括天体和心灵在内的一切置于数的理性下运行,但毕达哥拉斯的哲学美学观点始终摆脱不了他的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摆脱不了古希腊酒神崇拜和奥尔弗斯教的神秘性——诸天音乐给人灵魂带来的迷狂与净化。
不论是庄子“天籁”还是毕达哥拉斯“诸天音乐”都与人的至善境界相联系,在庄子看来是“全”“真”“独”的至人、神人、圣人,在毕达哥拉斯看来则是纯粹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家,“仿佛经验的哲学家只是材料的奴隶,而纯粹的数学家,正像音乐家一样,才是他那秩序井然的美丽世界的自由创造者”⑨[P60],这是他们定义的人的终极幸福和最完美的生存状态。这样,“天籁”和“诸天音乐”也就有了属人的价值和伦理学意义。混沌与酒神有何差异?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耐人寻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注释:
①庄子著,方勇译注.庄子[M].中华书局,2011.
②阎国忠.古希腊罗马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③吉尔伯特,库恩.美学史[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④叶秀山,王树人,姚介厚.西方哲学史·第二卷(上)[M],凤凰出版社,2004年.
⑤吴根友,王永灿.“天籁”与“卮言”新论[J].哲学动态,2014(9).
⑥波里克勒特.论法规[M],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商务印书馆,2014.
⑦凌继尧.西方美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⑧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⑨罗素.西方哲学史[M],商务印书馆,1982.
[1] 庄子著,方勇译注.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 叶秀山主编,姚介厚著.西方哲学史·第二卷(上)[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6] 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7] 吉尔伯特,库恩.美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8] 汝信主编,凌继尧、徐恒醇著.西方美学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9] 阎国忠.古希腊罗马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10]吴根友,王永灿.“天籁”与“卮言”新论[J].哲学动态,2014(9).
[11]张和平.“天籁”新解——兼论“天籁”与庄子哲学[J].厦门大学学报,2011(5).
[12]钱浩.再论庄子的“天籁”[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