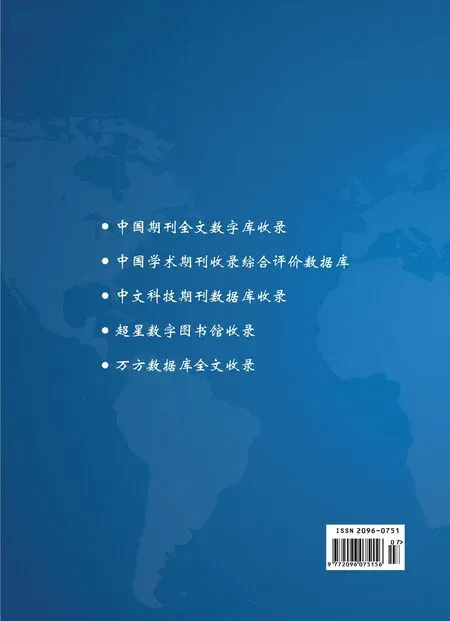从纪录片创作引发的若干思考
——以《北方的纳努克》为例
2018-04-02敖然
敖 然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 北京市 100024
纪录片以真实的生活为素材,以真人真事为对象,通过情节性的脚本自我构建,拍摄者通过影像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纪录片以真实为核心展现在大众面前。《北方的纳努克》拍摄于1920年,影片以季节为线索,以主人公爱斯基摩人纳努克的日常生活为拍摄对象,表现了他们捕鱼、捕猎海象、建造冰屋、与白人市场交易的场景,影片上映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基于田野,知己知彼
纪录片强调真实性,一部纪录片无论包括怎样的表现手法,其本质是以真实性为主,作为记录者首先要具有“田野意识”。所谓“田野意识”,本文认为记录者在拍摄之前,要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直接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然后在其基础上进行拍摄;纪录片本身就是表达一种文化,作为记录者在拍摄他者时,如果仅从自己的视角着手记录,最后呈现的影片极易与现实有偏差。本文认为,记录者要分清主位与客位,所谓主位就是强调研究者不受自身文化的束缚,置于被研究者的立场上,去了解、理解和研究问题,否则观察者在一个陌生的文化模式中,只能看到若干不相关联的因素,而看不到一个整体,用当地人的观点来努力理解当地人的文化。所谓客位是指研究是以调查者本身的立场为出发点来理解文化,研究者所使用的观念并不是当地人的观点。
弗拉哈迪本身是来自现代文明,当进入到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环境中,他并没有以自身高傲的姿态、浮光掠影地表现事物。而他首创了“交友式”的记录方法,在拍摄《北方的纳努克》的过程中,他花了22个月的时间,3次往返北极寒冷之地,与拍摄对象朝夕相处,深入把握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内涵,有效地组织所获材料,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通过“3个一”:一个主人公、一条主线、一个主题,镜头有力地记录了爱斯基摩人在苦寒之地的生存状态。由于记录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融洽,他们整个表现都是平静、淡然,仿佛没有摄像机的存在。
二、把握叙事风格,强调整体
视觉文化是随着影像的流行发展起来的,影像的出现给弗拉哈迪所处的年代的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体验。通过镜头的剪辑组合改变观众的视点,在叙述过程中展现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对素材的有效整合加之各种情节的建构,使得影片的叙事线索清晰明了、环环相扣、节奏更加匀称。影片《北方的纳努克》在结构上分成3个部分,天暖时期,人们修补捕猎的工具;寒冷时期,人们为食物而奔忙;在大风雪天气中,他们为生存所做种种努力。影片的主题展现的是爱斯基摩人纳努克一家人为生存寻找食物的种种场景,纳努克身上展现了弗拉哈迪的浪漫主义色彩。影片采用了好莱坞故事片的叙事方式,设置了高潮点,让观众随时发现兴奋点,比如大家伙在海水中共同捕猎海象时,那种紧张的气氛深深抓住了观众的心弦。另一方面,纳努克教儿子射箭的细节,在交易市场上,白人与纳努克之间的对话等镜头表达体现了影片浓浓的人文关怀。
《北方的纳努克》运用简洁的字幕来交代影片的背景,不拖沓、不冗余。整个影片在视觉上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弗拉哈迪在影片中一开始就营造了视觉上的悬念,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影片开始以银装素裹展现在大众视野,引人入胜,寒意袭人,这时只见主人公纳努克划着皮筏子从远处缓缓而来,然后在镜头下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纳努克划着皮筏子慢慢的驶过来,前头趴着Allee,然后他的妻子Nyla抱着他们的小孩子Cnayou,紧接着是Cumook,最后是一条狗。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皮筏竟然有这么大的容量,随后影片中出现了他们生吃鱼肉、用舌尖舔刀尖、早晨起床妻子把丈夫的靴子咬软等镜头,这不仅展示了爱斯基摩人的聪明才智,也让人感受到了现代文明与原始生活的碰撞。
纪录片不是“照相式”的记录,是讲究一些表现手法的,《北方的纳努克》中使用了平行蒙太奇。平行蒙太奇也称为并列蒙太奇,两条以上的情节线并行表现,分别叙述,最后统一在一个完整的情节结构中,或两个以上的事件相互穿插表现,揭示一个统一的主题,或一个情节。比如在《北方的纳努克》中有一段就运用了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在纳努克一家建造冰屋时,镜头一边表现了好猎手纳努克浇注热水融化冰块,使冰块更加严密结合在一起的场景;镜头另一边表现了孩子们在冰块上嬉戏玩耍的场景,镜头在大人和孩子之间转换,互相衬托、形成对比,体现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弗拉哈迪通过平行蒙太奇节省了影片篇幅、扩大了信息量、加强了影片的节奏感,这种拍摄手法被后来很多影片借鉴使用。另外影片采用了一些特写镜头与音乐搭配使用,更好的展现了影片的主题。
三、对于“真实性”的探讨
纪录片是为真实性服务的。在拍摄过程中某些因素限制了影片的表达,但是为了更好的展现主题,拍摄者会采用一些方法,“仿真、搬演、情景再现”等就成为了很好的补救措施。弗拉哈迪在《北方的纳努克》中就采用了“搬演”的手法,为了向观众展现爱斯基摩人猎捕海象的原始场景,把原来已经捕捉到的海象拉到海中,让纳努克以及同伴重新演绎一遍其父亲时期猎捕海象的场景。在建造冰屋时,冰屋通常是12英尺宽,弗拉哈迪为了展现更好的照明效果,要求冰屋为25英尺;因为冰屋是黑的,拍摄出来的效果不理想,为了尽可能的真实,拍摄只能在露天下进行,因此纳努克一家在冰天雪地里表演起床等细节引起了人们对“真实性”的讨论。很多人对《北方的纳努克》中的一些“搬演”场景有争议,认为这违背了真实客观的原则,而且为了配合拍摄,纳努克一家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储备食物,结果在第二年的寒冷季节被饿死,这也是很多人对此影片持批评之声的原因。本文对纳努克一家后来的命运暂不作讨论,本文认为对“纪录片真实性”的定义不能仅仅停留在把摄像机摆放在那里就可以了,弗拉哈迪推崇结果的真实,本文认为纪录片的真实具有相对性、虚幻性、局部性。由于时空的转瞬即逝,有很多原始的事物是不能再留存的,为了结果的真实,只能采用非常手段,尽可能避免主观因素,达到纪实的目的。在纪录片中经常有长镜头的使用,长镜头是增强纪录片真实感一个重要的美学方法,长镜头如同观众的眼睛,切实的表达镜头语言的完整性。《北方的纳努克》在纳努克把鱼叉投入冰窟窿的那个片段,采用长镜头的拍摄手法,我们并不会看到冰窟里有什么,然后镜头呈现了纳努克的紧拉绳索不放,企图把猎物从冰洞里拉出来,狩猎者与猎物反复周旋,这个场景扣人心弦,使观众身临其境,凸显了影片的真实感。此外,影片中“围捕海象”“离船上岸”“建造冰屋”等场景也都已经成为长镜头运用的最早典范,并为法国影评家巴赞的长镜头理论提供了依据。
本文认为纪录片的真实性还体现在拍摄对象在观看镜头里的自己时感到惊讶。拍摄出来的影片不单是让他者观看的,也应让被拍摄者进行观看,通过被拍摄者的观看反应可以估算出这部纪录片的成就之处和改进之处在哪些方面,这样更能显现出纪录片真实性的价值和对被拍对象的尊重。弗拉哈迪在影片拍摄结束后,第一批观众就是当地的爱斯基摩人,他在《北方的纳努克》一书中曾这样描述:他们(爱斯基摩人)一直向后看放映机的光源,就像看银幕一样,我以为这次放映不会成功,突然一个人大喊:“抓住它,抓住它”。他们以为海象真的会跑掉,当时屋子里一片混乱。爱斯基摩人在胶片中看到了自己和同伴的影子,他们开始互相耳语,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忽然之间,他们仿佛理解了我所做的一切。
四、对纪录片拍摄的借鉴意义
纪录片通过影像告诉观众现实世界的表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现实场景的通道;其次,纪录片向我们展示了视角之外的世界,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加强了他者与自我的沟通,从而减少心理上的隔阂。比如《北方的纳努克》中的很多生吃鱼肉、捕猎食物的原始场景等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他们整个民族的气质,在寒冷刺骨的极寒地区有这样一群爱斯基摩人,正是这样的艰苦环境造就了他们的生活习俗,也滋养了他们为生存而进行抗争的坚毅和勇气。最后,纪录片利用电影胶片、录音磁带逼真地记录下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已经逝去的事情,这也是一种对历史记录的手段。弗拉哈迪为古老文化的行将消逝深深叹息,正是在这种理解与崇敬的心态下,他毅然决定拍摄一部这样的影片。
纪录片不同于别的影像,作为记录者拥有了影像创作的能力,以摄像机为平台,运用影像叙事,传播其作品的文化意义,这就意味着其本身获得了文化权利。导演的存在威胁着社会演员的表演,如果导演过多干预演员的表演,或者说在影片中强烈地添加个人主观因素,这会打破对要记录事件的平衡。本文认为,作为导演要有建立“平衡感”的意识,把握大局,展现一种人文关怀。弗拉哈迪在他很多部作品中所展现的拍摄手法值得我们借鉴。第一,将参与观察作为拍摄的基础,了解被拍摄者的生活规律与文化特征,只有了解才有说话的权利,作品才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第二,通过建立与拍摄对象的平等关系,在主位与客位之间建立平衡关系,为拍摄对象赋予自主表达的权力,记录者和被摄者之间是唇齿相依的,都是为影片服务,两者必须相互尊重,营造一种和谐融洽的拍摄环境。第三,鼓励拍摄对象进行拍摄尝试,可以尝试与拍摄对象分享影像经验,观看素材或者唱片,获得进一步的反馈,将创作成果交给当地人评判。第四,事件定位跟踪拍摄方式,这是以一个较有典型意义的事件作为纪录对象的拍摄方式,如《北方的纳努克》中出现了爱斯基摩人一起捕猎海象的场景,这类事件性活动往往信息承载量大,是一种文化形态的集中展示。
五、对待不同族群文化的态度
通过观看《北方的纳努克》,笔者感受到弗拉哈迪已经很客观的展现了异族文化。无论是记录者还是观看者都应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评价,不能保留“刻板印象”。在现实生活中就有给异族“贴标签”的现象,由于这种标签的因素形成了人们的排斥心理,造成了一些心理上的隔阂和族群冲突。本文认为在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族群一直都存在对其他相邻群体的猜忌与恐惧,关注对方是否强大起来或者是被削弱下去,防止其他族群比自己拥有更多的东西,从而会威胁自己。族群之间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只有文化上的认同,才会有情感上的认同,我们要尊重差异,关心他人,各种人文类型的文化都有其优势和独到的价值,都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承认在不同思想文化传统中都能找到大家可以接受的东西,都有对人类社会积极贡献的部分,都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因素,才可以求同存异、美人之美,互相吸收和消化不同文化传统的优长,逐步通过沟通、宽容、互补,获得更多对利益和价值的共识。而这种共同思想、共同价值越多,对人类社会越好,人类社会才能拥有一个理智的情怀,形成广泛的共识,才能促使不同人文类型的人群和平共处,实现“天下大同”。拍摄纪录片就要以诚恳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展现某一事件或情况。
六、纪录片的当代意义
当代数字影像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纪录片提供了完备的创作手段,我们今天越来越多地受到视觉媒介的支配,我们的世界观、见解和信仰,越来越明显地受到视觉文化强有力的影响。学者米尔佐夫在其《什么是视觉文化》中谈到视觉文化研究的是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如何强调视觉表现经验,而非短视地强调视觉而排除其他一切感觉。视觉文化不仅意味着人们体验文化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会改变。影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重要角色,文化又以影像为载体成为了商品,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在大众传媒时代,受众的注意力有限,现在的消费者注重一种文化体验,图像的转瞬即逝,培养了大众对于视觉的直观化,更加追求感官效果,使得人们解决问题更依靠从影像中寻找依据。在这种景观的图像世界中,它注重追求平等、自由、时尚,不在乎传统的道德价值标准。由此追求快乐、消遣成为了人们新的价值观和追求的生活目标。
纪录片不光是担负着记录的职能,纪录片还担负着批评、教育、传播和审美功能。有些纪录片相对来说,内容比较枯燥、难以理解。而现在身处读图时代的文化产品通过“议程设置”控制了人们的文化消费,使人们的文化消费呈现娱乐化、平面化的现状,给人们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国度,犹如“温水煮青蛙”一般,慢慢地剥夺了人的主体性与自主意识,逐渐失去批评意识,步入“娱乐至死”的境地。这种消费氛围给纪录片的展现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特别是人类学纪录片传递着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它提供了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也可以说它代表着某个时期的文化。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停下脚步去看看,从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当然,作为记录者也不能为了迎合部分受众的需求、使利益最大化,制作出媚俗化、娱乐化产品,应用一种全景式的视角,要以促进社会进步,净化文化环境,提升受众的审美情绪为创作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