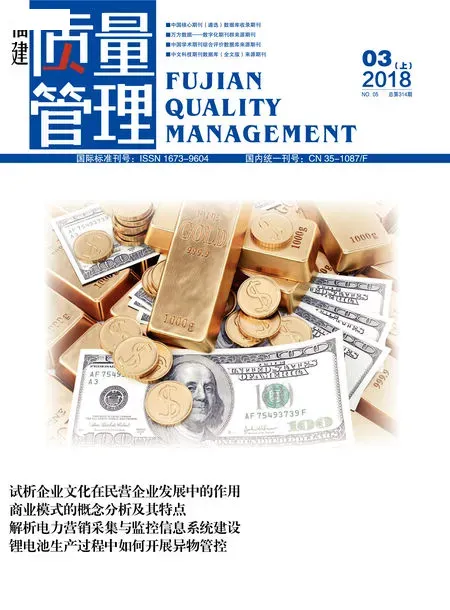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2018-04-02
(上海大学 上海 200444)
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先确立,其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标准。这个解释使得精神损害赔偿正式的出现在了我国的法律文书之中,开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先河。
但是真正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是在2010年7月1日起生效的《侵权责任法》。我国的精神损害权益保护起步晚,发展迅速,但是也仅仅是在侵权责任方面取得快速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对于在合同法领域的由于违约而造成的精神损害却没有进展,如何解决由于违约而产生的精神损害是我国民法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顾虑
(一)合同确定性、可预见性的突破,有可能会导致合同订立的一方承担超越其应承担的义务,使得另一方获得超越其应得的收益。精神损害是指当事人的非财产性损失,由于是精神性的不具有物质表现性,往往很难评估,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对于精神损害的评估和赔偿有可能导致其中一方因此而多重获益,违反民法的精神。多数的反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学者都持这样的观点,但是对于一些合同所言,精神损害是可以成为确定的可见的义务和损害的,比如丧葬合约,结婚事务的合约,以及特定物保管合同等。对于此种顾虑,可能要在合同的种类上作出一定的筛选和规定就可以避免。
(二)实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会给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法官权力的滥用,形成腐败。自由裁量权与腐败之间并没有一个必然的桥梁,没有自由裁量权的法官也可能腐败,有自由裁量权的法官也不是人人都贪腐,这其中没有必然的联系。实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是有先例可循的,在侵权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就是需要法官自由裁量的,为何当初可以这样设计,现在又要微词。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是对当事人精神权益的一种保护,是未来法益的发展的一个方向,而贪污腐败是一个一直存在的弊病,并不能以此作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弊端。
二、比较法方面的研究
(一)英国
在英国,法律最初对合同中涉及的精神损害赔偿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由于违约而导致损害的合同标的物的情感精神价值不加考虑,即便它们能够符合合同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要求。依据英国贵族院在1909年对Addis v.Gramophone Co.Ltd.—案判决时确立的判例法,英国法院对于感情的伤害这类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合同标的物的合同法上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①但是,之后英国法官还是在实践中对于一些精神损害打开大门,对于违反婚约的诉中的感情损害、身体伤害的感情损害、违反合同导致的不便或者当精神损害的发生根据合同的性质是违约的可料想的结果时,或精神损害是鲁莽违约所致时,判予物质赔偿。②而打破Addis案的以来的对于精神损害不赔偿规则,并进而开创了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先河的案件是著名的Jarvisv.Swan Tours Ltd.案件。此案件在英国确立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二)德国
《德国民法典》第253条规定:“非财产损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始得请求以金钱赔偿之。”据此因违约发生的精神伤害(即心力交瘁、压力大、抑郁症等),都属于非财产损害,不能依契约法的规定请求获得赔偿。③在实践中为突破253条,联邦法院做了重大的调整,其一是创设一般人格权,另一项是非财产性损害的商业化操作。法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通过将假期商业化,使假期利益具有财产性质,以便对损害进行赔偿。
在2002年4月18日德国议会颁布《关于修改损害赔偿法规定的第二法案》,该法案第确立非财产权益的保护不再以侵权责任为唯一基础,包括合同责任在内的其他责任同样可以为非财产权益的保护提供依据,被称为《德国民法典》上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的一次“划时代变革”。④
三、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司法的适用
(一)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性规则
第一,坚持对于违约精神损害必须是可预测性的。不能对所有的精神损害请求都予以支持,而必须坚持合同的可预测性的原则,保证合同的稳定性。对于在合同订立时社会的一般人都无法预料到的精神损害,法律不应该予以支持。这样有可能造成另一方承受不应该的损失,导致不公平现象,也不利于维护合同的效力,容易造成滥诉。
第二,坚持精神损害的标准是最低限度标准。最低限度标准是指以社会一般大众的精神感受为基准,不以个体的精神感受为标准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精神损害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也可以防止基于个人感受出现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滥诉。
第三,坚持过失相抵规则。我国《合同法》第120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害人对于违约精神损害存在过失,其过失部分成为对方减少赔偿的依据,法官可依自由裁量权减轻或免除违约方的赔偿责任。
(二)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构建思考
第一,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不应该全面覆盖,而应该向德国等国那样选择一些特定的合同类型,比如消费合同、服务合同等这些违约会导致相对人身、财产重大损失的合同。全面的覆盖所有种类的合同会导致社会对合同的不利反映,也会造成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滥诉。
第二,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由于精神损害本身的确定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而对于其损害的程度也是难以把握的,所以如果把确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力全部赋予法官,必然会导致法官的自由裁判权过大,容易滋生腐败问题。因此作者认为应该在合同法中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额度范围,将法官的自由裁判权控制在一定的限度范围内,这样既可以保证精神损害赔偿的实施,也可以确保司法的公正。
四、结论
综上所述,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的发展是一定的基础和可能性,通过对于国外经验的借鉴,我国对于违约精神权益的保护是可以达到世界发展的水平的。但是,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发展也会面对不少的问题,比如适用的范围,金额的确定,裁量权的使用等是不可忽视的。今后,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是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所必须的,也是中国立法司法应对精神权益保护的必经之路。
【注释】
①Addis v.Gramophone Co.Ltd,1909A.C.488(H.L.)
②G.H.Treitel.bid.195-196
③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④倪同木,夏万宏:《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问题研究—以<德国民法典>第253条之修改为中心》,法学评论,2010 年第2期
[1]王利明.合同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0-673页.
[2]陆青.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J].清华法学,2011年.
[3]崔建远.论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J].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8,(1).
[4]叶金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解释论框架[J].法学家,2011.(5)
[5]倪同木,夏万宏.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问题研究—以<德国民法典>第253条之修改为中心[J].法学评论,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