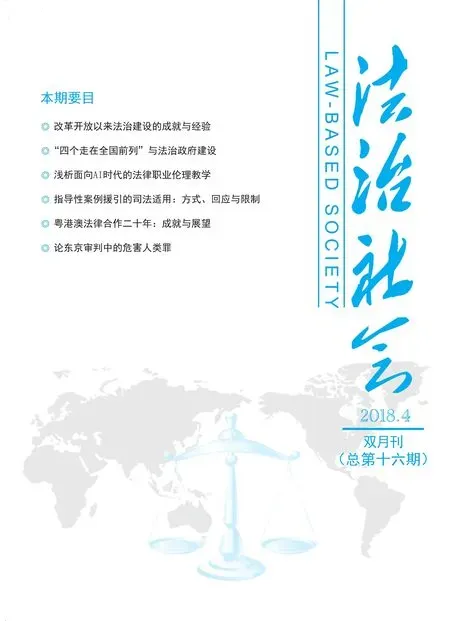论东京审判中的危害人类罪
——与纽伦堡审判对比的视角
2018-04-02张楠
张 楠
内容提要:危害人类罪是国际刑法中极为严重的罪行,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出现在 《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之后被运用到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危害人类罪引发了有关事后法、与战争罪相关联、以及未将部分罪行纳入追溯等问题。就危害人类罪相关的东京审判法庭宪章规定、起诉书中的指控、辩护人的辩护词、以及判决结果和公开的法官意见书等材料与纽伦堡审判中料做比较研究得出以上三个问题的答案:东京审判的起诉方希望将所有被告人的全部罪行被追溯,修改了法庭宪章致使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产生了难以区分的竟合,从而引发了追溯不完整且影响至今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两次世纪大审判,分别是审判德国法西斯的纽伦堡审判和审判日本法西斯的东京审判。两大国际审判都体现了人类正义和国际法的尊严。东京审判出现不仅仅是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乃至亚洲各个国家犯下的罪行的控诉和判决,也是国际刑事法庭的发展迈出的崭新一步。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中出现两项新的国际罪名——破坏和平罪和危害人类罪,“破坏和平罪”将发动 “侵略战争”视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而危害人类罪则是将对全人类共同危害的非人道主义行为正式纳入国际刑法的罪名中。本文就东京审判中危害人类罪引起的争议,结合国际法规定、法庭控诉及判决结果,对比纽伦堡审判危害人类罪的相关情况加以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
一、东京审判中危害人类罪引发的相关争议
危害人类罪,即反人道罪 (crimes against humanity),最初由纽伦堡审判法庭确立,危害人类罪是国际刑法用来控诉和惩罚与战争相关的反人道行为,如残酷的屠杀、非人性化的奴役、性暴力及虐待等行为。很长一段时间将其翻译为反人道罪,或违反人道罪、违背人道罪,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多数有关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的文献中,不少学者依旧将危害人类罪翻译为反人道罪。直到东京审判结束约半个世纪后,联合国安理会起草的 《前南国际法庭规则》将其正式确立为危害人类罪,在之后有关文献全部翻译为危害人类罪。
从两次军事法庭审判过后,德国和日本两个战败国在对待两次审判及战争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德国从政府到人民深刻反思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人民和犹太民族带来的种种苦难,而日本政府从未对 “南京大屠杀”及 “慰安妇”问题正式道过歉,甚至还有学者极力否认 “南京大屠杀”存在,①程兆奇:《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编造么?》,载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并且说东京审判是 “不公正审判”。可见,这些问题根源都在东京审判中有关危害人类罪的国际法规定、法庭审理以及判决结果。
(一)有关是否符合罪行法定原则的争议
由于纽伦堡审判之前并没有危害人类罪在国际法中明文规定,这与世界公认的刑法理论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因此检方不得不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证明危害人类罪的认定是合法的。东京审判事后有关危害人类罪是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讨论也在继续,其中大多数学者呈现两个观点:一是危害人类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原因是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检方都将其和战争罪关联,有关战争罪的大部分国际法渊源都是法定条文。②杜启新:《国际刑法中的危害人类罪》,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超出战争法相关的部分行为且符合危害人类罪特点的行为是已经多国实践并认可的国际习惯,国际习惯和国际公约法定条文都属于国际法渊源,由此认为危害人类罪的认定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二是认为危害人类罪某些方面确实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但站在国际法原则的角度,正义原则必须大于法定原则,由此认为危害人类罪是合法的。③参见前引②,杜启新书,第49页。笔者认为,罪行法定原则背后是国家权力法定、民主思想为其渊源,那么放在 “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的宏观层面,是否符合罪行法定原则要证明当时的国际社会,即世界各国是否将危害人类罪的行为纳入国际刑法控诉的范围,其中也包括是否有先前类似的国际法依据。由此可见,论证东京审判危害人类罪是否符合罪行法定原则,要从东京审判的国际法章程规定以及控辩双方主张意见来评估。
(二)与战争罪行为牵连的争议
因为危害人类罪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都不得不将其与战争罪牵连。但因此也带来了很多麻烦,比如检方确定被告人罪行和取证的困难,法庭质证和认定方面也出现了不少的障碍。从刑法学的角度看来,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牵连关系不可忽视,在国际法条文描述中颇有相似之处,由此引发了两个相关问题:
首先,犯罪认定的问题。国际刑法对两种罪行的认定标准是什么,以及如何规定这两类犯罪行为的牵连关系呢?两种犯罪行为的主体都属于国家元首级别或相关掌握国家权力的人物;犯罪行为方面都表现出对种族和地域人民虐待、残杀等非人道主义的对待行为。由此,东京审判中有关危害人类罪的指控是否能达到独立成立的标准,这样的认定标准给事后国际法庭危害人类罪的审判带来了何种影响?
其次,两种行为牵连影响了对被告人的量刑。总体看来,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之间存在较多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显而易见的不同之处。东京审判在围绕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的区别时的量刑是如何认定的?同时,东京审判通过庭审最终判决被告人危害人类罪的量刑方面对比纽伦堡审判相关量刑是否足够公正呢?
总结以上两个问题,要从东京审判危害人类罪国际法章程的规定解释、庭审判决结果来分析以上存在的争议。此外因为国际法相较于国内法的特殊性,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从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的国际法条文及庭审判决书中的认定内容来分析。
(三)部分危害人类罪行为未得到追溯的争议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一直是站在维护正义和和平的角度,为全人类的文明、自由而惩罚法西斯的行为,大大的推动了国际刑法的发展。但不得忽视两次审判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迄今对两次审判的批评之声也是接连不断。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揭秘和发现,日本不断出现为其翻案的声音,④程兆奇:《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页。我们发现有关东京审判对被告人的追溯和指控并不完满。有部分国外社会学家对东京审判的最终实质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比如东京审判有关性暴力问题——“慰安妇问题”。提出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日军当年对 “慰安妇”受害者的暴行至今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惩罚,是因为东京审判没有把此类行为作为国际罪行追溯造成的。⑤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中信集团出版社2017年版,第185页。再比如,对于安倍政府上台后右翼学者大肆否定 “南京大屠杀”的情况,有学者评论 “南京大屠杀”不断被日本学者质疑是因为东京审判对 “南京大屠杀”定性出现了问题,⑥李昕:《创伤记忆与社会认同: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公共建构》,载 《江海学刊》2017年第5期。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无疑不能与危害人类罪脱离关系,相比之下德国战后却很少出现对屠杀六百万犹太人事实和性质否定的声音。可见,对部分危害人类罪行为未被追溯引发的争议,需要通过对比纽伦堡审判相关的国际法规定、庭审记录和判决结果分析。
二、东京审判中危害人类罪的构成要件
东京审判中有关危害人类罪的国际法依据主要是来源于1946年4月26日修订完成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主要是依据1946年1月19日由盟军最高统帅宣布设立远东军事法庭的特别公告来完成的,由美国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签署。⑦姚丽:《二战全史》,汕头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页。下文将通过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来分析危害人类罪的构成要件。
(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的构成要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二章:“管辖与通则中的第五条,被告犯罪行为之管辖,本庭有关审理及处罚被检举有犯罪行为 (包括危害和平之罪行)之个人的或为某一团体一份子的远东战争犯罪,凡有下列行为之一,及构成应由个人单独负责,并应受本法庭管辖之罪行。第一项,破坏和平罪。第二项,战争罪。第三项,反人道罪 (即危害人类罪)。”⑧余先予、何勤华、蔡东丽:《东京审判——正义与邪恶之法律较量》,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01页。此条款是确立危害人类罪的规定。接着下文规定:“反人道罪,指在本法庭管辖区内,与战争发生前或在战争进行中,实行屠杀、灭绝、奴化、强迫迁徙,以及其他不人道之行为,或基于政治上或种族上之立场,强迫迁徙人口构成犯罪行为,不问此等行为是否违反犯罪地之本国法律。”⑨参见前引⑧,余先予等书,第302页。此外还规定了共谋行为:“凡参与计划预谋,或实施上述犯罪行为之首领、教唆犯或共犯对于执行该计划之一所为之一行为应负全部责任。”⑩参见前引⑧,余先予等书,第303页。第六条还规定了个人责任模式,“被告不得以其所居之官职地位或系主张执行政府或上司命令之事实,作为理由请求免除刑责。”①参见前引⑧,余先予等书,第302页。这是对危害人类罪具体要件的说明,以下将用传统刑法学对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即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来分析危害人类罪。
1.危害人类罪的客观要件方面
上文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对危害人类罪的客观要件可以分为这几个要素:犯罪客体、犯罪对象、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对象是犯罪主体——一般来说是被追责自然人或组织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个人自然人或者具体财物。从法条宪章的规定来看,危害人类罪的犯罪对象是 “战争前或进行中”的任何公民,这里的公民不需要考虑是否是在战争前后发生的所属地国籍和种族的非军人。除此之外,通过法条中出现的字眼 “杀害、灭绝、奴役、强迫迁徙人口,以及其他不人道行为”等可以推断出,危害人类罪的犯罪对象还包括了被侵害人的人格尊严,土地、财产、文化等。
犯罪客体是刑法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这些各种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被犯罪行为所侵害,这些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主要变现为各种权利和公共秩序。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都属于犯罪客观要件,但有所区分,犯罪行为侵犯了犯罪客体,不一定侵犯了犯罪对象。从法律的条文中可以看出,危害人类罪的犯罪客体并非是与传统刑法所保护的犯罪客体那样容易区分。单一看来,危害人类罪侵犯了受害人个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注意到法条使用了 “人口”这一词,说明了危害人类罪不单将侵害对象当作个体来看待,②参见前引②,杜启新书,第78页。更加强调了被害人口集体的权利和由此集体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因为在危害人类罪的规定语义上区分了个体和集体,这也使得危害人类罪与大部分国家传统刑法里所保护的犯罪客体不尽相同。综上,危害人类罪相比传统刑法中保护的个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及确定的法人组织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外,还多出一项针对不特定集体的人身财产权,以及这些集体所形成的良好社会秩序所组建的综合性质的社会关系。可见,危害人类罪的犯罪客体可以是个人、组织、集体权利与秩序交叉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
犯罪具体行为是犯罪主体实施犯罪实行的行为,是刑法学分析每一项犯罪的核心,犯罪行为也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标准。宪章中规定的危害人类罪的具体行为包括了 “屠杀”“灭绝种族”“奴役”“强迫迁徙”等要件,③[德]P·A·施泰尼格尔:《纽伦堡审判》,王昭仁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98页。即危害人类罪的主体只要实施了剥夺人民自由、类似于种族灭绝的大规模屠杀、使被害人丧失人格尊严以此虐待、强迫众多被害人离开原本的正常居住地等行为,就构成此项罪行。因为害怕疏漏部分犯罪行为,法条的制定者还规定了 “以及其他不人道行为”这样的兜底条款。
除了上述规定的具体行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限定了危害人类罪实施的时间为战争发生前和战争进行中,这一点是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的区分标准。此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第3款还规定了 “凡是参与规划或者实行旨在完成上述罪行之共同计划或者阴谋之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与共谋者,对于任何人为实现此种计划而做出之一切行为均应负责。”④参见前引④,程兆奇书,第91页。这样看来,危害人类罪不但惩处单个人实施此类犯罪,还规定了共谋行为也构成犯罪,且要负刑事责任。
2.危害人类罪的主观要件
主观要件将从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来分析。犯罪主体,就是所实施犯罪行为的自然人、法人等。对犯罪主体的分析和确立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刑事责任能力、身份问题、责任模式及法人是否能构成此罪。有关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没有规定有关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一般来说刑事责任能力需要考虑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和精神智力状态两个方面,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需要达到一定年龄和能够辩证自己行为两个条件。其次是有关被告人身份,官员等级、所属职务等。由于危害人类罪非比寻常的犯罪,能实施这样犯罪的被告人基本属于手中握有实权的政府官员和军人,确认被告人身份是法庭认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另外,精神智力正常也是一个重要标准。在东京审判中出现了一段插曲,由于被告人大川周明突然在法庭上精神失常,因此逃脱了审判的追诉。可见,精神智力问题确为是危害人类罪刑事责任能力的构成因素。
除了上述之外,法人是否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五条明确规定“本庭有关审理及处罚被检举有犯罪行为 (包括破坏和平之罪行)之个人的或为某一团体一份子的远东战争犯罪”,这里指出的 “某一团体”可见是指法人或类似于法人的组织。
犯罪主观方面指的是犯罪主体实施行为的心理状态、目的和动机等。传统刑法将犯罪主观方面分为故意和过失,主观故意又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规定了 “任何罪行之迫害行为”,这里既包括了故意违反战争法规,以及怠于阻止危害人类行为扩大等心理状态。此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规定 “基于政治上或者种族上的理由而进行”就是有关犯罪目的和动机的规定。危害人类罪大概涉及了两种犯罪主观方面,一种是基于政治上的理由,一种是种族上的理由,由这两种目的和动机而实施的危害人类罪。
有关责任模式,东京审判采用了个人刑事责任模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被告不得以其所居之官职地位或系主张执行政府或上司命令之事实,作为理由请求免除刑责。”⑤参见前引⑧,余先予等书,第301页。这项个人刑事责任模式是继承纽伦堡审判 《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确了手握国家权力的人,必将引导国家行使国际法承认的国家行为,个人的意识影响了国家意识是需要承担责任的。
(二)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的区别
危害人类罪脱胎于战争罪,与战争罪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⑥李明奇、廖恋:《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灭种罪的区别》,载 《理论界》2011年第7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有关战争罪的规定原文是:“所谓战争罪,是指违反战争法规或习惯之犯罪行为。”这里的战争法规或习惯,一般是指1907年的 《海牙第四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这部有关战争的国际法规定了有关交战团体资格,以及如何对待战俘和战争中占领区的一般规则,日本是这项国际法规的缔约国,所以违反上述国际法规应当被认为构成国际罪行。而危害人类罪作为一种新的罪行在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被庭审时,为反驳被告人的主张,检方有意识地让危害人类罪和战争产生关联,而战争罪是当时国际社会无可争议的罪行,这样被告人就难以对危害人类罪中审判合法性提出质疑了,⑦何勤华、朱淑丽、马贺:《纽伦堡审判——对德国法西斯的法律清算》,商务印刷馆2015年版,第90页。但这样却使得两种罪名产生了难以区分的竞合点。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的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有以下区别:第一,发生时间不同。战争罪必须发生在战争过程,而危害人类罪既可以发生在战争过程中,也可以发生在战争之前。第二,犯罪对象不同。战争罪的犯罪对象是非本国国民,包括军人、民兵、武装团体,以及放下武器的军人。而危害人类罪则不同,它的犯罪对象可以是任何国家的国民,包括行为人本国的国民,这是为了惩治一国政府虐待本国民众的行为。⑧参见前引⑥,李明奇等文。第三,犯罪客体不同。危害人类罪的犯罪客体是良好和平的国家及社会关系;战争罪的犯罪客体是国际法已规定的战争法规。第四,危害程度不同。危害人类罪的侵害对象 (包括已经真实攻击的和试图攻击的)必须达到一定数量才可以成立,而战争罪并没有此类要求。第五,保护的目的不同,危害人类罪保护的是公民,有关人道主义方面的基本权利,而战争罪是以违反战争法规为基准,并非单纯的对人道主义加以保护。
(三)比较纽伦堡审判章程的规定
根据纽伦堡审判制定是 《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第二章第6条第3项:“危害人类罪:系指在战争期间对平民人口进行的屠杀、灭绝、奴役、放逐或者其他非人道行为,或借口政治、种族或宗教的理由而犯的术语法庭有权受理的以构成犯罪或与犯罪有关的迫害行为,不管该行为是否触犯进行此类活动的所在国的法律”。⑨参见前引⑦,何勤华等书,第90页。接下来又规定:“凡参与拟定或执行旨在犯有上述罪行之一的共同计划或者共谋的领导者、组织者、发起者和同谋者。”⑩参见前引⑦,何勤华等书,第91页。由此对比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的规定,有关危害人类罪的犯罪行为、时间和目的、犯罪主观方面,有两点不相同:第一,删除了危害人类罪规定中的 “平民人口”一词;第二,删除了基于宗教目的而实施危害人类的 “宗教的理由”。
笔者认为删除这两点有三个理由。首先,军事法庭的设立者并非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东京审判主要针对的是日本法西斯对亚洲各国犯下的战争罪行,而日本虽然在亚洲各国发动侵略战争和大量残杀平民及战俘,却没有因为宗教原因而做出反人道的行为。这一点与纽伦堡审判要面对的事实并不一样,德国法西斯在残害犹太人的时候,利用了宗教问题发表有关歧视犹太人的言论,由此成为迫害犹太人的理由。其次,不增加这个理由的原因也是为了对法条本身不产生歧义。危害人类罪自从被规定在 《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后,引来了大量批评的声音,不少专业人士质疑危害人类罪的合法性,因此法的溯及力问题产生了很大的质疑。正因为纽伦堡审判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东京审判相关刑法的制定者不得不慎重考虑。最后,考虑到东京法庭待审理事实与纽伦堡法庭审理事实的不同,删除 “平民人口”使得法条本身与战争罪构成要件近似,也避免了危害人类罪合法性问题。
有关危害人类罪法条规定在两次审判宪章中的共同点是,都以破坏和平罪和战争罪为前提。在制定危害人类罪的时候,《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制定者就考虑到德国不是因为战争目的而大量残害六百万名犹太人,迫害犹太人有时出现在战争发生之中,或者发生在战争之前,也并非发起战争的理由,但与战争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由此可见,危害人类罪在两次二战大审判的立法和制定中虽然脱颖而出,但并非完全独立,其原因三点:一是担心危害人类罪的合法性受到强烈质疑,而由此关联到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有很多犯罪构成要素与战争罪极其相似,两者之间不太容易区分,尤其以犯罪行为和对象这两点相似为典型。二是担心战争罪不能将法西斯所犯的罪行全部受到控诉,所以将两者有所关联。因为危害人类罪造成了犯罪对象无法估量的伤害,使得检察官集团认为不能放过一个有关的个人和组织,将两项罪名关联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得危害人类罪的合法性问题有了解决的方法;缺点是法条竞合,使得起诉、取证和法庭审理增加了难度。三是尽管危害人类罪有关的问题诸多、争议较大,但依然被检察官团体起诉,原因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两次发生大量对平民血流成河的屠杀、抢劫及财产破坏已经超越普通战争罪惩罚的范围。可见,危害人类罪强调了反人道主义实施的行为。
三、东京审判中有关危害人类罪的法庭审理及判决结果
上述文字分析了有关危害人类罪两次审判的法律规范,我们看出了两者在立法之间的不同和相同点。要分析法庭认定的问题,就要先分析起诉书中有关指控的被告和事实,以及辩护人对这些事实的看法,即辩护人的观点。最后,将比较法庭的判决书有关危害人类罪的认定。
(一)东京审判有关危害人类罪的指控、辩护和判决结果
东京审判的原起诉书中一共指控了55项罪名,有大部分的罪名被破坏和平罪占据,只有3项是普通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危害人类罪没有被单独提出作为一项指控。其中法庭指控第一部分为破坏和平罪,第二部分为杀人罪,第三部分为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值得注意的是起诉书中第37项和第52项是有关杀人罪的指控是日军在亚洲、美国,荷兰等地犯下的惨无人道的屠杀和滔天罪行,比如第45项:“1937年12月12日已后在攻击南京时对目前姓名不明、人数不详的数万中国平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的杀害,这一项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①参见前引⑧,余先予等书,第80页。但是由于起诉项目众多,多数有重复和累赘,法庭最终是确定了十项,将第二部分有关杀人罪的全部删除,留下了有关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第54项和第55项。第54项和第55项分别是这样描述:“诉因五十四: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命令、授权及许可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诉因五十五: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无视遵守对俘虏平民的条约的行为。”②参见前引⑧,余先予等书,第82页。由此可见,前面日军的种种暴行在起诉书中被简化,但并非删去了确认的事实。③梅小璈、梅小侃:《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页。
在指控的被告人数中,原定的二十八名被告,只有二十五人最终接受完了审判。大川周明因为审判开始突然精神失常而被迫退出,另外两位在审判前自杀身亡。这最终接受审判的二十五名被告中,只有白鸟敏夫没有被指控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在检方举证方面,检方拿出大量的证据单独说明了日军危害人类罪的暴行,比如 “南京大屠杀”“菲律宾大屠杀”和 “修筑泰缅铁路虐待战俘”事件,这些证据大多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类是亲眼目睹者的口供,如审理 “南京大屠杀”是出庭作证的伍长德,审理 “菲律宾大屠杀”中在帕尼奥斯收容所关押过的年轻姑娘旺达格芙,④参见前引⑧,余先予等书,第185页。这类的证明证言主要是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检方由此来证明日军残暴的行为是确实存在的。第二类是检方出具的有关日本军人和官员的文件和日记之类的书证,证明这些例如马尼拉岸防长官颁发的日期为1944年12月以及1945年1月和2月的有关大规模屠杀菲律宾人的命令,文件这样写到 “在处决菲律宾人时,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尽量集中到一处,这样可以节省弹药和体力,尸体处理很麻烦,应把尸体塞进预定烧掉或炸毁的房屋里,或扔进河里”,⑤参见前引⑧,余先予等书,第186页。此类的证据,检方用来证明这种危害人类罪的行为是哪一类型,以及来证明这些行为是由于政府和军队的命令来下达的,并非某一军人或者单一部队的各人行为。第三类证据是证明日军的此类行为造成的危害程度,比如检方出示的一副菲律宾被虐待致死的统计表。
同时,辩护方也提出了不少反证,大概分为二点:一是总体否定日本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比如在审理菲律宾阶段辩护律师柯宁汉提出了1941年菲律宾不是主权国家,更不是 《日内瓦公约》的签署国。⑥参见前引⑧,余先予等书,第184页。二是证明日本实施杀害和虐待战俘平民是 “迫不得已”,因为当地人民的抵抗和军队机制的原因而推卸责任,这一点上东条英机的证言最为典型,例如当检察官问他巴丹死亡行军中为何会出现两万多名美国和菲律宾战俘的死亡,他的解释是:“按照日本的习惯,执行特定任务的司令官,不受东京具体命令的约束,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权。”再如检察官季南交叉询问东条英机:
“问:杀戮二百万以上中国人,曾考虑将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答:我对此深感不幸。
问:但所杀戮者不少是无辜民众。为什么要以此种残酷行为加诸此等与战争毫无关系之人民?
答:所谓,民众与战争无关系一节,中国与我们日本均属同样。但以一国指导者的政治家之地位而指导民众排日侮日,以致虐杀等,实属错误。”⑦参见前引⑧,余先予等书,第210页。
可以看出,东条英机对杀害了多少名中国人表示不知情,但不敢否定日军确实在中国土地上有暴行,他不认为杀戮太多中国人是犯罪,反而认为日军的上述残暴行为都是中国人排日造成的。
上述来看,有关危害人类罪的举证,检方举证的核心主要集中在危害人类罪的事实是否存在,这些行为确实是经过日本高级军队官员和政府官员认可的,以及这些行为给他国人民造成了怎样的伤害。而辩方的反证主要集中在,利用当时的国际法理论和对方国人格主体和主权的缺失,主张日本的行为是无罪的,而被告人自行辩护则主要集中在自己对所发生的严重事实没有过错,但辩方对于危害人类行为所造成的事实并没有举出它不存在的证据。
正因如此,大部分法官都肯定这些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就连主张日本侵略行为无罪的印度法官帕尔,⑧[日]中里成章:《帕尔法官——印度民族主义与东京审判》,陈卫平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页。也不得不承认日军在 “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浩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法庭认定方面,东京审判最终认定了指控的二十四名被告中的五名被告第54项指控成立,分别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和东条英机,七名被告的第55项指控成立,分别是畑俊六、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武藤章和重光葵,其中木村兵太郎和武藤章两项指控都成立。如对土肥原贤二有关虐待东南亚俘虏的判决,法庭最终没有采纳土肥原贤二对于不给俘虏食物和药物使其饿死和病死的辩词,土肥原贤二辩解称,“日本战局恶化,不能给俘虏良好的补给。”⑨参见前引⑧,余先予等书,第235页。但检方出具的证据证明食物和医药物都是能够提供的,法庭最终在判决书里写到:“土肥原贤二应采取阻止这类供给政策的责任。根据这类事实的认定,土肥原贤二的犯罪,与其说是适合罪状第55条,不如说是适合第54条。”⑩参见前引⑧,余先予等书,第236页。与土肥原贤二相同观点做出判决的还有板垣征四郎,法庭也认定其行为构成第54条而非第55条。而对于 “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判决书这样写到:“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的疾病既没有阻止他智慧在他知道下的作战行为,又没有阻碍他在发生这类暴行时访问该市达数日之久。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利统制他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本法庭根据罪状第五十五条判决被告松井石根有罪。”①参见前引⑧,余先予等书,第333页。可见,松井石根并没有因为第五十四项违反战争法规而屠杀南京市民而被判有罪,是因为虐待战俘而被认定有罪。然而,被判处死刑的七位被告人,都被法庭认定犯有第54项和第55项罪行,由此可以确定,东京审判对危害人类罪的量刑很重。
综上所述,东京审判在有关危害人类罪的指控、辩护和判决都集中在这些所指控的有关危害人类罪的事实是否成立,而不是有关合法性问题。在东京审判中较为突出的是确定了被告人怠于行使权力而放任危害人类罪的行为后果扩大或者不作为也将其归纳为危害人类罪。
(二)比较纽伦堡审判中的指控、辩护和判决结果
在纽伦堡审判中,赫尔曼·威廉·戈林等二十二名纳粹高级官员被指控不同程度的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其中被控危害人类罪的人有二十人,起诉书也将几个组织作为被告指控其犯有危害人类罪,比如党卫军组织和盖世太保。起诉书称被告人完全漠视并违反了人道主义法,以非常野蛮的方式实施了上述共同计划或密谋。这些方式和罪行构成了对国际条约、国内刑法、源自所有文明国家刑法的一般原则的侵犯,涉及并构成系统的行为过程的一部分。
起诉书的第2项、第3项指控分别指称被告人犯有 《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6条第1款规定的破坏和平罪的具体内容,该项指控与第3项指控所指的战争罪合并在一起,并参照第3项指控。与东京审判不同的是,起诉书列举了两项没有合并战争罪指控的危害人类罪。其一,被认为反对德国纳粹政府的德国平民,被未经审判而关押、谋杀和施以酷刑,即以违反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的方式镇压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其二,纳粹独裁政权还区分出不同的群体,基于政治、种族和宗教的理由加以迫害。此外,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虽然都确定了法庭有管辖法人组织犯罪的权利,纽伦堡审判起诉了党卫军、德国内阁、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等部门,因为这些组织正式秘密策划和迫害犹太人的具体实施组织。
在辩护方的工作方面,由于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和屠杀等具体的战争犯罪事实明白无误,辩论的中心自始至终都围绕国际法理论问题展开,②宋志勇:《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之比较》,载 《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2期。认为危害人类罪不具有合法性。尽管如此,辩方这方面的发言,以及和控方的激烈争论,都成为了事后有关危害人类罪溯及力问题的重要依据和理论观点。对此辩方强烈的质疑,控方提出了国际法并不是国际的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是逐渐存在于各国的风俗和习惯中的,条约实际上只不过是现存的法律原则加以表述,和对这些原则进行更加确切的解释而已。③朱淑丽:《纽伦堡审判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载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针对于此控方举出了 《凡尔赛公约》草案、《海牙第四公约》等成文国际法来说明反人道行为早已是各国否认的国际行为。④参见前引②,杜启新书,第24页。此外,对于个人承担战争责任问题,辩护方也认为战争是国家行为,个人不应承担责任。⑤参见前引②,宋志勇文。然而,对于被告人为自己辩护的方面,大部分被告人都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对于组织、法人所犯的罪行都不愿承认有责任。⑥张颖军:《从纽伦堡审判到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司法的法人责任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11期。对比东京审判,控辩双方将大部分言词都放在破坏和平罪,对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争议并不多。
在法庭宣判方面,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了长达二百多页的判决书,判决书详细列举了纳粹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共同密谋策划并准备侵略战争、对欧洲各国的侵略战争、迫害犹太人、屠杀平民、虐待俘虏、强制劳动、掠夺公私财产等累累罪行,同时对其违反的国际条约以及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解释。⑦参见前引②,宋志勇文。法庭最后判定二十二名被告有罪,其中被控危害人类罪的二十人中只有一位被告人被判无罪。并根据其罪行轻重,判处戈林、里宾特洛甫、罗森堡、凯特尔、施特莱歇尔、约德尔、绍克尔、弗兰克、弗利克、卡尔腾布龙纳、赛斯-英夸特、博尔曼12名绞刑,其他被告被判不等的有期徒刑。⑧参见前引②,宋志勇文。此外,德国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党卫队被宣判为犯罪组织。⑨黄肇炯、唐雪莲:《纽伦堡、东京审判与国际刑法》,载 《法学家》1996年第5期。可见,纽伦堡大多数被告人都被控诉犯有危害人类罪,而东京审判只有不到一半的被告人被判犯有危害人类罪。
除上述之外,还有部分情况是不相同,东京审判中的大川周明因为突然精神失常而被免去了审判,而纽伦堡法庭并没有作出此方面的决定,比如被告人沙赫特,在审判前一直患有严重的臆想症和健忘症,却依然被列入被告人名单;⑩参见前引⑦,何勤华等书,第96页。被告人马丁·博尔曼却在审判之前去向不明,法庭对他做出了缺席审判。由此可见,在纽伦堡审判中,精神失常不能成为被免去审判的理由,法庭也有作出缺席判决的权力,这是东京审判没有的,可见对法庭审理免责事由,东京审判要宽泛许多。
(三)小结
综上两部分说明,有关东京审判的危害人类罪的法庭审理和判决,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第一,两次审判存在一定的目的性指控,也就是说,检方的控诉有很强的目的性,纽伦堡审判的一位起草起诉书的检察官是犹太人,他和团队都希望审判犹太人被迫害的事件成为重点,促使了危害人类罪的出现。另外,东京审判不像纽伦堡审判那样起诉了相关组织和法人,是因为有危害人类罪相关事实的不同,在纽伦堡审判中事实残害犹太人的正好是这些组织,比如盖世太保,东京审判却多以军队去实施这类行为。可见,检方的起诉都选择性的。第二,两次审判都有是为了能最大限度的指控被告人的情况。东京审判的起诉书有相当部分的重叠性,纽伦堡审判中的缺席审判的出现,都被认为是不放过每一位被告人的表现。第三,危害人类罪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纽伦堡审判中,辩方的大量时间都围绕在这一理论方面,检方的起诉书,法官的判决书中都有相当的篇幅去说明此问题,东京审判的检方有意避开这个环节,将危害人类罪的部分情节改变为杀人罪。在庭审中有关危害人类罪方面,辩方的焦点也集中到指控事实是否存在而不是理论问题。第四,两次审判检方都为危害人类罪的合法性采取过措施,都将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相关联,造成了举证、认定以及量刑和个人责任的确定的困难。另外,还使得东京审判部分被害人的事实得不到确认和公正的判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危害人类罪的出现是为了控诉战争罪的缺点,为了控诉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大量无辜平民的屠杀和迫害,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浩劫使得检察官集团、被害国政府和人民都愤慨不已,为了最大程度的给被告人定罪,检察官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危害人类罪也因此诞生。但因为纽伦堡审判中合法性的争议问题,使得东京审判受到了影响,很多相关程度的屠杀和迫害事件没有严格的定性,部分被告人及部分人的罪行逃脱了追溯,甚至影响了现当代历史研究的走向。
四、结语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次审判,对国际法的贡献是极大的,两次审判中出现的新罪名,大大推动了国际刑法审判的模式和进程。从历史事实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给欧洲及亚洲人民带来了无法言语的痛苦和伤害,无法用违反战争国际法规这样的罪刑来描述,而且仅仅只用战争罪来惩罚被告人,对无辜牺牲的受害者是明显的不公平,危害人类罪就这样在两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诞生了。但危害人类罪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遭遇了罪刑法定原则意见持有者的反对。致使东京审判中的检察官团体不得不重新对此考虑,修改了起诉书而改变了危害人类罪原有的规定,从而使危害人类罪的特质变得不那么明显,也影响了法庭对部分日军在我国及东南亚犯下的种种暴行性质的认定。使得东京审判的检察官集团不敢轻易再将日军犯下的大屠杀等罪名单独作为危害人类罪来起诉,反而多列出了一项杀人罪,这项罪名法庭最终没有确立下来。所以,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无法以危害人类罪来定性,只能以违反战争法规而定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 “南京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被告人松井石根却没有因为违反战争罪法规屠杀平民治罪,而是因为虐待战俘而获罪,这直接改变了东京审判对 “南京大屠杀”的定性,并没有强调南京浩劫是一场非人道主义、大规模有组织的屠杀,而是认为其事件是战争主因发生的附带扩大化的事件。有关 “南京大屠杀”“菲律宾大屠杀”等事件是否应该以危害人类罪单独起诉审理,而非放在战争罪这一项中。东京审判法庭的我国法官梅汝璈先生在事后的笔记文章中,批评东京审判起诉书的特点时提到了原本起诉书存在的五十五项罪名有相互矛盾、缺乏逻辑等问题,将“南京大屠杀”等问题列为杀人罪而非危害人类罪,使得起诉书内容方面失去平衡。①参见前引③,梅小璈等书,第329页。至今为止,“南京大屠杀”不被认为是危害人类罪的行为,是局限于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这不仅成为了东京审判辩方以 “中国南京军人抵抗而实施杀人”这项理由来为屠杀抗辩的动因,也成为至今否认 “南京大屠杀”的右翼学者为其翻案的理由。②参见前引④,程兆奇书,第73页。
相比纽伦堡审判中检方控诉纳粹从1935年直到1945年十年间迫害屠杀600万名犹太人,那么“南京大屠杀”只有不到两个月仅仅在南京一个城市就有超过30万人遭到屠杀和各种迫害,甚至出现 “杀人比赛”等极其令人发指的情形,是否 “南京大屠杀”的性质更加严重呢?何况 “南京大屠杀”只是日军在亚洲各国屠杀别国人民中的一个事件而已。③参见前引③,梅小璈等书,第418页。
有关战争中慰安妇问题,近几年因为联合国人权组织的不断努力,国际法中频频出现了以女权主义和保护妇女权益的声音。位于日内瓦的国际法委员会组织的乌斯蒂尼亚·多尔格波尔等人调查了二次世界大战慰安妇问题的研究。这项调查揭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东京审判的确是没有给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性暴力问题足够重视。④参见[日]田中利幸日、[澳]蒂姆·麦科马克、[英]格里·辛普森:《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梅小侃译,上海交通大学2014版,第314页。而对女性的侵害行为,也属于危害人类罪控诉的范围中。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日本在战争中发生过数不尽的妇女被强奸,仅仅 “南京大屠杀”的那段时间每天就发生上百起,甚至有中国、朝鲜等国妇女被日军带走关在特定地方,由此来满足日军的要求。⑤参见前引④,程兆奇书,第74页。而危害人类罪的行为是多项的,包含了故意杀人、抢劫、强奸、侮辱和猥亵等,这些在东京审判里都没有被足够重视,使得日军犯下的有些罪名得不到法庭确认,导致日本右翼势力迄今为止拒不承认,没有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这样即是对受害人及受害国的不公平,也影响至今——日本政府迄今没有因为此事正式向我国受害者道过歉。不得不承认,东京审判是具有一定遗憾和缺陷的正义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