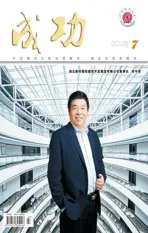刍议山崎丰子作品中的生态女性意识
2018-03-29姚琴
姚 琴
南昌大学 江西南昌 33003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处于复杂矛盾的急速成长期。期间,经济快速发展,而旧的社会恶习却仍有残留。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山崎在报社工作的同时,于1957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暖簾》出版后,几乎以一年一部的速度,一直持续到1969年写出《続白い巨塔》。在1973年完成《華麗なる一族》后,山崎作品的创作主题和视角从关西逐渐指向了全日本甚至全世界,展开了独具特色的气势恢宏的叙事创作,同年着手“战争三部曲”之一的《不毛地帯》的实地采访和创作,1983年第二部《二つの祖国》出版,1991年出版遗孤主题的长篇小说《大地の子》;1995年开始航空主题的长篇小说《沈まぬ太陽》连载,2009年涉及政坛主题的《運命の人》开始连载,可谓是硕果累累。2011年着手《約束の海》的取材,并于2013年开始期刊连载,本预期2014年1月完成共20回的连载。可惜的是,在第6回连载之后的9月29日,山崎丰子不幸辞世。山崎小说中,人性和战争是不变的两大主题,不遗余力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暴露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回顾山崎早期的几部作品,大阪商人的拼搏、努力、坚守精神贯穿其中,而且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博弈和纠缠也是重要主题。本文将分析《花のれん》《女の勲章》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重点通过《女の勲章》的文本分析,尝试性地探讨山崎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立场。
一、《花のれん》中的多加
《花のれん》创作于1958年,延续了第一部作品《暖簾》的主题,描写了一位大阪船场女性在曲艺界打拼的故事,获得了第39届直木奖。主人公——多加,由于丈夫沉迷于曲艺而不务正业,导致从父辈手上继承下来的服装店倒闭。为了挽救丈夫,于是多加把丈夫痴迷的曲艺当做生意来做,开了一家曲艺场。无奈丈夫仍旧游手好闲并沾花惹草,最终竟然死在了情妇家里。在丈夫的葬礼上,多加神差鬼使地穿上了以表“不事二夫”决心的白色丧服,从此走上了大阪女实业家的创业之路。多加性格隐忍、坚毅,即使被丈夫背叛,仍却为了经营好曲艺场,费劲心思且竭尽全力。即便是碰上有点心动的男性——市议员伊藤友卫,也是因为体格像丈夫。只可惜,伊藤因承受不了被关押一夜的耻辱,在拘留所自杀孤寂地离去……。与此相对,多加如愿地在众艺人的陪同下热热闹闹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多加丈夫的不作为、伊藤的软弱,和多加的隐忍、拼搏、坚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多加经历了波澜起伏之后,依旧勇敢面对。可是,我们不禁会想:在众多艺人的守护下热热闹闹离去的多加幸福了吗?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多加的独立中有了自我吗?这或许也是山崎想要留给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女の勲章》中的女性意识与自然
《女の勲章》写于1961年,主人公是一位出身于大阪船场名门之家的小姐。大阪的船场,形成于江户时期,是一条由特殊阶层所组成、既有牌号又有资产的巨商们所聚居的城堡。为显示自己的尊严和保护自家的财产,这个阶层有着商家封建家庭的严厉而独特的家规。成长于船场的式子显得清高孤傲,虽不批判但也觉得这些船场规矩过于古板、无聊。于是为追求一种欢快秀丽的美感,式子开办了一所圣和服装学院,走上了西洋服装设计师之路。由于当时的日本设计师行业几乎全是女人,妒忌之类风气盛行,尔虞我诈、互相倾轧。
虽然已经看不到昔日那种繁华景象……。八年前,式子正是生活在这种浓厚的气氛中,一直到遭到战争破坏为止。当时,在这条街上,商人们残酷而强悍,金钱是判断、衡量和推动一切事物的中轴。式子原本对此有反感,才摆脱出这种环境的。但在她的体内似乎还奔流着商家姑娘的血液。虽说外表上是被银四郎牵扯着,可实际在她身上还蕴藏着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积蓄一笔财产的素质。由于银四郎的出现,这种素质被招了出来,并迅速膨胀了。
式子为了在时装界立足,一失足受控于身边的美男子银四郎。银四郎出身名校,拥有强烈的自信和男性的贪婪,他想方设法操控身边的四个女人,将她们玩弄女人于股掌之间,并逐渐掌控了服装学院及其分校的实权。式子不幸卷入了银四郎与四个女人(式子、伦子、葛美和富枝)之间的利益争夺战中。式子虽然害怕、孤独却无力挣脱。
初夏的川面,在强烈的日光照射下腾起一层薄薄的白雾,江面上飘浮着发黑的垃圾和稻杆。每当船只到来,垃圾便被水浪拨向两边,拖出一条污秽的水带。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感顿时攫住了式子。她想,难道自己真的会象银四郎所说的那样,不知哪一天,犹如这被稻杆和垃圾所蒙尘的川面,也会被葛美和富枝们所玷污?
式子看到被垃圾等污染的江面,联想到了自己遭受的玷污和耻辱。可见在作者山崎眼中,女性的遭遇和自然遭受的破环是类同的。山崎作品中生态女性意识已初见端倪。式子看到发白的水泥路面长出的黄色小花,顿感孤独无力;她也不喜欢分校的混凝土搅拌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声普和铅灰色混凝土;置身于大自然中,式子觉得无比平静、满足和幸福。如此种种,在山崎作品中能感受到一种对于大自然的向往,可以读出作者对于在男权社会中想要追求独立自我却又无力的女性的同情。
二号女主人公——伦子,同样是一位有事业心的典型职业女性,她不满足于一生只同尿布、锅台打交道,连结婚都要仔细盘算、权衡是否对自己的事业有促进作用或者是否有益。当伦子看到富枝得到了附属服装工厂时,内心无比恼怒和嫉妒。她在算计着如何把银四郎拴在自己身边加以利用,实现自己成为名服装设计师的执着追求的目标。前男友野本憨厚、朴实、善良、简单,令人感到温暖柔和,跟他在一起使人能得到宁静的休息和幸福。富枝说:“伦子的前男友野本,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他憨厚,朴实,有男性的特点,他是个心地善良的男子汉。”
野本看穿了伦子追求行乐和虚荣的心,仍对伦子充满真挚的爱情和始终如一的诚恳的心,伦子不止一次地被他笃厚和诚实的为人所感动。但是与其享受平凡的幸福,她更渴求虚荣和欲望而取得的更大的幸福,更渴望获得充满着荣耀的轰轰烈烈的事业的成功。她远离了粗野的乡下佬野本,选择了满嘴的欺骗、冷酷和刻薄的银四郎,即便是和银四郎在一起,心里油然感到一种无法排遣的烦恼。
和伦子类似,式子最初并不接受银四郎建立分校和规模扩展的建议,不喜欢从大阪城远眺到了眼前杂乱无章的街道展。“天守阁昔日的那种辉煌壮丽,如今却感觉不到它的遗风了,完全失去当年的面貌了,更没有留下特别值得白石头教授光顾的文物!”
式子一见到白石教授那种孜孜不倦专心求学问、谨慎、克制、严肃而沉默的生活态度,总有一种从超凡脱俗中得到陶冶的感受,白石教授对于城堡的释义、对于爱情的执着、对于文学的素养等精神境界,让式子着迷并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
“人,不管是谁,都希望别人以某种形式承认自己的存在但是,如果被承认的方式发生了哪怕是些微的偏:差或失常,那么,她(他)的人生甚至也会失常起来。比如说,一个人想把声望和财富像勋章一样悬挂在胸前,但如悬挂的方式失去常态,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这或许是对式子眼下的一切最好的解释。听着白石教授的一番话,一阵强烈的茫然而孤寂的情绪袭向了她。自己当初怀着大阪名门小姐式的风度、自信、以及服装设计上才华踏入时装界,慢慢地在银四郎的影响下执迷于显身扬名的事,成了银四郎那种精于算计的人。自从她接触了白石教授后,仿佛昨日前那以往的繁忙和喧嚣,是那么遥远而飘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她感到安闲和满足,心里有了真正的充实。她想远离那服饰界的激烈竞争和彻底摆脱银四郎的操控。
式子对银四郎这种不择手段的态度,以及他的种种苛酷和无情,感到无法形容的厌恶。被银四郎夺去自尊心和自信心后,曾经为自己的成功而升腾起的那种幸福感瞬间消失和因失去自尊心而产生的愤恨,变成了一种暗淡的冰冷的东西。这种表面的幸福背后,那无边的被欺骗的耻辱感,让式子陷入更深的受辱的泥坑。
式子对银四郎如此的厚颜无耻深恶痛绝,想要果断切断和这种厚颜无耻之徒之间的一切联系。可是遭到银四郎一番奚落和恐吓,斥责式子自己追名逐利,他只不过利用了女人们的疯狂野心和虚荣心而已。
其后,式子竟然因为担心失去名声和财富,在银四郎温柔的抚爱和引诱下,在深深地感受到污辱和对他的无比憎恨中,听从了银四郎的摆布。她没有做到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清白高傲,一种无以名状的敬畏和痛苦包围了她。式子的母亲是大阪商家名门的小姐,家业继承人。她为了区别入赘作养子的父亲的身份,从衣饰、日常用品到餐具无不标上华丽的泥金画纹章。式子模仿母亲,无论在甲子园校,还是在大阪本校,都嵌上了华丽的彩色玻璃,作为学校的饰章。可是如今,自己失去了名门闺秀的尊严,失去了一个女人的自尊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和富有,甚至违背自己的良心,置身于内里肮脏而表面堂皇的荣华富贵中。
式子成了银四郎手中的提线木偶。为保住名气和富有,继续违心地忍受过着龌龊生活的那种丑态。式子虽然在服饰界取得了成功,却发自内心渴望得到伊东歌子那样恋爱、成家带来的平静的有情的幸福。生平第一次爱上了一个人的式子接受到了灵魂的洗礼,渴望摆脱沽名钓誉和追慕虚荣的生活,她主动一步一步靠近白石教授,大胆地追寻白石教授的足迹。
同时,又一想起在日本时和银四郎的那种龌龊关系,以及和三个女职员蒙受了同样的污辱时,便陷入了一种可怕的绝望中。而今,身背着这种沉重的十字架,从绝望的深渊中爬上来,希望得到白石教授的爱……。她为自己过去和银四郎的关系而感到羞愧、痛苦、悔恨,她觉得今天能继续爱白石教授,是自己灵魂的自救办法。
式子在夕阳残照的沙滩上,看到一群蒙头盖脚地披着黑色披风的妇女,蹲在沙滩上,面向大海一心在作着祷告祈求丈夫的平安归来,觉得她们是迄今见过的最使她感动的美好形象了。她满以为自己如今也已找到了值得等待的人,从而感到了慰藉并享受着这种痴情。
可是,女人的勋章,还在深深地吸引着式子。忽然,前面出现一抹光亮,抬眼寻去,原来正面的窗户上嵌着一块圆形的彩色玻璃。它,在夕阳的光照中,如同一轮燃烧着的火球。……这样的光彩和情景,似乎更为绚丽地反映出了自己于学校创办之初特意嵌在校部墙上那块彩色玻璃所显示的华丽与纯贞的自豪气概。这块太阳似的闪耀着夺目光彩的圆形玻璃深深地吸引着她。银四郎自信地认为:抓住了式子名利熏心、追逐名利、充满虚荣的特点。可是他算计错了,式子不再是当初乖乖地做自己的俘虏的那个式子了。她遇见了纯洁的、没有欺骗和耻辱的爱情,她开始憧憬美丽和温馨的生活。她悔恨自己落进了一个颇有经营能力的年轻男人的诱惑圈中,悔恨被银四郎虚情假意所感动,后悔成了虚伪柔情的俘虏,后悔不该同他一起踏进一个充满虚荣和追逐名利的世界……。
白石教授对式子是真心的,他原谅了式子和银四郎之间的过往,和式子商量好:朗贝尔时装展后,找银四郎清算之前的一切,开始二人的幸福生活。
式子和白石教授置身于傍晚的宁静中,面憧憬着即将到来的幸福:朗贝尔时装展取得了成功,银四郎得到了满足,在这种时刻,给予他所希望得到的一笔财产,从此与他分道扬镳。可是薄暮悄悄降临,刚才白岚袅袅的东山,此刻已被淡墨色的暮霭笼罩了。本来充满信心的清理,遭到惨败。……式子预感到无法从银四郎设置的圈套里自拔出来,自己和白石教授的幸福遭到了破坏,……她所追求的赖以生存的希望已经失去了!……难以挽回的绝望和沉重的悲哀,袭击着她的心。式子失去了一切,有的只是被白石教授拒绝后所产生的无法摆脱的绝望,以及由银四郎强加给她的耻辱。式子只能嘲笑、憎恶自己的愚昧:自己出于强烈追求事业成功以取得更多的名利地位的勋章来装饰自己的欲望,但这些沉重的勋章却把自己和过去紧紧拴在一起,并无情地夺去了自己与白石教授结合的幸福。
彩色玻璃继续微笑似地向她炫耀着明亮的光彩,最终自己被彩色玻璃勋章明亮的色彩给吞没了。银四郎的残酷诡计把式子逼上死路,银四郎虽感意外却毫不自责。他会沿用曾根口中残忍的“珍珠养殖法”继续制造女人的勋章——名声和财富,并残酷地获取珍珠佩戴到贵妇人的胸前,使女人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以满足自我私欲。试问:这场利益博弈、男女博弈中有真正的胜利者吗?回到山崎的永恒主题——人性的贪婪来看待这个问题,答案立马显现。
三、山崎小说、女性、生态
作品中时而可见作者对于环境破坏的描述,大多出现在女性的眼里。能揭示出蕴含于小说中的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及其山崎对于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展现了山崎作品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为虚荣而偷窃……这也许是一种潜藏于女人体内的最为丑恶的东西……”——式子的话语,以及“用这珍珠的一生来比喻女人可悲的一生”——曾根的话语,又是那么地富含哲理。
“生态女性主义”这个术语,最早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Francoised’Eaubonne(1920-2005)于1974年首次提出来。此后,作为一股强劲的文化思潮,影响日益扩大。生态女性主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入日本,虽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但其倡导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男女之间互相关爱,关怀和尊重,摒弃男尊女卑这种思想,力图构建一种可以使人与自然、人与人平等互助、共同发展繁荣,这个理念值得我们倡导和践行。生态女性主义关注受压迫的人们,特别是受压制的女性的命运。这一个个典型的悲剧女性形象和悲惨结局,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并引发了我们对于这一切悲剧的根源、当前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系列问题进行思考。不论是贪婪、傲慢的女性形象,抑或是坚毅、隐忍的大阪女商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们的生存之道该怎么走,应该是作为贤妻良母,还是女权主义者?不论如何,男女之间的相互尊重,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和谐,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正是山崎小说留给世人亟待解决的一个大课题。虽然总体来说,其笔下的女性并没能真正做到完整意义上的自我和独立,女性的幸福更过的还是依附于男性身上,但综合当时的创作背景,山崎能有如此的眼界和视角,来审视女性经历了急剧社会变革后,自我意识觉醒带来的女性独立精神的勇敢追求,谋求在男权社会中的解放,实属先列并值得大家赞扬。山崎丰子中后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设定是否做出了改变?具有哪些形象特征?将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