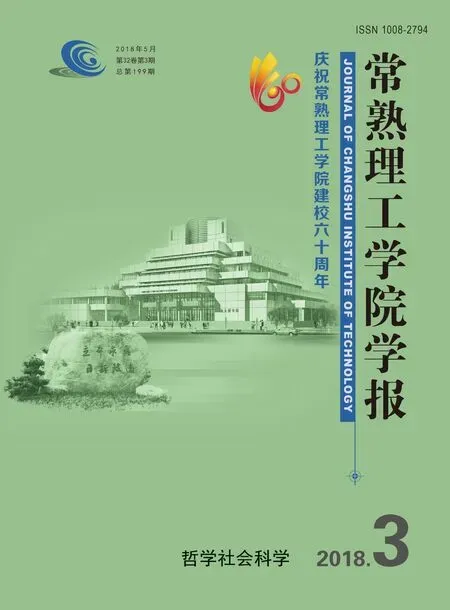古埃及文献中的外族人及其形象构建研究
2018-03-29徐昊
徐 昊
(南通大学 文学院历史系,江苏 南通 226019)
古埃及文明发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之中,自埃及向东穿过东部沙漠就可抵达红海沿岸;东北方向凭借西奈半岛与亚洲联接;向西越过沙漠则是古代利比亚部落的活动区域;向南沿尼罗河上游而行可进入努比亚地区;向北出尼罗河入海口就可直达地中海。受益于此,埃及很早就与外族文明建立了联系。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涅伽达(Naqada)文化二期(公元前3500年—前3150年),埃及就已通过叙利亚人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保持着联系。[1]34随着埃及步入文明时代,对外战争、贸易活动为埃及人提供了更多与外族接触的机会,大量涉及外族的文本与图像文献亦随之出现。实际上,古埃及文献中外族人的形象纷繁多样,既有亚洲的叙利亚人和赫梯人,也有非洲的努比亚人和利比亚人,还有源自欧洲的海上民族,这为我们研究古埃及人的“他者”观念和民族政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实际上,古埃及的外族人形象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学界关注,且不乏精辟论断。①学界曾围绕古埃及外族人的形象从不同视角展开研究,有的学者尝试将外族形象置于“他者”的语境中进行讨论,如郭丹彤:《埃及人心中的异邦》,《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52-59页;金寿福:《古埃及人如何构建他者形象》,《光明日报》,2017年11月13日第14版。也有学者将研究领域聚焦于具体的异族族群,如Snowden F M:Images and Attitudes: Ancient Views of Nubia and the Nubians, Expedition Magazine,1993,35:40-50;Mu-chou Poo:Enemies of Civilization: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er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Egypt, and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王欢:《古代埃及文献中的赫梯国王形象》,《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第18-24页。另外,还有学者从形象学范式入手,针对外族形象生成过程中所形成的“套式”(Stereotype)问题展开讨论,如Hall E S:The Pharaoh Smites his Enemies: A Comparative Study,Deutscher Kunstverlag,1986;Booth C:The Role of Foreigners in Ancient Egypt: A Study of Non-stereotypical Artistic Representations,BAR International Series,2005;Butner A:The Rhetoric and the Reality: Egyptian Conceptions of Foreigners during the Middle Kingdom, University of Tennessee,2007。然而,传统研究更侧重探讨古埃及人对外族人的负面形象塑造及其生成机制,①古埃及文献中外族人负面形象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Gilroy T D: Outlandish Outlanders: Foreigners and Caricature in Egyptian Art, Göttinger Miszellen. 2002,191:35-52; Smith S T: Wretched Kush, Routledge, 2003; Shih-Wei Hsu:Captured,Defeated, Tied and Fallen: Images of Enemies in Ancient Egypt, Göttinger Miszellen, 2017,252:71-87。对客观中立或褒扬式的外族形象塑造涉及较少,对外族人形象的构建方式及其功能的讨论也有待继续深入。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古埃及文本和图像文献入手,尝试选取古埃及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外族人形象进行诠释,结合古埃及宗教、政治和文化观念对外族人及其形象构建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加深我们对古埃及人外族观念的理解,拓展埃及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一、古埃及文献中的外族人
古埃及人的观念中固然没有系统和抽象的“种族”“族群”观念,但他们依然能够通过具体特征来分辨那些“非我族类”之人。事实上,埃及人在构建外族形象时巧妙地运用了两种形式:一是借助文本展现外族人的行为习惯、生活环境、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等情况;二是通过图像描绘外族人的外貌、肤色、体型、着装和地位等特征。
古埃及文本文献中的外族人一般被称作(xAstyw)[2]235和(psDt-pDwt)[3]570。象形文字名词主要由和两组符号组成,意为“山丘之地”或“荒漠之地”。古埃及人认为,尼罗河两岸埃及的河谷地区因受到河水滋润而土地肥沃,与周边那些外族人出没的,荒无人烟的山丘形成鲜明对比。而符号代表外族人在游牧狩猎时惯用的回旋飞镖,是象征外族人的固定符号。同时,由代表男人、女人以及代表复数的字符组成,指代一类人或一群人。因此,xAstyw译为“山丘之地的人”或“荒漠之地的人”,引申为外族人。另外,通常被译为“九弓”,主要指埃及北部的亚洲人、西部的利比亚人和南部的努比亚人等外族群体。它由(pDt)和(psDt)两组符号组成,意为“弓箭”,被埃及人认为是富有游牧和狩猎特征的外族部落的象征,最早出现在蝎子王权标头②蝎子王(Scorpion King)为古埃及前王朝时期(公元前3150—前3050年)最后一位国王。英国考古学家魁贝儿(Quibell)在埃及的希拉康波利斯(Hierakonpolis)的一座墓葬中发掘出了一个权标头,其上刻有蝎子王手持锄头耕耘的图像,图像上方有弓箭图案,学者们认为那是被蝎子王征服的部落象征。参见Quibell J E: Hierakonpolis, Bernard Quartich, 1900.之上。而则由三个符号组成,译为“九”。当然,在象形文字中不仅用于表示数词“三”,也是名词的复数形式,三个复数组合则意指其数量庞大,不计其数,用以泛指为数众多、繁殖力极强的外族人。[4]472
古埃及人同样擅长运用图像从视觉层面反映外族人特征。一方面,埃及人能够运用色彩体现外族人特征,彩色图像中所体现的皮肤颜色常成为埃及人认定外族人的重要标准。根据现代考古和人类学家的研究,埃及人的人种构成较为复杂,既有非洲尼格罗人种的特点,也有地中海人种的特点,其肤色为介于黑色和黄色、白色之间的过渡色。因此,从保存下来的古埃及彩色壁画中可以发现,“埃及人被涂成红色,努比亚人为黑色,利比亚人和爱琴海人为黄色或白色。”[5]19另一方面,埃及人常常会运用线条构图来勾勒出外族人在相貌和衣着上的特点。据收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一块法老拉美西斯三世(Ramesses III)时代(公元前1198年—前1166年)绘制的墙面贴砖显示,来自亚洲的叙利亚部落首领额头较低,长着突出的鹰钩鼻和长而尖的胡须;努比亚人则戴着大耳环。[6]165除此以外,很多浮雕中都会将非洲地区的努比亚人描绘成头戴鸵鸟羽毛,身披兽皮之人;而将亚洲人描绘为头发披肩,身穿羊毛边围裙的人。[7]9比起发式精美且身着优雅亚麻衣的埃及人,外族人以渔猎和游牧为生,仍处于原始与野蛮生存状态的特征尽显无遗。
二、古埃及文献中的外族人形象
早在公元前3100年,埃及就进入了王权专制时代,城市的兴起与南北埃及的统一为国家发展铺平了道路。环顾埃及周边区域,无论是同属于非洲的努比亚和利比亚地区,还是位于亚洲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其国力和文化发展程度皆远逊于埃及,有的地方甚至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原始部落时期。为了彰显国威,法老时常以镇压外族反叛为借口发动对外扩张战争,而此时的外族人多以“被镇压者”的形象出现。古王国(公元前2687年—前2191年)之前,“被镇压者”的形象则以“击打(敌人)图像”的形式呈现,早王朝时期(公元前3100-前2686年)的纳尔迈调色板(Narmer Palette)便是这种形象范式的典型案例,调色板上雕刻着法老纳尔迈抓住外族俘虏的头发,用武器击打俘虏头部的情景,[8]10这一图像被历代埃及法老沿用并进一步模式化,逐渐成为法老镇压外族人的固定主题。该图像甚至还曾流传到努比亚地区,公元1世纪左右仍被当地统治者使用。[9]46
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190年—前2061年)时,适逢埃及政局动荡,外族人乘虚而入,国家内忧外患。外族人被塑造成了充满敌意的“混乱制造者”,在著名的教谕文学作品《梅里卡拉王教谕》(The Teaching for King Merikare)中,埃及人这样形容亚洲人:“居无定所,却灾害不断,在沙漠中步行游走。他(们)从荷露斯时代(神话时代)就开始争斗。他(们)既不是征服者,也不能被征服……最重要的是,亚洲人憎恶埃及。”[10]152另一篇表现这一时代社会政治状况的文献《伊普味陈词》(The Admonitions of Ipuwer)更是痛陈外族人给埃及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外族人在整个埃及流窜。那是真的!(埃及人的)每一张脸庞都苍白惊恐!”[10]190外族人野蛮、落后与混乱的形象如此呈现出来。
当然,古埃及的文献中也能发现有关外族人亲善友好的记录,这部分外族人被认为是协助埃及维持秩序“玛阿特”(Maat)的重要力量,他们或是供职于埃及,或与埃及结盟,或是受埃及教化,与代表混乱的外族人群体有着本质区别。
外族人自古王国时期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埃及,开始逐渐融入埃及社会。很多外族人或被招募进埃及辅助部队,或充当雇佣军,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有些人还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埃及的文化和价值观,有的甚至皈依埃及宗教。其中不乏埃及化程度较高者,尤以努比亚的“麦查伊人”(Medjay)最具代表性,他们长期在埃及部队中服役,因常为埃及四处征战而颇受埃及法老和官员的信任。因之,《伊普味陈词》中将利比亚人和亚洲人认定为混乱之源,认为只有“麦查伊人与埃及交好。”[10]208除此以外,根据《卡叠什战役铭文》(Inscription of Battle of Kadesh)记载,来自地中海地区海上民族(Sea Peoples)的一支“舍尔登人”(Sherden)早在十九王朝时期就被编入法老军队的战斗序列。[11]136值得一提的是,据考古发现的卡叠什战役壁画图像显示,[12]30-35这些舍尔登军人的形象并未像亚洲人或努比亚人那样被刻意丑化。
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69年—前1081年)是古埃及历史上外交活动的活跃期,法老曾与周边地区强国结盟。因而,埃及文献中会出现涉及同盟国外族人的记录,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第一次联姻石碑铭文》(Inscription of the First Marriage Stele between Ramesses II and Hittite),这是关于十九王朝法老与赫梯公主缔结政治婚姻,巩固两国同盟关系的历史文献,文献提到:“赫梯伟大统治者的女儿远道而来,已抵达埃及。她被引领至陛下的跟前,(随行)队列中带着丰厚的贡赋,数不胜数,应有尽有。陛下注视着她俊美的面容,美艳绝伦,贵族们更是将其惊为天人!”[13]253此处的赫梯公主及其随从虽是外族人,却有着埃及盟友的身份,对其大方优雅和亲善友好形象的刻画无疑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在古埃及人的观念中,语言可被视为区分“我者”和“他者”的标准。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就曾提到:“埃及人称所有讲其他语言的人为野蛮人。”[14]473即懂得埃及语或受埃及教化的那部分外族人,可不被纳入野蛮人的范畴。事实也是如此,埃及文献《新努西的故事》(The story of Sinuhe)中记载的一位官员因为宫廷政变而逃往亚洲地区,一位部落首领友善地接待了他,并说:“同我在一起对你有益,你会听到埃及的话语。”[10]57此处,部落首领明显是深受埃及教化之人,其形象也与那些野蛮落后的外族人具有本质区别。
概言之,古埃及的外族人,实际就是指那些具有“非埃及”特性的族群。然而,这些“非我族类”的外族人并非仅以“被镇压者”和“混乱制造者”的形象在文献中出现,他们友好亲善的形象同样也是外族人诸多形象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三、外族人形象的构建方式
形象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关系,“是一定条件下的人和一定条件下的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关系。由于条件的单一或多重作用,形象常常是可变的。”[15]9所以,古埃及文献中的外族人形象常常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有的形象比较客观真实,有的则被刻意丑化歪曲,有的还被美化与粉饰。虽然外族人的形象时常会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但这些在本质上都遵循着埃及人独特的形象构建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古埃及人常将自己置于世界中心的位置,并在此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以埃及为中心式的外族人形象构建方式,这就导致了埃及人常会不自觉地以自身作为标准来构建他者形象。诚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言,“当一群人与其他文化相遇时,一般会发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一种是否认或无视文化间的距离,……第二种普遍的反应与前者相反,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其他的文化构建成为与自己的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16]169显然,彼得·伯克所提到的第二种反应更适用于古埃及人的外族观念,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外族人诸多不符合埃及人价值标准的差异特征在文献中往往被刻意强调,有的甚至被夸大。例如,在法老赫连霍布(Horemheb)统治时期(公元前1343年—前1315年)雕刻的一幅描绘了埃及看守者监管努比亚俘虏的浮雕,努比亚俘虏的额头上有尽显老态的皱纹,头颅则扭向不同方向,身体蜷缩,有的还张着嘴,呈现出畏惧、愤怒和彷徨的心态。[17]38这与埃及看守者年轻力壮、闲适镇定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反差,此举明显旨在强调外族人胆小畏缩和体力不支的形象特征。
其二,埃及人在构建外族人形象时,运用了想象和真实杂糅的构建方式。无论是在文本还是在图像中,不少外族人的形象都是埃及人结合自身文化和认知对外族人进行想象性塑造的结果。一些涉及外族人的古埃及文献中记录的外族人的形象其实与真实的埃及人毫无差别,只是经过想象后添加了一些强调其外族身份的特有标识。例如,《被诅咒的王子》(The Doomed Prince)记述一位因受到神灵诅咒而远走亚洲的埃及王子,他来到了西亚强国那哈林①那哈林即米坦尼王国(Mitanni),由古代西亚地区的胡里安人(Hurrian)建立,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活跃于叙利亚北部与两河流域地区,后在赫梯帝国与亚述帝国的进攻下灭亡。(Naharin),并通过国王的考验而迎娶了该国公主。[18]200-203除了故事中公主外嫁他国和公主居住的具有西亚特征的高塔等外族特性外,[19]184-185那哈林国王和公主所讲的语言、崇拜的神灵、奉行的礼节都与埃及人别无二致。很明显,这既有对真实埃及宫廷的描绘,也杂糅了一些虚构的外族想象因素。虽然故事将那哈林的国王和公主定位为外族人,但他们的形象其实更接近埃及人。
其三,外族人的形象构建深受不同时代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事实上,新王国时期是埃及人外族观念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受地理阻隔和交通不便等因素制约,埃及人能够接触到的异域范围有限,且长期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上保持着对外族人的绝对优势。因此,文献中常着重描绘外族人落后与野蛮的形象。另外,周边区域的外族人在第一中间期和古王国时期还曾不断渗透和劫掠埃及边境,[20]283成为埃及国家安全的隐患,因而在文献中才会以“被镇压者”和“混乱制造者”的形象出现。然而,至新王国时期,亚洲地区的赫梯、米坦尼、亚述和巴比伦帝国崛起,势力直逼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与埃及形成针锋相对的争霸局面。面对这些强国,埃及开始实践均势外交战略,推行平等互惠的外交政策。受此影响,部分外族人的形象开始由负面转向中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受到美化与粉饰。第三中间期(公元前1081年—前711年)之后,埃及又历经了利比亚王朝、努比亚王朝、亚述征服和波斯统治时代,埃及社会民族构成日益多元化,文献中外族人的特征也在民族融合的社会环境下日渐消解。
四、外族人形象构建的功能
藉由不同方式构建出的古埃及外族人形象,既可被视为埃及社会集体想象的集中反映,也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独特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即维护法老王权的合理性,显示官员的特殊地位以及实现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
首先,古埃及人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就如同埃及的创世神话,太阳神从象征着混乱的原始瀛水中升起,创造了代表着公正、和平的秩序——“玛阿特”,奠定了国家稳定的基础。然而,“玛阿特”并非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状态,它随时会受到混乱与邪恶的侵袭,秩序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破坏,法老的责任正是在邪恶与混乱显现时予以打击与毁灭,保证“玛阿特”顺利回归。[21]180外族人就是在此种背景下被纳入到埃及的宇宙观与创世体系之中,而法老征服与打击外族人的行为也就成了驱逐混乱与邪恶的一种手段,成了履行维护宇宙和国家秩序的一种义务。所以《涅菲尔提预言》这样描述法老:“他将会建立伊布赫卡要塞,这样亚洲人将永远不能进入埃及。他们会为乞丐搜寻水,这样他们的牲畜也能饮用。然后,玛阿特就会回到王座上,混乱将被驱逐。”[10]217受此观念影响,为了将自己形塑为引领人民战胜异族的伟大领袖,法老通常会将对外征服和镇压外族人的行动仪式化,以至于很多时候即便没有边患,法老也会形式化地宣称兴兵征讨外族人。[22]129班师凯旋之后,法老还会命人将镇压和打击外族人的文本和图像刻写在神庙或宫殿的墙壁上。因而,为了衬托法老的英勇与无畏,为了彰显王权的至高无上,文献常会刻意丑化和扭曲外族人的形象,甚至还会在图像中将外族人的形象置于法老或法老名字之下,象征法老的镇压行动。对此,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年—前1786年)的《阿蒙奈姆海特教谕》如此说道:“(法老)我攻击亚洲人的部落,让他们像一群狗那样畏缩。”[10]170同样,新王国之后逐渐增多的美化和粉饰外族人形象的记载,也只是从宣传的需求出发而对外族人的负面形象进行了必要的置换,只能将其视为埃及对外政策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法老王权的合理性。
其次,除了皇室的文献之外,外族人的形象还经常出现于涉及贵族和官员的文献之中。在发掘官员索贝克荷泰普的坟墓时,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幅描绘外族朝贡的壁画,在这位图特摩斯四世(Thutmose IV)统治时期(公元前1419年—前1410年)的财政官员的坟墓壁画上,描绘了来自亚洲和非洲的朝贡者,他们带着当地特产,携老扶幼,态度谦卑恭敬地献上贡品。[23]147-148依据纳贡惯例,外族的贡品除了由法老当面接收外,也会由重臣代为接收,之后再呈献给法老。外族人谦恭的形象在这里无疑突出了索贝克荷泰普的重要性,展现了他深受法老信任的独特地位。
另外,考古学家们在阿斯优特(Assiut)地区发掘出一套由四十人组成的木雕兵俑,它们出土于一位十二王朝时期的贵族墓穴,是被涂上黑色颜料的努比亚人,他们佩戴着弓和箭,与装备着青铜矛和盾牌的埃及士兵分列行进。[24]104古埃及人通常认为,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只是永生的开端,所以他们会悉心挑选随葬品,力图还原生前真实场景。通常,努比亚人在埃及军队中主要充当辅助兵和雇佣兵,负责策应由埃及军人构成的大部队展开行动。因此,努比亚士兵的形象表明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支建制完整的军队统帅,地位较为特殊。
最后,外族人的形象构建还是埃及人实现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埃及人在进行自我认同时,常会通过否定“他者”以确定“我者”身份,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定,例如他们将尼罗河认定为神给埃及的特殊恩赐,而异族则因为得不到神的眷顾而只能用雨水作为补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埃及人所具有的文化优越感,以丧葬文化为例,当谈到埃及人的安葬地点时,就出现了这样的表述:“你不应死于异族的土地上,因为亚洲人不会守护你。你也不应被放置在羊皮上,他们只会将这作为你的坟墓。”[10]62这表明外族人既不会保护死者,也不会为他建造墓穴来供奉尸体以及灵魂“卡”(Ka)和“巴”(Ba),也就意味着死者无法获得永生,而这却是笃信永恒来世的埃及人所无法接受的现实。透过丧葬文化的描述,埃及人完成了对“我者”形象的塑造,凸显出埃及文化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以此实现了对“他者”文化的否定,有效强化了埃及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事实上,埃及人的这种优越感直至古希腊时代还广为流传,希罗多德也曾提到,“埃及国王认为,埃及人在手工艺术领域远比所有其它外族人都要优秀。”[14]423
简言之,不同的文献中外族人形象构建的功能各有侧重:一是在皇家文献中,外族人形象的构建总是紧密围绕王权合法性而展开的;二是在涉及官员和贵族的文献中,外族人形象是以突出官员和贵族特殊身份地位为出发点而进行构建的;三是外族人的形象构建也可被认为是埃及人在文化层面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
总之,古埃及人将那些在体质特征、生活环境、语言文化等方面与自己有较大差异的族群称为外族人。为了体现法老王权的至高无上、显示某些官员和贵族独一无二的身份地位、彰显埃及在物质文化层面的优越性,古埃及人在不同的时代贯彻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描述方式,适时采用了真实与虚构杂糅的形象构建方式,从而塑造出了风格各异的外族人形象。除了以“被镇压者”的形象出现之外,外族人还因滋扰边境等行为而被认为是宇宙和埃及国家稳定的隐患,其“混乱制造者”的形象由此而来。不仅如此,我们通过深入梳理文字材料并结合考古资料发现,外族人还会以亲善友好的形象出现在埃及人的视野中。究其根本,纷繁多样的外族人形象是埃及人进行形象构建的产物。可以说,外族人的形象是埃及人自身形象反映的一面“镜子”,也是埃及人构建自我认同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方式,这对于深入理解古埃及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Ward W A. Relations between Egypt and Mesopotamia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Middle Kingdom[J].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964 (7).
[2]Erman A, Grapow H. Wörterbuch der Ägyptischen Sprache: Vol.III [M]. Berlin: Verlag von Reuther &Reichard, 1957.
[3] Erman A, Grapow H. Wörterbuch der Ägyptischen Sprache: Vol. I [M]. Berlin: Verlag von Reuther &Reichard, 1957.
[4]Helck W, Otto E. Lexikon der Ägyptologie :Vol. IV [M].Wei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5.
[5]Anthony F B. Foreigners in Ancient Egypt: Theban Tomb Paintings from the Early Eighteenth Dynasty (1550-1372 BC)[M]. New York: Bloomsbury, 2017.
[6]Museum of Fine Arts. Highlights, Arts of Ancient Egypt[M]. Bosto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press, 2003.
[7]Booth C. The Role of Foreigners in Ancient Egypt: A Study of Non-stereotypical Artistic Representations [M].Oxford: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2005.
[8]Quibell J E. Hierakonpolis [M]. London: Bernard Quartich, 1900.
[9]Hall S, The Pharaoh Smites his Enemies: A Comparative Study [M]. Munich: Deutscher Kunstverlag, 1986.
[10]Simpson W K.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Breasted J H.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Ⅲ [M].London: Histories & Mysteries of Man Ltd, 1988.
[12]Sandars N K. The Sea Peoples: Warriors of Ancient Mediterranean [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78.
[13]Kitchen K A. Ramesside Inscriptions: Vol. II [M].Oxford: B. H. Blackwell, 1979.
[14]Herodotus. Herodotus I: Book I & II [M]. translation by A. D. Godle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20.
[15]秦启文,周永康.形象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6]彼得·伯克.图像证史[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7]Gilroy T D. Outlandish Outlanders: Foreigners and Caricature in Egyptian Art [J]. Göttinger Miszellen,2002(191).
[18]Lichtheim 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II [M].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19]Biase-Dyson C D. Foreigners and Egyptians in the Late Egyptian Stories [M]. Leiden: Brill, 2013.
[20]刘文鹏.古代埃及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1] Hornung E. Conceptions God in Ancient Egypt: The One and The Many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22] Warburton D. Kadesh and the Egyptian Empire [J],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1997(12).
[23] Strudwick N. The British Museum Masterpieces of Ancient Egypt [M].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6.
[24] Egyptian Antiquities Organization. A Guide to the Egyptian Museum Cairo [M]. Cairo: General Egyptian Organization Press,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