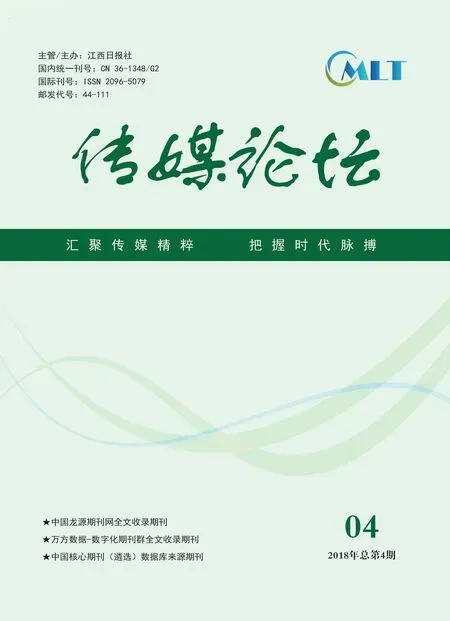影视赏析
——从《灰阑记》到《高加索灰阑记》
2018-03-28吴克张鑫
吴 克 张 鑫
(1.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 2.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灰》虽是布莱希特长期以来的创作冲动,但引起创作改编的欲望,是有前提的。《灰》中未有复杂的历史联系,主要人物少而精,故事围绕着一个家庭和几个与之有关的人物展开,这样抛开东方背景,很容易理解《灰》。包拯通过“灰阑”评判海棠和当家主母争子一案的情节,与《圣经》中所罗门王“一刀劈两半”的方式决出孩子母亲的故事十分相似,抓住东西方的心理共同点,改编后的戏剧才能拥有群众基础,成为传世经典。改编产生在跨文化语境下,在改编中,布莱希特除了进行文化过滤,还对其进行了深层地创造性改编。
一、主题的升格
(一)从《灰》到《高》,是从宗法关系改编到道德关系
《灰》中展示的母爱是对自己亲生骨肉,是天经地义的,母子情深善良的有点懦弱,老实的有点痴憨的海棠通过“灰阑”断案,争取到了自己的孩子。到了《高》却反其道行之,是米歇尔“均匀的呼吸、娇小的拳头”使格鲁雪“站起来低下头去,叹口气抱起孩子把他带走”,这里表现的是最本真的人性。
(二)从《灰》到《高》,是从养之爱改编到育之爱
《灰》中,通过“灰阑”断案,海棠冤情大白,人财双全,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海棠可以用该得的财产,养好自己和孩子。到《高》中,格鲁雪为了更好地抚养米歇尔,费尽心机,吃尽苦头。她无私、无畏、机智、忍耐等品质越突出,米歇尔越能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为品德优良的孩子,这比他得到总督所有的遗产都更值得,更使他富有。这正是格鲁雪不想让出孩子的原因,母爱被推向了更高的境界。
(三)从《灰》到《高》,是对“灰阑”断案的创新
《高》的“断案”是对传统惯性思维的逆转,布莱希特以格鲁雪的成功突破了狭隘的血缘关系,让观众思考何为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关系、人与物之间最理想的关系。正因为这样的“陌生化”思维,《高》就思想意义而言,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二、思想性的渗入
(一)从《灰》到《高》,是从普遍道德标准发展到为政治目的发声转变——用阶级标尺评价是非曲直
《高》突破《灰》的叙事结构,采用戏中戏模式,把“灰阑”断案保留在剧本中。“灰阑”断案属于“戏中”的第二条线——阿兹达克的线索,阿兹达克相较于包公的“符号化”形象,是被创造出来拥有完整叙事线的“典型形象”,他的判案方式既不像包公那样以法律为准绳,也不以事实为根据,表面上看像一个无赖醉鬼在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实际上他有一个不变的准则就是为穷人撑腰、为平民出气。阿兹达克是用阶级的标尺来衡量案件的是非曲直,这样一来使《高》在表现一般人性的同时,揉进更多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阶级意识、政治目的。
(二)从《灰》到《高》,是从活在当下到思索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对布莱希特的影响
《高》的楔子中农民们通过在讨论山谷归属问题时坐成一“圈”(“灰阑”)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山谷最后归罗莎卢森堡的农民所有,就像米歇尔最后归母亲格鲁雪所有。
细看三个“灰阑”故事,《灰》中的孩子判归海棠是因为血脉;《高》中的孩子判归格鲁雪是因为她可以让米歇尔更好成长;楔子中,山谷判归罗莎卢森堡的农民,因为他们能更好地开发它。通过对“灰阑”的两次陌生化改编,布莱希特架构了一个三重式结构,这种相映生辉的陌生化实验,引导观众更能关注戏剧的中心事件,并能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展开思考。
此时布莱希特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剧本渗透着他对人类历史发展法则的新解释。《高》中“灰阑”断案的解决方法相较《灰》更具有时代语境下的“能动性”。以致有评论说“这种新型的戏剧作品包含着重大的社会冲突和高度的社会热情,其主要目的在于改造社会”。
三、总结与启示
中西戏剧成长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各有千秋,应互相借鉴吸收。布莱希特对“陌生化”戏剧理论的实践,使改编具有了创造性。其创新意识和颠覆能力值得我们借鉴。而其剧作中暗含的政治性、倾向性,我更想把它理解为: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除了给人以审美感受外,还饱含着对社会、历史、人生、人性的探索热情,这是我们所缺少的一种情怀或使命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