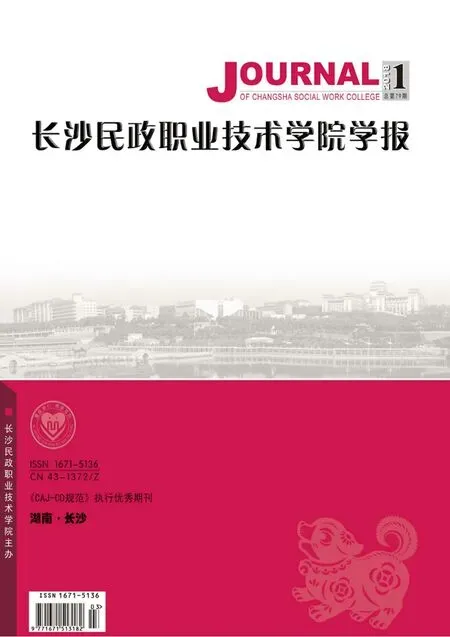唐诗中秦川意象所蕴含的帝京文化意蕴
2018-03-28陈燕
陈 燕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意象是构成诗歌的必要元素,它体现为一个个的词语分布在诗歌中,诗歌中的意象包括了客观世界的物象与诗人的主观情感。不同的作家或者同一作家在不同时期,面对同一个“象”会流露出不同的心理。唐诗中的“秦川”意象是诗人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心理的具体体现。据《全唐诗》的统计来看,“秦川”这一词语在唐诗中出现60余次。据研读分析后可以归纳出这一地理名词在唐诗中所代表的意象大致有四种:一是帝京国都,二是恋乡思亲,三是感时伤世和怀古咏史,四是离别送别。文中主要探讨第一种帝京国都意象及其所蕴含的帝京文化意蕴。后面三种意象不予分析。诗人笔中秦川意象所蕴含的帝京国都在唐代不同时期又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意蕴,要想分析它所蕴含的文化意蕴,首先得清楚秦川这一意象的地理范围。
一、秦川的地理所指
秦川这一概念在《中外地名大辞典》里有三种解释:“一是水名。即甘肃省清水县之清水。郦道元《水经注》曰:“清水上下,咸谓之秦川。”二是地名,《方舆纪要》曰:“陕西叫秦川,也称关中。”三是在广西省平南县西三十里,旧置秦川,相巡于此。”[1]从唐诗中有关秦川意象的诗歌阅读分析中可以确定了解到秦川这一意象多和帝京有关,而唐朝的帝都在陕西西安,符合上面第二种解释“陕西谓之秦川”。文人的心理界限和地理的实际范围往往存在一定出入。但是这种出入并不影响我们对秦川地理大致范围的判断,因为自古文人多有立功立名之心,只有朝廷能够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的足迹和理想往往以帝都为中心。所以可以大致确定秦川主要是指以陕西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有“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2]这样描写帝京的句子。李隆基的《初入秦川路逢寒食》有“自从关路入秦川,争道何人不戏鞭。”太宗、玄宗为帝王,他们笔下的秦川显然是指帝京为中心的关中地区。
二、秦川意象的概念界定
“意象”演化成一种诗歌理论始于六朝。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有“窥意象而运斤”,最先阐释了意象这一诗论。他强调要有澡雪精神,通过不断积累探索,“宰而玄解”、“寻声定墨”,从而能够对意象“运斧成斤”。刘勰笔下的意象是通过神思积累澡雪而成的,是指作家有真切的情感所寄托的想象的产物。清王夫之对意象理论的论述则更加成熟。他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提出了“景与情合,情以景生”的情景交融观点。并且是情景不离,情不离意,景不离意。他在《古诗评选》中提到情是虚无缥缈的,象源于瞬间的灵感。情生于景,景总含情,景是灵动变化的,情是真情,景里始终包含真情。景和情可以从细微之处生发,也可以从宏大的景象兴起,其出发点在于心与物达到契合,物我两忘,天人合一。他似乎把景当成了象,把情当成了意,这里主要用情与景来阐述意与象,他的阐述还是比较含蓄模糊。五四以来,这一概念得到了充分的解释。袁行霈先生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文中认为:“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3]陈植锷先生认为“意象是心灵化的意象。”从上面两种解释可以看出意象是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的统一。这两种定义可以综合用来解释秦川意象。本文所涉及的秦川意象属于地理意象,关于地理意象,张伟然在《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提出“地理意象就是地理客体的主观感知。”[4]地理客体在本文中就是秦川,主观感知就是诗人的情意。综上所述,秦川意象就是融入了诗人主观情意的地理物象,或是诗人借助秦川这一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是诗人心灵化的意象。
既然是心理意象,那么在诗歌表现中就会有虚实。秦川在唐诗中既有实指,又有虚指。而实指和虚指在唐诗中表达出的情绪也明显不同。李白《峨眉山月歌,送蜀僧宴入中京》有“长安大道横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这一句是实写,表达出诗人对帝京长安的富庶繁华、雄伟壮观的赞叹。而《乌夜啼》中“机中织锦秦川女”中的“秦川女”并不是实指某一个人,而是通过窦滔之妻苏氏思念丈夫的典故泛指女子对夫君的思念,是虚写,表达的情绪明显不同。不同的时代培养了不同的诗人。“盛唐因为向往事功,诗歌眼界广阔而气势博大。”[5]具有宏大的盛唐气象。中唐因其政治逐渐衰败,帝王安于享乐,求仙问道。诗歌乃是“退缩和萧瑟”[5],透露出苍劲萧瑟之音。晚唐诗人则远身避害,流连于自己的私人园地,关注日常狭小生活”,晚唐诗歌的境界就变得比较狭小了。这种境界的变化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给文人们带来的心理感受有关,这种心理感受导致同一诗歌意象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意蕴。要想弄清楚唐代不同时期诗人的心理感受,必须先对唐诗进行一个简单的划分。
三、唐诗的分期
唐诗的分期,宋人严羽最先进行论述,明人高棅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区分。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从诗歌兴衰交替发展的视角,把唐诗分为“初唐”、“盛唐”、“大历”、“元和”和“晚唐”五种体式,从诗歌体式进行划分,这种唐诗分期说界限非常明确。后来高棅的《唐诗品汇》将“四唐说”扩充成一个完美的体系,并且阐明了各个时期的演变情况。高棅将“初、盛、中、晚”的断限依据[6],下面又详细分为六种情况,并对各阶段的代表诗人和诗风进行了论说,论证逻辑严密,对唐诗的分期标准影响深远。五四以后,出现了“两唐说”,以安史之乱为界。为了能够恰当地分析唐代不同时期的诗人心理,从诗人心理来充分解释秦川意象在唐代不同时期所代表的帝京文化意蕴。以下将采用高棅的“四唐说”来对秦川意象所代表的帝京文化意蕴进行分析。
四、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时期秦川意象所代表的帝京文化意蕴
(一)初唐时期秦川所代表的帝京文化意蕴——宏大、雄伟的帝都描写
根据高棅在《唐诗品汇》中的划分,初唐应在贞观永徽到唐玄宗开元初(627—713)。初唐国家刚刚统一,国家急需开疆扩土来巩固政权,许多诗人投笔从戎,奔赴边关,满怀豪情壮志。初唐诗风整体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气。李世民本身就是帝王,他的诗歌就更能体现出宏大的气象。《帝京篇十首》“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2]从“雄”“壮”二字可以看出他笔下的秦川所代表的帝京是雄伟、壮丽的;“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宫殿重峦叠嶂,高耸入云,帝京给人一种旷远、博大、深邃的气象,也表现出对帝京繁华景象的赞美,开启了初唐诗人描写京都的传统。而关于帝京雄伟、宏大的描写,骆宾王和卢照邻也用他们的笔力秀出壮阔。“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帝京篇》)。在帝都这片土地上住着千门万户,城楼星罗棋布,“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八百里秦川延绵广袤,关塞众多,雄伟的汉宫伫立在我大唐,骆宾王笔下的帝京描写也是博大宏伟气象。还有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2]帝都长安大道条条相接,道上香车金玉随处可见,一派繁华景象。从以上的诗歌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宫阙巍峨,或者是秦川广阔,都是对帝京雄伟壮阔的生动描写。
(二)盛唐时期秦川所代表的帝京文化意蕴——对帝京热闹繁华气象的热情歌颂
据高棅的“四唐说”,盛唐主要指开元天宝间(713—756)。到了盛唐时期,盛世带给了人们更多的自信,使文人们胸襟更加开阔,唐诗出现宏大的盛唐气象。他们热情歌颂大唐帝国的强盛,并对帝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和对功名的追求。帝都因其地理优势、气候条件和经济优势常常成为贬谪文人和在外漂泊的游子或征夫的恋阙之都。他们把自己所处地方与秦川进行对比,突出了盛唐时关中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热闹繁华。李隆基的《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自从关路入秦川,争道何人不戏鞭。”在秦川大道上,人人都在玩耍,“公子途中妨蹴鞠,佳人马上废秋千。”王孙公子在踢球,女子在悠闲自得地荡秋千。一派和谐景象,寓目可见。王维的《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汤寓目之作》“汉主离宫接露台,秦川一半夕阳开。[2]王维这首诗以汉写唐,用“汉宫接露台”一词中显示的博大气象表明对大唐国力的赞美,他认为只有唐代才能有之前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相匹敌。“闻道甘泉能献赋,悬知独有子云才。”并且认为自己的才干并不比杨雄差,表现了诗人对功名的追求。只有处在一个开明的政治环境,诗人才会希望有所作为,也只有皇帝重用人才,那些未被任用的才敢满腹牢骚。还有另一首孟浩然的《越中送人归秦中》“试登秦岭望秦川,遥忆青门春可怜”。在秦岭上遥望秦川,那里山色秀丽,似乎是一座遥不可及的伊甸园。“仲月从此送君去,瓜时需及邵平田。”[2]这首诗既是对友人入京做官的一种祝福,也是孟浩然想积极进入帝京求取功名、有一番作为的美好心愿。诗人们积极出仕的乐观心态、对大唐政治经济文化的强烈自信、开阔的胸襟和视野,都能够在他们的诗歌里得到彰显,使他们的诗歌里呈现出一种宏大的盛唐气象。这种宏大的盛唐气象主要通过秦川意象表现出来。
(三)中唐时期秦川所代表的帝京文化意蕴——对大唐绝对权威的调侃
据高棅的“四唐说”中唐主要指大历贞元中(766—805)。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诗人们的心理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之前对帝京的向往、对大唐王朝的赞美、对人生理想抱负的强烈追求,变为对帝京的忧愤、失望、苦闷,对帝都集政治权力、经济、文化于一身的神圣崇拜转为戏谑嘲讽。李白生于盛唐时期,诗风作为盛唐诗歌气象的代表也是无疑的。但是他的一些诗歌也可以归入中唐。《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二有“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一进入成都就看到了堪与长安城阙九重相比的千门万户,蜀地的锦绣河山成为一绝,“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此此间无。”以帝京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似乎也寻觅不到。其三的“华阳新树号新丰,行入新都若旧宫”[2]将华阳与长安帝京做了对比,新丰的建筑繁华就像帝都长安一样。“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阳红。”柳树虽然没有秦川地区翠绿,但花红艳胜过秦川关中地区。从景物秀丽与经济繁华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诗人认为成都的气象并不比帝京差,在两地景物的壮观描绘中削弱了帝京的绝对权威,在看似赞美的笔调中寄予了深深的戏谑嘲讽。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见证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他的诗歌总是和民生疾苦息息相关。杜甫《暮归》“南渡桂水阙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鼙。”反映了漂泊在外的游子无家可归的状况。向北向南,行程都受到了阻隔,这也是诗人心理的阻隔,空有报国之志,却不受重用。也间接表明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并不开明,贤人并没有受到重用。除此之外,盛唐明净、雄壮的诗风也变得灰暗、凄凉,诗人的心态外向变得内敛。韦应物的《骊山行》“秦川八水长缭绕,汉氏五陵空崔巍。”[2]汉家五陵变得冷清,空寂的陵墓缭绕在迷离的秦川大地上。此时秦川所代表的帝京意象呈现出一种荒凉、阴冷的色调。钱起的《广德初銮驾后登高愁望二首》“愁看秦川色,惨惨云景晦。”从秦川意象中看到的是愁,是惨,是晦暗。抒写的帝京寄予了个人的苦闷与彷徨。从以上的诗歌分析可以看到中唐时期的帝京已失去了盛唐时期的政治绝对权威,对文人的吸引力也逐渐降低,文人们对帝京多了一层复杂的感情。由向往变得畏惧、叹息和嘲讽。
(四)晚唐时期秦川所代表的帝京文化意蕴——大唐王朝上空飘荡的一缕衰世之音
据高棅的”四唐说”晚唐主要指元和之际和开成以后。经过安史之乱,加之晚唐时期的甘露事变,文人心理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牛李党争对一些文人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文人们意识到政治的变幻莫测,他们忘记了去经世治国,在自己的园地避祸远身。这一时期的诗人,他们诗歌中的秦川意象反应的帝京已经不是先前的繁华、博大和雄伟。试看张祜的《散花楼》“锦江城外锦城头,回望秦川上轸忧,正值血魂来梦里,杜鹃声在散花楼。”[2]“锦江”、“秦川”都代表了帝京,从帝京望到的是忧愁,杜鹃声在散花楼中传响,听到的是哀伤,这时的帝京已经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荒凉、衰世之音。另外,杜牧的《池州送孟迟先辈》“明年忝谏官,绿树秦川阔。子提健笔来,势若夸父渴。……离别岂足更关意,衰老相随可奈何”。把当官的希望寄托在来年,既表现了希望友人官运亨通的良好愿望,也写出共同的不遇之感。李商隐由于涉入牛李党争,所以在政治上一直都不如意,诗歌比较隐晦地表达自己对朝廷的不满情绪。他笔下的秦川意象给人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李颀的《望秦川》“秦川朝望迥,日出正东峰。……客有归欤叹,凄其霜露浓。”诗人看到秦川上正冉冉升起的太阳,并没有欢快愉悦之情,而是感到全身充满寒意,凄凉归隐之思涌上心头。司空图的《战后南北史感遇十首》“乱后人间尽不平,秦川花木最伤情。”写出了战后帝京的萧瑟,也抒发了诗人的国家兴亡之感。张乔的《回鸾阁写望》“山压秦川重,河来虏塞深”读来感觉有几座山压在心底,帝京再也不像初盛唐时平坦开阔,而是重重受阻隔。刘兼《送二郎君归长安》“我儿辞去泪双流,蜀郡秦川两处愁。”先前繁华的帝京和蜀地现在都让人感到无比愁苦。总之,晚唐的帝京是文人笔下的荒凉之地,是诗人心中的伤感之地,是文人对大唐王朝失望而无奈的叹息。是文人宁愿逃避广阔的世界而独自隐藏在自己狭小世界而害怕提起的地方。这个地方已盛世不再,仅剩凄凉,在帝京的上空,黄骊不鸣,大雁已去,唯有高猿长叫,杜鹃啼血,处处回荡着一股衰世之音。
五、结语
不同的意象给人们呈现出不同的感觉,同一意象在不同时期也会给文人们带来不同的心理。秦川这一地理意象在唐诗所代表的帝京文化意蕴,随着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所呈现的帝京文化意蕴也有明显的不同。初唐是宏大、雄伟的帝都描写、盛唐是帝京繁华热闹的由衷赞美,中唐是大唐绝对权威的戏谑嘲讽、晚唐则弥漫着荒凉的衰世之音。通过“秦川”这一地理意象的分析,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出唐人心理的变化。由自信转为悠闲,最后到对尘世的逃避和失望。
【参考文献】
[1]段木干.中外地名大辞典[M].北京:人文出版社,1981.
[2]彭定求等编.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Z].中华活页文选,2007.2.
[4]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M].北京:中华书局,2014.10.
[5]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3.
[6]棅高 .唐诗品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