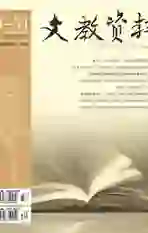从汲古阁书跋试论汲古阁刻书性质
2018-03-27赵鑫
赵鑫
摘 要: 坊刻又称“书林”,集中在金陵、苏州、福建、杭州、徽州、湖州、北京等地。苏州府常熟县的汲古阁,由毛晋创立,刊刻书籍数百种,流布海内外。坊刻和汲古阁的刻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特点十分鲜明,前者偏重在商业盈利的目的,后者偏重文化品位,文章以汲古阁书跋为切入点分析汲古阁刻书性质。
关键词: 毛晋 坊刻 家刻 书跋
一
毛晋作为明末清初重要的出版家和藏书家,师从钱谦益,自天启年间伊始在以后的40多年中出版了近600种书籍,他出版的书致力于使唐、宋、元作家的作品集,史书,儒家经典注疏及士人为读者对象的小说的宋元珍稀版本。
从出版史的角度来讲,把印刷品作为商品出售,以谋利为目的的是坊刻,否则便是家刻。但是这一条标准并不能把二者界分清楚,分歧比较大的是对毛晋汲古阁的看法。有人认为,毛晋自己斥资,他又是个学者,校对印刷的质量又很好,应该算作家刻;也有人认为,汲古阁编印发齐全,体制完整,人员众多,印刷量大,远销国外,是很完备的出版大企业,应该算是坊刻;也有人认为,毛晋刻书的前期,用“绿君亭”的名称,这时期出的书,应该算是家刻,后期用“汲古阁”的名称,应该算是坊刻。在出版史著作中,对汲古阁的归类尚未一致。
何忠林在《苏州大学学报》发表的《明代吴中著名藏书家出版家毛晋》一文中,将毛晉汲古阁归类为书坊,笔者觉得不太妥当。根据钱大成所编的毛晋年谱可知,毛晋刻书不是始于何忠林文中所提到的崇祯元年成立刻书作坊,而是在天启年间就已经刊刻颇具规模,后来由于屡试不中的原因,彻底放弃了仕途,在崇祯元年扩大了刊刻书籍的规模,并不是成立书坊售书。
在胡英发表的硕士论文《毛晋汲古阁刻书研究》中也认定毛晋为以刻书为业的坊刻家,该作根据叶德辉的观点“毛氏刻书,至今且尚遍天下,亦可见当时刊布之多,印行之广”,“光绪年间,旧书摊头插架皆是。”得出刊刻众多,流布寰宇,就只能是以出售书籍为生的坊刻家才有的成就。根据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汲古阁刻版存亡考》以及封树芬的研究基本推翻了上述的论述,叶氏所云光绪间“旧书摊头插架皆是”,“寻常之本”,当为书坊翻刻或仿刻毛本,由国图藏《汲古阁刻板存亡考》得知版本价格不同,初版即为汲古阁刊刻,大多数再版则为汲古阁衰落之后,书版散落在各处书坊翻刻而来。一些书贾为了射利,甚至伪造汲古阁本,影响了汲古阁本的声誉,使不明就里者混淆,并不是流布至清末的本子全部为汲古阁刊刻,所以胡英得出的结论并不存在立论的依据。
有人把坊刻和家刻混为一谈,归类于私人刻书,这样是不妥当的。家刻和坊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坊刻的书籍不仅在市场上流通,而且印刻周期短,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刻书机构,书坊别称书肆、书林、书堂、书棚、书铺等。进入明代书坊发展相当迅速,但坊刻正是因为从“射利”的角度出发,无论什么书,“闻价高,即为翻刻”,甚至有些书坊的老板为了节省成本,在翻刻部分书籍时,随意抽减书中文字,校勘不严,出现错字错篇,甚至于惊动官府,当然,这是说的士子必读的经书,因为经书是士人登官取禄的工具,错了会影响士人的前途,直接影响到政府基层选官的问题,所以官府会严查不待,如此重要的书籍都会刊刻出现大量的错误,普通的民俗读物必然会有更多的问题。
日常实用类图书,例如农书、医术、日用小丛书、年画、善书等;应试图书、童蒙读物;俗文学读物,如传奇、唱本、戏曲、民间通俗小说等,成为了书坊刊刻的三类最基本的图书。坊刻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关于小说的刊刻,特别是演绎史事的小说,这个在明代的书坊中特别明显,由于明代工商业的发达,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诞生,生活在都市的居民,不管是官吏还是地主,商贾,都需要饱食之余的娱乐,需要文化上的享受;而“市井细民”也同样在搜寻一种述愁解闷的手段,而小说技能满足前者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适合市井细民的兴趣,不需要深厚的文化背景就能理解内容。对于这样的书籍,官府的刻书机构又不屑一顾,于是就给书坊有了很好的生长空间,也给那些熟知史事又富有想象力的士人提供了除仕途之外的另一条求生之路,因而这类书自然地成为了书坊大量刊刻的主要类型。
家刻本顾名思义,某种意义上是在自己家里进行刊刻活动,属于私人印刻行为,区别于坊刻本因“射利”而刻和官刻本因事而刻。
家刻在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尽管部分家刻和书坊一样,经史子集无一不刻,所刻门类多,范围广,但是在家刻的整个发展体系中,“射利”并不是目的,藏书家自己刻书是家刻的主要构成部分。
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或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必须得有自己的藏书,这样他们必然倾心于书籍。各方求购图书、抄秘本珍籍、校旧刻本、编丛书、以及刻书,之后他们的藏书不断丰富,学者逐渐变为藏书家。随着藏书的增多,文化典籍的极大丰富,利用藏书进行研究的成果也不断增多,这样又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良性循环,为刻书进一步提供了素材。家刻的书籍更多是为了能够让学术成果能够在社会上广泛地流传,能够更好地保存当时的学术成果,增强学术的影响力。
毛晋汲古阁就是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最为规模的私家刻书典范。
二
根据出版印刻的规模来看,汲古阁的刻书算得上是坊刻,历史上终无定论,但从毛晋毛扆父子对于汲古阁的经营理念以及藏刻书书目来看,汲古阁的刻印更应该归于家刻,在毛晋的部分序跋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坊刻本的态度:
《癸辛杂识前集》跋云:“余向酷嗜是书,可与芥隐笔记南邨輟耕录并传,苦坊本舛繆,喜閔康侯缄正本见示,亟梓以公同好。”
《剑南诗稿》跋云:“近来坊刻寡陋不成帙,刘须溪本子亦十仅二三,甲子秋得翁子虡编辑剑南诗稿,又吴钱两先生严订夭天者,真名秘本也,亟梓行之,以公同好。”
《宋徽宗宫词》跋云:“五岳山人止选一百六十七首,坊刻或二百八十一首,或二百九十二首,或三百首有奇,多混入鄙俚赝作。”
《极玄集》跋云:“即留署中近刻,只挂空名于简端,虽然刘须溪点次鸿文典册,奚止什伯,悉为坊间冒滥,混入耳目,赝刻之行,日以长伪,何如原本之藏,适以存真也。”
《竹屋痴语》跋云:“宾王词,草堂集不多选,选入如玉蝴蝶,坊刻竟逸去,又如杏花天思佳客诸作,混入他人,先辈多拈出以慨时本之误。”
《介菴词》跋云:“又曾见琴趣外编六卷,章次颠倒,赝作颇多,不能悉举,至如席上赠人,清平乐,昔人称为集中之冠,反逸去可恨,坊本之乱真也。”
《花间集》跋云:“据陈氏云,花间集十卷,自温飞卿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今逸其二,已不可考,近来坊刻往往缪其姓氏,续其卷帙,大非赵弘基氏本来面目。”
《东观余论》跋云:“王氏书苑与诸书同梓,大是坊贾伎俩,伪谬脱简甚多,如周云□跋,原与周彝周洗及一柱爵各自著说,挑然四简,混为一段,款铭首尾,无从摸索,又刘原父跋弫仲医铭全文百五十余言,仅存二行半,不大失长睿本色耶。”
《西京杂记》跋云:“卷末记洪家有刘子骏书百卷,先公传之云云,按所谓先公者,歆之於向也,而馆阁书目以为洪父传之,非是,陈氏云,未必是洪作,晁氏云,江左人以为吴均依託为之,俱未可考,至若邇来坊刻作刘歆撰,抑可笑矣。”
《琴趣外篇》跋云:“昔年见吴门抄本,混入赵文宝诸词,亦名琴趣外篇,盖书贾射利,眩人耳目,最为可恨。”
从上述的态度可以明确地表现出毛晋对于当时坊刻本错误百出校刻粗糙的愤怒和失望,也并没有把自己所刻之书归为坊刻本。
三
小说,在《辞海》中的定义是:“文学的一大样式。一般通过情节描写,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和行动,塑造人物性格。现代西方”新小说派“则主张小说可不要情节或淡化情节。叙事角度灵活多样。”
在书跋中能够看到毛晋对于小说的态度:
在《却扫编》跋曰:“野史中能不涉荒唐谲诞新奇饰说。而简次朝宁之钜典法制。一代史馆之所未尝搜罗者。虽曰小說。实有攸关。班孟坚诸君叙列于百家之末。”
在《玉堂杂记》跋曰:“公集中有奉诏亲征龙飞闲居陵诸录,託言未刊为多,伤时事不欲令人见耳。茲纪亦在隐显之间,然多载朝制及君臣礼遇同官一心之事,堪补全史之遗,非若小说家琐亵炫目也,至其始末,已详具本序,及丁苏两公跋语云。”
在《辍耕录》跋曰:“惟辍耕录三十卷,上自庙廊实录,下逮村里肤言诗话小说,种种错见,其谱靖节贞白世系,尤简韵可喜。”
在《冷斋夜话》跋曰:“浮屠之裔,求其籍籍於述作之林,殆不多见矣,习小说家言者尤鲜,宋僧自文莹而外,觉范洪公,亦喜弄此事,洪公自是宗门杰士,盍不守面壁祖风,往往著书不惮,且有目为文字禪者,何哉。”
在《癸辛杂识前集》跋曰:“唐宋末诸家小说,多称某,盖祖五柳先生但书甲子之意,以自寓其悲愤云......”
在《琅嬛记》跋曰:“前人著书,多取名於本册中,如席夫所辑三卷,首载张茂先至琅嬛福地历观其书,因名琅嬛记,或以小说置之,然岂可与虞初置杨羡书生云云同视耶,其间如琴为暗香,棋为鬼阵,舞有百华,歌有双曲之类,奇名奇事,不可悉举。”
在《剧谈录》跋曰:“唐人最拈弄小说,虽金紫大老趋蹡殿陛之余,使命一方,鞅掌簿书之暇,尽日有所记录,积久成编,李文饶刘宾客尤兢兢耳,时至咸通以迨乾宁,其间韵事,足新耳目,况三辅曲江士庶,都冶景物,为之点次,事事俱堪捃拾也。”
在《诚斋杂记》跋曰:“予初从书目见诚斋杂记,误谓伊洛渊源之类,贮之宋儒道学簏中,未曾寓目,偶披伊席夫琅嬛记,援引凤凰台唱和,及吴淑姬张子冶合簪二则,注云,出诚斋杂记,因复觅而阅之,凡二卷,所记百二十余条,皆小碎杂事,新异可喜,绝无腐气,颇似太平广记,又不堕於淫亵迂诞,真小说家不多见者,急付梓人,以公同嗜,据周达夫序云,林载夫所著书并诗文凡十二种,恨未窥其全耳。”
综上所述,毛晋对于“小说”有两种态度,一种“小说”即是叙事杂记之意;另一种“小说”则是明清市井小说,他的态度是“堕於淫亵迂诞”。作为一个正统的知识分子,毛晋对于坊刻的明清通俗小说是排斥的,从汲古阁刊刻的众多与史料相关的书籍,以及《十七史》和《十三经》为代表的经史典籍,就可以看出毛晋以翻刻宋元版的珍善本作为刊刻目标,目的在于保存更多完本的古籍。
毛晋出版事业最值得注意的是出书的结构。在我国古代经史子集的典籍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十三经、二十一史、历代名家诗文集以及佛道经藏。这些内容,毛晋几乎都出版齐全了。他所出的书,从其总体来说,可以说是一部“四部要典”。当时,无论是实力雄厚的官刻,还是经营过数百年的书坊,都没有毛晋这样的成就。
四
毛晋自小接受良好的私塾教育,早习举子业,为明诸生,但在天启、崇祯年间“屡试南闱,不得志”,于是他放弃仕途,一心“为古人之学读书治生,之外无他事事矣”①。最终成为明末清初最杰出的藏书家和出版家之一,也是“弃儒入贾”的典型范例。
明代以朱注“四书”取士,早年从事举业的毛晋自然也熟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所谓的“弃儒入贾”,只是毛晋放弃了科举考试,不再在仕途上求发展,转而在商业世界求发展。但是毛晋没有忘却儒家的价值和精神训练,钱谦益赞赏他“壮从予游,益深知学问之指……盖世之好学者,有矣。其于内、外二典,世出世间之法,兼营并力,如饥渴之求饮食,殆未有如子晋者也”②。这些儒家价值和修养成为了他汲古阁出版事业成功的动力和精神基础。
毛晋为何在出版事业上如此注重道德修养呢?他从藏刻书伊始就有着身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对于商业经营活动看得很严肃,甚至很神圣,他对于刻书,让圣贤言流布寰宇的目的,具有高度的自觉,肯定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追求仕途的“士”是一样的。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良贾何负闳儒”。如沈垚所说,明清以来“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也就是说,从家族亲戚、州县,一切社会公共事业,道德责任以前由“士大夫”承担着的,落在了“商贾”身上。据《毛子晋年谱稿》“天启四年甲子(1624)”条记载,常熟由于特大水灾的侵害,很多居民住宅、堤坝、桥梁毁于一旦,毛晋带领乡邻“采石于金山,求木于胥口,糜金镪二百八十两有奇”,使得“一十八里,无揭、厉之患”等等。更说之,出版印刻书籍,涵盖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百家小说等各类书,刊行《六十种曲》、《津逮秘书》、《十七史》、《十三经》等丛书,也是为文化事业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利以义制”,即追求商业利润而不违背道德原则,事实上韩邦奇认为“士”如果抱着做官的目的去读圣贤书,其实也就是求“利”;相反,“商”如果逐利而不违背道德,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则恰恰保存了“义”。毛晋甚至于为了刊刻《十三经》《十七史》,不惜举世代积攒的财力,“亟弃负郭田三百亩以充之”、“犹幸数年以往,村居稍宁,扶病引雏,收其放失,补其遗忘,一十七部连床架屋,仍复旧观,然囗之全经,其费倍蓰,奚止十年之田而不偿也”,这种为了文化传承的出版精神和坊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汲古阁作为毛晋刻书的场所,出发点就在于刊刻经史,在《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中毛晋指出了他刻书的缘由“虽穷通有命,庶不失为醇儒”,就是以刻书来达成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追求,不能仕而优于仕。
综合考虑,无论是从刊刻的书籍种类以及对“小说”这种坊刻必不可少的刊印类型的主观排斥,还是从汲古阁书跋推断出毛晋对于坊刻本粗制滥造校刻不精的痛心疾首,加之毛晋自己斥资刻书,自己“卷帙从衡,丹黄纷杂,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迄今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矻矻不休者。”区别于坊刻射利为主,笔者认为毛晋汲古阁应该是明末清初最大的私家刻书机构,而非书坊。
注释:
①张海鹏,王世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251.
②张宗芝等.《以介编》:为昆湖毛隐居六十乞言小传(陈瑚).
③钱谦益.《牧斋全集·有学集·卷三十一》:毛子晋墓志铭,1140.
参考文献:
[1]毛晋.汲古阁书跋[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M].三联书店,2012.
[3]叶德辉.书林清话[M].中华书局,1957.
[4]胡英.毛晋汲古阁刻书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
[5]曹之.毛晋身世考略[J].图书与情报,2001.
[6]钱大成.毛子晋年谱稿[J].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第一卷第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