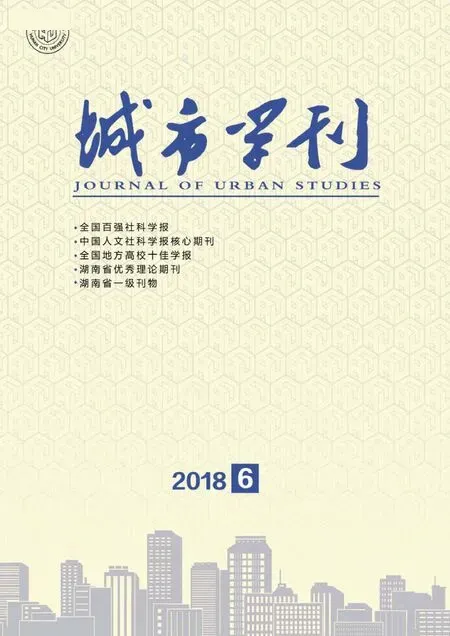政府治理协同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探索
2018-03-25傅晓华孙名浩傅泽鼎
傅晓华,孙名浩,傅泽鼎
政府治理协同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探索
傅晓华1 a, c,孙名浩1 b, c,傅泽鼎2
(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a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b 政法学院;c 生态文化与环境政策研究所,长沙 410004;2. 河海大学 水文水资源学院,南京 210000)
新型城镇化被寄予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活力的厚望。基于“最小作用量原理”,从政府治理协同理论分析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内涵:以民为本的发展之路、幸福快乐的人民之路、民族创新的特色之路。政府治理协同是破解新型城镇化难题的突破口,必须与资本自由流通协同,与整体长远利益协同,走向公共管理范式,从而解决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土地、户籍、财税、资金等问题,真正体现公共服务的本质内涵。
政府治理协同;新型城镇化;最小作用量原理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我们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到2020年底将完成建设的中期快速成长阶段并进入建设的后期成熟阶段。[1]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国务院多次提出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新型城镇化被寄予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活力的重任。2017年,中国新型城镇化率名义上超过58%,专家预测2020年将达63%,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其背后潜藏的种种矛盾、问题也日益凸显并不断激化,特别是存在大量重复建设与资源不节约现象。[2]中国整个改革进程是政府主导下推进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也不例外。政府治理协同就是破解新型城镇化各种矛盾的突破口和良方,是新型城镇化道路能否成功的核心问题。
一、从政府治理协同到新型城镇化道路
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采取积极的新型城镇化策略以减少农村人口,农业现代化才有希望,新“三农”问题才能有效解决。城市竞争力的形成不是单一因素的贡献,是由各种因素互动形成的综合竞争优势。[3]这也意味着新型城镇的结构优化源自管理文化的协同共振,遵循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凸显着这座城市(区域)对区域价值观及其相互关系的共识和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城镇化是“一城一品”人文城市,而非“千城一面”房产城市。
自洋务运动以来,我们曾学习西方走过城镇化道路,但“西方现代化和城镇化”竟是如此的充满了现代性悖论。从人类历史的终极命运和地球生态伦理的不断恶化角度来看,“西方道路”基因中的物质主义不仅是直接造成资源耗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罪魁祸首,同时也是间接导致国家关系紧张、霸权主义盛行和精神家园缺失的主导诱因。[4]处在工业社会初期的当代中国,虽然也曾出现过大跃进式的盲目“赶超”意识和改革初期的“GDP崇拜”,这些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如今,作为国家层面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经济升级版总体布局,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政策。“新型城镇化”核心价值——从哲学层面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从本体论上充分认识到社会公正是城市活力创造的源泉,实际上也是政府管理协同共振必然诉求。[5]人的新型城镇化(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根本,集中体现在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必定要以政府管理协同来推进。
(一)协同论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依据
协同论是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Haken)首次提出,以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学科,从非平衡有序结构系统探讨各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时的相似性。该理论已越来越多地解释和预言各种系统的非平衡有序现象。新型城镇化是社会协同发展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建城”,本质上是政府治理协同共振的“综合文化”城,体现出人类文明系统的非平衡有序性。从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和东部地区改革,到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道路,都是政府治理协同的必然。新型城镇化道路必然要遵循城镇(都市)内部各子系统与要素的协同共振,使城镇呈现出稳定有序结构的规定性。不同的政府治理理念支撑不同治理特征,政府治理协同才有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协调与和谐。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新”体现在治理文化的创新,遵循“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论;“型”体现在传统管理结构转变为新治理结构,即转型,主张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6]
爱因斯坦的“最小作用量原理”认为,宇宙诸法之下存在一个和谐世界,凡是符合“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物质及其思维都是和谐的。[7]这意味着支撑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政府治理系统中,就是以最少的能量取得最佳的效益,获得最大的效率,而不在于新型城镇化有多么轰轰烈烈,城市有多么大的规模。正如苏共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结构优化符合“最小作用量原理”,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圆俄罗斯的民族梦,发展到200万党员时,击败了德国法西斯。但拥有2 000万党员时,内部结构单一、集权严重,远离“最小作用量原理”,直接导致苏联解体。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历史源远流长,城乡居民格外分明,市民和村民就是中国人身份的象征,符合“最小作用量原理”,封建社会的特色城镇源远流长。中国管理文化就传统价值而言,原本是协同的,儒释道三位一体,有其独特的管理方式。[8]但强加了皇权,导致社会文化有涨落但外部环境因素不协同,因为皇权结构使儒学变儒教,排斥民主和外来文化,独尊“老大”,不符合“最小作用量原理”,管理文化必然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在相对封闭的封建社会是可以一定时期内稳定存在,但在现代开放系统必然打破平衡,近代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从此,政府管理文化成为一个开放系统,符合“最小作用量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管理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营造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文化底蕴,政府治理协同才初现端倪。
(二)新型城镇化道路有着丰富的内涵
“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7]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础是由简单概念和基本关系所组成的,具有简单统一性,符合“最小作用量原理”。封建社会管理机构的兵部、户部、刑部、吏部等比现在少得多的机构设置,但简单而协同,就是“最小作用量原理”体现,所以一定程度上比现在众多管理机构的设置都科学有效。只是后来多被皇权统治、天下一统而远离“最小作用量原理”,最终走向崩溃。新型城镇化的价值体系应遵循“最小作用量”追求城镇特色的“真、善、美”,走向超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当代中国治理文化。新型城镇化道路最关键的不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建设”,而是以民为本的尊严生活方式,在“最小作用量原理”基础上的民族创新,这才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灵魂。
其一,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之路。《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着力推动平衡发展,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加快成长……实施重点城市群规划,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是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人的主体在于民,以人为本的中心在“以民为本”,也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出发点和归宿。新型城镇化就是人民的物质、文化、政治生活水平都要不断持续提高。不能像某些地方,以新型城镇化为幌子,大搞房地产,造“鬼城”,过度将视角放在城镇化的“量”上而忽视了建设新型城镇化的“质”与“量”的同步推进。
其二,新型城镇化是幸福快乐的人民之路。给予民众发展和享受幸福的权利,是新型城镇化的价值追求。[9]新型城镇化道路不是少数人的热情,更不是开发商和某些官员勾结的纽带,是人民摆脱“普遍的奴隶制”的幸福快乐之路。公正平等,人人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快乐的权利。[10]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以人民幸福快乐为主旨,属于人民和世界,是基于我国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有效解决而设计。
其三,新型城镇化是民族创新的特色之路。创新驱动发展,没有民族创造力的城市是一座“死城”,新型城镇化必然拉动消费需求,消费层级相应提高,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会带来产业转型。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特别是支持与鼓励农民创业创新,拓宽增收渠道,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依托地区优势发挥产业引领带头作用,促进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之路,否则又是西方城市的仿造,缺少中国特色生命力而终结。
二、政府治理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功能
新型城镇化道路需要经济基础的硬支撑,更需要政府治理的软支撑,充分发挥两者的协同功能。“我们现在好像在大山脚下从不同的两边挖一条隧道,这个大山至今把不同学科分开,尤其是把‘软’科学和‘硬’科学分隔开。”[11]新型城镇化就正如这条隧道,经济、技术、土地等是硬系统,政府治理协同、城市文化与价值理念等是软系统。“硬”和“软”系统的多要素、差异性、多样性的协同放大、协同演化和协同导向。
第一,协同放大。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治理本质上是追求各要素协同优化组合,协同放大,促使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土地、户籍、公共服务、财税、经济发展等城镇要素为非平衡的开放系统,其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时时产生共鸣与涨落。这些要素结构的差异的非平衡性、非线性作用,导致政府治理协同放大,如有效的土地政策就能协调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可持续财政政策有利于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从而促使有序结构迅速形成,进而达成新型城镇化功能放大。再如新型城镇化对“三农”问题的缓解,只有大量农民转移进入城市,中国的“三农”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这就是新型城镇化功能协同放大,解决就不仅仅是村民变市民的问题。
第二,协同演化。新型城镇化道路实质就是现代化与政府治理的一个协同演化过程,是“最大”与“最小”尺度起源的交叉点,新型城镇化与政府治理协同相互对应,相互促进。新型城镇化的“最大”包括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最小”是个人幸福生活、接受好的公共服务、发展成果共享等,这些功能也是基层政府的主要功能。[12]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7年的58.5%,[13]体现出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农民的碰撞协同,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的交汇。这种协同演化正如同一行业的竞争者汇集在一条街上,分散的居民点汇集到一起形成集市,既是自然的力量,又是包含人为的因素。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共生、合作、协调地竞争,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也是新型城镇与政府治理协同演化的本质。
第三,协同导向。开放性是产生有序结构的必要条件。城镇是开放系统,有自发性特点,但其壮大和提升,离不开政府治理导向,离不开政策资源的倾力支持和社会良好的文化氛围。新型城镇化道路和政府治理协同导向才能产生良好的有序性。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中国新型城镇化造成了严重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政府导向问题,包括污染治理、协同管理等问题。政府治理协同是克服新型城镇化无序结构的关键,新型城镇化道路又是提升政府管理协同能力、促使政府功能与定位转型的重要途径,两者协同导向。[14]
三、从政府治理协同破解新型城镇化难题
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元素,必须建立在中国国情和发展进程基础上。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主要难题是土地、户籍、财税、资金的高效使用问题,解决这些硬件难题,必须首先从政府治理协同的软件入手。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种种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加上美国一手导演的贸易摩擦等国际因素,导致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困境加重,这是政府层面不可回避的问题。政府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与社会系统(新型城镇化是社会系统演化的一方面)协同进化。同时,新型城镇化道路不可能是一个地域的产物,也不是一个地域能实现的,在新型城镇化道路中,政府治理协同需要世界眼光,关注新型城镇化的资本自由流通、整体长远利益,走向现代管理范式。
(一)政府治理与资本自由流通协同
“推动世界前行的不只是经济资本,还有文化资本。”[15]经济资本的活力在于自由流通,自由是“最小作用量”的前提。没有资本的自由,就谈不上新型城镇化“最小作用量”,那么整个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就是清一色“造城”运动,不可能有地方特色。没有特色就没有生命力,更不要说文化传承、生态友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没有现成的模式,已经被西方验证和推广的模式在中国不一定能够行得通。政府治理首先要尊重城镇化规律和资本自由流通,然后才是依据地域特色“摸着石头过河”。
土地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资本。土地流转市场化就是尊重资本自由流通规律,这必须是新型城镇化道路中顶层设计要突破的核心问题,必须摈弃过度依赖地方土地财政的价值观念,这是房地产调控的核心问题,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城镇化,更多的体现为“土地新型城镇化”过程,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低征高卖”加剧了城乡利益矛盾,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城镇化模式,造成了千篇一律的城镇“脸谱化”,城市的人文地理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例如长沙从规模人口和经济体量等,确实发展了,但是“长沙味”没有了,也不是历史记忆中的长沙了。同时,政府管理破除“部门利益化”,转向“部门协同化”,才能有土地、金融、文化等资本自由流通。
人口新型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新型城镇化本质上是具备公共产品属性,人人都应该平等享有。人口新型城镇化意味着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化,政府管理协同才能有序推进农民工由“区位转换—身份转换—心理层面转换”[16]的完全市民化,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新型城镇化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城镇特别是大都市只要劳动力商品为其服务,排斥劳动者分享他们的“城市福利”。例如进城务工者子女受教育问题,长沙等大城市出台政策是“租售同权”,但事实上子女入学时有房和租房是区别对待的,政府管理如果不能协同解决城市接纳劳动者变市民的问题,就体现不出新型城镇化的“新”和“型”。尽管有小一部分的农民工在其所奉献的城市购买了住房,实际上也难以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这种由户籍制度造成的人的权利的不同导致的所享受权益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公正的主要根源,也是政府管理协调要面临的严峻考验。
在财税问题上,促进“非土地信用”的财税体制改革,解决地方政府资金困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十九大精神定调“房子是用来住的”属性,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公共服务及公共基础设施的均等化,配合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以人口城镇化为目标导向,相关联的公共设施、产业布局也须做出调整,公共财政的投入不可避免,不能再依赖“土地财政”。科学合理的财税体制机制的突破口应从政府治理的公平性出发,从房产税、遗产税等财产税和土地流转的交易税费征收,同时辅以公共财政法案下的地方债券融资和其他创新融资模式,不能以土地财政拉升的房价让普通百姓承担新型城镇化的成本。
(二)政府治理与整体长远利益协同
4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与现代化道路是伴随着改革进行的。近10多年来,新型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突破口”一直在寻找“主要矛盾”,但一直是“单项突破”,忽视了政府治理体系的协同,走出旧体制却无法建立协同的新体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府治理缺失长远利益考虑,好大喜功。如城乡一体的物价改革,导致全国性的“抢购风”,冒险闯关失败;清理城乡企业“三角债”,前清后欠到越清越多;大张旗鼓“砸三铁”越砸越铁,直到现在弱势群体“奋斗”的通道被堵死,寒门学子苦读成才却因无法“拼爹”而被边缘化;提高农民收入,却“差距越拉越大”,“新三农”问题使农民翻身难上加难;国企上市,却“圈钱”乱象丛生;各行各业“专项打击”和整顿,从左右摇摆到“一阵风”……诸如此类的城乡一体化,都是缺失整体和长远意识而导致顾此失彼无法达成政府治理协同。新城城镇化也是如此,考虑“融城”“阔城”而导致百姓望而却步的空城。
近10年时间,大约3亿农民工进城“造房”式新型城镇化,堪称“中国城市化”的大跃进。因户籍制度成为目前难以逾越的鸿沟及高房价等原因,“造城的人”不被城市接纳,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目前难以破解和既得利益群体不愿触及的难题。中国社科院对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和四川等5个省市农民工的调查发现,64%的调查对象认为社会不公平。[17]同时,农民工二代与其父辈在城市务工的目标不一,父辈是为了“进钱返乡”抚幼赡老。大量农民工二代不再选择返乡,其目标是“扎根城市”,如果城市再不收留他们,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新型城镇化也可能因此出现更多社会问题。政府管理如果仍然“抓主要矛盾”,一味追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单项突破”“专项发展”方法,而忽视整体和长远利益,就会使新型城镇化道路陷入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被动境地。新型城镇化道路再不能“以GDP为中心”,否则必然导致“以项目为中心”,而远离新型城镇化的真实内涵:以人为本、幸福生活、民族创新。经济的长远发展特别是经济要素与其他要素的协调发展对于稳定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至关重要。忽视“以人为本、幸福生活、民族创新”的目标及价值导向、忽视整体长远利益的政府管理与新型城镇化道路,必然会落入“三高两低”为特征“任务新型城镇化”“任期新型城镇化”“形象城镇工程”的窠臼。
关注长远的生态利益,这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之义。城镇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基础设施系统,包括城市的“肾”“肺”“皮”“口”“脉络”等。[18]新型城镇化是要保护城镇的这些生态器官,而不是一味的改变和重造,否则就是千篇一律的造城运动。乡村的生态河流、池塘、湿地等是城镇的“肾”,乡村的自然植被、林业、农业等绿色是城镇的“肺”,乡村地表、风情建筑和民族建筑以及有特色的道路等工程是城镇的“皮”,乡村的自然排放口、缓冲区和处置设施是城镇的“口”,乡村的山形水系、风水、生态廊道及交通动脉是城镇的“脉络”……这些生态要素从新型城镇化的长远利益进行有机整合,才是“一城一品”真实新型城镇化。毫无疑问,新型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热岛效应、水华效应、灰霾效应等“多彩效应”,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因此,须尽快完善“污染环境责任”立法,将环境责任上升到刑法高度。[19]在建设美丽公园同时,乡村景观也在随之消失,民族风情住宅和传统住宅被高楼大厦和红砖白瓦取代。一些村寨在新型城镇化中一味与城市国际接轨,反而丧失了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这些最吸引人的地方。这些都是违背生态规律的造城化。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城镇化建设的全过程的战略部署。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性是评判城市生态化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标准尺度。[20]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要注重环境要素发展和维护的顺自然特性,尊重生态发展规律,保护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实现宜居宜业新型城镇化风貌、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最终达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设定。
(三)传统范式向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
新型城镇化道路不能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而歪曲政府公共管理的本质内涵。过去几十年的土地财政,必然促使不断扩大土地储备规模,导致了城市区域范围逐渐扩大,从而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最为粗放的空间扩展道路。更为糟糕的是,土地出让是将土地未来50-70年的使用权一次性转让,实际上相当于本届政府向企业一次性收取若干年的地租。[21]在未来的时间,地方政府要负责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但以后的历届政府却不可能在已卖土地上再产生现金流,那这些钱从何而来?以后的历届政府怎么办?没人愿意回答,甚至没人愿意去想。
就传统政府管理层面来说,每一块土地的出让都是透支未来,寅吃卯粮,政府这种传统范式的管理模式,已经给新型城镇化埋下严重后患,房地产泡沫就是传统管理范式的一个例证而已。房地产开发企业一次性交付多年的地租,对企业来说是预支未来利润,属于负债经营,就购房者来说,通过银行贷款来支付房价,更是典型的负债投资和消费。政府以土地出让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同样是以透支企业和个人的未来收益为前提的。同时,由于土地财政主要用于城市建设,中国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扩大。这种粗放扩张性新型城镇化道路,只是城市建筑物的快速构筑,更没有相关城市社会秩序、精神秩序的建设,民众的生活幸福感并没有随之同步,反而普遍陷入焦虑状态。
新型城镇化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推进新型城镇化,就必须要有总体的改革设计,要向公共管理范式转化。政府管理各个部门协同,不仅仅关注管理层面的物质增长,更关注公共层面的精神、幸福等领域的价值。由政府传统管理范式留下看病难、上学难、出行难等“城市病”,必然要由公共管理来破解。
此外,需在政府治理协同下整体看待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特色小镇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三者在以人为本的核心发展观念上具备共性,在发展上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要将新型城镇化放在动态化的城乡互动关系中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多维度来重新审视城镇化建设,[22]城乡一体化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动力机制——社会力量;[23]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报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前提,两者必须协同推进;2016年《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及2017年发布的《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对发展特色小镇、重视特色小镇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作用及两者协同发展予以极大关注。绿色小镇建设符合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规划,两者在发展目标上存在极大耦合协调性。[24]
总之,新型城镇化是一个与政府治理协同演化的历史过程,新型城镇化进程有其自然属性,其演化方向不取决于政府治理。但是,新型城镇化的速率与质量、新型城镇化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政府治理协同的程度。必须清醒的认识和反思,我们所面对的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处于系统联系和系统运动的世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高度领略和全面认识新型城镇化、把握新型城镇化进程;[25]必须有政府治理协同,才得以顺利推进。
[1] 方创琳.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镇化与城市群取得的重要进展与展望[J]. 经济地理, 2018, 38(9): 1-9.
[2] 寒林飞, 郭建民, 柳振勇. 城市化道路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对我国当前城市化发展阶段的认识[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 21(3): 1-7.
[3] 周玉波. 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宏观分析[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3(3): 81-84.
[4] 傅晓华. 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D]. 长沙: 湖南农业大学, 2014.
[5] 刘芳, 吴欢伟. 从管理哲学看我国管理学的反思与接轨[J]. 中国行政管理, 2011, 305(11): 111-116.
[6] 谢翠蓉, 王婷婷. 和谐农村的伦理学探析[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15(5): 41-43.
[7]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27.
[8] 王云萍. 公共行政伦理:普遍价值与中国特色[J]. 中国行政管理, 2011, 318(12): 103-108.
[9] 郑彦妮, 蒋涤非. 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实现路径[M].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27(2): 68-72.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35.
[11] 黑格尔. 美学: 第1卷[M]. 朱光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979.
[12] 于秀琴, 张文政, 仝震. 基层政府服务力评估模式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 2012, 321(3): 44-47.
[13] 宋冬林, 姚常成. 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城镇化与城市群的道路选择[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6(5): 45-52.
[14] 徐传谌, 鲁雁. 从工业社会到生态社会: 政府的功能与定位[J]. 中国行政管理, 2011, 307(1): 53-57.
[15] 兰培. 文化产业在与资本共舞中铿锵前行[N]. 中国文化报, 2012-02-17(05).
[16] 何华玲.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政府角色、职能位移与市场“嵌入”[J]. 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5, 17(4): 5-12.
[17] 张立伟. 户籍改革应成为新型城镇化的破题处[N].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3-01-10(04).
[18] 傅晓华, 赵运林. 可持续发展视域下的城市生态探微[J]. 城市发展研究, 2008, 181(1): 1-4.
[19] 王树义, 刘海鸥.“环境污染责任”的立法特点及配套机制之完善[J].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5(3): 60-63.
[20] 赵运林, 傅晓华. 从可持续发展价值观透析城市生态化[J].城市问题, 2008(2): 2-6.
[21] 杨建科. 新常态战略下的新型城镇化:选择动力与规避陷阱[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7): 15-20.
[22] 李学灵. 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J].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6, 25(3): 37-38.
[23] 汪菁. 特色小镇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关系——以浙江湖州长兴县新能源小镇为例[J]. 城市学刊, 2017, 38(5): 73-77.
[24] 刘宏长. 土地出让金应用于城镇配套设施建设[J]. 中国经济周刊, 2013, 23(15): 5.
[25] 包心鉴. 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0(6): 8-13.
Explor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1 a, c,1 b, c,2
(1. a. College of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04, China; 2. College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He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0, China)
The new urbanization has been placed on the task of further releasing China’s economic vitalit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minimum action”,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 people-oriented development road, the happy and happy people’s road, and the characteristic road of national innovation. The collabor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is a breakthrough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new urbanization. It must cooperate with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 it must cooperate with the overall long-term interests, and move toward the public management paradigm, thus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l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fiscal taxes, and funds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road, reflecting the essence of public service.
governm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new urbanization; principle of minimum action
2018-06-12
湖南省重大委托项目(13WTA01)
傅晓华(1972-),男,湖南桂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生态哲学和环境规划与管理、农村环境治理和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研究;孙名浩(1993-),男,山东阳谷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研究;傅泽鼎(1998-),男,湖南桂阳人,主要从事水文与水资源、水利工程研究
F 291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8.06.003
2096-059X(2018)06–0012–06
(责任编校:彭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