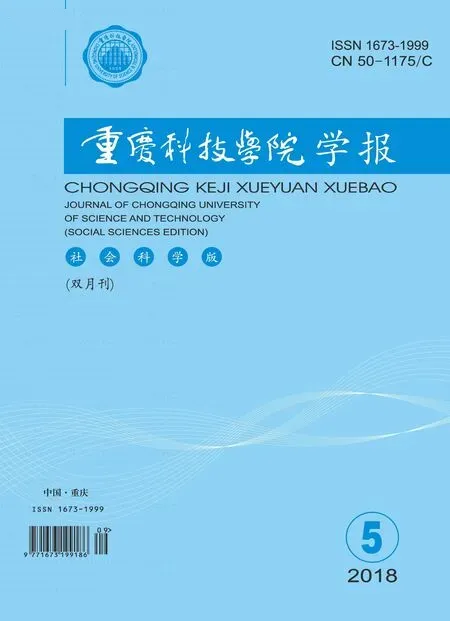欧·亨利与卡夫卡作品中的“小人物”对比研究
2018-03-22张秀娟张红雪
张秀娟,张红雪
欧·亨利(1862—1910)是美国现当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也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短篇小说艺术大师。他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对健康人性的深层关注和对现代人生的深切反思,展示与剖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矛盾和“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无独有偶,20世纪文学史上著名的天才、现代主义大师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在他的诸多小说中亦刻画了一系列小人物众生相,详细描述了他们羸弱的身体、自卑的心理、虫豸般的生存状态,以及其在一个异化世界里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荒诞和毁灭的。
虽然欧·亨利和卡夫卡的故事迥异,但他们不约而同地书写了生活中小人物努力奋斗、追求理想、争取自由与解放的卓绝艰难的抗争历程,呈现了个体生命的精彩瞬间和最终归宿,并探索和揭示了文学艺术世界的广度和深度。
一、欧·亨利与卡夫卡其人其作
欧·亨利一生历尽艰辛坎坷,他的人生经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大变革中,美国社会现实的缩影。早在童年时期,欧·亨利就失去了母亲,先后被寄宿在祖母和姑妈家,造成了他内向的性格。他成了一个“怕羞的、古怪的、文雅的和谦逊的人。总是用缄默来掩饰自己。 ”[1]536为生活所迫,他曾寄人篱下,也曾远离家乡,还被判过监禁。他先后做过学徒、牧羊人、银行出纳、土地局办事员、新闻记者、药剂师等等。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生活让欧·亨利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经历过西部牧场和东部都市不一样的风景,真切体会到各种社会矛盾和人性纠葛。这些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广泛的素材,也滋养了他洞察世态人情的睿智与深刻。他凭着自然的天赋、独特的个性、开朗的胸襟“却一生落在老鼠夹中,蘸着自己的心血,艰苦执着地进行创作。”[2]2就在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长期的穷困加上酗酒让他的身体急剧恶化,于1910年不幸逝世,年仅48岁。欧·亨利在短暂的一生里共创作了300多篇短篇小说,从某种角度来看,他的小说创作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的功能,把他从一种孤独、悲凉的日常生活中救赎出来,特别是从不断增长的精神困境中救赎出来。
与欧·亨利的贫病孤苦、颠沛流离相反,弗朗兹·卡夫卡是一个成功商人的儿子,一生没有离开过他居住的城市,也未曾离开过父母的庇护。这个法学博士一边做着稳定的保险公司的职员,一边执着于写作。然而,生活稳定、性情温和的卡夫卡,虽然受到同事的爱戴和朋友的尊敬却从来无法与身边人坦诚相见,他的四周好象镶上了一道玻璃墙。他微笑着“把世界朝自己打开,却把他自己封闭起来,不让这个世界了解他。”[3]25一个坚硬固执又粗暴刚愎的父亲,一个隐忍敏感、“唯夫命是从”的母亲剥夺了卡夫卡的童年快乐,再加之时代的阴影,疾病的折磨,婚恋的受挫,造就了他悲观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时时刻刻提防着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威胁,度过了相对安逸却又胆战心惊的41年的人生。卡夫卡通过创作向世人展现了生命个体全身心体验到的地狱般的黑暗世界,并从独特视角捕捉现代西方人巨大的心理危机和精神创伤。他书写小人物最细微、别致的心态和情绪,彰显荒诞、绝望的生存基调。卡夫卡软弱、顺从的性格只能在与外部世界隔离的文学空间里寻找到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他在烦躁喧嚣的人生里用孤独的心灵、自我的语言,诚实低调的写作,为异化中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深具生产力的另类生活形态。
二、小说主题对比研究
只有经历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正由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垄断寡头为了金钱、利益,不断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革新技术,实现工业化、产业化生产。人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无可避免的沦为挣钱的工具和金钱的奴隶。金钱助长了人类丑陋的贪欲,诱发了恶性竞争,也拉大了彼此间的心理距离。人们普遍感到孤独、迷茫、空虚与不安。
欧·亨利与卡夫卡,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名字。然而,在不同的文化语境和生存环境中,他们都致力于书写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与人生价值。欧·亨利与卡夫卡都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小说中的故事也大都发生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他们书写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聚焦社会底层中的小人物命运,讴歌信仰和赞美真、善、美并揭露和批判违反人性的假、丑、恶。在为了赚取金钱而坑蒙拐骗样样齐全、贪婪舞弊泛滥成灾的社会里,“小人物”首当其冲是指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的劳苦大众。他们已为生存而物化为机器,失去了身体和思维独立的自由。这是一群处在恶劣生存状态中,满含辛酸与劳苦的弱势阶层。然而,在文学作品中,他们的“小人物”通常有着双重指涉,首先从物质生活层面来看,他们经济贫困、社会地位低下;其次从精神空间、心理状态来看,他们性情柔弱、顺从,意志薄弱、缺乏自我。
欧·亨利小说的永恒魅力是描述了艰难的生活中“小人物”间相濡以沫、真挚温暖的感情和乐于奉献、一心向善的美好人性。《麦琪的礼物》中,德拉与拉姆为给深爱的人送一份礼物,各自牺牲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但毫无疑问,彼此的关爱与用心则是送给对方的最好礼物。这看似弄巧成拙的付出与牺牲却折射出小人物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本质。更高尚的是《爱的牺牲》中,乔和德雅丽为了成全对方,放弃了自身挚爱的艺术追求。《警察与赞美诗》里的流浪汉苏比一直保持着生命的尊严,他受教堂歌声的感化,决定痛改前非、自食其力。《重新做人》中的小偷吉米为了爱情毫不犹豫地放弃一切,改过自新;为了救人,他又冒着被抓的危险挺身而出。这些或可敬、或可爱、或可怜的人,虽挣扎在社会最底层,却保持了人性中爱的本能和正直善良的品性,让人们在充斥着欺骗与背叛的社会中仍愿意相信友情、爱情和终会到来的幸福。同样,卡夫卡最经典的“小人物”——《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在面对沉重的家庭责任和债务负担时挺身而出,忍受老板的戾气和同事的冷漠,只为改善家人的生活和实现妹妹的梦想。即便不幸异化为“甲虫”,也处处为家人考虑,怀着温柔的爱意直至死亡。《审判》中的约瑟夫·K穷尽一生,只为寻找一场审判,寻找正义和秩序。《乡村医生》中的医生冒着明知被骗的风险,也要深夜去出诊。《饥饿艺术家》中那个潦倒的艺术家即便没有观众和掌声,也要把饥饿作为至高无上的艺术呈献给大家。欧·亨利对人性和情感的描写与阐述饱含着对小人物的同情和爱意,对恶势力的憎恨及人性弱点的贬斥。卡夫卡描写小人物命运处境的同时,也揭开了荒诞世界里强大的外部法则。总而言之,两位大师在书写小人物“弱”的生存方式时,不仅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和人类严重的精神危机,体现出对社会现实的深层审视和对现代人生的深切反思。他们都将笔触落于对健康美好人性的关注和渴望,这种强烈的人性意识与社会批判精神使其作品具有极高的价值。
如果说欧·亨利侧重于描写生活的物质层面带给“小人物”的悲,那么,卡夫卡在他的艺术世界中,则不断述说“小人物”心灵与精神上的痛。卡夫卡的小人物形象更为光怪离奇,无论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变成了甲虫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还是无法确证自我身份而焦虑不安的约瑟夫·K,或是一个日夜停留在秋千上的杂技演员,亦或是那只惶惶不可终日的小动物……他们严重的精神危机是卡夫卡一切小人物生存的缩影:天生的敏感、惶恐、胆怯,经常无端的顾虑重重、焦虑不安,绝对的孤独无助,他们是卡夫卡个人内心世界的投影和客观化。
三、创作风格对比研究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以通俗易懂、短小精悍而著称。因为他选取真实的生活画面,白描出一个个社会底层人物。这些人物有学生、家庭主妇、无业游民、警察、小偷、酒鬼、赌徒等等。所以,出于生活真实与艺术共鸣,欧·亨利在描述时运用了通俗朴素的语言。对其小说的语言进行量化分析,从词汇、字系和句法可以发现:单词的拼写都较短,代词和名词的使用频率要远远大于其他词汇。因此,他的小说最明显的文体特征是文本基本由短句或句子片段构成,且被动语态很少。从语义层面来看,他的小说语篇大多采用第三人称行文,在开头和结尾以某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视角描述或评论。此外,美国文学“幽默”的传统在欧·亨利小说中体现出更为深沉的底蕴。欧·亨利独特的幽默表现在对语言的娴熟运用上。他的用词极具匠心,大量的讹音、谐音、俚语、双关及典故让小说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暗示、隐喻、意象和自由联想。苦难境遇中的“幽默”既折射出小人物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和昂扬不屈的意志信念,也透视出辛酸、嘲讽、悲凉的情绪。各种语言形式的自然运转使得行文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和思想深度。如《警察与赞美诗》中,苏比强烈的入狱希望是因为多年来,热情好客的布莱克威尔岛监狱一直是苏比冬天的寓所;《最后一片藤叶》中贫穷老画家的毕生杰作是墙上那片永远不会凋落的藤叶;还有《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旅馆、年轻人、木樨花香、发霉的家具等等都是象征的意象。正是作品字面含义上的弦外之音体现出欧·亨利的过人的智慧与阅历。
欧·亨利“独特的创作风格”除语言外,还体现在立意构思上的奇特新颖。小说整体的谋篇布局通常有两种模式,一是采用叙事者就是主人公的叙事策略,主人公引领着读者一步步往情节的发展迈步而去,如《警察与赞美诗》中,苏比步入监狱的过程;一是采用双线叙事结构,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并行不悖、同时发展,最后交融出强烈的艺术效果,如《最后一片藤叶》。小说按照人物的主体性思绪和行为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顺序即叙事的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的有机统一呈现出必然的结果,衍生出最为精彩的“欧·亨利式的结尾”。这一标志性的结尾是在“和缓的叙事节奏,机智的叙事语言,优美的圆形结构”[4]92的共同铺成下实现的,是一种“必然的悲剧”;逆转的结局虽说“意料之外”,却在叙事铺垫过程的“情理之中”。如《麦琪的礼物》里的悲喜交加,《警察与赞美诗》中的事与愿违,《幽默家自白》的善意与嘲讽……
欧·亨利的小说之所以精彩,还源于语音、词汇、句法上大量修辞手法的运用。语音手法的修辞格一般有押头韵、谐音、半谐音和拟声等;词汇手法的修辞格通常表现在拟人、比喻、移就、讽刺、夸张和典故的运用上;句法手法的修辞格主要体现在排比句、反问句、松散句、圆周句等句式上。修辞一方面实现了増强语言力量、表现作者情感和更为精确、形象传达思想的功能;另一方面极大地加强了作品独特的美感和艺术性。
欧·亨利描绘现实生活里各种小人物的遭遇,卡夫卡却很少关注生活的表面现象,他的一生是一个弱势的天才寻求拯救的心路历程。因此,他的小说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写作,自传色彩非常浓厚,小说人物大都是自身影像的显现。被现实一切障碍摧毁的不幸人生构成了卡夫卡悖谬化的人格模式与思维方式。写作既是他逃避现实的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他成全灵魂的唯一出路。卡夫卡的全部作品都是书写“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他的文学成就首先在于对小说形式技巧的探索实践,即卡夫卡式风格。如果把欧·亨利的创作风格概括为一个“实”字,那么,卡夫卡则是一个“玄”字,“不确定性”是其作品的根本特征之一。卡夫卡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悖谬化风格体现在叙事的语言、情节和修辞上。
语言的不确定性源于日常世俗生活与内心情感体验的背离,即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分裂。欧·亨利用日常语言描绘日常生活,而卡夫卡对这种语言产生了惶惑。在他看来,日常交流的词汇难以描述出超越生活经验的东西,“对于超越物质世界的一切问题,语言仅能略示梗概,但几无半分正确可言。”[5]9卡夫卡的小人物在摆脱日常生活的羁绊,追问自身本真存在的那个时刻是难以靠语言来实现表达意图的。如《变形记》里的甲虫从不停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到彻底的沉默;《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约瑟芬的歌唱只是简单的吹口哨。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布鲁姆·费尔德一成不变的生活竟然被两个莫名其妙的跳动的赛璐洛小球彻底打乱了。所以,若用语言来构筑这一切似是而非、虚无无序,卡夫卡只能宣称“我所写的并不是我所要说的,我所说的不同于我所想的,我所想的又有别于我应该想的。”[6]于是,他在叙事时采用的词汇大多是不确定性的,如“看来”“似乎”“好像”“也许”“其实”“显然”等等。“也许父母和代表正坐在桌子旁边窃窃私语,或许他们正靠在门内偷听”[7]357不确定性词汇的大量使用,加强并突出了小说情节的不确定。此外,小说多重点描叙人物现时当下的生存状态,人物与过去割裂了,也缺失了未来,时间的连续性被打破了。这就导致卡夫卡的小说常常没有开头,没有结尾,而是直奔某个逆转的瞬间。如“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卡夫卡不注重情节结构,因为他的关注点不是客观世界的万象,而是心灵最深处的焦虑,这些突发事件情节虽荒诞怪异,完全背离正常的逻辑秩序,却解释了小人物生存的各种可能性。《地洞》明明很安全,可那只小动物整日惶恐不安;《饥饿艺术家》把表演饥饿作为一生从事的艺术,虚弱不堪的身体能否安置孜孜不倦的灵魂?卡夫卡专注描写“灵魂疾病”的叙述方式和表现手法打破了人们对常规的认知,他的不合情理、荒谬怪诞绝非随心所欲的任性,而是摆脱了现实主义小说对时间、地点、结构、因果的限制和约束,把现实生活中的荒诞与异化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揭开,让人们在悖谬化叙事中发现隐蔽在现实背后的真相。卡夫卡式的可怕方式从情理现象看是反常的、怪诞的;从社会现象看却又是正常的、可能的。
卡夫卡最本质的创作原则是用写实主义的笔法,让梦幻和现实交混在一起,把世界表现为一种超验的、抽象的寓言。从修辞角度分析,他在作品中设置了大量“意象”,尤其是用抽象的意象以象征、隐喻的表现手法刻画真实与虚无的内在联系。“城堡”“甲虫”“法”等这些具体实物的存在不仅具备明确的意义,也表述着更为复杂、丰富的诠释可能,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此外,卡夫卡一方面用逼真的生活细节构建魔幻、荒谬的世界;另一方面,又善用夸张、怪诞、变形的想象来演绎真实,实践从表象到本真的超越。梦幻与现实的萦绕交错使卡夫卡的艺术世界既抽离了现实世界的维度,又与其丝丝入扣、水乳交融。
四、结语
文学创作与人生体验紧密相连,写作是欧·亨利与卡夫卡共同的宿命。他们都是生活中不幸的人,欧·亨利通过外在世界的自然呈现书写小人物的不幸命运和美好人性,以此宣扬人性向善的终极关怀;而卡夫卡则把眼光投向自身,展现小人物在世界中的各种存在之图,并且借助写作来重构自我、追寻个体的生命之光。当然,欧·亨利的艺术世界是在日常世界的基础上描绘小人物的生存百态;卡夫卡的艺术世界则远远超出日常世俗世界的广度和深度,他专研人物真实的心灵世界,直达生命存在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