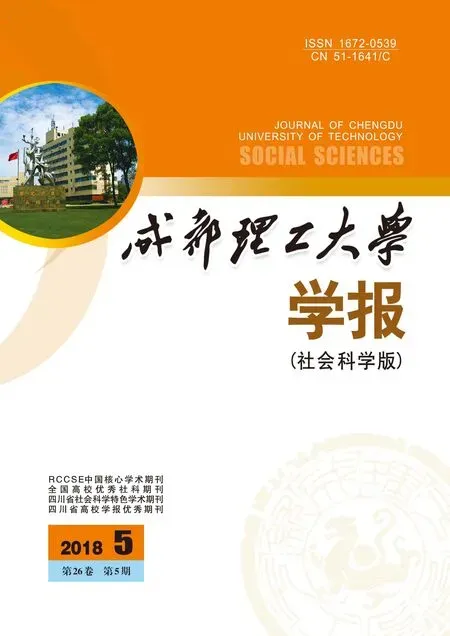孙犁晚年心态中的物我相宜
2018-03-20何洁
何 洁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 350007)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孙犁再次提笔进行文学创作。此时的孙犁已六十三岁,步入了晚年,此时的他已经是告别“老孙犁”逐渐变成“新孙犁”,呈现出有别于以往的复杂情思,他不仅对物有关注,而且在咏物的背后透露出身世之感。这样的感慨与情思正是孙犁在经历了病痛、批判、漂泊、故人离去,甚至“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动和人生变化后产生的。时间的洗涤、人事的变迁直接成就了孙犁独特的晚年心态和人生体验。当晚年的孙犁对旧物和失而复得之物的关注有了自己的目光,其中便寄寓了他晚年的心态与情感。学术界对孙犁晚年的心态多有研究,但目前尚无通过晚年与时代的关系来看晚年孙犁对物的独特心理。通过对咏物散文的研究,以物为媒介来看孙犁对物的态度和审美取向,利于我们探究该心态影响下孙犁是如何感受物,同时探究物对“新孙犁”的特殊意义。
一、聚散与残破的伤感:相似命运的体认
晚年的孙犁于散文中多次提到自己被抄去、抄去后发还的书籍。这些书籍多丢失于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时期,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除此之外,晚年的孙犁在行动上也有别于早年,对物多了份关心。其中包括对书籍的破损有着如对肌体的呵护、对旧物有着吝啬的留存、对残破的陶瓷有着道不明的伤感……在晚年孙犁的眼里,物都不是冷冰冰、可以忽视的存在。相反,在其散文中,多次写到物的经历,表现对失物和残物的关怀。这与孙犁对物的命运体认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孙犁认为物有聚散的命运。1974年,孙犁被抄去的书陆续地得以发还。此年4月,他于《西游记》的包书皮上谈到他对外物命运的认识以及应有的态度:“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1]369。孙犁认为,好比多变的天道,阴晴不定,好比当自己途经山川或是偶遇流水,途中也有可能遇见没有缘故的风或雨。孙犁基于对外界环境中偶然性遭遇的体察,便将此体验加于外物,认为物有自身聚散无定的命运,没有根由,难以掌控,由此进一步加重了孙犁晚年对物的命运观。这样便不难理解,晚年的孙犁在看到不同的牲口于不同时期的身价变化会如此唏嘘,以“万物兴衰相承,显晦有时”[2]34等语句感叹物的无定命运。在孙犁眼中,物的价值有起有伏,与人的关联也有聚有散,这些也加重了孙犁对事物恒定存在产生怀疑,甚至产生幻灭感。晚年的孙犁对物有命运的体察,除了增加他对物之散的幻灭感之外,也使得他有对物之聚存有珍惜,主要体现在对失而复得之物的庆幸与珍视。“抄去的书籍还能够发还,正如人能从这场灾难中活过来,原是我意想不到的。”[2]204对于书籍的发还,在孙犁看来是基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灾难”而言的。于“邪恶的极致”[3]241中,看到书籍能在灾难中重新发还,这不仅增加了孙犁对书籍的信心,也一定程度地弱化了“文化大革命”对孙犁的强度。所以对孙犁而言,书籍的发还犹如“活”过来一般,这正是因为物有流散的命运,因而他透露出物能再聚的惊喜。所以,晚年的孙犁在《一本小书的发现》中,对旧作重现产生重视,甚至庆幸于年老的自己还能再见到青年时期的著作。更为甚者,他对于发还的书籍还产生“久别重逢的感情”[2]207。
其次,对孙犁而言,物的命运如同人的命运。在孙犁的眼里,物的命运难以捉摸,而与时代政治不无关联。在《书的梦》中,作者细数了北平流浪与书结缘、土地改革时期上缴书籍以及游击式阅读的经历。孙犁一生爱书,却在不同的时期,与书的缘分深浅不一,孙犁不同的人生时期与书有着不同的相处方式,看书的经历的同时也看到自己的经历,所以对书之梦也是人之经历的反映。“书之遇,亦如人之遇”[1]383。孙犁将书籍的遭遇以人的遭遇进行看待,在孙犁的眼中,书的遭遇如人的遭遇一样是时代变迁的产物。除此之外,物的命运不仅反映人的命运,也反映了时代的不同。对时代命运的不同体认影响孙犁对物之命运有不同态度。孙犁的书籍一损失于抗战时期,二损失于土地改革时期,但这些都是在国家和民族发展时期难以避免的结果。正是救亡大于启蒙,在民族和国家宏大的愿景中,孙犁虽然可惜于书籍的失去但并不会为此感到伤感。相反,孙犁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抗战时期,漂泊辗转于战火之中,身边仍带着个别书籍抽空阅读。经历土地改革的孙犁,仍然坚持阅读和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仍有当藏书家的愿望。但“文化大革命”时期,孙犁对书籍被抄的事实却有了不同的态度,这是因为孙犁从物的命运中体察人和时代的命运。一方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孙犁更关注时代的危机,突出了对命运无常性的体认,以人的遭遇理解物的遭遇,将二者并举。孙犁将书籍的遭遇和人的遭遇相联系,甚至认为两者关系密不可分。例如1974年12月孙犁在《海上述林》的书衣上写道:“世事之变化无常,于书亦然乎?”[1]377“‘世事’即人事也,人事则包括个人的遭际与命运。”[4]103此处,孙犁将人事的命运与书的命运相对应,在关切于书籍命运的同时,也是在关注个人遭际的无常变化。另一方面,孙犁也通过对物之遭遇的冷漠而突显时代中人所遭遇的无奈。当孙犁在外开会时,红卫兵将孙犁家中的所有书橱加上封条。当他回到家中,他的弟弟因为知道孙犁平时对书籍的喜爱,故而特别安慰一番。孙犁对此的反应:“其实,我当时已顾不上这些东西。因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尚不知何如也。”[1]378-379孙犁虽爱书,但并非书痴,在孙犁看来,国家民族的命运已经在书籍的命运中反映,他也更为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当下的时代和环境已经使得孙犁无可奈何,他对于书籍的得失自然也无法挂在心头。
最后,对物有残破的伤感。晚年的孙犁在散文中不仅道出在不同的时代,物有无定的命运,也致力描绘物在经历风尘后的残破磨损。如上所言,在《装书小记》中,孙犁不仅写出自己保留下书籍的庆幸,更写出对残书包裹新装的投入。此番举动正是因为他不仅看到物有聚散的结果,也想到其中的过程和物可能遭受到的破坏。“书籍在外播迁日久,不只蒙受了风尘,而且因为搬来搬去,大部分也损伤了肌体”[3]13。晚年孙犁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归还之书有着不竭的歌咏,并且为发还中残存的书籍包裹新装。其中正是因为“纪念它们经历一番风雨之后,面貌一新”[3]13的安慰。因此,晚年的孙犁感同身受于物的破损,不愿直面,在散文写作中关注于对物进行一番修补。同样,面对破损的陶瓷人,孙犁也无法规避对破损物的感伤。他不愿有残破之物放于眼前,如修补残书一般,“我找了些胶水,对着阳光,很仔细地把它的断肢修复……”[5]288破损之物无法使孙犁无动于衷,因为晚年的孙犁将自己的残破意识投注于物中。“我的一生,残破印象太多了,残破意识太浓了”[5]288,残破意识使得感伤成为咏物散文中物情构建的一种基调,使其情透露出可奈何的悲观,甚至对事物往昔的美好进行追问。例如,孙犁在《我的绿色书》中谈到童年、“文化大革命”、“干校”时期,看到绿色植物遭砍伐后感慨:“我不知道,我过去走过的山坡、山道,现在的情景如何,恐怕也有很大变化吧!泉水还是那样清吗?果子还是那样甜吗?花儿还是那样红吗?”[5]297植物破坏是一种残破,此番的感叹正是孙犁残破意识一番流露,以植物的改变影射出时代中的破坏和心绪的无奈。
二、时代与人际的失落:远离外界的心灵庇护
在《答吴泰昌问》中,孙犁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有人对他进行批判,许多都有隔靴搔痒之嫌,仅有一次让他觉得正中下怀。批判者批评孙犁“这么多年,你生活上,花鸟虫鱼;作品里面,风花雪月”[6]10。孙犁从生活中对物的关注为边缘化的方式,有别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无论是沉浸于书,还是对自然的关注都是孙犁远离环境的手段。由此,物与孙犁形成性格与心理的适宜,晚年的咏物散文正是孙犁以物为庇护的产物。
其一,重建物的意义,排遣时代积郁。1994年,孙犁以“黄昏之恋”[5]435来形容自己对书的喜爱,表达自身与书的关系。由此可见,孙犁对书的喜爱程度超过了一般人对书的喜爱,有着自己独特的强烈感情。而这正是孙犁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到了晚年才对书的喜爱达成了有别以往的高度,这与孙犁在彼时的经历不无关联,与书对孙犁的功用、孙犁对书的心理依赖等因素有关。早在1962年,孙犁便在《石子》中直言:“人在寂寞无聊之时,爱上或迷上了什么,那种劲头,也是难以常情理喻的。”[3]178“文化大革命”时期,孙犁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产生否定,无所适从。此时的孙犁想到自杀,所幸未成功,可见那时的孙犁心理相当恐慌并需要精神建设。除了书籍被抄走的经历会带给孙犁对外物命运飘散的伤感之外,此时的孙犁也对那些“收藏多年、遭劫遣返、残破有损的书包皮”[7]6投以同样的感伤。包书皮的过程中,书无疑成为了孙犁建设心理的一个手段。1974年,孙犁于《潜研堂文集》的书衣上谈到“能安身心,其唯书乎”[1]367,以强烈情感感叹出书对与孙犁自身的功用和意义。孙犁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执着于修补书籍,尤其晚年继续藏书、修补书籍并在书衣上写下文思。这样“安心”的行为明显与“四人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相背道而驰,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毁坏书籍、摧毁文化,孙犁的举动无疑是在拯救文化。孙犁对书籍的收藏和保护是出于书籍给予他的审美价值。因此,书籍对于他的意义在于不为外在的标准所束缚,继而收集书籍、修补书籍也成为他寄托自我价值观、构建精神世界的途径。以自我的审美标准来对待书籍,这既是孙犁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待书籍、文化标准的反驳,也成为他构建自身审美世界的努力。即便对于时代主流而言孙犁显得边缘化,但藏书、修补书籍等行为的意义使他在晚年注意到物对于自身的价值。因此,对书籍的修补,对古籍的收藏和阅读成为他排遣和治愈内心压抑的方式。孙犁在书中注入的意义与时代相契合,以他对人生的体验在书籍之中看出新的意义。
其二,失落人际关系的慰藉。孙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搬入天津时,他便感受到“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3]369,并且为这样的变化而烦恼。正是对周围环境无法融入的异质性使得他晚年时在咏物散文中竭力地怀念童年与农村。除此之外,孙犁更痛感于身边之人不断离去后的孤独,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人和人的关系异化,而这些都是特殊时期的产物。由于不愿意面对这样丑恶的年代,孙犁在晚年回忆时多次表露出对当时存在的出卖或是污蔑朋友行迹的不满。于是,孙犁便在物中投注自己的价值认同,慰藉自己对人与人关系的失落。在《改稿举例》中,孙犁谈到他将《谈爱书》投稿《人民日报》时,有一节文字被删除。被删除的文字谈到“人的爱好,各有不同”[2]219,孙犁将自己对书的爱好对举于“‘抱粗腿’爱好的人”[2]219。这类人不仅对造反派表示五体投地的崇敬,甚至陷害那些他们曾经“抱过粗腿”但如今失去势力的人。但编辑在当时认为孙犁写《谈爱书》是谈及对书的喜爱,与他人见风使舵无关,便将此删除。孙犁晚年回忆,却认为编辑忽略了写作者的寓意。此番寓意正是孙犁并不认同于那些人物的“爱好”,即见利忘义之行,也不满于当时人与人关系的冷漠。因此,孙犁以书之爱寄托了他对外界失落人际关系的反拨,以对物的关注寄托他对人生的体悟与慰藉。
一方面,当孙犁面对他人的离去和变化,其将物当友,感叹于物陪伴自己时不变的物性。例如,他感叹火炉几十年的温暖,长久不变。《火炉》中,对火炉未停放暖的连续赞叹和感激中剔除了火炉其他的物性,仿佛只留下了永恒放暖的特征,使得火炉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火炉,更是一个忠于陪伴的朋友。同样,孙犁也感激书籍与之相伴一生并充盈着其人生的不同阶段。甚至是居住天津时,孙犁虽然由于院落环境嘈杂感到不适应,但是他也因邻居的更新换代而对院落产生怀旧之情。除此之外,孙犁对书籍也以“故旧”[8]296相称。当他与字画、印章等物进行告别时,却依旧恋恋不舍,念旧的产生正是出自于它们几十年的陪伴。可见,晚年的孙犁是有意识地将物当成朋友,由此,他在咏物散文中多次写到物时都感激外物的陪伴。
另一方面,在感叹“文化大革命”时期损坏友谊的不耻行径,晚年的孙犁亦怀物思友,寻找真正的友情。在此,他一方面在现实中表现出对友情的淡漠,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真挚友情的执着。当写物回忆他人时,孙犁十分注重对于他人赠物背后的赠予者的记挂。《木棍儿》中,除了怀念青春,讽刺棍棒之名,同时也有对所赠者——时达的回忆。甚至孙犁写作中回忆未尽,在附记中谈及二人互赠瓷器、画作、浮石等物,并且“我”与时达都十分珍惜,表面写赠物,实际是孙犁晚年借物怀友。物在孙犁的眼里是人和人之间情谊的联系。所以在《蚕桑之事》中,孙犁看到桑叶,便满怀情感地想起儿时一起养蚕伙伴的情谊,即便在他日相见,有话难投机的失落,但晚年的孙犁以体验观物,便在久远的时间中,以经历的不同给予了体谅。并且,当谈起扁豆时,其更谈起当初一同吃扁豆的老友。此友是孙犁“白发之时,能记忆不忘”[5]299的真交。孙犁以物思友,一则规避于孙犁于现实中对人际的失落,因“后之所谓同志,多有相违者矣”[5]299,二则追怀美好的回忆与人性。
三、老年意识中的生死叩问
无论是以命运观体验外物,或是将外物作为庇护所,这些都是孙犁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到了晚年所拥有的时代心绪。从停笔到再创作的数年之中,孙犁不仅跨越到“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也从中年迈入了老年。上述部分主要是谈论了迈入了老年的孙犁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的特有心态,此处主要探讨,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已是老者的孙犁在心态上的特征,以及该心态对他观物、体物的影响。
晚年的孙犁有明显的认老意识,即“新孙犁”对老年时的自我有平静的接受。孙犁在《澹定集·后记》中说自己第一本《晚华集》,人们认为取名“晚华”显得太老,于是就取名“秀露”。但在其《老荒集》《曲终集》取名都有明显的老年意识。《澹定集·后记》中就对其“认老”表述:“人老不服老,硬说七十如何,八十又如何,以及老骥伏杨,焕发青春之类,说者固然壮一时之气,听者当场也为之欢欣鼓舞,仔细想想,究竟不是滋味。因为毕竟老了。”[6]188所以晚年的文章便是老者的文章。虽然晚年孙犁文章中竭力地表明应将自己当作一名老人,但却总会在回忆中形成感伤。《鸡缸》中,谈到此物命运:“未委泥沙,已成古董。茫茫一生,与瓷器同”[6]196,表明鸡缸还未埋入泥土,却以成为古董。孙犁联想到自己,还未在有所作为却已老年,感叹鸡缸的身世,也在感叹自己的一生。由此,他以年老的状态体会外物的存在,敏感地体会着外物之旧。除此之外,孙犁对于物有着老者的依赖。在《我的绿色书》中,以植物的破坏联想环境是否改变的无奈与无力时候,作者写道:“见不到了,也不想再去打游击了。闭门读书吧。这些植物书,特别是其中各种植物图,的确给老年人,增添无限安静的感觉。”[5]297这里的“老年人”,是孙犁在融入外界感到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产生的身份体认;这里的书,便成为他关门的寄托,也是他弥补外界破坏的方式。这其中的躲避心态,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老年意识使孙犁对外物产生生死的思考。比如在《我的经部书》中讲到,“因为我特别爱好书,书就成了生死与共之物。”[5]119晚年的孙犁,一方面不得不思考生死问题,在“生死与共”中体会自身与外物跨越时间的感情,并更深刻地体会其中的沧桑感。另一方面,也正是在物中感知生死,使得他在晚年的咏物散文中呈现悼亡之致。晚年生命力逐渐衰落的孙犁,对于死亡的最深感知之处或许在于周围人的不断逝去。《木棍儿》中,谈到我与时达互赠礼物的友情。除此之外,孙犁更是借木棍儿谈及对这位亡友的哀悼:“时达几年前逝世了,讣告来得晚,我连个花圈,也没来得及送到他灵前。现在手里,摆弄着他十年前送我的一根棍子。”[8]294孙犁以物思友,在晚年意识的驱使下,自然会对亡友有怀念,并且反思自己对于他人的联系。摆弄手中亡友所赠之棍,除了怀念与感怀,更有斯人已逝的无奈和自己无所可为的愧疚。晚年的孤独会促使孙犁于往事中回顾曾经丰富的人际关系,但回忆时却发现,亲人故去,老友不在,反而更增加了自身在现实中的孤寂。
晚年孙犁的生死之思,除了在物中悼念逝去的亡友之外,也表现为对大限将至的恐惧与无奈。到了20世纪90年代,孙犁于“文化大革命”后复出文坛,无奈于文坛的不良现象,也因文事的纠缠而产生内心的虚无和消极之感。“孙犁再次感到生命的负重,即其所谓的生命的‘累赘感’。”[9]234在1993年所作的《题文集珍藏本》中,孙犁谈到这样一件事:一位女编辑抱着一个纸盒子,里面是《孙犁文集》。之后孙犁看着这一部书产生兴奋之感,显然是因为他怀想起自己曾经走过的青春岁月,并认为这是有血有泪的一部书。但之后他也产生了幻灭感,甚至觉得女编辑手中抱的不是他的著作,而是他的“骨灰盒”[5]515。晚年孙犁的生死体会,促进了他对外物的感情转向了悲观的一面,同时对外物原本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转变与矛盾。“如果说人在中青年因了实践的凭借而和世界建立了许多联系,向客体伸出了许多触角的话,到了晚年却因实践能力的丧失而萎缩了那些触角只剩下了孤独的主体与客体遥遥相望。”[10]74早年的孙犁在拯救民族的战火中感到激情澎湃,关注时代的新气象,例如在天灯中看到了四妮的新转变,歌颂新人。与此不同,晚年孙犁体会生死之思时会淡化了早年的激情,而感受到死亡意识下的孤独。在《谈爱书》中,“从今年起,我对书的感情渐渐淡漠……这恐怕和年岁有关,是大限将临的一种征兆,也很少买书了”[2]207。晚年的孙犁一方面在回忆自己与书经历世事,所以对书有着超乎寻常的喜爱。但同时,步入老年不断走向年迈的孙犁,也遭受着大限将至的恐惧与无奈,甚至对现实产生无力感,转变了对外物的态度,由喜爱到冷漠。总之,孙犁在对外物的淡漠是来源于他对年老的接受,对死亡的恐惧和内心的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