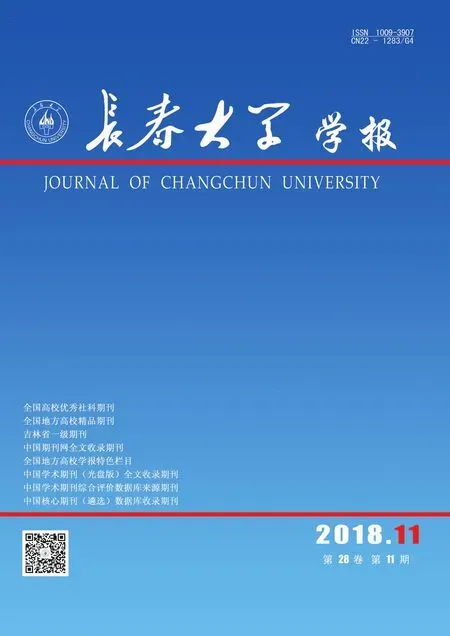中美两国青少年成长追寻比较研究
——以沈从文与福克纳作品为例
2018-03-20朱玲玲
朱玲玲,石 平
(蚌埠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1 问题的提出
沈从文(1902-1988)、福克纳(1897-1962)作为中美两国的文学大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人类的生存状态作了详细而深刻的描绘。民国时期、南北战争前后,分别是中国和美国社会两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通过对人物栩栩如生的刻画,沈从文和福克纳在作品中呈现了历史转型期的人类的生存状态。沈从文认为应“通过作品来表达对人,以及人在世界上的最终目标的深入理解”[1]287;福克纳“是人道主义者……深切关怀着在历史变革时期人的命运和人性的完整”[2]37。正因为对人类命运的密切关注,他们着重刻画了一系列的青少年人物形象,并借着他们来展望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未来。
2 文本提取与实证分析
论文提取沈从文与福克纳作品中的青少年人物以及他们的成长追寻作为研究素材,并在综合分析素材的基础上,分别从个人追寻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追寻与自然和谐共生、对美好人性的追寻、对美好爱情的追寻、对自我的追寻等五个方面分析沈从文与福克纳作品中的青少年成长追寻的异同。
2.1 个人追寻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
人是社会的人,他们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连。民国时期的中国积贫积弱,外部列强环饲,内部军阀混战、政治斗争严酷,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沈从文作品中的有志青年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勇敢地担当自己作为国家和民族一员的责任,解救受苦难、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在保卫国家、促进民族发展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追寻与发展。
《动静》里,年青军官冷静地看待战争,踏实地承担一个军人的责任与义务 ——勇敢作战,保家卫国;《懦夫》里,大学生凌介尊和李伯鱼作为无名义勇军上南方前线打仗;《黑夜》里的部队通讯员罗易、平平乘黑夜穿越封锁线送文件。这些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保家卫国的战争,在枪林弹雨中实现了个人成长。
《大小阮》中,富有的地主子弟小阮信仰共产主义,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唐山矿工大罢工等革命工作,后被捕死在监狱;《若墨医生》里,若墨医生夫妇为了人类的幸福,牺牲了年轻的生命,独留下不满半周岁的女儿;《菜园》里,玉少琛夫妇在清党运动中被杀害,玉家菜园也被有势力的绅士强行征借;《除夕》里,万里与雷卿等一些革命青年在除夕夜里暗杀了城中5个警察,雷卿不幸牺牲。这些有志青年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充满希望,即便当时政治斗争严酷,许多人不幸牺牲,但是他们仍然坚守共产主义信仰。正是因为他们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敢于奉献、敢于牺牲,才迎来了中国解放的曙光。
福克纳的作品也刻画了一些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有志青年,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对社会的责任、对家园的保卫联系在一起,以期实现自己的成长追寻。《押沙龙!押沙龙!》里,亨利·萨德本和查尔斯·邦为了保卫家园,在南北战争期间加入南方军队参战;《八月之光》里,乔安娜·伯顿为了解除白人身上的诅咒,从事解放黑人、支持黑人获得选举权的工作。
与沈从文作品不同的是,在福克纳的作品里,由于南北战争中南方军队参战的非正义性——为保卫奴隶制度而战,所以南方战败是必然的。参与战争的南方青年承受了物质资料的匮乏和精神世界的崩塌,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遭受磨难、又失去一切的亨利和邦灵魂上彻底堕落,亨利枪杀了同父异母的哥哥,自己也在逃亡中等死;邦用和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朱迪思结婚来获得父亲萨德本的注意,事实上,在作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受死的准备,他只是想要一个结果,一种解脱。美国南方奴隶制度不仅侵害了黑人的利益,更成了白人的诅咒,因此一些以伯顿家族为代表的白人以解除白人诅咒为目的,从事解放黑人的工作。由于战后“南方白人不能忍受黑人成为和他们平等的自由人这一现实,他们极力反对给予黑人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的权利”[3]。伯顿家族的工作招来了南方白人的愤恨,乔安娜·伯顿的祖父和哥哥都被以前的奴隶主杀害。同时,她又看不起黑人,无法真正融入黑人群体,遗传和环境使得孤独的伯顿在思想和行为上更像个男人,她的人生如苦行僧一般。“成长的轨迹既可以是上升的,也可以是下降的,甚至是可以以毁灭收场的”[4]。南方青年把自己的个人追寻与南北战争、解除白人诅咒联系在一起,结果因为其非正义性,他们没有实现个人的成长追寻,也不能从工作中获得救赎,反而以一种极端的毁灭收场。
2.2 追寻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类在本质上是与自然界统一的”[5]。人类最理想的生存方式就是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大自然中获得启示与成长。沈从文热衷于表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们的活力与生机,青少年是他着力最多的人群之一。“在沈从文的想象中,苗民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年轻时期的生活方式”[1]10,他们在野外劳动、嬉戏、做爱,富有生机与活力。
15岁的三三(《三三》)欢喜坐在溪边的石头上,伴着自然凉凉的风、淙淙的水声独自想着心事,把因为怕羞不方便对母亲说的少女心事说给鱼和虾米听,从自然中获得慰藉。她从未想过要离开自然,即便怀着少女模糊的心事,想到城里去生活,也不愿意与碾坊、鱼、鸭子、花猫分开。夭夭(《长河》)在母亲的管教下,终日在田野里劳作,养成聪敏、活泼、爱劳动、热情、大方、好客的性格。她依恋家乡,舍不得家乡的橘子树、牛、羊、鸡和鸭子,宁愿在乡下住。孤女翠翠(《边城》)和爷爷住在茶峒城溪边的白塔下,她爱坐在岸边大岩石上边看云朵、星星边想着少女的心事,在傩送为她唱歌的当晚,她梦到自己摘虎耳草。阿黑(《阿黑小史》)和五明在山上幽会、亲密,少男少女淳朴、热烈的感情在大自然中无需害羞的遮掩,只有最真诚的流露。“千百年来,雷公山和月亮山悉心尽意地呵护着自己的子民,养育着自己的孩子”[6],湘西的青少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茁壮、健康地成长,自然赋予他们生命力与灵性,他们依恋自然,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或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追寻,或在自然的启示下领悟生命的意义,坚强地成长起来。
在福克纳的作品中,青少年也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大自然中获得启示与成长,“自然背景的鲜明生动是福克纳作品给人深刻印象的特点之一”[7]57。艾萨克·麦卡斯林和乔·克里斯默斯都在“鲜明生动”的自然环境中完成了个人的成长。艾萨克(《去吧,摩西》)的老师山姆·法泽斯是印第安部落酋长的儿子。他在老师的引导下在大森林里学会了所有的打猎技巧,学会了坚毅、忍耐、勇敢和放弃,成长为一位优秀的猎人,一个正直的人,并把自然法则应用到自己的人生当中,放弃了祖先罪恶的遗产,得到了心灵的平静。乔(《八月之光》)在逃亡途中意识到自己多年来想得到的一切竟是“平和、从容和安静”,找到了生存的意义与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这些是树林和沼泽地给予他的启示。于是他放弃逃亡,放弃反抗,甘愿受死,实现了灵魂的救赎。在艾萨克和乔的成长经历中,“福克纳如此优美地体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神秘感悟”[8]。
2.3 对美好品德的继承
在沈从文与福克纳的作品中,人类古老的美好品质在青少年身上得到了传承,青少年也在习得这些美好品德的同时实现了个人的成长。“作为理想化的社会形态,湘西风土代表了道德的完善,人性的美好和生命的庄严。”[9]《边城》里的老船夫善良慷慨、信守诺言、自在快乐,他坚强面对生活的苦难,在女儿去世后,独自一人抚养遗孤翠翠。被他抚育养大的翠翠在他去世后,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勇敢地在碧溪岨渡船,并怀着希望等待下桃源的二老的归来。童养媳三翠(《一个女人》)善良能干,丈夫当兵牺牲后,她独自一人撑起一个家,照顾年幼的孩子、瘫痪的干妈,直到孩子成年娶媳妇,又照顾孙子。岁月在变,时代在变,她的美德一直没有消失、没有变。“沈从文……仍然相信中国的古老事物(不是指古老的儒家文化)能够改弦更张,为新的目的服务,用不着害怕西方,也不怕社会解体”[1]7,正如小说里继承了美好品德的青少年能坦然面对严酷的生活环境,忍受生命的苦难,仍不放弃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期望,他们在苦熬中等待美好的明天。
福克纳在作品里歌颂了那些具有怜悯、牺牲和耐劳精神的人们,并着重刻画了青少年对这些精神的继承,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乐观展望。他相信“只有传统价值观念,只有过去时代的人们身上那些他称之为‘古老的美德’,即‘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等人类的优秀品质才能帮助现代人克服自身和社会的问题,阻止人的堕落和道德价值的沦丧,并帮助他们在荒原般的现代生活中像人一样生活”[2]74。艾萨克(《去吧,摩西》)继承了老师山姆·法泽斯的精神——忍耐、勇气、毅力与谦卑。他勇敢地放弃遗产继承权,选择以木匠为生,忍耐物质生活的匮乏,获得了心灵的平静。卢修斯·普利斯特(《掠夺者》)从父母和祖父母那获得了精神上的关怀与道德教诲,成长为一个善良、正直、勇敢、有担当的绅士,所以他会为了帮助妓女科丽小姐而和出卖她隐私的奥蒂斯打架,并承担起参加赛马比赛赎回祖父汽车的担子。
2.4 对爱情的追寻
沈从文“尊重性爱,他的小说中人物特别是青年人,全不受封建旧俗的束缚”[1]215。《薄寒》里,中学史地教员希望得到勇敢、热情的男子的爱;《春》里,樊陆士向恋人求婚;《如蕤》里,如蕤是一个爱情至上的女子;《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里,巧秀与自家庄子的死敌田家庄子的一个青年私奔;《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里,豆腐铺老板暗恋会长最小的姑娘;还有三三、翠翠、阿黑……她们怀着少女特有的懵懂期望着美好的爱情。
福克纳也在作品里刻画了南北战争前后美国南方青年人对美好爱情的追寻。莉娜(《八月之光》)怀着身孕寻找情夫。乔·克里斯默斯(《八月之光》)在17岁时恋上风尘女子博比。他告诉了女友自己是黑鬼的秘密,为了她打死养父麦克伊琴,偷取养母的钱,只为了能和她结婚。叛逆的凯蒂(《喧哗与骚动》)期望从爱情中获得安慰,她深爱浪荡子达尔顿·艾密司,甚至心甘情愿失身。爱米丽(《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在父亲去世后大胆追寻爱情,甚至为了情人贺默·伯隆甘愿“堕落”,不顾身份和他一起驾车出游。
对比沈从文与福克纳作品中青年人对美好爱情的追寻,可以得出以下相异之处:沈从文主要以青少年对自由、美好爱情的追寻来歌颂“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旺盛的生命力”,追寻的结果成功或失败并不重要,关键是敢于追爱。而福克纳在作品里把青少年对自由美好爱情的追寻作为他们成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追寻的结果对他们以后的人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以乔、凯蒂和爱米丽为代表的大部分青少年,在追寻爱情失败后,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他们沉沦在苦难里,人生彻底毁灭。
2.5 对自我的追寻
伴随着“我是谁?”“我能做些什么?”的自我提问,青少年们开始更加关注自我的成长与发展。“一个个体在建构身份意识的过程中,知道并接受‘我是谁?’是他必须获取的原型经验。成长的过程就是认识自我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找寻‘我是谁?’的答案,年轻人在解决身份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成长,进而树立起自己的社会地位。”[10]沈从文作品里的青少年主要从“我能做些什么?”出发,探究自己对世界、对社会的贡献,这体现了民国时期青少年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同时也与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紧密相关。《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里,姓印的朋友从鼻子得来自信,想做个伟人。《从现实学习》叙述了作者本人在生活极端困苦中,提醒自己“别忘了信仰”,以文字为生活了下来。
混血儿在美国南方社会是尴尬的存在,他们是种族主义的牺牲品。孤儿乔·克里斯默斯(《八月之光》)不知道自己是白人还是黑人,游离在白人、黑人之外,孤独地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种族歧视的环境和对自己血统的疑问像牢笼般束缚着他,不得解脱。同样可能含有黑人血统的查尔斯·邦(《押沙龙!押沙龙!》)为了得到父亲萨德本的认可,不顾伦理禁忌和同父异母的妹妹朱迪思通婚,最后在婚礼前夕被亨利枪杀。乔和邦在寻根的途中迷失了自我,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拘泥于种族主义的框架,没有从更广阔的人性的角度来看待自己,认清自己是一个“人”,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理应有尊严地活着。
在福克纳作品中,还有一些青少年成为20世纪人与人之间情感疏离的牺牲品。达尔(《我弥留之际》)深爱母亲却得不到母亲艾迪的关爱。缺少父母关爱的他找不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在家庭和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是现代社会中的异化人。
3 结语
论文从把人生追求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追寻与自然和谐共生、对美好品德的继承、对爱情的追寻、对自我的追寻五个方面分析了沈从文与福克纳作品中青少年成长追寻的异同,并运用历史文化批评探究了造成这些异同的深层次原因。沈从文和福克纳的文学作品通过一个个鲜明的青少年的成长追寻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文化,这是个人的生命体悟,也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和南北战争前后的美国南方青少年整体的生存状况。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沈从文的理想“是要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11],福克纳写作的动机就是“为了振奋人心”[7]258,他们借着青少年展望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未来。青少年本身的不稳定性和可塑性以及对自身能力和外界世界本能的好奇心,驱使着他们追寻无限的可能性,追求着超越。可以说,正是这种超越意识推动着人类自身的发展。今日的青少年是明日国家的栋梁,今日青少年的追寻是明日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面貌。
中国民国时期和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基本上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和美国南方同处于社会转型期,经历了战争、旧传统的瓦解、新兴价值观念的兴起,这些决定了两位作家作品中的青少年的成长追寻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而美国南方处于奴隶主庄园制度瓦解、工业资本入侵时期,南方文艺复兴大放异彩,这些又决定了两位作家作品中青少年的成长追寻存在很多不同。沈从文和福克纳作品中青少年追寻的异同为我们提供了深切观察中西方历史、文化背景异同的渠道。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霸权甚嚣尘上,由于青少年自身的不稳定性和可塑性,文化帝国主义对青少年的影响尤其巨大。认清中国民国时期和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对青少年成长追寻的影响,有助于我们能动地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并发挥中国文化的优势和特点,引导我国青少年顺利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