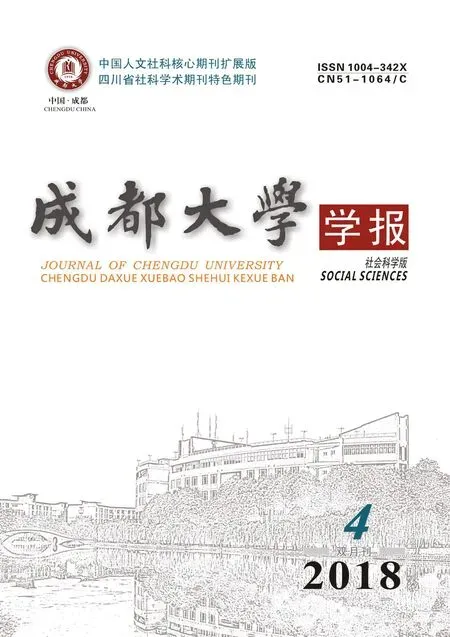川剧艺术家口述史(梅花奖得主卷)之崔光丽篇*
2018-03-19严铭万平张萍
严 铭 万 平 张 萍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2.四川经济日报社, 四川 成都 610030)
崔光丽,女,1964年3月生,辽宁省丹东人。朝鲜族。国家一级演员,2003年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民盟委员,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代表性传承人。文化部2016年度优秀专家,成都理工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工川剧旦角,师从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许倩云、王世泽,并受教于阳友鹤、陈书舫、王清廉、邓学莲等川剧名师。其唱腔华丽动听,表演细腻感人,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她的优雅的台步曾被外国观众誉为“东方芭蕾”。
12岁开始学戏,16岁时开始担纲主角演大戏,几十年来好戏连台,荣誉等身。先后主演《情探》《双拜月》《白蛇传》《和亲记》《天下第一佛》《易胆大》《柳荫记》《碧波红莲》《刁窗》《白鳝观景》《华蓥风雨》《好女人,坏女人》《铎声阵阵》等四十多个大小剧目。1990年获四川省川剧中青年演员广播大选赛优秀演员奖,1992年获四川省第六届振兴川剧调演优秀演员奖,1993年获全国地方戏曲(南方片)交流演出表演奖,1994年获四川省第七届振兴川剧调演表演一等奖,1995年获“立邦杯”第二届上海“戏歌”大赛绿叶奖,1995年被评选为四川省十佳演员,1999年以主演《天下第一佛》获首届中国川剧节金奖,2003年获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07年获文化部第12届“文华表演”奖,2010年获第20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最佳配角奖。此外,在电视连续剧《跑滩》《山月儿》、电影《黑森林》、戏曲电视剧《红楼外传》《山杠爷》中担任重要角色。1998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演播中演出小品《金虎闹春》。1997年演出的《柳荫记》(饰祝英台)由中央电视戏曲部拍摄录像,收入戏曲精品库,多次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采写时间:2017年11月22日
采写地点:成都市麓河会所
采写:严铭万平
摄录:赵民睿卢慧
严铭(以下简称严):崔老师,您好!今天是2017年11月22日,我们在麓河会所采访您,我很高兴。我知道您是川剧百花丛中的一朵金达莱,是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首先,想请您谈谈从事川剧艺术表演的经历。
崔光丽(以下简称崔):我从事川剧表演应该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当时我考入了简阳的川剧团艺训班,选拔制度非常的严格。为什么我选择麓河会所这个会所呢?这说来也是一种缘分。建立这个会所的小妹妹,当时也是我们训练班的一位成员,但那时她年龄太小,所以没有从事这份工作,所以说这就是一种缘分。今天很有幸你们来采访我,我选择这个地方呢,觉得还是一个情结吧。我要告诉人们,即使我们在各个行业都发展得很好,但依然初心不改,还是喜欢文化。所以在她做了很多企业以后,又反馈回来想做她的文化,在这个地方成立了麓河会。这又很巧合地把我们两姐妹联系起来。我说:“好,姐姐今天就在你的麓河会做采访。”这里又有一段小插曲,当时我13岁,考入简阳县(现称简阳市)的这个剧院。
严:具体是哪一年?
崔:1977年3月,我觉得“3”这个数字与我非常的有缘。我在家排行老三,自己的生日在三月份,并且自己工作时也在三月份,所以“3”这个数字对我有特别的意义。“3”放在传统文化里来讲,是一个吉利的大数。
严:3、6、9嘛!
崔:对对对,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北方人,我的父亲是一个军人,家人都不太同意我从事这份工作。我的父亲戎马一生,他认为自己的孩子还是应该多学文化知识,去实现他们所未完成的理想。我们家五个女儿性格不一,我占三,所以呢从小性格就开朗活泼倔强,自己既然选择了这个道路我就不会轻易放弃。当时考剧院,不是父母同意后带我去考,而是跟隔壁邻居一起去考的。当时考核的老师叫我跳个舞唱个歌。我还没唱完一首就叫我往上唱,那时心里还有点不舒服。现在回想起来就懂了,老师就是想看看我嗓子的音高。等待考核学生有那么多,不可能一个个地听完。结束后,我还听到老师说:这个小女孩皮肤还有点黑呢。当时,听着心里还有点不高兴,我觉得黑不影响啥啊,这就是性格使然吧!事实证明,我的实力还是可以。当时,一个班60人我名列前茅,第一年就转正了,那时候跟现在是没办法比的。
严:转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崔:转正就是原来你是学员嘛,现在就是正式的职工了。
严:就是正式的演员了。
崔:其实我真的特别感谢在简阳的那段时间,那是我人生打基础的地方,那些老师对我也特别的好。那时的条件十分的艰苦,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记忆。与现在的剧院相比,我们需要下乡去演出,睡地铺、坐拖拉机去乡村演出,很少能坐汽车,但是我觉得十分的温暖与感动。那时全院上下的老师把最好的位置让给我,坐驾驶台避免被风吹坏嗓子,时时刻刻都在关心我爱护我。那种温暖与感动至今留存在我内心深处,现在那种感动已经很少能见到了。我就在想:如果当时不是她们的这种呵护,我肯定不会坚持到今天,保持这种良好的状态。就是一种很纯的东西,很善良。
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非常淳朴。
崔:这种善良、淳朴、包容、豁达、乐观,给我奠定了一种很深很深的基础,让我在心里觉得,我将来一定要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好的、友善的东西,坚定“好的说不坏,坏的说不好”的信念。
严:崔老师,您的人生经历注定您要靠着自己的奋争、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去回赠在这条路上那些善良的人,是吧?
崔:对,就是说你帮助了别人,别人也会回报你。我现在也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其实,我并不是抱有目的性、功利性去帮助别人,但是我觉得人一定要是非。
严:就是要有是非观念。
崔:一定要有是非观念,好的就是好的,我就会去不计任何东西去帮助他。现在他们很多人都比我更为成功,是受了我的帮助,就是全靠了崔光丽怎么的,怎么样。其实我很欣慰,就是我认识了别人价值,他在经过别人的点滴帮助之后取得成绩,为社会、为别人有用、有贡献,这是一件让自己很开心愉悦的事情。
严:那您在简阳学习,转正之后,您一般从事哪些演出活动,或者是在艺术打拼过程中,您又经历了哪些?
崔:我是这样的,其实我在简阳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简阳,我16岁就登台演主角了。所以说,才有这么多老师呵护我关心我,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个好苗子,我们要保护她。在这样的情景下,我演了许多的大戏,很多的折子戏。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演出是一天要演三场戏,其中有两场我都是主角,还有一场要串角,就是说要演配角。虽然那个时候也有许多人喜欢看戏收门票,但是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可以叫你很好地去休息。简阳完了以后,有一段时间是在泸州市川剧团,他们要招兵买马。那个时候我们有个川剧理论家、学问家席明真先生,他原是重庆市文化局的局长,是一个非常的有名的行家。我们整个四川的戏曲包括演员他都很了解,当时他就把我介绍推荐到泸州,1986年我就从简阳调到泸州。但是在泸州我也是担任主要演员,如果你不优秀,泸州也不会要你。所以说,在泸州待了四年,也演了很多戏,大小角色都有。后来,又到了四川省川剧艺术学校,演一些折子戏、三幕戏,也是泸州市川剧团的主要演员。这个时候,四川省川剧学校要招一个明星班,把全省各地各个剧团的优秀演员全部纳入这个班。1987年我也有幸参加这个班,在班里三年,系统化学习了川剧表演,我们这一批人都是被特别选拔出来的,有着丰富的演出经验。按理说,我们这个班是四川省川剧界承上启下的最棒的一批人。具体说来,我们班有7个梅花奖得主——孙勇波、黄荣华、胡瑜斌、何伶、田蔓莎、肖德美和我。还有其他一些如李乔松这些优秀的演员,都是国家一级的演员,还有在我们剧院战斗在一线的何鸿劲等人。我们这一批人都算得上是四川省川剧界的精英了。因此,我在这个班里如鱼得水,更好地和同学互相学习,也有机会见识更高级别的老师。
很小时,我到重庆去演出《穆桂英挂帅》,担任主演,好评如潮,《重庆日报》也刊登过。我也非常有幸见到了川剧皇后许倩云老师,现在也是将近九十岁的老艺术家了。那时她就说很喜欢我,来看我演出,16岁我就拜她为师了,就一直跟随着她。在许倩云老师的带领下,我相继认识了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回到成都,我又结识了我第二位老师——王世泽老师,给我排了《碧波红莲》等作品。他是一个非常优秀有本事的老师,也精通旦角艺术、小生艺术,非常痛心的是他今年(2017年)已经过世了。看着老一辈艺术家们相继离去,有时就很感慨我们学到的东西真的太少了。这种感受你真的只有经历过才会知道,得到了的时候不觉得,失去的时候才觉得珍贵,真的非常感谢老师。在这个时候到了川剧艺术学校,又接触了很多老师、很多名家,包括王启年老师、陈书舫老师这些前辈。《柳荫记》中我饰演祝英台,这部戏是我对她们的很好传承,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传统戏是非常深入人心的,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也是大众所喜闻乐见的。
严:没错!这些都是经典。
崔:三年后我就被调到了四川省川剧院。
严:具体是哪一年?
崔:1990年至今都是待在四川省川剧院。我父亲一直不赞同我演戏,我性格是比较倔强的,就想着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直到我15岁演《白蛇传》时,他来看我演出,觉得这孩子演得还不错,这时他的观念才开始转变。后来,父亲给我说了这样两句话“台上认认真真演戏,台下踏踏实实做人”,一直鼓励着我坚守着这份事业,这也是一个军人家庭的家风。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父亲这两句话的意义。“踏踏实实做人”饱含着父亲对子女的关爱与期待,让我受用一生。
严:这确实是对您的一种鼓励,在您职业生涯中也有着特别的意义。
崔:对,父亲这两句话一直鞭策着自己,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不至于迷失、脱离做事的原则、轨道。
严:从您到川剧学校至今,出演了哪些剧目呢?
崔:从简阳开始算,大大小小几十出戏绝对有的。
严:应该有四十多种。
崔:是的。例如《白蛇传》《柳荫记》《情探》《和亲记》《天下第一佛》《好女人,坏女人》这些作品,就不一一列举了。我的行当比较广泛,不拘泥于一种形式,青衣、花旦、闺门旦、刀马旦我都演。
严:其中还有一些反串的角色,是吧?
崔:是,《柳荫记》中饰演的小生,《春江月》里也反串过一个小生。
严:您演过的许多戏我都很感兴趣,也看过一些。里面的人物如《十二寡妇征西》中的穆桂英,《碧波红莲》中的红二等,形象鲜明,从中也可以见出您的艺术功力。您认为您最满意的剧目是什么呢?
崔:我觉得艺无止境,我个人追求完美,只能说比较喜欢和钟情某个剧目。个人看法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一个说特别特别满意完美的剧目,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艺无止境。很多人都给予了你很高的肯定与荣誉,认为你已经非常可以了。为什么别人会认为你那么优秀啊,就是你对自己的不放纵,让你在艺术上追求精益求精、艺无止境。这个是一直伴随在我的艺术生涯的。对于我的一些剧目我是非常的喜欢,表演的每一个表情与动作都会去精雕细琢。但是,还是存在很多因素让你达不到你心中的理想境界。所以,有时候艺术也是一种遗憾的美,千万避免唯我主义。
严:许多人都是追求艺术的炉火纯青。
崔:炉火纯青是别人对你的认可,如果自己也认为自己炉火纯青,那么在艺术上你已经不可能再有创造性了,没有前进的空间了。
严:我也看到一些对您在《易胆大》饰演马五娘这个角色的评论,评价都很高,对角色的塑造出神入化,十分出彩,对于角色的把握非常到位。
崔:说起马五娘这个角色,我们先来谈谈这部戏。《易胆大》是十几年以前,我们四川省川剧的一个高峰,也可以算作是一个里程碑的阶段。那时候我已经得了梅花奖四年,其实一开始接这个角色是犹豫的,因为这是一个完全反串彩旦的角色,而我一般演青衣、花旦,彩旦与我的所有行当都不沾边。但领导考虑到我综合素质比较高,我还是接了下来。我没想到这个在剧目中只排得上第五六号的角色,却为我赢得如此大的荣誉,令我很震撼。凭着这个角色我获得了白玉兰最佳女配角奖。整部戏也获得了“文华表演奖”,为剧中演员也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度。所以,这个角色对我而言,是个人荣誉的见证,也是对我艺术功力的检验。这样一个小的角色凝结着我许多的心血和功夫,它运用了许多川剧的传统理念,在此基础上我也加入了我对角色的见解和元素。运用花旦的手势去丰富人物形象,不仅仅是表现一种袍哥式丑陋、凶悍的人物性格,而是去塑造出女性的美。能够得到大家都认可,对我自己也是一种鞭策和鼓励。在闲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样一个角色也维系着我生命的路途,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严:您是第二十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得主,在您所演的剧目当中,您认为哪些剧目为您“夺梅”助力?
崔:夺梅的过程很艰辛,我们那一届梅花奖规则做了一些改变,需要演三个折子戏加一个大戏,而我只准备了三个折子戏,因此就打算在陈巧茹的剧里参演一个B角。在戏中发挥自己的强项,演出个人特点,自己也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最后,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了两场也获得了很好的评价。传统戏的反串功力也为我塑造这个角色奠定了一个基础,而传统也正是我们新一代年轻人所缺失的,我们需要去重视。所以,现在之所以很多人演不好戏就是传统功力太差劲。有这个戏奠定基础,我的折子戏和《别洞观景》为我加很多分,评委说:“崔光丽你们这一代当中,你的《别洞观景》一定要传承流传下去,它体现了我们川剧的特点。”王世泽老师给我导演的《刁窗》也是如此,在传统的基础上,剔除了其中不足的地方加以完善。《好女人,坏女人》也是得到了许多老师的帮助,助我夺梅。在夺梅的过程中我算是比较艰辛的一个,其中也有许多故事不愿提及。演出的经费和服装费都没有,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把装房子的钱拿出来垫资。我非常地感谢我的母亲对我的支持,当时母亲病重依然对我说:“既然有机会追求自己的事业,就不要错过。”从以前到现在,我艺术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她的支持。
严:您身后这些亲人、老师还有朋友都给了您很大帮助。正因为您身边这些好人亲人的付出和牺牲才铸就了您今天这样的辉煌。
崔:对。
严:据报道您在出演新编川剧《铎声阵阵》这部戏反响很大,报道说您当时是带病演出的,您能说说这段经历吗?
崔:在剧中,女主角葛来凤的年龄跨度超过30岁,从18岁的少女直到老年阶段。原本按戏曲行当划分为“小花旦”“青衣”和“老旦”,结果发现远远不够。除了表演技艺本身的难度,我的身体状况更是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2014年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在北京接受了手术和8次化疗、28次放疗。现在还处在恢复期,家里人一开始全都反对我接下这部戏,最后还是母亲表示了支持。排这个戏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掉泪,中途差点就想退下,太累了。我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万一倒下了怎么对得起她?想来想去,还是不能这样做,当了逃兵保全自己,却辜负了大家的希望。我一定要将创作过程中的感动呈献给观众,让观众也获得感动。
我扮演葛来凤,从一个女人的少女时代到老年时期,经历大喜大悲,曲折的命运故事,大量的台词,表演细节,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也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好角色。一个演员遇到一个好角色不容易,我自己很珍惜这次机会。剧中的葛来凤,泼辣、率真、执着、坚强,生动地彰显出一个四川女人的坚韧不拔。我内心是很认可这个角色的,她一辈子跟命运抗争,争取幸福,虽然命运大起大落,但她表现出来的人性闪光点,却令人非常敬佩。(这部戏参加了2017年第十五届(银川)中国戏剧节,好评如潮并获得了2017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这部戏是在去年(2016年)排的,追溯这段经历要倒叙着说。前几年,我在美国接到文化厅艺术处杨处长(现省歌舞剧院院长)的电话,他说:“9月3日广元要搞一个女儿节,想排一个《武则天》剧目,能邀请你来演。但是我们的薪资不高。”我说:“可以啊!”我这个人比较直率,也不会去多想其他东西。归国前夕,和朋友聚餐就感到有些身体不适。回国后,到川医去检查就发现左臂下面长了一个东西。医生就建议留下来仔细检查一下,可那时已经和杨处签合同了,也不能言而无信。最后,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去到了广元。拍戏过程中,还是觉得特别不舒服,就去当地医院检查,医生说:“你这个得引起重视啊,我怀疑是癌变。”当时,我就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戏还有十天就要演出,现在换人也来不及了。换个角度思考,如果你不确定你到底得了什么病也是很麻烦的事情。我就马上给我北京医院的朋友打电话说明情况,她就叫我马上到北京去。于是,我做了个决定,去北京检查。从广元到成都再到北京,六个小时的里程,也是我自救的过程。当时,北京医院的医生就建议我住院,内心真的很挣扎,如果我不去演出就是对别人的不负责,所有的心血都会白费。我就给医生说:“能不能缓一缓,我马上就得要演出了。”医生也实在没办法,就说:“那行吧!你快去快回,我先把床位给你留着。”我就硬撑着演完了这几场戏,然后拎着箱子独闯北京。我的性格还挺像一个男孩子的,我热爱这份事业,也不愿辜负别人的期待。到北京检查后,确诊为乳腺癌。最开始心里打击很大不能接受,为什么命运会是这样。在这之前,我四十多岁才遇见真爱,与他步入婚姻的殿堂。爱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带给我温暖,支撑着我的信念,可是不久,他患病逝世了。爱人的离开让我长时间以来很郁闷,不能释怀,这可能也是造成我生病的一方面原因。所以得病之后,就像是从死神手里获得重生,面对世事也更淡泊和平静,更能够泰然处之。其实,我真的很感恩我还能健康地活着。既然我依然拥有生命,那就一定得让我做点事,我还有我存在的价值。在与疾病做斗争期间,我告诉我自己不能倒下。我告诉医生也告诉自己:一、不能残废;二、我不能苟且;三、我要重新站上舞台,证明我自己。就是这几个信念一直支撑着我走到今天,而我也确实做到了。一年以后,中国第一届川剧节,我就又代表广元得到一个金奖,为他们争得了荣誉。
严:具体是哪一年呢?
崔:就是2002年。
严:当时是个人专场演出吗?
崔:我的个人专场是十年以前拿梅花奖的时候了。时隔一年后,再次出演《武则天》这部戏还是考虑了很多因素。接戏其实对剧本还是很考究的,当时这些大导演都很忙,对剧本要求挺高。这部戏还是很好,就决定开拍。接到这个剧本我还是考虑很多,家里人全部都很反对,“你什么都有了,身体又这样,而且剧院也是一个小社会蛮麻烦的,干脆就不要去了。”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母亲,这次也是我的母亲这样关心我,可是她现在都还在医院。我心里还是很难过内疚,如果不是我执意要演这部戏,她可能不会病得这么重,出于对我的担心,夜不能寐,时时刻刻挂念着我。这一点真的特别对不起母亲。
严:有时候忠孝难两全,艺术和亲情也是如此。
崔:反言之,当我作出成绩来,到妈妈病床前时,她也感到很欣慰。越是这样我就越要做好。所以,有时候觉得只要妈妈您好了,我也就好了。母亲就是这样的伟大,有了母亲就有了一个家,让你安心,没有漂泊感、空虚感。感觉现在自己还是一个孩子似的,想努力把所有事情都做好,做完了以后给妈妈交一份作业,给妈妈说一句:“妈妈我又做好了。”就是这样,有时候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妈妈,我的生命就空了。
严:在父母眼中孩子永远是孩子。
崔:有时候我领着妈妈出去散步,同事就会说:“崔姐,看着好感动哦!”其实这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
严:听了您刚才说的这段经历,正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您身上有一种重要的精神动力,可能与您对川剧艺术的痴迷与执着有密切的关系。
崔: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信念和目标。一个人如果目标不明确,价值观不明确,那么他会处于游离状态,做不好事情。很多事情你认为很简单,我认为你能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那么你就不简单。
严:对,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崔:虽然说,现在川剧艺术比较低迷了,不像原来那么景气。但是,如果你能把低迷的东西做得景气,做得有价值,那么你就非常了不起了。如果谁都去追求物欲横流的东西,随波逐流,那有价值的东西就难以被发现。
严:大家都去追求时髦,而忽略像川剧这样有价值的艺术。
崔:对。
严:所以艺术中有关传统文化的东西是有生命力的,永远有着自己独特的光芒。最后,想问一下崔老师您对川剧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有什么看法?
崔:说到这点,我曾经也是多方面地呼吁过。川剧是一门非常辉煌灿烂的艺术,现在川剧确实也是到了比较危机的时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事实。因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人才问题,川剧艺术后继无人。如果一个家族、一个民族都没有人了,你对一个剧种都没有人了,还有希望吗?所以,现在千万不要去说个体怎么样,应该要集体呼吁把人才队伍建设起来。比如说原来把大量的地方剧种全部都裁掉了,人走茶凉,人才尽失。习大大执政后,大力复兴传统文化。我们也响应习大大的精神,呼吁我们的民族文化艺术快点回来。但当我们打开房门时,却发现我们家里一贫如洗,“没人了。”这也是让我非常着急的事情,包括我们四川省川剧院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对此,我们应该重视人才的培养。
严:就是要增强人才培养的意识。
崔:这个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对老演员(七八十岁)的保护。第二步,就是我们中年一代,也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怎样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作用,怎样把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第三步,年轻一代孩子们,怎么去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站在舞台上,让他们能感觉到自己投身的艺术的魅力与尊严,树立文化自信。再说,就是现在对川剧艺术家的待遇太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扼杀年轻一代孩子追求艺术的热情,在艰苦条件下也很难坚持下去。所以,没有合理化的安排,没有配套的设施的状况下,川剧发展传承不容乐观。
严:艺术的发展涉及到政府的投入问题。
崔:政府的投入方面,他们是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的。但我真的希望政府要把“好钢用到刀刃上”,要把投资用到精通这个行业、愿意为这个行业付出的人、愿意把事情做好的人。要把权力、财力、物力用到这些人身上才有希望。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这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因为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就是一个人民的艺术家,我没有任何一个行政职务。当你的艺术水准高于所有行政人员,但你没有权力,而只能依附于权力。那么,艺术都得打折扣,我们现在这个年龄阶段,看淡了生死,自己生活在艰苦条件下无所谓,但年轻一代孩子不一样,他们是文化传承的主力军。我们老一辈艺术家应该传递给他们正能量,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们艺术发展的消极状态。
严: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川剧的保护与传承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转变观念,重视的力度,还有社会的支持都很重要。崔老师,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辛苦您了。
崔:没关系,很高兴认识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