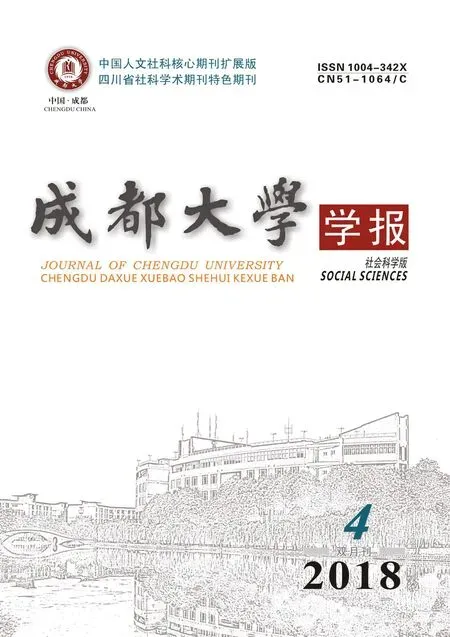从“有诗为证”看宋代小说的音乐化趋向
——以《碾玉观音》和《王幼玉记》为例
2018-03-19尹思琦
尹思琦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宋代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小说,不论是古体还是近体,或是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均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独特风格。体式特点上,诗词元素比例的加大尤为显著。在小说中往往以“有诗为证”的标志语引出诗词,其篇幅或长或短,或完整一首,或只言片语,形式较为灵活。而这些诗词元素的存在,正是宋代小说音乐化趋向的重要表现。
一、宋白话小说中诗词元素的音乐化表征及其功能
宋代小说有古体与近体也即所谓文言与白话之分。相对而言,古体小说产生较早,并且随着唐传奇的出现在唐代达到顶峰。而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到宋代才产生,它们一开始作为“说话”的底本而存在,因此又被称作“话本”。由于种种原因,传世的宋代话本并不多,且多经过后世加工而失去其原貌。程毅中先生据文献记载确定了十六种现存宋代话本小说[1]312-319,本文以《碾玉观音》为例分析,以略窥宋代白话小说风貌。
《碾玉观音》在《警世通言》中题为《崔待诏生死冤家》,题下注曰:“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2]91则此篇当为宋人小说无疑,《碾玉观音》是其原题,《警世通言》中的题目当为冯梦龙所改定。小说叙述咸安郡王府的刺绣丫鬟秀秀与玉匠崔宁相爱并私奔,因小人告发而使秀秀被杖毙。崔宁被发配至建康,竟不知秀秀魂魄跟随前往,并与崔宁继续生活。后崔宁发现秀秀为鬼,自己也终被拉入水中地府,二人共化为鬼。整个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本文主要探讨其体式上独具一格的特征。《碾玉观音》最显著的体式特征便是大规模的诗词插入,它们不仅应承艺人讲唱结合的表演模式,展现韵文的声乐韵律之美,也推动着故事的有序发展,缀连情节的起承转合,使得小说显现出音乐化的趋向。
(一)“入话”部分的诗词元素
入话,即小说开讲前的前言,近似唐代讲唱经文前的“押座文”。一般引用一首或几首诗词以作开场,一则营造说故事氛围,使客人渐次安静;二则等候未到的听众落座,不至错过太多情节与内容。《碾玉观音》的“入话”部分就用十一首咏春归的诗词作为引子。
首先是连续三首《鹧鸪天》词,其第一首:
山色晴岚影物佳,暖烘回雁起平沙。东郊渐觉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鸦,寻芳趁步到山家。陇头几树红梅落,红杏枝头未着花。[3]25
这是一首写意纯粹的春景词,小说中称是咏“孟春景致”,词义明白浅近而近口语。另两首分咏“仲春景致”和“季春景致”,也是延续了前一首浅白通俗的风格。之后小说借王安石、苏轼、秦观、邵雍、曾肇、朱敦儒和苏小妹七人之口分别赞美风、雨、絮、蝶、莺、杜鹃、燕七种春日景物的言辞,依次引入了与七种景物对应的七首诗词。其第一首:
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3]26
此为咏春风之诗,行文浅易畅达,诗笔直白俚俗。其余六首也都大体与此相类。有些诗句甚至直接使用白话,呈现出口语化与通俗化并举的市民趣味。最后是一首感叹春光已逝的七言律诗,小说中称之为《春归词》:
怨风怨雨两俱非,风雨不来春亦归。腮边红褪青梅小,口角黄消乳燕飞。蜀魄健啼花影去,吴蚕强食柘桑稀。直恼春归无觅处,江湖辜负一蓑衣![3]27
这首诗的风格与之前诗文异曲同工,一脉相承,在内容上总结全篇,并与开头咏春词交相呼应,从而使得这段内容与整篇小说情节脱节的文字成为了一个首尾连贯的独立整体。
入话部分通过穿插整整十一首诗词,从初春写到晚春,表现出对春归的强烈惋惜之情。这些诗词因素与正文有何关系?细察全文,从内容来说,一方面直接叙事,预设铺排咸安郡王因恐春归去,携钧眷游春而巧遇秀秀之事;另一方面与秀秀如春花般娇嫩的生命被郡王摧残的过程相契合,以诗词来创设环境,暗示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从文章的形式和主旨来看,这种广引诗词的方式,弱化了情感表达的力度,但说话人讲故事时,往往会即景生情,增加形象生动的说明,以吸引到场的听众。因而以当时说话的艺术形式而论,广引诗词恰恰是以又唱又说、说唱结合的方式来吸引听众的参与,音乐化的趋向大大增强了宋话本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二)正文部分的诗词元素
小说的正文部分也有许多诗词元素。在开篇不久秀秀将登台亮相时就出现了“尘随车马何年尽?情系人心早晚休”这样一句诗。说话人站出来,以一个“情”字、一个“休”字,简劲地暗示了本篇讲一出爱情悲剧,帮助听众总体上把握整个故事的基调。在秀秀正式出场后,小说随即插入了一首完整的韵文:
云鬓轻笼蝉翼,蛾眉淡指春山。朱唇缀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碎玉。莲步半折小弓弓,莺啭一声娇滴滴。[3]28
此段韵文对秀秀的外貌进行了细致详尽的描写,说话人袭用了一组脆生生的套语,程式化地描画女子的貌、声、色、姿,分明有《诗经·卫风·硕人》的影子,说出了我国传统对于女子的审美观,满足了市井平民的审美心理。如此熟谂,倍感亲切,从而使听众留下深刻的人物印象。从艺术上来说,全诗口语化特征明显,读来上口,平仄交替、抑扬顿挫具有语音上音调抑扬的音乐之美,创作出了音乐的氛围。也正是从这首词起,主人公秀秀的故事才算真正开始。小说在秀秀的父亲为虞候介绍完女儿的基本情况后,又用了一首《眼儿媚》词:
深闺小院日初长,娇女绮罗裳。不做东君造化,金针刺绣群芳样。斜枝嫩叶包开蕊,唯只欠馨香。曾向园林深处,引教蝶乱蜂狂。[3]28
这首词赞美秀秀绣技之高超,秀秀也因此被招入郡王府做绣女。随之小说又转到了男主人公崔宁的叙事线。当一切如常的时候,郡王府偏又失火,小说专门用了一段韵文来描写火势。男女主人公因大火得以相遇并相与饮酒。此时,小说用了“三杯竹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两句诗形容两人饮酒后的状态,以俗语、俚语入诗词,更显示出文人对市民俗化趣味的迎合,顺应“说话”技艺的表达技巧与方式。当夜秀秀以身相许,与崔宁双双私奔至潭州生活。奔逃之事尘埃落定,似乎一切归于平静。正当此时,崔宁归途中忽遇一男子,这时小说用了“谁家稚子鸣榔板,惊起鸳鸯两处飞”这样两句诗,上半回随之结束,显然故事又将发生大的转折。以“鸳鸯两处飞”,暗示着崔宁与秀秀二人的一生一死。上回的结尾诗,充分体现了说话人居于说话表演主宰者的地位,在增强艺术表现力的同时,更加注重故事的张弛有度和节奏回环,以引诗控制着说话的节奏和进程,在结构上,赋予话本小说紧密弛缓的节奏和从平淡到激烈的情感体验,如交响乐一样渐次加强,体现出回环往复的音乐美。
小说下半回开始时,同样用了一首《鹧鸪天》:
竹引牵牛花满街,疏篱茅舍月光筛。琉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簇豆梅。休懊恼,且开怀,平生赢得笑颜开。三千里地无知己,十万军中挂印来。[3]32
可以看出,这首词的内容同样与主体情节毫无关联,这其实也是说话人利用诗词来控制情节、节奏和气氛,使得结构上颇具回环往复的节奏美。另外,围绕这首词引申出了“刘两府”这样一个枝蔓故事,虽然小说以巧合的方式将这个枝蔓与主体情节嫁接到一起,但从内容上来看,它们之间还是相距甚远。所以这首词连同其所引申出的这个故事完全可以当作一个独立的部分来看,那么其功能与性质应该与小说开头的“入话”相同,或者说它就是下半回的“入话”。
然后,小说接着上半回末新出场的人物继续进行。此人的出现又将打破整个故事的平静。因为他的告密,郡王知道了崔宁与秀秀的安身之所,并派人来缉捕。结果如何呢?小说用“皂雕追紫燕,猛虎啖羊羔”两句诗来预示了故事后面的发展。两人被捉拿回府,并都受到了惩罚,崔宁被发配到建康,而秀秀则自称被赶出了郡王府,并追随崔宁前去。故事又一次归于平静。而当一切似乎都圆满的时候,之前的告密者郭排军又一次出现,而小说同样也插入了“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这样的诗句。与之前的情景如出一辙,郭排军又一次告密,郡王又一次派人来捕。在捉拿到人之前,也同样用两句韵文来预示后面的结果。于是秀秀又一次被捉拿到了郡王府,经此一折,崔宁方才识破秀秀鬼魂的身份。最后,小说用“两部脉尽总皆沉,一命已归黄壤下”两句诗点明结局:崔宁终被秀秀拉去一同做了鬼。小说的结尾部分是以四句韵文结束: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郭排军禁不住闲磕牙,璩秀娘舍不得生眷属,崔待诏撇不脱鬼冤家。[3]38
可以看出,这是对小说全篇的总结,含有一点说教的意味。同时用来提醒听众故事结束,可以散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碾玉观音》中的这些诗词元素的使用其实都是有特定规律的,特别是在正文部分,每一次诗词或诗句的出现都预示着关键人物或情节的出现与转折。这样的设置使得小说的主体情节被切割成了若干个情节单元,每一个情节单元都是故事向前推进的一个阶段。它们按照一定的线索有序连接并组合,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故事整体。
总的来说,诗词作为音乐元素文本在宋话本小说中的使用具有以下功能:一方面,诗词其本身便具备的韵律之美,声韵和谐、通顺明达且朗朗上口,极尽文字、句子本身的音乐之美;另一方面,诗词也在说唱与吟诵并存的演绎方式中,起到暗示情节、设置悬念、活跃气氛、吸引听众、增强小说表现力等作用,使得小说的结构安排呈现出张弛有度、回环往复的层次美与节奏美,从而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呈现出音乐化的趋向。在说书人说唱结合的讲述方式中,又增加了说书技艺的感染力,同时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娱乐消费功能。
二、从行文与诗笔特征看宋文言小说的音乐化趋向
除白话小说之外,宋代的文言小说,特别是传奇也表现出行文的通俗化和口语化,以及诗笔比例的加大与浅俗化等特征。这正是宋代文言小说向白话小说以及“说话”艺术靠拢的表现。下面以《王幼玉记》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王幼玉记》出自宋刘斧所撰《青琐高议》前集卷十,题“淇上柳师尹撰”,作者生平不详。又题下有副标题“幼玉思柳富而死”,应为编者所加。[4]1082这篇小说讲的是衡阳名妓王幼玉与东都人柳富相爱,后柳富被家人催促回京,然因故未能再回衡阳。幼玉遂思念成疾,抑郁而终,并化作鬼魂前去与柳富道别,约定来世再相会。整个故事与唐人《霍小玉传》极似,但情节较为平淡,缺少大的冲突。这里主要从其体式进行分析。
(一)行文的口语化
从语言上来说,这篇小说使用的是浅近的文言文。如小说开篇对幼玉的介绍:
王生名真姬,小字幼王,一字仙才,本京师人。随父流落于湖外,与衡州女弟女兄三人皆为名娼,而其颜色歌舞,甲于伦辈之上。群妓亦不敢与之争高下。幼玉更出于二人之上,所与往还皆衣冠士大夫。舍此,虽巨商富贾,不能动其意。[4]1082
可见作为一篇文言小说,此段文字浅近俚俗,其中有些句子甚至完全接近于白话。这种白话式的行文方式是宋代传奇的普遍现象。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是《青琐高议》中的《范敏》一篇,其中有段文字如下:
将军见而不悦曰:“巨翁安知李氏忆旧事而无新意乎?”李氏忿然曰:“唐帝有甚不如你这小鬼!”……将军大叫云:“今夜一处做血!”李氏云:“小魍魉,你今日其如何我?有两人管辖得你。”[4]1082
文中所使用的是非常纯粹的白话文,这其实与《王幼玉记》的浅白式行文现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凌郁之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宋代文言小说作者接近民间、适应民间、迎合民间”[5]157的表现,是很有道理的。
(二)诗笔比例的增加及其浅俗化特征
宋代传奇的另一个体式特征就是诗笔成分的加大。就《王幼玉记》这一篇而言,其中所羼入诗词有四首,且有一首长达六十句。很多唐传奇也会有诗词插入,但往往短短数句,其篇幅及所占比例并不似宋人传奇宏大。虽然也有像《莺莺传》这样以长篇诗歌插入者,但在唐传奇中仅是少数个例,并非普遍现象。然而我们遍检宋人传奇就会发现,这种大比例的诗笔现象在宋传奇中比比皆是,此处不再举例说明。
除了比例的增加,宋传奇中的诗词元素同样表现出了浅俗化的特征。下面以《王幼玉记》中的一首为例:
真宰无私心,万物逞殊形。嗟尔兰蕙质,远离幽谷青。清风暗助秀,雨露儒其泠。一朝居上苑,桃李让芳馨。[4]1083
此诗是小说开篇一个名叫夏公酉的名士写给幼玉的赠诗,意在赞美幼玉的绝美气质,诗旨很是直白,是一首中规中矩的咏人咏物诗。若是将这首诗与唐传奇中的引诗做比较,自然会高下立见。如《莺莺传》中的这一首: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6]4013
这是莺莺写给张生的约会诗。整首诗以月为引,意境空灵,虽寥寥数语,却极具韵味,与莺莺的形象及整篇小说的格调非常搭配,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为小说增色的效果。而反观《王幼玉记》中这首诗,在艺术上就显得拙劣得多。就文本来看,其存在与否并不会影响到小说整体艺术水平的高低。除此之外,还有一首长达六十句的七言歌行体长诗、一首《醉高楼》词和一首七言律诗。这些诗词与前面一首都有同样的特点,呈现出浅俗化的倾向。当然,这种倾向不仅限于《王幼玉记》一篇,而是宋代文言小说的一种普遍现象,这应该与文言小说在宋代的转型有关。孙副枢为《青琐高议》所撰序言一开始就评价撰者刘斧本人是“吐论明白,有足称道”[4]1007,据此似乎可以推测刘斧很可能就是一个擅长“吐论”的说话人,或者是一个“近似优伶的人物”,《青琐高议》则“可能就是刘斧用以说话的一个底本”[1]101。宋文言小说的行文口语化及诗笔成分的通俗化特征正是其向“说话”艺术靠拢的表现,它开始具备与白话小说相同的属性。总之,宋代文言小说既不以情节取胜,也不以语言取胜,而是与白话小说一样作为“说话”艺术的底本,将其艺术价值体现在具体的表演过程中。特别是其中的诗笔成分,也同样以音乐化方式呈现在“说话”表演中,成为了提升“说话”表演乃至小说文本艺术表现力的关键元素。
三、“说话”的表演模式及其中“唱”的部分
“说话”是一种盛行于宋元时期的说唱艺术,据耐得翁《都城纪胜》及吴自牧《梦梁录》等均有文献记载。且宋代说话有许多家,各家皆有其擅长的题材,此处不赘述,主要探讨其表演模式。
(一)“说话”的表演模式
在《清明上河图》中,有这么一幅场景:在一个十字路口的茶棚前,一群人围观一个老者,老者口中似乎念念有词,这个老者应该就是在表演“说话”,这是对宋代“说话”艺术最为直观的反映。可以看出,“说话”一般只有一个主说者,这是一种单人表演艺术。郑振铎先生以为说话是一种讲唱并重的艺术,而宋人“小说”中夹入的诗词元素皆是说话表演时的唱词。[7]581从上面的小说文本可知,在“说话”时,说与唱两种方式应该是交叉进行。以《碾玉观音》为例,其入话部分皆为诗词,故应该是以唱为主的,这类似于今天影视剧中的片头曲。在“说话”内容正式开始之后,主体情节则以“说”的方式进行,并会穿插或长或短的唱词,来表示故事内部情节单元的推进。这种“说”“唱”交叉的方式使得整个“说话”艺术更具层次感和节奏感,并能在保证主体情节顺畅和完整的情况下,适当地调节气氛,从而更好地掌控听众的情绪和注意力。最后在“说话”结束时,会演唱数句韵文,一般情况下多为四句,以此对整个故事进行评说,并点明主题,阐发故事的教化意义。
(二)“说话”表演中“唱”的部分
通过对上面两篇小说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篇小说中的诗词元素所占的比例都极大,当然,它们都是作为唱词而存在的,可见“唱”的部分在整个“说话”艺术中的重要性。而据《都城纪胜》记载:“小说,谓之银字儿。”[8]98这里的“小说”是“说话”类型中最典型的一种。那什么是“银字”呢?白居易《南园试小乐》诗有“高调管色吹银字”[9]1821一句,同时《新唐书·礼乐志》载:“银字之名,中管之格,皆前代应律之器也。”[10]474又清人沈雄《古今词话》曰:“银字,制笙以银作字,饰其音节。”[11]858可见,“银字”是一种笙类乐器,其主要功能是用来应和主旋律,故此乐器所奏出的音乐应当是极具韵律感的。而以“银字”标饰音节,也使得此乐器更加易学并具可操作性。《新唐书·礼乐志》把银字与琵琶、五弦、箜篌、筝及杖鼓、腰鼓、大鼓还有拍板、方响等乐器都归为俗部乐器。[10]474或许与这些乐器相比,“银字”无论是在演奏效果还是操作难度上更能满足说话人的需要,因此才被作为“说话”表演时的主配乐器被使用。
虽然不是所有的“说话”都会有配乐,但“银字”已成为了它的一个身份标签,并成为了它的别名,以此来强调“唱”的部分在“说话”中的重要地位。通过阅读文本可以发现,宋代相同题材的小说在情节上大都千篇一律,因此很多小说应该是无法以情节取胜的,但它依然能够流行于众艺荟萃的勾栏瓦舍,受到大众的喜爱和欢迎。究其原因,应该正是因为这些“唱”的元素的添加,调动了听众的情绪,从而使得乏味的剧情也表现出了高潮迭起的艺术效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唱”反而成为了“说话”艺术的灵魂与核心所在。
小说是“说话”伎艺由口头向案头转化的结果,因此取决于“说话”伎艺的讲唱方式和诗词文本的特点,话本也沿袭“说话”也呈现出音乐化的趋向。一则体现在诗词文本自身的长短结合,韵律和谐,表现声律之美;二则在于诗词作为小说叙事之辅,在情节推进的进程中或描摹画景、或烘托气氛、或暗示情节、或设置悬念,从而使得小说在叙事节奏上或舒缓、或急峻,张弛有度,在表现出婉曲动人的美学趣味之余,更彰显故事结构安排上的层次感和节奏感,从而使得小说呈现出回环往复、舒缓峻切的音乐化趋向。“说话”的规则直接影响到了话本小说创作者的审美意识形态和创作心理机制,即坚持遣词造句和篇章布局要与说唱形式和配乐曲调相和的“说话”的创作规则,由此形成了宋代小说韵散相兼的结构和深富节奏感与层次感的音乐特色。
此外,话本小说的情节结构大多为“入话+中间诗词韵语+结尾诗”。说话中的故事讲到紧要处时,说话人便插入一些诗词,由说转唱,通过吟唱调剂听众的情绪,并在讲说结尾时用一首散场诗来总括点明主题。本用来唱的诗词被小说家用来推动故事情节、烘托渲染气氛和状物赋景,这些音乐元素以一种若有若无的飘渺质感笼罩在小说文本之上,时刻从视觉和听觉上击打着读者的阅读神经。总而言之,正是在小说由口头向案头的转化过程中,音乐唱腔随之转为文字形态的诗词呈现出来。
宋代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转折期,正如程毅中所说,这是“小说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阶段”[1]1。这一时期,各种雅俗艺术互相融合,在这种局面之下,小说出现了音乐化的趋向。这种趋向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宋代小说文本形态的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宋代小说文本大都表现出了明显的艺术上的疲软状态。这一时期小说的主要存在形式并不在案头而在口头,直到元代以杂剧为代表的戏剧艺术盛行之后,原来依附于“说话”艺术的小说才不得不另辟蹊径,将其表现形态寄托于文本,从而彻底完成了由口头向案头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