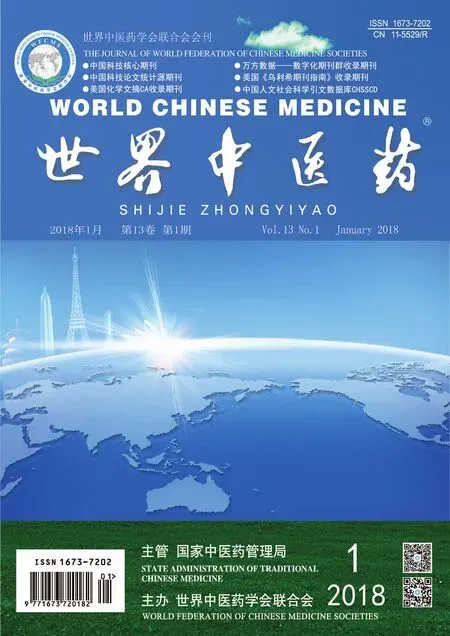痤疮的从湿热体质论治
2018-03-18李思琪俞若熙姜厚望
李思琪 俞若熙 姜厚望 王 琦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100029)
痤疮是一种常见的毛囊皮脂腺慢性炎性皮肤病,好发于颜面或胸背等皮脂腺分泌较多的部位。目前多认为的发病原因有雄性激素水平过高、皮脂腺分泌功能过于旺盛、毛囊导管角化过度以及局部的细菌感染等。其次,遗传、免疫、血液流变学等因素也被认为与痤疮发生有关[1]。临床上以粉刺、炎性丘疹、囊肿、结节等为主要表现,严重影响了容貌的美观,给患者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
目前西医治疗痤疮多采用内服维A酸类药物、抗真菌药、雌激素、雄激素拮抗剂、糖皮质激素等,外用过氧苯甲酰、抗生素、维A酸类等药物,以及光疗法等物理疗法[2]。虽然也发挥了一定的治疗效果,但存在诸多问题。国医大师王琦教授以体质学说为理论指导,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总结出了痤疮的发生与湿热体质有着密切的关系,认为湿热内蕴是痤疮发生的根本因素。现总结整理近年来从湿热体质角度来治疗痤疮的的理论及临床研究,以阐述从调理湿热体质来治疗痤疮的优势,为从湿热体质论治痤疮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1 流行病学调查
针对不同体质类型痤疮发病的情况,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痤疮患者的体质类型以湿热体质居多,从湿热体质论治痤疮,具有其优势。庄甄娜[3]调查300例痤疮患者,依照《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进行体质类型判定。结果显示湿热质(38.33%)为痤疮最常见体质类型,其次依次是阳虚质(18.00%)、阴虚质(12.33%)、平和质(10.00%)等。张景龙[4]对女性寻常性痤疮与患者体质类别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显示在300例痤疮患者中湿热质所占比例(28.30%)最大,其余依次为气郁质(14.97%)、痰湿质(13.57%)、阳虚质(11.35%)等。王静远[5]筛选出426例痤疮患者,平均年龄(25±5)岁,对体质分布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的体质类型以湿热质(22.5%)、痰湿质(17.8%)和瘀血质(16.9%)为主。赵亚等[6]对2 241名女性志愿者进行损美性疾病调查研究,在痤疮与体质关系调查中,发现随着痤疮程度的加重,湿热质所占比例明显增加,而平和质在未患痤疮人群中所占比例最高。刘亚南等[7]探讨寻常痤疮与中医体质的关系,调查了318例痤疮患者,其中体质类型分布的情况显示,湿热体质所占比例最大(23.54%),其后分别为阴虚质(14.14%)、痰湿质(13.50%)、阳虚质(13.32%)等。
2 现代医家从湿热论治痤疮的理论研究
多数医家采用辨证论治的方法来治疗痤疮,又因对痤疮发生的机制有不同的认识,所以通过辨证分型的方法来治疗痤疮,没有统一标准。现从湿热角度来探讨痤疮发病机制,以下为从湿热论治痤疮的一些常见分型。
2.1 脾胃湿热 杨国红认为,湿阻中焦,助湿化热,湿热互结,上蒸颜面而致发而为疮[8]。宋平认为,痤疮的内因是饮食不节,或嗜食辛辣,或大病久病之后伤脾[9]。脾运化失司,水湿内停,日久成痰,湿易郁而化热,湿热夹痰;或外感湿热之邪,内外之邪相互搏结,熏蒸肌肤而为痤疮。孙妍婧等[10]认为,阳明经脉与面部关系尤为密切,阳明血热郁滞,或湿热蕴结阳明气分,阻遏气血,形成痤疮。张毅认为,“痤疮之由,首责阳明”,阳明经循行于颜面部,而阳明多气多血,若经气循行不出,气郁化火[11]。又因患者多素体阳热偏盛、嗜食肥甘,使胃积热循经上蒸,蕴阻肌肤而发为痤疮。
2.2 肝胆湿热 钱秋海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发现痤疮不论实证还是虚实夹杂证,在发病过程中都存在着胆经湿热的表现,故只痤疮的治疗中清利肝胆湿热尤为重要[12]。王圣祥[13]认为,青年人年少气充,多肝火偏旺,青春期易发痤疮,女性以肝为先天,发病情况与多与月经有关,且痤疮患者多表现为情志不畅,与肝主情志联系密切,故病位在肝。痤疮的皮疹特点与湿热发病特征相符,且好发于足厥阴肝经循行的颜面,因此痤疮应从肝经湿热论治。王晖从肝论治痤疮,认为肝与痤疮的发生更为密切[14]。肝气郁滞、虚火上炎、湿热瘀郁是痤疮的主要病机,应以疏肝理气、清肝泻火、凉血化瘀、养血调气为主要治法。
2.3 肺热湿蕴 梁苹茂认为,痤疮的发生多由于肺经风热,湿热内蕴,从引起脾运化失司,湿浊内生,郁久生热滞于血络、肌肤,形成痤疮[15]。张发荣认为,痤疮的病位在心肺,病机以湿热蕴结上焦,兼感外邪为主,故以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加减治疗,内泻湿热,外散表邪[16]。李发枝重视体质辨证,认为痤疮病机以肺经血热和湿热蕴脾为主。临证常用清热达郁法、燥湿清热法[17]。
2.4 外感风邪,内蕴湿热 程益春认为,痤疮病在血分,主要由于血热以及感受风邪,湿邪留恋肌肤而引起。湿性重浊黏腻,使痤疮缠绵难愈,加之火热之邪,郁久化腐成毒。因此治疗痤疮应采取清热解毒,凉血燥湿之法[18]。刘景源认为,痤疮是由于内外合邪而引起。一般是由外感风热,内蕴痰湿,痰湿郁久则阻滞血行而成瘀,故引发痤疮[19]。
2.5 湿热毒瘀 马淑然认为,湿热毒瘀是痤疮的主要病因,以权衡“虚实夹杂、寒热错杂”的主次为辨证的关键[20]。将患病情况分为3期:初起以湿热为主;中期则为虚实夹杂;后期将以虚为主,常兼湿热毒瘀。刘友章治疗痤疮从湿热痰瘀入手,以分期辨证的方法施治[21]。将痤疮分为以湿热为主的发作期,以血热血瘀为主的恢复期,和肝郁脾虚为主的缓解期。分别以清热除湿,泻火解毒、凉血活血、疏肝健脾为重点来进行治疗。并始终遵循清热除湿,凉血活血之法。梁立经认为痤疮与湿热风毒痰瘀关系密切。脾胃运化失职,酿湿生热,上犯肺系,阻于肌肤,或青年阳盛,常伴有热象,热毒阻滞经络,生瘀生痰,袭于面部而成为痤疮。应以清热利湿,化痰除瘀,祛风解毒为治疗方法[22]。
2.6 湿热体质 王琦提出了“肤-体相关论”[23],认为不同的体质类型易患有不同的皮肤疾病。湿热体质者具有面垢油光,易生痤疮粉刺、口臭、酒糟鼻等特点,而痤疮的临床表现也符合湿热体质特征,认为湿热体质是痤疮发生的“土壤”,其发病机制与湿热体质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孝等[24]从“阳明主面”立论,认为湿热体质为痤疮发病的主要土壤。同时,根据“体质可调”“体病相关”理论,认为湿热郁伏阳明气血,是痤疮发病的的病机要点。傅杰英认为湿热体质者易发湿热蕴结型痤疮。湿热体质主要是由肝胆、脾胃功能的相对失调,肝胆、脾胃湿热蕴结,湿热之邪上蒸而成痤疮[25]。通过清利湿热、疏利肝胆、调理脾胃,调理湿热体质,从而治疗痤疮。
从以上理论研究可看出,湿热型痤疮的发病原因,或脾失运化又嗜食辛辣、肥甘,水湿内生,郁而化热;或外感风邪,内蕴湿热,久而成瘀;或因情志气郁化火,湿热相结,日久蕴结成毒。体现了湿热型痤疮以湿热体质为本,毒瘀痰结为标的特点[26]。更说明各种湿热症型痤疮演化的基础是湿热体质,痤疮的各种分型则与湿热体质具有从化关系。
3 湿热型痤疮的临床研究
近年来,随着对痤疮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医对于痤疮的治疗经验和手段越来越丰富。常用的内治法如内服中药、食疗等;外治法如中药面膜、中药熏洗疗法、针刺疗法、火针疗法、放血疗法、自血疗法、拔罐刮痧疗法,以及联合疗法等。以下为从湿热的角度对痤疮进行治疗的临床研究。
3.1 中药内服法
3.1.1 脾胃湿热 刘芳和宋业强[27]用经验方消毒饮治疗脾胃湿热型痤疮,该方有清热解毒,活血散结之效。选取60例门诊脾胃湿热型痤疮患者,观察组口服中药消毒饮(方药组成:金银花、蒲公英、丹参、牡丹皮、紫草等),愈显率为93.33%。对照组外用克林霉素磷酸脂凝胶,愈显率为36.67%。结果显示,中药消毒饮对脾胃湿热型痤疮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石荣贵[28]以自拟清热和胃降浊方来治疗胃肠湿热型痤疮,选取门诊胃肠湿热型痤疮患者,其中观察组31例口服清热和胃降浊方(药物组成:太子参、薏苡仁、茯苓、牡丹皮、丹参等),对照组19例口服罗红霉素以及维生素B6治疗。4周后观察治疗效果,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3.5%,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78.9%),说明自拟清热和胃降浊方对于胃肠湿热型痤疮具有良好的疗效。沈胡刚等[29]观察了清热解毒汤治疗肠胃湿热型痤疮的临床疗效。该研究选取肠胃湿热的痤疮患者,观察组56例,口服自拟清热解毒汤(药物组成:枇杷叶、黄芩、金银花、连翘、黄连等);对照组55例,口服罗红霉素。治疗8周后观察痤疮改善情况,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92.9%,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为78.2%)。结果显示,该方治疗肠胃湿热型痤疮疗效显着。
3.1.2 肝经湿热 魏晓燕[30]用清肝利湿法,治疗肝经湿热型痤疮,选取100例皮肤科门诊病例进行临床疗效观察。8周后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4%,优于口服盐酸米诺环素胶囊的对照组(总有效率为84%),且不良反应明显少于对照组。观察组方药组成为:龙胆草、栀子、黄芩、泽泻、车前子等。彭红华[31]用加味龙胆泻肝汤治疗由于肝火挟湿热上逆而引起痤疮,并观察其临床疗效。选取观察组58例,口服中药治疗,药物组成为龙胆草、山栀、木通、泽泻、车前子等;对照组36例采用西药治疗。20天后观察,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4.8%,对照组总有效率为80.6%。以上结果均显示,中药方剂内服治疗肝经湿热型痤疮的效果显著,明显优于单纯的西药治疗。
3.1.3 湿热蕴结 李强强等[32]以自拟白虎消痤汤加减来治疗湿热蕴结型痤疮,该研究纳入92例符合标准的痤疮患者,其中观察组47例,口服白虎消痤汤(药物组成为:生石膏、知母、薏苡仁、金银花、连翘等),随症加减;对照组45例,口服清热暗疮片。3周后观察临床疗效,观察组、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95.74%和71.11%。侯俊芝[33]采用自拟清热除湿解毒方(茵陈、山栀、黄芩、金银花、野菊花等)治疗湿热蕴结型痤疮。选取湿热型痤疮患者62例,口服自拟清热除湿解毒方治疗,4周后观察到治愈36例(58.1%),好转23例(37.1%),总有效率为95.2%,疗效显著。杨岚等[34]选取皮肤科门诊湿热型痤疮患者,观察清热除湿汤对湿热型痤疮的治疗效果。观察组32例,口服清热除湿汤(药物组成:龙胆草、车前草、生地黄、黄芩、白茅根等),该方由龙胆泻肝汤化裁而来,总有效率为90.63%;对照组16例,给予丹参酮胶囊治疗,总有效率为75%,疗程均为4周。结果显示,清热除湿汤治疗湿热型痤疮疗效良好。
3.1.4 湿热体质 王琦从湿热体质论治痤疮,认为湿热体质是痤疮发生的体质根源,所以把调体与清除湿热放在首位,临床用苇茎汤加味而成的消痤汤作为治疗湿热型痤疮的基础方,方药组成为芦根、冬瓜仁、薏苡仁、枇杷叶、桑白皮等。俞若熙等[35]采用病例系列研究方法,观察王琦教授应用该方治疗痤疮的临床疗效。对28例湿热体质痤疮患者进行疗效观察,结果显示总有效率为85.71%。并且后期随访,发现患者大部分预后良好。说明从湿热体质论治痤疮有其一定的优势。
3.2 其他治疗方法 王巧稚[36]用调神针法临床治疗湿热体质痤疮,通过膀胱经刮痧结合调神针法用来改善患者湿热体质。在其临床疗效的观察中,观察组总有效率89.66%,对照组总有效率75%。但是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体质的偏颇,并未完全将体质调整到平和状态,说明湿热体质的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欧俊男[37]通过体针配合刺络拔罐的方法治疗湿热蕴结型痤疮,体针主要穴位:曲池、合谷、三阴交、阴陵泉等,刺络拔罐选穴:膈俞穴、脾俞穴。观察组总有效率93.33%,疗效优于外用维A酸乳膏的对照组(总有效率76.67%)。王桂芳等[38]应用针刺结合中药(清热除湿汤)来治疗湿热蕴结型痤疮,观察组给予火针治疗、毫针针刺治疗、走罐结合中药口服加外敷治疗,总有效率为90.32%;对照组内服并外用西药治疗,总有效率为58.06%。结果显示该方法治疗湿热蕴结型痤疮的效果明显优于西药治疗。艾诗奇[39]应用背腧穴(心俞穴、胃俞穴、肝俞穴)刺络放血配合艾灸(合谷穴),来治疗肠胃湿热型痤疮,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87.5%。对照组外用克痤隐酮软膏,总有效率为54.4%。与单纯西药外用比较,该方法疗效显著,且无不良反应。有学者观察了刮痧配合放痧疗法,对于湿热蕴结型痤疮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刮痧放痧组的总有效率为90%,高于常规针刺把关治疗的对照组(总有效率63.33%),治疗效果良好。
4 讨论
湿热型痤疮是基于患者素来的湿热体质,受到体内外某些病因的影响,从而出现痤疮症状。因此病因去除后,可使痤疮的症状消失,但是往往由于没有改变患者的湿热体质,而出现痤疮反复发作的情况。临床上对于证的治疗比较容易,而调整体质的类型较为困难。湿热体质者对于湿热症候具有易感性,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导致痤疮极易复发。因此对于痤疮的治疗,应以患者平素体质为本,通过药物或对生活方式进行干预,调整偏颇体质状态,并以临床症状为标,根据伴随症状分析治疗。
痤疮这一疾病给患者的生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所以如何安全的治愈痤疮,成为了越来越多人所关心的话题。因痤疮这一疾病与湿热体质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应通过早期的体质辨别,找出痤疮的易发人群,从“治未病”角度进行干预,做到“未病先防”“已病防变”。通过调节湿热体质,可以从根源上达到治疗痤疮,防止复发的目的。因此,从湿热体质论治痤疮,为痤疮的治疗提供了新的诊疗思路,对痤疮患者生命质量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1]陈景华.美容保健技术[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118.
[2]肖宜敏.中西医治疗痤疮概况[J].内蒙古中医药,2016,35(1):145-147.
[3]庄甄娜.女性痤疮与中医体质类型及月经的相关性研究[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5.
[4]张景龙.300例女性寻常痤疮患者中医体质类型分析[J].中国合理用药探索,2017,14(4):1-4.
[5]王静远.痤疮患者的中医体质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D].杭州::浙江中医药大学,2015.
[6]赵亚,王济,方程,等.中国城市女性面部损美性因素与中医体质类型的相关性[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7):2368-2371.
[7]刘亚南,黄青,赵慧娟.318例寻常痤疮患者中医体质类型分析[J].中医杂志,2015,56(3):223-227.
[8]杨倩,杨国红.杨国红教授治疗痤疮的临床经验[J].光明中医,2015,30(6):1169-1171.
[9]郭真如,宋平.宋平运用温胆汤加减治疗脾胃湿热型痤疮[J].现代中医药,2016,36(5):71-72.
[10]孙妍婧,李祥林,杨岩.浅论寻常型痤疮与阳明经络的关系[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连续型电子期刊),2015,15(91):120,122.
[11]聂巧峰,张毅,黄时燕.张毅老师清泄阳明法治疗痤疮经验体会[J].内蒙古中医药,2014,33(36):33.
[12]曲芊芊,杨文军.钱秋海教授从肝胆湿热论治痤疮的经验[J].光明中医,2016,31(7):935-937.
[13]王圣祥.浅析痤疮从肝经湿热论治[J].中医临床研究,2014,6(35):84-85.
[14]金汀龙,陈霞波.王晖从肝论治痤疮经验[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39(1):30-31.
[15]李舒彬.梁苹茂疏散风热-清热祛湿法辨治痤疮[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5,29(6):12-13.
[16]黎慧英,张晓冉,董阳,等.张发荣运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疗痤疮经验[J].湖南中医杂志,2016,32(9):44-84.
[17]吕翠田,刘金涛.李发枝教授治疗痤疮经验[J].中医学报,2016,31(9):1312-1314.
[18]夏京,赵泉霖.程益春教授运用清热解毒法治疗痤疮的经验[J].光明中医,2016,31(1):30-31.
[19]王琦,刘宁,郑丰杰.刘景源教授治疗皮肤瘙痒与痤疮临床经验[J].现代中医临床,2016,23(2):31-32.
[20]牛晓雨,马淑然.马淑然论治痤疮经验[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11):3953-3955.
[21]曹彬,王超,邱俊.刘友章治疗痤疮经验[J].河南中医,2014,34(9):1669.
[22]张芸,颜洁.梁立经主任治疗痤疮经验[J].医药前沿,2015,5(17):334-335.
[23]王济,张惠敏,李玲孺,等.王琦教授“肤-体相关论”的提出及其在皮肤病诊疗中的应用[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36(7):476-479.
[24]英孝,倪诚,董伟,等.从“阳明主面”论治湿热体质痤疮的学术传承[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29(12):3692-3694.
[25]吴惠华,傅杰英.傅杰英教授调理湿热质治疗痤疮的临床经验介绍[C].珠海:国际数字医学会数字中医药分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数字中医药学术交流会,2016.
[26]俞若熙,倪诚,王琦.王琦教授从湿热体质论治痤疮的理论探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2,27(4):878-881.
[27]刘芳,宋业强.中药消毒饮治疗寻常痤疮30例[J].光明中医,2016,31(4):530-531.
[28]石荣贵.清热和胃降浊方治疗寻常痤疮31例观察[J].实用中医药杂志,2015,31(9):811-812.
[29]沈胡刚,金丽燕,陆明明,等.清热解毒汤治疗肠胃湿热型痤疮疗效观察[J].中国美容医学,2014,23(3):239-241.
[30]魏晓燕.清肝利湿法治疗肝经湿热型痤疮的临床观察[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2.
[31]彭红华.龙胆泻肝汤治疗寻常痤疮58例[J].广西中医学院学报,2001,18(1):41-42.
[32]李强强,赵统秀,张晓国,等.白虎消痤汤加减治疗湿热蕴结型痤疮47例[J].西部中医药,2014,27(6):91-92.
[33]侯俊芝.自拟清热除湿解毒方治疗湿热蕴结型痤疮62例疗效观察[J].医学美学美容(中旬刊),2015,24(4):157.
[34]杨岚,李元文,曲剑华.清热除湿汤治疗湿热型痤疮的临床观察[J].实用皮肤病学杂志,2016,9(1):56-58.
[35]俞若熙,王琦,倪诚,等.从湿热体质论治痤疮的临床疗效观察[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2,27(12):3240-3242.
[36]王巧稚.调神针法在针灸治疗湿热体质痤疮中的临床疗效观察[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6.
[37]欧俊男.体针配合刺络拔罐治疗湿热蕴结型痤疮的临床研究[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5.
[38]王桂芳,张春燕,崔海.针刺结合中药治疗湿热蕴结型痤疮31例疗效观察[J].北京中医药,2015,34(8):659-661.
[39]艾诗奇.背腧穴刺络放血配合艾灸治疗肠胃湿热型痤疮患者的疗效观察[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连续型电子期刊),2015,15(76):78.